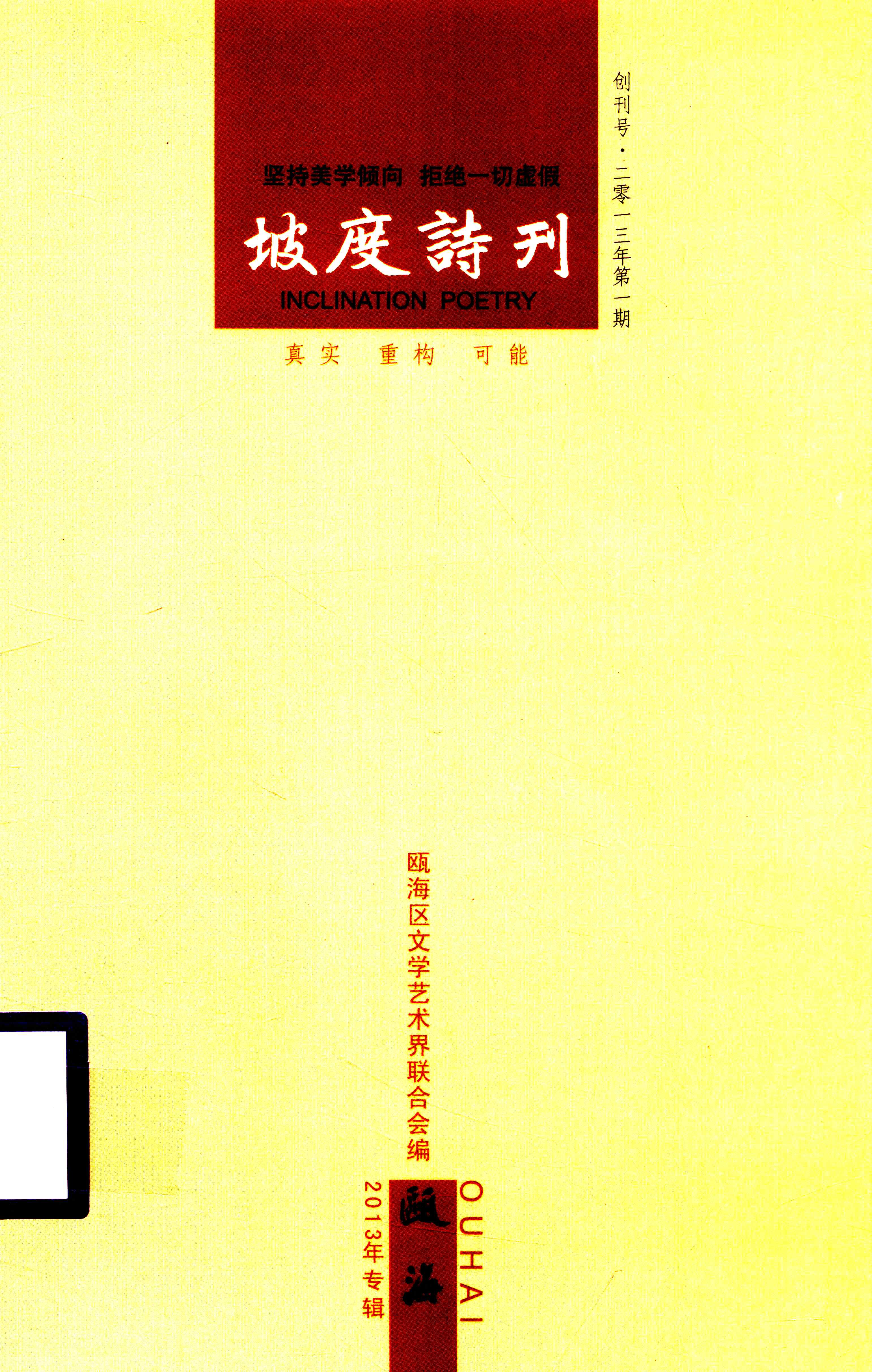内容
我介入温州文坛时间较晚,之前对温州本土的作家诗人所知甚少,
而诗人高崎则是我“所知甚少”者中很早就知道的一位。
我所知道的作为诗人身份的高崎大概来自某本偶然看到的刊物,从后来能搜索到的一些信息中得知,他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生于浙江最南端的苍南县,上世纪六十年代从国内某名牌大学毕业后,曾一度在温州市区某单位上班,后不知何种原因又返回老家苍南某山村隐居,于是就有了“自觉深入大自然腹地长达十八年”的人生体验。我想,这十八时间应是高崎致力于文学探索与写作的黄金年代,也是高崎耐住了寂寞和诱惑的卓绝岁月。在这十八年中,高崎除了发表大量的诗歌散文作品外,还写出了生命中最早的诗集《复眼》,此后又陆续出版了《顶点》《征服》《声音中的黄金》《洗礼以来》《圣迹》《手握两个世纪》等一大批文学著作,从而奠定了其“领跑中国现代诗的第一集团内”(王燕生语)的地位。
与高崎开始有文字上的交流大概在2009年,当时我创办主编的民间诗歌刊物《有巢》向他发出约稿函后,得到了他热情的回应,一位成名多年大诗人的信任让我的办刊之举深受鼓舞。而我们第一次近距离相见则是2010年初在浙江平阳举行的第十一届温州文学周上,初见印象的高崎个子瘦小,戴着一顶爵士帽,清癯儒雅,显得精神抖擞,略带闽南口音的普通话简洁有力,不时有警世之语。而他最让我记忆犹新的则是那双深凹进去的眼睛,那里面似乎拥有洞察一切的能量。从高崎的眼睛里我无法解读出他诗歌的奥秘,却能看到一份孤独着的自信,这或是一位饱经岁月濯洗诗人最可贵的品质。
平阳文学周之后,稔熟起来的高崎和我的交往更加频繁,我们除了在一些文学聚会上常常碰见外,每在节假日还能发发短信,相互致意,同时还在博客上互动不断。对于我新发的博文,他会第一时间跟帖点评,或褒或贬,往往一语中的,让我受益匪浅,当然我也常去他的博客学习,老一辈作家的严谨和谦逊给我的创作启发良多。高崎由于身体原因(听说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参加一些文学活动聚会有些困难,他每每看到我在博客上晒出活动照片后,就会打电话过来询问活动细节,有时候电话一打就是半个小时,从中我能感受到他对温州本土文学的热情和关切。作为文学晚辈,高崎对我的关注和帮助也是用心的,当他得知我的一次作品研讨会反响平平后,主动打来电话安慰,并认真阅读我的诗歌作品,梳理出一些他所看好的,然后发到自己的博客上予以推荐,给我以莫大的鼓励,让我储备了更多在文学道路上继续写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有一天高崎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自己研宄了很长时间,发现我的诗歌气质和美国著名诗人兼摇滚歌手鲍勃•迪伦接近,还专门找来几首鲍勃•迪伦的诗供我参考。且不论我的诗歌与鲍勃•迪伦有几分相似,高崎如此不遗余力地提携诗坛后进,着实让我感动。当然这些事例不仅仅限于我,在温州这片诗歌土地上可以说俯拾皆是。
高崎的诗歌除了意象诡丽、想象奇特外,对西方文本的介入较深,充盈着与他这个年龄不相称的颠覆力量。著名诗人西川说他“追求语言的绝对价值”;著名诗歌评论家沈泽宜将他与超现实主义诗人法国的艾吕雅、阿拉贡比照,还将他的语言与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美国诗人阿什贝利的“火焰意象学”相“触摸”,体现一种真正的大气;著名作家东君说,“高崎在中国老一辈诗人中算是一个异数”。在我看来,这些评价是恰如其分的,高崎对诗歌所具有的敏锐嗅觉总是让我这个文学晚辈因难以企及而心生“妒忌”。记得我一首诗中有一句“孤独将我惊醒”,高崎在博客上看到后特地给我打来电话,指出这句诗比较俗套,建议改成“我与孤独一起惊醒”。经他这样一改,一首诗的意境不知拔高了多少倍,换句话说,将腐朽化作了神奇,这是我需要毕生学习感悟的本领。
今年6月30日晚23时许,在温州的青年诗人泥人给我打来电话,说高崎猝然离世,具体时间不详。这是一个让人措手不及的消息,如同夏日的一记闷雷,重重击打在我的胸口。等一阵惊悸稍稍平息后,我急急向同是苍南籍的诗人孟想去电话证实。当然,如此兹事体大的“传言”终宄会被无情的电话铃声证实,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在得知确切消息的同时,我找出高崎去年寄给我的两本书和一封信。两本书中,一本是诗集《顶点》,另一本是评论集《分量:深的声音》,信是用圆珠笔写成的,内容谈及两本书的写作背景,以及授权我可在《顶点》中选发诗歌作品到《有巢》等等,字迹干净挺拔,一如他清癯的外形气质,这是我在这个夏夜里看得最缓慢也最沉重的手写文字。趁着夜色,我拟定两幅挽联送给高崎,一幅以乐清市现代汉诗学会的名义:深入自然十八年,黄金分量;纵横诗国三千里,顶点声音。另一幅以我个人的名义:诗路高崎凭大任;文山绝处赖先生。挽联借用了高崎一些己正式出版书籍的名称,固然不能概括高崎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卓然成就,但也寄托了我对他的追念。两天后,即7月2日下午,我与张艺宝、郑亚洪等一行三人赶往浙江最南端的苍南县城,只为见诗人高崎最后一面。
在苍南县城灵溪镇建兴东路258号的高崎生前寓所,诗人静静地躺在冰棺里,身体被一条红色的绸被覆盖着,看不到他的脸,无人知道他的下一首诗要写什么,也无人知道他最后一首诗所采用的意象,就像无人知道他离世时的情形,只有冰棺后的巨幅遗像用一贯深凹进去的眼睛看着每一个前来吊唁的人。作为诗人身份的高崎的灵堂布置样式与寻常去世者并无区别,房间里飘荡着嗡嗡的佛号声,一对红蜡烛几乎流干,孱弱的烛光扑闪不定,一双他生前穿过的黑皮鞋摆放在冰棺前的水泥地上,随时准备送他“上路”。当我们一行离开苍南时,天空突然呈现出一片久违的蓝,让人窒息的蓝。从蓝的深处,一轮红日正沿着静默的山脊回家。
2013年7月3日下午
而诗人高崎则是我“所知甚少”者中很早就知道的一位。
我所知道的作为诗人身份的高崎大概来自某本偶然看到的刊物,从后来能搜索到的一些信息中得知,他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生于浙江最南端的苍南县,上世纪六十年代从国内某名牌大学毕业后,曾一度在温州市区某单位上班,后不知何种原因又返回老家苍南某山村隐居,于是就有了“自觉深入大自然腹地长达十八年”的人生体验。我想,这十八时间应是高崎致力于文学探索与写作的黄金年代,也是高崎耐住了寂寞和诱惑的卓绝岁月。在这十八年中,高崎除了发表大量的诗歌散文作品外,还写出了生命中最早的诗集《复眼》,此后又陆续出版了《顶点》《征服》《声音中的黄金》《洗礼以来》《圣迹》《手握两个世纪》等一大批文学著作,从而奠定了其“领跑中国现代诗的第一集团内”(王燕生语)的地位。
与高崎开始有文字上的交流大概在2009年,当时我创办主编的民间诗歌刊物《有巢》向他发出约稿函后,得到了他热情的回应,一位成名多年大诗人的信任让我的办刊之举深受鼓舞。而我们第一次近距离相见则是2010年初在浙江平阳举行的第十一届温州文学周上,初见印象的高崎个子瘦小,戴着一顶爵士帽,清癯儒雅,显得精神抖擞,略带闽南口音的普通话简洁有力,不时有警世之语。而他最让我记忆犹新的则是那双深凹进去的眼睛,那里面似乎拥有洞察一切的能量。从高崎的眼睛里我无法解读出他诗歌的奥秘,却能看到一份孤独着的自信,这或是一位饱经岁月濯洗诗人最可贵的品质。
平阳文学周之后,稔熟起来的高崎和我的交往更加频繁,我们除了在一些文学聚会上常常碰见外,每在节假日还能发发短信,相互致意,同时还在博客上互动不断。对于我新发的博文,他会第一时间跟帖点评,或褒或贬,往往一语中的,让我受益匪浅,当然我也常去他的博客学习,老一辈作家的严谨和谦逊给我的创作启发良多。高崎由于身体原因(听说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参加一些文学活动聚会有些困难,他每每看到我在博客上晒出活动照片后,就会打电话过来询问活动细节,有时候电话一打就是半个小时,从中我能感受到他对温州本土文学的热情和关切。作为文学晚辈,高崎对我的关注和帮助也是用心的,当他得知我的一次作品研讨会反响平平后,主动打来电话安慰,并认真阅读我的诗歌作品,梳理出一些他所看好的,然后发到自己的博客上予以推荐,给我以莫大的鼓励,让我储备了更多在文学道路上继续写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有一天高崎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自己研宄了很长时间,发现我的诗歌气质和美国著名诗人兼摇滚歌手鲍勃•迪伦接近,还专门找来几首鲍勃•迪伦的诗供我参考。且不论我的诗歌与鲍勃•迪伦有几分相似,高崎如此不遗余力地提携诗坛后进,着实让我感动。当然这些事例不仅仅限于我,在温州这片诗歌土地上可以说俯拾皆是。
高崎的诗歌除了意象诡丽、想象奇特外,对西方文本的介入较深,充盈着与他这个年龄不相称的颠覆力量。著名诗人西川说他“追求语言的绝对价值”;著名诗歌评论家沈泽宜将他与超现实主义诗人法国的艾吕雅、阿拉贡比照,还将他的语言与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美国诗人阿什贝利的“火焰意象学”相“触摸”,体现一种真正的大气;著名作家东君说,“高崎在中国老一辈诗人中算是一个异数”。在我看来,这些评价是恰如其分的,高崎对诗歌所具有的敏锐嗅觉总是让我这个文学晚辈因难以企及而心生“妒忌”。记得我一首诗中有一句“孤独将我惊醒”,高崎在博客上看到后特地给我打来电话,指出这句诗比较俗套,建议改成“我与孤独一起惊醒”。经他这样一改,一首诗的意境不知拔高了多少倍,换句话说,将腐朽化作了神奇,这是我需要毕生学习感悟的本领。
今年6月30日晚23时许,在温州的青年诗人泥人给我打来电话,说高崎猝然离世,具体时间不详。这是一个让人措手不及的消息,如同夏日的一记闷雷,重重击打在我的胸口。等一阵惊悸稍稍平息后,我急急向同是苍南籍的诗人孟想去电话证实。当然,如此兹事体大的“传言”终宄会被无情的电话铃声证实,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在得知确切消息的同时,我找出高崎去年寄给我的两本书和一封信。两本书中,一本是诗集《顶点》,另一本是评论集《分量:深的声音》,信是用圆珠笔写成的,内容谈及两本书的写作背景,以及授权我可在《顶点》中选发诗歌作品到《有巢》等等,字迹干净挺拔,一如他清癯的外形气质,这是我在这个夏夜里看得最缓慢也最沉重的手写文字。趁着夜色,我拟定两幅挽联送给高崎,一幅以乐清市现代汉诗学会的名义:深入自然十八年,黄金分量;纵横诗国三千里,顶点声音。另一幅以我个人的名义:诗路高崎凭大任;文山绝处赖先生。挽联借用了高崎一些己正式出版书籍的名称,固然不能概括高崎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卓然成就,但也寄托了我对他的追念。两天后,即7月2日下午,我与张艺宝、郑亚洪等一行三人赶往浙江最南端的苍南县城,只为见诗人高崎最后一面。
在苍南县城灵溪镇建兴东路258号的高崎生前寓所,诗人静静地躺在冰棺里,身体被一条红色的绸被覆盖着,看不到他的脸,无人知道他的下一首诗要写什么,也无人知道他最后一首诗所采用的意象,就像无人知道他离世时的情形,只有冰棺后的巨幅遗像用一贯深凹进去的眼睛看着每一个前来吊唁的人。作为诗人身份的高崎的灵堂布置样式与寻常去世者并无区别,房间里飘荡着嗡嗡的佛号声,一对红蜡烛几乎流干,孱弱的烛光扑闪不定,一双他生前穿过的黑皮鞋摆放在冰棺前的水泥地上,随时准备送他“上路”。当我们一行离开苍南时,天空突然呈现出一片久违的蓝,让人窒息的蓝。从蓝的深处,一轮红日正沿着静默的山脊回家。
2013年7月3日下午
相关人物
陈鱼观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