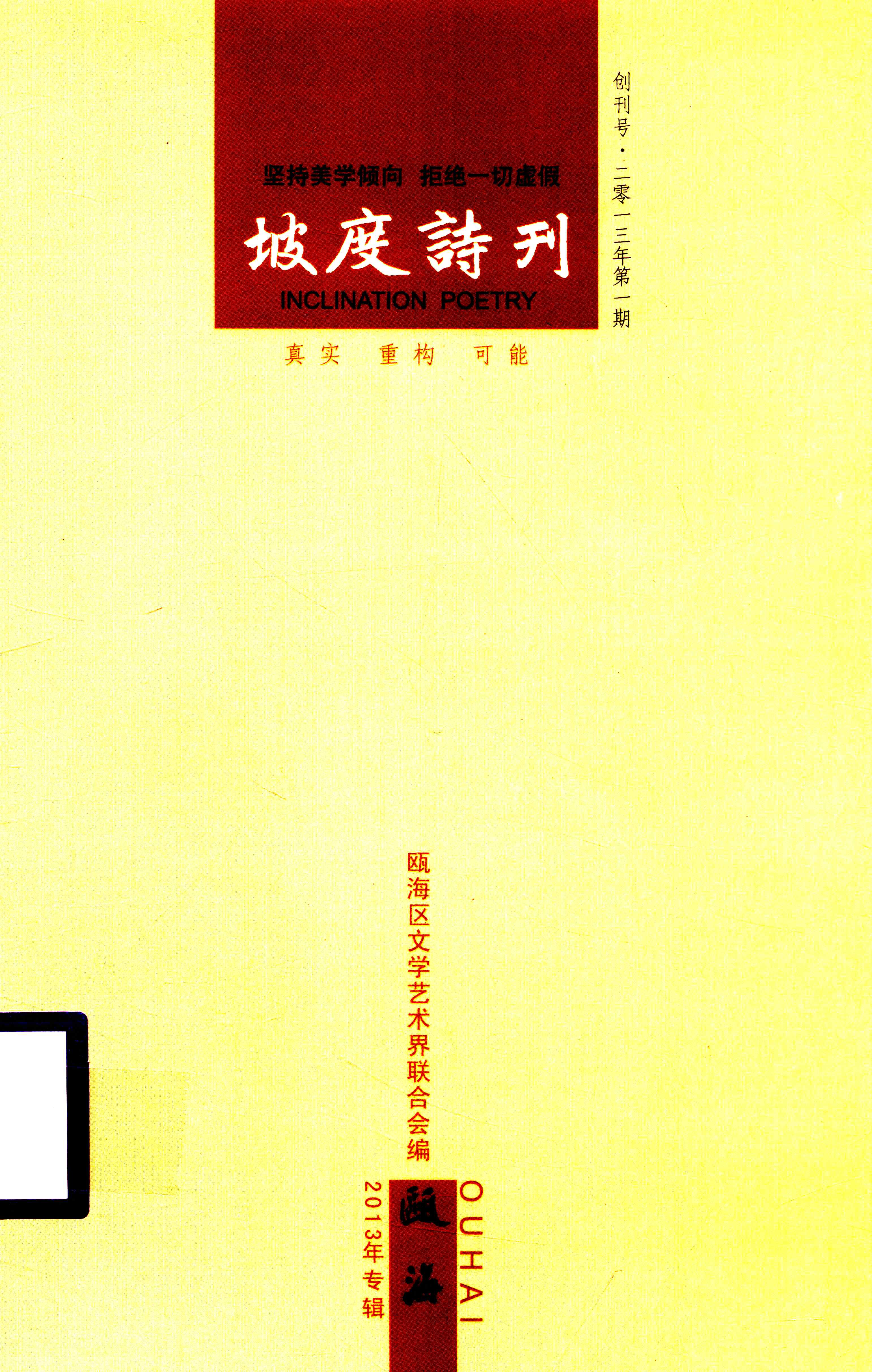内容
今年7月4日,代表坡度诗社
参加高崎老师的追悼会之后
就想着《坡度诗刊》要为他做个专题以表纪念
高崎老师的走是一个诗歌事件
不仅是温州的也是中国诗歌的
不只是他的,也是所有诗人的事件
同时他是我们所共同尊重的诗人
他高傲的骨骼,崎硕的语言和孤独的品质
是他作品和为人的一面独有的旗帜
对于他,除了瞻仰,我能说的就是
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活着,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深深缅怀
一一坡度诗社 泥人
纪念
温州诗人 高崎 纪念专题2011年5月,高崎在永嘉丽水街
马叙 摄
高崎(1945〜2013),原名高其士。祖籍福建,生于浙江温州。196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中国现代诗歌实验主义代表诗人。
历任浙大诗社社长,温州师院诗社顾问,温州市作协理事,苍南县文协常务副主席。200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作品见于《诗刊》、《中国作家》、《诗选刊》、《星星》、《江南》、《诗歌月刊》、《中国新诗刊》、匈牙利出版的《华人诗人作品选》等国内外书刊;作品入选《中国新诗年鉴》、《中国最佳抒情诗》、《一行诗人诗选》、《〈中国作家〉获奖作品选》、《2008年中国年度散文诗》、《2011年中国诗歌精选》等多种选本。
出版有文学专著《复眼》、《圣迹》、《顶点》、《征服》、《洗礼以来》、《手握两个世纪》《声音中的黄金》《分量:深的声音》等8部,主编《浙大诗选》(合编)等2部。
获文化部主办的全国诗歌赛大奖、浙江优秀文学作品奖、《中国作家》一等奖等奖项,并获2008年度和谐中国•优秀作品金奖。2011年与西川、欧阳江河、商震一齐入选诗刊社第二届青春回眸诗会。
当代文学界对高崎写作的评价是:“高崎始终置身于领跑中国现代诗的第一集团内”(王燕生);“在他那天才式的联翩的浮想中感到了诗意追逐的快乐,倾泻着令我们感到陌生的美丽。”(谢冕);“高崎追求语言的绝对价值”(西川);“他的诗,指向一种‘存在之诗’”(王家新);“许多学者与诗人以艾吕雅、阿拉贡等法国诗人比照高崎,而我们却从高崎诗中一种先锋派绘画式的语句中触摸到了美国诗人阿什贝里的‘火焰意象学';高崎的诗正在体现一种真正的大气。他的书引起阅读震撼”(沈泽宜)。高崎 作品选
昆虫记
我们已经被最细的昆虫打败
我们是狙击手,是船长,是灵与肉蜿蜒的道路
我们无理由从骄傲长出了胡子
昆虫的生命类似它的金色足迹
以无声的脚印走过无声的道路
它们高抬着鼻头,办完婚事,吃草,吃大米和流年之劫
它们恩爱交加,如同暴风雨合力浇顶
仿佛是辛辛那提最大幸福的一个投影
它们的母亲同样怕事,嗫嚅,同样气冲斗牛
每一条瓦槽也都是它们苦苦修缮的隐秘
没有一个王递给它们一枚硬币
重访渔寮
那些沙,沙地,不,是沙滩的
耳语,战胜,尔虞我诈或者三者存在于
一个海岸纷纷的意外里。耳语,战胜,尔虞我诈或者三者存在于
一个海岸纷纷的意外里。
质感。沙!一一哦,这个海边的
沙,类似那支俄罗斯圆舞曲过门的
平滑;细,也似天鹅湖飞禽
——上升到半空化为乌有的那朵轻敌的
柔意。
那些昆虫们轻车熟路地吐露着雨夜丝光。不,风光。
丝绸及其放肆的梦。或者是百分之百的暴雨
洗浴之后的清新,带来行走的袅娜质感。
一米,不,不到一米之外,是水,是海的水
细沙:将海岸情感之波晕化为金黄,不,
是另一种黄一一它低于黄土,不,高于龙袍。
它吞吐着细小的洞穴朝代,
细小的鬼话,小拳蟹的春宵
喜怒无常。小小火焰的神经质。它们都在
沙滩之下快活如仙,目无黑暗。
沙滩,还将它既定的海
深藏。一次潮,是漂亮内心里
自己神的顶点。胆大,
无忌。它像更合适的嘴巴
向海,一泻金黄色的燕颌儿
无数支手伸出去——小小的手掌,
沙粒的手掌,到底握住了
一个分量。像降B琴键一样固定。
一万年,整个大海无法
将一个轻浮的沙地移走。朋友,
这就是逻辑:不以善与恶作为定论。江心屿
走上江心屿
记忆立刻潮落潮起
林木依然澎湃着
乔木寻找早年的落叶
也要掘地千尺了
古寺板着脸聆听潮音
不一定与过去奔腾的吼声合拍
越过那座半圆拱桥的顶点
我是第十二次登临此地
信物依然绿着
找不到当年云的尸体
情话也己经面目俱非了
我当年就不是白鸥
而今己有白鸥的身份
飞翔时与春景相遇
我己不再是蒙面大盗了
心绪无暇可击
只想着妻儿在涛声以外
不要失散水
水蹚过周庄
水划过一条条铁轨与航道
水漫过远方的我的纸质呵
水,一贯的水:它的色相
它的烟影
它的矛盾
它的全部商贾,它的心,它的羞涩与邪念
它的枣状的甜蜜
它的幽灵与晶亮的桨声
它的喧嚷,它的骚动
它的招牌一如千里舟楫它的船只所载过的怀旧的
眷恋,异客的盲从,数不清的
质疑与拥趸
让袅娜的周庄置于无辜的淹没……
水,滑过低矮的周庄
粼粼的水刺激过的周庄
今天,用我的诗滋润过
将成为近代中国巨大的隐秘之一
重新
——余杭二白潭印象
重新翻晒别人吊诡的谓语
才吐出自己的诗句并非云烟重新奔走在别人的最前面
才发觉自己击桨的同样干练
重新想起水负驮的力量
其中有一股是来自辽阔的担当
院落黄昏
在海角的海角之内,
黄昏之外还有庞大的黄昏。
黄昏的另类意义是,
黎家不会将黄昏当作黄昏。
狗将嘴悄悄靠在后腿旁边,
安谧是不成问题的。
借着白昼的最后之光,
少女温柔的劳累显然大于时间。
树干多么粗大,果实硕壮,
它们腹内安置着一座座心仪的海洋。
时光许多,绿也太奢侈了,
少女还舍不得一线光阴,丢入绿荫里。
只有这时候干活才舒展呐,
纺出的棉线不计长度。
只有这时候干活才适合耳语,
谈些心跳的,或是不怕狗偷听的事儿。
这样,允许世界可以黑下来,
为了抒情的核心目的,姐妹们不理睬什么风暴!中国东部,有个诗人叫高崎
□马叙
打开高崎的博客,《分量:深的声音》,博客依旧,只是再也无人来更新了。高崎离开我们已经近五个月。高崎的诗,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不以他的离开而被忘记,在我,反而更深地记起他的诗。前些年,他一直叫我给他写篇诗评,但是我一直未动笔,我说,我还没有完全把握你的诗,等我基本把握了,再来写。却不知,一直到他走了,我还未写出诗评来。那一天,当我删除手机里高崎的号码时,突然感到无限的悲伤。
他刚走的那些日子,我曾与友人说起高崎,我说,高崎于当代诗歌是一个有意义的存在,只是太被忽略了。即使他的突然离去,也没有引起中国诗评界应有的关注。中国诗界,只是一个诗歌活动界,人们记住的只是那些诗歌活动家。
我喜欢高崎的诗。他的诗是拮牙的,他是有意识地在诗中设置了一道道的障碍,阻止当代读者在阅读中追求流畅阅读的坏习惯。他甚至在一个句子中把词语分开来,填入陌生意象,在词语中设置矛盾,设置悖论,迫使读者停顿下来,咀嚼意象与词语。与此同时,他借此打开词语与意象的天空,让互不相涉的意象翻滚而出,渲染诗的空间。我以为,高崎的这种写作,与高崎的内心世界密切相关。高崎在现实中可以说是世俗的,但是他又是一个内心高傲的诗人,因为写出了杰出的诗篇而不为人知,就有了一种迫切感,这迫切感是自己己经年近七十,但是作为一个与生俱来的天才式的诗人,为了不让这个庸俗的世界埋没了优秀的自己,用世俗的方式呈示自己,我以为,于高崎而言,一点都没有错,
因为他太孤独了,因为少有人能理解他与他的内心。也正因为此,高崎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痛苦的存在。有段时间,大约2009年,他曾给我打过几次电话,述说自己的诗的写作,嘱咐我写诗评。2011年,《诗刊》在永嘉开“青春回眸”诗会,在丽水街,我拍了高崎在午后强烈阳光下一张喝饮料的照片,他的深陷的眼窝,削瘦的双颊,因吸进液体饮料而深深凹陷进去,专注而忧伤一一在卡夫卡的头像照片中,我看到过这种状态。后来我在整理照片时,看到这一张,我想,这就是高崎,这个喝饮料的高崎与写诗的高崎是一致的。他的内心的是孤独的,痛苦的,同时又是忧伤的。这孤独、痛苦、忧伤,在这一刻被集中呈示了出来。他有首短诗,《南方》一一
没有冬天的地方,珍视暴雪的到来
我每次把一些亲切的雪米
埋伏到第二年的夏天
做着刻骨的梦幻,在炎热如歌的故乡
知道吗,亲爱的,我瞻仰上帝的容量,也瞻仰雪
瞻仰
被公牛粗暴吃过的
花草,及其精神,及其粪土。也瞻仰
灾难:一如用光,去堵住
银河的种种伤口
这是一首有着刻骨孤独品质的诗,如此自我,孤独,高傲,有若在远远的河岸上漫步,流水与世界与时间与生命构成了一个金属般的处所,然后把自我安置其中,享用这近乎残酷的孤独。“我每次把一些亲切的雪米/埋伏到第二年的夏天/做着刻骨的梦幻,在炎热如歌的故乡/知道吗,亲爱的,我瞻仰上帝的容量,也瞻仰雪”,这个高崎就是那个午后强烈阳光下喝饮料的高崎,他埋藏着一些词语,连同自己一同埋藏起来,在词语深处做着孤独的交易。这里有着他对世界的期望,但是这种期望却越来越加深着他的绝望:“瞻仰/被公牛粗暴吃过/花草,及其精神,及其粪土。也瞻仰/灾难:一如用光,去堵住/银河的种种伤口”。这是最典型的高崎语言风格,一如他所说的“刻骨的梦幻”,他的诗的语言也是刻骨的,他用尖刀般的词语,从事物的旁边(不那么直接地)划开口子,使得诗中的情绪突然地流露出来,用以加深这个绝望的世界。
他的另一首诗:《黄鹤楼》一一
一只鸟来过此处,喘气,筑草,交颈,飞走
有闲的人为它泡制了大楼。
我也来过此处,观望,抽烟,恐高,消逝
谁也没给他另一座建筑物。理由简单:你的宗教有“神”,你不是异物。
白云,神的爪牙,洋洋得意,仍然煽动。
另一个人只捞到空空的臆想,或破旧之光,
此楼,一个钟座。虚与实的曱状腺。
回忆事件是它的最正确刻度。
我满头大汗。体内的自恋也有流淌。
也埋伏了“想”许多,高度都无法干涉。
其中最大的念头是:
流浪太久了,大江两端
都没有底部,鹤唳仿佛错觉。
当人置于风景之中,完全是从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幽暗的存在,风景与我何干?它唯有加深着人的孤傲,一个黄鹤楼,是一个彻底的错觉,只有词语介入时,它才开始波动起来,而这个语词的创造者诗人高崎本身,也是一个错觉,是这个世界的错觉。这个世界存在过一个叫高崎的诗人么?这个叫高崎的诗人他写过黄鹤楼么?这黄鹤楼却又是一个与这个叫高崎的诗人毫无相关的所在。但是,高崎来了,语词来了,“我也来过此处,观望,抽烟,恐高,消逝/谁也没给他另一座建筑物。”他在此处看到了虚无,他完全游离了风景,他所到之处是另一座建筑物,但是这建筑物却是不存在的(“谁也没给他另一座建筑物”)!与前一首《南方》一样,高崎的这种孤独是具有金属质地的,被他自己所创造的词语所击,发出痛苦而铿锵的声音。
我平时读得比较多的是高崎的短诗。高崎还写了《顶点》《洗礼以来》等长诗。他的长诗气象万千,词语坚硬、奇异,有如石砌台阶,于一步步艰难的上升中,感受着意象的旋转与冲击。得空我还要再次认真地静下心来读高崎的长诗,感受长诗中的高崎与短诗中的高崎的区别。
这个短文,只写到高崎的极少部分,期待更有份量系统论述高崎的新的文章的出现。
高崎,于当代诗坛而言,是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诗人,他应该获得更高的评价与荣誉,应该为更多的人知道与崇敬。
以后,当我遇见外地的诗人朋友,我会说,你知道么,中国东部,有个诗人叫高崎!送别高崎
□陈鱼观
我介入温州文坛时间较晚,之前对温州本土的作家诗人所知甚少,
而诗人高崎则是我“所知甚少”者中很早就知道的一位。
我所知道的作为诗人身份的高崎大概来自某本偶然看到的刊物,从后来能搜索到的一些信息中得知,他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生于浙江最南端的苍南县,上世纪六十年代从国内某名牌大学毕业后,曾一度在温州市区某单位上班,后不知何种原因又返回老家苍南某山村隐居,于是就有了“自觉深入大自然腹地长达十八年”的人生体验。我想,这十八时间应是高崎致力于文学探索与写作的黄金年代,也是高崎耐住了寂寞和诱惑的卓绝岁月。在这十八年中,高崎除了发表大量的诗歌散文作品外,还写出了生命中最早的诗集《复眼》,此后又陆续出版了《顶点》《征服》《声音中的黄金》《洗礼以来》《圣迹》《手握两个世纪》等一大批文学著作,从而奠定了其“领跑中国现代诗的第一集团内”(王燕生语)的地位。
与高崎开始有文字上的交流大概在2009年,当时我创办主编的民间诗歌刊物《有巢》向他发出约稿函后,得到了他热情的回应,一位成名多年大诗人的信任让我的办刊之举深受鼓舞。而我们第一次近距离相见则是2010年初在浙江平阳举行的第十一届温州文学周上,初见印象的高崎个子瘦小,戴着一顶爵士帽,清癯儒雅,显得精神抖擞,略带闽南口音的普通话简洁有力,不时有警世之语。而他最让我记忆犹新的则是那双深凹进去的眼睛,那里面似乎拥有洞察一切的能量。从高崎的眼睛里我无法解读出他诗歌的奥秘,却能看到一份孤独着的自信,这或是一位饱经岁月濯洗诗人最可贵的品质。
平阳文学周之后,稔熟起来的高崎和我的交往更加频繁,我们除了在一些文学聚会上常常碰见外,每在节假日还能发发短信,相互致意,同时还在博客上互动不断。对于我新发的博文,他会第一时间跟帖点评,或褒或贬,往往一语中的,让我受益匪浅,当然我也常去他的博客学习,老一辈作家的严谨和谦逊给我的创作启发良多。高崎由于身体原因(听说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参加一些文学活动聚会有些困难,他每每看到我在博客上晒出活动照片后,就会打电话过来询问活动细节,有时候电话一打就是半个小时,从中我能感受到他对温州本土文学的热情和关切。作为文学晚辈,高崎对我的关注和帮助也是用心的,当他得知我的一次作品研讨会反响平平后,主动打来电话安慰,并认真阅读我的诗歌作品,梳理出一些他所看好的,然后发到自己的博客上予以推荐,给我以莫大的鼓励,让我储备了更多在文学道路上继续写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有一天高崎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自己研宄了很长时间,发现我的诗歌气质和美国著名诗人兼摇滚歌手鲍勃•迪伦接近,还专门找来几首鲍勃•迪伦的诗供我参考。且不论我的诗歌与鲍勃•迪伦有几分相似,高崎如此不遗余力地提携诗坛后进,着实让我感动。当然这些事例不仅仅限于我,在温州这片诗歌土地上可以说俯拾皆是。
高崎的诗歌除了意象诡丽、想象奇特外,对西方文本的介入较深,充盈着与他这个年龄不相称的颠覆力量。著名诗人西川说他“追求语言的绝对价值”;著名诗歌评论家沈泽宜将他与超现实主义诗人法国的艾吕雅、阿拉贡比照,还将他的语言与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美国诗人阿什贝利的“火焰意象学”相“触摸”,体现一种真正的大气;著名作家东君说,“高崎在中国老一辈诗人中算是一个异数”。在我看来,这些评价是恰如其分的,高崎对诗歌所具有的敏锐嗅觉总是让我这个文学晚辈因难以企及而心生“妒忌”。记得我一首诗中有一句“孤独将我惊醒”,高崎在博客上看到后特地给我打来电话,指出这句诗比较俗套,建议改成“我与孤独一起惊醒”。经他这样一改,一首诗的意境不知拔高了多少倍,换句话说,将腐朽化作了神奇,这是我需要毕生学习感悟的本领。
今年6月30日晚23时许,在温州的青年诗人泥人给我打来电话,说高崎猝然离世,具体时间不详。这是一个让人措手不及的消息,如同夏日的一记闷雷,重重击打在我的胸口。等一阵惊悸稍稍平息后,我急急向同是苍南籍的诗人孟想去电话证实。当然,如此兹事体大的“传言”终宄会被无情的电话铃声证实,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在得知确切消息的同时,我找出高崎去年寄给我的两本书和一封信。两本书中,一本是诗集《顶点》,另一本是评论集《分量:深的声音》,信是用圆珠笔写成的,内容谈及两本书的写作背景,以及授权我可在《顶点》中选发诗歌作品到《有巢》等等,字迹干净挺拔,一如他清癯的外形气质,这是我在这个夏夜里看得最缓慢也最沉重的手写文字。趁着夜色,我拟定两幅挽联送给高崎,一幅以乐清市现代汉诗学会的名义:深入自然十八年,黄金分量;纵横诗国三千里,顶点声音。另一幅以我个人的名义:诗路高崎凭大任;文山绝处赖先生。挽联借用了高崎一些己正式出版书籍的名称,固然不能概括高崎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卓然成就,但也寄托了我对他的追念。两天后,即7月2日下午,我与张艺宝、郑亚洪等一行三人赶往浙江最南端的苍南县城,只为见诗人高崎最后一面。
在苍南县城灵溪镇建兴东路258号的高崎生前寓所,诗人静静地躺在冰棺里,身体被一条红色的绸被覆盖着,看不到他的脸,无人知道他的下一首诗要写什么,也无人知道他最后一首诗所采用的意象,就像无人知道他离世时的情形,只有冰棺后的巨幅遗像用一贯深凹进去的眼睛看着每一个前来吊唁的人。作为诗人身份的高崎的灵堂布置样式与寻常去世者并无区别,房间里飘荡着嗡嗡的佛号声,一对红蜡烛几乎流干,孱弱的烛光扑闪不定,一双他生前穿过的黑皮鞋摆放在冰棺前的水泥地上,随时准备送他“上路”。当我们一行离开苍南时,天空突然呈现出一片久违的蓝,让人窒息的蓝。从蓝的深处,一轮红日正沿着静默的山脊回家。
2013年7月3日下午
参加高崎老师的追悼会之后
就想着《坡度诗刊》要为他做个专题以表纪念
高崎老师的走是一个诗歌事件
不仅是温州的也是中国诗歌的
不只是他的,也是所有诗人的事件
同时他是我们所共同尊重的诗人
他高傲的骨骼,崎硕的语言和孤独的品质
是他作品和为人的一面独有的旗帜
对于他,除了瞻仰,我能说的就是
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活着,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深深缅怀
一一坡度诗社 泥人
纪念
温州诗人 高崎 纪念专题2011年5月,高崎在永嘉丽水街
马叙 摄
高崎(1945〜2013),原名高其士。祖籍福建,生于浙江温州。196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中国现代诗歌实验主义代表诗人。
历任浙大诗社社长,温州师院诗社顾问,温州市作协理事,苍南县文协常务副主席。200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作品见于《诗刊》、《中国作家》、《诗选刊》、《星星》、《江南》、《诗歌月刊》、《中国新诗刊》、匈牙利出版的《华人诗人作品选》等国内外书刊;作品入选《中国新诗年鉴》、《中国最佳抒情诗》、《一行诗人诗选》、《〈中国作家〉获奖作品选》、《2008年中国年度散文诗》、《2011年中国诗歌精选》等多种选本。
出版有文学专著《复眼》、《圣迹》、《顶点》、《征服》、《洗礼以来》、《手握两个世纪》《声音中的黄金》《分量:深的声音》等8部,主编《浙大诗选》(合编)等2部。
获文化部主办的全国诗歌赛大奖、浙江优秀文学作品奖、《中国作家》一等奖等奖项,并获2008年度和谐中国•优秀作品金奖。2011年与西川、欧阳江河、商震一齐入选诗刊社第二届青春回眸诗会。
当代文学界对高崎写作的评价是:“高崎始终置身于领跑中国现代诗的第一集团内”(王燕生);“在他那天才式的联翩的浮想中感到了诗意追逐的快乐,倾泻着令我们感到陌生的美丽。”(谢冕);“高崎追求语言的绝对价值”(西川);“他的诗,指向一种‘存在之诗’”(王家新);“许多学者与诗人以艾吕雅、阿拉贡等法国诗人比照高崎,而我们却从高崎诗中一种先锋派绘画式的语句中触摸到了美国诗人阿什贝里的‘火焰意象学';高崎的诗正在体现一种真正的大气。他的书引起阅读震撼”(沈泽宜)。高崎 作品选
昆虫记
我们已经被最细的昆虫打败
我们是狙击手,是船长,是灵与肉蜿蜒的道路
我们无理由从骄傲长出了胡子
昆虫的生命类似它的金色足迹
以无声的脚印走过无声的道路
它们高抬着鼻头,办完婚事,吃草,吃大米和流年之劫
它们恩爱交加,如同暴风雨合力浇顶
仿佛是辛辛那提最大幸福的一个投影
它们的母亲同样怕事,嗫嚅,同样气冲斗牛
每一条瓦槽也都是它们苦苦修缮的隐秘
没有一个王递给它们一枚硬币
重访渔寮
那些沙,沙地,不,是沙滩的
耳语,战胜,尔虞我诈或者三者存在于
一个海岸纷纷的意外里。耳语,战胜,尔虞我诈或者三者存在于
一个海岸纷纷的意外里。
质感。沙!一一哦,这个海边的
沙,类似那支俄罗斯圆舞曲过门的
平滑;细,也似天鹅湖飞禽
——上升到半空化为乌有的那朵轻敌的
柔意。
那些昆虫们轻车熟路地吐露着雨夜丝光。不,风光。
丝绸及其放肆的梦。或者是百分之百的暴雨
洗浴之后的清新,带来行走的袅娜质感。
一米,不,不到一米之外,是水,是海的水
细沙:将海岸情感之波晕化为金黄,不,
是另一种黄一一它低于黄土,不,高于龙袍。
它吞吐着细小的洞穴朝代,
细小的鬼话,小拳蟹的春宵
喜怒无常。小小火焰的神经质。它们都在
沙滩之下快活如仙,目无黑暗。
沙滩,还将它既定的海
深藏。一次潮,是漂亮内心里
自己神的顶点。胆大,
无忌。它像更合适的嘴巴
向海,一泻金黄色的燕颌儿
无数支手伸出去——小小的手掌,
沙粒的手掌,到底握住了
一个分量。像降B琴键一样固定。
一万年,整个大海无法
将一个轻浮的沙地移走。朋友,
这就是逻辑:不以善与恶作为定论。江心屿
走上江心屿
记忆立刻潮落潮起
林木依然澎湃着
乔木寻找早年的落叶
也要掘地千尺了
古寺板着脸聆听潮音
不一定与过去奔腾的吼声合拍
越过那座半圆拱桥的顶点
我是第十二次登临此地
信物依然绿着
找不到当年云的尸体
情话也己经面目俱非了
我当年就不是白鸥
而今己有白鸥的身份
飞翔时与春景相遇
我己不再是蒙面大盗了
心绪无暇可击
只想着妻儿在涛声以外
不要失散水
水蹚过周庄
水划过一条条铁轨与航道
水漫过远方的我的纸质呵
水,一贯的水:它的色相
它的烟影
它的矛盾
它的全部商贾,它的心,它的羞涩与邪念
它的枣状的甜蜜
它的幽灵与晶亮的桨声
它的喧嚷,它的骚动
它的招牌一如千里舟楫它的船只所载过的怀旧的
眷恋,异客的盲从,数不清的
质疑与拥趸
让袅娜的周庄置于无辜的淹没……
水,滑过低矮的周庄
粼粼的水刺激过的周庄
今天,用我的诗滋润过
将成为近代中国巨大的隐秘之一
重新
——余杭二白潭印象
重新翻晒别人吊诡的谓语
才吐出自己的诗句并非云烟重新奔走在别人的最前面
才发觉自己击桨的同样干练
重新想起水负驮的力量
其中有一股是来自辽阔的担当
院落黄昏
在海角的海角之内,
黄昏之外还有庞大的黄昏。
黄昏的另类意义是,
黎家不会将黄昏当作黄昏。
狗将嘴悄悄靠在后腿旁边,
安谧是不成问题的。
借着白昼的最后之光,
少女温柔的劳累显然大于时间。
树干多么粗大,果实硕壮,
它们腹内安置着一座座心仪的海洋。
时光许多,绿也太奢侈了,
少女还舍不得一线光阴,丢入绿荫里。
只有这时候干活才舒展呐,
纺出的棉线不计长度。
只有这时候干活才适合耳语,
谈些心跳的,或是不怕狗偷听的事儿。
这样,允许世界可以黑下来,
为了抒情的核心目的,姐妹们不理睬什么风暴!中国东部,有个诗人叫高崎
□马叙
打开高崎的博客,《分量:深的声音》,博客依旧,只是再也无人来更新了。高崎离开我们已经近五个月。高崎的诗,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不以他的离开而被忘记,在我,反而更深地记起他的诗。前些年,他一直叫我给他写篇诗评,但是我一直未动笔,我说,我还没有完全把握你的诗,等我基本把握了,再来写。却不知,一直到他走了,我还未写出诗评来。那一天,当我删除手机里高崎的号码时,突然感到无限的悲伤。
他刚走的那些日子,我曾与友人说起高崎,我说,高崎于当代诗歌是一个有意义的存在,只是太被忽略了。即使他的突然离去,也没有引起中国诗评界应有的关注。中国诗界,只是一个诗歌活动界,人们记住的只是那些诗歌活动家。
我喜欢高崎的诗。他的诗是拮牙的,他是有意识地在诗中设置了一道道的障碍,阻止当代读者在阅读中追求流畅阅读的坏习惯。他甚至在一个句子中把词语分开来,填入陌生意象,在词语中设置矛盾,设置悖论,迫使读者停顿下来,咀嚼意象与词语。与此同时,他借此打开词语与意象的天空,让互不相涉的意象翻滚而出,渲染诗的空间。我以为,高崎的这种写作,与高崎的内心世界密切相关。高崎在现实中可以说是世俗的,但是他又是一个内心高傲的诗人,因为写出了杰出的诗篇而不为人知,就有了一种迫切感,这迫切感是自己己经年近七十,但是作为一个与生俱来的天才式的诗人,为了不让这个庸俗的世界埋没了优秀的自己,用世俗的方式呈示自己,我以为,于高崎而言,一点都没有错,
因为他太孤独了,因为少有人能理解他与他的内心。也正因为此,高崎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痛苦的存在。有段时间,大约2009年,他曾给我打过几次电话,述说自己的诗的写作,嘱咐我写诗评。2011年,《诗刊》在永嘉开“青春回眸”诗会,在丽水街,我拍了高崎在午后强烈阳光下一张喝饮料的照片,他的深陷的眼窝,削瘦的双颊,因吸进液体饮料而深深凹陷进去,专注而忧伤一一在卡夫卡的头像照片中,我看到过这种状态。后来我在整理照片时,看到这一张,我想,这就是高崎,这个喝饮料的高崎与写诗的高崎是一致的。他的内心的是孤独的,痛苦的,同时又是忧伤的。这孤独、痛苦、忧伤,在这一刻被集中呈示了出来。他有首短诗,《南方》一一
没有冬天的地方,珍视暴雪的到来
我每次把一些亲切的雪米
埋伏到第二年的夏天
做着刻骨的梦幻,在炎热如歌的故乡
知道吗,亲爱的,我瞻仰上帝的容量,也瞻仰雪
瞻仰
被公牛粗暴吃过的
花草,及其精神,及其粪土。也瞻仰
灾难:一如用光,去堵住
银河的种种伤口
这是一首有着刻骨孤独品质的诗,如此自我,孤独,高傲,有若在远远的河岸上漫步,流水与世界与时间与生命构成了一个金属般的处所,然后把自我安置其中,享用这近乎残酷的孤独。“我每次把一些亲切的雪米/埋伏到第二年的夏天/做着刻骨的梦幻,在炎热如歌的故乡/知道吗,亲爱的,我瞻仰上帝的容量,也瞻仰雪”,这个高崎就是那个午后强烈阳光下喝饮料的高崎,他埋藏着一些词语,连同自己一同埋藏起来,在词语深处做着孤独的交易。这里有着他对世界的期望,但是这种期望却越来越加深着他的绝望:“瞻仰/被公牛粗暴吃过/花草,及其精神,及其粪土。也瞻仰/灾难:一如用光,去堵住/银河的种种伤口”。这是最典型的高崎语言风格,一如他所说的“刻骨的梦幻”,他的诗的语言也是刻骨的,他用尖刀般的词语,从事物的旁边(不那么直接地)划开口子,使得诗中的情绪突然地流露出来,用以加深这个绝望的世界。
他的另一首诗:《黄鹤楼》一一
一只鸟来过此处,喘气,筑草,交颈,飞走
有闲的人为它泡制了大楼。
我也来过此处,观望,抽烟,恐高,消逝
谁也没给他另一座建筑物。理由简单:你的宗教有“神”,你不是异物。
白云,神的爪牙,洋洋得意,仍然煽动。
另一个人只捞到空空的臆想,或破旧之光,
此楼,一个钟座。虚与实的曱状腺。
回忆事件是它的最正确刻度。
我满头大汗。体内的自恋也有流淌。
也埋伏了“想”许多,高度都无法干涉。
其中最大的念头是:
流浪太久了,大江两端
都没有底部,鹤唳仿佛错觉。
当人置于风景之中,完全是从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幽暗的存在,风景与我何干?它唯有加深着人的孤傲,一个黄鹤楼,是一个彻底的错觉,只有词语介入时,它才开始波动起来,而这个语词的创造者诗人高崎本身,也是一个错觉,是这个世界的错觉。这个世界存在过一个叫高崎的诗人么?这个叫高崎的诗人他写过黄鹤楼么?这黄鹤楼却又是一个与这个叫高崎的诗人毫无相关的所在。但是,高崎来了,语词来了,“我也来过此处,观望,抽烟,恐高,消逝/谁也没给他另一座建筑物。”他在此处看到了虚无,他完全游离了风景,他所到之处是另一座建筑物,但是这建筑物却是不存在的(“谁也没给他另一座建筑物”)!与前一首《南方》一样,高崎的这种孤独是具有金属质地的,被他自己所创造的词语所击,发出痛苦而铿锵的声音。
我平时读得比较多的是高崎的短诗。高崎还写了《顶点》《洗礼以来》等长诗。他的长诗气象万千,词语坚硬、奇异,有如石砌台阶,于一步步艰难的上升中,感受着意象的旋转与冲击。得空我还要再次认真地静下心来读高崎的长诗,感受长诗中的高崎与短诗中的高崎的区别。
这个短文,只写到高崎的极少部分,期待更有份量系统论述高崎的新的文章的出现。
高崎,于当代诗坛而言,是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诗人,他应该获得更高的评价与荣誉,应该为更多的人知道与崇敬。
以后,当我遇见外地的诗人朋友,我会说,你知道么,中国东部,有个诗人叫高崎!送别高崎
□陈鱼观
我介入温州文坛时间较晚,之前对温州本土的作家诗人所知甚少,
而诗人高崎则是我“所知甚少”者中很早就知道的一位。
我所知道的作为诗人身份的高崎大概来自某本偶然看到的刊物,从后来能搜索到的一些信息中得知,他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生于浙江最南端的苍南县,上世纪六十年代从国内某名牌大学毕业后,曾一度在温州市区某单位上班,后不知何种原因又返回老家苍南某山村隐居,于是就有了“自觉深入大自然腹地长达十八年”的人生体验。我想,这十八时间应是高崎致力于文学探索与写作的黄金年代,也是高崎耐住了寂寞和诱惑的卓绝岁月。在这十八年中,高崎除了发表大量的诗歌散文作品外,还写出了生命中最早的诗集《复眼》,此后又陆续出版了《顶点》《征服》《声音中的黄金》《洗礼以来》《圣迹》《手握两个世纪》等一大批文学著作,从而奠定了其“领跑中国现代诗的第一集团内”(王燕生语)的地位。
与高崎开始有文字上的交流大概在2009年,当时我创办主编的民间诗歌刊物《有巢》向他发出约稿函后,得到了他热情的回应,一位成名多年大诗人的信任让我的办刊之举深受鼓舞。而我们第一次近距离相见则是2010年初在浙江平阳举行的第十一届温州文学周上,初见印象的高崎个子瘦小,戴着一顶爵士帽,清癯儒雅,显得精神抖擞,略带闽南口音的普通话简洁有力,不时有警世之语。而他最让我记忆犹新的则是那双深凹进去的眼睛,那里面似乎拥有洞察一切的能量。从高崎的眼睛里我无法解读出他诗歌的奥秘,却能看到一份孤独着的自信,这或是一位饱经岁月濯洗诗人最可贵的品质。
平阳文学周之后,稔熟起来的高崎和我的交往更加频繁,我们除了在一些文学聚会上常常碰见外,每在节假日还能发发短信,相互致意,同时还在博客上互动不断。对于我新发的博文,他会第一时间跟帖点评,或褒或贬,往往一语中的,让我受益匪浅,当然我也常去他的博客学习,老一辈作家的严谨和谦逊给我的创作启发良多。高崎由于身体原因(听说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参加一些文学活动聚会有些困难,他每每看到我在博客上晒出活动照片后,就会打电话过来询问活动细节,有时候电话一打就是半个小时,从中我能感受到他对温州本土文学的热情和关切。作为文学晚辈,高崎对我的关注和帮助也是用心的,当他得知我的一次作品研讨会反响平平后,主动打来电话安慰,并认真阅读我的诗歌作品,梳理出一些他所看好的,然后发到自己的博客上予以推荐,给我以莫大的鼓励,让我储备了更多在文学道路上继续写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有一天高崎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自己研宄了很长时间,发现我的诗歌气质和美国著名诗人兼摇滚歌手鲍勃•迪伦接近,还专门找来几首鲍勃•迪伦的诗供我参考。且不论我的诗歌与鲍勃•迪伦有几分相似,高崎如此不遗余力地提携诗坛后进,着实让我感动。当然这些事例不仅仅限于我,在温州这片诗歌土地上可以说俯拾皆是。
高崎的诗歌除了意象诡丽、想象奇特外,对西方文本的介入较深,充盈着与他这个年龄不相称的颠覆力量。著名诗人西川说他“追求语言的绝对价值”;著名诗歌评论家沈泽宜将他与超现实主义诗人法国的艾吕雅、阿拉贡比照,还将他的语言与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美国诗人阿什贝利的“火焰意象学”相“触摸”,体现一种真正的大气;著名作家东君说,“高崎在中国老一辈诗人中算是一个异数”。在我看来,这些评价是恰如其分的,高崎对诗歌所具有的敏锐嗅觉总是让我这个文学晚辈因难以企及而心生“妒忌”。记得我一首诗中有一句“孤独将我惊醒”,高崎在博客上看到后特地给我打来电话,指出这句诗比较俗套,建议改成“我与孤独一起惊醒”。经他这样一改,一首诗的意境不知拔高了多少倍,换句话说,将腐朽化作了神奇,这是我需要毕生学习感悟的本领。
今年6月30日晚23时许,在温州的青年诗人泥人给我打来电话,说高崎猝然离世,具体时间不详。这是一个让人措手不及的消息,如同夏日的一记闷雷,重重击打在我的胸口。等一阵惊悸稍稍平息后,我急急向同是苍南籍的诗人孟想去电话证实。当然,如此兹事体大的“传言”终宄会被无情的电话铃声证实,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在得知确切消息的同时,我找出高崎去年寄给我的两本书和一封信。两本书中,一本是诗集《顶点》,另一本是评论集《分量:深的声音》,信是用圆珠笔写成的,内容谈及两本书的写作背景,以及授权我可在《顶点》中选发诗歌作品到《有巢》等等,字迹干净挺拔,一如他清癯的外形气质,这是我在这个夏夜里看得最缓慢也最沉重的手写文字。趁着夜色,我拟定两幅挽联送给高崎,一幅以乐清市现代汉诗学会的名义:深入自然十八年,黄金分量;纵横诗国三千里,顶点声音。另一幅以我个人的名义:诗路高崎凭大任;文山绝处赖先生。挽联借用了高崎一些己正式出版书籍的名称,固然不能概括高崎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卓然成就,但也寄托了我对他的追念。两天后,即7月2日下午,我与张艺宝、郑亚洪等一行三人赶往浙江最南端的苍南县城,只为见诗人高崎最后一面。
在苍南县城灵溪镇建兴东路258号的高崎生前寓所,诗人静静地躺在冰棺里,身体被一条红色的绸被覆盖着,看不到他的脸,无人知道他的下一首诗要写什么,也无人知道他最后一首诗所采用的意象,就像无人知道他离世时的情形,只有冰棺后的巨幅遗像用一贯深凹进去的眼睛看着每一个前来吊唁的人。作为诗人身份的高崎的灵堂布置样式与寻常去世者并无区别,房间里飘荡着嗡嗡的佛号声,一对红蜡烛几乎流干,孱弱的烛光扑闪不定,一双他生前穿过的黑皮鞋摆放在冰棺前的水泥地上,随时准备送他“上路”。当我们一行离开苍南时,天空突然呈现出一片久违的蓝,让人窒息的蓝。从蓝的深处,一轮红日正沿着静默的山脊回家。
2013年7月3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