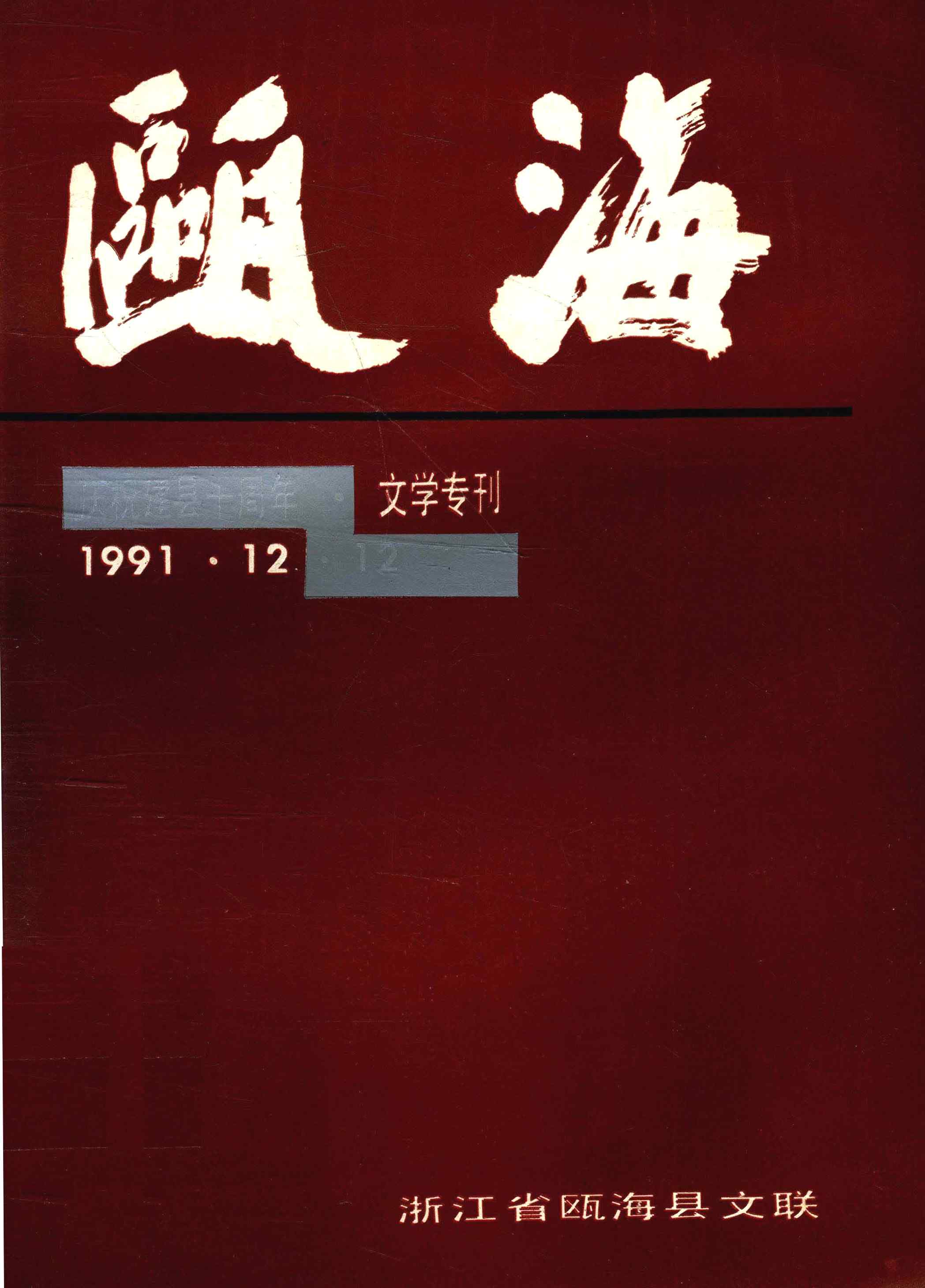内容
扯掉掩饰,再现真实
——序《逝去的饥饿》
李敏
读完李永汉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逝去的饥饿》,我被书中形形色色人物的命运深深的牵动。我禁不住思绪万千,浮想联翩……
当今时代,各行各业,突飞猛进。图书行业更是生机盎然。各种体裁的出版物甚而广之。而真正能够在人们脑际中留下深刻印象,又敢于剖露历史史实,更具有历史记载历史意义的又凸现文学价值的作品甚而微之,而《逝去的饥饿》真正填补了这一空缺。它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对“三年饥荒”的历史史料进行考证的求证价值,而且还具有足以引发人们对“民以食为天”的现实问题进行反思的思考,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有人问:“三年饥饿”是哪朝哪代的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李永汉先生的《逝去的饥饿》——其故事独具特色、曲折多变、跌宕起伏。全文以“大跃进、浮夸风、征粮、抗征、统购统销、赈灾……”为主线,紧紧围绕“饥饿”一词作文章。讴歌了以赵兴国、张志远、郭明为代表的无私奉献的豁达情怀,克勤克俭的工作作风,知难而进的人生理念,使他们得到了人民的高度信任和充分肯定。作品高度赞扬了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着力塑造了一名典型的、独特的文学人物郭明及五个花季少女的曲折、悲惨的爱情故事;深刻地揭露了以樊如仁、荀光明等为反
面代表的荒淫无度、贪得无厌、投机钻营,欲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最终受到法律制裁和道德、良心谴责的官场人物的丑恶嘴脸……
作者成功地运用了顺叙的写作手法逐渐展开了故事画面,一些对故事情节的刻画,虽然作者只是点到为止、淡淡的几笔却让读者拍案叫绝。而这种刻画在作品中俯拾即是。我们不难看到一些精彩绝妙的画面:赵兴国开仓放粮赈灾,群众感动得跪地叩谢……然而赵兴国的私自开仓放粮赈灾在当时是违反国家政策的,当赵兴国被捕,警察给他戴上锃亮的手铐时,恸心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把警察和警车围得水泄不通,人民痛哭流涕,“赵所长是好人,不能抓走……”的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张志远为赈救灾民从省上告到中央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使灾情得到了缓解;善良纯洁涉世未深的宋佳丽被荀光明强奸未遂而跳楼自杀的悲惨场面,让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樊如仁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与吕艳珊在一起下乡工作中勾搭成奸,在宿舍、桔林里一次次苟合的丑恶画面……作者以讽刺、幽默、辛辣的笔调对人生、事业、仕途、人性、良知等诸多方面描绘得栩栩如生,尤如一幅幅浓缩了的人生百态图呈现在读者眼前。
从《逝去的饥饿》荡气回肠、宕荡起伏、曲折多变的画面中我们深深地感悟到:作者为我们提出了非常严峻的问题——民以食为天。节约粮食、饱不忘饥、忆苦思甜。是当代的我们每一个人不可忽视的话题。随着时代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水土的自然流失、不合理的各种建筑,迫使农耕面积逐渐减少,这些现象早已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虽已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但在某些地区并未落到实处。竭力期待有关部门加强管理,还我耕地……
《逝去的饥饿》这部长篇小说让我为之激动、为之感慨。人类社会更需要这样的作家去扯掉历史的面纱,再现饥荒、艰难的岁月,从而启迪世人,教育后代的警世之作。
2005年8月于北京
橘是故乡红
翁德汉
瞿溪是个离温州市区不远的古镇,民风古朴历史悠长,很有文化底蕴。而它也是台湾著名女作家琦君创作的灵感之泉。
在瞿溪琦君故居,挂有琦君手书的一副字:“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忘掉故乡,我若能不再哭,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这句话出自琦君散文集《烟愁》后记。从琦君的第一本散文小说合集《琴心》算起,先后出版了《烟愁》、《琦君小品》、《红纱灯》、《三更有梦书当枕》、《桂花雨》、《细雨灯花落》、《读书与生活》、《千里怀人月在峰》、《与我同车》等五十多本。琦君在散文中,尽情地抒发真挚热烈的感情,有对故乡山水和童年生活的回忆,有对父母师长挚友深沉的怀念,有对在台湾生活的叙写,又有对异国旅游的观感,以及专给小读者写的小散文,但写得最好最多的,是怀乡思亲的散文。故乡在她的文章的份
量是最大最大的。琦君写着:“我们从大陆移植来此(“移植”一词,用得何等精妙),匆匆将三十年。生活上尽管早已能适应,而心灵上又何尝能一日忘怀于故土的一事一物。水果蔬菜是农乡的好,鸡鱼鸭肉是家乡的鲜。当然,风景是家乡的美,月是故乡的明。”琦君唯一一次来温州时,她的亲人总是会问她:“你吃橘子了没有?香吗?”而她总是会答:“香,真香。”五月初五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大年夜吃年糕。每到了这样的日子,琦君总会想起故乡的美味。甚至,连家乡的水也使她夜不能寐,她在《水是故乡甜》里写道:“说实在的,既使是真正天然的矿泉水,饮啜起来,在感觉上,在心灵上,比起大陆故乡的‘山泉’来,能一样的清洌甘美吗?”如果能回来再喝一口故乡的水,多好啊。她那么盼望海天连成一片,山水连成一线,能回到故乡,“享受壮阔的山水田园之美,呼吸芳香静谧的空气。我渴望那一天,难道那一天还会远吗?”(《写作回顾》)
琦君,原名潘希真,自幼失去双亲,由伯父伯母抚养长大,她的文章里的父亲母亲就是伯父和伯母。琦君对伯父和伯母的感情是非常深的。散文《母亲新婚时》《母亲那个年代》《母亲的偏方》《母亲的手艺》《母亲母样》《髻》《毛衣》《母亲的教导》都在正面把母亲作为主角写。这些文章或表现母亲的能干,或表现母亲的慈祥,或表现母亲对女儿的爱,或表现母亲的幽怨等,每一篇文章都讲述了母亲某一个方面的特点,合起来看,一个活活的母亲就树立在我们的面前。这些文章是琦君最感人的作品,也是琦君对童年时代的回忆,是对故乡人和事的追想。
对我们来说,琦君最响亮的作品是《橘子红了》,因为这个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以后,红极一时。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说:“看琦君的文章就好像翻阅一本旧相簿,一张张泛了黄的相片都承载着如许沉厚的记忆与怀念,时间是这个世纪的前半段,地点是作者魂牵梦萦的江南。”白先生的这句话就是对着《橘子红了》而言。《橘子红了》以江南的某地(我宁愿认为是在瞿溪这个小镇)为背景,讲述了父亲和母亲和这辈人的一个
故事。我没有看过电视,但从文章看来,我更多的还是感受琦君对故乡事和故乡景的描述,以小说为基调进行自己的心灵回乡之旅。
琦君曾经回来一次,但她有可能再回来重温吗?橘是故乡红,人是故乡亲啊。
谁的眼泪在飞
——读杨绛《我们仨》
亲情是一道汩汩的水,流入你的心田,流入我的心田,亲情是一抹遥远的希望,使我坚强,使你坚强,使我们宽容。这是我读杨绛(总觉得直呼其名有不敬之意,还是叫杨先生吧)的《我们仨》的最真切的感受。
生于一九一一年的杨先生对我来说,是奶奶辈的人物。用现代人三年一代沟的说法,不知道是代了多少沟了。但是,我一看到这本作者伴着眼泪写完的《我们仨》时,我毫不犹豫地买了。抛开互联网,告别夜生活,我静静地用两个夜晚的时间读完了这本书。
《我们仨》这个题目,本来是杨先生要写的。1996年底,病中的钱瑷知道母亲要写《我们仨》后,要求先让她写几篇。当时重病在床的钱瑷只能在别人的帮助下艰难地写作,完成5篇后在母亲的劝说下才停止。1997年3月,钱瑷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开人世。第二年,钱钟书先生也去世了。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杨绛先生先后失去两个至亲,一家人计划好的《我们仨》暂时搁浅。直到去年,她才有勇气重新审视和回忆一家三口所经历过的岁月,完成这本书。同时,钱瑷写的几篇也都作为附件附在书的后面。
读这本书,有时候觉得是钱瑷在写,有时候觉得是杨先生在写。读到深处,已经分辨不出他们一家三口,谁是谁了。“阿瑷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
妈。”“阿瑷常说:‘我和爸爸是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玩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亲情到深处,家里人的角色都分不清楚了。谁最大?谁最小?不是钱钟书最大,不是钱瑷最小。也许,只有亲情最大,人最小。
杨先生总是用平静的语气叙述她的故事,《干校六记》、《洗澡》这样,《我们仨》也这样。在温婉平实的文字中,蕴涵着深邃和厚重;所写的都是日常的枝节,却处处显出浓郁的人情味,及真正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那股朗朗清气。“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瑷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一场生别死离,在杨先生的笔下,就用一个简单的词语“失散”来了结了。但是,这个“失散”却把老人的心完全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杨先生一个人思念他们三个人,思念的是这份难以言表的亲情。杨先生生钱瑷住院的时候,钱钟书常“做坏事”:打翻墨水瓶染了房东家的桌布,砸了台灯,弄坏门轴。但杨先生说一声“不要紧,我会修”,钱钟书便放下了心。在家里,杨先生是母亲,是妻子,是整个家庭的主心骨。杨先生就是用她的宽容、坚强,把“我们仨”的亲情故事演绎下来。书后录有钱瑷的几幅铅笔素描,展现了钱钟书在女儿眼中的凡人面貌:有一幅画钱钟书在夏夜赤膊摇扇读书;一幅画他“衣冠端正而未戴雅齿”;更有一幅画他“如厕”,却题为“室内音乐”,令人捧腹。在这幽默、快乐、“不正经”的背后,依稀能看到杨先生的身影。
杨先生披露了他们一家的故事,人有认为这有违他们一向对自己家庭生活状况保持低调的“惯例”。很明显,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对外界、特别是对媒体保持低调,对于钱、杨二位大家是一贯的做法。曾有媒体试图做《我们仨》的全文连载,被杨先生婉言谢绝,以为“碰上有不喜欢的读者那不是耽误人家时间吗”;杨先生不求别人相信和喜欢,只要共鸣和分享。
生命,因为什么而美丽
弗里达·卡哈罗(FridaKahlo,1907-1954),墨西哥现代史上最著名的女画家,共产主义者,双性恋者。六岁那年,弗里达不幸染上小儿麻痹症,十八岁那年,她在一次车祸中受重创,临近死亡的边缘。一生,她一共做过三十二次手术。
弗里达是一个传奇人物,她的生平故事被无数的人重写过,有关她的小说、戏剧、舞蹈、传记文学和电影举不胜举。去年十月,好莱坞又推出一部以她的生平故事改编的电影。这部也叫《弗里达》的电影作为2002年威尼斯电影节的开幕片,由女导演茱莉·泰摩执导,塞尔玛·海耶克演女主人公。
传记电影拍起来想必有些难度,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展现人物的一生是摆在导演和演员面前的课题,而且传记人物的生平有些定型,比较难以表达出来。弗里达的一生,是爱欲纵横的一生。这一生里充满了疾病、痛苦、流产、渴望、同性恋、画、自恋,还有衣服、宠物、装饰、玩具。一部传记电影,往往会夸张、放大人物。但是弗里达的一生,不用夸张和放大,如果把真实的表现出来,就很“夸张”了,因为就算在现代人看来,弗里达的一生,也是很夸张的一生。冲着这点,我就很想看看这部电影。
终于是等到了。远方的朋友给我寄来了碟片。
但结果还是让我料到了。
要表现弗里达爱欲纠缠、恣意妄为的一生,是颇为不易的。看看那些匪夷所思的画作,那些你闭上眼睛就会想到的画作,你就不难想象她是怎样一个激进的艺术家,一个怎样的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和情感极端强烈和脆弱的爱人。没有一颗偏执、敏感、痛苦的心,就不会画出扭曲的梦魇,血淋淋血管交互的心脏,被钉子钉满一身肉体,还有无数幅莫名其妙的自画像。
对照真实的弗里达,在叙事结构和表现手法上,影片的表现
只能称为中规中矩,对于弗里达一生的叙述似乎过于温情。导演还是不敢真实的表达弗里达夸张的一生,仿佛在担心自己一不小心踩过界,弗里达的狂野生活方式就会超出大多数观众接受的范围(要知道弗里达的生活方式恐怕在今天仍然不能为人们所接受,更遑论上个世纪初)。但是这样的浅尝辄止显然并不能令了解弗里达的观众满意:那些画作后面流动的是什么?是弗里达丰沛的情感和内心,是生活的痛苦和画家种种的无奈,就象影片的末尾弗里达的丈夫里维拉所说的一段话:她的画,有的甜美如同微笑,有的绝望得如同生活的苦难。很遗憾的是,在本片里,很少看到人物精彩的内心戏,缺乏对人物暗涌的情感的揭示。影片也描写了弗里达和里维拉开放式的婚姻,不过那看起来似乎不过是弗里达在自己对里维拉的爱和里维拉永远不羁的心之间的一个折衷,其实他们之纠缠一世,内里的感情是复杂得多的。或许,导演不懂吧,只能粗暴的处理了弗里达的感情。影片里也有两个表现女画家双性恋的镜头,但在我看来那只是一种典型的艺术家作派,不修边幅的闲散作风,随随便便的刷了一把。显然,弗里达的那种火热的激情不仅仅是这么的简单,弗里达绝对不是影片里的弗里达。
塞尔玛·海耶克应该说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虽然在本片中她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自己的美貌(再也没有那些为了突出她的美色特意制造出来的特写镜头),但是相信作为一个演员,特别是墨西哥演员,这是一次期待已久的机会:饰演一个墨西哥的标志性人物的荣耀和挑战。看完以后,总觉得她的表演还少了点什么,也许有点空洞,毕竟,弗里达这样的人难演。况且,塞尔玛·海耶克的世界和弗里达的世界是那么的不同。
影片充满饱和的色彩世界,在服装、置景方面都突显了墨西哥的传统,符合弗里达的个性和爱好。同时细腻的事件处理,和女性视角都可以看出1952年出生于美国麻萨诸塞州的导演的影子,也只有细腻的女导演才能表现出来。
但可惜,我们还得继续等,等真正的弗里达出现。
梅泉诗书有余香
黄舟松
读《泉村集》有感
因工作关系,重游茶山,特别留意点缀在溪山之间的文化史迹,也特意拜访了两位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化老人王学钊、谷斌臣先生,得赠大作多部,如获至宝。犹惊艳于王学钊、林长春先生编校的乡土历史文献《雅川艺文·泉村集》,入眼即爱不释手,坐在车里就狼吞虎咽起来。茶山人的艺文就像茶山的溪山和杨梅,也像茶山的民间雅士一样,要细细品味,但这一切的珍品我都还来不及细品,而放下书后生出的一些感触,却在这本书之外。
茶山给我的感觉,是文气绵长,文风鼎盛,耕读之风,弥满山林,似乎溪山泉石、亭阁梅兰之上都依附
着民间文人的文魂灵气,但在经历过一番变乱之后,这一方的文气似乎嘎然而止,渐有烟消云散之势。溪山之间,前人的遗迹已如凤毛麟角,难觅其踪,更别说一派浓郁的文化氛围了。像王学钊先生这样的人,在今人眼里已是奇人,能与其志同道合的人,自然也是凤毛麟角。
像王先生和谷先生这样的人,应该算是茶山耕读文化的传人。而文化的传承是需要一种环境,一种氛围,一种如林长春先生所说的“基因”的。这个基因的载体就是先贤的遗迹和他们流传下来的作品。王先生之所以能成为今日的王先生,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或普通的教师,或其他什么角色,恐怕正是因为从小就特别留意于那些在旁人眼里毫无价值的更不能“当饭吃”的正日益被历史所掩埋的文化史迹,从中获得启迪,吸取养料,甚至获得精神上的支持和蕴藉。
且看一段王先生的经历:
“……我和徐日久总算是同住在洞桥下西向,古与今的邻居。石板道坦在童年日日经过,这两株大榕树和樟树自己年龄幼小看到自己老,到现在虽有一些年老的伤痕但还是很茂盛,童年每年八月初一在徐宅祠堂里看社戏,现在仍旧照样八月初一演戏,我在生产队时也曾在一涉园遗址上为樟树锄草除虫,一涉园里遗留下来的太湖石藏在我家,我真是‘园日涉以成趣’了!”
“与先人为邻”的感觉造就了今日的王先生,所以在王先生的身上就看到了徐凝的影子,同时,我相信徐凝的影子一定一直深藏在王先生的心中。“梅泉诗书有余香”是我此次茶山之行的真实感受,但由此产生的感触,主要的却是一丝隐忧。王先生和谷先生都已是古稀老人,他们的传人安在?就像一棵老树,已只剩几片老叶。文化的断裂不是一件小事。正如一棵老树,如果将它砍断,会有什么结果?
行者无疆
王永贞
初识阿云,是在一次采访中,临走时奉送一本书法作品集。心想,一个长期在基层工作,且政务缠身的人,还能有这份闲情雅致去侍弄书法,是否是故意附庸风雅?当静心看完作品集之后,才感悟到一个行者的闲逸痴迷之心和追求无疆的艺术境界。
随着交往的日益加深,兄弟般的无话不谈,也从中窥视到阿云书法历程践行了一个行者的本质。行走之前,没有人授他七十二变,以应付书法路上的九九八一难。在行走中逐渐觉悟,在觉悟中稳步前往。他的历程,也证实了他是一个天资颇高的觉悟者。这种天赋,使他丰富的生活履历,变成了对书法的体察和顿悟。他从山灵水秀的泽雅走出,从乡村教师到机关干部,从瓯越大地到巴蜀山区。直到今天,在高楼与高楼,官场与官场,浮躁与现实之间度过了几十
个春秋。更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山区农民的儿子,时常聆听山风吹拂树林的婆娑之响,目睹春雷过时山洪的呼啸而至,倾听山鸟和清泉的悄然和鸣……这种对大自然的贴近,有着原始生命气息的激情与酣畅,变成他笔下奔泻而出的生气勃勃景象,摄人心魄般的音乐之境。
古人一直将“气韵生动”作为书法的最高准则。书法虽是点画、结体、章法等现象构成,但其艺术欣赏时,必然要透过这些现象才能领悟其力感、情致、气韵和风格。观阿云的每一幅作品,都在欣赏一曲曲无声的音乐。其作品是生命与自然的合一,宏观与微观的统一,既体现浑雄宏大的韵致,而具体方向与流转之中又暗含入精入微的情趣,呈现出既气势磅礴又旋律优美,别开生面的艺术景象。章方松先生在序言中说,“书法之道,道法自然”,“书之妙也,本无定法;率真自然,贵在悟性。”观阿云书法给人感觉是不修边幅,不受传统之拘束,有着一种拙朴的自然之美。在此,我非常赞同方松先生的观点,拙到极处是至美。
他的作品集里有联曰:“溪窗听雨,石榻观云。”我想这应该是他感悟书法之道吧。观其书如观其人,阿云兄不管是从政还是遣兴于书法,都始终能够做到闲情雅思,在优雅平淡之中追求完美,直至无心自达。他一向视书法为闲事,以悠闲之心待之,以平静消遣的方式待之,将其作为消除烦闷,净化心灵的娱乐。正是这种痴迷,日积月累,终成正果。每逢亲朋好友索字,他会一口答应,甚至精裱后送到府上。令人温情盎然。行者总是在追慕古人之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然后独枝一帜自辟新境。
阿云是位行者。行者总是怀着一颗虔诚之心的,行者在漫漫的行走过程中领略万千气象,行者总是在追求无疆,以达无极。
(作者系中国青年诗人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中国企业报企划部主任)
——序《逝去的饥饿》
李敏
读完李永汉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逝去的饥饿》,我被书中形形色色人物的命运深深的牵动。我禁不住思绪万千,浮想联翩……
当今时代,各行各业,突飞猛进。图书行业更是生机盎然。各种体裁的出版物甚而广之。而真正能够在人们脑际中留下深刻印象,又敢于剖露历史史实,更具有历史记载历史意义的又凸现文学价值的作品甚而微之,而《逝去的饥饿》真正填补了这一空缺。它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对“三年饥荒”的历史史料进行考证的求证价值,而且还具有足以引发人们对“民以食为天”的现实问题进行反思的思考,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有人问:“三年饥饿”是哪朝哪代的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李永汉先生的《逝去的饥饿》——其故事独具特色、曲折多变、跌宕起伏。全文以“大跃进、浮夸风、征粮、抗征、统购统销、赈灾……”为主线,紧紧围绕“饥饿”一词作文章。讴歌了以赵兴国、张志远、郭明为代表的无私奉献的豁达情怀,克勤克俭的工作作风,知难而进的人生理念,使他们得到了人民的高度信任和充分肯定。作品高度赞扬了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着力塑造了一名典型的、独特的文学人物郭明及五个花季少女的曲折、悲惨的爱情故事;深刻地揭露了以樊如仁、荀光明等为反
面代表的荒淫无度、贪得无厌、投机钻营,欲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最终受到法律制裁和道德、良心谴责的官场人物的丑恶嘴脸……
作者成功地运用了顺叙的写作手法逐渐展开了故事画面,一些对故事情节的刻画,虽然作者只是点到为止、淡淡的几笔却让读者拍案叫绝。而这种刻画在作品中俯拾即是。我们不难看到一些精彩绝妙的画面:赵兴国开仓放粮赈灾,群众感动得跪地叩谢……然而赵兴国的私自开仓放粮赈灾在当时是违反国家政策的,当赵兴国被捕,警察给他戴上锃亮的手铐时,恸心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把警察和警车围得水泄不通,人民痛哭流涕,“赵所长是好人,不能抓走……”的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张志远为赈救灾民从省上告到中央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使灾情得到了缓解;善良纯洁涉世未深的宋佳丽被荀光明强奸未遂而跳楼自杀的悲惨场面,让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樊如仁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与吕艳珊在一起下乡工作中勾搭成奸,在宿舍、桔林里一次次苟合的丑恶画面……作者以讽刺、幽默、辛辣的笔调对人生、事业、仕途、人性、良知等诸多方面描绘得栩栩如生,尤如一幅幅浓缩了的人生百态图呈现在读者眼前。
从《逝去的饥饿》荡气回肠、宕荡起伏、曲折多变的画面中我们深深地感悟到:作者为我们提出了非常严峻的问题——民以食为天。节约粮食、饱不忘饥、忆苦思甜。是当代的我们每一个人不可忽视的话题。随着时代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水土的自然流失、不合理的各种建筑,迫使农耕面积逐渐减少,这些现象早已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虽已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但在某些地区并未落到实处。竭力期待有关部门加强管理,还我耕地……
《逝去的饥饿》这部长篇小说让我为之激动、为之感慨。人类社会更需要这样的作家去扯掉历史的面纱,再现饥荒、艰难的岁月,从而启迪世人,教育后代的警世之作。
2005年8月于北京
橘是故乡红
翁德汉
瞿溪是个离温州市区不远的古镇,民风古朴历史悠长,很有文化底蕴。而它也是台湾著名女作家琦君创作的灵感之泉。
在瞿溪琦君故居,挂有琦君手书的一副字:“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忘掉故乡,我若能不再哭,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这句话出自琦君散文集《烟愁》后记。从琦君的第一本散文小说合集《琴心》算起,先后出版了《烟愁》、《琦君小品》、《红纱灯》、《三更有梦书当枕》、《桂花雨》、《细雨灯花落》、《读书与生活》、《千里怀人月在峰》、《与我同车》等五十多本。琦君在散文中,尽情地抒发真挚热烈的感情,有对故乡山水和童年生活的回忆,有对父母师长挚友深沉的怀念,有对在台湾生活的叙写,又有对异国旅游的观感,以及专给小读者写的小散文,但写得最好最多的,是怀乡思亲的散文。故乡在她的文章的份
量是最大最大的。琦君写着:“我们从大陆移植来此(“移植”一词,用得何等精妙),匆匆将三十年。生活上尽管早已能适应,而心灵上又何尝能一日忘怀于故土的一事一物。水果蔬菜是农乡的好,鸡鱼鸭肉是家乡的鲜。当然,风景是家乡的美,月是故乡的明。”琦君唯一一次来温州时,她的亲人总是会问她:“你吃橘子了没有?香吗?”而她总是会答:“香,真香。”五月初五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大年夜吃年糕。每到了这样的日子,琦君总会想起故乡的美味。甚至,连家乡的水也使她夜不能寐,她在《水是故乡甜》里写道:“说实在的,既使是真正天然的矿泉水,饮啜起来,在感觉上,在心灵上,比起大陆故乡的‘山泉’来,能一样的清洌甘美吗?”如果能回来再喝一口故乡的水,多好啊。她那么盼望海天连成一片,山水连成一线,能回到故乡,“享受壮阔的山水田园之美,呼吸芳香静谧的空气。我渴望那一天,难道那一天还会远吗?”(《写作回顾》)
琦君,原名潘希真,自幼失去双亲,由伯父伯母抚养长大,她的文章里的父亲母亲就是伯父和伯母。琦君对伯父和伯母的感情是非常深的。散文《母亲新婚时》《母亲那个年代》《母亲的偏方》《母亲的手艺》《母亲母样》《髻》《毛衣》《母亲的教导》都在正面把母亲作为主角写。这些文章或表现母亲的能干,或表现母亲的慈祥,或表现母亲对女儿的爱,或表现母亲的幽怨等,每一篇文章都讲述了母亲某一个方面的特点,合起来看,一个活活的母亲就树立在我们的面前。这些文章是琦君最感人的作品,也是琦君对童年时代的回忆,是对故乡人和事的追想。
对我们来说,琦君最响亮的作品是《橘子红了》,因为这个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以后,红极一时。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说:“看琦君的文章就好像翻阅一本旧相簿,一张张泛了黄的相片都承载着如许沉厚的记忆与怀念,时间是这个世纪的前半段,地点是作者魂牵梦萦的江南。”白先生的这句话就是对着《橘子红了》而言。《橘子红了》以江南的某地(我宁愿认为是在瞿溪这个小镇)为背景,讲述了父亲和母亲和这辈人的一个
故事。我没有看过电视,但从文章看来,我更多的还是感受琦君对故乡事和故乡景的描述,以小说为基调进行自己的心灵回乡之旅。
琦君曾经回来一次,但她有可能再回来重温吗?橘是故乡红,人是故乡亲啊。
谁的眼泪在飞
——读杨绛《我们仨》
亲情是一道汩汩的水,流入你的心田,流入我的心田,亲情是一抹遥远的希望,使我坚强,使你坚强,使我们宽容。这是我读杨绛(总觉得直呼其名有不敬之意,还是叫杨先生吧)的《我们仨》的最真切的感受。
生于一九一一年的杨先生对我来说,是奶奶辈的人物。用现代人三年一代沟的说法,不知道是代了多少沟了。但是,我一看到这本作者伴着眼泪写完的《我们仨》时,我毫不犹豫地买了。抛开互联网,告别夜生活,我静静地用两个夜晚的时间读完了这本书。
《我们仨》这个题目,本来是杨先生要写的。1996年底,病中的钱瑷知道母亲要写《我们仨》后,要求先让她写几篇。当时重病在床的钱瑷只能在别人的帮助下艰难地写作,完成5篇后在母亲的劝说下才停止。1997年3月,钱瑷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开人世。第二年,钱钟书先生也去世了。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杨绛先生先后失去两个至亲,一家人计划好的《我们仨》暂时搁浅。直到去年,她才有勇气重新审视和回忆一家三口所经历过的岁月,完成这本书。同时,钱瑷写的几篇也都作为附件附在书的后面。
读这本书,有时候觉得是钱瑷在写,有时候觉得是杨先生在写。读到深处,已经分辨不出他们一家三口,谁是谁了。“阿瑷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
妈。”“阿瑷常说:‘我和爸爸是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玩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亲情到深处,家里人的角色都分不清楚了。谁最大?谁最小?不是钱钟书最大,不是钱瑷最小。也许,只有亲情最大,人最小。
杨先生总是用平静的语气叙述她的故事,《干校六记》、《洗澡》这样,《我们仨》也这样。在温婉平实的文字中,蕴涵着深邃和厚重;所写的都是日常的枝节,却处处显出浓郁的人情味,及真正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那股朗朗清气。“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瑷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一场生别死离,在杨先生的笔下,就用一个简单的词语“失散”来了结了。但是,这个“失散”却把老人的心完全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杨先生一个人思念他们三个人,思念的是这份难以言表的亲情。杨先生生钱瑷住院的时候,钱钟书常“做坏事”:打翻墨水瓶染了房东家的桌布,砸了台灯,弄坏门轴。但杨先生说一声“不要紧,我会修”,钱钟书便放下了心。在家里,杨先生是母亲,是妻子,是整个家庭的主心骨。杨先生就是用她的宽容、坚强,把“我们仨”的亲情故事演绎下来。书后录有钱瑷的几幅铅笔素描,展现了钱钟书在女儿眼中的凡人面貌:有一幅画钱钟书在夏夜赤膊摇扇读书;一幅画他“衣冠端正而未戴雅齿”;更有一幅画他“如厕”,却题为“室内音乐”,令人捧腹。在这幽默、快乐、“不正经”的背后,依稀能看到杨先生的身影。
杨先生披露了他们一家的故事,人有认为这有违他们一向对自己家庭生活状况保持低调的“惯例”。很明显,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对外界、特别是对媒体保持低调,对于钱、杨二位大家是一贯的做法。曾有媒体试图做《我们仨》的全文连载,被杨先生婉言谢绝,以为“碰上有不喜欢的读者那不是耽误人家时间吗”;杨先生不求别人相信和喜欢,只要共鸣和分享。
生命,因为什么而美丽
弗里达·卡哈罗(FridaKahlo,1907-1954),墨西哥现代史上最著名的女画家,共产主义者,双性恋者。六岁那年,弗里达不幸染上小儿麻痹症,十八岁那年,她在一次车祸中受重创,临近死亡的边缘。一生,她一共做过三十二次手术。
弗里达是一个传奇人物,她的生平故事被无数的人重写过,有关她的小说、戏剧、舞蹈、传记文学和电影举不胜举。去年十月,好莱坞又推出一部以她的生平故事改编的电影。这部也叫《弗里达》的电影作为2002年威尼斯电影节的开幕片,由女导演茱莉·泰摩执导,塞尔玛·海耶克演女主人公。
传记电影拍起来想必有些难度,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展现人物的一生是摆在导演和演员面前的课题,而且传记人物的生平有些定型,比较难以表达出来。弗里达的一生,是爱欲纵横的一生。这一生里充满了疾病、痛苦、流产、渴望、同性恋、画、自恋,还有衣服、宠物、装饰、玩具。一部传记电影,往往会夸张、放大人物。但是弗里达的一生,不用夸张和放大,如果把真实的表现出来,就很“夸张”了,因为就算在现代人看来,弗里达的一生,也是很夸张的一生。冲着这点,我就很想看看这部电影。
终于是等到了。远方的朋友给我寄来了碟片。
但结果还是让我料到了。
要表现弗里达爱欲纠缠、恣意妄为的一生,是颇为不易的。看看那些匪夷所思的画作,那些你闭上眼睛就会想到的画作,你就不难想象她是怎样一个激进的艺术家,一个怎样的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和情感极端强烈和脆弱的爱人。没有一颗偏执、敏感、痛苦的心,就不会画出扭曲的梦魇,血淋淋血管交互的心脏,被钉子钉满一身肉体,还有无数幅莫名其妙的自画像。
对照真实的弗里达,在叙事结构和表现手法上,影片的表现
只能称为中规中矩,对于弗里达一生的叙述似乎过于温情。导演还是不敢真实的表达弗里达夸张的一生,仿佛在担心自己一不小心踩过界,弗里达的狂野生活方式就会超出大多数观众接受的范围(要知道弗里达的生活方式恐怕在今天仍然不能为人们所接受,更遑论上个世纪初)。但是这样的浅尝辄止显然并不能令了解弗里达的观众满意:那些画作后面流动的是什么?是弗里达丰沛的情感和内心,是生活的痛苦和画家种种的无奈,就象影片的末尾弗里达的丈夫里维拉所说的一段话:她的画,有的甜美如同微笑,有的绝望得如同生活的苦难。很遗憾的是,在本片里,很少看到人物精彩的内心戏,缺乏对人物暗涌的情感的揭示。影片也描写了弗里达和里维拉开放式的婚姻,不过那看起来似乎不过是弗里达在自己对里维拉的爱和里维拉永远不羁的心之间的一个折衷,其实他们之纠缠一世,内里的感情是复杂得多的。或许,导演不懂吧,只能粗暴的处理了弗里达的感情。影片里也有两个表现女画家双性恋的镜头,但在我看来那只是一种典型的艺术家作派,不修边幅的闲散作风,随随便便的刷了一把。显然,弗里达的那种火热的激情不仅仅是这么的简单,弗里达绝对不是影片里的弗里达。
塞尔玛·海耶克应该说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虽然在本片中她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自己的美貌(再也没有那些为了突出她的美色特意制造出来的特写镜头),但是相信作为一个演员,特别是墨西哥演员,这是一次期待已久的机会:饰演一个墨西哥的标志性人物的荣耀和挑战。看完以后,总觉得她的表演还少了点什么,也许有点空洞,毕竟,弗里达这样的人难演。况且,塞尔玛·海耶克的世界和弗里达的世界是那么的不同。
影片充满饱和的色彩世界,在服装、置景方面都突显了墨西哥的传统,符合弗里达的个性和爱好。同时细腻的事件处理,和女性视角都可以看出1952年出生于美国麻萨诸塞州的导演的影子,也只有细腻的女导演才能表现出来。
但可惜,我们还得继续等,等真正的弗里达出现。
梅泉诗书有余香
黄舟松
读《泉村集》有感
因工作关系,重游茶山,特别留意点缀在溪山之间的文化史迹,也特意拜访了两位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化老人王学钊、谷斌臣先生,得赠大作多部,如获至宝。犹惊艳于王学钊、林长春先生编校的乡土历史文献《雅川艺文·泉村集》,入眼即爱不释手,坐在车里就狼吞虎咽起来。茶山人的艺文就像茶山的溪山和杨梅,也像茶山的民间雅士一样,要细细品味,但这一切的珍品我都还来不及细品,而放下书后生出的一些感触,却在这本书之外。
茶山给我的感觉,是文气绵长,文风鼎盛,耕读之风,弥满山林,似乎溪山泉石、亭阁梅兰之上都依附
着民间文人的文魂灵气,但在经历过一番变乱之后,这一方的文气似乎嘎然而止,渐有烟消云散之势。溪山之间,前人的遗迹已如凤毛麟角,难觅其踪,更别说一派浓郁的文化氛围了。像王学钊先生这样的人,在今人眼里已是奇人,能与其志同道合的人,自然也是凤毛麟角。
像王先生和谷先生这样的人,应该算是茶山耕读文化的传人。而文化的传承是需要一种环境,一种氛围,一种如林长春先生所说的“基因”的。这个基因的载体就是先贤的遗迹和他们流传下来的作品。王先生之所以能成为今日的王先生,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或普通的教师,或其他什么角色,恐怕正是因为从小就特别留意于那些在旁人眼里毫无价值的更不能“当饭吃”的正日益被历史所掩埋的文化史迹,从中获得启迪,吸取养料,甚至获得精神上的支持和蕴藉。
且看一段王先生的经历:
“……我和徐日久总算是同住在洞桥下西向,古与今的邻居。石板道坦在童年日日经过,这两株大榕树和樟树自己年龄幼小看到自己老,到现在虽有一些年老的伤痕但还是很茂盛,童年每年八月初一在徐宅祠堂里看社戏,现在仍旧照样八月初一演戏,我在生产队时也曾在一涉园遗址上为樟树锄草除虫,一涉园里遗留下来的太湖石藏在我家,我真是‘园日涉以成趣’了!”
“与先人为邻”的感觉造就了今日的王先生,所以在王先生的身上就看到了徐凝的影子,同时,我相信徐凝的影子一定一直深藏在王先生的心中。“梅泉诗书有余香”是我此次茶山之行的真实感受,但由此产生的感触,主要的却是一丝隐忧。王先生和谷先生都已是古稀老人,他们的传人安在?就像一棵老树,已只剩几片老叶。文化的断裂不是一件小事。正如一棵老树,如果将它砍断,会有什么结果?
行者无疆
王永贞
初识阿云,是在一次采访中,临走时奉送一本书法作品集。心想,一个长期在基层工作,且政务缠身的人,还能有这份闲情雅致去侍弄书法,是否是故意附庸风雅?当静心看完作品集之后,才感悟到一个行者的闲逸痴迷之心和追求无疆的艺术境界。
随着交往的日益加深,兄弟般的无话不谈,也从中窥视到阿云书法历程践行了一个行者的本质。行走之前,没有人授他七十二变,以应付书法路上的九九八一难。在行走中逐渐觉悟,在觉悟中稳步前往。他的历程,也证实了他是一个天资颇高的觉悟者。这种天赋,使他丰富的生活履历,变成了对书法的体察和顿悟。他从山灵水秀的泽雅走出,从乡村教师到机关干部,从瓯越大地到巴蜀山区。直到今天,在高楼与高楼,官场与官场,浮躁与现实之间度过了几十
个春秋。更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山区农民的儿子,时常聆听山风吹拂树林的婆娑之响,目睹春雷过时山洪的呼啸而至,倾听山鸟和清泉的悄然和鸣……这种对大自然的贴近,有着原始生命气息的激情与酣畅,变成他笔下奔泻而出的生气勃勃景象,摄人心魄般的音乐之境。
古人一直将“气韵生动”作为书法的最高准则。书法虽是点画、结体、章法等现象构成,但其艺术欣赏时,必然要透过这些现象才能领悟其力感、情致、气韵和风格。观阿云的每一幅作品,都在欣赏一曲曲无声的音乐。其作品是生命与自然的合一,宏观与微观的统一,既体现浑雄宏大的韵致,而具体方向与流转之中又暗含入精入微的情趣,呈现出既气势磅礴又旋律优美,别开生面的艺术景象。章方松先生在序言中说,“书法之道,道法自然”,“书之妙也,本无定法;率真自然,贵在悟性。”观阿云书法给人感觉是不修边幅,不受传统之拘束,有着一种拙朴的自然之美。在此,我非常赞同方松先生的观点,拙到极处是至美。
他的作品集里有联曰:“溪窗听雨,石榻观云。”我想这应该是他感悟书法之道吧。观其书如观其人,阿云兄不管是从政还是遣兴于书法,都始终能够做到闲情雅思,在优雅平淡之中追求完美,直至无心自达。他一向视书法为闲事,以悠闲之心待之,以平静消遣的方式待之,将其作为消除烦闷,净化心灵的娱乐。正是这种痴迷,日积月累,终成正果。每逢亲朋好友索字,他会一口答应,甚至精裱后送到府上。令人温情盎然。行者总是在追慕古人之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然后独枝一帜自辟新境。
阿云是位行者。行者总是怀着一颗虔诚之心的,行者在漫漫的行走过程中领略万千气象,行者总是在追求无疆,以达无极。
(作者系中国青年诗人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中国企业报企划部主任)
相关地名
瓯海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