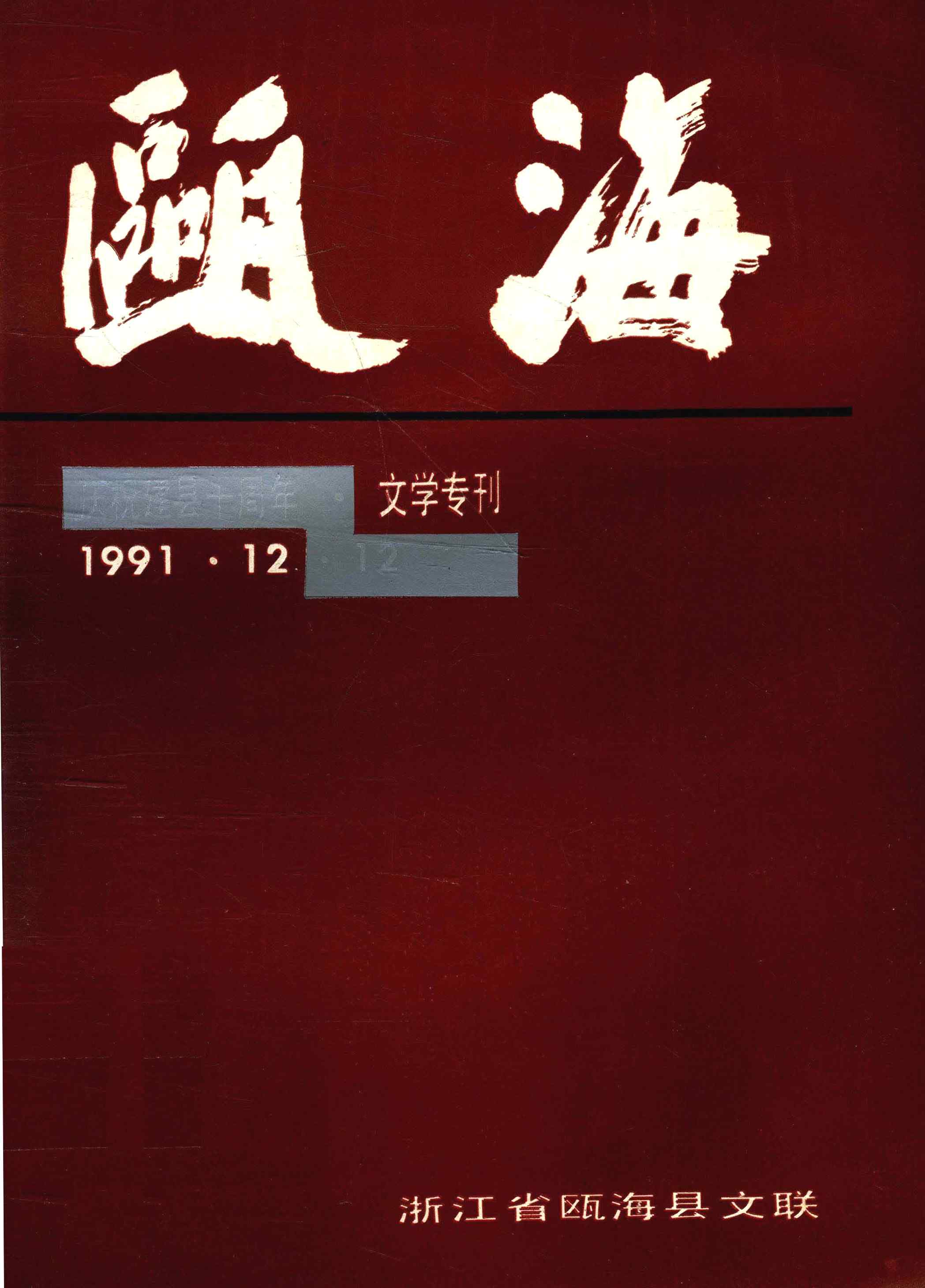内容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浴血奋战两年九个月,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使美军付出了伤亡近四十万人的沉重代价。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美国侵略者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已经到了一个人人喊打但又不敢打的地步,我们中国站了出来。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要说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还是抗美援朝以后。
朝鲜战场上,据不完全统计,志愿军牺牲了142409人。抗美援朝的每一胜利都是志愿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每座志愿军的坟墓都是一部英烈传。长眠在坟墓中的烈士们,虽没有从他们的时代得到什么,但是他们的时代却因为有了他们而光辉灿烂。
多山的朝鲜蜂腰部,有一条由北向南的公路从三歇马岭盘旋而过。三面环山叫岙;四面环山叫谷。在峰回路转处,在高山深谷中有座孤坟,群山环绕,绿树成荫。几片淡淡的云,一溪静静的水,陪伴着坟中的志愿军对空监视哨排长朱光耀。他的短暂一生,以一名共产党人的优秀本色,让无数活着的战友铭刻于心,愈久弥坚。
1954年4月5日,朝鲜停战后的第一个清明节,青山滢滢,细雨霏霏,山谷开遍了白、红、粉、紫、雪青色的杜鹃花。带着水珠的花儿静默肃立。那些常跑三歇马岭的志愿军驾驶员,自发掬一捧野花,接踵前往坟前瞻仰祭扫,缅怀逝者,寄托哀思。革命军队中虽已养成“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的习惯,但往坟前一站,敬礼,献花,表达深切怀念之情,仍禁不住热泪滚滚。一位自称是朱排长未婚妻的年轻女军人,趴在坟前,失声痛哭,开始泪如雨下,而后泪尽眼枯。
烈士坟前,“清明时节‘泪’纷纷”。一早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美国政府就实行全面支持蒋介石进行内战的政策,仇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为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敌视中国人民,以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进占我台湾,对新中国形成新月形包围圈,企图将新中国扼杀于摇篮之中。1950年自8月27日起,侵朝美军飞机连续多次侵入我国东北领空,在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宽甸等城镇上空进行侦察和扫射、投弹。美国无视我国警告,悍然命令侵略军越过“三八线”,占领距离我国边境只有五公里的朝鲜楚山镇,用炮火轰击和机枪扫射我国领土,叫嚣“要把赤色的中国洗成白色”,把战争强加给我们。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中国人民与美帝国主义的一场军事较量是不可避免的了。1950年10月8日,毛主席命令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19日,从安东、长甸河口和辑安跨过鸭绿江。10月25日,志愿军在朝鲜云山地区的间洞南山、朝阳洞东南山和玉女峰一线,打响了震惊世界的抗美援朝第一枪。后来,这一天被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纪念日。
志愿军战士有首诗:“美帝好比一把火,烧了朝鲜烧中国;中国邻居快救火,救朝鲜就是救中国。”1950年12月,二连理发员朱光耀所在的部队奉命从蜀、黔剿匪第一线撤了下来,奔赴朝鲜“救火”。
过鸭绿江之前,部队在安东一带进行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三视”教育。一天,二连连部围坐在临街有玻璃窗的一间房子里,讨论“该不该打”和“敢不敢打”。窗上四块玻璃,每块玻璃用纸条贴成一个“米”字,以防敌机丢炸弹震碎玻璃。阳历12月,正值“大雪冬至雪花飞”,东北的十冬腊月滴水成冰。室内烧着炉子,炉子上放着水壶。水整天沸腾着,蒸汽既调节气温又保护易干燥的鼻子。此时,房内热气腾腾,讨论七嘴八舌。
连首长分头下各班参加讨论去了。连部讨论由文化教员方世觉、理发员朱光耀主持。文化教员,排级待遇,虽不带兵,也算一名干部。朱光耀,连部党小组长。连队党支部工作一般按照“先党内后党外”的次序,党员领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支部决议的精神与要求,要比群众全面些、透彻些。只有党员自己思想先进,才能走在群众前面,率领群众同心同德完成上级所给予的任务。因此,凡连部司号员、卫生员、通信员、运输员文书等“七大员,八大员”开会,朱光耀就是负责人之一,相当于连部的“小政委”。由于人民军队的性质决定,旧社会统称的伙夫、马夫、挑夫、剃头匠,人民军队里改称炊事员、饲养员、运输员、理发员。尽管部队中有上下级和职务分工不同,最高的司令员、政治委员,最低的司号员、卫生员、通信员等等,都是对共同的革命事业负责。家族分祖、父、同、儿、孙五辈,军队内部都是同辈,指挥员和战斗员,都是 “员”字辈,都是人民勤务员,都有同样的光荣,在政治上和人格上一律平等,互相之间只有革命同志关系和工作关系,称呼没有尊贵与卑贱之分。
朱光耀理发是向他父亲学的,他父亲理发是向他外公学的,在家乡算得上“三代名剪”。在连队推、剪基本上无用武之地,一把剃刀,半个月内刮一百三十五个光头、十八个络腮胡子。把批评说成“刮胡子”,那是比方。朱光耀手中那把刀,除了司号员“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用不着刮,其余的上至连首长,下至“八大员”,只要时间允许,一月刮二次胡子,谁也不能例外。
社会上卖鸡毛揮子、修鞋、剃头“三不吆喝”。农村理发店是当地的“新闻中心”,顾客等的无聊,嘴巴没有地方安排,在那里发表高论、交流信息。但理发老师总不能扳着顾客的头,呱啦呱啦唾沫星乱溅,再说工作一走神,弄不好给人头上划道口子,惹事。所以只听不说,习惯成自然,朱光耀不爱说话,更不爱吆喝。同样下蛋,鸡叫鸭不叫。他从小受过他父亲严格训练,先替冬瓜刮霜、南瓜刮皮练腕子,练就的“刀功”,不论大、小、阔、扁、圆,头型各异;不论方、圆、梨、菱等七种脸型,理发修面,顾客光听到“割草”的声音,用不着担心。朱光耀像队列操似的练姿势。三分天赋,七分磨练,他理发的姿势很优美。他中等身材,四肢匀称,五官端正,皮肤光滑微黑,配上一双贼亮贼亮的眼睛,显得格外有精神。左上眼皮有指甲盖那么大一个疤,“瑕不掩瑜”,仍不失为一名标准军人。
连队在一个地方一住下,朱光耀端上一张凳,挂上咖啡色的搪刀布。他两腿直立,自然分开,一脚向斜前方伸出,另一脚与身体平面成直角,近似队列动作“稍息”;身体直立,胸部微挺、收腹,腰部自然挺直,两眼平视,又像队列动作“立正”。在实际操作中,不断调整站立位置和轮换双脚姿势。“轻磨重搪紧扒皮”,技术和艺术相结合。他持剃刀的手腕灵活、柔软、稳当、有力,无论正手刀、反手刀、推刀、削刀、滚刀,上下左右,往返快慢,恰倒好处,技巧娴熟,动作迅速。人家一小时剃六个光头,他剃七个。平常时候,他喜欢将十八名络腮胡子安排在星期天上午一次性解决。这时文化教员方世觉、司号员刘长法都会帮忙。刘长法捂热毛巾。方文教熟练地将胡刷放在热水碗里浸泡,拿起、排出过多的水,在肥皂上来回搓磨,然后在需要刮剃的部位画圆圈,从下巴开始,逐渐移动到两腮,而后是上唇与鼻子之间涂肥皂沫。朱光耀拿刀从右鬓角入手,面颊、嘴唇,直到颈部,顺刮逆剃,动作细致,不留“死角”。三人流水作业,十八个“刺猬”,经三个小时“修理”,变得容光焕发。
朱光耀有时也向刘长法学吹号。方文教在油灯下坚持给他们俩“开小灶”,教他们多识几个字。他们三人间,官兵关系、党群关系、知识分子与工农分子的关系,十分融洽。想不到这天讨论“敢不敢打”时,方文教与刘长法吵得面红耳赤,难解难分。起因就是方文教的发言。方说:“朝鲜战争,是一场弱国与强国的较量、武器装备落后的军队与技术装备先进的军队的较量。一部美国历史,就是一部靠战争开疆拓土、发家致富的历史,每次战争推动美国经济往上窜,美军装备往现代上‘化’,二战使美帝成为独一无二的经济巨无霸,其海军和空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技术装备上,堪称世界第一。陆军是一支具有高度现代化的诸兵种合成军队,一个军就有各种火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一个军只有三十六门。每个师有坦克一百四十多辆,而我们一辆也没有,基本上我们还处于‘小米加步枪’的阶段,与美军相比,优劣悬殊。美帝还拥有杀伤力很大的原子弹……”听着听着,刘长法站起来坐下,坐下又站起来。“暧,暧,你是不是杜鲁门派来的?杜鲁门一个月给你多少钱?”未等方文教分析我军的政治优势、人的因素优势、战术优势,他早憋不住了,直着嗓子大喊。
司号员刘长法,自小就没了爹娘,由奶奶拉扯四处讨饭。后来奶奶也死了。糠菜不糊口,乞讨无路走,在那个世道讨饭也不容易,一天下来三尺肠子闲着二尺半。十二岁那年,国民党曹福林的整编第五十五师路过他家乡,他当了一个排副的勤务兵。在旧社会,老百姓称国民党的空军是“少爷兵”,海军是“流氓兵”,陆军是“乞丐兵”。国民党陆军层层克扣军饷,一年多来,他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饿急了,石头都想吃。鲁西南战役,1947年7月8日把他解放过来,才十三岁。当了俘虏,第一顿饭,没有顾得上夹菜,半斤重的白面馍馍,吃了三个,鞋带开了,也弯不下腰系。解放军看他又瘦又小,发路费要他回家。人家话还没说完,他眼泪哗一下流了下来,大声哭道:“从娘肚出生以来,第一次尝到饱的滋味,就叫俺回家。”解放军也是穷苦岀身,一看这场面,说:“小是小了点,是棵好苗,看谁要?”卫生队的军医带上调剂,挑护理员、卫生员,第一批没挑上。第二批挑通信员,也没看上,把他急得直哭。越哭越没人看上。第五批团里的号长带上三个营的号目挑司号员,真是有缘,第一眼就看好了他这个“小鬼”。
号长问:“小鬼,愿不愿学吹号?”他用左手袖子擦了眼泪,再用右手袖子擦了鼻涕,连忙说:“只要不让俺回家,吹啥也愿意。”不知谁说了句:“‘吹牛’愿不愿意?”他答:“吹牛就吹牛。” 引起一阵哄笑。
军号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曲谱简单,易于掌握,是一种传达军令的通信工具。红军初创时期就有司号员。两军厮杀,军号可以号令三军,鼓舞士气,震撼和迷惑敌人。小小军号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营号目是位“伯乐”,向号长要求:“这个明明推光头偏叫留长发(刘长法)的给我们一营。”别看刘长法大字不识一个,但他“心有灵犀一点通”,不管号目用“逃、来、米、勿、少”简谱,还是用“合、食、一、让、吃”的工尺谱,只要是号谱一点就通,一记就牢。军号是由铜合金制造的,金光灿灿。有号嘴、号身、号碗、连接箍,形同乐队的小号,但无阀键。他原先只摸过一次唢呐,手背还被吹鼓手狠狠打了一掌。军号,不用说吹,就是摸也没有摸过。他不枉是军号“千里马”,一教就会,一练底气十足。千里跃进大别山,他跟在号目屁股后面,“教养一致,学用一致”,边行军边练习吹号。他吹的军号响亮而不走调,已经能按规定的号谱和号音传递命令和识别敌我了。
1947年10月,刘长法走马上任到二连当司号员。号目像嫁闺女似的,精心挑选一把军号,以便“小鬼”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号目思忖:单圈管号声音宏亮,通信距离较远,吹奏费力。双圈管号声音清脆,通信距离较近,吹奏省力。他人小肺活量有限,正式发给他一把双圈管军号。他双手接过军号,有一种使命高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的感觉。他用一根非常漂亮的绶带系在军号上,从左肩斜挂在右侧,军号闪着金光,红色飘带迎风招展。传达号令时右手将号嘴放在唇上,运用丹田之气鼓起腮帮,嘀嘀哒哒“振聋发聩”,声震旷野。他吹:“值星排长,催诸位起床,诸位还在床上——”这是起床号。
“大米干饭白菜汤,大米干饭白菜汤”,这是开饭号。
“戴连长,各排长,点点名,查査看——”二连长姓戴。这是晚点名。
行军,全连走得气喘吁吁,忽听他用军号告诉大家:“走不动的慢慢走,走得动的不要走——”大家听到休息号,原地坐在背包上休息,掉队的慢慢跟上。
在硝烟弥漫、枪声大作的战场,听到他急促的军号声:“嘀哒得嘀嘀嘀,嘀哒得嘀嘀嘀——”,战士们上好刺刀,跃出战壕,高喊着“冲啊!” “杀啊!”勇往直前,向敌阵冲去。他的冲锋号,使战士热血沸腾,使敌人胆战心惊。战士们听他的军号行动。野战军司令员姓刘,他也姓刘。司令员,司号员,只差一个字,战士们干脆把他改称为“司令员”,为了有别于刘伯承司令员,大家亲热地叫他“小刘司令员”。
他一米六的个头,瘦瘦的,没事站着喜欢抓耳挠腮,战友们说他像猴子,没进化好。他有很好的体力和耐力,有一股坚忍不拔、奋不顾身的内在气质。他虽然只有十六岁,却是一位经过多次真刀真枪磨练的老资格,是连里的战斗骨干。他一根肚肠通到底,挖出心来见得天。他学文化,底子差,吃了不少苦头。方文教给他鼓劲:“文化的根是苦的,但他的果子是甜的”,“葡萄是一点一点成熟的,文化是一天一天积累的”。他一听急了,说:“方文教,以后上课,能不能不用‘果子’、‘葡萄’这些可以吃的东西打比方?人家听了哪有心思听你讲课。”自从连里来了方文教,他努力学习文化,连里第一批摘文盲帽,其中就有他刘长法。
在他小小脑袋瓜里,有种思维方式,把自己的国家的可爱当作强大,把自己的部队看得比友邻部队能征善战,而说到二连他更是翘起大拇指,用上了从方文教那里学来的一句上海话:“一等那姆嗨”。团里司号员集中活动,人家问他:“听说你们连长讲话‘三句半’?”他就告诉人家,那是“简单扼要,水平高。”人家又问:“你们指导员讲课大问题套小问题,挺罗嗦的?” 他剋人家:“你懂什么,讲道理就是要掰开揉碎耐心启发战士觉悟。”说到文化教员,也是他二连的最棒,“比祁建华强”。“速成识字的教学方法,借助汉语拼音字母当拐棍,我们解放军个个都是飞毛腿,要那‘拐棍’干啥?”他不说方文教不会汉语拼音,而是硬说扫盲用不着汉语拼音。理发员也是自己连的好,一个小时多剃一个头,“哪像你们连的理发员,‘剃头不用刀,一根一根往下薅。’生薅硬拔,把别人的头扳过来推过去。我们二连的朱光耀是围着别人转。”就是自己炊事班蒸的馒头,也比人家的大。全连上下谁都知道他是一个不折不扣“胳臂往里拐”的人。他这种秉性,哪能听得方文教把中国说成“弱国”,把美帝说成“强国”、“世界第一”?战友们说他像猴子,他这会儿就成了 “翻脸猴子”。他先给方文教扣了一顶帽子,然后接着说:“装备好有什么了不起,蒋介石装备好,也不过给我们当运输大队长。你帮人家吹,吓唬谁?”知识分子就是历史上的“士”,正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方文教今天被自己的学生“无的放失”、“噼里啪啦”噎嗓子的话顶得喘不过气来,气得他七窍生烟,投五投六地说:“说我是杜鲁门派来的,你、你、你才是自己跑到国民党里打共产党。”“嗳,嗳,谁不晓得我在国民党部队里是勤务兵,端洗脸水的……”“端洗脸水,端洗脸水伺候反动派,洗了脸,打共产党有精神。”方文教觉得还不解气,用上海话嘟嚷了一句:“不等阿拉话说完,侬来搅啥个百叶结(胡搅蛮缠)”。
卫生员、通信员、运输员都批评方文教立场有问题,文书则批评司号员断章取义、乱扣大帽子。人虽少,大家抢着发表看法,中间搀杂着方文教与刘长法的唇枪舌剑,乱成一锅粥。房间里的水蒸气似乎不是从炉子上的开水壶中冒出来的,而是从大家嘴里说话带出来的。
这时党小组长朱光耀说话了:“一位老同志、一位文化教育干部,讨论问题像吵架,锣对锣,鼓对鼓,自由发言变成了互相攻击。讨论,要摆事实,讲道理,谈认识。争论要把焦点放在指导员布置的题目上,不要针对个人。”别看他平时三砖打不出一句话,关键时刻,讲起道理来却是一套一套,战友们戏称他说话“恕不零售”,“专营批发”。
部队“一切行动听指挥”,有铁的纪律,但民主作风特别好。官兵一致的原则就是军队内部团结一致的原则,其实质就是军队中的民主精神,就是全体人员在政治上的一律平等。人人都有主人翁的责任感,才能使上下级之间、党员与非党群众之间、新老同志之间、工农分子与知识分子之间互相关心、爱护、尊重、帮助,达到亲密团结,使连队具有坚强无比的战斗力。
刘长法不愧人叫“小刘司令员”,他接过朱光耀的话茬,说:“俺刚才那番话,屁股没坐在凳子上(出了原则的意思),‘走了火’,请方文教原谅。不过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只要一提美帝国主义就来气,手上拿两个破原子弹吓唬人、欺负人。”说着又问方文教:“实话实说,你怕不怕美国佬?”“怕死不当兵。”方文教边翻笔记本边说:“我是上海人,因为日本鬼子侵略,八岁那年,随父母‘厂矿内迁’到重庆,上海复旦大学、商务印刷厂也移设重庆。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五年半时间,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政略轰炸’、‘无区别轰炸’、‘地毯式轰炸’、‘地狱式轰炸’。‘咣——’‘咣——’剧烈的爆炸声震耳欲聋。1939年5月3日、4日两天,63架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投下炸弹176枚、燃烧弹116枚,炸死我们的同胞3991人,炸伤2287人,炸毁房屋4871栋。重庆的老百姓居无宁日哪,阿拉方觉世是在日本炸弹爆炸声中长大的。唉,怕有何用?”方觉世,上海人,1937年随父母逃日本鬼子,定居重庆,在重庆大轰炸中读完小学,重庆解放正在上大学一年级。他对中国文化有很浓的兴趣。章太炎说做学问有两种:一是求是,二是致用。他学习追求“致用”与“求是”。1950年1月参军,分配二连当文化教员。1949年,新中国的文盲占80%,二连的文盲占74%。他有雄心壮志,筹划着全连文盲一、二年内能认2000常用字,会写200—300字的应用文。中国文字愈来愈多,秦《仓颉篇》仅3300字,东汉《说文解字》增至9353字,明代《字汇》已有33179字,1915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多达48000字。他下了一番苦功从48000字中挑选出2000常用字。他苦于自己没有学过汉语拼音,在识字教学上不能利用这个行之有效的拐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教识字按汉字构造: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一个字一个字教。象形,象形,象实物之形。他教“日”、“月”,先画太阳、月亮。会意,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字组合在一起,表示一个新的意思。三人为“众”,三木为“森”,三水为“淼”,“上不上、下不下,卡住了”,四方木为“楞”。汉字80%是形声字,“饭”、“馍”、“饺”、“饼”、“枇杷”、“番薯”,讲得直吊刘长法的胃口。待大家认得500字以上,他采取“分散识字”法,把下一步应当学会的字,有计划地分配在自己编的课文里。他没有进过师范,不懂得教育学、教学法,但他的文化基础扎实,学识渊博,反正扫除文盲是一项群众性工作,学习时间由连队统一安排,“能者为师”,识字的教不识字的,不拘一格,因人施教。他培养了许多“小教员”,包教包学。教识字,形、音、义,读、写、用一丝不苟,二连扫盲进度在全团中上水平。1950年8月1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决定全军自1951年初起,在三年之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由于1950年10月开始抗美援朝,迫使这一教育计划没有实施就予以“推迟”,因此,他只能“见缝插针”扫盲。
大学一年级,也是大学生。方觉世这位大学生在连里当文化教员,是稀有元素。部队从剿匪转为抗美援朝,面对美、英、加、澳大利亚、菲律宾、南非等众多说英语的“联合国军”,迫切需要英语翻译。群工科相信“兵上三千出韩信”,以为在大学生中找翻译不是一件难事。找方觉世面试。方觉世读过英语,但他是一位喜欢就学,不喜欢就不学的人。他不喜欢英语,喜欢中文。他认为中文无字型变化之累,无定形文法之弊。英文是一种含糊的语文,像他这种不圆通的人,注定翻译不好具有含糊特性的文字。中文远胜英文简洁,他有理由学不好英文。他在高三做英文作业,翻着华美词典,累得满头大汗,把“我仍旧一无所知”误译成“我不比以前更聪明”,“她是一个朴素的女人”误译成“她是一个家庭妇女”,“我十分迷惑”误译成“我完全错了”,十道题错了九道半,而汉语作业十道题对了九道半。学了那么多年的英文,能使他记住的单词属于两类:一类是学了之后用于调侃的,“‘法石’(Father父亲)、‘买石’(Mather母亲)敬禀者,儿在校中读‘鲍克’(Book书)”,他仅记住了“父”、“母”、“书”三个英文单词。“我骂先生‘讨天四’(Tortoise龟),先生骂我是‘道格’(Dog狗)”,又记了“龟”、“狗”二个单词;另一类是与上海话搭上关系的。上海闲话“钞票多得来麦克麦克”,英语“麦克”(Much)是很多的意思。上海话“混枪势”的“枪势”,音译自英语中的Chance(运气)。开在小阁楼上的天窗,上海话叫“老虎窗”,与老虎没关系,而是从英语Roof(屋顶)中直译过来的,他至死也不会忘记英语中的“很多”、“运气”、“屋顶”这些词。除此之外,“科长同志,我学英语是‘王伯伯’(上海话嘲讽健忘者),对不起,还给老师了”。至于那些揭露敌人丑恶面目,宣传我们的政治主张,启发敌军士兵的觉悟,破坏敌人战斗力的英语,对他来说可以用四个字形容:“一窍不通”。就是战场上常用的“放下武器”、“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几句话,还是他刚从一连文教那里学来“现炒现卖”的。不是谦虚,方觉世认为自己的英语水平,是“王胖子的裤腰带——稀松。”他向群工科科长明确表示:“不愿‘滥竽充数’。”那时知识分子参军,“自报家门”,自报家庭出身。他父母是“白领”,国民党工厂的高级职员。职员在阶级成分上有点暧昧,虽然没有生产资料,但也没有参加体力劳动,他在“家庭出身”这一栏,钢笔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最后横下一条心填上一个“小资产阶级”。他在师里参加学习《社会发展史》,知道“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猴子变人,劳动创造人。重庆解放不久,市面上就有了“劳动布”。他就是脱下麦尔登上衣、凡立丁裤子,穿上劳动布新工装来参军的。通过学习增强了劳动观念。他明白一个道理:正确的世界观是在劳动中确立的。他下决心:这辈子,要用自己的脑力、体力劳动改造世界。他积极要求下连队。他教战士识字造句:“劳动人民”、“劳动成果”、“国际劳动节”、“劳动光荣”、“好逸恶劳”、“不劳而获”。他参加劳动大汗淋漓、两手血泡。他不是担心自己不劳动变回去,变成猴子,而是要通过劳动,奉献自己的青春,使自己变得更崇高。他与战士打成一片,把根扎在连队,与战士同呼吸、共命运、心相连、情相通。他与刘长法、朱光耀成了莫逆之交。刘长法坚定、勇敢、勤劳、爱说爱动,朴实中带有几分天真,嫉恶如仇,许多优点,值得自己学习。此刻,他后悔自己不该对刘长法生气、发火、挖苦。如今全军上下一听美军越过“三八线”,扩大侵略战争,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上前线,在这种氛围中如有人怕美军、怕原子弹、怕苦怕战,认为到朝鲜打仗是“多管闲事”、“引火烧身”,岂不自找不自在?老军长就承认自己看不起美国人,说“朝鲜多大个地方?在‘三八线’尿泡尿就能滋到釜山去。”人称“疯子军长”。彭总却夸:“那是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乐观主义的战士讨论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那真有点“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的味道。
连部学习告一段落,方文教给“三视”教育作小结:我们深受日本鬼子侵略之苦,不愿再受二茬罪;“唇亡齿寒”、“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保卫东方和世界和平,是我们人民军队的国际主义义务,该打。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政治上赢得中朝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军事上,我们有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的传统,而且善于近战、夜战、山地战和白刃格斗,以己之长,制敌之短;“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认清美帝国主义虚弱的本质,师出有名,师直为壮,敢打必胜。
方文教“敢打”二字刚出口,席地而坐的刘长法一跃而起,嘴里喊着“方文教讲得好,呱唧,呱唧”,两手举过头顶,带头鼓起掌来。
“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这个毛主席早年论断,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树立不怕一切困难敢于胜利的精神起到了巨大作用。全军的战斗热情被调动起来了,士气高昂。
还没宣布散会,有人敲窗户,嘭,嘭,嘭,嘭,敲得既急又重,幸好玻璃厚,没被敲碎,像有什么紧急军情似的。谁?玻璃上结着厚厚的冰花,看不清。“针眼大的洞,牛头大的风”,为了保暖,除了炉子烟囱拐了个弯通向室外,整个房子捂得严严实实,隔音。窗外的人叫些什么,含含糊糊,谁也听不清。一撩棉门帘,进来一位女军人,用高八度的嗓音,冲着朱光耀喊:“哥哥”。
她是给她的哥哥送棉鞋来的。有人说:东北脚长,西北脚厚,山东脚肥,广东脚窄,温州脚瘦,昆明脚小,唯独她哥哥的脚怪。从小到大没穿过几双鞋,一出门把鞋别在腰带上,赤着脚四乡八邻跑,没有鞋的约束,脚板扁平奇大,且茧疤密布,踏冰霜不知冷,踩炭火不觉烫,大步流星走在有角有楞的碎石上,没有疼痛的感觉。他穿的鞋,只有她和他妈做才合脚。她听十三兵团的同行说,朝鲜战场第一、二、三次战役,志愿军冻伤多,特别那双脚。她与她的哥哥一个兵团。兵团要入朝参战,没有合脚的鞋,她担心冻坏她哥哥的脚,熬更守夜突击做了一双絮了一斤新棉花的棉鞋。袼褙是家里带的。跑遍了毛泽东大街和斯大林大街凑齐一切材料。她用九股麻纳出这又厚又结实的鞋底,断了四根大号针,锥子扎了自己十八个窟窿,白鞋底成了“血染的风采”。上鞋弯针,一寸上三针半,走远路不易脱帮。大功告成,再上鞋摊钉了轮胎底的前后掌,耐磨。用剩下一块方布,裹成包袱一拎,从军、师、团、营,一路找到二连。见到了哥哥,要不是当着众人的面,“习惯成自然”早抓住哥哥两只粗手左摇右晃了。她当自己还是小姑娘哩。她放下棉鞋,问:“哥哥,我给你写了六封信,为啥没回?”朱光耀解释道:“剿匪,忙。停下来几天,要给同志们理发。”方文教从炉子上的水壶倒了碗滚烫的开水,递给朱光耀。朱光耀再递给他这位长不大的妹妹。转身向大家介绍:“我妹妹,刘芝兰,兵团野战医院护士。去兵团医院,找她。”方文教从小学到大学,男女混班,见了女同志,习以为常,并不紧张拘束,说:“阿拉去医院,还是兵团医院,真是‘霉头触到印度国’了。(上海话,极言倒霉的意思)不去,不去,哈哈,哈哈。”刘长法说:“‘张王李赵遍地刘’,你也姓刘,我也姓刘,你应该是我的姐姐,怎么会是他的妹妹?”朱光耀送走妹妹,回到房间,大家七嘴八舌问:“既然是兄妹,为什么一个姓朱,一个姓刘?”
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已经到了一个人人喊打但又不敢打的地步,我们中国站了出来。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要说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还是抗美援朝以后。
朝鲜战场上,据不完全统计,志愿军牺牲了142409人。抗美援朝的每一胜利都是志愿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每座志愿军的坟墓都是一部英烈传。长眠在坟墓中的烈士们,虽没有从他们的时代得到什么,但是他们的时代却因为有了他们而光辉灿烂。
多山的朝鲜蜂腰部,有一条由北向南的公路从三歇马岭盘旋而过。三面环山叫岙;四面环山叫谷。在峰回路转处,在高山深谷中有座孤坟,群山环绕,绿树成荫。几片淡淡的云,一溪静静的水,陪伴着坟中的志愿军对空监视哨排长朱光耀。他的短暂一生,以一名共产党人的优秀本色,让无数活着的战友铭刻于心,愈久弥坚。
1954年4月5日,朝鲜停战后的第一个清明节,青山滢滢,细雨霏霏,山谷开遍了白、红、粉、紫、雪青色的杜鹃花。带着水珠的花儿静默肃立。那些常跑三歇马岭的志愿军驾驶员,自发掬一捧野花,接踵前往坟前瞻仰祭扫,缅怀逝者,寄托哀思。革命军队中虽已养成“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的习惯,但往坟前一站,敬礼,献花,表达深切怀念之情,仍禁不住热泪滚滚。一位自称是朱排长未婚妻的年轻女军人,趴在坟前,失声痛哭,开始泪如雨下,而后泪尽眼枯。
烈士坟前,“清明时节‘泪’纷纷”。一早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美国政府就实行全面支持蒋介石进行内战的政策,仇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为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敌视中国人民,以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进占我台湾,对新中国形成新月形包围圈,企图将新中国扼杀于摇篮之中。1950年自8月27日起,侵朝美军飞机连续多次侵入我国东北领空,在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宽甸等城镇上空进行侦察和扫射、投弹。美国无视我国警告,悍然命令侵略军越过“三八线”,占领距离我国边境只有五公里的朝鲜楚山镇,用炮火轰击和机枪扫射我国领土,叫嚣“要把赤色的中国洗成白色”,把战争强加给我们。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中国人民与美帝国主义的一场军事较量是不可避免的了。1950年10月8日,毛主席命令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19日,从安东、长甸河口和辑安跨过鸭绿江。10月25日,志愿军在朝鲜云山地区的间洞南山、朝阳洞东南山和玉女峰一线,打响了震惊世界的抗美援朝第一枪。后来,这一天被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纪念日。
志愿军战士有首诗:“美帝好比一把火,烧了朝鲜烧中国;中国邻居快救火,救朝鲜就是救中国。”1950年12月,二连理发员朱光耀所在的部队奉命从蜀、黔剿匪第一线撤了下来,奔赴朝鲜“救火”。
过鸭绿江之前,部队在安东一带进行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三视”教育。一天,二连连部围坐在临街有玻璃窗的一间房子里,讨论“该不该打”和“敢不敢打”。窗上四块玻璃,每块玻璃用纸条贴成一个“米”字,以防敌机丢炸弹震碎玻璃。阳历12月,正值“大雪冬至雪花飞”,东北的十冬腊月滴水成冰。室内烧着炉子,炉子上放着水壶。水整天沸腾着,蒸汽既调节气温又保护易干燥的鼻子。此时,房内热气腾腾,讨论七嘴八舌。
连首长分头下各班参加讨论去了。连部讨论由文化教员方世觉、理发员朱光耀主持。文化教员,排级待遇,虽不带兵,也算一名干部。朱光耀,连部党小组长。连队党支部工作一般按照“先党内后党外”的次序,党员领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支部决议的精神与要求,要比群众全面些、透彻些。只有党员自己思想先进,才能走在群众前面,率领群众同心同德完成上级所给予的任务。因此,凡连部司号员、卫生员、通信员、运输员文书等“七大员,八大员”开会,朱光耀就是负责人之一,相当于连部的“小政委”。由于人民军队的性质决定,旧社会统称的伙夫、马夫、挑夫、剃头匠,人民军队里改称炊事员、饲养员、运输员、理发员。尽管部队中有上下级和职务分工不同,最高的司令员、政治委员,最低的司号员、卫生员、通信员等等,都是对共同的革命事业负责。家族分祖、父、同、儿、孙五辈,军队内部都是同辈,指挥员和战斗员,都是 “员”字辈,都是人民勤务员,都有同样的光荣,在政治上和人格上一律平等,互相之间只有革命同志关系和工作关系,称呼没有尊贵与卑贱之分。
朱光耀理发是向他父亲学的,他父亲理发是向他外公学的,在家乡算得上“三代名剪”。在连队推、剪基本上无用武之地,一把剃刀,半个月内刮一百三十五个光头、十八个络腮胡子。把批评说成“刮胡子”,那是比方。朱光耀手中那把刀,除了司号员“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用不着刮,其余的上至连首长,下至“八大员”,只要时间允许,一月刮二次胡子,谁也不能例外。
社会上卖鸡毛揮子、修鞋、剃头“三不吆喝”。农村理发店是当地的“新闻中心”,顾客等的无聊,嘴巴没有地方安排,在那里发表高论、交流信息。但理发老师总不能扳着顾客的头,呱啦呱啦唾沫星乱溅,再说工作一走神,弄不好给人头上划道口子,惹事。所以只听不说,习惯成自然,朱光耀不爱说话,更不爱吆喝。同样下蛋,鸡叫鸭不叫。他从小受过他父亲严格训练,先替冬瓜刮霜、南瓜刮皮练腕子,练就的“刀功”,不论大、小、阔、扁、圆,头型各异;不论方、圆、梨、菱等七种脸型,理发修面,顾客光听到“割草”的声音,用不着担心。朱光耀像队列操似的练姿势。三分天赋,七分磨练,他理发的姿势很优美。他中等身材,四肢匀称,五官端正,皮肤光滑微黑,配上一双贼亮贼亮的眼睛,显得格外有精神。左上眼皮有指甲盖那么大一个疤,“瑕不掩瑜”,仍不失为一名标准军人。
连队在一个地方一住下,朱光耀端上一张凳,挂上咖啡色的搪刀布。他两腿直立,自然分开,一脚向斜前方伸出,另一脚与身体平面成直角,近似队列动作“稍息”;身体直立,胸部微挺、收腹,腰部自然挺直,两眼平视,又像队列动作“立正”。在实际操作中,不断调整站立位置和轮换双脚姿势。“轻磨重搪紧扒皮”,技术和艺术相结合。他持剃刀的手腕灵活、柔软、稳当、有力,无论正手刀、反手刀、推刀、削刀、滚刀,上下左右,往返快慢,恰倒好处,技巧娴熟,动作迅速。人家一小时剃六个光头,他剃七个。平常时候,他喜欢将十八名络腮胡子安排在星期天上午一次性解决。这时文化教员方世觉、司号员刘长法都会帮忙。刘长法捂热毛巾。方文教熟练地将胡刷放在热水碗里浸泡,拿起、排出过多的水,在肥皂上来回搓磨,然后在需要刮剃的部位画圆圈,从下巴开始,逐渐移动到两腮,而后是上唇与鼻子之间涂肥皂沫。朱光耀拿刀从右鬓角入手,面颊、嘴唇,直到颈部,顺刮逆剃,动作细致,不留“死角”。三人流水作业,十八个“刺猬”,经三个小时“修理”,变得容光焕发。
朱光耀有时也向刘长法学吹号。方文教在油灯下坚持给他们俩“开小灶”,教他们多识几个字。他们三人间,官兵关系、党群关系、知识分子与工农分子的关系,十分融洽。想不到这天讨论“敢不敢打”时,方文教与刘长法吵得面红耳赤,难解难分。起因就是方文教的发言。方说:“朝鲜战争,是一场弱国与强国的较量、武器装备落后的军队与技术装备先进的军队的较量。一部美国历史,就是一部靠战争开疆拓土、发家致富的历史,每次战争推动美国经济往上窜,美军装备往现代上‘化’,二战使美帝成为独一无二的经济巨无霸,其海军和空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技术装备上,堪称世界第一。陆军是一支具有高度现代化的诸兵种合成军队,一个军就有各种火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一个军只有三十六门。每个师有坦克一百四十多辆,而我们一辆也没有,基本上我们还处于‘小米加步枪’的阶段,与美军相比,优劣悬殊。美帝还拥有杀伤力很大的原子弹……”听着听着,刘长法站起来坐下,坐下又站起来。“暧,暧,你是不是杜鲁门派来的?杜鲁门一个月给你多少钱?”未等方文教分析我军的政治优势、人的因素优势、战术优势,他早憋不住了,直着嗓子大喊。
司号员刘长法,自小就没了爹娘,由奶奶拉扯四处讨饭。后来奶奶也死了。糠菜不糊口,乞讨无路走,在那个世道讨饭也不容易,一天下来三尺肠子闲着二尺半。十二岁那年,国民党曹福林的整编第五十五师路过他家乡,他当了一个排副的勤务兵。在旧社会,老百姓称国民党的空军是“少爷兵”,海军是“流氓兵”,陆军是“乞丐兵”。国民党陆军层层克扣军饷,一年多来,他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饿急了,石头都想吃。鲁西南战役,1947年7月8日把他解放过来,才十三岁。当了俘虏,第一顿饭,没有顾得上夹菜,半斤重的白面馍馍,吃了三个,鞋带开了,也弯不下腰系。解放军看他又瘦又小,发路费要他回家。人家话还没说完,他眼泪哗一下流了下来,大声哭道:“从娘肚出生以来,第一次尝到饱的滋味,就叫俺回家。”解放军也是穷苦岀身,一看这场面,说:“小是小了点,是棵好苗,看谁要?”卫生队的军医带上调剂,挑护理员、卫生员,第一批没挑上。第二批挑通信员,也没看上,把他急得直哭。越哭越没人看上。第五批团里的号长带上三个营的号目挑司号员,真是有缘,第一眼就看好了他这个“小鬼”。
号长问:“小鬼,愿不愿学吹号?”他用左手袖子擦了眼泪,再用右手袖子擦了鼻涕,连忙说:“只要不让俺回家,吹啥也愿意。”不知谁说了句:“‘吹牛’愿不愿意?”他答:“吹牛就吹牛。” 引起一阵哄笑。
军号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曲谱简单,易于掌握,是一种传达军令的通信工具。红军初创时期就有司号员。两军厮杀,军号可以号令三军,鼓舞士气,震撼和迷惑敌人。小小军号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营号目是位“伯乐”,向号长要求:“这个明明推光头偏叫留长发(刘长法)的给我们一营。”别看刘长法大字不识一个,但他“心有灵犀一点通”,不管号目用“逃、来、米、勿、少”简谱,还是用“合、食、一、让、吃”的工尺谱,只要是号谱一点就通,一记就牢。军号是由铜合金制造的,金光灿灿。有号嘴、号身、号碗、连接箍,形同乐队的小号,但无阀键。他原先只摸过一次唢呐,手背还被吹鼓手狠狠打了一掌。军号,不用说吹,就是摸也没有摸过。他不枉是军号“千里马”,一教就会,一练底气十足。千里跃进大别山,他跟在号目屁股后面,“教养一致,学用一致”,边行军边练习吹号。他吹的军号响亮而不走调,已经能按规定的号谱和号音传递命令和识别敌我了。
1947年10月,刘长法走马上任到二连当司号员。号目像嫁闺女似的,精心挑选一把军号,以便“小鬼”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号目思忖:单圈管号声音宏亮,通信距离较远,吹奏费力。双圈管号声音清脆,通信距离较近,吹奏省力。他人小肺活量有限,正式发给他一把双圈管军号。他双手接过军号,有一种使命高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的感觉。他用一根非常漂亮的绶带系在军号上,从左肩斜挂在右侧,军号闪着金光,红色飘带迎风招展。传达号令时右手将号嘴放在唇上,运用丹田之气鼓起腮帮,嘀嘀哒哒“振聋发聩”,声震旷野。他吹:“值星排长,催诸位起床,诸位还在床上——”这是起床号。
“大米干饭白菜汤,大米干饭白菜汤”,这是开饭号。
“戴连长,各排长,点点名,查査看——”二连长姓戴。这是晚点名。
行军,全连走得气喘吁吁,忽听他用军号告诉大家:“走不动的慢慢走,走得动的不要走——”大家听到休息号,原地坐在背包上休息,掉队的慢慢跟上。
在硝烟弥漫、枪声大作的战场,听到他急促的军号声:“嘀哒得嘀嘀嘀,嘀哒得嘀嘀嘀——”,战士们上好刺刀,跃出战壕,高喊着“冲啊!” “杀啊!”勇往直前,向敌阵冲去。他的冲锋号,使战士热血沸腾,使敌人胆战心惊。战士们听他的军号行动。野战军司令员姓刘,他也姓刘。司令员,司号员,只差一个字,战士们干脆把他改称为“司令员”,为了有别于刘伯承司令员,大家亲热地叫他“小刘司令员”。
他一米六的个头,瘦瘦的,没事站着喜欢抓耳挠腮,战友们说他像猴子,没进化好。他有很好的体力和耐力,有一股坚忍不拔、奋不顾身的内在气质。他虽然只有十六岁,却是一位经过多次真刀真枪磨练的老资格,是连里的战斗骨干。他一根肚肠通到底,挖出心来见得天。他学文化,底子差,吃了不少苦头。方文教给他鼓劲:“文化的根是苦的,但他的果子是甜的”,“葡萄是一点一点成熟的,文化是一天一天积累的”。他一听急了,说:“方文教,以后上课,能不能不用‘果子’、‘葡萄’这些可以吃的东西打比方?人家听了哪有心思听你讲课。”自从连里来了方文教,他努力学习文化,连里第一批摘文盲帽,其中就有他刘长法。
在他小小脑袋瓜里,有种思维方式,把自己的国家的可爱当作强大,把自己的部队看得比友邻部队能征善战,而说到二连他更是翘起大拇指,用上了从方文教那里学来的一句上海话:“一等那姆嗨”。团里司号员集中活动,人家问他:“听说你们连长讲话‘三句半’?”他就告诉人家,那是“简单扼要,水平高。”人家又问:“你们指导员讲课大问题套小问题,挺罗嗦的?” 他剋人家:“你懂什么,讲道理就是要掰开揉碎耐心启发战士觉悟。”说到文化教员,也是他二连的最棒,“比祁建华强”。“速成识字的教学方法,借助汉语拼音字母当拐棍,我们解放军个个都是飞毛腿,要那‘拐棍’干啥?”他不说方文教不会汉语拼音,而是硬说扫盲用不着汉语拼音。理发员也是自己连的好,一个小时多剃一个头,“哪像你们连的理发员,‘剃头不用刀,一根一根往下薅。’生薅硬拔,把别人的头扳过来推过去。我们二连的朱光耀是围着别人转。”就是自己炊事班蒸的馒头,也比人家的大。全连上下谁都知道他是一个不折不扣“胳臂往里拐”的人。他这种秉性,哪能听得方文教把中国说成“弱国”,把美帝说成“强国”、“世界第一”?战友们说他像猴子,他这会儿就成了 “翻脸猴子”。他先给方文教扣了一顶帽子,然后接着说:“装备好有什么了不起,蒋介石装备好,也不过给我们当运输大队长。你帮人家吹,吓唬谁?”知识分子就是历史上的“士”,正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方文教今天被自己的学生“无的放失”、“噼里啪啦”噎嗓子的话顶得喘不过气来,气得他七窍生烟,投五投六地说:“说我是杜鲁门派来的,你、你、你才是自己跑到国民党里打共产党。”“嗳,嗳,谁不晓得我在国民党部队里是勤务兵,端洗脸水的……”“端洗脸水,端洗脸水伺候反动派,洗了脸,打共产党有精神。”方文教觉得还不解气,用上海话嘟嚷了一句:“不等阿拉话说完,侬来搅啥个百叶结(胡搅蛮缠)”。
卫生员、通信员、运输员都批评方文教立场有问题,文书则批评司号员断章取义、乱扣大帽子。人虽少,大家抢着发表看法,中间搀杂着方文教与刘长法的唇枪舌剑,乱成一锅粥。房间里的水蒸气似乎不是从炉子上的开水壶中冒出来的,而是从大家嘴里说话带出来的。
这时党小组长朱光耀说话了:“一位老同志、一位文化教育干部,讨论问题像吵架,锣对锣,鼓对鼓,自由发言变成了互相攻击。讨论,要摆事实,讲道理,谈认识。争论要把焦点放在指导员布置的题目上,不要针对个人。”别看他平时三砖打不出一句话,关键时刻,讲起道理来却是一套一套,战友们戏称他说话“恕不零售”,“专营批发”。
部队“一切行动听指挥”,有铁的纪律,但民主作风特别好。官兵一致的原则就是军队内部团结一致的原则,其实质就是军队中的民主精神,就是全体人员在政治上的一律平等。人人都有主人翁的责任感,才能使上下级之间、党员与非党群众之间、新老同志之间、工农分子与知识分子之间互相关心、爱护、尊重、帮助,达到亲密团结,使连队具有坚强无比的战斗力。
刘长法不愧人叫“小刘司令员”,他接过朱光耀的话茬,说:“俺刚才那番话,屁股没坐在凳子上(出了原则的意思),‘走了火’,请方文教原谅。不过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只要一提美帝国主义就来气,手上拿两个破原子弹吓唬人、欺负人。”说着又问方文教:“实话实说,你怕不怕美国佬?”“怕死不当兵。”方文教边翻笔记本边说:“我是上海人,因为日本鬼子侵略,八岁那年,随父母‘厂矿内迁’到重庆,上海复旦大学、商务印刷厂也移设重庆。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五年半时间,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政略轰炸’、‘无区别轰炸’、‘地毯式轰炸’、‘地狱式轰炸’。‘咣——’‘咣——’剧烈的爆炸声震耳欲聋。1939年5月3日、4日两天,63架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投下炸弹176枚、燃烧弹116枚,炸死我们的同胞3991人,炸伤2287人,炸毁房屋4871栋。重庆的老百姓居无宁日哪,阿拉方觉世是在日本炸弹爆炸声中长大的。唉,怕有何用?”方觉世,上海人,1937年随父母逃日本鬼子,定居重庆,在重庆大轰炸中读完小学,重庆解放正在上大学一年级。他对中国文化有很浓的兴趣。章太炎说做学问有两种:一是求是,二是致用。他学习追求“致用”与“求是”。1950年1月参军,分配二连当文化教员。1949年,新中国的文盲占80%,二连的文盲占74%。他有雄心壮志,筹划着全连文盲一、二年内能认2000常用字,会写200—300字的应用文。中国文字愈来愈多,秦《仓颉篇》仅3300字,东汉《说文解字》增至9353字,明代《字汇》已有33179字,1915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多达48000字。他下了一番苦功从48000字中挑选出2000常用字。他苦于自己没有学过汉语拼音,在识字教学上不能利用这个行之有效的拐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教识字按汉字构造: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一个字一个字教。象形,象形,象实物之形。他教“日”、“月”,先画太阳、月亮。会意,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字组合在一起,表示一个新的意思。三人为“众”,三木为“森”,三水为“淼”,“上不上、下不下,卡住了”,四方木为“楞”。汉字80%是形声字,“饭”、“馍”、“饺”、“饼”、“枇杷”、“番薯”,讲得直吊刘长法的胃口。待大家认得500字以上,他采取“分散识字”法,把下一步应当学会的字,有计划地分配在自己编的课文里。他没有进过师范,不懂得教育学、教学法,但他的文化基础扎实,学识渊博,反正扫除文盲是一项群众性工作,学习时间由连队统一安排,“能者为师”,识字的教不识字的,不拘一格,因人施教。他培养了许多“小教员”,包教包学。教识字,形、音、义,读、写、用一丝不苟,二连扫盲进度在全团中上水平。1950年8月1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决定全军自1951年初起,在三年之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由于1950年10月开始抗美援朝,迫使这一教育计划没有实施就予以“推迟”,因此,他只能“见缝插针”扫盲。
大学一年级,也是大学生。方觉世这位大学生在连里当文化教员,是稀有元素。部队从剿匪转为抗美援朝,面对美、英、加、澳大利亚、菲律宾、南非等众多说英语的“联合国军”,迫切需要英语翻译。群工科相信“兵上三千出韩信”,以为在大学生中找翻译不是一件难事。找方觉世面试。方觉世读过英语,但他是一位喜欢就学,不喜欢就不学的人。他不喜欢英语,喜欢中文。他认为中文无字型变化之累,无定形文法之弊。英文是一种含糊的语文,像他这种不圆通的人,注定翻译不好具有含糊特性的文字。中文远胜英文简洁,他有理由学不好英文。他在高三做英文作业,翻着华美词典,累得满头大汗,把“我仍旧一无所知”误译成“我不比以前更聪明”,“她是一个朴素的女人”误译成“她是一个家庭妇女”,“我十分迷惑”误译成“我完全错了”,十道题错了九道半,而汉语作业十道题对了九道半。学了那么多年的英文,能使他记住的单词属于两类:一类是学了之后用于调侃的,“‘法石’(Father父亲)、‘买石’(Mather母亲)敬禀者,儿在校中读‘鲍克’(Book书)”,他仅记住了“父”、“母”、“书”三个英文单词。“我骂先生‘讨天四’(Tortoise龟),先生骂我是‘道格’(Dog狗)”,又记了“龟”、“狗”二个单词;另一类是与上海话搭上关系的。上海闲话“钞票多得来麦克麦克”,英语“麦克”(Much)是很多的意思。上海话“混枪势”的“枪势”,音译自英语中的Chance(运气)。开在小阁楼上的天窗,上海话叫“老虎窗”,与老虎没关系,而是从英语Roof(屋顶)中直译过来的,他至死也不会忘记英语中的“很多”、“运气”、“屋顶”这些词。除此之外,“科长同志,我学英语是‘王伯伯’(上海话嘲讽健忘者),对不起,还给老师了”。至于那些揭露敌人丑恶面目,宣传我们的政治主张,启发敌军士兵的觉悟,破坏敌人战斗力的英语,对他来说可以用四个字形容:“一窍不通”。就是战场上常用的“放下武器”、“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几句话,还是他刚从一连文教那里学来“现炒现卖”的。不是谦虚,方觉世认为自己的英语水平,是“王胖子的裤腰带——稀松。”他向群工科科长明确表示:“不愿‘滥竽充数’。”那时知识分子参军,“自报家门”,自报家庭出身。他父母是“白领”,国民党工厂的高级职员。职员在阶级成分上有点暧昧,虽然没有生产资料,但也没有参加体力劳动,他在“家庭出身”这一栏,钢笔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最后横下一条心填上一个“小资产阶级”。他在师里参加学习《社会发展史》,知道“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猴子变人,劳动创造人。重庆解放不久,市面上就有了“劳动布”。他就是脱下麦尔登上衣、凡立丁裤子,穿上劳动布新工装来参军的。通过学习增强了劳动观念。他明白一个道理:正确的世界观是在劳动中确立的。他下决心:这辈子,要用自己的脑力、体力劳动改造世界。他积极要求下连队。他教战士识字造句:“劳动人民”、“劳动成果”、“国际劳动节”、“劳动光荣”、“好逸恶劳”、“不劳而获”。他参加劳动大汗淋漓、两手血泡。他不是担心自己不劳动变回去,变成猴子,而是要通过劳动,奉献自己的青春,使自己变得更崇高。他与战士打成一片,把根扎在连队,与战士同呼吸、共命运、心相连、情相通。他与刘长法、朱光耀成了莫逆之交。刘长法坚定、勇敢、勤劳、爱说爱动,朴实中带有几分天真,嫉恶如仇,许多优点,值得自己学习。此刻,他后悔自己不该对刘长法生气、发火、挖苦。如今全军上下一听美军越过“三八线”,扩大侵略战争,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上前线,在这种氛围中如有人怕美军、怕原子弹、怕苦怕战,认为到朝鲜打仗是“多管闲事”、“引火烧身”,岂不自找不自在?老军长就承认自己看不起美国人,说“朝鲜多大个地方?在‘三八线’尿泡尿就能滋到釜山去。”人称“疯子军长”。彭总却夸:“那是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乐观主义的战士讨论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那真有点“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的味道。
连部学习告一段落,方文教给“三视”教育作小结:我们深受日本鬼子侵略之苦,不愿再受二茬罪;“唇亡齿寒”、“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保卫东方和世界和平,是我们人民军队的国际主义义务,该打。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政治上赢得中朝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军事上,我们有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的传统,而且善于近战、夜战、山地战和白刃格斗,以己之长,制敌之短;“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认清美帝国主义虚弱的本质,师出有名,师直为壮,敢打必胜。
方文教“敢打”二字刚出口,席地而坐的刘长法一跃而起,嘴里喊着“方文教讲得好,呱唧,呱唧”,两手举过头顶,带头鼓起掌来。
“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这个毛主席早年论断,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树立不怕一切困难敢于胜利的精神起到了巨大作用。全军的战斗热情被调动起来了,士气高昂。
还没宣布散会,有人敲窗户,嘭,嘭,嘭,嘭,敲得既急又重,幸好玻璃厚,没被敲碎,像有什么紧急军情似的。谁?玻璃上结着厚厚的冰花,看不清。“针眼大的洞,牛头大的风”,为了保暖,除了炉子烟囱拐了个弯通向室外,整个房子捂得严严实实,隔音。窗外的人叫些什么,含含糊糊,谁也听不清。一撩棉门帘,进来一位女军人,用高八度的嗓音,冲着朱光耀喊:“哥哥”。
她是给她的哥哥送棉鞋来的。有人说:东北脚长,西北脚厚,山东脚肥,广东脚窄,温州脚瘦,昆明脚小,唯独她哥哥的脚怪。从小到大没穿过几双鞋,一出门把鞋别在腰带上,赤着脚四乡八邻跑,没有鞋的约束,脚板扁平奇大,且茧疤密布,踏冰霜不知冷,踩炭火不觉烫,大步流星走在有角有楞的碎石上,没有疼痛的感觉。他穿的鞋,只有她和他妈做才合脚。她听十三兵团的同行说,朝鲜战场第一、二、三次战役,志愿军冻伤多,特别那双脚。她与她的哥哥一个兵团。兵团要入朝参战,没有合脚的鞋,她担心冻坏她哥哥的脚,熬更守夜突击做了一双絮了一斤新棉花的棉鞋。袼褙是家里带的。跑遍了毛泽东大街和斯大林大街凑齐一切材料。她用九股麻纳出这又厚又结实的鞋底,断了四根大号针,锥子扎了自己十八个窟窿,白鞋底成了“血染的风采”。上鞋弯针,一寸上三针半,走远路不易脱帮。大功告成,再上鞋摊钉了轮胎底的前后掌,耐磨。用剩下一块方布,裹成包袱一拎,从军、师、团、营,一路找到二连。见到了哥哥,要不是当着众人的面,“习惯成自然”早抓住哥哥两只粗手左摇右晃了。她当自己还是小姑娘哩。她放下棉鞋,问:“哥哥,我给你写了六封信,为啥没回?”朱光耀解释道:“剿匪,忙。停下来几天,要给同志们理发。”方文教从炉子上的水壶倒了碗滚烫的开水,递给朱光耀。朱光耀再递给他这位长不大的妹妹。转身向大家介绍:“我妹妹,刘芝兰,兵团野战医院护士。去兵团医院,找她。”方文教从小学到大学,男女混班,见了女同志,习以为常,并不紧张拘束,说:“阿拉去医院,还是兵团医院,真是‘霉头触到印度国’了。(上海话,极言倒霉的意思)不去,不去,哈哈,哈哈。”刘长法说:“‘张王李赵遍地刘’,你也姓刘,我也姓刘,你应该是我的姐姐,怎么会是他的妹妹?”朱光耀送走妹妹,回到房间,大家七嘴八舌问:“既然是兄妹,为什么一个姓朱,一个姓刘?”
相关地名
瓯海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