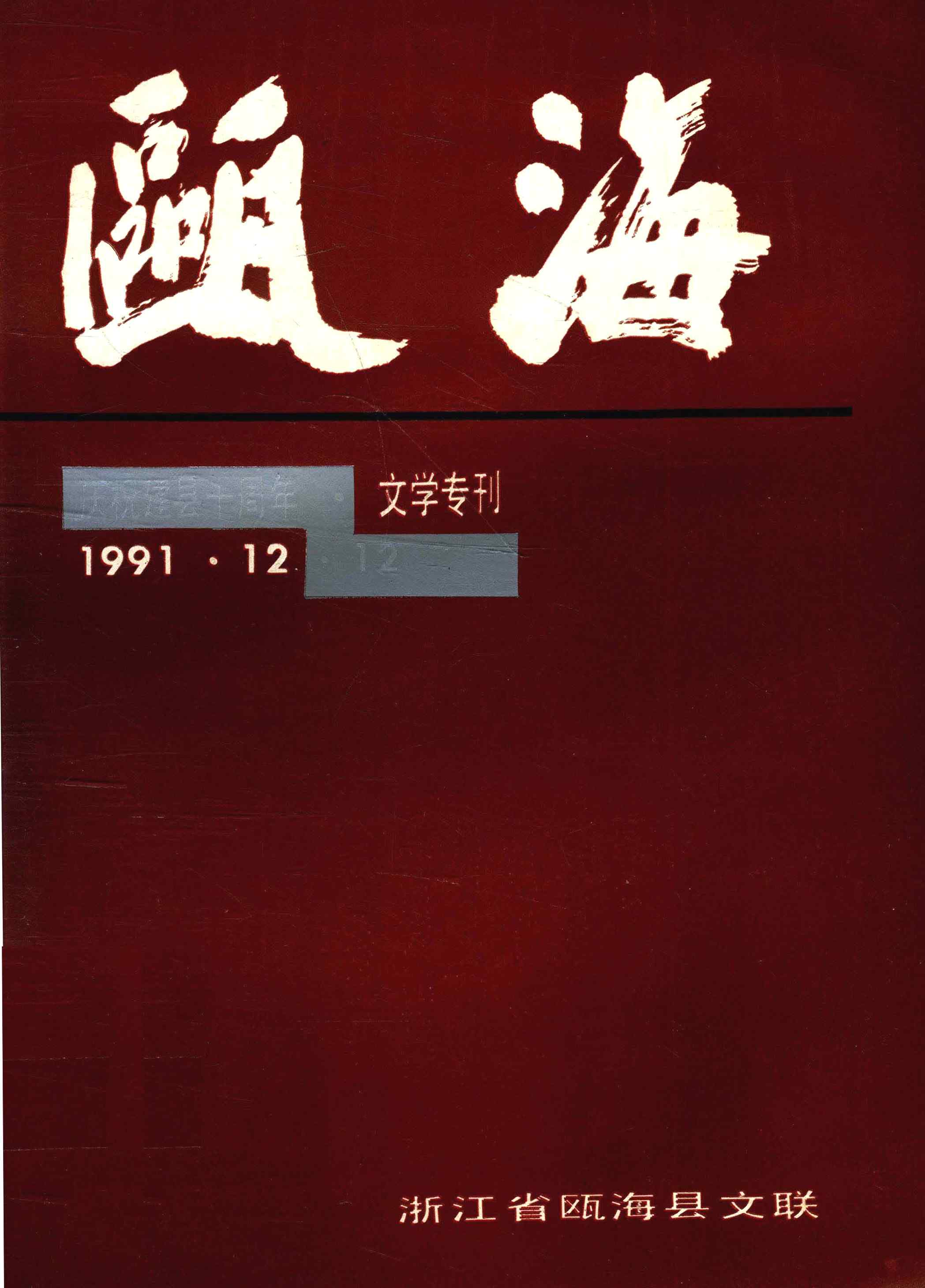内容
郭斌的路
(长篇小说《岁月烟云》节选)
1
1948年秋天。国共两党在长江南北两岸,各自陈兵百万,一时间大江上空战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
长江南岸S镇。
秋风萧瑟,尘土迷蒙,街面冷落,行人稀少,一派兵荒马乱景象。
四五辆载着人和行李家什的马车,先后飞驰过街道向南奔去,车尾卷起了一片黄色尘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一些为避战乱的富裕人家。
远方传来“得得”的马蹄声。一个身材高大的军官骑着棕色的骏马沿着街面逡巡而来,身后跟着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卫兵。
在一个卖日用杂品的地摊面前,军官勒住马首停下。他朝着地摊上的手杖看了半晌,问摊主:“这手杖多少钱一根?”
摊主郭斌答:“长官,这是盐城产的手杖。你看,都是柏树做的,质地坚硬,上等货呐。”
“多少钱一根?”军官问。
“六万块一根。”
军官问:“你这里共有多少根?”
“六十三根。”
军官说:“不够!我要一百根。”
郭斌迷惑不解地问:“要这么多干什么?”
“别噜嗦!这是军事秘密,你问这个干啥?”站在旁边的警卫兵训斥道。
郭斌吓得连声说是。他指着不远处的小木屋:“长官,你等等,我马上去拿。”
“慢!”军官瞟了一眼这个四十多岁的摊主,想了一问:“听你的口音好像是澄州人?”
郭斌答:“是,是澄州西岙人。”
“为什么到这儿来干这营生?”军官威严地问。
“这……在家乡生活不下去,到这里摆地摊卖些日用品维持生计。”郭斌垂着两手毕恭毕敬地回答。
军官思忖了一下,对身后的两个警卫兵说:“先付他五十万定金,下午你们来拿手杖。”说完一拉马缰绳,飞驰而去,街路上扬起了一片尘土。
郭斌为一早就做了笔大生意感到喜出望外,接过定金,满面笑容对警卫兵连声说:“长官您走好。”
到了下午,两个警卫兵来了,说:“我们团长要你把手杖亲手送到团部去。”
郭斌忐忑不安起来了:不是说好下午由警卫兵来取手杖的吗?怎么变了要他自己把手杖送到团部?他想起几天前就有个士兵到他地摊上买了六七张椅子不给钱,向他讨钱反而被揍了一顿。莫非今天又……他望了一下眼前两个铁青着脸不容说话的警卫兵,只得说:“长官请等下,待我把地摊上的东西收拾一下……
郭斌将地摊上的东西搬进屋子里以后,怀着懊丧和不安的心情,肩挑手杖跟着两个警卫兵走进了团部。他见到团长放下肩上的手杖后,立即返身就往回走,他怕如果要手杖的钱会挨揍,吃不消。
这时,团长开口了:“怎么啦,不要钱就走?”声音是温和的。
但在郭斌听来这是官场上的套话,你要是真的向他讨要钱,他就马上变脸,要手下人揍你。郭斌恭敬地说:“不,这点手杖就算是小人孝敬给长官们……”
团长笑了:“哪能买了末事勿给钞票?又麻烦你老远的送了过来,总得坐一下歇歇力嘛,来人,给他送茶。”团长说的是澄州方言,郭斌奇怪了:难道团长也是澄州人?于是,他也用方言问:“你阿是澄州人?”
团长点了点头:“我叫陈琪,澄州北岙人。”
还有什么比千里之外遇到同乡感到亲切呢。郭斌内心涌动丝丝温暖,顿时感到与团长的心贴近了。他说:“真凑巧啊,你住在北岙我住在西岙,原来我们住得恁近,只隔一条溪呐。少年时候,我到门前坦小学读书,是扎起裤脚踏着碇步走过去的,溪水时常把我的裤脚打湿。尤其是雨后,碇步很滑溜。有一次我滑跌在溪水里,连书包都打湿了,回家让父亲骂了一顿……”说起故乡和少年趣事,他没完没了。
站在旁边的两个警卫兵傻了眼,他们除了团长说的“来人”“送茶”这话听清楚外,其他的一点也听不懂,他们还以为团长与郭斌是在讲少数民族的地方方言呢。
待郭斌喝了茶,团长又问他叫什么名字,读过书没有?共读了几年书?在镇上摆地摊赚钱多不多,生活过得怎么样?郭斌一一作了回答。最后团长问他,愿意不愿意在这里当兵?。
郭斌想:摆地摊确实也难赚钱,可是要他当兵心里又不愿意。老百姓恨死了国民党的兵,为了逃避抽壮丁他才到这里来摆地摊谋生糊口,现在团长问他要不要当兵,他心中一时拿不定主意,便推说回去想好了以后再定。
这时,一个副官模样的青年进来报告:“团长,老人们都到齐了,就等你去。”
“好,我马上就来。”团长说。
2
团部的大院里站着一群须发霜白的老人,他们不知道团长为什么突然叫他们来到团部,大家心里不安的挤着站在一起。陈琪理解他们的心情,走到一位老人面前,亲切地叫了声:“老大爷,你好,今天我请你来团部玩玩,是想请你帮我办件事呐。”说着递给他一根手杖。接着,他又热情地说笑着发给每个老人一根手杖。老人们这才宽下心来。
陈琪给老人发了手杖后,站到团部大院的台阶上高声喊:“来人!把那个强买东西不给钱还打了人家的家伙带过来!”
话音刚落,两个彪形大汉押着个捆绑着的士兵走过来。
陈团长威严地宣布:“罚打一百军棍,禁闭两天。”
彪形大汉当场按着那个士兵趴下,举起扁担狠狠的打,没多久就打得这个士兵屁股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行刑毕,彪形大汉将扁担靠在墙根,扁担钉上还挂着片沾满殷红鲜血的皮肉。
打完违犯军纪的士兵后,陈团长向老人们拱手作揖说:“父老乡亲们,我陈某人奉命到贵地驻防,军纪不严。手下士兵横行霸道,骚扰乡里,干了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我在这里向大家道歉了。”接着他高声宣布:今后你们如看到士兵横行霸道,就用我给他们的手仗尽管打他,扭送他到团部,我陈某人一定严惩不贷,决不食言!陈团长的最后两句话声如洪钟,震耳欲聋。说得老人们敬仰不己,脸上露出了笑容。
郭斌目睹陈团长严办违犯军纪士兵的经过,尤其看到扁担钉上挂着的那片触目惊心的血淋淋皮肉,心里感触很深。回到小木屋内,心里想:要不要去团郭当兵呢?看来这个团长与国民党有的军官不一样。自己在镇上摆地摊也难以维持生计,不如暂时去当兵混口饭吃。陈团长是同乡人,对自己好便罢,不好相处的话找个机会开小差。想定之后,第二天到团部对陈琪说:“我愿意在这儿当兵。”
就这样,郭斌参加了国民党军队。
在陈琪的团部里,由于大战迫在眉睫,充斥着紧张、恐怖的气氛,同样是派兵荒马乱的景象。
郭斌当兵后,陈琪见他为人老实,且有点文化,又是同乡人,遂有收为心腹之意。便委任他为团部庶务长,经过一段时间考察,改任侍从参谋,不久,提升为一营一连连长。
翌年四月廿日,国民党反动派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长江北岸百万解放军即将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渡长江。廿一日傍晚,郭斌突然接到陈琪命令,要连长以上军官紧急集中团部开会。他走到团部,看到岗哨密布,警卫班战士手拿张开机头的驳壳枪,气氛异常紧张。预感到将有重大事件到来,心理上做好了准备。
陈琪见连以上军官到齐,便宣布会议开始。他两手拄在会议桌上,用冷静、沉着的语音分析了长江南北形势,江防部署,以后庄严地宣布:“现在我命令:全团起义!谁不同意可发表意见。”这时,站在他身旁的团参谋长忽地拔出手枪指着陈琪说:“你想反水,我毙了你!”只听见“啪”的一声,说时迟那时快,团参谋长应声倒地,污血喷射到会议桌上,浸红了一大块台布。
原来陈琪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早已掌握参谋长是师部暗地安插在团部的特务,开会前已作周密安排,不等他开枪,警卫战士抢先动手杀了他。陈琪环顾了一下四周,说:“同意或不同意起义的都请发表意见。”郭斌从腰间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说:“国民党反对派腐败透顶,我赞成全团立即起义。谁不同意,参谋长就是样子!”这时,全团所有连级以上军官都表示没有异议。
于是,陈琪拿下头上的军帽,摘掉青天白日帽徽,将它摔到地上。立即发布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在今晚渡江攻占南京,全团战士要配合作战,保证解放大军安全渡江!……”
3
南京解放后,陈琪担任了K县军管会主任。郭斌任后勤处处长。生活开始安定起来,他想起了家,想起了妻子和子女现在生活到底怎么样了?儿子郭明参加工作了没有?尤其是到了星期天,当地的工作人员都回家和亲人团聚,他心里的这个愿望就更加强烈了,他想请假回澄州一趟看望妻子和儿子郭明。这天,郭斌伏案午睡,朦胧中游览九华山,混混沌沌,虚无飘渺间,一老者飘然来到面前,老者童颜鹤发,银髯飘拂,风度睿智,慈祥可亲。郭斌知是非尘世中人,遂求问养生长寿避祸消灾之道。老者曰:“大道轮回,周而复始,生死荣枯,天命已定。”言毕,隐入云雾而去。
此后不久,一日,两名公安人员突然来到郭斌面前,问清楚姓名后宣布了逮捕命令,给他套上锃亮冰冷的手铐,押解到法院审判,这时他才知道事情突然变化的根源。
原来陈琪在起义以后,解放军收编了他下属的国民党军队。但一营三连的连长是原先团参谋长的亲信,当时伪装起义,后又叛变,在枪杀我们党派去的连队指导员后下海投敌了。于是情况变得错综复杂起来。人民解放军保卫部门对起义人员进行了甄别审查,清除混入革命队伍的反革命份子。
某师保卫处对陈琪进行了甄别审查。保卫处汪处长问陈琪:“部队收编后,那天是你送指导员到三连的吗?”
陈琪说是。
汪处长又问:“指导员到三连时,你对原来的三连连长说了些什么话?”
陈琪臁:“我说指导员是上级党委派来的,你要尊重他的意见,服从党的绝对领导。”
“当时三连连长他怎么说?”汪处长接着问。
陈琪说:“他说欢迎指导员来三连工作,保证服从党的领导。”
汪处长说:“你对三连连长就说了这些话?”
陈琪说:“就这些话。”
汪处长严肃的说:“不对,据有人反映,你将三连连长拉到旁边又悄悄地说了些话。有没有这件事?说了些什么话?”
陈琪想了一下说:“哦,我记起来了,确有这件事。”
汪处长说:“你同三连连长悄悄地说了什么话?”
“我对他说,解放军纪律严明,你喜欢嫖妓,今后不允许你再弄。”陈琪说。
汪处长说:“按你这样说,你是没有说过指使三连连长叛变的话喽?”
陈琪说:“我以党性保证,绝对没有说过半句唆使三连连长叛变的话。”
汪处长说:“可现在的事实是,三连连长在枪杀指导员后下海投敌了。有人反映是你陈琪指使的。”
陈琪指着胸口说:“我再次以党性向你保证,绝对没有此事!”
汪处长说:“有人反映你的党籍是假的。此事我们正在调查中。”说着,汪处长走出了办公室。
对陈琪审查的事,因三连连长已下海投敌,无人证明当时陈琪与三连连长的讲话内容,这事成了重大疑点。加以陈琪是否系我党地下党员也无法证实。因为这时,解放大军在突破“长江防线”占领南京后,后续部队早已纷纷南下。陈琪一时找不到地下党单线联系的上级,保卫部门按照“有罪推定”的规定,认为陈琪系伪装起义混入我军的反革命分子。陈琪遂被人民政府抓了起来,全团因此案而被株连的达一百多人。
郭斌也被株连。并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判刑五年,押送江西某地劳改。当他手里拿着判决书时,想起了解放前为逃避抓壮丁,连夜逃离澄州老家。后来跟着陈琪起义,原以为是走上了光明的道路,谁知转眼间竟变成了反革命,今后还有何面目去见妻儿和澄州父老父亲?但是,当他想起梦中老者之言,知道这是劫数,不禁长吁叹息:在劫难逃,在劫难逃啊!
红花树
杨菊英
梁三送走了哥哥德旺。德旺哥要上省城骨科医院医治那受伤的脚。临别时,梁三再三叮嘱哥哥,到了省城,记得写封信回来,免得她在家总是挂念。
汽车慢慢地消失了,梁三往回走,她家就在前面的红花村。
红花村依山傍水,山上山下,村里村外,多是红花树。时值新春,红花树红蕾初绽,露出一片片肥嫩的花瓣。在艳阳的映照下,满村闪耀着瑰丽的红光,溢彩流丹,惹眼极了。
原先,这里的红花树也并没有这么多,只是在那荒诞的年头里,把那值钱的,能换油盐,食粮的果树、竹林扫光了。红花树木质差不值钱,又不挂果,所以幸存下来,它独享一隅的水土阳光,越长越多。如今,人勤、花美、日子红火,红花村真是个好地方。可是那些年,谁有心思欣赏花儿呢?花儿再红再美,也不能充饥饱肚。村里的后生哥们,只好望花兴叹:“红花平平挂满枝,阿哥无钱娶妻难;阿妹含泪嫁下山,阿哥爬树多凄凉!”
红花村有个自古相传的风俗,哥哥娶不上老婆,妹妹要出嫁,哥哥就得在妹妹出门时去爬树。为什么要爬树呢?历来就有不同的解释,按村里长辈们的说法,就是不让人低看,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爬得高高的,就显得比妹妹有出息了。这大抵也是中国农民祖传下来的一种精神胜利法吧。
梁三的父母过世太早,丢下他们兄妹四人,娘死得真惨!碰上六○年大饥荒,娘到附近国营农场翻木薯,饿得受不了,煨了条木薯吃,中毒死在路上。那时梁三还未脱奶,瘦得皮包骨的,整天闭着眼睛哇哇地哭个不停。人家看了可怜,送给人养,哥哥舍不得,为了养活梁三,德旺天天吃木薯干,省下一把米就磨成粉,煮糊糊来一口一口地喂她,喂饱了又抱着她睡觉。那时德旺还是一个十三、四岁的放牛娃,他要把脚下的三个妹妹拉扯大,有多艰难啊!这些,后来听德旺说起来,梁三扑在哥哥怀里足足哭了半天!
德旺对梁三的爱有多深啊!兄妹相依为命,留给梁三铭心刻骨的记忆。她不明白为什么哥哥辛辛苦苦把他后一个妹妹拉扯大了,当她们出嫁时,哥哥要去爬树?
她记得大姐相亲时,私下要了人家一笔彩礼。姐妹商量,想用自己的身价给哥哥娶嫂子,当人家把彩礼送上门来,哥哥一看就火了,冲着人家大骂:“你们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什么时候跟你喊价嫁妹妹?”当面把人家的彩礼退了回去。
大姐出嫁那天,哥哥只好按照村里的习俗,老老实实地去爬树。那天,哥哥爬得高高的,别人在树下哈哈大笑,哥哥却老是沉着脸,当他俯下头来看见大姐拉着她的手,依依不舍地辞行时,几滴泪水从树上掉了下来,那时,哥哥多痛心啊!
爬了一次树之后,哥哥便落人笑柄了。上市下井,耳边都响起人家窃窃的嘲笑声:
“是他,爬过树啦!”
“他还有两个妹妹,还得爬两次哩!”
背上“爬树哥”这个名声,哥哥就更难娶嫂子了,人家姑娘见他,远远就避开去,十个“爬树哥”九个打光棍。哥哥自己也觉得低人一等,每次赶集都戴着一顶大竹帽,把头埋得低低的。
第二年春,红花树开花的时候,二姐又要出嫁了。这回三妹可不让哥哥爬树了。她不明白二姐为什么要离开她和哥哥,兄妹一起过日子,没有米,吃清水也是甜的。要是她,宁愿一辈子不嫁人,她不愿离开哥哥。可是人家都笑她傻,哪有姑娘大了不嫁人的?
二姐出嫁那天,碰上寒潮南下,天气骤然变冷,淫雨霏霏,落花纷纷。一只乌鸦孤零零地站在红花树上,向着阴沉沉的天空,“呜呜哇哇”地嘶叫了几声,叫得人们心里都发毛了。
“呸呸!”邻居张婶一边向红花树上抛石头,一边念着:“大吉大利!大吉大利!”把乌鸦吓飞了。
这天兆头真不好,满门喜气都给那该死的乌鸦冲跑了。二姐以为运气不好,吓得哭了。哥哥安慰妹妹:“天气变,乌鸦叫,这是平常事,怕什么呢?你放心出门去!”
张婶催哥哥去爬树,好让二姐快点出嫁。哥哥沉着脸不作声。爬树的滋味他尝过了,大姐出嫁时他不是爬得高高的吗?得到什么好处呢?反而落人家笑柄,做不起人了。管它什么风俗不风俗,决意不爬了。
“哎呀,怎么还呆着,二妹要出门了!”张婶从背后推了哥哥一把,又念念有词:“兄高妹低,大吉大利;兄把妹骑,合情合理!”说着又跑进屋里,拿出哥哥一条黑裤,挂在堂屋门口,吩咐二姐出门时一定要从裤档下走过。这蒙昧而古怪的风俗,真叫人无所适从。
二姐不敢冒犯风俗,见哥哥还未爬树,迟迟不敢出门,他只好去爬树了。他来到院子前面那棵笔直的红花树下,看热闹的孩子们团团把他围起来,象看马戏一样,乐得嘻嘻哈哈的。
哥哥心情不好,刚才喝了一杯酒,头昏昏的,手脚拦索索的,没有一点劲,怎么爬呀!梁三怕哥哥跌倒,慌忙跑过来抱着树,哭着:“哥哥,快下来呀!”
“傻妹!”人们把她支开,一齐对着哥哥呐喊:“用力,用力!”“爬高一点,再往上爬!”
不知什么时候,树梢上挂着一只断线的风筝,被风吹得“飒飒”作响。孩子们一股劲地冲着哥哥喊:“风筝,风筝,德旺叔叔,给我们把风筝取下来!”
哥哥仰头望了风筝一眼,又往树顶上爬。突然“嗄吱”一声,树枝断了,哥哥从树上摔了下来。
哥哥跌伤了,踝关节脱臼了,痛得要命!梁三扑在哥哥身上伤心地哭了起来。
那时家里穷得锅底朝天,哪里有钱请医生治疗呢?村里一位老伯采了几篮草药给哥哥敷,肿消了,痛止了,可是脚骨却歪了。耽误了好几年,现在能否治得好呢?梁三心里还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
送走了哥哥,她更加不放心,二十年来,她第一次与哥哥分手,哥哥跛着脚,独自到很远很远的省城去,那地方怎么样呢?这一切都叫她牵挂呀!
她慢慢地向村前的石拱桥走去。在追索往事的同时,又对现在和未来充满着憧憬和忧虑。生活总是这样,有喜又有忧……
“梁三!”忽然有人叫他。
她抬头一看,啊,是阿芳嫂。她正匆匆地从村里走来,她算是村里最漂亮的媳妇,两道黑黑的柳叶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红润润的脸上有两个美丽的笑涡。可是自从她丈夫死后,就难得见她一笑。这时,她手里紧紧地捏着一样东西,疾步走上桥头,象是要去追赶什么似的。
“梁三,客车来了吗?”
“阿芳嫂,你要赶班车吗?上哪里?”
“不,你哥哥……”
“我哥哥走了。”
“车开走了?”
“刚刚开走的,你有什么事吗?”
“不……”阿芳嫂失望地把手里的东西放回口袋里。梁三看见了,那是钱。莫非她想给哥哥送钱?自从哥哥跌伤以后,阿芳嫂总是悄悄地来探望,有时也帮梁三给哥哥敷药换药。平时有一把菜,一条瓜,一只鸡蛋,也是悄悄地放到梁三的厨房里,真难得她的好心呀!
“梁三,你哥的钱带够了吗?”
“够了,带上一千多元,不少吧?”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我以为明天才走哩。唉,都怪我赶集回迟了……”
“阿芳嫂,你看我哥哥的脚会医好吗?”
“会医好的!”阿芳嫂瞟了梁三一眼,“你不叫你哥捎信回来?”
“开车时,我又叮嘱了,我想他一定会捎信回来的。”
阿芳嫂把梁三拉到怀里,两人偎依着,从桥上走下来。桥下的溪流清悠悠的,映着她俩亲妮的身影,多像姐妹俩啊!
送别可哥那天,红花才刚刚开花,现在落花纷纷,屋顶上,院子里,到处都撒满殷红的花瓣。每天早晨,梁三打扫院子,看到这红艳艳的花瓣,就思念起哥哥来。花开花落,掐指一算,差不多二个月了,哥哥为什么还没有捎信回来呢?
她每天中午从田里回来,把锄头往厂拱桥边一倚,就站在桥上朝公路上望去。她知道乡府的邮递员每天中午都从公路上经过,把报纸和信件送到村委去。如果红花村有邮件,他那辆绿色的“蓝雁”就会拐个弯,冲向这石拱桥上来。邮递员就站在桥上,用那铜锣般的声音朝村里喊着:“喂!某某有信啰!”可是,近一段时间,邮递员总是飞一样地从公路上冲过去,连看也不看这石拱桥一眼,真叫人失望啊!
叫梁三怎么不思念哥哥呢?为了把三个妹妹拉扯大,哥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啊!那几年哥哥见妹妹们大了,还穿得破破烂烂的,心里过意不去。他上水库工地搬石头,听说水库指挥部需要柴烧,他就在歇响时,冒着暑天的烈日,到山上砍柴,一个中午砍一担,卖了几趟柴,给妹妹们每人剪了几尺花布。在三个妹妹中,哥哥对三妹还要偏上几分。哥哥每次在山上掏鹧鸪蛋,都煮熟了带回给三妹吃。有时还要逗逗梁三,让她闭上眼睛,再把东西给她。梁三也乖顺地闭上眼睛,把手伸得长长的。哥哥就把自己带回的番石榴,山稔子等野果放到她的手上。
哥哥心疼三妹,三妹更心疼哥哥,哥哥跌伤之后,三妹日夜陪伴和照料哥哥。哥哥不能下地劳动,里里外外都是三妹一肩承担。自从实行责任制之后,梁三承包了两亩责任田和几亩坡地。自己又犁又耙,又种又收,家里打的食粮不比别人少,加上种甘蔗、果子等,收入也还可观。这些钱全用来给哥哥医治受伤的脚,只盼着哥哥早日痊愈归来,就什么也不愁了。
她站在桥上,桥下的溪水像镜子一样照着她苗条的倩影。现在梁三已经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大姑娘了。因为她勤快,手脚麻利,又体贴哥哥,贤慧出了名,山前山后,上村下村都慕名上门提亲。这么好的姑娘,谁不想娶她当媳妇呢?可是门前踏低狗吠瘦,梁三一概谢绝,开口说:“我不嫁!”闭口也说:“我一辈子留在家伺候哥哥!”
要不上梁三,有的又眼红又嫉妒,放出许多风言风语。村里过去的风俗,姑娘二十岁出头不找婆家,人家就说你留在家里压台风。怪活传到德旺的耳里,德旺心里很难受。他对梁三说:“梁三,你听见了吗?咱兄妹都落人话柄了,说什么‘爬树哥哥变跛脚,台风妹妹守故庙’难听啊?”
“阿哥,别管它?”梁三把怨气咽回肚里,吱了吱嘴唇,说了这句话自己极不情愿说出的话。
梁三真的不想嫁人吗?不,世界上有哪个少女不怀春,每天早晨,她对着镜子梳妆的时候,总爱久久地端详着自己,好像自己变了,镜子里的春容叫梁三入迷地看馋了眼。她眉毛是那样弯,深潭似的眼睛闪着迷人的水光,小巧的嘴辰像红花一样红艳,胸脯也越来越丰满,去年做的花短袖衫,绷得紧紧的,越发显出线条来!她不好意思地把镜面背了过去,单自己没出息。自己的有什么好看。
以往,花开花落与她毫无相干,现在喜欢坐在窗前忘情地望着花枝出神,红花开越发激漾了她的春心。
梁三从来没照过相,可是也爱偷偷地拿着一张照片看了又看。那是谁呢?只有她知道。那是后山村一位后生哥。她爱上了他。
家里不缺柴烧,她三几天又到后山去砍柴,那后生哥也总爱帮她砍。可是两人见了面又什么都不说。那后生每次送她出山时都问她:“我们的事……你怎么总不说呀?”她都是冷冷地回答说:“别等我,我永远不嫁人了!”
谁都知道这是违心话。梁三是舍不得离开相依为命的哥哥,她不愿伤了哥哥的心。自己从小就失去母亲之爱,哥哥给她手足之情,又给她母爱的温暖,她能为了自己的幸福,把孤单和痛苦留给哥哥吗?能让跛了脚的哥哥再去爬节三次树吗?不,她愿意留在家,陪伴、照料哥哥一辈子。
德旺也很理解梁三的心,他舍不得叫心爱的妹妹离开自己,可是她不能拖累妹妹,不愿意耽误妹妹的青春年华。哥哥关心地问她:“梁三,你心疼哥哥,我知道,可是你自己的事不能瞒着哥哥,没有爸妈,哥哥要为你作主,成全了你的婚事,也叫黄泉下的爸妈放心。后山村那青年怎么样……”
“哥!”梁三打断了哥哥的话,她避开哥哥的目光,脸“刷”地涨红了。
“梁三,只怪哥哥不中用……叫你们在家吃了不少苦,也没有给你们找个好婆家。大妹和梁二的婚姻都是别人撮合的,并不是称心如意,婚后日子也不太舒心,只有你是自己找的,听说那青年挺不错……”
“哥……没那回事,别听人家瞎说,我……我不能离开你……”
梁三矢口否认,可是她的神志已告诉了哥哥。
这天晚上,梁三听见哥哥尽在唉声叹气。她不知怎么安慰哥哥,只是轻轻地走到床前问了一声:“哥,你还不睡?”
“我就睡……”德旺一点睡意也没有。
梁三帮哥哥捻小了灯火。
回到了自己的房里,她也睡不着。她的心里很乱,许多念头和一些未曾有过的想法一齐向心里涌来,叫她不想也得想。她是个单纯,乖顺的姑娘,她除了上过集场,不知道外面的景什么世界,不懂得什么奢望和享受,只知道田里的谷子要用自己的汗水去换,店里的布要卖了自己养的鸡去买;父母抚养子女,子女要考顺父母,哥哥心疼妹妹,妹妹要体贴哥哥;除此之外,还有夫妻之爱……她看到的就是这些。近年来,村里的姐妹后象出巢的鸟儿一样,一个个地飞到山下的村里去,有的人要了人家的钱,还要了薄的,厚的,棉的,毛的……她从不眼红和嫉妒人家,这些不属于她,大姐、二姐出嫁时,想要也不能要,哥哥反对他们这样做。只是她近来有一个荒唐的想法,听到别的村有几桩换亲的新间,妹妹换嫂子,她也在心里想:我怎不也给哥哥换一个呢。只要哥哥幸福,付出再大的牺牲我也愿意。这个念头只在心里一闪,她又不敢想了。后山村那个后生哥在苦苦地等待她,要不是哥哥跌伤了脚,不能种田和料理生活,她早就把自己的爱情奉献给了他。
这时,哥哥是否睡着了?怎么不听见他的鼾声呢?忽然轻轻的一声门响,是哥哥开门吗?夜深了,哥哥出去做什么呢?这时,梁三耳朵特别灵,听见哥哥的脚步声向院子前面走去。不一会,又听见摇落树叶的风之声异常。她敏感地想到哥哥会做出什么愚蠢的举动来。她赶紧开了门,追了出去。
月光如霜,树影斑驳。哥哥已抱着红花树一步一步地往上攀。
“哥哥!”梁三慌忙地扑向红花树,她望着哥哥垂着左脚,用右脚撑着树,双手吃力地向上攀绿的身影,梁三哭了,泪水从眼窝里溢了出来!
“哥哥,你别爬了!”梁三声音含着热泪:“哥哥,下来吧!”
“三妹,我能爬了!”德旺得意地重复着,“我能爬了!妹,你的婚事不能再拖了!”
“哥,你下来!”梁三用拳头捶着树干,“你爬得再高我也不出嫁了!”
德旺俯下头来,望见梁三脸上的泪花,他的手软了,爬不动了,只好慢慢地滑了下来,兄妹在树下抱在一起,揪心地哭了……
想到这些,梁三心里有多难堪啊!一串泪珠从她脸上滚了下来,滴进清清的溪水里,水面飘浮着一片片红花,泪水伴着落花,悠悠地向桥下流去,她的心也随着流水飞向遥远的省城。……哥哥的脚治得怎么样了呢?他为什么忘记了她的叮嘱,不写封信回来呢?
“梁三!”阿芳嫂提着一篮衣服向石拱桥边走来。
梁三忙抹干眼泪,迎了上去:“阿芳嫂,我帮你洗。”
阿芳嫂瞟了梁三一眼,见她眼睛红红的,脸上挂满了泪痕,关切地问:“梁三,你怎么啦?”
“没什么……”
“又想你哥啦?”
“嗯。”梁三担心地说:“阿芳嫂,不知哥哥的脚医好没有,她为啥不捎个信回来呢?”
“不用急,会医好的,昨晚夜……”阿芳嫂想说什么又突然停住,脸暮地泛起了红云。
“什么”梁三敏感地问:“你梦见我哥?”
“我梦见他回来了!”阿芳嫂问,“你挠你哥是啥样子?”
“一定是医好了,大步大步地走了回来,踩得这石拱桥咚咚地响!”
“对,他一回来就在红花树下逞能,给大家来了个单脚独立,又来一个金鸡啄米,可神气哩!”
“你的梦真妙!”梁三乐得泼起水来,水花溅了阿芳嫂一脸。
“死丫头,看你乐的!”两人对视着,咯咯地笑起来。
梁三从阿芳嫂的篮里拿过一件衣服,涂上肥皂,轻轻地柔着,肥皂泡从手里飞起来,飘在水面,映着阳光,呈现出绚丽的光彩,好看极了。
“梁三,好日子总算盼到了,你哥回来,你自己的事也该办了。”啊芳嫂关心地开导她,“花逢春开,果逢秋熟,你看,这红花树,不久前才挂蕾,现在落花随水流,红花能有几日鲜?”
梁三凝望着水面的肥皂泡,默默无语。谁不珍惜自己的青春呢?可是,如果自己丢下哥哥嫁出去,谁帮哥挑水?谁帮哥哥洗衣服?责任因谁来种呢?
“阿芳嫂,我要等哥哥医好脚,等他要上嫂子……”
“梁三,你真有心!待你哥回来,我每天过去帮帮不行吗?你放心就是了!”
梁三激动地看了阿芳嫂一眼,真难得她这么热心呀!她守寡六年,年经轻轻的,为什么不再出嫁呢?她结婚才一年,丈夫就病故了,那时小叔子还在念中学,婆婆又有哮喘病,她嫁了就没人伺候。现在小叔子毕业回来了,家里有了顶梁柱,她满可放心走了,可是她却不肯离开,好象在等待着谁。莫非她对我哥……
梁三正想着,水中忽然冒出一个高高的人影,是谁,梁三抬头看:啊!是哥哥!他挺立在桥上朝她后望,那样子可英武哩!
德旺满脸红光,健步地向她们走来。梁三乐得一下子扑了上去,拉着哥哥的手,高兴地问:“哥哥,你的腿治好了!”
“好了!”德旺瞟了阿芳嫂一眼,放下提包,拉开马步,给妹妹和阿芳嫂来个单脚独立,又来个金鸡啄米……
“啊!这不是梦吗?”阿芳嫂一时又像回到梦里。她醉心地笑了,那失去的笑涡,又回到她的脸上……
春深花更艳。梁三门前的红花树,像一束束高燃的红烛,喜鹊飞舞,喜气盈门。她正在闺房里梳装打扮,她准备出嫁了!
不一会,后山村的人吹着唢呐,敲锣打鼓地来迎亲,满村的孩子也跟着跑到院子里来看热闹,一个个跳着,喊着:“梁三出嫁了,又看德旺叔爬树啦!”
梁三披红挂彩,笑盈盈地被姐妹们簇拥着从闺房出来。德旺呢?怎么还不去爬树!啊!只见他穿得光鲜鲜的,戴着一朵大红花,从屋里出来,在繁花的映照下,显得更年轻、英俊、容光焕发。孩子们眼都傻了,德旺叔怎么也当起新郎倌了?原来他与梁三同时成亲哩!
梁三出门时,阿芳嫂也在爆竹声中被几位大嫂送入门来。
不一会,德旺从堂屋的八仙桌上拿出一袋双喜糖果分发给孩子们:“先吃喜糖一人一把。”
孩子们调皮地回:“这回不爬树了!”
德旺笑着说:“你们爱看,我再爬给你们看不过,你们这一代人不再当‘爬树哥’了!”
孩子们吃着喜糖,乐哈哈地笑了,幸福的笑声荡遍红花村……
(长篇小说《岁月烟云》节选)
1
1948年秋天。国共两党在长江南北两岸,各自陈兵百万,一时间大江上空战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
长江南岸S镇。
秋风萧瑟,尘土迷蒙,街面冷落,行人稀少,一派兵荒马乱景象。
四五辆载着人和行李家什的马车,先后飞驰过街道向南奔去,车尾卷起了一片黄色尘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一些为避战乱的富裕人家。
远方传来“得得”的马蹄声。一个身材高大的军官骑着棕色的骏马沿着街面逡巡而来,身后跟着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卫兵。
在一个卖日用杂品的地摊面前,军官勒住马首停下。他朝着地摊上的手杖看了半晌,问摊主:“这手杖多少钱一根?”
摊主郭斌答:“长官,这是盐城产的手杖。你看,都是柏树做的,质地坚硬,上等货呐。”
“多少钱一根?”军官问。
“六万块一根。”
军官问:“你这里共有多少根?”
“六十三根。”
军官说:“不够!我要一百根。”
郭斌迷惑不解地问:“要这么多干什么?”
“别噜嗦!这是军事秘密,你问这个干啥?”站在旁边的警卫兵训斥道。
郭斌吓得连声说是。他指着不远处的小木屋:“长官,你等等,我马上去拿。”
“慢!”军官瞟了一眼这个四十多岁的摊主,想了一问:“听你的口音好像是澄州人?”
郭斌答:“是,是澄州西岙人。”
“为什么到这儿来干这营生?”军官威严地问。
“这……在家乡生活不下去,到这里摆地摊卖些日用品维持生计。”郭斌垂着两手毕恭毕敬地回答。
军官思忖了一下,对身后的两个警卫兵说:“先付他五十万定金,下午你们来拿手杖。”说完一拉马缰绳,飞驰而去,街路上扬起了一片尘土。
郭斌为一早就做了笔大生意感到喜出望外,接过定金,满面笑容对警卫兵连声说:“长官您走好。”
到了下午,两个警卫兵来了,说:“我们团长要你把手杖亲手送到团部去。”
郭斌忐忑不安起来了:不是说好下午由警卫兵来取手杖的吗?怎么变了要他自己把手杖送到团部?他想起几天前就有个士兵到他地摊上买了六七张椅子不给钱,向他讨钱反而被揍了一顿。莫非今天又……他望了一下眼前两个铁青着脸不容说话的警卫兵,只得说:“长官请等下,待我把地摊上的东西收拾一下……
郭斌将地摊上的东西搬进屋子里以后,怀着懊丧和不安的心情,肩挑手杖跟着两个警卫兵走进了团部。他见到团长放下肩上的手杖后,立即返身就往回走,他怕如果要手杖的钱会挨揍,吃不消。
这时,团长开口了:“怎么啦,不要钱就走?”声音是温和的。
但在郭斌听来这是官场上的套话,你要是真的向他讨要钱,他就马上变脸,要手下人揍你。郭斌恭敬地说:“不,这点手杖就算是小人孝敬给长官们……”
团长笑了:“哪能买了末事勿给钞票?又麻烦你老远的送了过来,总得坐一下歇歇力嘛,来人,给他送茶。”团长说的是澄州方言,郭斌奇怪了:难道团长也是澄州人?于是,他也用方言问:“你阿是澄州人?”
团长点了点头:“我叫陈琪,澄州北岙人。”
还有什么比千里之外遇到同乡感到亲切呢。郭斌内心涌动丝丝温暖,顿时感到与团长的心贴近了。他说:“真凑巧啊,你住在北岙我住在西岙,原来我们住得恁近,只隔一条溪呐。少年时候,我到门前坦小学读书,是扎起裤脚踏着碇步走过去的,溪水时常把我的裤脚打湿。尤其是雨后,碇步很滑溜。有一次我滑跌在溪水里,连书包都打湿了,回家让父亲骂了一顿……”说起故乡和少年趣事,他没完没了。
站在旁边的两个警卫兵傻了眼,他们除了团长说的“来人”“送茶”这话听清楚外,其他的一点也听不懂,他们还以为团长与郭斌是在讲少数民族的地方方言呢。
待郭斌喝了茶,团长又问他叫什么名字,读过书没有?共读了几年书?在镇上摆地摊赚钱多不多,生活过得怎么样?郭斌一一作了回答。最后团长问他,愿意不愿意在这里当兵?。
郭斌想:摆地摊确实也难赚钱,可是要他当兵心里又不愿意。老百姓恨死了国民党的兵,为了逃避抽壮丁他才到这里来摆地摊谋生糊口,现在团长问他要不要当兵,他心中一时拿不定主意,便推说回去想好了以后再定。
这时,一个副官模样的青年进来报告:“团长,老人们都到齐了,就等你去。”
“好,我马上就来。”团长说。
2
团部的大院里站着一群须发霜白的老人,他们不知道团长为什么突然叫他们来到团部,大家心里不安的挤着站在一起。陈琪理解他们的心情,走到一位老人面前,亲切地叫了声:“老大爷,你好,今天我请你来团部玩玩,是想请你帮我办件事呐。”说着递给他一根手杖。接着,他又热情地说笑着发给每个老人一根手杖。老人们这才宽下心来。
陈琪给老人发了手杖后,站到团部大院的台阶上高声喊:“来人!把那个强买东西不给钱还打了人家的家伙带过来!”
话音刚落,两个彪形大汉押着个捆绑着的士兵走过来。
陈团长威严地宣布:“罚打一百军棍,禁闭两天。”
彪形大汉当场按着那个士兵趴下,举起扁担狠狠的打,没多久就打得这个士兵屁股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行刑毕,彪形大汉将扁担靠在墙根,扁担钉上还挂着片沾满殷红鲜血的皮肉。
打完违犯军纪的士兵后,陈团长向老人们拱手作揖说:“父老乡亲们,我陈某人奉命到贵地驻防,军纪不严。手下士兵横行霸道,骚扰乡里,干了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我在这里向大家道歉了。”接着他高声宣布:今后你们如看到士兵横行霸道,就用我给他们的手仗尽管打他,扭送他到团部,我陈某人一定严惩不贷,决不食言!陈团长的最后两句话声如洪钟,震耳欲聋。说得老人们敬仰不己,脸上露出了笑容。
郭斌目睹陈团长严办违犯军纪士兵的经过,尤其看到扁担钉上挂着的那片触目惊心的血淋淋皮肉,心里感触很深。回到小木屋内,心里想:要不要去团郭当兵呢?看来这个团长与国民党有的军官不一样。自己在镇上摆地摊也难以维持生计,不如暂时去当兵混口饭吃。陈团长是同乡人,对自己好便罢,不好相处的话找个机会开小差。想定之后,第二天到团部对陈琪说:“我愿意在这儿当兵。”
就这样,郭斌参加了国民党军队。
在陈琪的团部里,由于大战迫在眉睫,充斥着紧张、恐怖的气氛,同样是派兵荒马乱的景象。
郭斌当兵后,陈琪见他为人老实,且有点文化,又是同乡人,遂有收为心腹之意。便委任他为团部庶务长,经过一段时间考察,改任侍从参谋,不久,提升为一营一连连长。
翌年四月廿日,国民党反动派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长江北岸百万解放军即将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渡长江。廿一日傍晚,郭斌突然接到陈琪命令,要连长以上军官紧急集中团部开会。他走到团部,看到岗哨密布,警卫班战士手拿张开机头的驳壳枪,气氛异常紧张。预感到将有重大事件到来,心理上做好了准备。
陈琪见连以上军官到齐,便宣布会议开始。他两手拄在会议桌上,用冷静、沉着的语音分析了长江南北形势,江防部署,以后庄严地宣布:“现在我命令:全团起义!谁不同意可发表意见。”这时,站在他身旁的团参谋长忽地拔出手枪指着陈琪说:“你想反水,我毙了你!”只听见“啪”的一声,说时迟那时快,团参谋长应声倒地,污血喷射到会议桌上,浸红了一大块台布。
原来陈琪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早已掌握参谋长是师部暗地安插在团部的特务,开会前已作周密安排,不等他开枪,警卫战士抢先动手杀了他。陈琪环顾了一下四周,说:“同意或不同意起义的都请发表意见。”郭斌从腰间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说:“国民党反对派腐败透顶,我赞成全团立即起义。谁不同意,参谋长就是样子!”这时,全团所有连级以上军官都表示没有异议。
于是,陈琪拿下头上的军帽,摘掉青天白日帽徽,将它摔到地上。立即发布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在今晚渡江攻占南京,全团战士要配合作战,保证解放大军安全渡江!……”
3
南京解放后,陈琪担任了K县军管会主任。郭斌任后勤处处长。生活开始安定起来,他想起了家,想起了妻子和子女现在生活到底怎么样了?儿子郭明参加工作了没有?尤其是到了星期天,当地的工作人员都回家和亲人团聚,他心里的这个愿望就更加强烈了,他想请假回澄州一趟看望妻子和儿子郭明。这天,郭斌伏案午睡,朦胧中游览九华山,混混沌沌,虚无飘渺间,一老者飘然来到面前,老者童颜鹤发,银髯飘拂,风度睿智,慈祥可亲。郭斌知是非尘世中人,遂求问养生长寿避祸消灾之道。老者曰:“大道轮回,周而复始,生死荣枯,天命已定。”言毕,隐入云雾而去。
此后不久,一日,两名公安人员突然来到郭斌面前,问清楚姓名后宣布了逮捕命令,给他套上锃亮冰冷的手铐,押解到法院审判,这时他才知道事情突然变化的根源。
原来陈琪在起义以后,解放军收编了他下属的国民党军队。但一营三连的连长是原先团参谋长的亲信,当时伪装起义,后又叛变,在枪杀我们党派去的连队指导员后下海投敌了。于是情况变得错综复杂起来。人民解放军保卫部门对起义人员进行了甄别审查,清除混入革命队伍的反革命份子。
某师保卫处对陈琪进行了甄别审查。保卫处汪处长问陈琪:“部队收编后,那天是你送指导员到三连的吗?”
陈琪说是。
汪处长又问:“指导员到三连时,你对原来的三连连长说了些什么话?”
陈琪臁:“我说指导员是上级党委派来的,你要尊重他的意见,服从党的绝对领导。”
“当时三连连长他怎么说?”汪处长接着问。
陈琪说:“他说欢迎指导员来三连工作,保证服从党的领导。”
汪处长说:“你对三连连长就说了这些话?”
陈琪说:“就这些话。”
汪处长严肃的说:“不对,据有人反映,你将三连连长拉到旁边又悄悄地说了些话。有没有这件事?说了些什么话?”
陈琪想了一下说:“哦,我记起来了,确有这件事。”
汪处长说:“你同三连连长悄悄地说了什么话?”
“我对他说,解放军纪律严明,你喜欢嫖妓,今后不允许你再弄。”陈琪说。
汪处长说:“按你这样说,你是没有说过指使三连连长叛变的话喽?”
陈琪说:“我以党性保证,绝对没有说过半句唆使三连连长叛变的话。”
汪处长说:“可现在的事实是,三连连长在枪杀指导员后下海投敌了。有人反映是你陈琪指使的。”
陈琪指着胸口说:“我再次以党性向你保证,绝对没有此事!”
汪处长说:“有人反映你的党籍是假的。此事我们正在调查中。”说着,汪处长走出了办公室。
对陈琪审查的事,因三连连长已下海投敌,无人证明当时陈琪与三连连长的讲话内容,这事成了重大疑点。加以陈琪是否系我党地下党员也无法证实。因为这时,解放大军在突破“长江防线”占领南京后,后续部队早已纷纷南下。陈琪一时找不到地下党单线联系的上级,保卫部门按照“有罪推定”的规定,认为陈琪系伪装起义混入我军的反革命分子。陈琪遂被人民政府抓了起来,全团因此案而被株连的达一百多人。
郭斌也被株连。并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判刑五年,押送江西某地劳改。当他手里拿着判决书时,想起了解放前为逃避抓壮丁,连夜逃离澄州老家。后来跟着陈琪起义,原以为是走上了光明的道路,谁知转眼间竟变成了反革命,今后还有何面目去见妻儿和澄州父老父亲?但是,当他想起梦中老者之言,知道这是劫数,不禁长吁叹息:在劫难逃,在劫难逃啊!
红花树
杨菊英
梁三送走了哥哥德旺。德旺哥要上省城骨科医院医治那受伤的脚。临别时,梁三再三叮嘱哥哥,到了省城,记得写封信回来,免得她在家总是挂念。
汽车慢慢地消失了,梁三往回走,她家就在前面的红花村。
红花村依山傍水,山上山下,村里村外,多是红花树。时值新春,红花树红蕾初绽,露出一片片肥嫩的花瓣。在艳阳的映照下,满村闪耀着瑰丽的红光,溢彩流丹,惹眼极了。
原先,这里的红花树也并没有这么多,只是在那荒诞的年头里,把那值钱的,能换油盐,食粮的果树、竹林扫光了。红花树木质差不值钱,又不挂果,所以幸存下来,它独享一隅的水土阳光,越长越多。如今,人勤、花美、日子红火,红花村真是个好地方。可是那些年,谁有心思欣赏花儿呢?花儿再红再美,也不能充饥饱肚。村里的后生哥们,只好望花兴叹:“红花平平挂满枝,阿哥无钱娶妻难;阿妹含泪嫁下山,阿哥爬树多凄凉!”
红花村有个自古相传的风俗,哥哥娶不上老婆,妹妹要出嫁,哥哥就得在妹妹出门时去爬树。为什么要爬树呢?历来就有不同的解释,按村里长辈们的说法,就是不让人低看,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爬得高高的,就显得比妹妹有出息了。这大抵也是中国农民祖传下来的一种精神胜利法吧。
梁三的父母过世太早,丢下他们兄妹四人,娘死得真惨!碰上六○年大饥荒,娘到附近国营农场翻木薯,饿得受不了,煨了条木薯吃,中毒死在路上。那时梁三还未脱奶,瘦得皮包骨的,整天闭着眼睛哇哇地哭个不停。人家看了可怜,送给人养,哥哥舍不得,为了养活梁三,德旺天天吃木薯干,省下一把米就磨成粉,煮糊糊来一口一口地喂她,喂饱了又抱着她睡觉。那时德旺还是一个十三、四岁的放牛娃,他要把脚下的三个妹妹拉扯大,有多艰难啊!这些,后来听德旺说起来,梁三扑在哥哥怀里足足哭了半天!
德旺对梁三的爱有多深啊!兄妹相依为命,留给梁三铭心刻骨的记忆。她不明白为什么哥哥辛辛苦苦把他后一个妹妹拉扯大了,当她们出嫁时,哥哥要去爬树?
她记得大姐相亲时,私下要了人家一笔彩礼。姐妹商量,想用自己的身价给哥哥娶嫂子,当人家把彩礼送上门来,哥哥一看就火了,冲着人家大骂:“你们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什么时候跟你喊价嫁妹妹?”当面把人家的彩礼退了回去。
大姐出嫁那天,哥哥只好按照村里的习俗,老老实实地去爬树。那天,哥哥爬得高高的,别人在树下哈哈大笑,哥哥却老是沉着脸,当他俯下头来看见大姐拉着她的手,依依不舍地辞行时,几滴泪水从树上掉了下来,那时,哥哥多痛心啊!
爬了一次树之后,哥哥便落人笑柄了。上市下井,耳边都响起人家窃窃的嘲笑声:
“是他,爬过树啦!”
“他还有两个妹妹,还得爬两次哩!”
背上“爬树哥”这个名声,哥哥就更难娶嫂子了,人家姑娘见他,远远就避开去,十个“爬树哥”九个打光棍。哥哥自己也觉得低人一等,每次赶集都戴着一顶大竹帽,把头埋得低低的。
第二年春,红花树开花的时候,二姐又要出嫁了。这回三妹可不让哥哥爬树了。她不明白二姐为什么要离开她和哥哥,兄妹一起过日子,没有米,吃清水也是甜的。要是她,宁愿一辈子不嫁人,她不愿离开哥哥。可是人家都笑她傻,哪有姑娘大了不嫁人的?
二姐出嫁那天,碰上寒潮南下,天气骤然变冷,淫雨霏霏,落花纷纷。一只乌鸦孤零零地站在红花树上,向着阴沉沉的天空,“呜呜哇哇”地嘶叫了几声,叫得人们心里都发毛了。
“呸呸!”邻居张婶一边向红花树上抛石头,一边念着:“大吉大利!大吉大利!”把乌鸦吓飞了。
这天兆头真不好,满门喜气都给那该死的乌鸦冲跑了。二姐以为运气不好,吓得哭了。哥哥安慰妹妹:“天气变,乌鸦叫,这是平常事,怕什么呢?你放心出门去!”
张婶催哥哥去爬树,好让二姐快点出嫁。哥哥沉着脸不作声。爬树的滋味他尝过了,大姐出嫁时他不是爬得高高的吗?得到什么好处呢?反而落人家笑柄,做不起人了。管它什么风俗不风俗,决意不爬了。
“哎呀,怎么还呆着,二妹要出门了!”张婶从背后推了哥哥一把,又念念有词:“兄高妹低,大吉大利;兄把妹骑,合情合理!”说着又跑进屋里,拿出哥哥一条黑裤,挂在堂屋门口,吩咐二姐出门时一定要从裤档下走过。这蒙昧而古怪的风俗,真叫人无所适从。
二姐不敢冒犯风俗,见哥哥还未爬树,迟迟不敢出门,他只好去爬树了。他来到院子前面那棵笔直的红花树下,看热闹的孩子们团团把他围起来,象看马戏一样,乐得嘻嘻哈哈的。
哥哥心情不好,刚才喝了一杯酒,头昏昏的,手脚拦索索的,没有一点劲,怎么爬呀!梁三怕哥哥跌倒,慌忙跑过来抱着树,哭着:“哥哥,快下来呀!”
“傻妹!”人们把她支开,一齐对着哥哥呐喊:“用力,用力!”“爬高一点,再往上爬!”
不知什么时候,树梢上挂着一只断线的风筝,被风吹得“飒飒”作响。孩子们一股劲地冲着哥哥喊:“风筝,风筝,德旺叔叔,给我们把风筝取下来!”
哥哥仰头望了风筝一眼,又往树顶上爬。突然“嗄吱”一声,树枝断了,哥哥从树上摔了下来。
哥哥跌伤了,踝关节脱臼了,痛得要命!梁三扑在哥哥身上伤心地哭了起来。
那时家里穷得锅底朝天,哪里有钱请医生治疗呢?村里一位老伯采了几篮草药给哥哥敷,肿消了,痛止了,可是脚骨却歪了。耽误了好几年,现在能否治得好呢?梁三心里还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
送走了哥哥,她更加不放心,二十年来,她第一次与哥哥分手,哥哥跛着脚,独自到很远很远的省城去,那地方怎么样呢?这一切都叫她牵挂呀!
她慢慢地向村前的石拱桥走去。在追索往事的同时,又对现在和未来充满着憧憬和忧虑。生活总是这样,有喜又有忧……
“梁三!”忽然有人叫他。
她抬头一看,啊,是阿芳嫂。她正匆匆地从村里走来,她算是村里最漂亮的媳妇,两道黑黑的柳叶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红润润的脸上有两个美丽的笑涡。可是自从她丈夫死后,就难得见她一笑。这时,她手里紧紧地捏着一样东西,疾步走上桥头,象是要去追赶什么似的。
“梁三,客车来了吗?”
“阿芳嫂,你要赶班车吗?上哪里?”
“不,你哥哥……”
“我哥哥走了。”
“车开走了?”
“刚刚开走的,你有什么事吗?”
“不……”阿芳嫂失望地把手里的东西放回口袋里。梁三看见了,那是钱。莫非她想给哥哥送钱?自从哥哥跌伤以后,阿芳嫂总是悄悄地来探望,有时也帮梁三给哥哥敷药换药。平时有一把菜,一条瓜,一只鸡蛋,也是悄悄地放到梁三的厨房里,真难得她的好心呀!
“梁三,你哥的钱带够了吗?”
“够了,带上一千多元,不少吧?”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我以为明天才走哩。唉,都怪我赶集回迟了……”
“阿芳嫂,你看我哥哥的脚会医好吗?”
“会医好的!”阿芳嫂瞟了梁三一眼,“你不叫你哥捎信回来?”
“开车时,我又叮嘱了,我想他一定会捎信回来的。”
阿芳嫂把梁三拉到怀里,两人偎依着,从桥上走下来。桥下的溪流清悠悠的,映着她俩亲妮的身影,多像姐妹俩啊!
送别可哥那天,红花才刚刚开花,现在落花纷纷,屋顶上,院子里,到处都撒满殷红的花瓣。每天早晨,梁三打扫院子,看到这红艳艳的花瓣,就思念起哥哥来。花开花落,掐指一算,差不多二个月了,哥哥为什么还没有捎信回来呢?
她每天中午从田里回来,把锄头往厂拱桥边一倚,就站在桥上朝公路上望去。她知道乡府的邮递员每天中午都从公路上经过,把报纸和信件送到村委去。如果红花村有邮件,他那辆绿色的“蓝雁”就会拐个弯,冲向这石拱桥上来。邮递员就站在桥上,用那铜锣般的声音朝村里喊着:“喂!某某有信啰!”可是,近一段时间,邮递员总是飞一样地从公路上冲过去,连看也不看这石拱桥一眼,真叫人失望啊!
叫梁三怎么不思念哥哥呢?为了把三个妹妹拉扯大,哥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啊!那几年哥哥见妹妹们大了,还穿得破破烂烂的,心里过意不去。他上水库工地搬石头,听说水库指挥部需要柴烧,他就在歇响时,冒着暑天的烈日,到山上砍柴,一个中午砍一担,卖了几趟柴,给妹妹们每人剪了几尺花布。在三个妹妹中,哥哥对三妹还要偏上几分。哥哥每次在山上掏鹧鸪蛋,都煮熟了带回给三妹吃。有时还要逗逗梁三,让她闭上眼睛,再把东西给她。梁三也乖顺地闭上眼睛,把手伸得长长的。哥哥就把自己带回的番石榴,山稔子等野果放到她的手上。
哥哥心疼三妹,三妹更心疼哥哥,哥哥跌伤之后,三妹日夜陪伴和照料哥哥。哥哥不能下地劳动,里里外外都是三妹一肩承担。自从实行责任制之后,梁三承包了两亩责任田和几亩坡地。自己又犁又耙,又种又收,家里打的食粮不比别人少,加上种甘蔗、果子等,收入也还可观。这些钱全用来给哥哥医治受伤的脚,只盼着哥哥早日痊愈归来,就什么也不愁了。
她站在桥上,桥下的溪水像镜子一样照着她苗条的倩影。现在梁三已经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大姑娘了。因为她勤快,手脚麻利,又体贴哥哥,贤慧出了名,山前山后,上村下村都慕名上门提亲。这么好的姑娘,谁不想娶她当媳妇呢?可是门前踏低狗吠瘦,梁三一概谢绝,开口说:“我不嫁!”闭口也说:“我一辈子留在家伺候哥哥!”
要不上梁三,有的又眼红又嫉妒,放出许多风言风语。村里过去的风俗,姑娘二十岁出头不找婆家,人家就说你留在家里压台风。怪活传到德旺的耳里,德旺心里很难受。他对梁三说:“梁三,你听见了吗?咱兄妹都落人话柄了,说什么‘爬树哥哥变跛脚,台风妹妹守故庙’难听啊?”
“阿哥,别管它?”梁三把怨气咽回肚里,吱了吱嘴唇,说了这句话自己极不情愿说出的话。
梁三真的不想嫁人吗?不,世界上有哪个少女不怀春,每天早晨,她对着镜子梳妆的时候,总爱久久地端详着自己,好像自己变了,镜子里的春容叫梁三入迷地看馋了眼。她眉毛是那样弯,深潭似的眼睛闪着迷人的水光,小巧的嘴辰像红花一样红艳,胸脯也越来越丰满,去年做的花短袖衫,绷得紧紧的,越发显出线条来!她不好意思地把镜面背了过去,单自己没出息。自己的有什么好看。
以往,花开花落与她毫无相干,现在喜欢坐在窗前忘情地望着花枝出神,红花开越发激漾了她的春心。
梁三从来没照过相,可是也爱偷偷地拿着一张照片看了又看。那是谁呢?只有她知道。那是后山村一位后生哥。她爱上了他。
家里不缺柴烧,她三几天又到后山去砍柴,那后生哥也总爱帮她砍。可是两人见了面又什么都不说。那后生每次送她出山时都问她:“我们的事……你怎么总不说呀?”她都是冷冷地回答说:“别等我,我永远不嫁人了!”
谁都知道这是违心话。梁三是舍不得离开相依为命的哥哥,她不愿伤了哥哥的心。自己从小就失去母亲之爱,哥哥给她手足之情,又给她母爱的温暖,她能为了自己的幸福,把孤单和痛苦留给哥哥吗?能让跛了脚的哥哥再去爬节三次树吗?不,她愿意留在家,陪伴、照料哥哥一辈子。
德旺也很理解梁三的心,他舍不得叫心爱的妹妹离开自己,可是她不能拖累妹妹,不愿意耽误妹妹的青春年华。哥哥关心地问她:“梁三,你心疼哥哥,我知道,可是你自己的事不能瞒着哥哥,没有爸妈,哥哥要为你作主,成全了你的婚事,也叫黄泉下的爸妈放心。后山村那青年怎么样……”
“哥!”梁三打断了哥哥的话,她避开哥哥的目光,脸“刷”地涨红了。
“梁三,只怪哥哥不中用……叫你们在家吃了不少苦,也没有给你们找个好婆家。大妹和梁二的婚姻都是别人撮合的,并不是称心如意,婚后日子也不太舒心,只有你是自己找的,听说那青年挺不错……”
“哥……没那回事,别听人家瞎说,我……我不能离开你……”
梁三矢口否认,可是她的神志已告诉了哥哥。
这天晚上,梁三听见哥哥尽在唉声叹气。她不知怎么安慰哥哥,只是轻轻地走到床前问了一声:“哥,你还不睡?”
“我就睡……”德旺一点睡意也没有。
梁三帮哥哥捻小了灯火。
回到了自己的房里,她也睡不着。她的心里很乱,许多念头和一些未曾有过的想法一齐向心里涌来,叫她不想也得想。她是个单纯,乖顺的姑娘,她除了上过集场,不知道外面的景什么世界,不懂得什么奢望和享受,只知道田里的谷子要用自己的汗水去换,店里的布要卖了自己养的鸡去买;父母抚养子女,子女要考顺父母,哥哥心疼妹妹,妹妹要体贴哥哥;除此之外,还有夫妻之爱……她看到的就是这些。近年来,村里的姐妹后象出巢的鸟儿一样,一个个地飞到山下的村里去,有的人要了人家的钱,还要了薄的,厚的,棉的,毛的……她从不眼红和嫉妒人家,这些不属于她,大姐、二姐出嫁时,想要也不能要,哥哥反对他们这样做。只是她近来有一个荒唐的想法,听到别的村有几桩换亲的新间,妹妹换嫂子,她也在心里想:我怎不也给哥哥换一个呢。只要哥哥幸福,付出再大的牺牲我也愿意。这个念头只在心里一闪,她又不敢想了。后山村那个后生哥在苦苦地等待她,要不是哥哥跌伤了脚,不能种田和料理生活,她早就把自己的爱情奉献给了他。
这时,哥哥是否睡着了?怎么不听见他的鼾声呢?忽然轻轻的一声门响,是哥哥开门吗?夜深了,哥哥出去做什么呢?这时,梁三耳朵特别灵,听见哥哥的脚步声向院子前面走去。不一会,又听见摇落树叶的风之声异常。她敏感地想到哥哥会做出什么愚蠢的举动来。她赶紧开了门,追了出去。
月光如霜,树影斑驳。哥哥已抱着红花树一步一步地往上攀。
“哥哥!”梁三慌忙地扑向红花树,她望着哥哥垂着左脚,用右脚撑着树,双手吃力地向上攀绿的身影,梁三哭了,泪水从眼窝里溢了出来!
“哥哥,你别爬了!”梁三声音含着热泪:“哥哥,下来吧!”
“三妹,我能爬了!”德旺得意地重复着,“我能爬了!妹,你的婚事不能再拖了!”
“哥,你下来!”梁三用拳头捶着树干,“你爬得再高我也不出嫁了!”
德旺俯下头来,望见梁三脸上的泪花,他的手软了,爬不动了,只好慢慢地滑了下来,兄妹在树下抱在一起,揪心地哭了……
想到这些,梁三心里有多难堪啊!一串泪珠从她脸上滚了下来,滴进清清的溪水里,水面飘浮着一片片红花,泪水伴着落花,悠悠地向桥下流去,她的心也随着流水飞向遥远的省城。……哥哥的脚治得怎么样了呢?他为什么忘记了她的叮嘱,不写封信回来呢?
“梁三!”阿芳嫂提着一篮衣服向石拱桥边走来。
梁三忙抹干眼泪,迎了上去:“阿芳嫂,我帮你洗。”
阿芳嫂瞟了梁三一眼,见她眼睛红红的,脸上挂满了泪痕,关切地问:“梁三,你怎么啦?”
“没什么……”
“又想你哥啦?”
“嗯。”梁三担心地说:“阿芳嫂,不知哥哥的脚医好没有,她为啥不捎个信回来呢?”
“不用急,会医好的,昨晚夜……”阿芳嫂想说什么又突然停住,脸暮地泛起了红云。
“什么”梁三敏感地问:“你梦见我哥?”
“我梦见他回来了!”阿芳嫂问,“你挠你哥是啥样子?”
“一定是医好了,大步大步地走了回来,踩得这石拱桥咚咚地响!”
“对,他一回来就在红花树下逞能,给大家来了个单脚独立,又来一个金鸡啄米,可神气哩!”
“你的梦真妙!”梁三乐得泼起水来,水花溅了阿芳嫂一脸。
“死丫头,看你乐的!”两人对视着,咯咯地笑起来。
梁三从阿芳嫂的篮里拿过一件衣服,涂上肥皂,轻轻地柔着,肥皂泡从手里飞起来,飘在水面,映着阳光,呈现出绚丽的光彩,好看极了。
“梁三,好日子总算盼到了,你哥回来,你自己的事也该办了。”啊芳嫂关心地开导她,“花逢春开,果逢秋熟,你看,这红花树,不久前才挂蕾,现在落花随水流,红花能有几日鲜?”
梁三凝望着水面的肥皂泡,默默无语。谁不珍惜自己的青春呢?可是,如果自己丢下哥哥嫁出去,谁帮哥挑水?谁帮哥哥洗衣服?责任因谁来种呢?
“阿芳嫂,我要等哥哥医好脚,等他要上嫂子……”
“梁三,你真有心!待你哥回来,我每天过去帮帮不行吗?你放心就是了!”
梁三激动地看了阿芳嫂一眼,真难得她这么热心呀!她守寡六年,年经轻轻的,为什么不再出嫁呢?她结婚才一年,丈夫就病故了,那时小叔子还在念中学,婆婆又有哮喘病,她嫁了就没人伺候。现在小叔子毕业回来了,家里有了顶梁柱,她满可放心走了,可是她却不肯离开,好象在等待着谁。莫非她对我哥……
梁三正想着,水中忽然冒出一个高高的人影,是谁,梁三抬头看:啊!是哥哥!他挺立在桥上朝她后望,那样子可英武哩!
德旺满脸红光,健步地向她们走来。梁三乐得一下子扑了上去,拉着哥哥的手,高兴地问:“哥哥,你的腿治好了!”
“好了!”德旺瞟了阿芳嫂一眼,放下提包,拉开马步,给妹妹和阿芳嫂来个单脚独立,又来个金鸡啄米……
“啊!这不是梦吗?”阿芳嫂一时又像回到梦里。她醉心地笑了,那失去的笑涡,又回到她的脸上……
春深花更艳。梁三门前的红花树,像一束束高燃的红烛,喜鹊飞舞,喜气盈门。她正在闺房里梳装打扮,她准备出嫁了!
不一会,后山村的人吹着唢呐,敲锣打鼓地来迎亲,满村的孩子也跟着跑到院子里来看热闹,一个个跳着,喊着:“梁三出嫁了,又看德旺叔爬树啦!”
梁三披红挂彩,笑盈盈地被姐妹们簇拥着从闺房出来。德旺呢?怎么还不去爬树!啊!只见他穿得光鲜鲜的,戴着一朵大红花,从屋里出来,在繁花的映照下,显得更年轻、英俊、容光焕发。孩子们眼都傻了,德旺叔怎么也当起新郎倌了?原来他与梁三同时成亲哩!
梁三出门时,阿芳嫂也在爆竹声中被几位大嫂送入门来。
不一会,德旺从堂屋的八仙桌上拿出一袋双喜糖果分发给孩子们:“先吃喜糖一人一把。”
孩子们调皮地回:“这回不爬树了!”
德旺笑着说:“你们爱看,我再爬给你们看不过,你们这一代人不再当‘爬树哥’了!”
孩子们吃着喜糖,乐哈哈地笑了,幸福的笑声荡遍红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