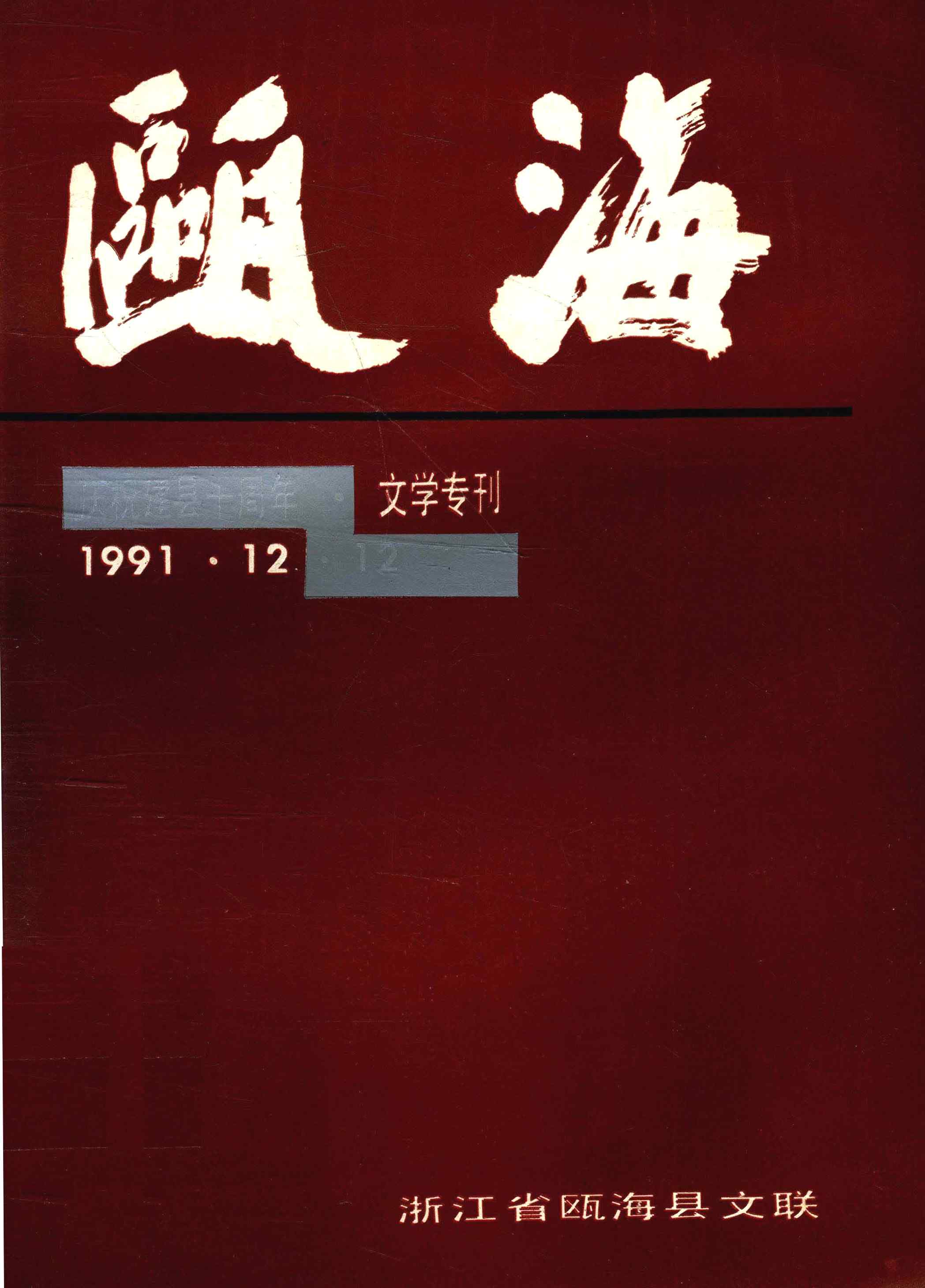内容
小说三题
李永汉
秀才·文盲
方翔大学本科毕业,写得一手好文章,是单位里公认的秀才;他妻子兰兰只读到小学三年级,连报纸也看不懂,基本上是文盲。文化差距如此之大,怎么会结合在一起呢?单位里有些人开始也弄不懂,后来才逐渐清楚,这里边包含着特殊因素。
兰兰的父亲贫农出身,她本人是产业工人,长得清丽俊俏,亭亭玉立;方翔虽是秀才,但那时的说法,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子又不高,戴着副深度眼镜。他和兰兰结成夫妻,据方翔说是响应“知识分子要和工农分子相结合”的号召,可兰兰说是方翔攀了高枝,让“她的优势补了他的劣势”。不管怎么说,反正这起婚事是抹上了那个时代的时髦潮流色彩罢了。
基于上面这些原因,婚后方翔在兰兰面前就低了一截,惟命是从。尽管如此,但小两口还是恩恩爱爱过着日子。没四、五年,孩子一个接着一个来到人间,于是家务事也就跟着多起来了。
夫妻俩平日上班,他们和孩子的脏衣物只好集中在星期天洗涤。兰兰站在井旁,把板刷和肥皂交给他说:“你刷,我洗。”
方翔“噢”的应了一声弯着身子刷起来,兰兰又嫌他抓不住重点,说:“上衣领头和袖口,裤屁股和裤脚是比较脏的地方,要用力刷。”他马上改进,照办。
方翔刷完衣物,兰兰又把吊桶交给他:“把井水吊上来,让我漂洗。”他又“噢”了一声把吊桶放进井里开始吊水。
方翔这么听妻子的话,还有个绝对不能同别人说的隐秘:兰兰长得漂亮,很得他的欢心,但她性格倔犟,如顺着她的话去做,夜里她对他就风情万状,体贴入微,如不按她的话办,她就冷若冰霜,拿起枕头到床那一头去睡。
后来,市场上有了洗衣机,方翔就去买了一只。但兰兰还是站在洗衣机旁指指点点,说衣裤的每个口袋都要先检查一遍,不要让硬币或杂物掉进去,以免损坏洗衣机;衣服领头和袖口等重点处要先刷一番再放进去等等。
这天,是休息日。上午,方翔把头一天晚上全家浴后的衣服放进洗衣机,按照程序,扭开水龙头开关,设定“标准洗涤”的按钮,洗衣机就按照指令转动起来了。
可是,没有多久,洗衣机发出了“轧、轧”的响声,最后干脆停了下来:离心机不转,出水口也不畅通了。方翔束手无策,心虚地对兰兰说:“你看是否请个师傅来修理?”兰兰白了他一眼:“张口就是请人,没80元修理费行吗?恐怕又是硬币卡了出水口,让我试试看。”这倒是事实,以前这洗衣机就曾发生过硬币卡住出水口的事。于是,他抓着头皮自责地说:“可能又是我不小心,在某次洗衣时忘了检口袋,那就麻烦你动手查一查吧。”
兰兰在厂里曾干过钳工,她拿来螺丝刀三下两下拆开洗衣机的后盖板,检查了输水管道,果真是两个一元钱的硬币卡住出水口,硬币锈迹斑斑的,看来是掉进去好些时间了,慢慢被冲洗到出水口卡住的。兰兰把它挖了出来,再按照程序设定按钮,洗衣机就又转了起来。兰兰要方翔拿这两个硬币去农贸市场买菜。摊主秤好菜接过硬币一看,说:“这钱不好用!”方翔说:“硬币上的国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994年的字迹都还认得出来,只是锈了而已,怎么不好用?”
“不好用就不好用!”摊主断然拒绝。方翔只好空着双手回家。
兰兰听了他没买来菜的原委后说:“你不会到银行去调换?连这点脑筋都转不过来,还能写出好文章!”
方翔拍拍脑袋,说了声:“真是的。”到附近一家银行分理处去了。
储蓄柜一个涂抹着口红的小姐拿着硬币看了半晌,皱着眉头问:“这钱怎么锈得这样?”方翔就把洗衣时忘了检口袋,让硬币掉到洗衣机里,卡住出水口,时间久了,生了锈等等说了一遍。
“我们银行规定,锈的不能调换!”
于是,他又把国徽和字迹还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话重复了一遍,可是这位小姐最终还是拒绝调换,他只得手里又捏着这两枚硬币返家。
兰兰正在厨房洗碗,方翔把银行不肯调换的话对她说了。她乜了他一眼,接过硬币用废铁丝球使劲揩擦了几下,不到半分钟,硬币露出了本色,锃光闪亮的。她说:“这硬币本来就是好的嘛,你去与他们理论!”
方翔摇头叹息,心里有了一种说不出来的不平之感:秀才碰见兵有理讲不清。倒还可以说得过去。可遇到银行小姐,怎么也有理讲不清!?他把这个意思同兰兰说了。
兰兰笑着说:“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去与她理论!”
方翔听了她刚从电视剧里学来的话,不禁也笑了起来,说:“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即使真理在你这边,但碰到蛮不讲理的人和僵守教条者,也永远得不到它们承认的。既然如此,我看算了罢,不必耿耿于怀。”
爷爷·孙子
小强五岁时,他爸爸和妈妈到外地办企业,把他寄养在爷爷家。
小强活泼顽皮,整天光着屁股和弄堂里的孩子玩捉迷藏和老鹰抓小鸡,弄得脸上和全身都脏兮兮的,爷爷说:“你这样脏,晚上我不同你一起睡。”任爷爷怎么说,小强嘻皮笑脸,晚上还是钻到爷爷床底角睡。爷爷只好摇头,要小强奶奶天天给他洗澡后才让他上床。
读小学后,小强迷上了踢足球,放学回来就与邻居的小球迷踢得天昏地黑,时常把邻居的窗玻璃踢碎,邻居上门告状,爷爷少不了又是道歉,又要赔钱。爷爷就要小强放学回家不要踢足球,小强梗着脖子说爷爷旧脑筋,不懂足球。这下爷爷不高兴了:“什么话?我不懂足球!”就拿起话筒打长途电话给小强爸爸,说管不了小强了,要儿子把小强转学到外地,让小强跟他爸妈在一起。小强爸爸就在电话里大声训斥小强,说春节前回家要狠狠地揍他。小强为此噘着小嘴巴好几天不同爷爷讲话。
上中学后,小强在学校操场里踢足球了,爷爷向邻居道歉和赔钱的事也就没有了。但小强放学回家打开电视就看体育频道,后来又喜欢上流行歌曲,什么天王巨星、歌后的,他都能叫得出名字。而爷爷爱看京剧,小强说:“这有什么好看,一个老大娘独自坐着,一唱就是十分钟,也不知她在唱什么,听得烦死人了。”爷爷说:“你不懂艺术,你只配听那些歌星像牛叫似唱的歌!”
爷爷与孙子在艺术欣赏上视角完全不同,意见分歧很大。
这天,某集团公司的旗舰专卖店开业,场面十分宏伟,奏军乐、舞狮子、悬汽球、放白鸽,市领导剪彩,还请来外地一个著名的当红歌星助阵,电视台当晚现场转播。
当那个歌星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手拿话筒,伸拳踢腿,摇头摆臀,又唱又叫时,小强就连连喝彩:“真棒!酷极了!”
小强的爷爷在旁边看着连连摇头:“唱得像码头工人在搬货时呼叫的号子,这算什么艺术?”
“哼!”小强打了个鼻头铳,冷笑一声,脸上露出不屑的神气,那架式分明是在示意爷爷:这是巨星的艺术,你那会欣赏?
爷爷又说话了:“又伸拳又踢腿,这那儿是在唱歌?我看像个走江湖卖膏药的,在卖膏药前拍着胸膛,先弄一套拳脚一样。”
小强不高兴了:“你别再说了好不好!?”
爷爷也生气了:“我又不是在说你,我是说那个唱歌的嘛,嘿嘿,听别人说,他这么干嚎了几分钟,就拿了十多万,这是什么世道!那年郭兰英来,唱得多么好,也只是演完卸妆后吃顿夜餐……”
“你还说!”啪的一声屏幕黑了。
这是小强用遥控器把电视机关掉的。爷爷顿时气得手一拍沙发,走回卧室,用力把卧室的门一推,门关上时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响声。
小强奶奶走进卧室来了,她数落小强爷爷:“你怎么同孙子吵架?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孩子喜欢流行歌曲,他们把那些什么天王啊歌后啊当作偶像来崇拜。这同我们年轻时喜欢和崇拜赵丹、郭兰英不也一样吗?老头子,要知道,他们是新一代追星族啊!”
“我看他们是纨绔子弟,高消费群体!”爷爷并未被说服,反而接着数落起他们来:“穿壹佰多元一件的T恤衫和千元一双的运动鞋,吃一杯冰淇淋要三元,唉!成了新的贵族了。你看,我身上的这件衬衫,十五元!全新的,起码可穿三年哩。”
“你这思想跟不上形势啦,瞧瞧这住宅小区里的孩子们,那个不穿得风风光光,八楼的小丫前天还骑着她爸刚买给她的太空摩托车上学堂读书哩。我说我们小强还是很听话,认真学习的好孩子,老头子,要求不要太高。”
爷爷连连摇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奶奶笑着说:“不要杞人忧天,江山代有才人出,十四亿人口,能出千分之一的精英人物就了不得了。人人都想望子成龙怎么可能?依我看,倒是望子成草符合一般规律。”
“喔,你是想要他们都变成草包?”爷爷被说得笑了起来。
“那能这样说话,我的意思是:草的生命力最强,放在什么地方都能顽强的生存下去。如果大家都愿意像草那样平凡,人世间男人争权夺利,女人争风吃醋的事也就少了许多了。”
“对,说得好!白居易说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草好,草最好。”爷爷笑着逗趣奶奶。
“你不生气了?”
“不生气了。你都望小强成草了,我还生什么屁气。”
“那好,宽容、厚道、上慈、下孝为居家处世修身养性之本。睡吧,睡吧。”奶奶掖了掖他的被子,笑着走出卧室,拐进了她孙子小强的房间。
翌日清晨,小强走进爷爷的卧室,笑着掀开被窝说:“爷爷,爷爷,不要睡懒觉了,快点起床锻炼去,我陪你散步。”
住宅小区傍河的林荫道上,空气里充溢着清新、湿润的气息,绿化地上的杜鹃花一簇簇,红艳艳的,小强扶着他爷爷在散步。
爷爷在林荫道上散步,小强像保镖似的跟着他。
爷爷问小强:“你对爷爷没意见了?”“什么意见?我都忘了呢。”“不与我抢电视频道了?”爷爷笑着问。
“奶奶说,明天去买个小彩电摆到你卧室里给你看,我看大屏幕的。”
“喔,你看大的,爷爷看小的,这公平吗?”
“爷爷,大屏幕磁场幅射大,对你眼睛不利,小彩电好,你可以躺在床上看,这多惬意啊!”小强顽皮地做了个很舒服的样子。
爷爷刮了一下小强的鼻子:“你什么都有理,奶奶真的把你宠坏啦。”
“嘻嘻,嘻嘻,”小强躲到爷爷的背后,用手常轻轻的拍打着爷爷的背脊“爷爷,舒服吗?”
“舒服,舒服,还是我小强好哩。”爷爷绽开笑脸说。
打工·老板
刘海平上高二时,由于家里穷,辍学从边远地区到东南沿海的M城打工,在一家服装厂当个普通修理工。
刘海平健壮英俊,风华正茂,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工作埋头苦干,很得老板的青睐。也成了厂里众多女工的追求对象。缝纫车间的车工闵小虹,也是外来的打工妹,高中文化,长得颀长俊美,气质文静,颇有才情。不久,她与刘海平从互相爱慕到很快堕入爱河。但由于两人都在异地打工,无论从经济状况和客观珠境来说,都尚未具备婚嫁条件,因而也还只是处在热恋阶段。
这天,缝纫车间主任周阿姨叫人通知刘海平,要他到办公室说有事同他商量。
周阿姨五十岁上下,人胖胖的,性格直爽,她笑容可掬开门见山问:“小刘,今年多大了?”
“二十五岁。”
“有爱人了吗?”
“没有,条件不具备,等过几年再说。”
“条件可以创造啊。”她倒了杯茶送到小刘手里“我给你介绍个好不好?”
“周阿姨莫开玩笑,我一个穷打工的,谁愿意嫁给打工的。”
刘海平心里嘀咕:难道是闵小虹?如果是这事,她当面同我讲就行了,何必通过周阿姨呢,哦,是了,姑娘家说这些事总是羞羞答答的,也许周阿姨说的……?于是,他试探着问:“周阿姨,你说的是谁啊?”
“这你先别问,她的要求只要人老实、能干就行。经济条件差问题也不大,她可以资助你,我想就你最合适。”
刘海平听得一头雾水,忙问:“她到底是谁啊?”
“她啊,五官端正,模样俊秀。尤其是家庭经济条件极好,她爸愿意陪嫁女儿一百平方米的结婚房,彩电、冰箱、高档音响齐备,结婚费用全由他来包。你如同意……”
刘海平心里想:这就绝对不是闵小虹了。可是,天上不会掉下好吃的馅饼世上那有这么便宜的事?就笑了起来说:“周阿姨不要开我的玩笑。”说完转身就走。
周阿姨连忙拉住刘海平:“我是同你说真话,你同意的话,这事包在我身上。”
“那她到底是谁家姑娘?”刘海平迟疑着问。
“就是我们这家服装厂老板的女儿,名叫王大丫,虽说年龄比你大三岁,但还是黄花闺女哩。如今城里时兴晚婚,她又会挑拣,所以才未出嫁。怎么样,满意了吧?”
刘海平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乏力地掉到了办公室的沙发上。他见过王大丫,那次他在车间里,她两眼盯着他定神看,嘻嘻地笑着。由于她是老板的女儿,他只得礼貌地报以微笑。过了几天,王大丫脸上抹着厚厚脂粉,穿着红色衣衫又到车间里来,靠近他身旁好久不走。
工友们看到这样子,就打趣她:“大丫,有对象了没有?”
“快啦!有啦!”王大丫接口答。
“几时吃喜糖啊?”
“我要三天订婚,五天就结婚。”
工友们哄堂大笑,她也跟着拍手嘻嘻哈哈笑着。
想起这些事,刘海平说:“周阿姨,她是个弱智的人啊。”
“人是有点那个……可她不缺胳膊不缺腿,模样儿也不错。要不是这样,老板肯花这么多的钱陪嫁?光嫁妆就得一百多万哩。”
刘海平默默无言,他想到了闵小虹。
周阿姨接着开导他:“小刘,你要想得远些,大丫是老板独生女儿,掌上明珠,他想招个女婿上门,还不是为了年纪大了这份家产有个可靠的人?这对你来说是难逢的好运,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我看,你答应这门婚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将来你当了老板,连我都还靠你照顾哩。”
刘海平内心矛盾重重,坐在沙发上低头沉思,半晌,抬头说:“周阿姨,让我再想想,明天告诉你。”
“行,不过,我要提醒你,如果不答应这门亲事,你要考虑……”
这天晚上,刘海平失眼了。尤其是他想到周阿姨那句要考虑后果,要不要饭碗的话时,更无法入睡了。
他起床走到厂女式宿舍的楼下,叫闵小虹下楼来,说有要事与她商量。
夜深沉,月似钩,秋风萧瑟,落叶飘零。两人坐在服装厂生活区旁边的草坪上,四周静悄悄的,气氛十分冷落。刘海平心里像塞着一团乱麻,思绪纷繁,一时不知从何说起,闵小虹见他神色凝重,又不开口说话,就说:“夜这么深了,叫我出来,怎么又不说话?”
刘海平凄楚地叹了口气,这才把周阿姨给王大丫说媒给他,如不答应将会丢掉饭碗;而他已把闵小虹作为红颜知己,心系小虹,难以割舍。但事情又到了别无选择的地步。如不答应大丫亲事,则必被辞退;远离故乡,为了生存,他想来想去只好答应周阿姨的说媒。刘海平说完心事,声泪俱下:“命运迫使我做出了无奈的选择,希望你宽恕我,原谅我,你对我的似海深情我将永生难忘……”
听完刘海平的话,闵小虹沉思半晌,她抑制着痛苦的感情说:“我理解你的处境和你做出的艰难选择,我不会怨恨你,命运使我们相遇在一处,上帝赐给了我们相亲相爱的权利,可这相爱令人感到太沉重、太哀伤了。但是,你我的恋情,将在我的人生苦旅中,永远留下记忆,在凄风苦雨的夜晚伴随着失眠的灯光。”说着,说着,她悲痛得哽咽难言,苍白的脸上掉下了晶莹的泪珠。
……
端午的情结
林益贵
已经年过八旬的爷爷走在下午的烈日之下。他从城市的一条不知名的小巷里走出来——根据他行走时的姿势也许应该说他是一步一步地抠出来的。爷爷要走出这条小巷去乘共公汽车,他想坐在公共汽车到城市的另一方向著名的街道——耀井路。
这是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九年的端午节,也许在爷爷的余生中,这个日子他再也不会忘却了。爷爷要记住端午节,并非因为它是我们的大诗人屈原的祭日,因为爷爷根本就不知道历史上曾经有个大诗人名字叫屈原,如果谁要对爷爷说楚怀王以及屈原的故事,爷爷会说,别在我面前掉书袋?要我学吗,我再也不会学什么了,你对我说了也是白说的。爷爷可以忘掉他自己一年一度的生日,也毫不理会诸如“五·一”、“十·一”等重要的节日,在他心目中,只有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冬节才是每一年中重要的节日,其他的节日对于他们存在与否是一样的。他从来不会去想元旦应该怎么过,劳动节应该如何过,国庆节要怎样过,这些在他的心中并没有很明显的概念。好几年过去了,对于端午节,爷爷总还是津津乐道;每逢端午节,当爷爷的后辈们来到他面前看望他的时候,他总要说起关于端午节与他所遇上的一个好人对他做了件好事的故事。
爷爷在下午的烈日下走着:他右手拿着一包用透明的塑料包装起来的白糖,左手不住地伸进裤兜中拿出那条已经伴随了他两年多的洁白的手绢擦着脸上的汗水。手绢已经湿透了爷爷的裤兜。只是不知道是爷爷额上的汗水经过手绢的转移之后而湿了裤兜还是有汗水如泉般地从爷爷的大腿上涌出来。八十来岁了的爷爷,他漫长的生命旅程中他还未用过拐杖,故而当他在路上走着的时候他还可以腾出一只手来擦犹如泉涌的汗水,尽管缺少第三只脚的帮忙,他依然能够平稳地走着,而且还能健步如飞!
爷爷已经来到了公共汽车的停靠站。当他接近公共汽车的站头时,刚好有一辆他想乘坐的113路汽车要离开。爷爷跑向车站,跑得有点踉跄,但他终于没赶上车。于是,他就到那一建筑在一米见方宽度的公路绿化带上狭窄的候车廓站住,下午的阳光微微仄仄地照射在候车廓的五张深红色的玻璃钢座椅上,还有五六人在候车廓守望,爷爷并不知道他们是否易与他坐同一辆车。爷爷一低头就发现那几张座椅上都有几个非常明显的鞋印,于是,他喃喃地说,谁这么缺德,谁这么缺德啊,这椅子是让人坐的,这样叫人怎么坐呢。说着这些话从裤兜中拿出自己的手绢,将那几张座椅上的鞋印轻轻地擦去,并招呼那些已经站在候车廓的人坐。这时有一个女人满怀感激样地对爷爷说,阿公,你心真好!你这样的好心,一定会活到一百岁的。
爷爷坐下之后片刻,便发现他要乘坐的113路公共汽车的车厢。车厢里已经没有空余的座位了。当白发苍苍的爷爷上车的时候,好几位大红三四十岁左右的纷纷向爷爷打招呼,邀请他坐。爷爷仿佛有点应接不暇了,便不住地说,你们太好了,真对不起你们,你们太好了,对不起你们的。终于,爷爷选择了一个靠右边窗前的座位坐下了。汽车启动的时候,爷爷转过身来向窗外望了望,却见到那一候车廓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了几个穿着学生服的小伙子,他们的屁股坐在那椅子的靠背上,双脚离开了地面,而踩在那几张玻璃的座椅上。爷爷叹了口气,却忽然觉得刚才说他心好的那位女人似乎有点面熟,好像曾经在哪里见过似的,但是在哪里见过,在爷爷的记忆中却掏不出那样子的一个地点。
在汽车上,爷爷发现在车厢里的二三十个人中,他没有一个认识的,他虽然感觉到有点寂寞,只是那点寂寞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因为爷爷找到了打发寂寞的良方,凭着爷爷数十年的生活经验,凭着爷爷所说的“吃过的盐比别人吃过的饭还要多,走过的桥比别人走过的路还要长”的经历,他要找出一些令人洗耳恭听的东西注定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于是爷爷添油加醋说着这个城市里尽人皆知的已经流传了数百年的故事,丰富和充实流传于民间的关于某些伟人的轶事,说着一些貌合神离或者神合貌离的已经被公认了的事件的内幕。于是爷爷又大谈发生在四十年前这城市边缘的故事,大谈“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人遭受某种“凌迟”的故事,讲二十年前在发生在这个城市的市长身边的桃色事件……每一桩事他都只讲了一点点,不住地跳跃着话题,在公共汽车的车厢里留下了许多悬念。爷爷爽朗的声音在车厢里回旋,就连公共汽车司机也好像受了爷爷所说的故事的吸引,特意将车开得很慢很慢,似乎生怕假如开得快了,会错过了爷爷说着的故事的结局。汽车非常平稳地在街道上行驶,一车的乘客全都沉醉在爷爷的话语中,好几个人甚至忘了在他们的目的地下车,直到来到下一站头公共汽车的自动报站系统说出了站名的时候,他们才猛然省悟原来乘车已经乘过头了,只好非常惋惜地下了车。
忽然,爷爷的眼前一亮,他知道他应该下车了。他忽然将他说着的东西全部收住,爷的话题题好像是放牧在草场上的羊群,天黑之时它们都要回到栏圈里去了。却露出赞赏的眼神,说,这里的变化真大,这里的变化偌大!前年还是一片荒着的地,里面有十几间茅草盖起来的厕所,一大片草乱糟糟地长着,到黄昏时分,蚊子飞来飞去地伸手可以抓到一大把。现在都变成屋了。这些屋还造得这么高这么好看!
爷爷下了车,从一条小巷进去了。因为他知道从这条小巷里进去,是抄了条捷径。耀井路在爷爷八十多年的生涯的光辉历程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尽管耀井路也许可以算是这个城市里被冠以“××路”名的路当中最为狭窄的一条路了。但是爷爷清楚地记得它曾经的繁华:多年以来,它一直是以这个城市的商贸中心地带,吃穿住用行一应俱全,虽然大约仅仅能通过一辆大客车的宽度,两端低矮的房屋都仅仅只是一层楼的高度,路边的很多房子在爷爷最初见到时就显得老气横秋了,有几间甚至歪歪的好像就人躺倒在地上。它们全都充满着古色古色的气息,据说其中最老的房子年龄已经有六百多岁了。可就是在这些古老的房子所簇拥的这条马路上,爷爷曾经数次一连走了七八个小时的路从八十里的乡下来到耀井路,而后精心在那些小店中挑选锄头和犁耙等种地的工具带回到乡下。当年爷爷还住在乡下的时候,每次在耀井路买了东西回到乡下之后,总要对那些十几岁二十来岁的青年讲述城市里的盛景,在言谈中不时地表达出一种非常自豪的情怀,耀井路也经常成为爷爷在夏日的星空之下与他的后辈们分享的乘凉的话题,爷爷讲述这个城市尤其耀井路上的风景,讲述耀路上曾经发生过的许多故事,讲述他们的山村与耀井路的关系……在夏日的星空下,爷爷讲得每一件事总给他早年生活的乡村,他已经生活了生命中的绝大部分时光的山村带来神往与期待。爷爷所说的关于这座城市,关于繁华的耀井路的每一个音节都好像是夜空中的星星,在乡民的头顶上在他们的眼前闪烁着幽幽的光芒,照亮了他们的夏夜。耀井路上还有一根电线杆,让爷爷刻骨铭——三十年前的一天,一群戴着红袖章的小孩子硬是将爷爷拉过去在那根电线杆上捆了半天,这是爷爷此生所遭受的唯一的却是最为痛苦的一次折磨。每当爷爷说起那些小毛孩子的来历时,他总要愤愤地骂上几十分钟,并总要流露出非常悲伤的神色说起当时他在柱子上的小家伙付之一炬的那种盛况空前的火光。电线杆是混凝土浇铸的,中间的一段却是用铁片连接起来的,仿佛一个人伤了手之后打上了绷带,此特征爷爷记忆得非常深刻。那一层铁片仿佛萦绕着爷爷此生的那一段遭际,仿佛隐藏了也仿佛是记录了爷爷此生所经受的不愿人提及的那一段伤痕。
此时,爷爷面对着的却是一排废墟。从前车水马龙的景象已经只是他脑海中的残枝败叶了,那些低矮的房子,那一间接一间的小店铺都已经消失,只见三三两两的零星几个人在这堆废墟上忙碌着。爷爷只看到他们弓着背起起落落地,爷爷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在忙着什么。
哦,人已经搬走了,人都已经搬光了吧。爷爷喃喃地自言自语……那一位好人搬到哪里去了……
去年的端午节,爷爷第五十次经过耀井路。他发觉那耀井路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繁华依旧,,依然是那样的车水马龙,依然那样地熙熙攘攘。在又一次经过那根特征鲜明的电线杆下时,爷爷不由自由主地好像瞻仰灵隐寺里的佛祖塑像一般地肃穆在这根电线杆下,许久许久。那时刻,电线杆边的面摊的老板见到爷爷那股庄重的神色,他们也觉得非常诧异,大概就是怀着对爷爷这种专注眼神的好奇吧。不知多少小时过去,眼见的夕阳已经西仄,夕阳的余辉不经意地将那根电线杆涂上了一层金黄色。爷爷终于起身要走了。在这一段时间里,谁能断定爷爷的手脚是否曾经动过毫厘。
忽然,爷爷朦胧地听到有人呼喊,阿公,你的钱……,阿公,你的钱掉了。爷爷认为那声音与他无关的。因为他此前的几百次来到这个城市,尚未有人叫过他“阿公”往常有人叫他“公”字的时候,“公”字总带着意义非常明确的前缀,比如外公,比如舅公……而没有人直接用“阿公”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称呼来叫他的,“阿”算是怎样的一种意义呢,是表示尊敬还是表示蔑视,是表示亲近还是表示相当疏远的关系,实在无法确定。直到有人跑到他的前面了,爷爷才知道那非常清脆的“阿公”声就是朝着他喊的。同时,爷爷也注意到了跑到他前面说他钱丢了的是一个年约四十岁的女人,她的胸前系着一条白色的围裙,白色的围裙,白色的围裙是黑一块黄一块的。爷爷说,你看错了吧,我的钱在裤兜中好好地呆着呢,不会是我丢的,你在这里等待那一位丢了钱的人吧。女人说,阿公,这是你的吗?她边说边将手上的一张塑料纸拿到爷爷的面前。塑料纸中四五张百元币折叠得方方正正地弓着。看到这样的包装,爷爷终于把手伸进裤兜,裤兜中的钱确实不见了。于是,爷爷非常高兴地将他的钱拿回来。
直到今天,在这个端午节前,许多次,爷爷提起这一件事,他若有感慨地说,这样好的人不多的,捡到了钱并把钱还给人家这样的人很少的。很多人看到别人丢掉的钱,往自己的腰包里揣还惟恐来不及。那个女人的良心这么好,我应该拿点东西去酬谢她……哎,我这一生从来没吃过别人的苦水,从来不占别人的便宜,只有别人占我的便宜,让人一点,也是积德呀。我已经积下了不少的功德,我一定会很平安的,老了的时候一定不会拖累后辈的。我积下的功德,也会让你们后辈一生平安的!忽然又是一个端午节来临!爷爷从小店里买了一包糖。
爷爷站在那一根电线杆边,若有感慨般地对着耀井路。先年的繁华景象忽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的仅只是一片破破烂烂的废墟,原本鳞次栉比的小屋如今已经只剩下断壁残垣。爷爷轻轻地说,多么可惜呀,那些整日可以赚到很多钱的人,现在他们到哪里去找那容易赚钱的地方呢,好好的一条街道,就这样消失了。
爷爷发现,在废墟的两边,先年不会出现的一些房子,忽然出现在这一片废墟的两侧,那些房子也与原来排列在耀井路两侧的那些屋子一个模样,也是那么低矮,那么黑乎乎地排列着,那些屋檐下仿佛有人群攒动的模样。而那根电线杆依然那么坚强地挺立在废墟中,很有点鹤立鸡群的味道。
爷爷瞥了一眼那根电线杆,又看了一眼那位对他拾金不昧的女人曾经住过的那一块地盘。忽然,爷爷发现:地上躺着几张百元的大钞,也是用那种无色透明的塑料纸包着的,与爷爷去年丢在那儿的钱包装一模一样。
爷爷俯下身子,伸手小心翼翼地将这一包钱拿了起来,他的右手伸进自己的裤兜中,发现自己的裤兜中的钱还安稳地呆着。爷爷将钱高高地举起,大声地喊,谁丢了钱,谁钱丢了?
转眼间,一个多小时已经过去,夕阳已经开始西下。阳光正在渐渐地黯淡,太阳的脸蛋红红地挂在西边的天空中,也染红了爷爷的饱经沧桑的老脸。夕阳装饰在云海,那种远方的鲜红色,在爷爷前的废墟上烙下了火一样的颜色,隐隐约约地照出废墟上的一点光明,是紫色的。
终于爷爷见到有人向他中来,那个人似乎低着头焦急地寻打着什么东西似的。爷爷关切地部,后生儿,你丢了钱,是吗?那是一面色黝黑的男青年,只有十八九岁的样子。他跑得那么匆忙,当爷爷冷不丁地那样问他的时候,他先是一愣,似乎并不知道爷爷在问他什么。当他一眼看到爷爷手中的钱时,连忙换成一幅高兴的神色,说,阿公,我中午在这一段路上丢了钱,现在正在寻找着呢。您已经捡到了?谢谢你。爷爷说,这钱大概是你的了,拿回去吧,注意放得好一点,钱难赚啊。
这个小伙子一把抓过爷爷手中的钱,依然快速地跑着,倏忽便消失在废墟上,仿佛已经在地平线上沉没了,一个黑影渐渐消失在夜幕降临的时候。
望着那个小伙子远去的背影,爷爷欣慰地说,我又积了一回德了!
回家之后,爷爷如往常一样要数一下他口袋的钱。可是,当他将手伸进右侧的裤兜时,却发现裤兜已经空了,什么也没有。
这三百元钱哪里去了呢,一定是让那个娃娃骗走了。爷爷略带忧伤地说,看来,我的这些钱是注定要丢的。破财消灾,破财消灾,爷爷淡淡地说,今年我们会更平安了。
李永汉
秀才·文盲
方翔大学本科毕业,写得一手好文章,是单位里公认的秀才;他妻子兰兰只读到小学三年级,连报纸也看不懂,基本上是文盲。文化差距如此之大,怎么会结合在一起呢?单位里有些人开始也弄不懂,后来才逐渐清楚,这里边包含着特殊因素。
兰兰的父亲贫农出身,她本人是产业工人,长得清丽俊俏,亭亭玉立;方翔虽是秀才,但那时的说法,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子又不高,戴着副深度眼镜。他和兰兰结成夫妻,据方翔说是响应“知识分子要和工农分子相结合”的号召,可兰兰说是方翔攀了高枝,让“她的优势补了他的劣势”。不管怎么说,反正这起婚事是抹上了那个时代的时髦潮流色彩罢了。
基于上面这些原因,婚后方翔在兰兰面前就低了一截,惟命是从。尽管如此,但小两口还是恩恩爱爱过着日子。没四、五年,孩子一个接着一个来到人间,于是家务事也就跟着多起来了。
夫妻俩平日上班,他们和孩子的脏衣物只好集中在星期天洗涤。兰兰站在井旁,把板刷和肥皂交给他说:“你刷,我洗。”
方翔“噢”的应了一声弯着身子刷起来,兰兰又嫌他抓不住重点,说:“上衣领头和袖口,裤屁股和裤脚是比较脏的地方,要用力刷。”他马上改进,照办。
方翔刷完衣物,兰兰又把吊桶交给他:“把井水吊上来,让我漂洗。”他又“噢”了一声把吊桶放进井里开始吊水。
方翔这么听妻子的话,还有个绝对不能同别人说的隐秘:兰兰长得漂亮,很得他的欢心,但她性格倔犟,如顺着她的话去做,夜里她对他就风情万状,体贴入微,如不按她的话办,她就冷若冰霜,拿起枕头到床那一头去睡。
后来,市场上有了洗衣机,方翔就去买了一只。但兰兰还是站在洗衣机旁指指点点,说衣裤的每个口袋都要先检查一遍,不要让硬币或杂物掉进去,以免损坏洗衣机;衣服领头和袖口等重点处要先刷一番再放进去等等。
这天,是休息日。上午,方翔把头一天晚上全家浴后的衣服放进洗衣机,按照程序,扭开水龙头开关,设定“标准洗涤”的按钮,洗衣机就按照指令转动起来了。
可是,没有多久,洗衣机发出了“轧、轧”的响声,最后干脆停了下来:离心机不转,出水口也不畅通了。方翔束手无策,心虚地对兰兰说:“你看是否请个师傅来修理?”兰兰白了他一眼:“张口就是请人,没80元修理费行吗?恐怕又是硬币卡了出水口,让我试试看。”这倒是事实,以前这洗衣机就曾发生过硬币卡住出水口的事。于是,他抓着头皮自责地说:“可能又是我不小心,在某次洗衣时忘了检口袋,那就麻烦你动手查一查吧。”
兰兰在厂里曾干过钳工,她拿来螺丝刀三下两下拆开洗衣机的后盖板,检查了输水管道,果真是两个一元钱的硬币卡住出水口,硬币锈迹斑斑的,看来是掉进去好些时间了,慢慢被冲洗到出水口卡住的。兰兰把它挖了出来,再按照程序设定按钮,洗衣机就又转了起来。兰兰要方翔拿这两个硬币去农贸市场买菜。摊主秤好菜接过硬币一看,说:“这钱不好用!”方翔说:“硬币上的国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994年的字迹都还认得出来,只是锈了而已,怎么不好用?”
“不好用就不好用!”摊主断然拒绝。方翔只好空着双手回家。
兰兰听了他没买来菜的原委后说:“你不会到银行去调换?连这点脑筋都转不过来,还能写出好文章!”
方翔拍拍脑袋,说了声:“真是的。”到附近一家银行分理处去了。
储蓄柜一个涂抹着口红的小姐拿着硬币看了半晌,皱着眉头问:“这钱怎么锈得这样?”方翔就把洗衣时忘了检口袋,让硬币掉到洗衣机里,卡住出水口,时间久了,生了锈等等说了一遍。
“我们银行规定,锈的不能调换!”
于是,他又把国徽和字迹还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话重复了一遍,可是这位小姐最终还是拒绝调换,他只得手里又捏着这两枚硬币返家。
兰兰正在厨房洗碗,方翔把银行不肯调换的话对她说了。她乜了他一眼,接过硬币用废铁丝球使劲揩擦了几下,不到半分钟,硬币露出了本色,锃光闪亮的。她说:“这硬币本来就是好的嘛,你去与他们理论!”
方翔摇头叹息,心里有了一种说不出来的不平之感:秀才碰见兵有理讲不清。倒还可以说得过去。可遇到银行小姐,怎么也有理讲不清!?他把这个意思同兰兰说了。
兰兰笑着说:“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去与她理论!”
方翔听了她刚从电视剧里学来的话,不禁也笑了起来,说:“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即使真理在你这边,但碰到蛮不讲理的人和僵守教条者,也永远得不到它们承认的。既然如此,我看算了罢,不必耿耿于怀。”
爷爷·孙子
小强五岁时,他爸爸和妈妈到外地办企业,把他寄养在爷爷家。
小强活泼顽皮,整天光着屁股和弄堂里的孩子玩捉迷藏和老鹰抓小鸡,弄得脸上和全身都脏兮兮的,爷爷说:“你这样脏,晚上我不同你一起睡。”任爷爷怎么说,小强嘻皮笑脸,晚上还是钻到爷爷床底角睡。爷爷只好摇头,要小强奶奶天天给他洗澡后才让他上床。
读小学后,小强迷上了踢足球,放学回来就与邻居的小球迷踢得天昏地黑,时常把邻居的窗玻璃踢碎,邻居上门告状,爷爷少不了又是道歉,又要赔钱。爷爷就要小强放学回家不要踢足球,小强梗着脖子说爷爷旧脑筋,不懂足球。这下爷爷不高兴了:“什么话?我不懂足球!”就拿起话筒打长途电话给小强爸爸,说管不了小强了,要儿子把小强转学到外地,让小强跟他爸妈在一起。小强爸爸就在电话里大声训斥小强,说春节前回家要狠狠地揍他。小强为此噘着小嘴巴好几天不同爷爷讲话。
上中学后,小强在学校操场里踢足球了,爷爷向邻居道歉和赔钱的事也就没有了。但小强放学回家打开电视就看体育频道,后来又喜欢上流行歌曲,什么天王巨星、歌后的,他都能叫得出名字。而爷爷爱看京剧,小强说:“这有什么好看,一个老大娘独自坐着,一唱就是十分钟,也不知她在唱什么,听得烦死人了。”爷爷说:“你不懂艺术,你只配听那些歌星像牛叫似唱的歌!”
爷爷与孙子在艺术欣赏上视角完全不同,意见分歧很大。
这天,某集团公司的旗舰专卖店开业,场面十分宏伟,奏军乐、舞狮子、悬汽球、放白鸽,市领导剪彩,还请来外地一个著名的当红歌星助阵,电视台当晚现场转播。
当那个歌星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手拿话筒,伸拳踢腿,摇头摆臀,又唱又叫时,小强就连连喝彩:“真棒!酷极了!”
小强的爷爷在旁边看着连连摇头:“唱得像码头工人在搬货时呼叫的号子,这算什么艺术?”
“哼!”小强打了个鼻头铳,冷笑一声,脸上露出不屑的神气,那架式分明是在示意爷爷:这是巨星的艺术,你那会欣赏?
爷爷又说话了:“又伸拳又踢腿,这那儿是在唱歌?我看像个走江湖卖膏药的,在卖膏药前拍着胸膛,先弄一套拳脚一样。”
小强不高兴了:“你别再说了好不好!?”
爷爷也生气了:“我又不是在说你,我是说那个唱歌的嘛,嘿嘿,听别人说,他这么干嚎了几分钟,就拿了十多万,这是什么世道!那年郭兰英来,唱得多么好,也只是演完卸妆后吃顿夜餐……”
“你还说!”啪的一声屏幕黑了。
这是小强用遥控器把电视机关掉的。爷爷顿时气得手一拍沙发,走回卧室,用力把卧室的门一推,门关上时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响声。
小强奶奶走进卧室来了,她数落小强爷爷:“你怎么同孙子吵架?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孩子喜欢流行歌曲,他们把那些什么天王啊歌后啊当作偶像来崇拜。这同我们年轻时喜欢和崇拜赵丹、郭兰英不也一样吗?老头子,要知道,他们是新一代追星族啊!”
“我看他们是纨绔子弟,高消费群体!”爷爷并未被说服,反而接着数落起他们来:“穿壹佰多元一件的T恤衫和千元一双的运动鞋,吃一杯冰淇淋要三元,唉!成了新的贵族了。你看,我身上的这件衬衫,十五元!全新的,起码可穿三年哩。”
“你这思想跟不上形势啦,瞧瞧这住宅小区里的孩子们,那个不穿得风风光光,八楼的小丫前天还骑着她爸刚买给她的太空摩托车上学堂读书哩。我说我们小强还是很听话,认真学习的好孩子,老头子,要求不要太高。”
爷爷连连摇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奶奶笑着说:“不要杞人忧天,江山代有才人出,十四亿人口,能出千分之一的精英人物就了不得了。人人都想望子成龙怎么可能?依我看,倒是望子成草符合一般规律。”
“喔,你是想要他们都变成草包?”爷爷被说得笑了起来。
“那能这样说话,我的意思是:草的生命力最强,放在什么地方都能顽强的生存下去。如果大家都愿意像草那样平凡,人世间男人争权夺利,女人争风吃醋的事也就少了许多了。”
“对,说得好!白居易说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草好,草最好。”爷爷笑着逗趣奶奶。
“你不生气了?”
“不生气了。你都望小强成草了,我还生什么屁气。”
“那好,宽容、厚道、上慈、下孝为居家处世修身养性之本。睡吧,睡吧。”奶奶掖了掖他的被子,笑着走出卧室,拐进了她孙子小强的房间。
翌日清晨,小强走进爷爷的卧室,笑着掀开被窝说:“爷爷,爷爷,不要睡懒觉了,快点起床锻炼去,我陪你散步。”
住宅小区傍河的林荫道上,空气里充溢着清新、湿润的气息,绿化地上的杜鹃花一簇簇,红艳艳的,小强扶着他爷爷在散步。
爷爷在林荫道上散步,小强像保镖似的跟着他。
爷爷问小强:“你对爷爷没意见了?”“什么意见?我都忘了呢。”“不与我抢电视频道了?”爷爷笑着问。
“奶奶说,明天去买个小彩电摆到你卧室里给你看,我看大屏幕的。”
“喔,你看大的,爷爷看小的,这公平吗?”
“爷爷,大屏幕磁场幅射大,对你眼睛不利,小彩电好,你可以躺在床上看,这多惬意啊!”小强顽皮地做了个很舒服的样子。
爷爷刮了一下小强的鼻子:“你什么都有理,奶奶真的把你宠坏啦。”
“嘻嘻,嘻嘻,”小强躲到爷爷的背后,用手常轻轻的拍打着爷爷的背脊“爷爷,舒服吗?”
“舒服,舒服,还是我小强好哩。”爷爷绽开笑脸说。
打工·老板
刘海平上高二时,由于家里穷,辍学从边远地区到东南沿海的M城打工,在一家服装厂当个普通修理工。
刘海平健壮英俊,风华正茂,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工作埋头苦干,很得老板的青睐。也成了厂里众多女工的追求对象。缝纫车间的车工闵小虹,也是外来的打工妹,高中文化,长得颀长俊美,气质文静,颇有才情。不久,她与刘海平从互相爱慕到很快堕入爱河。但由于两人都在异地打工,无论从经济状况和客观珠境来说,都尚未具备婚嫁条件,因而也还只是处在热恋阶段。
这天,缝纫车间主任周阿姨叫人通知刘海平,要他到办公室说有事同他商量。
周阿姨五十岁上下,人胖胖的,性格直爽,她笑容可掬开门见山问:“小刘,今年多大了?”
“二十五岁。”
“有爱人了吗?”
“没有,条件不具备,等过几年再说。”
“条件可以创造啊。”她倒了杯茶送到小刘手里“我给你介绍个好不好?”
“周阿姨莫开玩笑,我一个穷打工的,谁愿意嫁给打工的。”
刘海平心里嘀咕:难道是闵小虹?如果是这事,她当面同我讲就行了,何必通过周阿姨呢,哦,是了,姑娘家说这些事总是羞羞答答的,也许周阿姨说的……?于是,他试探着问:“周阿姨,你说的是谁啊?”
“这你先别问,她的要求只要人老实、能干就行。经济条件差问题也不大,她可以资助你,我想就你最合适。”
刘海平听得一头雾水,忙问:“她到底是谁啊?”
“她啊,五官端正,模样俊秀。尤其是家庭经济条件极好,她爸愿意陪嫁女儿一百平方米的结婚房,彩电、冰箱、高档音响齐备,结婚费用全由他来包。你如同意……”
刘海平心里想:这就绝对不是闵小虹了。可是,天上不会掉下好吃的馅饼世上那有这么便宜的事?就笑了起来说:“周阿姨不要开我的玩笑。”说完转身就走。
周阿姨连忙拉住刘海平:“我是同你说真话,你同意的话,这事包在我身上。”
“那她到底是谁家姑娘?”刘海平迟疑着问。
“就是我们这家服装厂老板的女儿,名叫王大丫,虽说年龄比你大三岁,但还是黄花闺女哩。如今城里时兴晚婚,她又会挑拣,所以才未出嫁。怎么样,满意了吧?”
刘海平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乏力地掉到了办公室的沙发上。他见过王大丫,那次他在车间里,她两眼盯着他定神看,嘻嘻地笑着。由于她是老板的女儿,他只得礼貌地报以微笑。过了几天,王大丫脸上抹着厚厚脂粉,穿着红色衣衫又到车间里来,靠近他身旁好久不走。
工友们看到这样子,就打趣她:“大丫,有对象了没有?”
“快啦!有啦!”王大丫接口答。
“几时吃喜糖啊?”
“我要三天订婚,五天就结婚。”
工友们哄堂大笑,她也跟着拍手嘻嘻哈哈笑着。
想起这些事,刘海平说:“周阿姨,她是个弱智的人啊。”
“人是有点那个……可她不缺胳膊不缺腿,模样儿也不错。要不是这样,老板肯花这么多的钱陪嫁?光嫁妆就得一百多万哩。”
刘海平默默无言,他想到了闵小虹。
周阿姨接着开导他:“小刘,你要想得远些,大丫是老板独生女儿,掌上明珠,他想招个女婿上门,还不是为了年纪大了这份家产有个可靠的人?这对你来说是难逢的好运,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我看,你答应这门婚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将来你当了老板,连我都还靠你照顾哩。”
刘海平内心矛盾重重,坐在沙发上低头沉思,半晌,抬头说:“周阿姨,让我再想想,明天告诉你。”
“行,不过,我要提醒你,如果不答应这门亲事,你要考虑……”
这天晚上,刘海平失眼了。尤其是他想到周阿姨那句要考虑后果,要不要饭碗的话时,更无法入睡了。
他起床走到厂女式宿舍的楼下,叫闵小虹下楼来,说有要事与她商量。
夜深沉,月似钩,秋风萧瑟,落叶飘零。两人坐在服装厂生活区旁边的草坪上,四周静悄悄的,气氛十分冷落。刘海平心里像塞着一团乱麻,思绪纷繁,一时不知从何说起,闵小虹见他神色凝重,又不开口说话,就说:“夜这么深了,叫我出来,怎么又不说话?”
刘海平凄楚地叹了口气,这才把周阿姨给王大丫说媒给他,如不答应将会丢掉饭碗;而他已把闵小虹作为红颜知己,心系小虹,难以割舍。但事情又到了别无选择的地步。如不答应大丫亲事,则必被辞退;远离故乡,为了生存,他想来想去只好答应周阿姨的说媒。刘海平说完心事,声泪俱下:“命运迫使我做出了无奈的选择,希望你宽恕我,原谅我,你对我的似海深情我将永生难忘……”
听完刘海平的话,闵小虹沉思半晌,她抑制着痛苦的感情说:“我理解你的处境和你做出的艰难选择,我不会怨恨你,命运使我们相遇在一处,上帝赐给了我们相亲相爱的权利,可这相爱令人感到太沉重、太哀伤了。但是,你我的恋情,将在我的人生苦旅中,永远留下记忆,在凄风苦雨的夜晚伴随着失眠的灯光。”说着,说着,她悲痛得哽咽难言,苍白的脸上掉下了晶莹的泪珠。
……
端午的情结
林益贵
已经年过八旬的爷爷走在下午的烈日之下。他从城市的一条不知名的小巷里走出来——根据他行走时的姿势也许应该说他是一步一步地抠出来的。爷爷要走出这条小巷去乘共公汽车,他想坐在公共汽车到城市的另一方向著名的街道——耀井路。
这是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九年的端午节,也许在爷爷的余生中,这个日子他再也不会忘却了。爷爷要记住端午节,并非因为它是我们的大诗人屈原的祭日,因为爷爷根本就不知道历史上曾经有个大诗人名字叫屈原,如果谁要对爷爷说楚怀王以及屈原的故事,爷爷会说,别在我面前掉书袋?要我学吗,我再也不会学什么了,你对我说了也是白说的。爷爷可以忘掉他自己一年一度的生日,也毫不理会诸如“五·一”、“十·一”等重要的节日,在他心目中,只有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冬节才是每一年中重要的节日,其他的节日对于他们存在与否是一样的。他从来不会去想元旦应该怎么过,劳动节应该如何过,国庆节要怎样过,这些在他的心中并没有很明显的概念。好几年过去了,对于端午节,爷爷总还是津津乐道;每逢端午节,当爷爷的后辈们来到他面前看望他的时候,他总要说起关于端午节与他所遇上的一个好人对他做了件好事的故事。
爷爷在下午的烈日下走着:他右手拿着一包用透明的塑料包装起来的白糖,左手不住地伸进裤兜中拿出那条已经伴随了他两年多的洁白的手绢擦着脸上的汗水。手绢已经湿透了爷爷的裤兜。只是不知道是爷爷额上的汗水经过手绢的转移之后而湿了裤兜还是有汗水如泉般地从爷爷的大腿上涌出来。八十来岁了的爷爷,他漫长的生命旅程中他还未用过拐杖,故而当他在路上走着的时候他还可以腾出一只手来擦犹如泉涌的汗水,尽管缺少第三只脚的帮忙,他依然能够平稳地走着,而且还能健步如飞!
爷爷已经来到了公共汽车的停靠站。当他接近公共汽车的站头时,刚好有一辆他想乘坐的113路汽车要离开。爷爷跑向车站,跑得有点踉跄,但他终于没赶上车。于是,他就到那一建筑在一米见方宽度的公路绿化带上狭窄的候车廓站住,下午的阳光微微仄仄地照射在候车廓的五张深红色的玻璃钢座椅上,还有五六人在候车廓守望,爷爷并不知道他们是否易与他坐同一辆车。爷爷一低头就发现那几张座椅上都有几个非常明显的鞋印,于是,他喃喃地说,谁这么缺德,谁这么缺德啊,这椅子是让人坐的,这样叫人怎么坐呢。说着这些话从裤兜中拿出自己的手绢,将那几张座椅上的鞋印轻轻地擦去,并招呼那些已经站在候车廓的人坐。这时有一个女人满怀感激样地对爷爷说,阿公,你心真好!你这样的好心,一定会活到一百岁的。
爷爷坐下之后片刻,便发现他要乘坐的113路公共汽车的车厢。车厢里已经没有空余的座位了。当白发苍苍的爷爷上车的时候,好几位大红三四十岁左右的纷纷向爷爷打招呼,邀请他坐。爷爷仿佛有点应接不暇了,便不住地说,你们太好了,真对不起你们,你们太好了,对不起你们的。终于,爷爷选择了一个靠右边窗前的座位坐下了。汽车启动的时候,爷爷转过身来向窗外望了望,却见到那一候车廓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了几个穿着学生服的小伙子,他们的屁股坐在那椅子的靠背上,双脚离开了地面,而踩在那几张玻璃的座椅上。爷爷叹了口气,却忽然觉得刚才说他心好的那位女人似乎有点面熟,好像曾经在哪里见过似的,但是在哪里见过,在爷爷的记忆中却掏不出那样子的一个地点。
在汽车上,爷爷发现在车厢里的二三十个人中,他没有一个认识的,他虽然感觉到有点寂寞,只是那点寂寞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因为爷爷找到了打发寂寞的良方,凭着爷爷数十年的生活经验,凭着爷爷所说的“吃过的盐比别人吃过的饭还要多,走过的桥比别人走过的路还要长”的经历,他要找出一些令人洗耳恭听的东西注定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于是爷爷添油加醋说着这个城市里尽人皆知的已经流传了数百年的故事,丰富和充实流传于民间的关于某些伟人的轶事,说着一些貌合神离或者神合貌离的已经被公认了的事件的内幕。于是爷爷又大谈发生在四十年前这城市边缘的故事,大谈“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人遭受某种“凌迟”的故事,讲二十年前在发生在这个城市的市长身边的桃色事件……每一桩事他都只讲了一点点,不住地跳跃着话题,在公共汽车的车厢里留下了许多悬念。爷爷爽朗的声音在车厢里回旋,就连公共汽车司机也好像受了爷爷所说的故事的吸引,特意将车开得很慢很慢,似乎生怕假如开得快了,会错过了爷爷说着的故事的结局。汽车非常平稳地在街道上行驶,一车的乘客全都沉醉在爷爷的话语中,好几个人甚至忘了在他们的目的地下车,直到来到下一站头公共汽车的自动报站系统说出了站名的时候,他们才猛然省悟原来乘车已经乘过头了,只好非常惋惜地下了车。
忽然,爷爷的眼前一亮,他知道他应该下车了。他忽然将他说着的东西全部收住,爷的话题题好像是放牧在草场上的羊群,天黑之时它们都要回到栏圈里去了。却露出赞赏的眼神,说,这里的变化真大,这里的变化偌大!前年还是一片荒着的地,里面有十几间茅草盖起来的厕所,一大片草乱糟糟地长着,到黄昏时分,蚊子飞来飞去地伸手可以抓到一大把。现在都变成屋了。这些屋还造得这么高这么好看!
爷爷下了车,从一条小巷进去了。因为他知道从这条小巷里进去,是抄了条捷径。耀井路在爷爷八十多年的生涯的光辉历程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尽管耀井路也许可以算是这个城市里被冠以“××路”名的路当中最为狭窄的一条路了。但是爷爷清楚地记得它曾经的繁华:多年以来,它一直是以这个城市的商贸中心地带,吃穿住用行一应俱全,虽然大约仅仅能通过一辆大客车的宽度,两端低矮的房屋都仅仅只是一层楼的高度,路边的很多房子在爷爷最初见到时就显得老气横秋了,有几间甚至歪歪的好像就人躺倒在地上。它们全都充满着古色古色的气息,据说其中最老的房子年龄已经有六百多岁了。可就是在这些古老的房子所簇拥的这条马路上,爷爷曾经数次一连走了七八个小时的路从八十里的乡下来到耀井路,而后精心在那些小店中挑选锄头和犁耙等种地的工具带回到乡下。当年爷爷还住在乡下的时候,每次在耀井路买了东西回到乡下之后,总要对那些十几岁二十来岁的青年讲述城市里的盛景,在言谈中不时地表达出一种非常自豪的情怀,耀井路也经常成为爷爷在夏日的星空之下与他的后辈们分享的乘凉的话题,爷爷讲述这个城市尤其耀井路上的风景,讲述耀路上曾经发生过的许多故事,讲述他们的山村与耀井路的关系……在夏日的星空下,爷爷讲得每一件事总给他早年生活的乡村,他已经生活了生命中的绝大部分时光的山村带来神往与期待。爷爷所说的关于这座城市,关于繁华的耀井路的每一个音节都好像是夜空中的星星,在乡民的头顶上在他们的眼前闪烁着幽幽的光芒,照亮了他们的夏夜。耀井路上还有一根电线杆,让爷爷刻骨铭——三十年前的一天,一群戴着红袖章的小孩子硬是将爷爷拉过去在那根电线杆上捆了半天,这是爷爷此生所遭受的唯一的却是最为痛苦的一次折磨。每当爷爷说起那些小毛孩子的来历时,他总要愤愤地骂上几十分钟,并总要流露出非常悲伤的神色说起当时他在柱子上的小家伙付之一炬的那种盛况空前的火光。电线杆是混凝土浇铸的,中间的一段却是用铁片连接起来的,仿佛一个人伤了手之后打上了绷带,此特征爷爷记忆得非常深刻。那一层铁片仿佛萦绕着爷爷此生的那一段遭际,仿佛隐藏了也仿佛是记录了爷爷此生所经受的不愿人提及的那一段伤痕。
此时,爷爷面对着的却是一排废墟。从前车水马龙的景象已经只是他脑海中的残枝败叶了,那些低矮的房子,那一间接一间的小店铺都已经消失,只见三三两两的零星几个人在这堆废墟上忙碌着。爷爷只看到他们弓着背起起落落地,爷爷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在忙着什么。
哦,人已经搬走了,人都已经搬光了吧。爷爷喃喃地自言自语……那一位好人搬到哪里去了……
去年的端午节,爷爷第五十次经过耀井路。他发觉那耀井路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繁华依旧,,依然是那样的车水马龙,依然那样地熙熙攘攘。在又一次经过那根特征鲜明的电线杆下时,爷爷不由自由主地好像瞻仰灵隐寺里的佛祖塑像一般地肃穆在这根电线杆下,许久许久。那时刻,电线杆边的面摊的老板见到爷爷那股庄重的神色,他们也觉得非常诧异,大概就是怀着对爷爷这种专注眼神的好奇吧。不知多少小时过去,眼见的夕阳已经西仄,夕阳的余辉不经意地将那根电线杆涂上了一层金黄色。爷爷终于起身要走了。在这一段时间里,谁能断定爷爷的手脚是否曾经动过毫厘。
忽然,爷爷朦胧地听到有人呼喊,阿公,你的钱……,阿公,你的钱掉了。爷爷认为那声音与他无关的。因为他此前的几百次来到这个城市,尚未有人叫过他“阿公”往常有人叫他“公”字的时候,“公”字总带着意义非常明确的前缀,比如外公,比如舅公……而没有人直接用“阿公”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称呼来叫他的,“阿”算是怎样的一种意义呢,是表示尊敬还是表示蔑视,是表示亲近还是表示相当疏远的关系,实在无法确定。直到有人跑到他的前面了,爷爷才知道那非常清脆的“阿公”声就是朝着他喊的。同时,爷爷也注意到了跑到他前面说他钱丢了的是一个年约四十岁的女人,她的胸前系着一条白色的围裙,白色的围裙,白色的围裙是黑一块黄一块的。爷爷说,你看错了吧,我的钱在裤兜中好好地呆着呢,不会是我丢的,你在这里等待那一位丢了钱的人吧。女人说,阿公,这是你的吗?她边说边将手上的一张塑料纸拿到爷爷的面前。塑料纸中四五张百元币折叠得方方正正地弓着。看到这样的包装,爷爷终于把手伸进裤兜,裤兜中的钱确实不见了。于是,爷爷非常高兴地将他的钱拿回来。
直到今天,在这个端午节前,许多次,爷爷提起这一件事,他若有感慨地说,这样好的人不多的,捡到了钱并把钱还给人家这样的人很少的。很多人看到别人丢掉的钱,往自己的腰包里揣还惟恐来不及。那个女人的良心这么好,我应该拿点东西去酬谢她……哎,我这一生从来没吃过别人的苦水,从来不占别人的便宜,只有别人占我的便宜,让人一点,也是积德呀。我已经积下了不少的功德,我一定会很平安的,老了的时候一定不会拖累后辈的。我积下的功德,也会让你们后辈一生平安的!忽然又是一个端午节来临!爷爷从小店里买了一包糖。
爷爷站在那一根电线杆边,若有感慨般地对着耀井路。先年的繁华景象忽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的仅只是一片破破烂烂的废墟,原本鳞次栉比的小屋如今已经只剩下断壁残垣。爷爷轻轻地说,多么可惜呀,那些整日可以赚到很多钱的人,现在他们到哪里去找那容易赚钱的地方呢,好好的一条街道,就这样消失了。
爷爷发现,在废墟的两边,先年不会出现的一些房子,忽然出现在这一片废墟的两侧,那些房子也与原来排列在耀井路两侧的那些屋子一个模样,也是那么低矮,那么黑乎乎地排列着,那些屋檐下仿佛有人群攒动的模样。而那根电线杆依然那么坚强地挺立在废墟中,很有点鹤立鸡群的味道。
爷爷瞥了一眼那根电线杆,又看了一眼那位对他拾金不昧的女人曾经住过的那一块地盘。忽然,爷爷发现:地上躺着几张百元的大钞,也是用那种无色透明的塑料纸包着的,与爷爷去年丢在那儿的钱包装一模一样。
爷爷俯下身子,伸手小心翼翼地将这一包钱拿了起来,他的右手伸进自己的裤兜中,发现自己的裤兜中的钱还安稳地呆着。爷爷将钱高高地举起,大声地喊,谁丢了钱,谁钱丢了?
转眼间,一个多小时已经过去,夕阳已经开始西下。阳光正在渐渐地黯淡,太阳的脸蛋红红地挂在西边的天空中,也染红了爷爷的饱经沧桑的老脸。夕阳装饰在云海,那种远方的鲜红色,在爷爷前的废墟上烙下了火一样的颜色,隐隐约约地照出废墟上的一点光明,是紫色的。
终于爷爷见到有人向他中来,那个人似乎低着头焦急地寻打着什么东西似的。爷爷关切地部,后生儿,你丢了钱,是吗?那是一面色黝黑的男青年,只有十八九岁的样子。他跑得那么匆忙,当爷爷冷不丁地那样问他的时候,他先是一愣,似乎并不知道爷爷在问他什么。当他一眼看到爷爷手中的钱时,连忙换成一幅高兴的神色,说,阿公,我中午在这一段路上丢了钱,现在正在寻找着呢。您已经捡到了?谢谢你。爷爷说,这钱大概是你的了,拿回去吧,注意放得好一点,钱难赚啊。
这个小伙子一把抓过爷爷手中的钱,依然快速地跑着,倏忽便消失在废墟上,仿佛已经在地平线上沉没了,一个黑影渐渐消失在夜幕降临的时候。
望着那个小伙子远去的背影,爷爷欣慰地说,我又积了一回德了!
回家之后,爷爷如往常一样要数一下他口袋的钱。可是,当他将手伸进右侧的裤兜时,却发现裤兜已经空了,什么也没有。
这三百元钱哪里去了呢,一定是让那个娃娃骗走了。爷爷略带忧伤地说,看来,我的这些钱是注定要丢的。破财消灾,破财消灾,爷爷淡淡地说,今年我们会更平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