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 内容出处: | 《丹丘之旅:蒲华与晚清台州士林》 图书 |
| 唯一号: | 110820020210004363 |
| 颗粒名称: | 序 |
| 页数: | 4 |
| 页码: | 1-4 |
内容
言此刻,我的眼前,又出现了他的形象:一袭长衫,略带皱褶,隐隐也沾着些许征尘,似乎还浸渍着酒痕;长长的脸颊,略显清瘦,鼻梁高挺着,一双眼睛侧视人寰,炯炯有神,透出坚定和傲然;他儒雅而率真,豪宕而桀骜。这是蒲华的艺术形象。三十多年了,这个形象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那时,确切地说,应该是一九八四年秋天,青涩的我正在浙东名山巾子山上读师范。几乎每天晚上的夜自习后,我都跑到业师蒋文韵先生的书斋“小固山馆”里,听他谈艺说文。某个晚上,我发现他的洁白的墙壁上新挂上了一幅油画,经先生说明,我才知道,方方的镜框内站立着的,就是海上画派四杰。其中四杰之一蒲华的名字,我较为熟悉(因为先生经常向我提起),他的清雅而兀傲的形象,更是一下子就吸引了我。那时,先生家中经常挂着蒲华的墨竹画,一年更换几次,他也经常向我讲起蒲华的种种轶事。后来,蒲华留在台州的重要文化史迹“花山题壁”在温岭重新发现了,先生惊喜异常,他赋诗撰文,而稿子往往长久地修改着,蒙先生信任,誊抄的工作,就多半由我担任。因此,我对蒲华的生平事迹(包括寓居台州的史实)、艺术成就逐渐有所了解,也渐渐对他增加了几分景仰之心。
蒲华(1832—1911),字作英,号胥山野史。原名成,初字竹云、卓英、竹英。
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晚清杰出的书画家,近代中国海上画派的代表性画家, 与任颐、吴昌硕、虚谷同为海上画派先驱。善画竹,工画山水花卉,花卉在青藤、白阳间。精草书,笔意奔放,时罕其匹。也能诗,诗风清丽豪逸。他壮岁即橐笔出游。清同治三年(1864)夏间,初客明州(今宁波),随后到台州。寓居台州三十年,中间也往来于宁波、上海、杭州、嘉兴及温州一带。晚岁寓沪。蒲华的书画反映了突破传统的时代精神,富有创新精神,堪称一代艺术巨擘。
在毕业后离开巾子山的三十多年里,我与挚爱蒲华的业师经常保持着联 系,或书信往还,或山馆相见,同时我还关注着他发表在书刊上的文章,因此, “蒲华”二字不时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或在耳畔响起。我深切地了解到,业师的生命中早早地融入了蒲华的一切。青年时代,他生活俭朴,节衣缩食,省下的钱,往往用来购买蒲华的书画。中年时期,他曾在临海东大街旧书店看到一幅蒲华作于临海文士马葵臣家的书作,因“索价过当,囊羞无奈”,只得“抄件而归”,其怅然久之的情状可以想见。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业师政治问题的解决和工作、生活的逐渐安定,他积极参与蒲华书画的展览,不辞辛劳受邀编纂蒲华的书画集,也拔冗奔走在嘉兴、台州各地,寻访蒲华的遗墨史迹。这之中,我猜想,他为系统深入研究蒲华做着准备。
前年,业师来函,让我闲中到他位于临海东湖之畔的家中一趟,我如约而至,见到九十五岁高龄的先生身体朗健,思维清晰,十分欣慰。临别,先生将两大盒装的古籍及资料郑重地赠交到我手中,说是于我或许有用。我握别先生, 心中感激不已。回到家中,我急切地打开其中的一个纸盒,跃入眼帘的是我非常熟悉的先生的手迹,两本线装的笔记本封面上赫然写着“追踪随录”、“蒲华年表”等字。这两本资料,完成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是先生一生考察、研究蒲华的心血结晶。尤其是《追踪随录》,是先生几十年考察寻访蒲华一生踪迹(尤其是在台踪迹)的札记,许多资料至今为世所未见,十分珍贵!先生将这两大本资料赐赠于我,可能是他感到自己毕竟已年高,精力不济,难以完成蒲华研究的夙愿,又知我爱好地方文史,交给我是比较好的选择。
《追踪随录》札记手稿在手后,我经常翻阅,尤其是看到蒲华在台州的行迹多有新颖鲜活的史料,我不禁欢喜雀跃。他与晚清台州的诸多士人交往的情景,仿佛从先生遒劲灵动的笔迹中再现,同时许多问题也不时地萦绕心头,如: 蒲华寓居台州长达三十年,虽中间离开过,却不时地回来,这是一种怎样的因缘呢?他在台州,与士人交游如此广泛,留下许多诗歌书画,台州的广大士子也乐于与他交往,诗酒酬唱,书画雅集,此中反映了他们怎样的一种精神风貌? 于是,我渐渐产生了系统研究蒲华与晚清台州士人世界的想法。业师知道后, 非常高兴,勉励有加。于是,我就不胜冒昧地开笔了。经过两个寒暑的辛勤笔耕,书稿《丹丘之旅———蒲华与晚清台州士林》终于完成。两年里,我梳理业师的《蒲华年表》《追踪随录》,也细读台州文博界前辈王及先生陆续赠我的《蒲华研究》《蒲华年谱长编》《蒲华诗文集》等著作,十分感念前辈们筚路蓝缕的开拓 之功,也体悟到了蒲华在台三十年的心路历程以及他和士子们风雅飞扬的精神世界。
学术著作的撰写,当然要严谨求实,但随着新史学观念的不断推广,许多历史研究著作的触觉视野、布局结构、叙述方式都呈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气象和面貌。笔者在写作本书时,也在写作手法和史料的运用上,作了一些新的尝试,如口述史料的运用,在我过去的学术著作中是不曾有过的。又如,以想象激活史料的手法,在近年出版的一些学术著作中,也屡见不鲜,本书也斗胆使用,并初尝甜头。这里不妨举个例子。我们知道,蒲华晚清时期寓居台州期间,由于生活所迫和性情使然,也喜与方外人士交往,或居于道观佛寺。我想象,台州当时的一些道观佛寺里,是留有蒲华的印迹的。当然,学术研究,不能仅止于此,只靠猜想性论述,还须史料的佐证,于是我细心检阅晚清至民国时留下的地方文献,特别是蒲华曾长时寓居、逗留地域的方志,果不其然,我在项士元先生所纂的《巾子山志》上,真的发现了一条虽不起眼,但却十分有用的史料,当年巾子山的一些佛寺确实存留下蒲华的书画行迹。又如,蒲华与他的画竹的老师临海傅濂有没有正面交集?这要考证傅濂生活于临海的年代与蒲华在台州活动的时间有没有交集。笔者细加爬梳,也发现了有价值的史料,那就是现藏于临海博物馆的编号为1761的《山水图轴》,有题识曰:“时在丁卯新秋月,西湖残客濂拙笔。”题识中的“丁卯”当是同治六年,当时蒲华也已到了台州。由此可见,他们相见于临海,是不无可能的。
当然,这种探索性的手法,是否稳妥可靠,是否能入大方之家的法眼,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和论证,也期待学界通人的不吝指教。
关于本书的题目正题“丹丘之旅”,有必要略加阐释。蒲华长时寓居台州的史实,实际上也有他的挚友临海士子马葵臣的诗歌《怀蒲作英(戊辰)》一诗可为佐证,其诗曰:“行踪倏忽又经年,月下樽前忆谪仙。秀水钟灵涛万丈,台山游历路三千。无拘竟似鸥同癖,有兴能随鹤共翩。日日披图聊慰念,何如携手艳阳天。”诗中的“台山游历路三千”,就非常形象地描述了蒲华长时游历台州的情景。可以说,蒲华的人生道路、艺术之旅的最壮实的年岁是在台州度过的。台州,又别称为“丹丘”,这是历代方志旧集里昭然可考的①。因此,笔者以为,用“丹丘之旅”作为题目正题是较为妥当的。
本书的重点不在撰述蒲华留在台州的诗歌书画艺术,因为这方面已经有不少前辈作了有价值的探索,而是着眼于蒲华寓居台州三十年的活动轨迹、交游情况,特别是蒲华艺术成长中的台州元素以及他与晚清台州士子的高度契合的精神世界,由此折射出晚清台州士林的总体风貌,侧面体现出当时台州的风雅之盛。读者读后当能谅察之。当然具体效果如何,深待方家批评指正!
蒲华(1832—1911),字作英,号胥山野史。原名成,初字竹云、卓英、竹英。
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晚清杰出的书画家,近代中国海上画派的代表性画家, 与任颐、吴昌硕、虚谷同为海上画派先驱。善画竹,工画山水花卉,花卉在青藤、白阳间。精草书,笔意奔放,时罕其匹。也能诗,诗风清丽豪逸。他壮岁即橐笔出游。清同治三年(1864)夏间,初客明州(今宁波),随后到台州。寓居台州三十年,中间也往来于宁波、上海、杭州、嘉兴及温州一带。晚岁寓沪。蒲华的书画反映了突破传统的时代精神,富有创新精神,堪称一代艺术巨擘。
在毕业后离开巾子山的三十多年里,我与挚爱蒲华的业师经常保持着联 系,或书信往还,或山馆相见,同时我还关注着他发表在书刊上的文章,因此, “蒲华”二字不时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或在耳畔响起。我深切地了解到,业师的生命中早早地融入了蒲华的一切。青年时代,他生活俭朴,节衣缩食,省下的钱,往往用来购买蒲华的书画。中年时期,他曾在临海东大街旧书店看到一幅蒲华作于临海文士马葵臣家的书作,因“索价过当,囊羞无奈”,只得“抄件而归”,其怅然久之的情状可以想见。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业师政治问题的解决和工作、生活的逐渐安定,他积极参与蒲华书画的展览,不辞辛劳受邀编纂蒲华的书画集,也拔冗奔走在嘉兴、台州各地,寻访蒲华的遗墨史迹。这之中,我猜想,他为系统深入研究蒲华做着准备。
前年,业师来函,让我闲中到他位于临海东湖之畔的家中一趟,我如约而至,见到九十五岁高龄的先生身体朗健,思维清晰,十分欣慰。临别,先生将两大盒装的古籍及资料郑重地赠交到我手中,说是于我或许有用。我握别先生, 心中感激不已。回到家中,我急切地打开其中的一个纸盒,跃入眼帘的是我非常熟悉的先生的手迹,两本线装的笔记本封面上赫然写着“追踪随录”、“蒲华年表”等字。这两本资料,完成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是先生一生考察、研究蒲华的心血结晶。尤其是《追踪随录》,是先生几十年考察寻访蒲华一生踪迹(尤其是在台踪迹)的札记,许多资料至今为世所未见,十分珍贵!先生将这两大本资料赐赠于我,可能是他感到自己毕竟已年高,精力不济,难以完成蒲华研究的夙愿,又知我爱好地方文史,交给我是比较好的选择。
《追踪随录》札记手稿在手后,我经常翻阅,尤其是看到蒲华在台州的行迹多有新颖鲜活的史料,我不禁欢喜雀跃。他与晚清台州的诸多士人交往的情景,仿佛从先生遒劲灵动的笔迹中再现,同时许多问题也不时地萦绕心头,如: 蒲华寓居台州长达三十年,虽中间离开过,却不时地回来,这是一种怎样的因缘呢?他在台州,与士人交游如此广泛,留下许多诗歌书画,台州的广大士子也乐于与他交往,诗酒酬唱,书画雅集,此中反映了他们怎样的一种精神风貌? 于是,我渐渐产生了系统研究蒲华与晚清台州士人世界的想法。业师知道后, 非常高兴,勉励有加。于是,我就不胜冒昧地开笔了。经过两个寒暑的辛勤笔耕,书稿《丹丘之旅———蒲华与晚清台州士林》终于完成。两年里,我梳理业师的《蒲华年表》《追踪随录》,也细读台州文博界前辈王及先生陆续赠我的《蒲华研究》《蒲华年谱长编》《蒲华诗文集》等著作,十分感念前辈们筚路蓝缕的开拓 之功,也体悟到了蒲华在台三十年的心路历程以及他和士子们风雅飞扬的精神世界。
学术著作的撰写,当然要严谨求实,但随着新史学观念的不断推广,许多历史研究著作的触觉视野、布局结构、叙述方式都呈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气象和面貌。笔者在写作本书时,也在写作手法和史料的运用上,作了一些新的尝试,如口述史料的运用,在我过去的学术著作中是不曾有过的。又如,以想象激活史料的手法,在近年出版的一些学术著作中,也屡见不鲜,本书也斗胆使用,并初尝甜头。这里不妨举个例子。我们知道,蒲华晚清时期寓居台州期间,由于生活所迫和性情使然,也喜与方外人士交往,或居于道观佛寺。我想象,台州当时的一些道观佛寺里,是留有蒲华的印迹的。当然,学术研究,不能仅止于此,只靠猜想性论述,还须史料的佐证,于是我细心检阅晚清至民国时留下的地方文献,特别是蒲华曾长时寓居、逗留地域的方志,果不其然,我在项士元先生所纂的《巾子山志》上,真的发现了一条虽不起眼,但却十分有用的史料,当年巾子山的一些佛寺确实存留下蒲华的书画行迹。又如,蒲华与他的画竹的老师临海傅濂有没有正面交集?这要考证傅濂生活于临海的年代与蒲华在台州活动的时间有没有交集。笔者细加爬梳,也发现了有价值的史料,那就是现藏于临海博物馆的编号为1761的《山水图轴》,有题识曰:“时在丁卯新秋月,西湖残客濂拙笔。”题识中的“丁卯”当是同治六年,当时蒲华也已到了台州。由此可见,他们相见于临海,是不无可能的。
当然,这种探索性的手法,是否稳妥可靠,是否能入大方之家的法眼,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和论证,也期待学界通人的不吝指教。
关于本书的题目正题“丹丘之旅”,有必要略加阐释。蒲华长时寓居台州的史实,实际上也有他的挚友临海士子马葵臣的诗歌《怀蒲作英(戊辰)》一诗可为佐证,其诗曰:“行踪倏忽又经年,月下樽前忆谪仙。秀水钟灵涛万丈,台山游历路三千。无拘竟似鸥同癖,有兴能随鹤共翩。日日披图聊慰念,何如携手艳阳天。”诗中的“台山游历路三千”,就非常形象地描述了蒲华长时游历台州的情景。可以说,蒲华的人生道路、艺术之旅的最壮实的年岁是在台州度过的。台州,又别称为“丹丘”,这是历代方志旧集里昭然可考的①。因此,笔者以为,用“丹丘之旅”作为题目正题是较为妥当的。
本书的重点不在撰述蒲华留在台州的诗歌书画艺术,因为这方面已经有不少前辈作了有价值的探索,而是着眼于蒲华寓居台州三十年的活动轨迹、交游情况,特别是蒲华艺术成长中的台州元素以及他与晚清台州士子的高度契合的精神世界,由此折射出晚清台州士林的总体风貌,侧面体现出当时台州的风雅之盛。读者读后当能谅察之。当然具体效果如何,深待方家批评指正!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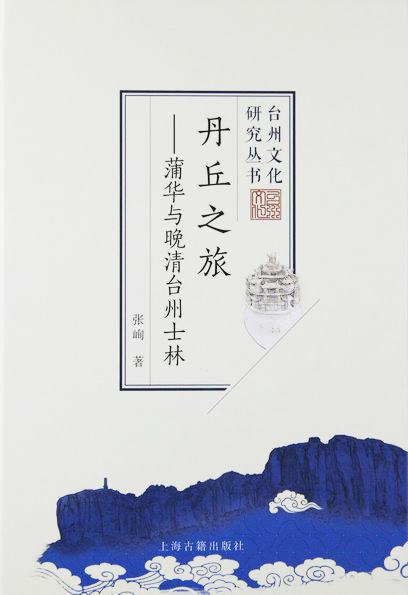
《丹丘之旅:蒲华与晚清台州士林》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书分为五章,主要内容包括:游幕缘由、游幕之初:花前共举觞、长期寓居:台山游历路三千、蒲华艺术成长中的台州元素、风雅之盛:蒲华与晚清台州士林的精神世界。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