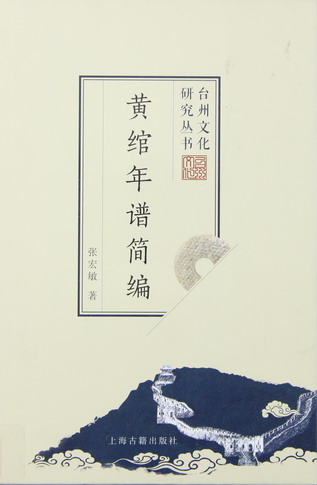内容
家训小引道七府君久庵公所著《家训》,虽日用诰诫,莫不表里于经,驰骤于史,谆谆数千万言,实足为天下明训,岂徒为子孙虑深远?迨传至不肖,而仅留其半,遍访老成,家余无存者,不胜痛恨太息,于职守者每致咎焉。因谨书所见十二条于《谱》,吾族子孙,尚其无忘先训。
端本一,吾家祖先教子孙营生之道。男子读书之外,以耕种为业,各务本等生理,不许渔贾远海、经营末利;或至借放银谷,不许过取利息、勾留票券、故延岁月、重沓复算。女子中馈、织纴以外,以孳养鸡豚鹅鸭为务,不许干预门外之事,及妒忌多言、玩亵戏笑,以致丧败廉耻。累世祖母暨先母鲍太夫人,皆以顺德配助而无愧也。
一,人家以道德为本而不在势利。父子至性在道德,夫妇至恩在道德,兄弟至亲在道德,长幼至爱在道德,婢仆至恭在道德,亲友至情在道德,以至读书为仕只在道德,而不在富贵。故可仕、可止、可久、可速,各随其宜,庶几不为市井庸俗鄙夫。思于此立志,是为正本。其本既正,万事无失,方能兴育贤才,保家永世。所谓道者,顺其当然之理;所谓德者,得其忠恕之德。
一,吾欲尔子孙皆读书,非欲尔皆仕,但愿读书知义礼,知为人之方,以成其身而已。其仕与否,皆随其才质,以听命与数而不可强,强则不惟无成而反误其平生,以致落魄浪荡。近日,乡里游民之多争竞、妒忌之甚,皆由于此,实不可不知,所深戒也。
一,吾家世读书业儒为事,虽不立道学门户,然所以相传饬身教家、处官处世,皆合圣贤执中之道,并无为人矜炫之事。
一,黄鲁直云:“四民皆当世业,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 然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有才气者出,便当名世矣。”此言虽若寻常,亦为士大夫家所当知也。
一,一家之事定于一人,犹一国之事定于一君。所谓一人者,家之主也。
家主之志不定,一家之事皆不定;家主之志定,一家之事皆定。家主志于尚德则一家皆尚德,家主志于道义则一家皆道义,家主志于敛约则一家皆敛约,家主志于勤俭则一家皆勤俭,家主志于势利则一家皆势利,家主志于淫佚则一家皆淫佚,家主志于欺诳则一家皆欺诳,家主志于争胜则一家皆争胜,家主志于浮薄则一家皆浮薄,家主志于夸大则一家皆夸大。盖有不言而喻、不约而同、不令而行者,诚可畏也。凡为家主者,可不慎哉,可不敬哉! 志学一,古人云:“学莫先立志。”故古人之学,志于仁、志于道、志于德而已。孔门之言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世儒之言曰:“志于道德者则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则富贵不足以累其心。”知志于仁而无恶,则知不志于仁必不免于恶矣;知志道德不可累于功名,况可累以富贵乎?知仁之必当志、知道德之必当志,则知所立志矣。
一,夫仁,犹木之有根;道,犹行之有路;德,犹居之有宅。木而无根,可乎? 行而无路,可乎?居而无宅,可乎?知斯三者决不可无,则知所立志矣。濂溪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亦不失其令名。” 所谓“志伊尹之志”、“学颜子之学”,亦在于仁、于道、于德而已。若舍仁、舍道、舍德,别无可以为志、为学矣。
一,夫学当以仁、以道、以德为志,然生于其时则有时王之制。故孔子之为学,虽祖述乎尧舜而必宪章乎文武,盖以时制不可不遵也。今时之制,以科第取士,以举业为学,士生今世,欲学必由举业,欲仕必由科第,此所不能逃者。
要知举业之初,以明经为本,原不外乎圣学;则知科第取士之本,原不外乎仁与道、德。皆由世人急于名利,逐其末而忘其本,乃自异于圣而自绝于仁与道、德也,岂国家制度固如此哉!吾家自曾祖、先祖、先君以来,皆由科第而仕,皆自秀才为举业时,即知所立志,皆知切己体认,求有得于身心,故发于举业皆与众人不同,故居官处家亦与众人不同。吾少承荫叙,后闻横渠“荫袭”之说,遂谢应举,然于举业未尝不究心。但所以究心,视今日众人所学有不同耳。宋儒有云:“凡学之道,必须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经》、《语》、《孟》中。我所未能者,当勉而行之。或我所行,未合于《六经》、《语》、《孟》者,便思改之,先务躬行,非徒诵书作文而已。”又云:“凡读书如《论语》,将诸弟子问处便作己问,将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耳。”张子韶又云:“如看唐朝事,则若身预其中,人主性情如何?时在朝士大夫,孰为君子,孰为小人?其处事,孰为当,孰为否?皆令胸次晓然,可以口讲指画,则机会圆熟,他日临事必过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当蓄之于心,以此发之笔下, 则文章不为空言矣。” 一,凡教子弟,不可先令作文字,只教熟读经书及子、史、古文、程文之类; 讲解俱明,使之有本,然后教作文字,庶使专心诵读,不敢玩物、蹉跎岁月。皆教子弟之要也,为父师者不可不知也。
一,圣人之学,艮止以存其心,执中以尽其道,云“人心”、“道心”以辩其体, 云“危”、“微”以明其体之所以辨,云“精”、“一”以致其工之所以用,此乃圣学之要也。自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及颜、曾、思、孟没而圣学无传, 至东汉摩腾、竺法兰以其经入中国而其说闻于中国,至南北朝达摩入中国[而] 其法行于中国,历唐迄宋而盛,故当时士大夫无不事禅学者。虽圣学之兴,亦自禅学而来,以至于今。凡圣学皆以虚无为本,而失圣人“艮止”、“执中”之旨。
吾幸得之遗经而验之于身心,涉历星霜,每尝笔之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易》、《诗》、《书》诸经,谓之“原古”。又尝笔之于《日录》及诸门人所记,人谓之《明道编》,颇明千古圣学之要。今时制虽主朱注,吾子孙欲学圣学而业举子者,能取而时玩之,不惟圣学于此有得,虽举业亦能明其纲领宗旨而得益,以为终身成立之本矣,庶不孤吾平生之苦心也。
一,凡子弟欲务学,切不可以室家之务扰其心,其或犯兹戒者,决无有成之理。昔胡安定与孙明复同读书泰山,得家问,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 不复展读,恐其乱志。可以为法。
一,昔人论作文之法,有曰:“地步高则局段高,见识高则意度高,气量高则骨格高,此培养其身心也。读书多则学力富,历世深则才力健,此培养其材识也。养元气以充其本,养题意以极其变,此培养其思虑也。乃至论其体格,则叙事之文贵简实、议论之文贵精到、辞令之文贵婉切、辞赋之文贵婉丽。论其体段,则历代有风气之殊,诸家有材气之别。”以上皆宜融会贯通,此入境之法也。识得培养、入境二法,方可言作文字,文可以易言哉! 一,松坞府君平生读书,手不释卷,晚好读《通鉴纲目》。日取一编,坐所谓松坞观焉,见忠臣孝子则喜见于色,见奸臣贼子[则]掩卷大骂。卒之前一日, 是书犹在手。
一,先祖文毅公少失怙恃,励志问学,即以古贤圣自期。虽至寒馁,不以为意。怠,则书姓名于掌,以木枋击之。又自呼其姓名曰:“汝父母俱亡,汝可不知自立而自怠乎?” 一,文毅公少年尝读书于洞黄集怡楼上,婶母以盂蜜盘糍来馈,食糍用蜜。
公方发愤,误认砚墨为蜜,食已,人见其唇墨,往视之,盂蜜如故,知发愤之深, 食不知其味也。
一,文毅公幼失怙恃,艰苦备尝,岁歉,食麰粥。先职方公老婢,北人,不习治麰,杂芒粃,不可入口。日盛一器,俟其凝,画为四块,读倦剔其芒而食,旦暮尽四块。弟妹幼弱不能食,以麰易米食之而自麰,笃于友爱如此。
一,文毅公虽居官,(尝)[常]读书。为文选郎中,稍暇即手不释卷。及为南京工部侍郎,犹夜读。或问曰:“尚欲科举乎?”曰:“不然,圣贤行己治人之方悉在于是,读书则使心有归宿,不致外驰。” 一,昔胡澹庵见杨龟山,[龟]山举两肘示之曰:“吾此肘不离案三十年,然后于道有进。”张无垢谪横浦,寓城西宝界寺,寝室有矩窗,每日昧爽,辄抱书立窗下,就明而读,如是者十四年。洎北归,窗下双跬之迹隐然,至今犹存。前辈为学,勤苦如此。然龟山盖少年事;无垢乃晚年,犹难也。此皆为学所当知也。
一,赵东山曰:“袁公伯长尝问于虞公伯生,曰:‘为文当何如?’虞公曰:‘子浙人也,子欲为文,当问诸浙中庖者。予川人也,何足以知之?’袁公曰:‘庖者何以知文乎?’虞公曰:‘川人之为庖也,粗块而大脔,浓酰而厚医,非不果然属餍也,而饮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则不然,凡水陆之产皆择取柔甘、调其湆齐,澄之有方而洁之不已,视之冷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鳞介之珍不易故性。故余谓文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袁公矍然,称之曰:‘善。’”夫作文之法在多读书,多读古书明其理,则用句用字皆练且有根据、有典则,不空疏。又当如水中着盐,使饮水者知其味,此浙庖之谓也。若用之卼臲有迹,则又蜀庖之不若,不但粗块大脔、浓酰厚医而已也。
教养一,先君与先叔侹为稚子,日收谷簸不实,俗谓之淘有。谷中有遗粒,先君与先叔复簸之,得谷数升,藏之。一日,取谷至东浦舟中买梨枣食,曰:“此我自己谷也。”祖母蔡夫人闻之,曰:“父母在,子妇无私货。汝等为稚子,有自己谷也?”辄语先文毅公,皆痛责。先君悔悟终身。绾为童子时,尝闻先君语。
一,先母之教子孙,不以华衣美食,一言之妄、一行之差,必不轻贷。平居必以古人德行、节义、阴功贻后,足为持身治家之法者,谆谆语之不倦。岁时必集诸妇、诸孙妇、孙女为燕会,亦谆谆语之不倦。绾童子时,文毅公及先君皆在仕途,尝谆切寄书训教:“毋学市井子弟,见人面敬背侮,与人语面是背非,流为轻薄,终不可反。”若此之训甚多,先母皆揭于所坐壁上。绾兄弟少有过差,必令跪壁下,语之曰:“尔祖、尔父之所以惓惓教尔者何如?尔可不遵耶?”甚至痛棰之乃已。
一,先母鲍太淑夫人常语绾兄弟曰:“汝今成人,毋谓自能,忽我教训。我自孕汝等,即居静寝,毫发罔念不敢萌于心,非理之色不敢接于目,非理之声不敢入于耳,饮食之味常淡泊而邪味浓厚无所嗜,非理不正之语无所言,寝处起居皆有常,喜怒笑必有则。至生汝等,自怀抱至今,疾痛疴痒、贤愚寿夭,顷刻不敢忘于心,亦未尝不念汝家祖父欲教汝、爱汝辈之心而有忽。汝可不知、不常常思念而忽我之教、之爱耶?” 一,凡子孙少年教养之方,不可示以有余,使其骄满,不可与之金帛,恣其费用,衣服不可与之华靡,饮食不可与之甘美。吾先母教养吾兄弟五人,自少不以华衣,不以美食。衣必兄弟相传,虽至敝犹补缀以衣之;食有鱼肉,必各分一小楪,使之有节,虽蔬菜亦不使之纵。一言之妄、一行之差,必不轻贷。平居必以古人德行、阴功贻后。足为持身治家之法者,谆谆语之不倦。
一,吾乡人子孙多令为吏,年来益甚,虽故家旧族亦然。殊不知一至公门为吏,便坏本心,遂学奸猾、说谎之习,敢为欺公、玩法之为,卒之丧门灭类、破家荡产。吾家之子孙,切宜知戒。
一,“酒”、“色”、“财”、“气”四字皆能致疾、犯刑、坏名、灾己、丧身、亡家,惟“色”一字为尤酷。子弟自十一、二、三、四岁,天癸未通,习俗诱化,又被一种淫佚儇薄之徒故意哄嫐,早开情窦,丧其天元真气,夭寿绝嗣,浪败身家。及至十六、七、八、九岁,血气未定,惟色是耽,不惟自速死亡,幸而不死则终身病疾羸痿,百事皆做不成。纵生子孙,非凶折则必愚昧浮薄,且习与性成,以至丧失行止,坏家法、乱风俗,皆由于此。为父母者,实当以此提撕,不可忽也。
一,吾家先世家庭之教,最严而有礼。凡子姓,每日晨见必揖,至暮见必揖而退。凡常侍寝庭及候宾客,虽冠,皆侍立终日不许坐。凡设几席,列肴馔,斟酒捧蔬,虽一切劳役,皆子弟躬为之,不许辄退避。吾兄弟昔侍先君、先妣,日皆如此供役。
一,横渠先生曰:“勿谓小儿无记性,所历事皆能不忘。故善养子者,当其婴孩,鞠之使得所养,令其和气。及长而性美,示以好恶有常。至如养犬者不欲其升堂,则待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复食之于堂,则使孰从?虽日挞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养异类且尔,况人乎?故养正者,圣功也。”此横渠先生教养小儿之训,故详述以为尔辈鞠养子孙之所当知。
一,家养正《语录》云:“人家子弟惟可使觌德,不可使觌利。”此言最切要, 子孙当刻骨知之。
一,又云:“养子弟如养芝兰,既积学以培植之,又积善以滋润之,父子之间不可溺于小慈。自少律之以严,绳之以礼,则长无不肖之悔。”噫,欲为子孙虑者尽之矣! 励志一,凡有富必有贫,有贵必有贱,此理势然也。世皆以为富者子孙必不可使贫,贵者子孙必不可使贱,殊不知富贵、贫贱有命,岂能久富无贫、久贵无贱者哉?为子孙勿以祖父富贵必欲富贵,惟贵修德以承之耳。虽果富贵而不修德,则富贵何益?果贫贱而能修德,则贫贱何损?如国初吾乡郭饶阳先生,不过一知县耳;杜清献公后人号梅屋、曰清贫者,不过一布衣耳,至今人皆景仰。
陕西李某官止同知,竟为关中先达。如宋之史浩、贾涉辈,身为大官,其后子孙嵩之、弥远、似道,虽为宰相封王,乃贻千古吐骂,二氏家声反为之坠。由此观之,官岂在大?吾子孙能有如郭、杜、李者,吾愿足矣。徒富贵如嵩之、似道辈, 岂吾愿哉?吾或死,亦不瞑目于地下矣。
一,汉疏广曰:“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富者,众之怨也,吾既无以教子孙,不欲益其过。”信乎!少闻外祖颍州公云:“温州府有李同知者,是北方人,自书对联于门曰:‘子孙贤似我,要钱做恁么;子孙不如我,要钱做恁么。’”其言甚可味也。后见王祭酒虎谷云:“陕西近来士林之有材之人皆由李同知,其人清俭笃实,教人有方,乃关中前辈。”恐温州之李同知,即此人也。
一,罗大经曰:“东山先生杨伯子尝为余言:‘某昔为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官,尝至某位中,见案上有近时人诗文一编,西山一见,掷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问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笔头虽写得数句,所谓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读之将恐染神乱志,非徒无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谢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晋公、王岐公、吕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辈,亦非无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东山乃诚斋万里之子,父子皆以清操重于世,不但文章而已,此言实后生业文艺者所当知也。
一,方蛟峰八字格言:“富莫大于蓄道德,贵莫大于为圣贤,贫莫大于不闻道,贱莫大于不知耻。仕能行道之谓达,贫不安分之谓穷,流芳百世之谓寿,得志一时之谓夭。” 师友一,吾家先世,家学相承,以至于今,实非一日。七世叔祖柏四谏议府君恪, 与柏十九洗马府君仍,与吾八世祖桂二处士和,同游叶水心先生之门,得《易》学之传。谏议府君与泉溪潘评事禋为友,评事卒,府君尝赋诗挽之,曰“水心心上《易》,同悟到玄真”之句。洗马府君与泉溪潘秘教起余为友,秘教卒,亦有诗挽之,曰“云路迟吾到,恩波及子多”之句。吾世祖慎,又创读书堂,专以读书教子弟为事。叶水心先生尝题诗于上。传承三世,其堂毁于火,吾十世祖轲又复建之。
一,吾大闾十二族祖七六府君、邕州教授清湘先生讳石,实与考亭门人、同族黄勉斋幹、孙竹湖应时为友,相与淬励,以究朱学。家居创楼,藏书数千卷以事检阅,孙竹湖为之题匾,曰“步云楼”。友人林晓庵昉为之记。
一,兵部府君与兄桃溪府君少从叶拙讷先生士冕、程成趣先生完游,二先生之学皆原于贞成郭先生。贞成之言曰:“敬者,天命之所流行,衽席之上, 一有不敬则天命于兹息矣。”故二先生之学皆以诚敬为本,而拙讷先生尤为端确。府君兄弟喜得依归,朝夕相与淬励,勤苦学问,一言一行皆以二先生为法, 凡闻见有疑必穷,探得其要领而后止,故二府君德器大成,超然远诣。兵部府君成进士,为天下名士;桃溪府君亦不失为一乡名师。
一,曾祖为职方主事,徽州歙县侍郎吴公宁时为郎中,与曾祖契谊笃厚。卒之日,先祖年十三,奔曾祖母丧归,不在侧,吴公为敛。先祖既仕,厚视吴公之家, 及先君,至今子孙数世犹为通家,亲爱不绝,可见前辈僚友交情非今日之可及。
一,文毅公应荐举,退归,未入学。谢文肃公初为秀才,未冠,一日趋金浦云先生馆,请问可交之友。浦云默然不答,思之良久,曰:“在今学校中,择可交之友甚难。其人有黄某者,吾家之甥也,此人乃可交之友,不惟今日交之,可以终身。”方语未毕,文毅公适至,文肃公问:“为何人?”浦云曰:“此所言吾甥也。” 文肃公甚喜,同坐。茶罢,文毅公出,从而至江边旧居,遂拜文毅公而定交,果至终身,以至子孙而交谊不废。二公皆为我朝名臣,则文肃公之问交,浦云之为择交,皆可为世法矣。
一,文毅公自秀才即以圣贤自待,超然思远于俗。与文肃公为友,同居庠序,因贫窭流辈诸生皆务夸扬,惟二公退然自修。或见凌侮,皆不为意。出入起处,必与文肃俱:或寓旅舍,或憩息道傍,或共炊爨,或共锄圃而讲习不废; 或制一衣,二公共为之,圆领不能裁,以茶钟规圆而自缝之。其清苦刻励如此。
一,谢文肃公曰:“须友以成,宁可少哉!余托交定轩公,天假之缘,一语而合,遂至忘年,切磋磨砺,终始无间。既成进士而出,天下名士不为不多,而平生知己惟西涯、东山二公;回视吾乡,则惟定轩公一人而已。定轩尝谓余曰: ‘姻连骨肉,人皆有之;朋友之交,至或旷世,不一二人焉。’涉历之久,余始信其言之不诬也。余无似,有愧于公多矣。噫,须友以成,信哉!” 一,郑少谷善夫,字继之,闽人也。予为后军,告病归。过浒墅,始会继之。
继之时为户部主事,督税浒墅,至舟中一拜,遂定交,期访余山中。别几十年, 果至山中,不失前约。及凡期约,皆一一不失,可谓有范氏之风。今日朋友益见少也。继之初学,刻意诗文,蹈清高而已,无志于道。及闻予言,遂有志求道,又欲邀其友孙太初、高宗吕、傅木虚与予游而共学。故太初弃方外而有室家,又以《竹林精舍诗》寄予以定交。高宗吕亦尝访予山中。及继之,皆惜不寿,余每思继之志远意真,使天假之年,其进可量哉!余因念生平海内朋友,如湛甘泉若水、王阳明守仁、朱白浦节、徐横山爱、席元山书、胡静庵世宁、邵端峰锐、吕泾野柟、应石门典、罗东川侨、何柏斋瑭、钟筠溪芳、王顺涯道、梁默庵谷, 及安庆何唐、竹溪周清、天台布衣王西轩宗元,虽形迹亲疏、丽泽滋益有不同, 而其心庶几始终之义。
一,阳明往年因徐曰仁卒,有书与吾,曰:“自宗贤归,日切山中之想。自曰仁卒,无复入世之心。”其当时交友笃厚之情如此,今不可见矣。
技艺一,吾少年日尝学书、学画,因欲学问,恐其妨功,故皆弃之。晚年因不试居闲,偶因相知谈书画,忽复挥毫,漫成幅素,诸子见而习之,皆精笔意。
一,《颜氏家训》曰:“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惟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萧子云每叹曰:‘吾著《齐书》,勒成一典,文章宏义,自谓可观,唯以笔迹得名,亦异事也。’王褒,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犹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曰:‘假使吾不知书,吾不至今日邪!’以此观之,慎勿以书自命。虽然,厮猥之人,以能书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也。” 一,《颜氏家训》曰:“画绘之工,亦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常有梁元帝手画蝉雀白扇及马图,亦难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写真,坐上宾客,随宜点染, 即成数人,以问童孺,皆知姓名矣。萧贲、刘孝先、刘灵,并文学已外,复佳此法。
玩阅古今,特可宝爱。若官未通显,每被公私使令,亦为猥役。吴郡顾士端出身湘东国侍郎,后为镇南府刑狱参军,有子曰庭西,朝中书舍人,父子并有琴书之艺,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怀羞恨。彭城刘岳,槖之子也,仕为骠骑府管记、平氏县令,才学快士,而画绝伦,后随武陵王入蜀,下牢之败,遂为陆护军画支江寺壁,与诸工巧杂处。向使三贤都不晓画,直运素业,岂见耻乎?” 婚姻一,汉匡衡曰:“配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夫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自上世以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
一,配匹为生民之始,故古之婚姻必择有德。然闺门之德不可外见,必视其世族,观其祖考,察其家风,参以庶事,而可知也。上至帝王婚姻,必大国诸侯、先圣王之后、勋贤之裔,否则甥舅之国,不以微贱上敌至尊,故其福祚盛大, 子孙蕃昌。自黄帝以至三代,下及汉唐宋,其兴皆始于婚姻之得人,其衰皆由于配匹之非人。故婚姻之际,可不慎哉! 一,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乱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恶疾不取,丧父长子不取。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有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凡此,圣人所以顺男女之际,重婚姻之始也。
一,文中子曰:“古者男女之族,各择德焉,不以财为礼。” 一,文中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无数,教人以乱。且贵贱有等, 一夫一妇,庶人之职也。” 一,司马温公曰:“凡议婚姻,当先察其壻与妇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贵。壻苟贤矣,今虽贫贱,安知异时不富贵乎?苟为不肖,今虽富贵,安知异时不贫贱乎?妇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时之富贵而娶之,彼挟其富贵, 鲜有不轻其夫而傲其舅姑,养成骄妒之性,异日为患,庸有极乎?借使因妇财以致富,依妇势以取贵,苟有丈夫之志气者,能无愧乎?” 治家一,先母欲创造室庐,则预于二十余年,积聚山木,无一不备。文毅公殁于官,舆柩归,襄事毕,先母乃白先君:“诸子皆将有家矣,无室以居之,奈何?”先君检遗箧,仅存俸金数百两,余则一无所有,先君颇难之。先母曰:“吾久备之矣。”乃尽以所有告先君,先君乃喜,始获有居宇之庇。
一,吾家自曾祖至吾,历世素无厚积,赖承先业及母氏鲍太夫人勤俭积累之遗,有此田亩。每岁除纳粮及公私费用外,所余不多。又赖积庆为朝官,幸一切杂泛差役,及一切劝借营办之类,皆获优免,尚可支持。尔等子孙,只宜常以清苦勤俭自励,若一日骄奢怠惰则恐不继。
一,民生衣食,以农为本;农事之忧,水旱为急;水旱之来,凶歉不免,故水旱之于衣食,不可不备。故范蠡之师计然,计然之策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行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范蠡用之,以兴货殖,卒强越以复吴仇,此虽非君子之所尚,然十二年水旱之相半,而水旱之来,凶歉当预备,又岂不为民生衣食先务之当知哉! 一,先君在外之日,先母极严内外之防。其门之扃,系之以绳,穴壁引绳, 入室启门,消息皆在室中。室前之窗,垂之以帘,帘之四围,各以片竹钉之,使不可卷;以纸糊帘之下半,使无所窥。未晨则促侍婢起炊爨,既具则盛以盂,置于门内庋板上,立室中,呼诸仆至窗前付属之,乃令开门,使人携去。食讫,以器置门外庋板上,喝云收家伙,然后令侍婢往携入。他若治家之常、饔飱之候、集事之节,无一不可为法。
一,人家内外之当谨,此古今治家之至要。每见人家凡有淫乱之事,必至衰败。人心荡肆,贤才不兴,纵有聪明子孙,亦皆夭折无成,必出鬼祟,百怪俱兴。吾见亦不罕矣,痛宜谨之。
一,《内则》曰:“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男子入内,不啸不指,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一,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馌之敬,相待如宾。与之归,言诸文公曰: “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臣闻‘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文公以为下军大夫。
一,罗大经曰:“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为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奸富也,而务本之农皆为仆妾于奸富之家矣。噫!” 勤俭一,曾祖为职方主事,日出入无马,乘驴,跟随只一皁一童。一日,童以驴私雇与人,不知为盗驴者所诳,骑入杀驴,市而烹之。所服圆领乃双线粗布,而绣荷鹭为补。今人家口袋隶卒粗衣犹不肯用,其清素如此。
一,人家生财,岂有他道?只循“勤俭”二字而已。今人惟务竞利而好奢侈,不知《大学》“生众食寡,为疾用舒”之道,所以每致丧败。为吾子孙者切当以竞利为戒,只循《大学》生财之勤俭有常,当用则用,不可悭吝,当节则节,不可奢侈,则财恒足矣。
一,先母性甘淡薄,日食惟淡饭、蔬菜,饮以热水。非有宾客来,未尝自买一肉、宰一鸡。至于祀先,则极其诚敬丰腆,具物无俭。嫁时妆衣,服之终身, 虽极敝坏,重复补缀,犹洁净而无垢,属纩之日始脱而尚存,将宝藏之,所以示我子孙亲戚及子妇辈。有馈必收蓄,以待宾客之用。子孙侍侧,常有赐馔。亲旧来谒,无间疏贫,必留款酒食。未尝多市而常见有余。
一,人家田产、金帛之类实不宜多,但能勤俭,稍得自给,为庶足以存其心, 为士足以养廉节,多则必为身家之累、子孙之害。凡骄奢淫逸、傲惰放肆、丧败覆亡,皆由于此。
一,人家不论贫富大小,凡金帛菽粟之类,常宜度量节约,常留有余,以待公私缓急之需。虽至乏亦宜忍省,不宜殉物纵欲,不量事力,嬴缩过用,竭费以致不给,借贷于人,以速丧败。
一,人家时节饮食及宴宾之礼,皆当有节,不可奢侈。若不有节,必不可继日,后必致废家荡产,流离乞丐,及为盗贼,皆由此始,吾见甚多。凡人家之败, 皆由饮食、衣服奢侈所致。如吾邑年来城市乡村、大家小户皆败,实有四端,此亦一端也。司马温公之言,实为可训,吾故识之于后。
一,司马温公曰:“先公为郡牧判官,客至未尝不置酒,或行之三,或行之五,不过七行,酒沽于市,菓止梨枣栗柿,肴止脯醢菜羹,器用甆漆,当时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会数而礼勤,物薄而情厚。今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菓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常数日营聚,然后敢发书。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故不随俗奢靡者鲜矣。嗟乎,风俗颓敝如是,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 内德一,五世祖统五府君尽以居产美者让之群从,祖母金氏欣然乐承,略无疑沮。视今锄耨箕帚而有难色谇语,相去何如也? 一,继高祖母祝氏,高祖晚年婢,生第八子,高祖时在田舍,前七子皆成室家,产业分析已久。祖母呼诸子与妇,谓之曰:“尔翁生少子,不可不育。但翁年老,万一事有不讳,少子无依且无产以为生,奈何?”诸子妇欣然乐育,愿合所析产业重作八分均分。长子妇李氏躬为抱乳。比长,文毅公教之读书,始终扶植,后为延平司训。此家之将兴,祯祥所至,故有此事。家之将亡,则必起妒害残贼之意,岂有此哉! 一,曾祖母金太淑人少无父,事母至孝,遇疾病屡祈于天,愿以身代处。姊妹恩意笃甚,衣服奁妆每让美与姊妹,而自取其薄者。既归曾祖,恭俭淑慎,曾祖读书夜分,必躬织纴以待之。及曾祖为职方,犹服布素,食蔬食,淡然无所欲,每以“居官当清慎尽职”为劝勉。
一,婢妾之于有家,关系甚大,今人家皆不知此理而每忽之。其故始于为夫者不知寡欲正身,率之以道,为妻者但知争欲妒忌,抚之皆不以恩,甚者凌暴惨毒,无所不至,以至蓬首垢面,皲足龟毛,腹无常饱,身无完衣,丧其廉耻,又不规检,或至于奸,家法由此而坏。或至为盗,财货为之日空,且子孙昵近,诱引失义,为害有不可胜言者。知此,则为夫者必当先事寡欲、正身,以导其妻, 使为妻者知不以欲为重,念彼亦人子,以笃恩爱,然后教之以道义,则家法整而家道正矣。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至哉言乎! 一,先文毅公于南京侍郎(南京)①,务简蚤休,斋居必读书。虽燕居,亦左右置几,一公自居,一夫人居之,相敬如宾,阅书有关内德及家人之道,必详释近喻,以晓夫人。故夫人德器成就,端庄简重,性虽严整而心地平直忠厚,所以福遗子孙。
一,先母每日必昧旦而兴,夜必终二鼓乃寝,率以为常。平生寡疾,间有痁疟疾,虽寒热交攻,至不可堪,拥衾默坐一榻。子妇更以为劝,亦少偃即起。
一,绾家自始祖都监公以来,世居邑南海上万山中,曰“洞黄”。至文毅公为秀才,始迁邑中。先母既归先君,文毅公方为文选郎中,一室萧然,徒四壁立而已。先母因念绾家先祖累世为官,皆清白自守,而家贫如此,以家人不事生业故也,由是,遂矢志克家。虽先君仕宦终身,未尝从至官所。作家之始,悉以所有妆奁鬻之,得五十金,典田为亩五十,岁入可租百石。由此,益务勤俭,滋树蓄居,傍有园几二亩,百种具备,岁时宾祭及人事往来之需,皆取给于此。作二十余年,有田千余亩。文毅公久在宦途,始闻之,以他人诡籍,及问,方知其详,乃骇而难之。
一,吾家祖先教子孙治家之道,必严内外之辨。一切男子及仆从之类,成童以上,并不许擅入内门。女子及婢姊苍头之类,八岁以上,不许辄出外门,倘有不得已急事,必须伴而出。夜行必以烛,不许暗行。
一,吾家祖先以来,家法最严,嫌疑之别极慎。先妣鲍太淑人,内外之防尤谨。
一,先君早年读书山舍,既仕,则多离居、暂居。生吾兄弟五人。既生五弟,即居外寝。日间入内寝,先母见,必起立。寝中置一座,先君中坐,母傍坐而不敢并。惟岁时子孙罗拜,则暂并坐,退又复故处。先君契阔在外,略无离索之叹。虽为子者,终身未尝稍见有一动之狎、一言之戏,所谓“相敬如宾”。
情欲之感,无介乎仪容。
朔节一,古人教人,必严朔望之仪,必谨晨昏之令,此最为规矩。况人有家,生齿日繁,若无规矩则必心身日放,任纵自恣,无所拘束,则乱矣。
一,朔者一月之始,望者一月之中①,所以不可不严。晨者一日之始,昏者一日之终,所以不可不谨。节序自元旦至除日,凡九节,一岁之始之终,所以不可不重。重之者,使人知岁功代谢,光阴可惜,不可不及时警励也。但观《七月》与《蟋蟀》之诗,可见矣。及汉以来,又有大酺之令,亦因时行之,则余时皆当勤励也。必至节序,方许饮食,此亦古人张弛之义,然劝励之意亦在其中矣。
一,凡遇朔望日、昧爽直日,一人主击鼓,始击咸起,盥漱总栉。再击,皆着本人各等礼服至祠堂,及应谒各祠,家长帅子弟诣各神前,焚香燃灯,四拜讫退,揖尊长讫,诸子弟以次相揖。择子弟声音洪亮者,诵太祖皇帝木铎牌,曰: “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及画角三声,又言曰:“为君难,为臣难,难又难;创业难,守成难,难又难;启家难,保家难,难又难。”诵讫,总揖而退。
一,凡常日之晨、昧爽直日,一人击响板,内外闻声即起,子孙诣父母前作揖,讫后各执所事,如读书、治农圃、纺织之类,皆当勤谨。至夜,必继烛以勤其事,不可早睡,习为淫逸。
一,古人夙兴夜寐之节,皆观天地阴阳之理以顺万物之情。明而动,晦而休。其兴必以鸡鸣为候,故君子修身皆自昧旦丕显,不以有事而蚤,无事而宴。
其兴居皆顺阴阳之理以为常,故《内则》有曰“凡内外,鸡初鸣,咸盥漱,衣服,敛枕簟,洒扫室堂及庭,布席,各从其事”,此乃有家之常也。
端本一,吾家祖先教子孙营生之道。男子读书之外,以耕种为业,各务本等生理,不许渔贾远海、经营末利;或至借放银谷,不许过取利息、勾留票券、故延岁月、重沓复算。女子中馈、织纴以外,以孳养鸡豚鹅鸭为务,不许干预门外之事,及妒忌多言、玩亵戏笑,以致丧败廉耻。累世祖母暨先母鲍太夫人,皆以顺德配助而无愧也。
一,人家以道德为本而不在势利。父子至性在道德,夫妇至恩在道德,兄弟至亲在道德,长幼至爱在道德,婢仆至恭在道德,亲友至情在道德,以至读书为仕只在道德,而不在富贵。故可仕、可止、可久、可速,各随其宜,庶几不为市井庸俗鄙夫。思于此立志,是为正本。其本既正,万事无失,方能兴育贤才,保家永世。所谓道者,顺其当然之理;所谓德者,得其忠恕之德。
一,吾欲尔子孙皆读书,非欲尔皆仕,但愿读书知义礼,知为人之方,以成其身而已。其仕与否,皆随其才质,以听命与数而不可强,强则不惟无成而反误其平生,以致落魄浪荡。近日,乡里游民之多争竞、妒忌之甚,皆由于此,实不可不知,所深戒也。
一,吾家世读书业儒为事,虽不立道学门户,然所以相传饬身教家、处官处世,皆合圣贤执中之道,并无为人矜炫之事。
一,黄鲁直云:“四民皆当世业,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 然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有才气者出,便当名世矣。”此言虽若寻常,亦为士大夫家所当知也。
一,一家之事定于一人,犹一国之事定于一君。所谓一人者,家之主也。
家主之志不定,一家之事皆不定;家主之志定,一家之事皆定。家主志于尚德则一家皆尚德,家主志于道义则一家皆道义,家主志于敛约则一家皆敛约,家主志于勤俭则一家皆勤俭,家主志于势利则一家皆势利,家主志于淫佚则一家皆淫佚,家主志于欺诳则一家皆欺诳,家主志于争胜则一家皆争胜,家主志于浮薄则一家皆浮薄,家主志于夸大则一家皆夸大。盖有不言而喻、不约而同、不令而行者,诚可畏也。凡为家主者,可不慎哉,可不敬哉! 志学一,古人云:“学莫先立志。”故古人之学,志于仁、志于道、志于德而已。孔门之言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世儒之言曰:“志于道德者则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则富贵不足以累其心。”知志于仁而无恶,则知不志于仁必不免于恶矣;知志道德不可累于功名,况可累以富贵乎?知仁之必当志、知道德之必当志,则知所立志矣。
一,夫仁,犹木之有根;道,犹行之有路;德,犹居之有宅。木而无根,可乎? 行而无路,可乎?居而无宅,可乎?知斯三者决不可无,则知所立志矣。濂溪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亦不失其令名。” 所谓“志伊尹之志”、“学颜子之学”,亦在于仁、于道、于德而已。若舍仁、舍道、舍德,别无可以为志、为学矣。
一,夫学当以仁、以道、以德为志,然生于其时则有时王之制。故孔子之为学,虽祖述乎尧舜而必宪章乎文武,盖以时制不可不遵也。今时之制,以科第取士,以举业为学,士生今世,欲学必由举业,欲仕必由科第,此所不能逃者。
要知举业之初,以明经为本,原不外乎圣学;则知科第取士之本,原不外乎仁与道、德。皆由世人急于名利,逐其末而忘其本,乃自异于圣而自绝于仁与道、德也,岂国家制度固如此哉!吾家自曾祖、先祖、先君以来,皆由科第而仕,皆自秀才为举业时,即知所立志,皆知切己体认,求有得于身心,故发于举业皆与众人不同,故居官处家亦与众人不同。吾少承荫叙,后闻横渠“荫袭”之说,遂谢应举,然于举业未尝不究心。但所以究心,视今日众人所学有不同耳。宋儒有云:“凡学之道,必须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经》、《语》、《孟》中。我所未能者,当勉而行之。或我所行,未合于《六经》、《语》、《孟》者,便思改之,先务躬行,非徒诵书作文而已。”又云:“凡读书如《论语》,将诸弟子问处便作己问,将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耳。”张子韶又云:“如看唐朝事,则若身预其中,人主性情如何?时在朝士大夫,孰为君子,孰为小人?其处事,孰为当,孰为否?皆令胸次晓然,可以口讲指画,则机会圆熟,他日临事必过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当蓄之于心,以此发之笔下, 则文章不为空言矣。” 一,凡教子弟,不可先令作文字,只教熟读经书及子、史、古文、程文之类; 讲解俱明,使之有本,然后教作文字,庶使专心诵读,不敢玩物、蹉跎岁月。皆教子弟之要也,为父师者不可不知也。
一,圣人之学,艮止以存其心,执中以尽其道,云“人心”、“道心”以辩其体, 云“危”、“微”以明其体之所以辨,云“精”、“一”以致其工之所以用,此乃圣学之要也。自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及颜、曾、思、孟没而圣学无传, 至东汉摩腾、竺法兰以其经入中国而其说闻于中国,至南北朝达摩入中国[而] 其法行于中国,历唐迄宋而盛,故当时士大夫无不事禅学者。虽圣学之兴,亦自禅学而来,以至于今。凡圣学皆以虚无为本,而失圣人“艮止”、“执中”之旨。
吾幸得之遗经而验之于身心,涉历星霜,每尝笔之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易》、《诗》、《书》诸经,谓之“原古”。又尝笔之于《日录》及诸门人所记,人谓之《明道编》,颇明千古圣学之要。今时制虽主朱注,吾子孙欲学圣学而业举子者,能取而时玩之,不惟圣学于此有得,虽举业亦能明其纲领宗旨而得益,以为终身成立之本矣,庶不孤吾平生之苦心也。
一,凡子弟欲务学,切不可以室家之务扰其心,其或犯兹戒者,决无有成之理。昔胡安定与孙明复同读书泰山,得家问,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 不复展读,恐其乱志。可以为法。
一,昔人论作文之法,有曰:“地步高则局段高,见识高则意度高,气量高则骨格高,此培养其身心也。读书多则学力富,历世深则才力健,此培养其材识也。养元气以充其本,养题意以极其变,此培养其思虑也。乃至论其体格,则叙事之文贵简实、议论之文贵精到、辞令之文贵婉切、辞赋之文贵婉丽。论其体段,则历代有风气之殊,诸家有材气之别。”以上皆宜融会贯通,此入境之法也。识得培养、入境二法,方可言作文字,文可以易言哉! 一,松坞府君平生读书,手不释卷,晚好读《通鉴纲目》。日取一编,坐所谓松坞观焉,见忠臣孝子则喜见于色,见奸臣贼子[则]掩卷大骂。卒之前一日, 是书犹在手。
一,先祖文毅公少失怙恃,励志问学,即以古贤圣自期。虽至寒馁,不以为意。怠,则书姓名于掌,以木枋击之。又自呼其姓名曰:“汝父母俱亡,汝可不知自立而自怠乎?” 一,文毅公少年尝读书于洞黄集怡楼上,婶母以盂蜜盘糍来馈,食糍用蜜。
公方发愤,误认砚墨为蜜,食已,人见其唇墨,往视之,盂蜜如故,知发愤之深, 食不知其味也。
一,文毅公幼失怙恃,艰苦备尝,岁歉,食麰粥。先职方公老婢,北人,不习治麰,杂芒粃,不可入口。日盛一器,俟其凝,画为四块,读倦剔其芒而食,旦暮尽四块。弟妹幼弱不能食,以麰易米食之而自麰,笃于友爱如此。
一,文毅公虽居官,(尝)[常]读书。为文选郎中,稍暇即手不释卷。及为南京工部侍郎,犹夜读。或问曰:“尚欲科举乎?”曰:“不然,圣贤行己治人之方悉在于是,读书则使心有归宿,不致外驰。” 一,昔胡澹庵见杨龟山,[龟]山举两肘示之曰:“吾此肘不离案三十年,然后于道有进。”张无垢谪横浦,寓城西宝界寺,寝室有矩窗,每日昧爽,辄抱书立窗下,就明而读,如是者十四年。洎北归,窗下双跬之迹隐然,至今犹存。前辈为学,勤苦如此。然龟山盖少年事;无垢乃晚年,犹难也。此皆为学所当知也。
一,赵东山曰:“袁公伯长尝问于虞公伯生,曰:‘为文当何如?’虞公曰:‘子浙人也,子欲为文,当问诸浙中庖者。予川人也,何足以知之?’袁公曰:‘庖者何以知文乎?’虞公曰:‘川人之为庖也,粗块而大脔,浓酰而厚医,非不果然属餍也,而饮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则不然,凡水陆之产皆择取柔甘、调其湆齐,澄之有方而洁之不已,视之冷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鳞介之珍不易故性。故余谓文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袁公矍然,称之曰:‘善。’”夫作文之法在多读书,多读古书明其理,则用句用字皆练且有根据、有典则,不空疏。又当如水中着盐,使饮水者知其味,此浙庖之谓也。若用之卼臲有迹,则又蜀庖之不若,不但粗块大脔、浓酰厚医而已也。
教养一,先君与先叔侹为稚子,日收谷簸不实,俗谓之淘有。谷中有遗粒,先君与先叔复簸之,得谷数升,藏之。一日,取谷至东浦舟中买梨枣食,曰:“此我自己谷也。”祖母蔡夫人闻之,曰:“父母在,子妇无私货。汝等为稚子,有自己谷也?”辄语先文毅公,皆痛责。先君悔悟终身。绾为童子时,尝闻先君语。
一,先母之教子孙,不以华衣美食,一言之妄、一行之差,必不轻贷。平居必以古人德行、节义、阴功贻后,足为持身治家之法者,谆谆语之不倦。岁时必集诸妇、诸孙妇、孙女为燕会,亦谆谆语之不倦。绾童子时,文毅公及先君皆在仕途,尝谆切寄书训教:“毋学市井子弟,见人面敬背侮,与人语面是背非,流为轻薄,终不可反。”若此之训甚多,先母皆揭于所坐壁上。绾兄弟少有过差,必令跪壁下,语之曰:“尔祖、尔父之所以惓惓教尔者何如?尔可不遵耶?”甚至痛棰之乃已。
一,先母鲍太淑夫人常语绾兄弟曰:“汝今成人,毋谓自能,忽我教训。我自孕汝等,即居静寝,毫发罔念不敢萌于心,非理之色不敢接于目,非理之声不敢入于耳,饮食之味常淡泊而邪味浓厚无所嗜,非理不正之语无所言,寝处起居皆有常,喜怒笑必有则。至生汝等,自怀抱至今,疾痛疴痒、贤愚寿夭,顷刻不敢忘于心,亦未尝不念汝家祖父欲教汝、爱汝辈之心而有忽。汝可不知、不常常思念而忽我之教、之爱耶?” 一,凡子孙少年教养之方,不可示以有余,使其骄满,不可与之金帛,恣其费用,衣服不可与之华靡,饮食不可与之甘美。吾先母教养吾兄弟五人,自少不以华衣,不以美食。衣必兄弟相传,虽至敝犹补缀以衣之;食有鱼肉,必各分一小楪,使之有节,虽蔬菜亦不使之纵。一言之妄、一行之差,必不轻贷。平居必以古人德行、阴功贻后。足为持身治家之法者,谆谆语之不倦。
一,吾乡人子孙多令为吏,年来益甚,虽故家旧族亦然。殊不知一至公门为吏,便坏本心,遂学奸猾、说谎之习,敢为欺公、玩法之为,卒之丧门灭类、破家荡产。吾家之子孙,切宜知戒。
一,“酒”、“色”、“财”、“气”四字皆能致疾、犯刑、坏名、灾己、丧身、亡家,惟“色”一字为尤酷。子弟自十一、二、三、四岁,天癸未通,习俗诱化,又被一种淫佚儇薄之徒故意哄嫐,早开情窦,丧其天元真气,夭寿绝嗣,浪败身家。及至十六、七、八、九岁,血气未定,惟色是耽,不惟自速死亡,幸而不死则终身病疾羸痿,百事皆做不成。纵生子孙,非凶折则必愚昧浮薄,且习与性成,以至丧失行止,坏家法、乱风俗,皆由于此。为父母者,实当以此提撕,不可忽也。
一,吾家先世家庭之教,最严而有礼。凡子姓,每日晨见必揖,至暮见必揖而退。凡常侍寝庭及候宾客,虽冠,皆侍立终日不许坐。凡设几席,列肴馔,斟酒捧蔬,虽一切劳役,皆子弟躬为之,不许辄退避。吾兄弟昔侍先君、先妣,日皆如此供役。
一,横渠先生曰:“勿谓小儿无记性,所历事皆能不忘。故善养子者,当其婴孩,鞠之使得所养,令其和气。及长而性美,示以好恶有常。至如养犬者不欲其升堂,则待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复食之于堂,则使孰从?虽日挞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养异类且尔,况人乎?故养正者,圣功也。”此横渠先生教养小儿之训,故详述以为尔辈鞠养子孙之所当知。
一,家养正《语录》云:“人家子弟惟可使觌德,不可使觌利。”此言最切要, 子孙当刻骨知之。
一,又云:“养子弟如养芝兰,既积学以培植之,又积善以滋润之,父子之间不可溺于小慈。自少律之以严,绳之以礼,则长无不肖之悔。”噫,欲为子孙虑者尽之矣! 励志一,凡有富必有贫,有贵必有贱,此理势然也。世皆以为富者子孙必不可使贫,贵者子孙必不可使贱,殊不知富贵、贫贱有命,岂能久富无贫、久贵无贱者哉?为子孙勿以祖父富贵必欲富贵,惟贵修德以承之耳。虽果富贵而不修德,则富贵何益?果贫贱而能修德,则贫贱何损?如国初吾乡郭饶阳先生,不过一知县耳;杜清献公后人号梅屋、曰清贫者,不过一布衣耳,至今人皆景仰。
陕西李某官止同知,竟为关中先达。如宋之史浩、贾涉辈,身为大官,其后子孙嵩之、弥远、似道,虽为宰相封王,乃贻千古吐骂,二氏家声反为之坠。由此观之,官岂在大?吾子孙能有如郭、杜、李者,吾愿足矣。徒富贵如嵩之、似道辈, 岂吾愿哉?吾或死,亦不瞑目于地下矣。
一,汉疏广曰:“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富者,众之怨也,吾既无以教子孙,不欲益其过。”信乎!少闻外祖颍州公云:“温州府有李同知者,是北方人,自书对联于门曰:‘子孙贤似我,要钱做恁么;子孙不如我,要钱做恁么。’”其言甚可味也。后见王祭酒虎谷云:“陕西近来士林之有材之人皆由李同知,其人清俭笃实,教人有方,乃关中前辈。”恐温州之李同知,即此人也。
一,罗大经曰:“东山先生杨伯子尝为余言:‘某昔为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官,尝至某位中,见案上有近时人诗文一编,西山一见,掷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问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笔头虽写得数句,所谓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读之将恐染神乱志,非徒无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谢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晋公、王岐公、吕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辈,亦非无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东山乃诚斋万里之子,父子皆以清操重于世,不但文章而已,此言实后生业文艺者所当知也。
一,方蛟峰八字格言:“富莫大于蓄道德,贵莫大于为圣贤,贫莫大于不闻道,贱莫大于不知耻。仕能行道之谓达,贫不安分之谓穷,流芳百世之谓寿,得志一时之谓夭。” 师友一,吾家先世,家学相承,以至于今,实非一日。七世叔祖柏四谏议府君恪, 与柏十九洗马府君仍,与吾八世祖桂二处士和,同游叶水心先生之门,得《易》学之传。谏议府君与泉溪潘评事禋为友,评事卒,府君尝赋诗挽之,曰“水心心上《易》,同悟到玄真”之句。洗马府君与泉溪潘秘教起余为友,秘教卒,亦有诗挽之,曰“云路迟吾到,恩波及子多”之句。吾世祖慎,又创读书堂,专以读书教子弟为事。叶水心先生尝题诗于上。传承三世,其堂毁于火,吾十世祖轲又复建之。
一,吾大闾十二族祖七六府君、邕州教授清湘先生讳石,实与考亭门人、同族黄勉斋幹、孙竹湖应时为友,相与淬励,以究朱学。家居创楼,藏书数千卷以事检阅,孙竹湖为之题匾,曰“步云楼”。友人林晓庵昉为之记。
一,兵部府君与兄桃溪府君少从叶拙讷先生士冕、程成趣先生完游,二先生之学皆原于贞成郭先生。贞成之言曰:“敬者,天命之所流行,衽席之上, 一有不敬则天命于兹息矣。”故二先生之学皆以诚敬为本,而拙讷先生尤为端确。府君兄弟喜得依归,朝夕相与淬励,勤苦学问,一言一行皆以二先生为法, 凡闻见有疑必穷,探得其要领而后止,故二府君德器大成,超然远诣。兵部府君成进士,为天下名士;桃溪府君亦不失为一乡名师。
一,曾祖为职方主事,徽州歙县侍郎吴公宁时为郎中,与曾祖契谊笃厚。卒之日,先祖年十三,奔曾祖母丧归,不在侧,吴公为敛。先祖既仕,厚视吴公之家, 及先君,至今子孙数世犹为通家,亲爱不绝,可见前辈僚友交情非今日之可及。
一,文毅公应荐举,退归,未入学。谢文肃公初为秀才,未冠,一日趋金浦云先生馆,请问可交之友。浦云默然不答,思之良久,曰:“在今学校中,择可交之友甚难。其人有黄某者,吾家之甥也,此人乃可交之友,不惟今日交之,可以终身。”方语未毕,文毅公适至,文肃公问:“为何人?”浦云曰:“此所言吾甥也。” 文肃公甚喜,同坐。茶罢,文毅公出,从而至江边旧居,遂拜文毅公而定交,果至终身,以至子孙而交谊不废。二公皆为我朝名臣,则文肃公之问交,浦云之为择交,皆可为世法矣。
一,文毅公自秀才即以圣贤自待,超然思远于俗。与文肃公为友,同居庠序,因贫窭流辈诸生皆务夸扬,惟二公退然自修。或见凌侮,皆不为意。出入起处,必与文肃俱:或寓旅舍,或憩息道傍,或共炊爨,或共锄圃而讲习不废; 或制一衣,二公共为之,圆领不能裁,以茶钟规圆而自缝之。其清苦刻励如此。
一,谢文肃公曰:“须友以成,宁可少哉!余托交定轩公,天假之缘,一语而合,遂至忘年,切磋磨砺,终始无间。既成进士而出,天下名士不为不多,而平生知己惟西涯、东山二公;回视吾乡,则惟定轩公一人而已。定轩尝谓余曰: ‘姻连骨肉,人皆有之;朋友之交,至或旷世,不一二人焉。’涉历之久,余始信其言之不诬也。余无似,有愧于公多矣。噫,须友以成,信哉!” 一,郑少谷善夫,字继之,闽人也。予为后军,告病归。过浒墅,始会继之。
继之时为户部主事,督税浒墅,至舟中一拜,遂定交,期访余山中。别几十年, 果至山中,不失前约。及凡期约,皆一一不失,可谓有范氏之风。今日朋友益见少也。继之初学,刻意诗文,蹈清高而已,无志于道。及闻予言,遂有志求道,又欲邀其友孙太初、高宗吕、傅木虚与予游而共学。故太初弃方外而有室家,又以《竹林精舍诗》寄予以定交。高宗吕亦尝访予山中。及继之,皆惜不寿,余每思继之志远意真,使天假之年,其进可量哉!余因念生平海内朋友,如湛甘泉若水、王阳明守仁、朱白浦节、徐横山爱、席元山书、胡静庵世宁、邵端峰锐、吕泾野柟、应石门典、罗东川侨、何柏斋瑭、钟筠溪芳、王顺涯道、梁默庵谷, 及安庆何唐、竹溪周清、天台布衣王西轩宗元,虽形迹亲疏、丽泽滋益有不同, 而其心庶几始终之义。
一,阳明往年因徐曰仁卒,有书与吾,曰:“自宗贤归,日切山中之想。自曰仁卒,无复入世之心。”其当时交友笃厚之情如此,今不可见矣。
技艺一,吾少年日尝学书、学画,因欲学问,恐其妨功,故皆弃之。晚年因不试居闲,偶因相知谈书画,忽复挥毫,漫成幅素,诸子见而习之,皆精笔意。
一,《颜氏家训》曰:“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惟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萧子云每叹曰:‘吾著《齐书》,勒成一典,文章宏义,自谓可观,唯以笔迹得名,亦异事也。’王褒,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犹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曰:‘假使吾不知书,吾不至今日邪!’以此观之,慎勿以书自命。虽然,厮猥之人,以能书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也。” 一,《颜氏家训》曰:“画绘之工,亦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常有梁元帝手画蝉雀白扇及马图,亦难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写真,坐上宾客,随宜点染, 即成数人,以问童孺,皆知姓名矣。萧贲、刘孝先、刘灵,并文学已外,复佳此法。
玩阅古今,特可宝爱。若官未通显,每被公私使令,亦为猥役。吴郡顾士端出身湘东国侍郎,后为镇南府刑狱参军,有子曰庭西,朝中书舍人,父子并有琴书之艺,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怀羞恨。彭城刘岳,槖之子也,仕为骠骑府管记、平氏县令,才学快士,而画绝伦,后随武陵王入蜀,下牢之败,遂为陆护军画支江寺壁,与诸工巧杂处。向使三贤都不晓画,直运素业,岂见耻乎?” 婚姻一,汉匡衡曰:“配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夫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自上世以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
一,配匹为生民之始,故古之婚姻必择有德。然闺门之德不可外见,必视其世族,观其祖考,察其家风,参以庶事,而可知也。上至帝王婚姻,必大国诸侯、先圣王之后、勋贤之裔,否则甥舅之国,不以微贱上敌至尊,故其福祚盛大, 子孙蕃昌。自黄帝以至三代,下及汉唐宋,其兴皆始于婚姻之得人,其衰皆由于配匹之非人。故婚姻之际,可不慎哉! 一,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乱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恶疾不取,丧父长子不取。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有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凡此,圣人所以顺男女之际,重婚姻之始也。
一,文中子曰:“古者男女之族,各择德焉,不以财为礼。” 一,文中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无数,教人以乱。且贵贱有等, 一夫一妇,庶人之职也。” 一,司马温公曰:“凡议婚姻,当先察其壻与妇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贵。壻苟贤矣,今虽贫贱,安知异时不富贵乎?苟为不肖,今虽富贵,安知异时不贫贱乎?妇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时之富贵而娶之,彼挟其富贵, 鲜有不轻其夫而傲其舅姑,养成骄妒之性,异日为患,庸有极乎?借使因妇财以致富,依妇势以取贵,苟有丈夫之志气者,能无愧乎?” 治家一,先母欲创造室庐,则预于二十余年,积聚山木,无一不备。文毅公殁于官,舆柩归,襄事毕,先母乃白先君:“诸子皆将有家矣,无室以居之,奈何?”先君检遗箧,仅存俸金数百两,余则一无所有,先君颇难之。先母曰:“吾久备之矣。”乃尽以所有告先君,先君乃喜,始获有居宇之庇。
一,吾家自曾祖至吾,历世素无厚积,赖承先业及母氏鲍太夫人勤俭积累之遗,有此田亩。每岁除纳粮及公私费用外,所余不多。又赖积庆为朝官,幸一切杂泛差役,及一切劝借营办之类,皆获优免,尚可支持。尔等子孙,只宜常以清苦勤俭自励,若一日骄奢怠惰则恐不继。
一,民生衣食,以农为本;农事之忧,水旱为急;水旱之来,凶歉不免,故水旱之于衣食,不可不备。故范蠡之师计然,计然之策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行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范蠡用之,以兴货殖,卒强越以复吴仇,此虽非君子之所尚,然十二年水旱之相半,而水旱之来,凶歉当预备,又岂不为民生衣食先务之当知哉! 一,先君在外之日,先母极严内外之防。其门之扃,系之以绳,穴壁引绳, 入室启门,消息皆在室中。室前之窗,垂之以帘,帘之四围,各以片竹钉之,使不可卷;以纸糊帘之下半,使无所窥。未晨则促侍婢起炊爨,既具则盛以盂,置于门内庋板上,立室中,呼诸仆至窗前付属之,乃令开门,使人携去。食讫,以器置门外庋板上,喝云收家伙,然后令侍婢往携入。他若治家之常、饔飱之候、集事之节,无一不可为法。
一,人家内外之当谨,此古今治家之至要。每见人家凡有淫乱之事,必至衰败。人心荡肆,贤才不兴,纵有聪明子孙,亦皆夭折无成,必出鬼祟,百怪俱兴。吾见亦不罕矣,痛宜谨之。
一,《内则》曰:“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男子入内,不啸不指,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一,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馌之敬,相待如宾。与之归,言诸文公曰: “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臣闻‘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文公以为下军大夫。
一,罗大经曰:“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为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奸富也,而务本之农皆为仆妾于奸富之家矣。噫!” 勤俭一,曾祖为职方主事,日出入无马,乘驴,跟随只一皁一童。一日,童以驴私雇与人,不知为盗驴者所诳,骑入杀驴,市而烹之。所服圆领乃双线粗布,而绣荷鹭为补。今人家口袋隶卒粗衣犹不肯用,其清素如此。
一,人家生财,岂有他道?只循“勤俭”二字而已。今人惟务竞利而好奢侈,不知《大学》“生众食寡,为疾用舒”之道,所以每致丧败。为吾子孙者切当以竞利为戒,只循《大学》生财之勤俭有常,当用则用,不可悭吝,当节则节,不可奢侈,则财恒足矣。
一,先母性甘淡薄,日食惟淡饭、蔬菜,饮以热水。非有宾客来,未尝自买一肉、宰一鸡。至于祀先,则极其诚敬丰腆,具物无俭。嫁时妆衣,服之终身, 虽极敝坏,重复补缀,犹洁净而无垢,属纩之日始脱而尚存,将宝藏之,所以示我子孙亲戚及子妇辈。有馈必收蓄,以待宾客之用。子孙侍侧,常有赐馔。亲旧来谒,无间疏贫,必留款酒食。未尝多市而常见有余。
一,人家田产、金帛之类实不宜多,但能勤俭,稍得自给,为庶足以存其心, 为士足以养廉节,多则必为身家之累、子孙之害。凡骄奢淫逸、傲惰放肆、丧败覆亡,皆由于此。
一,人家不论贫富大小,凡金帛菽粟之类,常宜度量节约,常留有余,以待公私缓急之需。虽至乏亦宜忍省,不宜殉物纵欲,不量事力,嬴缩过用,竭费以致不给,借贷于人,以速丧败。
一,人家时节饮食及宴宾之礼,皆当有节,不可奢侈。若不有节,必不可继日,后必致废家荡产,流离乞丐,及为盗贼,皆由此始,吾见甚多。凡人家之败, 皆由饮食、衣服奢侈所致。如吾邑年来城市乡村、大家小户皆败,实有四端,此亦一端也。司马温公之言,实为可训,吾故识之于后。
一,司马温公曰:“先公为郡牧判官,客至未尝不置酒,或行之三,或行之五,不过七行,酒沽于市,菓止梨枣栗柿,肴止脯醢菜羹,器用甆漆,当时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会数而礼勤,物薄而情厚。今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菓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常数日营聚,然后敢发书。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故不随俗奢靡者鲜矣。嗟乎,风俗颓敝如是,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 内德一,五世祖统五府君尽以居产美者让之群从,祖母金氏欣然乐承,略无疑沮。视今锄耨箕帚而有难色谇语,相去何如也? 一,继高祖母祝氏,高祖晚年婢,生第八子,高祖时在田舍,前七子皆成室家,产业分析已久。祖母呼诸子与妇,谓之曰:“尔翁生少子,不可不育。但翁年老,万一事有不讳,少子无依且无产以为生,奈何?”诸子妇欣然乐育,愿合所析产业重作八分均分。长子妇李氏躬为抱乳。比长,文毅公教之读书,始终扶植,后为延平司训。此家之将兴,祯祥所至,故有此事。家之将亡,则必起妒害残贼之意,岂有此哉! 一,曾祖母金太淑人少无父,事母至孝,遇疾病屡祈于天,愿以身代处。姊妹恩意笃甚,衣服奁妆每让美与姊妹,而自取其薄者。既归曾祖,恭俭淑慎,曾祖读书夜分,必躬织纴以待之。及曾祖为职方,犹服布素,食蔬食,淡然无所欲,每以“居官当清慎尽职”为劝勉。
一,婢妾之于有家,关系甚大,今人家皆不知此理而每忽之。其故始于为夫者不知寡欲正身,率之以道,为妻者但知争欲妒忌,抚之皆不以恩,甚者凌暴惨毒,无所不至,以至蓬首垢面,皲足龟毛,腹无常饱,身无完衣,丧其廉耻,又不规检,或至于奸,家法由此而坏。或至为盗,财货为之日空,且子孙昵近,诱引失义,为害有不可胜言者。知此,则为夫者必当先事寡欲、正身,以导其妻, 使为妻者知不以欲为重,念彼亦人子,以笃恩爱,然后教之以道义,则家法整而家道正矣。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至哉言乎! 一,先文毅公于南京侍郎(南京)①,务简蚤休,斋居必读书。虽燕居,亦左右置几,一公自居,一夫人居之,相敬如宾,阅书有关内德及家人之道,必详释近喻,以晓夫人。故夫人德器成就,端庄简重,性虽严整而心地平直忠厚,所以福遗子孙。
一,先母每日必昧旦而兴,夜必终二鼓乃寝,率以为常。平生寡疾,间有痁疟疾,虽寒热交攻,至不可堪,拥衾默坐一榻。子妇更以为劝,亦少偃即起。
一,绾家自始祖都监公以来,世居邑南海上万山中,曰“洞黄”。至文毅公为秀才,始迁邑中。先母既归先君,文毅公方为文选郎中,一室萧然,徒四壁立而已。先母因念绾家先祖累世为官,皆清白自守,而家贫如此,以家人不事生业故也,由是,遂矢志克家。虽先君仕宦终身,未尝从至官所。作家之始,悉以所有妆奁鬻之,得五十金,典田为亩五十,岁入可租百石。由此,益务勤俭,滋树蓄居,傍有园几二亩,百种具备,岁时宾祭及人事往来之需,皆取给于此。作二十余年,有田千余亩。文毅公久在宦途,始闻之,以他人诡籍,及问,方知其详,乃骇而难之。
一,吾家祖先教子孙治家之道,必严内外之辨。一切男子及仆从之类,成童以上,并不许擅入内门。女子及婢姊苍头之类,八岁以上,不许辄出外门,倘有不得已急事,必须伴而出。夜行必以烛,不许暗行。
一,吾家祖先以来,家法最严,嫌疑之别极慎。先妣鲍太淑人,内外之防尤谨。
一,先君早年读书山舍,既仕,则多离居、暂居。生吾兄弟五人。既生五弟,即居外寝。日间入内寝,先母见,必起立。寝中置一座,先君中坐,母傍坐而不敢并。惟岁时子孙罗拜,则暂并坐,退又复故处。先君契阔在外,略无离索之叹。虽为子者,终身未尝稍见有一动之狎、一言之戏,所谓“相敬如宾”。
情欲之感,无介乎仪容。
朔节一,古人教人,必严朔望之仪,必谨晨昏之令,此最为规矩。况人有家,生齿日繁,若无规矩则必心身日放,任纵自恣,无所拘束,则乱矣。
一,朔者一月之始,望者一月之中①,所以不可不严。晨者一日之始,昏者一日之终,所以不可不谨。节序自元旦至除日,凡九节,一岁之始之终,所以不可不重。重之者,使人知岁功代谢,光阴可惜,不可不及时警励也。但观《七月》与《蟋蟀》之诗,可见矣。及汉以来,又有大酺之令,亦因时行之,则余时皆当勤励也。必至节序,方许饮食,此亦古人张弛之义,然劝励之意亦在其中矣。
一,凡遇朔望日、昧爽直日,一人主击鼓,始击咸起,盥漱总栉。再击,皆着本人各等礼服至祠堂,及应谒各祠,家长帅子弟诣各神前,焚香燃灯,四拜讫退,揖尊长讫,诸子弟以次相揖。择子弟声音洪亮者,诵太祖皇帝木铎牌,曰: “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及画角三声,又言曰:“为君难,为臣难,难又难;创业难,守成难,难又难;启家难,保家难,难又难。”诵讫,总揖而退。
一,凡常日之晨、昧爽直日,一人击响板,内外闻声即起,子孙诣父母前作揖,讫后各执所事,如读书、治农圃、纺织之类,皆当勤谨。至夜,必继烛以勤其事,不可早睡,习为淫逸。
一,古人夙兴夜寐之节,皆观天地阴阳之理以顺万物之情。明而动,晦而休。其兴必以鸡鸣为候,故君子修身皆自昧旦丕显,不以有事而蚤,无事而宴。
其兴居皆顺阴阳之理以为常,故《内则》有曰“凡内外,鸡初鸣,咸盥漱,衣服,敛枕簟,洒扫室堂及庭,布席,各从其事”,此乃有家之常也。
附注
① 录自《洞黄黄氏宗谱》,1915年重修本。笔者按:《阳明后学文献丛书》本《黄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由于交稿日期较早,未能及时收录《家训》一卷。
① “南京”二字,系衍文。
① “中”,底本原作“终”,兹据文意改。
相关人物
黄绾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