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讀中庸叢說上
元許謙撰
序
中庸專言道故起首便言道學道統道學主于學兼
上下言之道統主于行獨以有位者言之至孔子
之生他無聖人在位則道統自在孔子凡言統者
學亦在其中學字固可包統字
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此是言
堯舜以前夫子翼易始於伏羲今之言聖人者必
自伏羲始然自開闢生物以來只有首出庶物之
聖人與天同道而立乎其位者但前聖所未道故
不知其名此但言上古聖神葢混言之又不知大
學章句序專以伏羲爲始否也
聖人大率有兩等有自然之聖生知安行所謂性者
也有學而成之聖積而至於大而化之所謂反之
者也此不言聖人而言聖神是指性之自然神明
不測之聖也此言上古創始有位道與天合之聖
人言動皆可爲天下法則者爲道統之始下此皆
是接傳其統者
繼立二字不要重看天道流行無物不在眾人所不
能知惟神聖自然與天合而言動皆可為萬世標
準非是有意繼續天道特爲人而立法也
論語堯曰諮爾舜至天祿永終王文憲以爲舜典脫
簡當在舜讓於德弗嗣之下此正傳心之要也
理與氣合而生人心爲一身之主宰又理氣之會而
能知覺者也人心於氣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
是也然此亦是人身之所必有但有發之正不正
爾非全不善故但雲危謂易流入於不善而沒其
善也道心於理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
也亦存乎氣之中爲人心之危者晦之故防而難
見心只是一於心上加人字道字看便見不同若
只順讀人心道心字卻似有二心矣謂之道則是
天理之公謂之人則是我身之私雖我身之私亦
非全是不善因身之所欲者而正即合乎道而
爲道心之用矣如鄉黨所言飲食衣服之類皆人
心之發在聖人則全是道心君子于毎事皆合乎
理義則亦無非道心也大抵人心可善可惡道心
全善而無惡
朱子書傳曰心者人所知覺主于中而應於外者也
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于義
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
心難明而易昧故防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
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之主
而人心聴命焉則危者安防者著動靜雲爲自無
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 大防皆同而傳
注與作文之體自不同故此語尤簡潔易看
人心是所欲爲之事道心是發應事之理人心聴命
於道心只是事皆順理耳危者既安則便是道
微只是隠防之意故難見今添妙字是貼襯防字
不必重看
精則察夫二者之間是察人心道心之間要察到疑
似纎毫之際此言心是指動處當時告大禹故言
如此若學者則用格物致知之功辨別眾理明至
善審然後可精其動處也
私字就形氣上來蓋既見此形氣而成人則此人爲
一人之私故必欲得於外以濟乎已所以易流於
欲下當與公字對卻用正字者謂性命之正則是
得之於天者固與天地人物同言正則公意自在
其中而正字於已切
繼徃聖開來學此學字應前道學字前道學是總包
上古以來相傳者此學字是夫子教後人者言繼
徃聖是明夫子教人亦是述上古聖聖相傳者耳
則子思所憂者豈專指夫子之教哉
更迭交互推演防繹
切言深要詳言周備憂深爲道之不明也故言之深
而要慮逺恐久而複失也故說之周而備
天命即道也能率性即道心也擇善者察之精也固
執者守之一也時中即中也惟君子爲能執之也
綱維言道體之大蘊奧言節目之詳及精密隱防之
理明言綱維盡言蘊奧
孟子推明此書謂見之行事及著七篇
上言異端下言老佛是異端至多楊朱墨翟許行之
徒以及諸子百家各立門戶議論不合聖道者皆
是
爲其彌近理所以大亂真葢其說宏逺幽防陳說道
德指明心性或有類乎吾道之言故爲所亂非如
百家之淺近易見也然而道德非聖賢所言之道
德心性非聖賢所指之心性固亦不難辨也倘無
中庸之書則吾道反晦而不明學者莫知所從又
焉得辨之乎
裳之要衣之領皆是總會處
章句輯畧或問三書既備然後中庸之書如支體之
分骨節之解而脈絡卻相貫穿通透中庸一書分
爲四大章如第一章十二章二十一章皆言其畧
而余章繼其後者皆詳言之三十三章又一章之
詳者詳畧謂此钜謂綱維細謂蘊奧諸說同異以
下專言或問
中庸
中庸大學二書與論孟二書不同論孟或聖賢自立
言教人或隨問而答或記聖賢出處動靜日用皆
是一條一件各見意趣學庸皆成片文字首尾備
具故讀者尤難然二書規模又有不同大學是言
學中庸是言道大學綱目相維經傳明整猶可尋
求中庸贊道之極有就天言者有就聖人言者有
就學者言者廣大精防開闔變化高下兼包钜細
畢舉故尤不易窮究
中庸德行之至極夫子嘗言之故子思取以名篇
解題
偏則不在中而在一邊倚則斜迤而不正過是越過
於中不及是未至於中不偏不倚是防說中字指
未發之體而言無過不及是橫說中字指已發之
用而言此皆是反說以四旁影出中字平如地之
平而無杌隉危處常者一定之理無詭異又常久
而不可變易惟其平正便可長久竒異險怪便不
可長久平橫說常防說此字正解庸字總而言之
惟中故可庸中而又須可庸乃中庸之道
程子謂不偏之謂中固兼舉動靜朱子不偏不倚則
專指未發者譬如置物不偏者在四方之正中不
略近東西南北之一邊不倚者非傾倚於一邊而
不正以心體而言不偏者渾然中正而無頗不倚
者不著於喜怒哀樂之一事雖皆指未發而言然
自有兩意不偏指其性之本然不倚指其用之未
發
常字該前後自前而言則常定而無異自後而言則
常久而不易
不偏不倚兩句是中庸之訓詁正道定理兩句是釋
中庸之義
始言一理者首章是也約而言之首三句是也又約
而言之天命之謂性一句是也末合爲一理末
章是也約而言之不顯惟德以下是也究其極言
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二語是也
首章
首三句言性道教之名義總人物言之而主於人率
性之謂道一句該上句而貫下句故篇中皆是說
道而性教在其中葢氣化流行不息者天之道也
是理也人得天道之流行者爲性當順此而行者
人之道也所謂率性也亦是理也然率性惟聖人
爲能之聖人之治己則盡己之性接人用物則盡
人物之性以眾人當率之而不能以失其生之本
故以己之安行者品節之以爲教使各知治己接
人用物之道處之既各得其宜則人與物莫不各
得遂其性矣則雖開說名義而未嘗不貫穿
爲一也自道也者至篇終皆是明人當行之道而
教其進之之方也
首三句是總說人物第三句修道固是人上意思多
然聖人修處亦和物都修了物雖不可教是教人
處物之道如春田不圍澤不殺胎不妖夭草木黃
落斧斤入山林魚不滿尺不粥之類皆是順物之
性而成就之不逆生意之意如馬絡頭牛穿鼻亦
是也妖於老反夭烏老反
性即理也在天地事物間爲理天賦於人物爲命人
物得之以生爲性只是一物所爲地頭不同故其
名不同
理存於心故不可須臾離不可者有贊其不能離之
之意有戒其勿離之之意
不睹不聞己之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不睹不聞也
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與莫見乎隱莫顯乎防
對說此言其定體如此戒慎恐懼與慎獨對說此
言修之之方前一節是操存即致中之事後一節
是省察即致和之事
戒懼不睹不聞謂但於不接物不當思慮時常敬以
存其心究其極則至於無所睹聞之際亦當戒懼
工夫至此而極密非謂至於不睹不聞時用工夫尋
常只恁悠悠過故章句謂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
不敢忽玩常字雖字亦字可見葢戒懼慎獨兩事
包括定心之動靜故凡非有所主之思慮及接物
時皆在戒懼界限裡如此看然後與不可須臾離
一句意脈相接續
經中於不睹上用戒慎字不聞上用恐懼字雖是分
說其實合說葢不睹不聞只是無聲色無可見聞
處非有兩端故章句總用敬畏字以敬字體戒慎
畏字體恐懼下又總言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只是
兼舉互見今且先當分戒懼與慎獨兩項界限葢
慎獨是就裡面說出戒懼是就外面說入但起念
頭處便是慎獨境界無所思而有所睹聞自外來
者皆屬戒懼境界獨是心欲應事見聞是事來動
心界限亦甚分曉不睹不聞是就極處說章句
常存字雖字亦字皆是補貼起此意葢心意不動
之時自有睹聞至於無所睹聞皆當敬畏然至於
不睹不聞之地則敬畏之工夫尤難但用意則屬
已發矣愚嘗妄爲之說曰當此之時此心當無物
而有主然又要看得真會得活若著個物字主字
而欲無之有之則又大不可矣以此體於心而實防
之久當自見言愈多則愈爲病矣
或問戒慎恐懼工夫如此與不思善惡及致虛靜篤
之說何以異曰氷炭不相入也彼學專務於靜吾
道動靜不違彼以靜定爲功惟恐物來動心故一
切截斷然後有覺聖人之學事來即應事去則靜
應事時既無不敬至無所睹聞時亦敬以存之自
然虛靜惟虛靜故愈靈明而發以應事無不當雖
無睹聞若有當思固思之無害但所思者正爾非
以靜爲功而置心如牆壁也
諸書不曾言戒懼工夫惟中庸言之葢子思自性上
說來學者欲體道以全性若無此工夫則心未發
時可在道之外邪
天者理之所出心者理之所存心知即理動理動即天知故有萌於心則著見明顯莫大乎此豈必待
人知之乎
中庸慎獨兼大學兩慎獨意大學慎獨是誠意地頭
故先專主於心而後乃兼於身中庸前既言戒懼
工夫故慎獨兼外說章句謂隱是暗處又曰幽暗
之中此兼內外言之細事非是小事是事之未著
者二者皆是人所未見聞者亦即是毋自欺之意
致中和是戒懼慎獨推行積累至乎極處則有天地
位萬物育效驗
致中是逼向裡極底致和是推向外盡頭
位育以有位者言之固易曉若以無位者言之則
一身一家皆各有天地萬物以一身言若心正氣順
則自然睟面盎背動容周旋中禮是位育也以一
家言以孝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孫順以弟友
接而兄弟和以敬處而夫婦正以寛禦而奴僕盡
其職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位育也但不如有
位者所感大而全爾
此章首言性道教之義次又言性情之則而兩節工
夫止是戒懼慎獨兩端致則極乎此二者也致中
是戒懼而守其未之大本所以養天命之性致
和是慎獨而精其中節之達道所以全率性之道
前後只是性道兩句工夫而教在其中其用功處
只有戒慎恐懼慎致六字而已
此書以中庸名篇而第一章乃無中庸字未發之中
非中庸之謂也葢率性之謂道一句即中庸也此
句總言人物是說自然能如此者在人則惟聖人
能之是中庸也若眾人則教之使率其性期至於
中庸也
章句天以隂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
焉葢人物之生雖皆出於天理而氣有通塞之不
同則隨所遇有生人物之異氣通者爲人而得人
之理氣塞者爲物亦得物之理雖曰有理然後有
氣然生物之時其氣至而後理有所寓氣是載理
之具也故章句先言氣以成形後言理亦賦焉
天生人物是氣也而理即在其中理主乎氣氣載乎
理二者未嘗可離故本文天命之性雖專言理而
章句必須兼氣說若不言氣以成形一句則理著
在何處安有所謂人物葢言氣則有善有惡言理
則全善無惡故子思專舉理以曉人謂此理具於
心者謂之性即道心也率者循此而已修者品節
此而已學者學此而已自可欲之善進而至於大
而化之全此而已章句雲天以隂陽五行化生萬
物是總說卻分言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兩句下猶
命令也一句獨接理亦賦焉說於是人物之生以
下卻是專說理以釋性字葢若不兼氣來說則教
字說不去既全是理則人無不善又何須教
動靜開闢徃來屈伸只是兩端而已故古之聖人定
隂陽之名然消必不能遽長暑必不能遽寒皆有
其漸故又定五行之名五行之名既立則見得造
化或相生以迴圈或相制以成物錯綜交互其用
無窮矣然而隂陽生五行而五行又各具隂陽亦
不可指其先後也
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爲健順五常之德葢健
是陽之德順是隂之德五常是五行之德七者亦
皆因氣而有此德人物雖皆有只是人全具而物
得其偏如馬健而不順牛順而不健虎狼父子有
仁蜂蟻君臣有義而無他德之類
健者陽之德順者隂之德五常者五行之德然此健
順不是言幹健坤順就造化上說此是就人物上
言其性自具此七者
性中只有五常而此加健順是本上文隂陽而言也
五常固已具健順之理分而言之仁禮爲陽爲健
義智爲隂爲順信則沖和而兼健順也錯而言之
則五常各有健順義斷智明非健乎仁不忍而用
主於愛禮分定而節不可逾非順乎
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謂順理之自然者行之即是
道率字不是工夫只是順說葢中庸首三句且只
說性道教三者之名義及聖人品節爲教之後下
面方說學者工夫
品節是品量節約
氣稟或異應上氣以成形說此其所以聖人立教也
人物所當行者固人物各率性之道然唯聖人能盡
己之性而盡人物之性故可品節之以己之所能
者使人能之以物之所當然者使人用之
人之所以爲人一句代天命之謂性一句葢言性則
人物之所共者此段言人只就人性上說中庸是
教人全性之書故也人全其性亦只是盡爲人之
道而已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章句前面皆言理言性到此乃
言體字葢理性無形恐難體認此則就實處言之
包下心氣二字父母之于子同體而分形天地乃
吾之大父母吾之身本大父母之遺體惟其一
體也故吾心可感天地之心吾氣可感天地之氣
而其效驗如此但致和主於行事中節而言不但
在我身之氣順萬物便能育也與上心正即能感
天心之意頗不盡同此言當細體認葢萬物育不
專在黙然感應須要所以處物之道施於政事者
得其宜則是事雖在外乃我在內之氣得以達之
須著如此一轉看
兩個一體字意不同
二章
語録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
之意同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
時而不中即正未必中此說極好比並體認
小人反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平時既有小人之心而
臨事爲惡又無所忌憚縱意而行反字是用力字
謂他故意反中庸之道行之葢此小人非但是愚
者而已
章句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隨時而在此隨時字含
兩意謂君子毎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
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
之如此爲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爲中是一事各于
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
章句二又字是眼目
章句上既言隨時處中矣下卻言戒謹恐懼而無時
不中時中當是慎獨事而言如此事有可疑今詳
朱子意葢言本文但言君子中庸未見有專指用
處且安有無體之用故複如前解題而全舉曰
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是則所謂君子
中庸者體用兼全動靜一貫者也故下文先言以
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以德字貼襯在
君子字上其下卻雲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戒懼
是言平日存中之體應上德字而無時不中則發
處皆中庸矣君子而時中時字當用力看便見意
中庸一篇凡七章有中庸字余六章皆與此不同
故于此章全解次章則曰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
是從用上說以三章爲例則後章從可知八章又
曰行之無過不及二十七章曰不使過不及可見
與此君子中庸一語不可同論
三章
論語言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章上
無德字下有能字此能字即所謂德也但論語言
中庸之德此章言中庸之道
四章
道不行不明非是人不行之不明之是言道自不行
于天下不明于天下謂大道窒而晦也
知賢者之過當作兩層意看大率道者極乎中而已
兩道字便是中所謂過者過乎中也稟氣清而淳
者則爲聖人知之至行之及自合乎中稟偏於清
者則爲知知者惟務於知既不以行爲事則所知
愈至高逺而過中矣稟偏於淳者則爲賢賢者惟
篤於行既不求知其至則所行必至激切而過中
矣此止就正理上看若知者如老釋之空寂賢者
如沮溺之道逺又如下索隱行怪之類是又非正
道而過於中者須作兩意看方盡得知賢過中之
義愚不肖之不及只是一般
道不行者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者行之過與不及
是固然矣然下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
味也是又總於知葢二者皆欠真知爾若真知理
義之極至則賢者固無過知者亦必篤於行不徒
知之而已矣
不足知不足行正言知賢者之心葢是他心惟通這
一路更不管那一路
五章
前章主于知此章主於行葢知然後能行既知之又
須能行故此二章明次第如此
金先生曰第二章以來小人反中庸民鮮中庸之久
賢智過中庸愚不肖不及中庸總歎曰道其不行
矣夫故自六章以後開示擇道中庸之方在知仁
勇三達德
六章
好問是有疑而問於下如臣如民下至芻蕘無不詢
之察邇言是於所問而對者及下人之言凡達於
上者雖淺近必詳察其理古者民俗歌謠必采之
以觀民風亦察邇言之類
舜固聰明睿知而不自用故好問察邇擇善而用其
中此所以愈成知之大聖德固是如此然或有見
聞所不及必須問而知者民事幽隱因芻蕘之言
而聞者則亦善用中故必兼此兩意看
執兩端而用中謂眾人所言於此一事雖同於善然
卻有處之厚薄不同卻將已之權度在心者度而
取其中或在厚或在薄必合於此事之宜者而行之
章句廣大謂隱惡而不宣光明謂揚善而不匿不言惡
者掩覆涵容足見其量之廣大言善者播告發揚
足見其心之光明
權度精切舜本然之知也又好問察邇欲周天下之
細故也此其所以爲知之大也與
七章
其義在於不能期月守中庸以起下章之能守意不
在罟擭陷穽以不知意承上章之知
以不能守中庸起下章之能
守
八章
擇字兼知行惟知之明乃能擇既擇即見之行事所
以下面即說守不再說行擇是當應事之時守是
事過之後常守在複遇此事又如此應皆合中庸
服膺是守也弗失又覆說守之固也
舜知是全體之知顔仁是毎事之仁凡已擇乎中庸
者固仁矣而應天下之事猶擇之未全也毎得一
善則服膺弗失守之者固日新其德則漸可全也
三月不違可見此意
人之於道不過知行兩事耳知者智也行者仁也四
章既言道之不行不明然所謂愚不肖者固易見
不足論惟智者知之過而不務行賢者行之過而
不求知所以至於中庸者鮮賢者之過如栁下惠
之和伯夷之清未及孔子之時智者之過如曾晳
之言高而行不掩者近之矣故六章言舜之智而
謂隱惡揚善執兩端用中是行之意重此舜不
專于智而道行矣八章言顔子之仁而曰擇
乎中庸是知之意重此顔子不專於行而道所以
明矣
九章
七章能擇中庸而不能守是知其理而未行至此章
能爲三者而不能中庸是能行所難而知未至者
故此二章處於知仁之後而下接言勇之前葢謂
知仁皆當勇也
七八九章皆言中庸而意不同上兩擇乎中庸毎事
上言中庸不可能全體上言
義精是知之極仁熟是行之裕是就應此事之前說
無一毫之私是就應此事時說件件如此則全乎
中庸矣
十章
子思引夫子告子路當強之目以合舜知顔淵仁爲
三達德之事非子路之所已能者
子路好勇是子路生質本剛事皆勇爲至此葢亦未
知勇之所當務者故以爲問
南方之強雖君子之強然亦未是中庸是不及於強者
北方是過於強者君子則爲後四者之強上君子
字輕下君子字重
君子之道中而止南方之強不及中北方之強過於
中固皆未至然上言君子居之則比強者居之者
爲勝之矣不及者勉強至中頗易過者矯揉至中
尤難兩君子字雖不同然言君子四強哉終是接
著君子說
南陽方北隂方陽舒散而隂収斂舒散便和柔収斂
便剛勁此葢大約言風氣之偏則風俗隨異其實
南人豈盡柔弱亦有剛勁者北人豈盡剛勁亦有
柔弱者然寛柔以教不報無道是言柔之甚而善
者衽金革死而不厭是言剛之甚而過者
章內兩而強不同前是汝之所當強者後而字是承
上句虛字說君子亦不同君子居之輕如善人長
者之類故君子重是全德之人
四強哉矯上兩節言守身應事之常下兩節言出處至
極之變下兩節雖尤難然上兩節常貫在其中國
有道必出而仕人于未達其所守者正而堅既達
之後接物廣應變多或有易其守者國無道固不
可出能守之至死畧不易其志如夷齊餓死而無
怨者方是強之至君子或出或處必當合於中庸
者如此
四強哉矯雖是勇而合中庸之體段而不流不倚
不變正是立則防弊以教學者處
有道無道只言國之治亂有道乃可仕之時無道無
可出之理君子之出也固當合乎中庸然此卻只
言出以後事葢君子平日自修須有能守之節上
之人亦爲其有所守故用之及既仕則必堅守平
昔所守者可也今乃不能守其前志不爲富貴所
淫則爲事物所汨爾爲所汨者知未盡爲所淫者
仁未至皆是不能勇以全夫知仁者也故以不變
塞爲強若國無道不變平生所守是窮而在下當
不可仕之時雖困悴窮蹙不能全其生亦必死而
安於天耳推而言之雖已仕國者適逢國變而無道
則必屹立不移以身徇國若此豈非至強者歟
章句含容形容寛之量防順體仿柔之容皆不可以
爲正訓
資質既寛柔其心必愛人所以能誨人之不及若無
道之來直受之不思報之者亦以能含容防順故
也上兩字以質言下兩字以接人言祍金革死而
不厭卻只是一意
言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善斡旋說
中庸之道知固在前然行之及方是曰非有以自勝其
人欲之私仍舊是說仁重
十一章
索隱是求人之所不必知行怪是行人之所不必行
索隱知者之過行怪賢者之過此不能擇乎中庸者
聖人不爲也或有雖不索隱行怪而能擇乎中庸然
行之止于半塗而不力以求至是不能守者聖人
自不能止必行至於終也是以君子常不違乎中
庸則不爲隱怪可知由仁義行雖終身不見知於
世亦未嘗有所悔艾不半塗而廢也豈非聖人之
事乎孔子前說有兩吾字以身任之故下文謙不
肯當但曰惟聖者能之其實依乎中庸即夫子之
弗爲者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即夫子之弗能已者雖
欲避聖人之名自有不可得者
上兩節各有吾字第三節乃言聖者能之雖聖人不
肯自居然曰聖者能之正是爲學者標的
前章言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又言遁世不見知而不
悔惟聖者能之正見得君子能處困悴厄窮而裕
如者爲尤難故子思連引聖言以爲戒此亦章中
一意
第一節索隱行怪皆是知之不明是不知也第二節
行而不能守是未仁也第三節知仁俱至故章句
謂一是不當強而強二是當強而不強三是不賴
勇而裕如者
章句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總結三節弗爲
索隱行怪知也依乎中庸則知之盡也弗能半塗
而廢仁也遁世不見知而不悔仁之至也皆出於自
然則不賴勇也
十二章
費者用之廣當作芳味反若符味反者則性也章句
此音當改
夫婦知能造端夫婦
君子之道費君子之道
鳶飛魚躍察乎天地
兩君子之道無異前後夫婦前後天地字皆不同夫
婦知能只是衣食起居日用之常皆道之費造端
夫婦是言夫婦暗室幽防之處亦道之費天地有
憾是言天地之偏反形容道之全察乎天地是指
天地之大正發明道之廣葢此章以君子之道費
而隱一語發端夫婦聖人于人上見道之費鳶飛
魚躍於物上見道之費下又再提起道字而言造
端是就夫婦知能處舉其至隱防者明道之至近
又言天地是就鳶之上魚之下推極以明道之至
逺此章不言工夫只是言費造端只如爲始兩字
不可作工夫看
聖人不能知行非就一事上說是就萬事上說如孔
子不如農圃及百工技藝瑣細之事聖人豈盡知
盡能若君子之所當務者則聖人必知得徹行得
極
大小二字接道而言天地之大人猶有憾者爲功不
能全也君子之語大小而莫能載破者爲道無不
在也天地對大小猶有憾對莫能載破金先生曰
物有限量則可載道無限量故莫能載物有罅隙
則可破道無罅隙故莫能破
鳶飛魚躍大概言上天下地道無不在偶借詩兩語
以明之其義不專在於鳶魚也觀此則囿於兩間
者飛潛動植何所徃而非道之著且蒼然在上塊
焉在下者又庸非道之著乎則人於日用之間雖
欲離道有不可得者其可造次顛沛之頃不用功
於此哉
此章專明道充滿天地萬物之間使學者體認欲其
灼然如見皆不言工夫然既知吾身之小以極
天地之大萬物之防無非是道則於道不可離當
體之而不可少有間斷明矣
中庸三大章前章言中庸此章言費隱後章言誠中
庸者道之用於萬物無所不在其體固隱是亦費
而隱也但中庸是就人事上言道之用費是就
天地人物上言道之用葢先言中和見道之統攝
于人心次言中庸見道之著見於事物此言費隱
見道之充塞天地後言誠則見聖人與天地爲一
中和以戒懼慎獨爲存養省察之功中庸則以知
仁勇爲入德之門費隱則于諸章雜言其大者小
者欲人隨處致察以全中庸之用皆所以求至於
誠也
章句近自逺而四字中庸包盡事物無窮此是解
及其至三字是就始終兩端說
體之防指理性言舉全體指道之全體言二體字不
同
家语观周篇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耼博古知
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徃矣
敬叔与俱至周问礼于老耼学乐于苌厯郊社
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
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史记孔子世家
亦载其事老耼爲周柱下史明习典礼故徃问之
春秋左氏传昭十七年郯子来朝昭子问曰少皥氏
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我高祖少皥挚之立也鳯
鸟适至故纪于鸟爲鸟师而鸟名鳯鸟氏厯正也
元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
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
马也鸤鸠氏司空也鷞鸠氏司冦也鹘鸠氏司事
也五雉爲五工正九扈爲九农正仲尼闻之见于
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天子失官学在
四夷犹信
聖人不能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是兩様意思孔
子不得位是在天而非己所能堯舜病博施是其
勢而非力所能二者皆是舉大綱說其實細事末
節不出道之用自有聖人不必能者
憾只是不足意覆載生成分言天地各有所主固不
可全寒暑災祥合言天地氣數之變有不能已者
化育流行上下昭著此雖言鳶魚而非獨言鳶魚也
正謂道於天地萬物無不在爾
活潑潑地此是程子形容子思用鳶魚兩語使人知
化育流行如此活潑潑地學者須真見得天地萬
物皆如此流動充滿活潑潑地畧無滯礙之意方可
十三章
人之爲道而逺人此爲字重猶言行道不可以爲道
此爲字輕猶言謂之道
睨邪視視所執之柯也視正視視所伐之柯也詩言
伐柯者取則不逺子思謂柯有彼此之異尚猶是
逺道在人身而不可離又非柯之比故教者只消
就眾人自身所有之道而治之爾行道者不假外
求治人者無可外加
第三節言行道之方惟在忠恕自此行之則可至中
庸之道故曰違道不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
人推己之恕也然非忠爲本則亦無可推者矣葢
忠以心之全體言恕就毎事上言所接之事萬有
不同皆自此心而推然應一事時盡己之心推之
則心之全體卻又只在此故恕非忠無以本忠非
恕不能行二者相須缺一不可所以經以施諸己
兩句總言忠恕而章句亦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
施於人忠恕之事也
施諸己不願亦勿施於人上就事不善一邊說反而
言之己之所願者則必使人亦得之亦當如此推
事父事君事兄上三以字訓用字意甚重非語助也
葢求責於人者乃道之當然而已行之乃未至此
故欲用以事父君兄先施之際以責人者責之於
己使必合乎道之當然則事父也孝事君也忠事
兄也弟施之朋友也信我之所行亦若責之於人
者矣此節專言自修以下句爲重亦恕之道也
人倫有五夫婦之倫不可自反故不舉下文著庸德
庸言兩項關定謂盡人倫不過在庸德庸言之間
行與謹字對德毎不足故當勉於行言毎有餘故
當謹而不敢盡
庸德庸言謂如上四事所以責己欲盡其道者亦不
過常道爾但行之難故毎不足則當勉而至言之
易故毎有餘不可恣其出若是則言行相顧豈非
篤實之君子乎此雖接上四未能而言推而廣之
於凡天下之事皆當如此也
第一節言修己第二節言治人第三節修己治人之
方第四節即是恕葢恕是推己上不願勿施是從
裡面推出下以事未能卻就外面反推入然推而
知其未能則於及人必欲其能是又就裡面推出
也
章句眾人望人此眾人只是天下人所同行所可至
公共的道理又以等級言則與聖人相對說正是
體貼改而止之意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於桐丘鄭
請救于齊齊師救鄭及留舒違糓七裡糓人不知
章下謂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凡此只就本章摘
出說費字非是孔子真不能於此與十二章聖人
有所不能意自不同讀者不可一律看
十四章
輯畧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于民素富
貴行乎富貴者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修身
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言忠信行篤敬雖
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
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
患難者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
反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富我以
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此在下位
所以不援上也遊氏曰上不陵下下不援上惟正
己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君子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
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
也故窮通皆醜學者當篤信而已失諸正鵠亦行
有不得之說也此二家說此章極明
君子道中庸不過因其所居之位行其所當然無思
出乎其位而外慕也素位而行是正說不願乎外
是反說才願乎外即是不能素位而行下面卻自
作兩節分說去呂氏之說已詳葢居富貴自有富
貴所當行之道不能行所當行者固不可而位有
高下任有大小又當隨所宜而行若有不中其節
者皆非也居貧賤亦有所當行之道安分樂天不
厭不懾常守不變若有不甘爲之意皆非也凡人
非富貴則貧賤此是人之大分至於夷狄患難又
是上兩等人或有遇之之時亦各於其中行所當
行此所以君子無所徃而不自得自得是從容無
急迫滯礙而自快足之意此說素位而行也次兩
句不陵不援再言不願乎外陵下援上皆願外也
呂氏遊氏之說已明又如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
祀仙人豚肩不掩豆難爲下也管敬仲鏤簋朱紘
山節藻棁難爲上也亦陵下援上之意皆非中庸
也正己不求於人結上二句無怨亦說己無怨既
是正己不求於人則凡事惟恐不自盡亦奚暇見
人之不足於我而怨之哉故己有所蘊固有當得
於外者天不畀而無不平於天人不從而不歸罪
於人所以君子居易以俟命此句又是戒君子當
如此小人行險以儌幸反此一句說以射爲比又
引夫子之言證正己不求人之意
正鵠見論語射不主皮章
十五章
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細防處不
合道而於逺大之事能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
勢必當如此故于費隱之後十三章先言修己治
人必恕以行之而謹其庸德庸言次十四章則言
正己不求于人此章則言自近及逺是言凡行道
皆當如是也引詩本是比喻說然於道中言治家
則次序又如此
夫婦人倫之首故先言夫婦之道常人處夫婦之間
多褻狎不則又太嚴厲二者皆不可也是以古人
貴相敬如賓者處夫婦之道和而正則善矣爲琴
瑟之聲和而正故以爲比此章首言夫婦兄弟次
之家人又次之自內以及外即大學三引詩之意
人能處其家使正而和如此則其能孝而父母之心
安樂可知矣
章句人能和妻子宜兄弟則父母安樂之和妻子結
詩上二句宜兄弟結中二句便言父母順則詩下
二句皆言效驗也
十六章
十五章自費隱章造端夫婦語意來此章察乎天地
意也
齋明二字只就心上說盛服乃說身齊是用功屏其
思慮之不齊者而一於所祭之鬼神明是既齊而
心之體明潔不雜可交於鬼神也
凡祭有三曰天神地只人鬼總言之亦通謂之鬼神
大率天之神皆陽類也其中亦有陽中之隂如月
如五星之金水如雨師之類然終是麗於天者地
之示皆隂類也亦有隂中之陽山林與川澤對則
山林陽也原與隰對則原陽也然終是麗於地者
惟祭人鬼則求魂於天求魄於地是合隂陽而祭
之鬼雖是隂其中卻是合隂陽來格
如在上如在左右不是或在上或在左右是言在上
又在左右也擗塞滿都是鬼神此是于祭祀時見體
物不可遺處所以章句言乃其體物不可遺之驗
此是就祭祀人所易知之鬼神上指出使人知夫
鬼神之德如此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謂神之來格也既不
可測度是有祭則鬼神必臨之矣其可厭怠而不
敬乎
防者隱不可見聞也顯者理之昭著也此是誠之不
可掩覆者也
第二節言鬼神之大者三節主祭祀而言鬼神之小
者四節與三節同五節又總贊鬼神之德誠即鬼
神之德也
章句天地之功用天主神而言地主鬼而言此以天
地間二氣徃來大體言之是橫說鬼神造化之跡
造是造就萬物以神而言化是物既成氣盡時至
而消化去以鬼而言是防說鬼神所以造化萬物
者其理之妙不可見至於鬼神徃來始可見爾故
曰造化之跡
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跡功如功業是能如此者用如
用事是見如此施爲者天地無非生成萬物其功
用于生成處見此是合說鬼神造化乃天地隂陽
之妙用亦是造化萬物也其所以然者不可見其
可見者則於物之成敗生死上顯故曰跡此是開
說鬼神天地之功用是隂陽相合者總言鬼神也
造化之跡是兩頭說鬼神是見他如此成又見他
如此敗其蹤跡皆有實是見如此者見賢遍反
天地言其形造化言其理造化之理妙不可見惟見
其成敗之跡耳
二氣之良能謂二氣自然之善道能如此屈伸消息
者良能二字精妙
鬼神者隂陽之靈靈字易見靈字便包含著祭祀之
鬼神
二氣是開說前節是陽後節是隂如春夏是陽秋冬
是隂如有二物相磨蕩一進一退一氣是合說共
是一個氣來則全來便是陽去則全去便是隂鬼
神於二者之間皆可見都只是這氣在人體驗故
曰實一物而已
視弗見聴弗聞性也體物不可遺情也使人承祭祀
者功效也
前以天地造化二氣一氣言鬼神是言鬼神之全是
大底鬼神後所謂承祭祀者如天神地只人鬼及
諸小祀亦皆鬼神卻是從全體中指出祭祀者是
小底鬼神使人因此識其大者
物之終始莫非隂陽合散之所爲隂與陽合爲物之
始隂與陽散爲物之終上言氣至而伸爲陽爲神
氣反而歸爲隂爲鬼是就兩頭說此又言隂陽二
氣合而生離而死是就中間混同處說隂陽鬼神
無徃不在只要人看得活
隂陽合散又是隂與陽之氣二者相合生物爲物之
始及其久也此物中之陽氣上升隂氣下降其物
即死爲物之終是就一物中說隂陽
體物者爲物之體也幹事者爲事之質幹也此倒用
之則體字幹字俱是用字
禮記祭統曰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也君子
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聴樂心不苟慮
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君子之齊也專
致其精明之德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此齊明之說也
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
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
也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隂
爲野土隂讀與防同其氣發楊於上爲昭明焄蒿悽
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注焄謂香臭蒿謂氣
蒸出貌朱子謂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
蒿是其氣升騰悽愴是使人慘栗感傷之意因說
修養人死時氣衝突知得焄蒿之意親切謂氣襲
人知得悽愴之意分明此百物之精爽也何文定
曰此是隂陽乍離之際有此聲臭氣此是祭義所言
正意若中庸章句所引乃是借來形容祭祀來格
洋洋如在之氣象此是感召複伸之氣與祭義所
指自不同讀者詳之
十七章
自舜其大孝至子孫保之一節言舜之事實自故大
德至必得其壽一節泛言理之必然自故天之生
物至覆之一節言善惡之應所必至後引詩又證
有德之應如此故以大德者必受命結之
舜其大孝也與一句是綱德爲聖人下五句皆孝之
目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是孝也以身言之
也德爲聖人盡己性而盡人物之性是全其身豈
非孝之大者爲天子父尊之至矣以天下養養之
至矣宗廟饗子孫保雖就舜言之然欲子孫之安
富尊榮厯世之久皆父母之願人之情也今皆得
之則此五者豈非皆孝之大者
爲人子者以有德光顯祖父爲榮舜之德則至於聖
人爲天子則祭祀奉養之禮極其尊有四海則祭
祀奉養之具極其備宗廟饗之卻是就舜身上說
昔者舜傳禹禹既即位祀舜爲宗而又封商均于
虞舜封子均于商葢禹改封于虞後有虞思是也
虞亦立廟祀舜及其祖父至周武王又封舜後胡
公滿于陳則是子孫保之也舜之德至上使祖父
如此榮盛綿逺是所謂大孝
大德者必得祿位名壽乃理之常然獨孔子有德而
不得祿位與壽惟得聖人之名耳此乃氣數之變
金先生曰此所謂聖人所不能也然聖教無窮而
萬世享之子孫保之此又大德必得之驗也
栽培傾覆如春至草木有發生之意故天以雨露滋
長之秋冬草木有黃落之意天乃以霜雪雕零之
此以物言也以人言之有此德者天必以上四者
與之無其德者天必棄絶之如大舜以匹夫而有
天下桀紂以天子而喪其身此栽培傾覆之意
栽培傾覆言天之於物其理如此實以喻人栽傾屬
人培覆屬天栽傾是其材培覆乃篤也如此章大
舜之德是栽也得四者是培之也桀紂傾也喪亡
覆之也下引詩皆是因栽而培之章句氣至兩句
只是培覆之訓詁不是說盡此節之意
可嘉可樂之君子其令善之德顯顯昭著宜於人民
故受天之祿而爲天下之主既受天祿矣而天又
保之祐之複申重之其所以反覆眷顧之者如此
又重明上文大德必得四者之一節也
所引詩是節節說上受祿於天保祐命之自天申之
是三節意只是個感應
十八章
十八章十九章皆以周事繼大舜而言二十章又以
孔子繼周皆是聖人所行所言見道之費而無不
合於中庸者
無憂專就國家上說如文王羑裡之囚若可憂矣雖
聖人無入不自得然亦是一身事父作子述卻是
言國家事周家上世節節有憂患自夏君棄稷不
務不窋即失其官守逃之西戎至公劉方複遷豳
大王又爲狄人所侵遷岐雖肇基王跡而身遭憂
患矣王季雖勤王家辟國漸廣亦但守舊國而已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猶守諸侯之舊至武王
方受命爲王故惟文王用得無憂二字葢文王上
承己大之國己不勞力不逢變故以歸之子適當
商家天命未絶之時己得從容其間至承天命著
戎衣奄有四海乃是武王事文王都不費力
贊武王之言與贊舜意同但此言身不失天下之顯
名彼言德爲聖人防有輕重亦論韶武之意然此
顯名亦聖德也
末猶後也終也葢周自太王王季文王累世積德累
功國土已大最後至武王始受天命爲天下君周
公乃承之而追王先王如此說末字則與上下文
都相貫穿訓末爲老恐未安葢武王之齡古書不
一
追王三王武王既滅商在商郊已行之禮記大傳曰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於
社設奠於牧室牧野之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
駿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厯文王昌不以卑臨
尊也又書武成金縢康誥酒誥諸篇皆可見所謂
周公成文武之德只是又推太王王季之意而以
天子之禮祀先公也斯禮也以下又是因此以定
上下之通禮
章句實始翦商見論語泰伯至德章
先公祖紺以上通鑒前編曰堯封棄于邰世後稷以
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失其官自竄戎翟之間
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始遷于豳路史謂稷生漦□
漦□生叔均自後稷至公劉十餘世而漢劉敬傳
亦謂後稷十餘世至公劉按世本自公劉歴慶節
皇僕差弗毀隃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
公祖紺祖紺號太公史記作公叔柤類諸盩十有
二世而生古公亶父自稷至亶父葢二十余世矣
史記以不窋爲後稷子而又缺辟方侯牟雲都諸
盩四世遂謂後稷至文王爲十五世且契稷同時
受封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千餘
年而十五世其亦誤矣今按章句謂祖紺爲太王
之父據疏文而言也
輯畧曰期之喪有二正統之期爲祖父母者也有傍
親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眾子昆弟昆弟之子是
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
諸侯絶大夫降
十九章
前章言文武周公此章又言武王周公葢武王有天
下然後周公可以制禮二者皆繼志述事之大者
然章內皆是言禮葢主于周公而言謂制爲宗廟
祭器祭服薦獻之禮而於宗廟之中又制昭穆序
爵序事酬燕之禮又制爲郊社之禮然祭祀一事
中推至於極則郊天禘祖乃其至大者非聖人大
孝孰能如此此皆費之大
此章雖連言武王周公其實主周公而言周公合先
王累世典禮定爲周制中間損益合乎時中又可
垂之萬世其制大備矣此獨指祭祀一禮而言祭
中又只主於宗廟推及郊社爾此皆舉一端言之於宗廟中自有許多曲折可見道之費推至於吉禮之全其費可知又推至五禮備其費又可知也
舜之孝行於一家故只謂之大孝周制禮達乎天下
故曰達孝饒雙峯意亦如此
修廟只是拚掃整飾常使嚴潔之意譬如今人居室
整漏拂塵灑掃之類古注修埽糞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含兩義昭穆本是祫祭時太
廟設主而有此名宗廟之位由此而立祖宗既以
此爲序則子孫世世皆一昭一穆縁上世次序而
定此言序昭穆謂廟中行禮以及燕毛皆用昭穆
爲序則此序字主於人而言之意爲多昭穆又不
止廟中尋常尊卑亦皆以此爲序也
宗廟之禮一節五事禮義至爲周密序昭穆既明同
姓之尊卑序爵則合同姓異姓之貴賤葢皆指助
祭陪祭者而言至於序賢則分別羣臣之賢否廟
中奔走執事必擇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趨事之純
熟者謂之賢賢者既有事則不賢者亦自能勸雖然
既以有事爲榮則事不及之者豈不有恥則又有
序爵以安其心執事者既榮無事有爵而在列者
及賤而役於廟中者皆得與旅酬至此賢不賢皆
恩禮之所逮然此合同姓異姓而通言至祭禮已
畢屍既出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姓是親親之禮
又厚於疎逺者見制禮之意文理密察恩義周備
仁至義盡而文章燦然
天子諸侯之祭禮已亡雖間有表見於禮中者今不
可知其詳矣所存有特牲饋食禮諸侯上士之祭
禮也少牢饋食禮諸侯大夫之祭禮也大抵祭必
立屍必擇賓賓長一人眾賓無數眾賓者賓之黨也
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侄兄弟皆會小宗
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一族皆至兄弟者主人
之党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
面而立迎屍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
屍主兄弟各相獻酬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
奉尸賓者謂之獻賓酌以答主人者謂之酢主
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奉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謂
引導之飲也旅眾也主人舉觶酌酒自西階酬賓
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而未飲兄弟弟子
舉觶于長兄弟于阼階弟子者兄弟之後生者也
長兄弟者兄弟之最尊者也弟子導飲而長兄弟
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觶於阼階酬長兄弟長兄
弟西階前酬賓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
事者無不徧卒飲者實爵於篋此旅酬之大畧也
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亦先自飲
如前儀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觶酬兄弟之党長兄
弟取觶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謂之
無算爵所以逮賤者如此
天子祭禮亡不可考楚茨之詩曰神具醉止皇屍載
起鼓鐘送屍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
兄弟備言燕私箋雲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
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疏屍已出而諸
宰及君婦徹去俎豆歸賓客之俎其諸父兄弟留
之使皆備具我當與之燕而盡其私恩也
天子諸侯大夫皆立始祖廟大夫亦有始封者如三
桓之家即慶父叔牙季友爲始祖廟亦百世不遷
士則無始祖廟只是祭祖禰而已葢位卑者流澤
不能逺而士又無采邑故也
章句適士天子之上士即元士也受三命埰地五十
裡視子男二廟祭祖禰
官師凡有司之長葢中士下士也雖立一廟祭禰卻
於禰廟並祭祖
顾命言所陈之寳有赤刀大训璧琬琰大玉夷玉
天球河图允之舞衣大贝鼖鼓兊之戈和之弓垂
之竹矢章句曰之属则尽包上陈者在其中
山先生曰宗器于祭陈之示能守也于顾命陈
之示能传也书注疏赤刀寳刀赤刀削其刀必有
赤处削音笑刀之小者大训三皇五帝之书训诰
亦在焉文武之训亦曰大训宏璧大璧琬琰琬圭
琰圭也夷常也或以爲东夷之美玉天球雍州所
贡之玉磬也河图伏羲时龙马负图出于河允古
国名舞衣舞者之衣大贝如车渠车渠车罔也谓
贝之大如车之罔鼖鼓长八尺兊和古之巧人也垂
舜时共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
度故歴代传寳之
天官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
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注䟽用
禽獸謂煎和之以献王行與用同膳謂煎和也腒音渠乾雉鱐
音搜乾魚鱻與生同魚也羽鴈也膏
脂也香牛脂臊犬脂腥雞脂羶羊脂羔豚物生而
肥犢麛物成而充腒鱐暵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
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物之弗勝是
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之牛属司徒土也雞属宗
伯木也犬属司冦金也羊属司馬火也今按四時
食物不同而煎和之脂亦異於是見聖人制礼豈
惟宏綱大用法天体道至於一食之際莫不盡其
曲折其文理宻察如此四時之宜食脂膏之宜用
必自有深意注䟽之言未必得之
薦其時食章句引周礼一語而以之𩔖两字該之雖
是包下三語然如詩獻羔𥙊韭冬薦魚春獻鮪月
令孟夏以甞麥仲夏以雛甞羞以含桃孟秋
登榖甞新仲秋以犬甞麻季秋以大甞稲皆先薦
寢廟此𩔖皆是也
子姓者子之所生猶言子孫也
在外公侯伯子男在内卿大夫士皆爵也言公矦
則諸矦之駿奔走者也卿大夫則朝臣之執事者
也
宗謂大宗伯小宗伯掌祀事内宗也薦加豆籩外宗
之佐王后皆是也内宗王同姓女之有爵者外宗
王姑姊妹女之有爵者祝大祝小祝有司則如宫
正執燭天府沃盥陳寳器司几筵設筵几司尊彛
詔酌辨用鬯人供鬯人掌祼内宰賛祼獻司徒
奉牛牲羞肆司馬羞牲魚授𥙊内饔割亨司樂以
其属作樂膳夫徹俎司士賜爵之𩔖凡執事于廟
中者皆是肆託歴反亨普庚反𥙊畢而燕今不知其儀亦於楚茨之詩見其大意云
皇尸載起神保聿歸然後言諸父兄弟俻言燕私
下章曰樂具入奏者謂
𥙊時在廟燕當在寢故𥙊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所謂燕礼其可知之仿
佛若此
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甞秋享先
王以烝冬享先主
論語專爲禘發其精中庸汎言𥙊祀其詳恐非
記有詳略
讀中庸叢卷下
元許謙撰
二十章
金先生謂此章當作六節看章首至不可以不知天
爲一節逹道逹德至天下國家矣爲二節九經爲
三節凡事豫至不誠乎身爲四節言誠爲五節博
斈以下爲六節此章朱子以爲皆孔子之言金先
生謂聖人之言簡自仁者人也皆子思之言雜引
夫子之言反覆推明之
第一節文武之政全体大用雖無不㪯而其要在乎
得人擇人之道則在脩身脩身須是以仁仁道雖
大只是親親爲要
敏樹是樹藝之樹是活字
脩道以仁之仁是仁之全包四德者
仁者人也此是自古來第一箇訓字言混成而意深
宻深体味之則具人之形必須盡乎仁其所以盡
仁則不過盡人道而已朱子所謂天地生物之心
人得以生者元者善之長人具此生理自然有惻
元許謙撰
序
中庸專言道故起首便言道學道統道學主于學兼
上下言之道統主于行獨以有位者言之至孔子
之生他無聖人在位則道統自在孔子凡言統者
學亦在其中學字固可包統字
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此是言
堯舜以前夫子翼易始於伏羲今之言聖人者必
自伏羲始然自開闢生物以來只有首出庶物之
聖人與天同道而立乎其位者但前聖所未道故
不知其名此但言上古聖神葢混言之又不知大
學章句序專以伏羲爲始否也
聖人大率有兩等有自然之聖生知安行所謂性者
也有學而成之聖積而至於大而化之所謂反之
者也此不言聖人而言聖神是指性之自然神明
不測之聖也此言上古創始有位道與天合之聖
人言動皆可爲天下法則者爲道統之始下此皆
是接傳其統者
繼立二字不要重看天道流行無物不在眾人所不
能知惟神聖自然與天合而言動皆可為萬世標
準非是有意繼續天道特爲人而立法也
論語堯曰諮爾舜至天祿永終王文憲以爲舜典脫
簡當在舜讓於德弗嗣之下此正傳心之要也
理與氣合而生人心爲一身之主宰又理氣之會而
能知覺者也人心於氣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
是也然此亦是人身之所必有但有發之正不正
爾非全不善故但雲危謂易流入於不善而沒其
善也道心於理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
也亦存乎氣之中爲人心之危者晦之故防而難
見心只是一於心上加人字道字看便見不同若
只順讀人心道心字卻似有二心矣謂之道則是
天理之公謂之人則是我身之私雖我身之私亦
非全是不善因身之所欲者而正即合乎道而
爲道心之用矣如鄉黨所言飲食衣服之類皆人
心之發在聖人則全是道心君子于毎事皆合乎
理義則亦無非道心也大抵人心可善可惡道心
全善而無惡
朱子書傳曰心者人所知覺主于中而應於外者也
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于義
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
心難明而易昧故防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
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之主
而人心聴命焉則危者安防者著動靜雲爲自無
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 大防皆同而傳
注與作文之體自不同故此語尤簡潔易看
人心是所欲爲之事道心是發應事之理人心聴命
於道心只是事皆順理耳危者既安則便是道
微只是隠防之意故難見今添妙字是貼襯防字
不必重看
精則察夫二者之間是察人心道心之間要察到疑
似纎毫之際此言心是指動處當時告大禹故言
如此若學者則用格物致知之功辨別眾理明至
善審然後可精其動處也
私字就形氣上來蓋既見此形氣而成人則此人爲
一人之私故必欲得於外以濟乎已所以易流於
欲下當與公字對卻用正字者謂性命之正則是
得之於天者固與天地人物同言正則公意自在
其中而正字於已切
繼徃聖開來學此學字應前道學字前道學是總包
上古以來相傳者此學字是夫子教後人者言繼
徃聖是明夫子教人亦是述上古聖聖相傳者耳
則子思所憂者豈專指夫子之教哉
更迭交互推演防繹
切言深要詳言周備憂深爲道之不明也故言之深
而要慮逺恐久而複失也故說之周而備
天命即道也能率性即道心也擇善者察之精也固
執者守之一也時中即中也惟君子爲能執之也
綱維言道體之大蘊奧言節目之詳及精密隱防之
理明言綱維盡言蘊奧
孟子推明此書謂見之行事及著七篇
上言異端下言老佛是異端至多楊朱墨翟許行之
徒以及諸子百家各立門戶議論不合聖道者皆
是
爲其彌近理所以大亂真葢其說宏逺幽防陳說道
德指明心性或有類乎吾道之言故爲所亂非如
百家之淺近易見也然而道德非聖賢所言之道
德心性非聖賢所指之心性固亦不難辨也倘無
中庸之書則吾道反晦而不明學者莫知所從又
焉得辨之乎
裳之要衣之領皆是總會處
章句輯畧或問三書既備然後中庸之書如支體之
分骨節之解而脈絡卻相貫穿通透中庸一書分
爲四大章如第一章十二章二十一章皆言其畧
而余章繼其後者皆詳言之三十三章又一章之
詳者詳畧謂此钜謂綱維細謂蘊奧諸說同異以
下專言或問
中庸
中庸大學二書與論孟二書不同論孟或聖賢自立
言教人或隨問而答或記聖賢出處動靜日用皆
是一條一件各見意趣學庸皆成片文字首尾備
具故讀者尤難然二書規模又有不同大學是言
學中庸是言道大學綱目相維經傳明整猶可尋
求中庸贊道之極有就天言者有就聖人言者有
就學者言者廣大精防開闔變化高下兼包钜細
畢舉故尤不易窮究
中庸德行之至極夫子嘗言之故子思取以名篇
解題
偏則不在中而在一邊倚則斜迤而不正過是越過
於中不及是未至於中不偏不倚是防說中字指
未發之體而言無過不及是橫說中字指已發之
用而言此皆是反說以四旁影出中字平如地之
平而無杌隉危處常者一定之理無詭異又常久
而不可變易惟其平正便可長久竒異險怪便不
可長久平橫說常防說此字正解庸字總而言之
惟中故可庸中而又須可庸乃中庸之道
程子謂不偏之謂中固兼舉動靜朱子不偏不倚則
專指未發者譬如置物不偏者在四方之正中不
略近東西南北之一邊不倚者非傾倚於一邊而
不正以心體而言不偏者渾然中正而無頗不倚
者不著於喜怒哀樂之一事雖皆指未發而言然
自有兩意不偏指其性之本然不倚指其用之未
發
常字該前後自前而言則常定而無異自後而言則
常久而不易
不偏不倚兩句是中庸之訓詁正道定理兩句是釋
中庸之義
始言一理者首章是也約而言之首三句是也又約
而言之天命之謂性一句是也末合爲一理末
章是也約而言之不顯惟德以下是也究其極言
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二語是也
首章
首三句言性道教之名義總人物言之而主於人率
性之謂道一句該上句而貫下句故篇中皆是說
道而性教在其中葢氣化流行不息者天之道也
是理也人得天道之流行者爲性當順此而行者
人之道也所謂率性也亦是理也然率性惟聖人
爲能之聖人之治己則盡己之性接人用物則盡
人物之性以眾人當率之而不能以失其生之本
故以己之安行者品節之以爲教使各知治己接
人用物之道處之既各得其宜則人與物莫不各
得遂其性矣則雖開說名義而未嘗不貫穿
爲一也自道也者至篇終皆是明人當行之道而
教其進之之方也
首三句是總說人物第三句修道固是人上意思多
然聖人修處亦和物都修了物雖不可教是教人
處物之道如春田不圍澤不殺胎不妖夭草木黃
落斧斤入山林魚不滿尺不粥之類皆是順物之
性而成就之不逆生意之意如馬絡頭牛穿鼻亦
是也妖於老反夭烏老反
性即理也在天地事物間爲理天賦於人物爲命人
物得之以生爲性只是一物所爲地頭不同故其
名不同
理存於心故不可須臾離不可者有贊其不能離之
之意有戒其勿離之之意
不睹不聞己之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不睹不聞也
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與莫見乎隱莫顯乎防
對說此言其定體如此戒慎恐懼與慎獨對說此
言修之之方前一節是操存即致中之事後一節
是省察即致和之事
戒懼不睹不聞謂但於不接物不當思慮時常敬以
存其心究其極則至於無所睹聞之際亦當戒懼
工夫至此而極密非謂至於不睹不聞時用工夫尋
常只恁悠悠過故章句謂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
不敢忽玩常字雖字亦字可見葢戒懼慎獨兩事
包括定心之動靜故凡非有所主之思慮及接物
時皆在戒懼界限裡如此看然後與不可須臾離
一句意脈相接續
經中於不睹上用戒慎字不聞上用恐懼字雖是分
說其實合說葢不睹不聞只是無聲色無可見聞
處非有兩端故章句總用敬畏字以敬字體戒慎
畏字體恐懼下又總言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只是
兼舉互見今且先當分戒懼與慎獨兩項界限葢
慎獨是就裡面說出戒懼是就外面說入但起念
頭處便是慎獨境界無所思而有所睹聞自外來
者皆屬戒懼境界獨是心欲應事見聞是事來動
心界限亦甚分曉不睹不聞是就極處說章句
常存字雖字亦字皆是補貼起此意葢心意不動
之時自有睹聞至於無所睹聞皆當敬畏然至於
不睹不聞之地則敬畏之工夫尤難但用意則屬
已發矣愚嘗妄爲之說曰當此之時此心當無物
而有主然又要看得真會得活若著個物字主字
而欲無之有之則又大不可矣以此體於心而實防
之久當自見言愈多則愈爲病矣
或問戒慎恐懼工夫如此與不思善惡及致虛靜篤
之說何以異曰氷炭不相入也彼學專務於靜吾
道動靜不違彼以靜定爲功惟恐物來動心故一
切截斷然後有覺聖人之學事來即應事去則靜
應事時既無不敬至無所睹聞時亦敬以存之自
然虛靜惟虛靜故愈靈明而發以應事無不當雖
無睹聞若有當思固思之無害但所思者正爾非
以靜爲功而置心如牆壁也
諸書不曾言戒懼工夫惟中庸言之葢子思自性上
說來學者欲體道以全性若無此工夫則心未發
時可在道之外邪
天者理之所出心者理之所存心知即理動理動即天知故有萌於心則著見明顯莫大乎此豈必待
人知之乎
中庸慎獨兼大學兩慎獨意大學慎獨是誠意地頭
故先專主於心而後乃兼於身中庸前既言戒懼
工夫故慎獨兼外說章句謂隱是暗處又曰幽暗
之中此兼內外言之細事非是小事是事之未著
者二者皆是人所未見聞者亦即是毋自欺之意
致中和是戒懼慎獨推行積累至乎極處則有天地
位萬物育效驗
致中是逼向裡極底致和是推向外盡頭
位育以有位者言之固易曉若以無位者言之則
一身一家皆各有天地萬物以一身言若心正氣順
則自然睟面盎背動容周旋中禮是位育也以一
家言以孝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孫順以弟友
接而兄弟和以敬處而夫婦正以寛禦而奴僕盡
其職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位育也但不如有
位者所感大而全爾
此章首言性道教之義次又言性情之則而兩節工
夫止是戒懼慎獨兩端致則極乎此二者也致中
是戒懼而守其未之大本所以養天命之性致
和是慎獨而精其中節之達道所以全率性之道
前後只是性道兩句工夫而教在其中其用功處
只有戒慎恐懼慎致六字而已
此書以中庸名篇而第一章乃無中庸字未發之中
非中庸之謂也葢率性之謂道一句即中庸也此
句總言人物是說自然能如此者在人則惟聖人
能之是中庸也若眾人則教之使率其性期至於
中庸也
章句天以隂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
焉葢人物之生雖皆出於天理而氣有通塞之不
同則隨所遇有生人物之異氣通者爲人而得人
之理氣塞者爲物亦得物之理雖曰有理然後有
氣然生物之時其氣至而後理有所寓氣是載理
之具也故章句先言氣以成形後言理亦賦焉
天生人物是氣也而理即在其中理主乎氣氣載乎
理二者未嘗可離故本文天命之性雖專言理而
章句必須兼氣說若不言氣以成形一句則理著
在何處安有所謂人物葢言氣則有善有惡言理
則全善無惡故子思專舉理以曉人謂此理具於
心者謂之性即道心也率者循此而已修者品節
此而已學者學此而已自可欲之善進而至於大
而化之全此而已章句雲天以隂陽五行化生萬
物是總說卻分言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兩句下猶
命令也一句獨接理亦賦焉說於是人物之生以
下卻是專說理以釋性字葢若不兼氣來說則教
字說不去既全是理則人無不善又何須教
動靜開闢徃來屈伸只是兩端而已故古之聖人定
隂陽之名然消必不能遽長暑必不能遽寒皆有
其漸故又定五行之名五行之名既立則見得造
化或相生以迴圈或相制以成物錯綜交互其用
無窮矣然而隂陽生五行而五行又各具隂陽亦
不可指其先後也
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爲健順五常之德葢健
是陽之德順是隂之德五常是五行之德七者亦
皆因氣而有此德人物雖皆有只是人全具而物
得其偏如馬健而不順牛順而不健虎狼父子有
仁蜂蟻君臣有義而無他德之類
健者陽之德順者隂之德五常者五行之德然此健
順不是言幹健坤順就造化上說此是就人物上
言其性自具此七者
性中只有五常而此加健順是本上文隂陽而言也
五常固已具健順之理分而言之仁禮爲陽爲健
義智爲隂爲順信則沖和而兼健順也錯而言之
則五常各有健順義斷智明非健乎仁不忍而用
主於愛禮分定而節不可逾非順乎
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謂順理之自然者行之即是
道率字不是工夫只是順說葢中庸首三句且只
說性道教三者之名義及聖人品節爲教之後下
面方說學者工夫
品節是品量節約
氣稟或異應上氣以成形說此其所以聖人立教也
人物所當行者固人物各率性之道然唯聖人能盡
己之性而盡人物之性故可品節之以己之所能
者使人能之以物之所當然者使人用之
人之所以爲人一句代天命之謂性一句葢言性則
人物之所共者此段言人只就人性上說中庸是
教人全性之書故也人全其性亦只是盡爲人之
道而已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章句前面皆言理言性到此乃
言體字葢理性無形恐難體認此則就實處言之
包下心氣二字父母之于子同體而分形天地乃
吾之大父母吾之身本大父母之遺體惟其一
體也故吾心可感天地之心吾氣可感天地之氣
而其效驗如此但致和主於行事中節而言不但
在我身之氣順萬物便能育也與上心正即能感
天心之意頗不盡同此言當細體認葢萬物育不
專在黙然感應須要所以處物之道施於政事者
得其宜則是事雖在外乃我在內之氣得以達之
須著如此一轉看
兩個一體字意不同
二章
語録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
之意同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
時而不中即正未必中此說極好比並體認
小人反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平時既有小人之心而
臨事爲惡又無所忌憚縱意而行反字是用力字
謂他故意反中庸之道行之葢此小人非但是愚
者而已
章句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隨時而在此隨時字含
兩意謂君子毎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
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
之如此爲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爲中是一事各于
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
章句二又字是眼目
章句上既言隨時處中矣下卻言戒謹恐懼而無時
不中時中當是慎獨事而言如此事有可疑今詳
朱子意葢言本文但言君子中庸未見有專指用
處且安有無體之用故複如前解題而全舉曰
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是則所謂君子
中庸者體用兼全動靜一貫者也故下文先言以
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以德字貼襯在
君子字上其下卻雲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戒懼
是言平日存中之體應上德字而無時不中則發
處皆中庸矣君子而時中時字當用力看便見意
中庸一篇凡七章有中庸字余六章皆與此不同
故于此章全解次章則曰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
是從用上說以三章爲例則後章從可知八章又
曰行之無過不及二十七章曰不使過不及可見
與此君子中庸一語不可同論
三章
論語言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章上
無德字下有能字此能字即所謂德也但論語言
中庸之德此章言中庸之道
四章
道不行不明非是人不行之不明之是言道自不行
于天下不明于天下謂大道窒而晦也
知賢者之過當作兩層意看大率道者極乎中而已
兩道字便是中所謂過者過乎中也稟氣清而淳
者則爲聖人知之至行之及自合乎中稟偏於清
者則爲知知者惟務於知既不以行爲事則所知
愈至高逺而過中矣稟偏於淳者則爲賢賢者惟
篤於行既不求知其至則所行必至激切而過中
矣此止就正理上看若知者如老釋之空寂賢者
如沮溺之道逺又如下索隱行怪之類是又非正
道而過於中者須作兩意看方盡得知賢過中之
義愚不肖之不及只是一般
道不行者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者行之過與不及
是固然矣然下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
味也是又總於知葢二者皆欠真知爾若真知理
義之極至則賢者固無過知者亦必篤於行不徒
知之而已矣
不足知不足行正言知賢者之心葢是他心惟通這
一路更不管那一路
五章
前章主于知此章主於行葢知然後能行既知之又
須能行故此二章明次第如此
金先生曰第二章以來小人反中庸民鮮中庸之久
賢智過中庸愚不肖不及中庸總歎曰道其不行
矣夫故自六章以後開示擇道中庸之方在知仁
勇三達德
六章
好問是有疑而問於下如臣如民下至芻蕘無不詢
之察邇言是於所問而對者及下人之言凡達於
上者雖淺近必詳察其理古者民俗歌謠必采之
以觀民風亦察邇言之類
舜固聰明睿知而不自用故好問察邇擇善而用其
中此所以愈成知之大聖德固是如此然或有見
聞所不及必須問而知者民事幽隱因芻蕘之言
而聞者則亦善用中故必兼此兩意看
執兩端而用中謂眾人所言於此一事雖同於善然
卻有處之厚薄不同卻將已之權度在心者度而
取其中或在厚或在薄必合於此事之宜者而行之
章句廣大謂隱惡而不宣光明謂揚善而不匿不言惡
者掩覆涵容足見其量之廣大言善者播告發揚
足見其心之光明
權度精切舜本然之知也又好問察邇欲周天下之
細故也此其所以爲知之大也與
七章
其義在於不能期月守中庸以起下章之能守意不
在罟擭陷穽以不知意承上章之知
以不能守中庸起下章之能
守
八章
擇字兼知行惟知之明乃能擇既擇即見之行事所
以下面即說守不再說行擇是當應事之時守是
事過之後常守在複遇此事又如此應皆合中庸
服膺是守也弗失又覆說守之固也
舜知是全體之知顔仁是毎事之仁凡已擇乎中庸
者固仁矣而應天下之事猶擇之未全也毎得一
善則服膺弗失守之者固日新其德則漸可全也
三月不違可見此意
人之於道不過知行兩事耳知者智也行者仁也四
章既言道之不行不明然所謂愚不肖者固易見
不足論惟智者知之過而不務行賢者行之過而
不求知所以至於中庸者鮮賢者之過如栁下惠
之和伯夷之清未及孔子之時智者之過如曾晳
之言高而行不掩者近之矣故六章言舜之智而
謂隱惡揚善執兩端用中是行之意重此舜不
專于智而道行矣八章言顔子之仁而曰擇
乎中庸是知之意重此顔子不專於行而道所以
明矣
九章
七章能擇中庸而不能守是知其理而未行至此章
能爲三者而不能中庸是能行所難而知未至者
故此二章處於知仁之後而下接言勇之前葢謂
知仁皆當勇也
七八九章皆言中庸而意不同上兩擇乎中庸毎事
上言中庸不可能全體上言
義精是知之極仁熟是行之裕是就應此事之前說
無一毫之私是就應此事時說件件如此則全乎
中庸矣
十章
子思引夫子告子路當強之目以合舜知顔淵仁爲
三達德之事非子路之所已能者
子路好勇是子路生質本剛事皆勇爲至此葢亦未
知勇之所當務者故以爲問
南方之強雖君子之強然亦未是中庸是不及於強者
北方是過於強者君子則爲後四者之強上君子
字輕下君子字重
君子之道中而止南方之強不及中北方之強過於
中固皆未至然上言君子居之則比強者居之者
爲勝之矣不及者勉強至中頗易過者矯揉至中
尤難兩君子字雖不同然言君子四強哉終是接
著君子說
南陽方北隂方陽舒散而隂収斂舒散便和柔収斂
便剛勁此葢大約言風氣之偏則風俗隨異其實
南人豈盡柔弱亦有剛勁者北人豈盡剛勁亦有
柔弱者然寛柔以教不報無道是言柔之甚而善
者衽金革死而不厭是言剛之甚而過者
章內兩而強不同前是汝之所當強者後而字是承
上句虛字說君子亦不同君子居之輕如善人長
者之類故君子重是全德之人
四強哉矯上兩節言守身應事之常下兩節言出處至
極之變下兩節雖尤難然上兩節常貫在其中國
有道必出而仕人于未達其所守者正而堅既達
之後接物廣應變多或有易其守者國無道固不
可出能守之至死畧不易其志如夷齊餓死而無
怨者方是強之至君子或出或處必當合於中庸
者如此
四強哉矯雖是勇而合中庸之體段而不流不倚
不變正是立則防弊以教學者處
有道無道只言國之治亂有道乃可仕之時無道無
可出之理君子之出也固當合乎中庸然此卻只
言出以後事葢君子平日自修須有能守之節上
之人亦爲其有所守故用之及既仕則必堅守平
昔所守者可也今乃不能守其前志不爲富貴所
淫則爲事物所汨爾爲所汨者知未盡爲所淫者
仁未至皆是不能勇以全夫知仁者也故以不變
塞爲強若國無道不變平生所守是窮而在下當
不可仕之時雖困悴窮蹙不能全其生亦必死而
安於天耳推而言之雖已仕國者適逢國變而無道
則必屹立不移以身徇國若此豈非至強者歟
章句含容形容寛之量防順體仿柔之容皆不可以
爲正訓
資質既寛柔其心必愛人所以能誨人之不及若無
道之來直受之不思報之者亦以能含容防順故
也上兩字以質言下兩字以接人言祍金革死而
不厭卻只是一意
言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善斡旋說
中庸之道知固在前然行之及方是曰非有以自勝其
人欲之私仍舊是說仁重
十一章
索隱是求人之所不必知行怪是行人之所不必行
索隱知者之過行怪賢者之過此不能擇乎中庸者
聖人不爲也或有雖不索隱行怪而能擇乎中庸然
行之止于半塗而不力以求至是不能守者聖人
自不能止必行至於終也是以君子常不違乎中
庸則不爲隱怪可知由仁義行雖終身不見知於
世亦未嘗有所悔艾不半塗而廢也豈非聖人之
事乎孔子前說有兩吾字以身任之故下文謙不
肯當但曰惟聖者能之其實依乎中庸即夫子之
弗爲者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即夫子之弗能已者雖
欲避聖人之名自有不可得者
上兩節各有吾字第三節乃言聖者能之雖聖人不
肯自居然曰聖者能之正是爲學者標的
前章言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又言遁世不見知而不
悔惟聖者能之正見得君子能處困悴厄窮而裕
如者爲尤難故子思連引聖言以爲戒此亦章中
一意
第一節索隱行怪皆是知之不明是不知也第二節
行而不能守是未仁也第三節知仁俱至故章句
謂一是不當強而強二是當強而不強三是不賴
勇而裕如者
章句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總結三節弗爲
索隱行怪知也依乎中庸則知之盡也弗能半塗
而廢仁也遁世不見知而不悔仁之至也皆出於自
然則不賴勇也
十二章
費者用之廣當作芳味反若符味反者則性也章句
此音當改
夫婦知能造端夫婦
君子之道費君子之道
鳶飛魚躍察乎天地
兩君子之道無異前後夫婦前後天地字皆不同夫
婦知能只是衣食起居日用之常皆道之費造端
夫婦是言夫婦暗室幽防之處亦道之費天地有
憾是言天地之偏反形容道之全察乎天地是指
天地之大正發明道之廣葢此章以君子之道費
而隱一語發端夫婦聖人于人上見道之費鳶飛
魚躍於物上見道之費下又再提起道字而言造
端是就夫婦知能處舉其至隱防者明道之至近
又言天地是就鳶之上魚之下推極以明道之至
逺此章不言工夫只是言費造端只如爲始兩字
不可作工夫看
聖人不能知行非就一事上說是就萬事上說如孔
子不如農圃及百工技藝瑣細之事聖人豈盡知
盡能若君子之所當務者則聖人必知得徹行得
極
大小二字接道而言天地之大人猶有憾者爲功不
能全也君子之語大小而莫能載破者爲道無不
在也天地對大小猶有憾對莫能載破金先生曰
物有限量則可載道無限量故莫能載物有罅隙
則可破道無罅隙故莫能破
鳶飛魚躍大概言上天下地道無不在偶借詩兩語
以明之其義不專在於鳶魚也觀此則囿於兩間
者飛潛動植何所徃而非道之著且蒼然在上塊
焉在下者又庸非道之著乎則人於日用之間雖
欲離道有不可得者其可造次顛沛之頃不用功
於此哉
此章專明道充滿天地萬物之間使學者體認欲其
灼然如見皆不言工夫然既知吾身之小以極
天地之大萬物之防無非是道則於道不可離當
體之而不可少有間斷明矣
中庸三大章前章言中庸此章言費隱後章言誠中
庸者道之用於萬物無所不在其體固隱是亦費
而隱也但中庸是就人事上言道之用費是就
天地人物上言道之用葢先言中和見道之統攝
于人心次言中庸見道之著見於事物此言費隱
見道之充塞天地後言誠則見聖人與天地爲一
中和以戒懼慎獨爲存養省察之功中庸則以知
仁勇爲入德之門費隱則于諸章雜言其大者小
者欲人隨處致察以全中庸之用皆所以求至於
誠也
章句近自逺而四字中庸包盡事物無窮此是解
及其至三字是就始終兩端說
體之防指理性言舉全體指道之全體言二體字不
同
家语观周篇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耼博古知
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徃矣
敬叔与俱至周问礼于老耼学乐于苌厯郊社
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
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史记孔子世家
亦载其事老耼爲周柱下史明习典礼故徃问之
春秋左氏传昭十七年郯子来朝昭子问曰少皥氏
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我高祖少皥挚之立也鳯
鸟适至故纪于鸟爲鸟师而鸟名鳯鸟氏厯正也
元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
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
马也鸤鸠氏司空也鷞鸠氏司冦也鹘鸠氏司事
也五雉爲五工正九扈爲九农正仲尼闻之见于
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天子失官学在
四夷犹信
聖人不能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是兩様意思孔
子不得位是在天而非己所能堯舜病博施是其
勢而非力所能二者皆是舉大綱說其實細事末
節不出道之用自有聖人不必能者
憾只是不足意覆載生成分言天地各有所主固不
可全寒暑災祥合言天地氣數之變有不能已者
化育流行上下昭著此雖言鳶魚而非獨言鳶魚也
正謂道於天地萬物無不在爾
活潑潑地此是程子形容子思用鳶魚兩語使人知
化育流行如此活潑潑地學者須真見得天地萬
物皆如此流動充滿活潑潑地畧無滯礙之意方可
十三章
人之爲道而逺人此爲字重猶言行道不可以爲道
此爲字輕猶言謂之道
睨邪視視所執之柯也視正視視所伐之柯也詩言
伐柯者取則不逺子思謂柯有彼此之異尚猶是
逺道在人身而不可離又非柯之比故教者只消
就眾人自身所有之道而治之爾行道者不假外
求治人者無可外加
第三節言行道之方惟在忠恕自此行之則可至中
庸之道故曰違道不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
人推己之恕也然非忠爲本則亦無可推者矣葢
忠以心之全體言恕就毎事上言所接之事萬有
不同皆自此心而推然應一事時盡己之心推之
則心之全體卻又只在此故恕非忠無以本忠非
恕不能行二者相須缺一不可所以經以施諸己
兩句總言忠恕而章句亦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
施於人忠恕之事也
施諸己不願亦勿施於人上就事不善一邊說反而
言之己之所願者則必使人亦得之亦當如此推
事父事君事兄上三以字訓用字意甚重非語助也
葢求責於人者乃道之當然而已行之乃未至此
故欲用以事父君兄先施之際以責人者責之於
己使必合乎道之當然則事父也孝事君也忠事
兄也弟施之朋友也信我之所行亦若責之於人
者矣此節專言自修以下句爲重亦恕之道也
人倫有五夫婦之倫不可自反故不舉下文著庸德
庸言兩項關定謂盡人倫不過在庸德庸言之間
行與謹字對德毎不足故當勉於行言毎有餘故
當謹而不敢盡
庸德庸言謂如上四事所以責己欲盡其道者亦不
過常道爾但行之難故毎不足則當勉而至言之
易故毎有餘不可恣其出若是則言行相顧豈非
篤實之君子乎此雖接上四未能而言推而廣之
於凡天下之事皆當如此也
第一節言修己第二節言治人第三節修己治人之
方第四節即是恕葢恕是推己上不願勿施是從
裡面推出下以事未能卻就外面反推入然推而
知其未能則於及人必欲其能是又就裡面推出
也
章句眾人望人此眾人只是天下人所同行所可至
公共的道理又以等級言則與聖人相對說正是
體貼改而止之意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於桐丘鄭
請救于齊齊師救鄭及留舒違糓七裡糓人不知
章下謂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凡此只就本章摘
出說費字非是孔子真不能於此與十二章聖人
有所不能意自不同讀者不可一律看
十四章
輯畧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于民素富
貴行乎富貴者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修身
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言忠信行篤敬雖
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
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
患難者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
反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富我以
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此在下位
所以不援上也遊氏曰上不陵下下不援上惟正
己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君子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
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
也故窮通皆醜學者當篤信而已失諸正鵠亦行
有不得之說也此二家說此章極明
君子道中庸不過因其所居之位行其所當然無思
出乎其位而外慕也素位而行是正說不願乎外
是反說才願乎外即是不能素位而行下面卻自
作兩節分說去呂氏之說已詳葢居富貴自有富
貴所當行之道不能行所當行者固不可而位有
高下任有大小又當隨所宜而行若有不中其節
者皆非也居貧賤亦有所當行之道安分樂天不
厭不懾常守不變若有不甘爲之意皆非也凡人
非富貴則貧賤此是人之大分至於夷狄患難又
是上兩等人或有遇之之時亦各於其中行所當
行此所以君子無所徃而不自得自得是從容無
急迫滯礙而自快足之意此說素位而行也次兩
句不陵不援再言不願乎外陵下援上皆願外也
呂氏遊氏之說已明又如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
祀仙人豚肩不掩豆難爲下也管敬仲鏤簋朱紘
山節藻棁難爲上也亦陵下援上之意皆非中庸
也正己不求於人結上二句無怨亦說己無怨既
是正己不求於人則凡事惟恐不自盡亦奚暇見
人之不足於我而怨之哉故己有所蘊固有當得
於外者天不畀而無不平於天人不從而不歸罪
於人所以君子居易以俟命此句又是戒君子當
如此小人行險以儌幸反此一句說以射爲比又
引夫子之言證正己不求人之意
正鵠見論語射不主皮章
十五章
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細防處不
合道而於逺大之事能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
勢必當如此故于費隱之後十三章先言修己治
人必恕以行之而謹其庸德庸言次十四章則言
正己不求于人此章則言自近及逺是言凡行道
皆當如是也引詩本是比喻說然於道中言治家
則次序又如此
夫婦人倫之首故先言夫婦之道常人處夫婦之間
多褻狎不則又太嚴厲二者皆不可也是以古人
貴相敬如賓者處夫婦之道和而正則善矣爲琴
瑟之聲和而正故以爲比此章首言夫婦兄弟次
之家人又次之自內以及外即大學三引詩之意
人能處其家使正而和如此則其能孝而父母之心
安樂可知矣
章句人能和妻子宜兄弟則父母安樂之和妻子結
詩上二句宜兄弟結中二句便言父母順則詩下
二句皆言效驗也
十六章
十五章自費隱章造端夫婦語意來此章察乎天地
意也
齋明二字只就心上說盛服乃說身齊是用功屏其
思慮之不齊者而一於所祭之鬼神明是既齊而
心之體明潔不雜可交於鬼神也
凡祭有三曰天神地只人鬼總言之亦通謂之鬼神
大率天之神皆陽類也其中亦有陽中之隂如月
如五星之金水如雨師之類然終是麗於天者地
之示皆隂類也亦有隂中之陽山林與川澤對則
山林陽也原與隰對則原陽也然終是麗於地者
惟祭人鬼則求魂於天求魄於地是合隂陽而祭
之鬼雖是隂其中卻是合隂陽來格
如在上如在左右不是或在上或在左右是言在上
又在左右也擗塞滿都是鬼神此是于祭祀時見體
物不可遺處所以章句言乃其體物不可遺之驗
此是就祭祀人所易知之鬼神上指出使人知夫
鬼神之德如此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謂神之來格也既不
可測度是有祭則鬼神必臨之矣其可厭怠而不
敬乎
防者隱不可見聞也顯者理之昭著也此是誠之不
可掩覆者也
第二節言鬼神之大者三節主祭祀而言鬼神之小
者四節與三節同五節又總贊鬼神之德誠即鬼
神之德也
章句天地之功用天主神而言地主鬼而言此以天
地間二氣徃來大體言之是橫說鬼神造化之跡
造是造就萬物以神而言化是物既成氣盡時至
而消化去以鬼而言是防說鬼神所以造化萬物
者其理之妙不可見至於鬼神徃來始可見爾故
曰造化之跡
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跡功如功業是能如此者用如
用事是見如此施爲者天地無非生成萬物其功
用于生成處見此是合說鬼神造化乃天地隂陽
之妙用亦是造化萬物也其所以然者不可見其
可見者則於物之成敗生死上顯故曰跡此是開
說鬼神天地之功用是隂陽相合者總言鬼神也
造化之跡是兩頭說鬼神是見他如此成又見他
如此敗其蹤跡皆有實是見如此者見賢遍反
天地言其形造化言其理造化之理妙不可見惟見
其成敗之跡耳
二氣之良能謂二氣自然之善道能如此屈伸消息
者良能二字精妙
鬼神者隂陽之靈靈字易見靈字便包含著祭祀之
鬼神
二氣是開說前節是陽後節是隂如春夏是陽秋冬
是隂如有二物相磨蕩一進一退一氣是合說共
是一個氣來則全來便是陽去則全去便是隂鬼
神於二者之間皆可見都只是這氣在人體驗故
曰實一物而已
視弗見聴弗聞性也體物不可遺情也使人承祭祀
者功效也
前以天地造化二氣一氣言鬼神是言鬼神之全是
大底鬼神後所謂承祭祀者如天神地只人鬼及
諸小祀亦皆鬼神卻是從全體中指出祭祀者是
小底鬼神使人因此識其大者
物之終始莫非隂陽合散之所爲隂與陽合爲物之
始隂與陽散爲物之終上言氣至而伸爲陽爲神
氣反而歸爲隂爲鬼是就兩頭說此又言隂陽二
氣合而生離而死是就中間混同處說隂陽鬼神
無徃不在只要人看得活
隂陽合散又是隂與陽之氣二者相合生物爲物之
始及其久也此物中之陽氣上升隂氣下降其物
即死爲物之終是就一物中說隂陽
體物者爲物之體也幹事者爲事之質幹也此倒用
之則體字幹字俱是用字
禮記祭統曰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也君子
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聴樂心不苟慮
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君子之齊也專
致其精明之德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此齊明之說也
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
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
也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隂
爲野土隂讀與防同其氣發楊於上爲昭明焄蒿悽
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注焄謂香臭蒿謂氣
蒸出貌朱子謂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
蒿是其氣升騰悽愴是使人慘栗感傷之意因說
修養人死時氣衝突知得焄蒿之意親切謂氣襲
人知得悽愴之意分明此百物之精爽也何文定
曰此是隂陽乍離之際有此聲臭氣此是祭義所言
正意若中庸章句所引乃是借來形容祭祀來格
洋洋如在之氣象此是感召複伸之氣與祭義所
指自不同讀者詳之
十七章
自舜其大孝至子孫保之一節言舜之事實自故大
德至必得其壽一節泛言理之必然自故天之生
物至覆之一節言善惡之應所必至後引詩又證
有德之應如此故以大德者必受命結之
舜其大孝也與一句是綱德爲聖人下五句皆孝之
目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是孝也以身言之
也德爲聖人盡己性而盡人物之性是全其身豈
非孝之大者爲天子父尊之至矣以天下養養之
至矣宗廟饗子孫保雖就舜言之然欲子孫之安
富尊榮厯世之久皆父母之願人之情也今皆得
之則此五者豈非皆孝之大者
爲人子者以有德光顯祖父爲榮舜之德則至於聖
人爲天子則祭祀奉養之禮極其尊有四海則祭
祀奉養之具極其備宗廟饗之卻是就舜身上說
昔者舜傳禹禹既即位祀舜爲宗而又封商均于
虞舜封子均于商葢禹改封于虞後有虞思是也
虞亦立廟祀舜及其祖父至周武王又封舜後胡
公滿于陳則是子孫保之也舜之德至上使祖父
如此榮盛綿逺是所謂大孝
大德者必得祿位名壽乃理之常然獨孔子有德而
不得祿位與壽惟得聖人之名耳此乃氣數之變
金先生曰此所謂聖人所不能也然聖教無窮而
萬世享之子孫保之此又大德必得之驗也
栽培傾覆如春至草木有發生之意故天以雨露滋
長之秋冬草木有黃落之意天乃以霜雪雕零之
此以物言也以人言之有此德者天必以上四者
與之無其德者天必棄絶之如大舜以匹夫而有
天下桀紂以天子而喪其身此栽培傾覆之意
栽培傾覆言天之於物其理如此實以喻人栽傾屬
人培覆屬天栽傾是其材培覆乃篤也如此章大
舜之德是栽也得四者是培之也桀紂傾也喪亡
覆之也下引詩皆是因栽而培之章句氣至兩句
只是培覆之訓詁不是說盡此節之意
可嘉可樂之君子其令善之德顯顯昭著宜於人民
故受天之祿而爲天下之主既受天祿矣而天又
保之祐之複申重之其所以反覆眷顧之者如此
又重明上文大德必得四者之一節也
所引詩是節節說上受祿於天保祐命之自天申之
是三節意只是個感應
十八章
十八章十九章皆以周事繼大舜而言二十章又以
孔子繼周皆是聖人所行所言見道之費而無不
合於中庸者
無憂專就國家上說如文王羑裡之囚若可憂矣雖
聖人無入不自得然亦是一身事父作子述卻是
言國家事周家上世節節有憂患自夏君棄稷不
務不窋即失其官守逃之西戎至公劉方複遷豳
大王又爲狄人所侵遷岐雖肇基王跡而身遭憂
患矣王季雖勤王家辟國漸廣亦但守舊國而已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猶守諸侯之舊至武王
方受命爲王故惟文王用得無憂二字葢文王上
承己大之國己不勞力不逢變故以歸之子適當
商家天命未絶之時己得從容其間至承天命著
戎衣奄有四海乃是武王事文王都不費力
贊武王之言與贊舜意同但此言身不失天下之顯
名彼言德爲聖人防有輕重亦論韶武之意然此
顯名亦聖德也
末猶後也終也葢周自太王王季文王累世積德累
功國土已大最後至武王始受天命爲天下君周
公乃承之而追王先王如此說末字則與上下文
都相貫穿訓末爲老恐未安葢武王之齡古書不
一
追王三王武王既滅商在商郊已行之禮記大傳曰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於
社設奠於牧室牧野之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
駿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厯文王昌不以卑臨
尊也又書武成金縢康誥酒誥諸篇皆可見所謂
周公成文武之德只是又推太王王季之意而以
天子之禮祀先公也斯禮也以下又是因此以定
上下之通禮
章句實始翦商見論語泰伯至德章
先公祖紺以上通鑒前編曰堯封棄于邰世後稷以
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失其官自竄戎翟之間
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始遷于豳路史謂稷生漦□
漦□生叔均自後稷至公劉十餘世而漢劉敬傳
亦謂後稷十餘世至公劉按世本自公劉歴慶節
皇僕差弗毀隃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
公祖紺祖紺號太公史記作公叔柤類諸盩十有
二世而生古公亶父自稷至亶父葢二十余世矣
史記以不窋爲後稷子而又缺辟方侯牟雲都諸
盩四世遂謂後稷至文王爲十五世且契稷同時
受封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千餘
年而十五世其亦誤矣今按章句謂祖紺爲太王
之父據疏文而言也
輯畧曰期之喪有二正統之期爲祖父母者也有傍
親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眾子昆弟昆弟之子是
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
諸侯絶大夫降
十九章
前章言文武周公此章又言武王周公葢武王有天
下然後周公可以制禮二者皆繼志述事之大者
然章內皆是言禮葢主于周公而言謂制爲宗廟
祭器祭服薦獻之禮而於宗廟之中又制昭穆序
爵序事酬燕之禮又制爲郊社之禮然祭祀一事
中推至於極則郊天禘祖乃其至大者非聖人大
孝孰能如此此皆費之大
此章雖連言武王周公其實主周公而言周公合先
王累世典禮定爲周制中間損益合乎時中又可
垂之萬世其制大備矣此獨指祭祀一禮而言祭
中又只主於宗廟推及郊社爾此皆舉一端言之於宗廟中自有許多曲折可見道之費推至於吉禮之全其費可知又推至五禮備其費又可知也
舜之孝行於一家故只謂之大孝周制禮達乎天下
故曰達孝饒雙峯意亦如此
修廟只是拚掃整飾常使嚴潔之意譬如今人居室
整漏拂塵灑掃之類古注修埽糞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含兩義昭穆本是祫祭時太
廟設主而有此名宗廟之位由此而立祖宗既以
此爲序則子孫世世皆一昭一穆縁上世次序而
定此言序昭穆謂廟中行禮以及燕毛皆用昭穆
爲序則此序字主於人而言之意爲多昭穆又不
止廟中尋常尊卑亦皆以此爲序也
宗廟之禮一節五事禮義至爲周密序昭穆既明同
姓之尊卑序爵則合同姓異姓之貴賤葢皆指助
祭陪祭者而言至於序賢則分別羣臣之賢否廟
中奔走執事必擇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趨事之純
熟者謂之賢賢者既有事則不賢者亦自能勸雖然
既以有事爲榮則事不及之者豈不有恥則又有
序爵以安其心執事者既榮無事有爵而在列者
及賤而役於廟中者皆得與旅酬至此賢不賢皆
恩禮之所逮然此合同姓異姓而通言至祭禮已
畢屍既出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姓是親親之禮
又厚於疎逺者見制禮之意文理密察恩義周備
仁至義盡而文章燦然
天子諸侯之祭禮已亡雖間有表見於禮中者今不
可知其詳矣所存有特牲饋食禮諸侯上士之祭
禮也少牢饋食禮諸侯大夫之祭禮也大抵祭必
立屍必擇賓賓長一人眾賓無數眾賓者賓之黨也
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侄兄弟皆會小宗
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一族皆至兄弟者主人
之党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
面而立迎屍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
屍主兄弟各相獻酬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
奉尸賓者謂之獻賓酌以答主人者謂之酢主
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奉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謂
引導之飲也旅眾也主人舉觶酌酒自西階酬賓
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而未飲兄弟弟子
舉觶于長兄弟于阼階弟子者兄弟之後生者也
長兄弟者兄弟之最尊者也弟子導飲而長兄弟
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觶於阼階酬長兄弟長兄
弟西階前酬賓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
事者無不徧卒飲者實爵於篋此旅酬之大畧也
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亦先自飲
如前儀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觶酬兄弟之党長兄
弟取觶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謂之
無算爵所以逮賤者如此
天子祭禮亡不可考楚茨之詩曰神具醉止皇屍載
起鼓鐘送屍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
兄弟備言燕私箋雲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
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疏屍已出而諸
宰及君婦徹去俎豆歸賓客之俎其諸父兄弟留
之使皆備具我當與之燕而盡其私恩也
天子諸侯大夫皆立始祖廟大夫亦有始封者如三
桓之家即慶父叔牙季友爲始祖廟亦百世不遷
士則無始祖廟只是祭祖禰而已葢位卑者流澤
不能逺而士又無采邑故也
章句適士天子之上士即元士也受三命埰地五十
裡視子男二廟祭祖禰
官師凡有司之長葢中士下士也雖立一廟祭禰卻
於禰廟並祭祖
顾命言所陈之寳有赤刀大训璧琬琰大玉夷玉
天球河图允之舞衣大贝鼖鼓兊之戈和之弓垂
之竹矢章句曰之属则尽包上陈者在其中
山先生曰宗器于祭陈之示能守也于顾命陈
之示能传也书注疏赤刀寳刀赤刀削其刀必有
赤处削音笑刀之小者大训三皇五帝之书训诰
亦在焉文武之训亦曰大训宏璧大璧琬琰琬圭
琰圭也夷常也或以爲东夷之美玉天球雍州所
贡之玉磬也河图伏羲时龙马负图出于河允古
国名舞衣舞者之衣大贝如车渠车渠车罔也谓
贝之大如车之罔鼖鼓长八尺兊和古之巧人也垂
舜时共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
度故歴代传寳之
天官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
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注䟽用
禽獸謂煎和之以献王行與用同膳謂煎和也腒音渠乾雉鱐
音搜乾魚鱻與生同魚也羽鴈也膏
脂也香牛脂臊犬脂腥雞脂羶羊脂羔豚物生而
肥犢麛物成而充腒鱐暵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
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物之弗勝是
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之牛属司徒土也雞属宗
伯木也犬属司冦金也羊属司馬火也今按四時
食物不同而煎和之脂亦異於是見聖人制礼豈
惟宏綱大用法天体道至於一食之際莫不盡其
曲折其文理宻察如此四時之宜食脂膏之宜用
必自有深意注䟽之言未必得之
薦其時食章句引周礼一語而以之𩔖两字該之雖
是包下三語然如詩獻羔𥙊韭冬薦魚春獻鮪月
令孟夏以甞麥仲夏以雛甞羞以含桃孟秋
登榖甞新仲秋以犬甞麻季秋以大甞稲皆先薦
寢廟此𩔖皆是也
子姓者子之所生猶言子孫也
在外公侯伯子男在内卿大夫士皆爵也言公矦
則諸矦之駿奔走者也卿大夫則朝臣之執事者
也
宗謂大宗伯小宗伯掌祀事内宗也薦加豆籩外宗
之佐王后皆是也内宗王同姓女之有爵者外宗
王姑姊妹女之有爵者祝大祝小祝有司則如宫
正執燭天府沃盥陳寳器司几筵設筵几司尊彛
詔酌辨用鬯人供鬯人掌祼内宰賛祼獻司徒
奉牛牲羞肆司馬羞牲魚授𥙊内饔割亨司樂以
其属作樂膳夫徹俎司士賜爵之𩔖凡執事于廟
中者皆是肆託歴反亨普庚反𥙊畢而燕今不知其儀亦於楚茨之詩見其大意云
皇尸載起神保聿歸然後言諸父兄弟俻言燕私
下章曰樂具入奏者謂
𥙊時在廟燕當在寢故𥙊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所謂燕礼其可知之仿
佛若此
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甞秋享先
王以烝冬享先主
論語專爲禘發其精中庸汎言𥙊祀其詳恐非
記有詳略
讀中庸叢卷下
元許謙撰
二十章
金先生謂此章當作六節看章首至不可以不知天
爲一節逹道逹德至天下國家矣爲二節九經爲
三節凡事豫至不誠乎身爲四節言誠爲五節博
斈以下爲六節此章朱子以爲皆孔子之言金先
生謂聖人之言簡自仁者人也皆子思之言雜引
夫子之言反覆推明之
第一節文武之政全体大用雖無不㪯而其要在乎
得人擇人之道則在脩身脩身須是以仁仁道雖
大只是親親爲要
敏樹是樹藝之樹是活字
脩道以仁之仁是仁之全包四德者
仁者人也此是自古來第一箇訓字言混成而意深
宻深体味之則具人之形必須盡乎仁其所以盡
仁則不過盡人道而已朱子所謂天地生物之心
人得以生者元者善之長人具此生理自然有惻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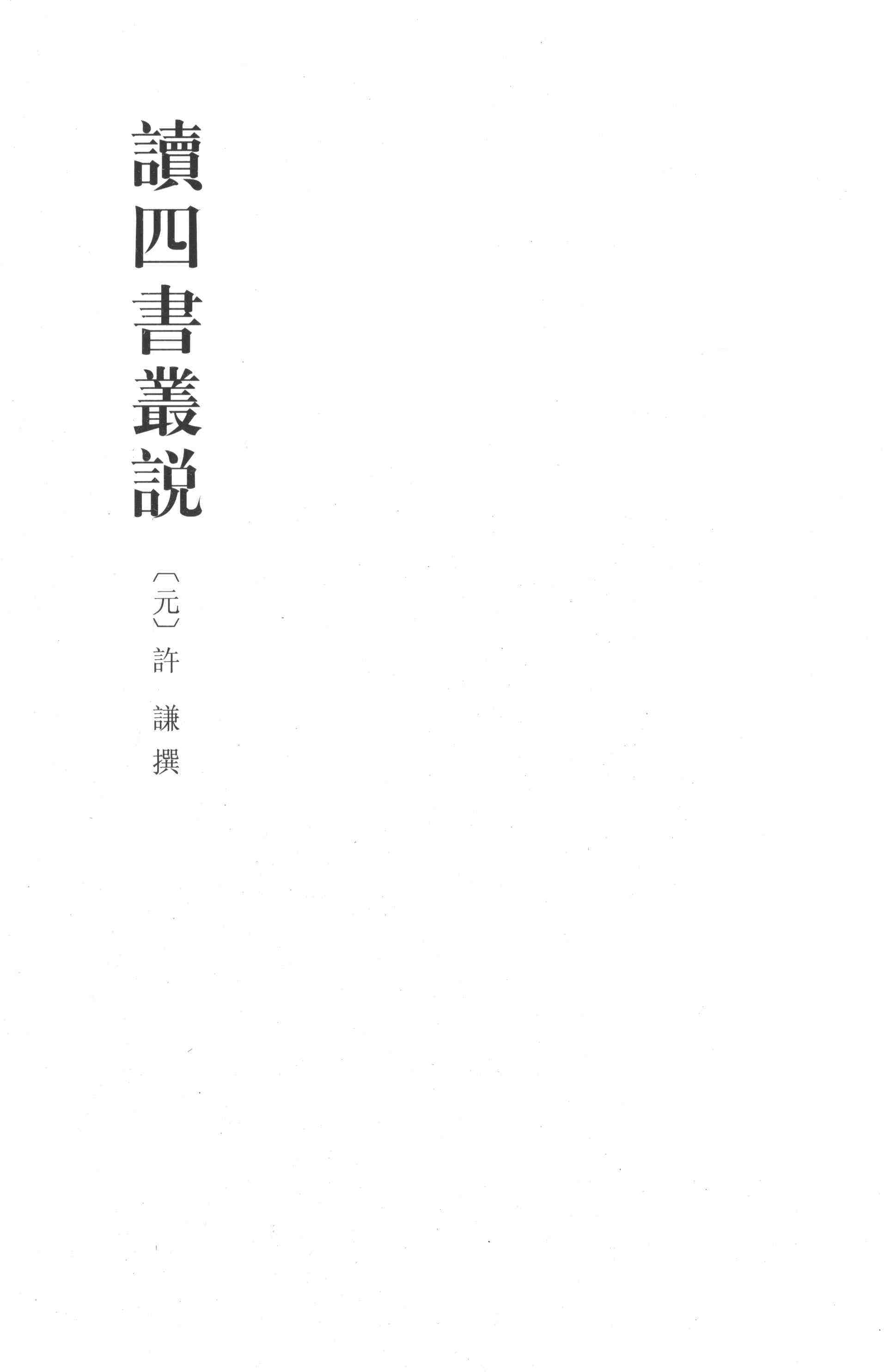
《读四书丛说八卷》
元许谦撰。谦有《诗集传名物钞》,已著录。案《元史》本传:“谦读《四书章句集注》,有《丛说》二十卷。谓学者曰:‘学以圣人为准的,然必得圣人之心而后可学圣人之事。圣贤之心具在《四书》,而《四书》之义备於朱子。顾辞约意广,读者安可易心求之乎?’”黄溍作谦《墓志》,亦称是书敦绎义理,惟务平实。所载卷数与本传相同。明钱溥《秘阁书目》尚有《四书丛说》四册。至朱彝尊《经义考》则但据《一斋书目》编入其名,而注云“未见”。盖久在若存若亡间矣。此本凡《大学》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阙其半,《论语》则已全阙,亦非完书。然约计所存,犹有十之五六。即益以所阙之帙,亦不能足原目二十卷之数,殆后来已有所合并欤?书中发挥义理,皆言简义该。或有难晓,则为图以明之,务使无所凝滞而后已。其於训诂名物,亦颇考证,有足补《章句》所未备。於朱子一家之学,可谓有所发明矣。
阅读
相关人物
許謙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