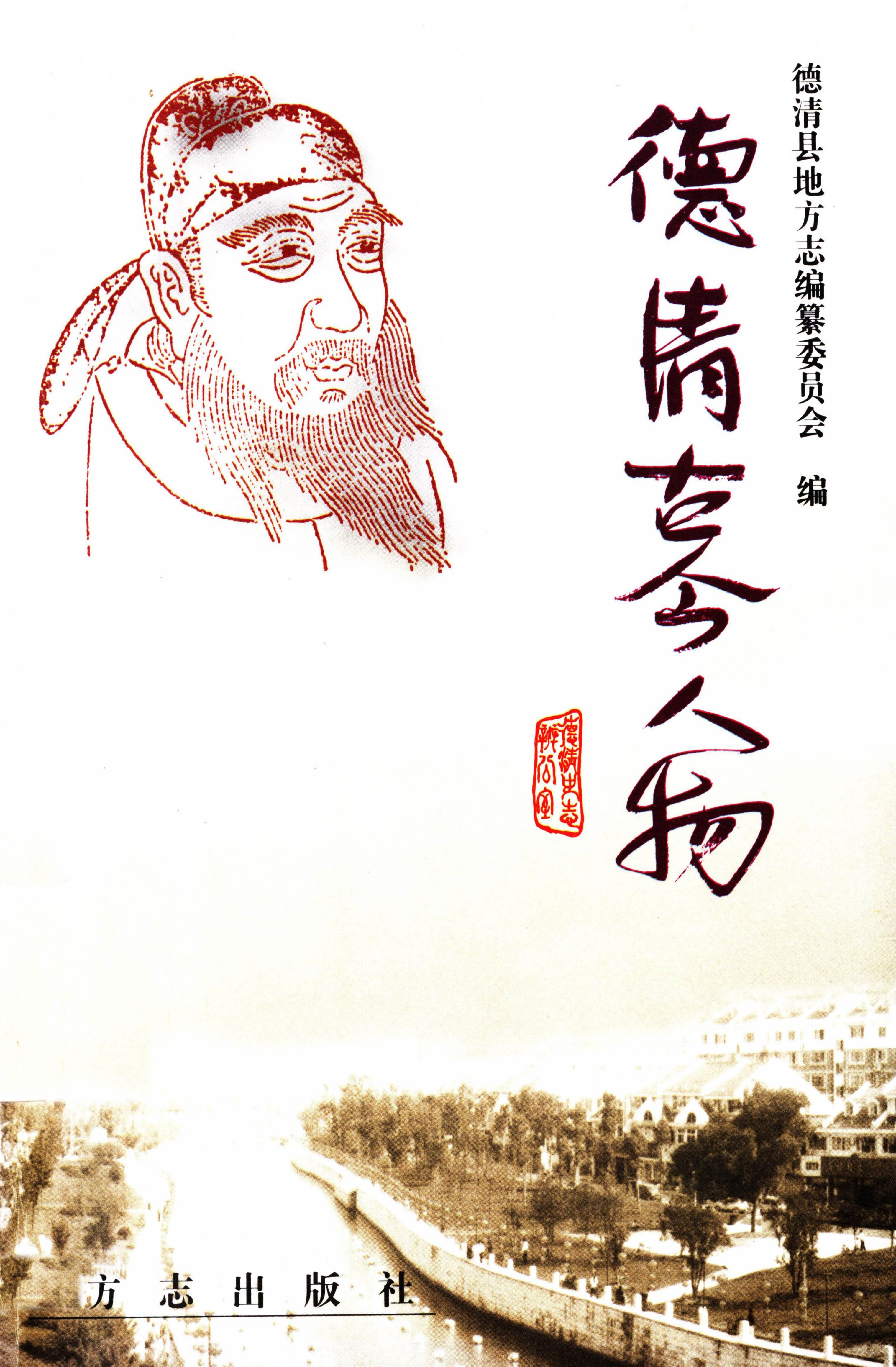内容
我记忆中的沈兹九大姐
冰心
1934年的春夏之交,我和老伴吴文藻在北京燕京大学执教,曾从进步的朋友那里,看到申报副刊《妇女园地》。我当时就感到它与当时一般的妇女刊物不同它是在号召妇女争取解放,宣传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等切中时弊的进步思想。读后我对这个刊物的主编沈兹九产生了无限的钦佩。她眼界之高,见识之广,不是一般普通妇女编辑所能企及的。可惜的是《妇女园地》刊行不久,即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逼迫停刊了。而接着出来的《妇女生活》也是沈兹九主编的,我更是高兴得不断地读着。1935年到1936之间,是我的老伴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教学期满七年的例假,我们到欧美旅游了一年,回到祖国几天后,“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1938年,文藻在敌后的云南大学执教,我和孩子为逃避空袭,住到云南郊外的呈贡。那时的国民党教育部次长顾毓诱是文藻在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从重庆到呈贡来看我们说“蒋夫人宋美龄对我说,‘我的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同学谢冰心,抗战后躲在云南,应该请她来妇女生活指导委员会做点文化教育工作。”我被她“躲”字激怒了,于1941年初就应邀到了重庆。其实,我和宋美龄并没有同过学。我是在1923年燕京大学毕业,得了学士学位,同时又得了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才到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去读硕士学位的。那时宋美龄已经读完本科四年而离开了。
我到重庆就任后,发现那“妇女生活指导委员会”原来是“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而文化教育组的工作,就是搞蒋介石发
起“新生活运动”的那一套!我的前任就是我所钦佩的沈兹九大姐。她就是认为文化教育组应该做些抗日救国工作,而同宋美龄进行多次斗争。宋美龄仍是固执己见,兹九大姐才愤而辞职的。这些话是在我就任后不久,同时还在指委会工作的史良和刘清扬悄悄告诉我的(那时她们为了统战工作,暂时留在会内)。我觉得我是落进了圈套!我立即写了辞呈,退还了工资,连夜搬到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上去。
我真正见到沈兹九同志,是在解放后“十年动乱”后期的北京。那时各民主党派正合组召开政治学习会。她是民主同盟会的会员,我是民主促进会的会员。我第一次和她握手相见,惊诧地发现她不是我想象中的高高大大、声如洪钟的女兵,而是一位身材瘦小,平易近人的知识妇女。她的发言总是十分透彻、精采,和我交谈时也是笑容满面而且很幽默,在我一生接触的朋友中,她是我最敬爱的女友之一。
我从1980年初伤腿后,行动不便,不能参加社会活动了。沈大姐大概身体也不好,我们几乎十年没有见面了。今年的1月初旬得到她逝世的讣告,我不禁潸然泪下。从此,我们在世上没有相见的机会了!安息吧,沈兹九大姐,您一生为党、为国、为人民特别是为妇女做了那么多那么重要的工作,您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您是不朽的!
1990年2月2日雪夜
(转载《女界文化战士沈兹九》)
悼念西苓
夏衍
在中国电影界人才寥落的时候,骤听到西苓的死讯,真是一件哀寂的事情,特别是战时需要新的干部来创造,而这有力的艺术武器还被支配在模仿横行,形式偏重的作风下面的现在。
中国有电影已经近三十年,而名符其实地可以说有了“中国电影”的那还是“九·一八”以后的事情。电影工作的重要,已被屡屡提出了,而“新”的文化人始终视这一领域的工作为畏途,戴白手套的“艺术家”望着这一被脏手捏着的武器摇头,对于企图从这脏手里面夺回这一武器的人们,暗中报之以轻蔑和恶意的冷笑。在旧人的排挤和新人的鄙视之下,极少数不怕龌龊和不相信这一领域真是龌龊到底的“文化人”突入了当时被叫做“黑暗圈”的电影场,在生活的泥泞中打滚,在恶意的荆棘中潜行,使中国电影能够在十年中追上了二十年来的落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的辛酸与苦战,在今天恐怕只有极少数当时亲身经历的人才能理解了,这极少数的中间,西苓是最初冲入这个圈子,而又是在这个圈子里遭受了最大限度的虐待与排挤的一个。
我认识西苓是在1923年,距今是十八年了,从他的京都美术学生时代,经过“艺术剧社”、“中华艺大”、“明星影片公司”,一直到抗战爆发前一瞬的“一贯”大公演,除出他在桂林的一个短时期之外,工作上有了不断的关联,因为相处日久,幸也许不幸,我知道了更多别人所不易知道的他的性癖和弱点。他在戏剧界的短短的十载生涯,是充满了斗争和矛盾的历史。在荆棘的道路上,他是一个
勇敢的斗士,但同时他更是一个彻底的弱者,为了达成一个目的,他可以忍受有洁癖的文化人所绝对不能忍受的羞辱,但是他可以毫无抵抗地接受足以使他整个计划陷于无法完成之让步。他常常苦笑,这苦笑表示他的顽强,但同时也正表示他懦弱。他酷爱卓别林,而本质上却是一个甘地主义的信徒。他的艺术是一种以柔胜刚,以弱胜强的使刚者强者看了自己觉得不好意思的苦笑,而他的人生哲学却是一种潜藏在不抵抗之深底的顽强的抵抗。
在泥泞中,他走了十年,也从这泥泞中,他生产了中国电影艺术上也许在一个短时期之内不会被人忘记的珠玉般的作品,从《上海二十四小时》、《船家女》到《十字街头》,这是一个飞跃,可是当他用不抵抗和妥协累积起来的“地位”好容易草奠基础的时候,命运的恶战便不容情地将他从世界上夺去了。
不单是为了友情,在戏剧电影界寥落的时候,一个真正酷爱电影的“熟练工”的逝去,总觉得是一件难以排遣使人哀寂的事情。
1942年
(转载《夏衍杂文随笔集》)
俞平伯幼受曲园老人的熏陶
郑逸梅
德清俞平伯,名铭衡,生于1900年,去年(1980年)八十寿辰。他学识渊博,著作等身,海内外人士,都为他遥举杯觞,以代华封三祝。
平伯乃曲园老人的曾孙,老人享耄耋之寿,故平伯幼年,犹日亲沐老人的教泽,可谓异数。当他四岁时,未上书房,由他母亲教读《大学》章句。有时,长姐教他读唐诗。每天晚上,由保姆抱到老人居室内,以循定省故例。某晚,他玩得很高兴,直至八点多种,该回屋去睡觉了,他还是赖着不肯走,经多方催促和哄骗,才勉强离去,临行却对保姆等念了一句:“送君还旧府”。这句原是他长姐教他的唐人诗,恰巧合着当时的情况。一时听到的都很惊喜,老人更掀髯大笑,连呼“可儿!”即忙告诉平伯的母亲。
平伯七、八岁时,老人命他每晚来做功课,他倚着方桌,老人坐着靠壁的大椅子,口授文字,以部首偏旁为序,如从木的为“松”、“柏”、“桃”、“李”等,从水的为“江”、“海”、“河”、“汉”等,命他一一写在用竹纸订成的本子上,较冷僻的字写不出来,老人写给他看,照样录下,每晚所写不多,时间也不长,但持之以恒,给他很大的进益。后来老人病了,才告辍止。他回忆有句云:“九秩衰翁灯影坐,口摹苫帖教重孙。”光绪丙午(1906年)中秋,老人于院中燃着斗香。这是吴中的俗尚,斗高数尺,可点整夜,斗的四周,遍插五色尖角的彩旗。他喜欢得很,因为看过京剧,武将背后插有旗帜,正想把斗中的彩旗拔下来,自己插在颈背间以壮威风,可是老人忽发吟
兴,要大家联句,命他先开头。这一下,他搔头摸耳,大感为难,逼着逼着,才逼出了七个字来“八月中秋点斗香”,老人认为尚可,第二句是平伯母亲的:“承欢儿女奉高堂”。第三句是平伯长姐的,已记不起来,老人结句:“添得灯光胜月光。”这事经过七十多年,成为旧话了。
曲园老人,人称他“拼命著书”,平伯传着衣钵,著书很多,如《冬夜》、《雪朝》、《西还》、《燕知草》、《杂拌儿》、《红楼梦研究》、《古槐梦遇》、《古槐书屋词》、《读词偶得》、《读诗札记》、《清真词释》等,嘉惠后学,贡献很大。
他于1917年(丁已年)十月和舅舅的女儿许定驯结婚。1977年,又复岁次丁已,梁孟偕老,整整六十花甲,平伯著《重圆花烛歌》,用古风叙述,某刊物上曾全篇登载。许夫人娴雅能曲,凡唱《西厢记》的,一般为《南西厢》,北曲传唱甚稀,而许夫人能唱北曲“哭宴”一折,由电台录音,然而录音被毁,前又重唱试录,以二胡伴奏,成绩很好。
他夫妇俩居北京数十年,而旧寓仍在苏州马医科巷,即春在堂故址,(编者按现已建成“俞樾先生故居”),可供四方人士游赏。
(原载《艺坛百影》)
(作者系原南社社长)
语可诲人光可鉴物
冯其庸
俞平老于去年十月逝世,噩耗传来,不胜痛悼,于时,我在天水,不能往吊。今年一月中,周颖南大兄自新加坡来,携来平老与他通信的复印稿,沉鼓鼓的两大包。他告诉我说,平老与他的通信已结集,很快出版,要我赶写一序。看样子已经事属紧近,无可推委,只得惶恐应命。
我与平老交往,已是平老的晚年,且因为平老年高,我也不敢多去打扰他,因而也就失去了不少请教的机会。此番面对着这么一大堆俞老的信件,又要我作序,我自然应该认真拜读。前前后后,我在这匆迫的时间里,一共读了三遍,我深深感到这对我是补上了十年学,或者说,弥补了我未能与平老多所请教的遗憾。
我国的文学传统,是十分重视书信的。在著名的《昭明文选》里,就收有书信三卷。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魏文帝《与吴质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等等,都收在文选里。至今流传下来的墨迹,则更是不可胜数,较早的有陆机的《平复帖》,王羲之的《丧乱帖》、《孔待中帖》等,还有转成石刻的《十七帖》,至于唐宋元明清各朝的名人尺牍,更是难计其数。
俞平老是当代著名的学者,著名的“红学家”,他与颖南大兄的通信,自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三日起①,到去年九月三日最后一封信,在这短短的十二年中,已经是积书盈尺了。这还仅仅是平老给颖南大兄一个人的信,推想过去他与其他人的通信,如他早年与顾颉刚的通信,及他在信中不时提到的他与叶圣陶老的通信,还有与
王伯祥、谢国桢诸老的通信,总之,他一辈子所作的书信,不知该有多少?可这是平老创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啊!如今在平老去世三个月后,颖南兄已经将此书信集编好付刊,这种精神实在令人感动。也可以稍慰平老于地下。平老的书信,是学问的渊薮,也是他生平的实录。他对往事的回忆,他对朋友的怀念,他对诗词的论评,他不经意间留下来的散文精品,以及他对“红学”的关切,还有作为书信文学,他在这方面留下的典范,特别是他一生襟怀磊落,豁达率真,对他的夫人则六十余年伉俪情深,一往如昔,这一切,都漾溢在他的书信里。我们只要随便翻读,就会感到这些书信语可诲人,光可鉴物。
平老是一位高寿的老人,整整活了将近一个世纪。又是一位早年成名的作家,他在二十岁以后就异军突起,步入文坛了。所以他的前尘梦影,稍一回忆乙,对后人来说,就成为历史实录。在这部书信集里,在在可以见到。例如一九七九年“五四”周甲纪念,他写《追忆往事诗》十章云:
一
星星之火可燎原,如睹江河发源始。
后此神州日日新,太学举幡辉青史。
二
风雨操场昔会逢②,登坛号召血书雄。
喧呼声彻闲门巷,惊耳谁家丈室中。③
三
马缨花发半城红④,振臂扬旌此日同。
一自权门撄众怒,赵家楼焰已腾空⑤。
四
罢课争将罢市连,新闻组好作宣传。
已教巨贾无青眼,又向当街散白钱⑥。
五
风生蘋末启舆谈,何用文心别苦甘。
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⑦。
六
阅人成世水成川,小驻京华六十年⑧。
及见天街民主化,重瞻魏阙峻于前。
七
清明时节家家雨⑨,五月花开分外鲜。
“四五”真堪随“五四”,波澜壮阔后居先。
八
“外抗强权”如反霸,“内除国贼”抵锄奸⑩。
昔年学子孤军起,今日工农大众欢。
九
北河沿浅柳毵毵。军幕森严忆“六三”■。
唤醒群伦增愤激,呼声遍应大江南■。
十
吾年二十态犹孩■,得遇千秋创局开。
耄及更教谈往事,竹枝渔鼓尽堪咳。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作于北京
以上十首追忆往事诗,历历叙这六十年前“五四”运动的前前后后,诸如学生大游行、北大预科风雨操场上的学生大会、火烧赵家楼、市民的大罢市、北大《新潮》期刊的诞生、一九一九年六月三日北洋政府军逮捕学生的“六三”事件等等,皆是当时的史实,可补史籍之失载。又如追怀顾颉刚先生的《思往日》五首附跋,记述他与顾老的交往和共研《石头记》的情况,不仅使我们可以得知两位大学者的深厚友谊,而且诗味醇厚深永,加以跋文稍稍阐发,令人把玩不已:
思往日
五首附跋
——追怀顾颉刚先生
其一
昔年共论《红楼梦》,南北鳞鸿互唱酬。
今日还教成故事,零星残墨荷甄留。
一九二一年与兄商谈《石头记》,后编入《红楼梦辨》中,乃吾二人之共同成绩。当时商札往还颇多,于今一字俱无。兄处独存其稿,闻《红楼梦学刊》将甄录之,亦鸿雪缘也。
其二
少同里闬未相识,信宿君家壬戍年。
正是江南樱笋好,明朝同泛在湖船。
一九二二年初夏,予将游美国,自杭往苏,访兄于悬桥巷寓,承留止宿,泛舟行春桥外。自十六岁离苏州,其后重来,匆匆逆旅,吴趋坊曲,挈伴同游,六十年中亦惟有此耳。
其三
悲守穷庐业已荒,悴梨新杭各经霜。
灯前有客跫然至,慰我萧寥情意长。
一九五四年甲午秋夕,承见访于北京齐化门故居。
呴沫情殷,论文往迹,不复道矣。
其四
朋簪三五尽吴音,合向耆英会上寻。
秘笈果然人快睹,征文考献遂初心。
六十年代初,兄每约吴门旧雨作真率之余,余浙籍也而生长苏州,亦得预焉。会时偶出珍翰异书相示。君夙藏《桐桥倚棹录》,盖孤本也,予为题绝句十八章。其十七云:“梓乡文献费搜
寻,夙稔君家雅意深。盼得流传人快读,岂惟声价重离林。”其后此书于一九八○年重印。
其五
毅心魄力迥气俦,长记闲谈一句留。
吧息比邻成隔世,而君著述已千秋。
兄尝以吴语语我夫妇云“吾弗是会做,吾是肯做。”生平坚毅宏远之怀,略见于斯。晚岁多病,常住医院。寓在三里河,与舍下毗邻。余去秋造访,于榻前把晤,面呈近刊词稿乞正,君呼小女读之,光景宛在目前,何期与故人遽尔长别哉!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三日,北京
一九七〇年,俞老下放到河南息县,于乡居生活,后来也颇多忆述,他在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给颖南兄的信中说新岁以来,体愈软弱,写作极少,兹抄奉一诗博粲,虽只廿八字,于昔下放河南居乡情况颇能概括,所居为农民弃屋,其敝陋不能想像,若遇大风雨雪皆有危险。经岁平安,感谢上苍,并非诗情,乃是实感,遂以白话写之,如是而已。
诗云:
出水银鳞不自怜,相依一往宛如前
旧茅未为秋风破,经岁平安全谢天
一九七○年在息县东岳集,借住农家废舍,东风夜卷茅栊,幸居停夜起维修,翌晨犹见残茅,飘浮塘上。遂忆杜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云云。方喜其适逢诗景,忧患余生,溺人必笑,初不觉处境之险也。
耐圃■后有《鹧鸪天》词云:
愁雨雪,变晴阴,农村广阔记犹新。友人相过居邻
好,汲井分柴助我勤。
于艰虞中见襟怀之开朗焉。而今人去三春,那更西窗剪烛,栖尘月梦,何幸天怜;促柱幺弦,终归辍响,昔日曾睹吾茅舍者,家中亦只韦柰、润民挈女华栋三人耳,设使他年重到,旧迹都迷,又不知其作何感想也。
我们读他给颖南兄的这封信,这首诗,诗后的附记,他夫人的《鹧鸪天》词,以及词后的短文,可以想见,这位七十老翁的乡居生活是何等艰难,而他和他夫人的襟怀又是何等的朗照!住在破茅屋里,突然遇上了大风雨,人也不堪其苦,可俞老却“方喜其适逢诗景”,俞夫人则说:“农村广阔记犹新”,这是何等的襟怀!
特别要提到的是俞老的《临江仙》纪事词,兹引录如下:
丙丁之际,有纪时事之《临江仙》,近稍流传而词或未安,改写于左:
周甲良辰虚废,一年容易秋冬。休夸时世若为容。新妆传卫里,裙样出唐宫。任尔追踪雉曌,终归啜泣途穷。能诛褒妲是英雄。生花南史笔,愧煞北门公。
己未正月
附注:
一、周甲两句谓婚姻六十年。
二、时世,犹言时妆。花间词“点翠匀红时世”。
三、天津于明代始设卫,曰天津卫。俗称卫里,今亦罕用。
四、雉,汉吕后名。曌,即照字,唐武后名,自造此字。
五、《诗经》:“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六、杜甫《北征》诗:“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谓杨妃。
七、南史氏,春秋时齐之太史,承上句借谓诗史。
八、北门学士,唐时谄事武后者。
平戏涂
很明显,这首词是鞭笞江青的,“丙丁之际”是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七年,词题就写明了“纪时事”,江青于一九七六年(丙辰)垮台,词语说:“新装传卫里”,“任尔追踪雉曌”,则毫无疑问是指江青。
我们统观以上所引的四组忆旧之作,从“五四”运动起,到他与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一九七○年他下放河南息县,一直到“丙丁之际”“四人帮”垮台,概括了多少重要史事。“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现在距离“四人帮”垮台,转瞬又已经首尾十六年了,俞老的这些追忆,也真正成为了史诗。
这里,我还要提到的是,在他与颖南兄的通信里,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商量《重圆花烛歌》的问题,他与叶圣陶老、谢国桢老也曾多次通信讨论此诗。此诗后来由颖南兄将俞老的手书和谢老的写本以及各家的题跋合印成册,以庆祝俞老九十华诞,我也曾为此卷写过跋文。从俞老晚年的诗作来说,这无疑是压卷之作,虽然是“重圆花烛歌”,但实际上也是一首史诗,全诗一百句,从一九一七年俞老与许氏表姊结婚起,一直写到一九七七年,中间六十年来的重大史事皆有概括。但恰恰省略了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俞老的这种省略,当然不是疏忽,也不是害怕,因为诉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灾难,一般来说,是毋庸害怕的,更没有什么“难言之隐”。俞老之所以不写这一段,是因为这是人所共知,人所共经的一场历史性的大灾难,现在灾难刚刚过去,余痛犹存,即使要说也说不完,倒不如不说也罢。所以我认为这一段“空白”,反而更使读者低徊思量,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我的这种体会,是否切合实际,现在平老已经不在,无从质证,只好姑妄言之而已。至于这首诗的艺术手法,我认为是融《秦妇吟》和“梅村体”于一炉,去其华瞻,增其质实。我的这种想法,是否能得其十一,也只能说是姑妄言之。
大家知道,俞平老不仅是学问大家,诗词名家,而且还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和闯将,他的新诗集《冬夜》、《西还》、《忆》,他的散文集《杂拌儿》、《燕知草》、《杂拌儿之二》等等,曾著名于世。这里摘录二通书信和二篇短文,以见俞平老散文的丰采。有人曾说,平老的散文是受《红楼梦》和《浮生六记》的影响,平老曾郑重说明,与其说他是受《红楼梦》和《浮生六记》的影响,毋宁说是受六朝四六骈文的影响来得符合实际,现在先引录平老的书信。颖南兄:
多日未通书问,以情怀甚劣,偃卧斗室,笔墨抛荒故也。
以内子之丧,承远致电音,旋奉手书吊唁,情意深厚,殁存均感!丧事至简,一日而毕。室内一切如旧,而伊人杳然。固知以理遣情,奈无处不枨触何。贱体幸粗安,堪纾远念。
前为兄题诗卷者,若北京张伯驹,上海李宝森皆作古人矣,不胜叹惋。若去岁佳游,诚可念也。
闻吴下曲园近有修复之说,云1985年可落成,自是佳讯,得见与否,未可定也。
言为心声,其辞多感,谅察为幸。
匆颂
俪祉,不具
平伯82.3.7
致荒芜■
示新诗,浣诵欣快。多历忧患,诗与年进,而一管狼毫,犹不减当年之勇,若弟者偶尔命笔,情多衰飒,弥觉不逮。近访圣翁(叶圣陶老人——引者)得一章,音旨尚和,即以候
教。以精神惝怳怳,涉笔易讹,奈何!
十一月十日
读以上两封信,虽然不能说是六朝四六骈文,但晋贤翰札和六朝文体的影响,依然可以寻绎。所以平老自述,信是实话。现在再摘录短文如下:
读“送春诗”书后■
余近句云:“儿情空自许,无复古来人。”(意即古时人,但“古、来”亦可分读,谓古人与来者也。)
顷上海汪补齐(葆楫)先生惠赠其先兄应千日记印本(前岁曾见其手稿本),读之颇多感想。其宣统辛亥二月朔日记云“送春诗所见甚伙,求其扫除翳障,独闻畦町者,实属不可多得,某报载有送春绝句云:
‘春竟归何处?年年说送春。可怜春自在,送尽古今人。’作者
不详,一憾事也。”赏音非虚,其遗憾诚有如君所言者。末句与上述拙作相似,七十余年后亦巧遇也。少小同在吴门,君出就学,我则家居,坊巷咫尺,无缘识面,其草桥同学,若伯祥、颉刚、圣陶者,其后皆为我忘年之交,共臻耄耋,而君独早世,观其遗文,美志不遂,良可痛惜。
时一九八五年乙丑春,平伯读后记
癸亥年初五之梦
平伯
似在老君堂归寓,得一古书琴谱之类,闻妻在隔壁吟唱。其曲名《辞祠禄词》(注),只听了三数句,清晰能理解。文词雅驯,似唐宋
八家,音调和平宛转,有似阳关三叠,醉翁操,歌罢寂然。初不拟出视,以不觉其身故,亦无伤逝之怀。于时天色阴沉欲雨,心情黯淡。旋醒,天甫黎明。
予昔有《梦雨吟》云:“闻声思暂对,睹影记前姿。”今则空间声而不睹影,又岂能暂对耶,晨起九点书。时润儿夫妇在返天津途中,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七日。
注:一名三同音字。宋人祠禄为大臣宫观虚衔,略似今之退休
养老金。
槐客平生
谈“咏花绝句”
平伯
昔有京师看花绝句云:
燕京游赏影匆匆,桃杏先春不耐风。
得见花王须秉烛,藤萝纡紫海棠红。
梨英未必逊丁香,素艳同登白玉堂。
何事春归恼红药,折为瓶供殿群芳。
以其平易,每以应属书者。
顷重阅儿时残帙,毗陵程惠英女史著《凤双飞》弹词,其第五十回开篇云:
梅花落尽杏花红,艳李天桃向日秾,
自是梨花多簿命,不关轻薄五更风。
其三、四句意颇凄凉。忆前人句云:“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怨五更风。”相似而更深美,不知二者是否有关?即余之旧作,是逞臆闲吟,抑效颦唱本书,亦茫如捕风矣。
甲子岁正月十四日,亡妻二周年
纪念书于北京三里河
以上三篇文章,总共只有六百来字,但每一篇都是写得珠圆玉润,曲折尽意,而且余味无穷,这实在是已经到了小品文的至高境界,这也才显出俞平老作为散文大家的风范。
最后,我们当然不会忘记俞平老更是一位“红学”大家,在他的通信里,是不可能不涉及到“红学”的,事实上,也确是从不同的角度涉及到了“红学”。现在我把这些涉及“红学”的信,择其要者,引述如下:
一九七九年五月,《红楼梦学刊》创刊,红学界举行大会,这是一次难得的红学盛会,当时红学界的前辈全部到了,计有茅盾、王昆仑、叶圣陶、俞平伯、顾颉刚、吴组缃、启功、吴世昌、吴恩裕、周汝昌、张毕来、端木蕻良等等。先是学刊编委邀请俞老任顾问,俞老因年高婉辞,后来邀请他参加成立大会,他欣然允诺。他在会后一九七九年六月二日的信中说:
上月《红楼梦学刊》开会颇盛,我非编委,亦偕圣翁列席,港报有传真照片,未知得见否?可见俞老对这次盛会是很重视的,事实上这一次确是红学界群贤毕至的盛会,现在上述与会的十二位老人,已经有七位去世了。
俞老对一九八○年六月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的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也是十分关心的,曾在好多次信中提及此事,如一九八○年一月一日的信中说:
《红楼梦》讨论会,将于六月中旬在美国威斯康辛开会,策纵来书意甚恳切,我自因衰病未能去,负此佳约,但总需写些诗歌文章以酬远人之望,亦不能草率,故颇费心。
他在一九八○年七月二日的信里说:
《红楼》本是难题,我的说法不免错误,批判原可,但不宜将学术与政治混淆。现得到澄清便好。承热情关垂,感谢感谢!
威斯康辛盛会情况,略见报载。如有人以电子计算机来研
“红”,得到前八十,后四十回是一人所作之结论,诚海外奇谈也。……
《红楼梦》成为“红学”,说者纷纷,目迷五色。我旧学抛荒,新知缺少,自不能多谈,只觉得宜作文艺、小说观,若历史、政治等尚在其次,此意亦未向他人谈也。
又他在一九八○年七月十四日的信里说:
承惠“红会文件”,首尾完整,阅之有味。论文中似以余英时、潘重规为较好,未知然否?“红学”索隐派祖蔡孑民,考证派宗胡适之(虽骂胡适,仍脱不了胡的范围)。考证派虽煊赫,独霸文坛,其实一般社会,广大群众的趣味仍离不开索隐,所谓双峰并峙,各有千秋也。于今似皆途穷矣。索隐即白话“猜谜”,猜来猜去,各猜各的,既不揭穿谜底,则终古无证明之日,只可在茶余酒后作谈助耳,海外此派似尚兴旺。考证切实,佳矣,却限于材料。材料不足,则伪造之,补拟之,例如曹雪芹像有二,近来知道皆非也。一或姓俞,一或姓潘,而同字雪芹。殆所谓“走火入魔”者欤!拉杂书之,以博一笑,不足为外人道也。
俞老在另外一些信里,还有一些关于“红会”的谈论,但大致相同,这里不再重复。
在俞老的信里反复谈论得较多的一件事,是关于吴世昌与周汝昌有关曹雪芹佚诗真伪问题的争论。
如一九八○年七月二日的信说:
周汝昌拟补曹诗,先不明言,近始说出,态度不甚明朗。吴世昌却硬说是真雪芹作,周决做不出,在港《广角镜》以长文攻击,且涉政治,更为不妥。
又同年七月十日信说:
周拟补三诗,如当时明说就好。吴武断第一首为曹氏原作却无证据,只说诗做得好,周决计做不出,不能说服人。又同年七月十四日信说:
前者兄托我请顾老写字,我只将纸送去,转述仰慕之意,未及其他。当二十年代之初,顾和我讨论《红楼梦》,以后即未再谈。及至写来一看,即此补拟之作,颇出意外。即转寄兄,而申明我表存疑,以诗虽尚佳,而来历不明也。今吴周之争,周则勉强交代,吴则盛气凌人,不知尚有后文否?我未参与,亦听之任之耳。
承嘱写字不难,而措词匪易。顾认为真笔,可以应入书,我知其拟作,即无从再提。确证其伪,与顾书对照,显彰友人之失;含糊其词,愈增来者之疑惑,即所谓“不必要的争论”也,以有此困难,遂未能应嘱,务乞谅之为幸。此外,在早些时候,即一九八○年三月五日和三月十八日,当顾老写好此诗后,他就反复说:
顾翁自动写些诗,殊可喜。如有笺道谢,我可转去。
此诗之真伪,我却不敢定。因众说不同也。
三月五日
所传雪芹诗句,难定是否原作,而顾翁墨迹堪珍,良朋酒边致赏,不虚矣。
平启三月十八日对于这首所谓曹雪芹的佚诗的态度,俞平老自始至终一直抱不信任的态度,对两家的批评,也显得十分公正。特别是他对顾老所写此诗,真是投鼠忌器,但他仍旧把它分开,对老朋友的书法,推重爱护备至,对所书的诗句,则仍持不信任态度,两者泾渭分明,清浊不能含糊。前辈学人的这种严正不阿的凛凛风范,实在是后学的楷模。
俞平老的这部通信集,实在是一份丰富的遗产,其内容决不是这短短的叙文所能表述完的。亦只能是取一勺以见大海而已。
一九八七年七月七日,平老曾自题云:
历历前尘吾倦说,方知四纪阻华年。确实,俞平老没有能给我们留下他的传记或者回忆录来,从这方面
来看,也许这位经受了长时期的惊涛骇浪的老人是“倦说”“前尘”了。但是,当我一次又一次地读完了这部书信集后,我又兴奋地感到,其实他没有“倦说”,相反,他却通过书信的方式,给他的知友,也是给后人,说了许多许多。这应该说,是颖南兄的一大功劳。
一九八八年,下距这位老人逝世大约不到两年的时候,他写下了以下的诗句:
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
严霜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
儒林外史录是诗只半首,可惜也。戊辰晚秋写于京师赠颖南兄留念
俞平伯
这首诗,仿佛是这位老人的总结,或者是他的偈语。他写下这首诗,大概也是有所寄托的罢。当然,这仍是我的臆说。
一九九一年二月十日夜一时
于京华宽堂
注:①见本书信。
②原汪一九一九年五月三日晚,在京北河沿北京大学预科之风雨操场,
召开京师各高等学校学生大会。
③原汪时侍亲寓居东华门箭杆胡同,与大学后垣比邻。
④原汪京师道树,旧多马缨花,俗称绒花,天安门前尤盛。
⑤原注曹汝霖住东单赵家楼胡同。
⑥原汪参加北大学生会新闻组时,偕友访京商会会长,要求罢市,欲散发
传单而纸张不足,代以送殡用之纸钱,上加朱戳标语,其不谙世情如此。
⑦原汪先是北大中国文学门班中同学王持期刊凡三,《新潮》为其中之
⑧原汪一九一五年来京,迄今六十五年,其间离京他往者数载。
⑨原注:丙辰清明节微雨。
■原注:引文八字,乃“五四”时口号。
■原注:北河沿西岸清译学馆,后为北大预科,又称三院。其年六月三日北洋政府军警拘禁各校生徙于北。残柳乾河,帐逢罗布。
■原注:其后政府摄于众议,巴黎和约山东条款卒未签字。
■原注:当时余浮慕新学,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浅。
■俞老的夫人许宝驯。
■此信是节录。
■原件无题,这是我暂拟的。——庸。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
冰心
1934年的春夏之交,我和老伴吴文藻在北京燕京大学执教,曾从进步的朋友那里,看到申报副刊《妇女园地》。我当时就感到它与当时一般的妇女刊物不同它是在号召妇女争取解放,宣传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等切中时弊的进步思想。读后我对这个刊物的主编沈兹九产生了无限的钦佩。她眼界之高,见识之广,不是一般普通妇女编辑所能企及的。可惜的是《妇女园地》刊行不久,即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逼迫停刊了。而接着出来的《妇女生活》也是沈兹九主编的,我更是高兴得不断地读着。1935年到1936之间,是我的老伴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教学期满七年的例假,我们到欧美旅游了一年,回到祖国几天后,“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1938年,文藻在敌后的云南大学执教,我和孩子为逃避空袭,住到云南郊外的呈贡。那时的国民党教育部次长顾毓诱是文藻在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从重庆到呈贡来看我们说“蒋夫人宋美龄对我说,‘我的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同学谢冰心,抗战后躲在云南,应该请她来妇女生活指导委员会做点文化教育工作。”我被她“躲”字激怒了,于1941年初就应邀到了重庆。其实,我和宋美龄并没有同过学。我是在1923年燕京大学毕业,得了学士学位,同时又得了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才到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去读硕士学位的。那时宋美龄已经读完本科四年而离开了。
我到重庆就任后,发现那“妇女生活指导委员会”原来是“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而文化教育组的工作,就是搞蒋介石发
起“新生活运动”的那一套!我的前任就是我所钦佩的沈兹九大姐。她就是认为文化教育组应该做些抗日救国工作,而同宋美龄进行多次斗争。宋美龄仍是固执己见,兹九大姐才愤而辞职的。这些话是在我就任后不久,同时还在指委会工作的史良和刘清扬悄悄告诉我的(那时她们为了统战工作,暂时留在会内)。我觉得我是落进了圈套!我立即写了辞呈,退还了工资,连夜搬到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上去。
我真正见到沈兹九同志,是在解放后“十年动乱”后期的北京。那时各民主党派正合组召开政治学习会。她是民主同盟会的会员,我是民主促进会的会员。我第一次和她握手相见,惊诧地发现她不是我想象中的高高大大、声如洪钟的女兵,而是一位身材瘦小,平易近人的知识妇女。她的发言总是十分透彻、精采,和我交谈时也是笑容满面而且很幽默,在我一生接触的朋友中,她是我最敬爱的女友之一。
我从1980年初伤腿后,行动不便,不能参加社会活动了。沈大姐大概身体也不好,我们几乎十年没有见面了。今年的1月初旬得到她逝世的讣告,我不禁潸然泪下。从此,我们在世上没有相见的机会了!安息吧,沈兹九大姐,您一生为党、为国、为人民特别是为妇女做了那么多那么重要的工作,您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您是不朽的!
1990年2月2日雪夜
(转载《女界文化战士沈兹九》)
悼念西苓
夏衍
在中国电影界人才寥落的时候,骤听到西苓的死讯,真是一件哀寂的事情,特别是战时需要新的干部来创造,而这有力的艺术武器还被支配在模仿横行,形式偏重的作风下面的现在。
中国有电影已经近三十年,而名符其实地可以说有了“中国电影”的那还是“九·一八”以后的事情。电影工作的重要,已被屡屡提出了,而“新”的文化人始终视这一领域的工作为畏途,戴白手套的“艺术家”望着这一被脏手捏着的武器摇头,对于企图从这脏手里面夺回这一武器的人们,暗中报之以轻蔑和恶意的冷笑。在旧人的排挤和新人的鄙视之下,极少数不怕龌龊和不相信这一领域真是龌龊到底的“文化人”突入了当时被叫做“黑暗圈”的电影场,在生活的泥泞中打滚,在恶意的荆棘中潜行,使中国电影能够在十年中追上了二十年来的落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的辛酸与苦战,在今天恐怕只有极少数当时亲身经历的人才能理解了,这极少数的中间,西苓是最初冲入这个圈子,而又是在这个圈子里遭受了最大限度的虐待与排挤的一个。
我认识西苓是在1923年,距今是十八年了,从他的京都美术学生时代,经过“艺术剧社”、“中华艺大”、“明星影片公司”,一直到抗战爆发前一瞬的“一贯”大公演,除出他在桂林的一个短时期之外,工作上有了不断的关联,因为相处日久,幸也许不幸,我知道了更多别人所不易知道的他的性癖和弱点。他在戏剧界的短短的十载生涯,是充满了斗争和矛盾的历史。在荆棘的道路上,他是一个
勇敢的斗士,但同时他更是一个彻底的弱者,为了达成一个目的,他可以忍受有洁癖的文化人所绝对不能忍受的羞辱,但是他可以毫无抵抗地接受足以使他整个计划陷于无法完成之让步。他常常苦笑,这苦笑表示他的顽强,但同时也正表示他懦弱。他酷爱卓别林,而本质上却是一个甘地主义的信徒。他的艺术是一种以柔胜刚,以弱胜强的使刚者强者看了自己觉得不好意思的苦笑,而他的人生哲学却是一种潜藏在不抵抗之深底的顽强的抵抗。
在泥泞中,他走了十年,也从这泥泞中,他生产了中国电影艺术上也许在一个短时期之内不会被人忘记的珠玉般的作品,从《上海二十四小时》、《船家女》到《十字街头》,这是一个飞跃,可是当他用不抵抗和妥协累积起来的“地位”好容易草奠基础的时候,命运的恶战便不容情地将他从世界上夺去了。
不单是为了友情,在戏剧电影界寥落的时候,一个真正酷爱电影的“熟练工”的逝去,总觉得是一件难以排遣使人哀寂的事情。
1942年
(转载《夏衍杂文随笔集》)
俞平伯幼受曲园老人的熏陶
郑逸梅
德清俞平伯,名铭衡,生于1900年,去年(1980年)八十寿辰。他学识渊博,著作等身,海内外人士,都为他遥举杯觞,以代华封三祝。
平伯乃曲园老人的曾孙,老人享耄耋之寿,故平伯幼年,犹日亲沐老人的教泽,可谓异数。当他四岁时,未上书房,由他母亲教读《大学》章句。有时,长姐教他读唐诗。每天晚上,由保姆抱到老人居室内,以循定省故例。某晚,他玩得很高兴,直至八点多种,该回屋去睡觉了,他还是赖着不肯走,经多方催促和哄骗,才勉强离去,临行却对保姆等念了一句:“送君还旧府”。这句原是他长姐教他的唐人诗,恰巧合着当时的情况。一时听到的都很惊喜,老人更掀髯大笑,连呼“可儿!”即忙告诉平伯的母亲。
平伯七、八岁时,老人命他每晚来做功课,他倚着方桌,老人坐着靠壁的大椅子,口授文字,以部首偏旁为序,如从木的为“松”、“柏”、“桃”、“李”等,从水的为“江”、“海”、“河”、“汉”等,命他一一写在用竹纸订成的本子上,较冷僻的字写不出来,老人写给他看,照样录下,每晚所写不多,时间也不长,但持之以恒,给他很大的进益。后来老人病了,才告辍止。他回忆有句云:“九秩衰翁灯影坐,口摹苫帖教重孙。”光绪丙午(1906年)中秋,老人于院中燃着斗香。这是吴中的俗尚,斗高数尺,可点整夜,斗的四周,遍插五色尖角的彩旗。他喜欢得很,因为看过京剧,武将背后插有旗帜,正想把斗中的彩旗拔下来,自己插在颈背间以壮威风,可是老人忽发吟
兴,要大家联句,命他先开头。这一下,他搔头摸耳,大感为难,逼着逼着,才逼出了七个字来“八月中秋点斗香”,老人认为尚可,第二句是平伯母亲的:“承欢儿女奉高堂”。第三句是平伯长姐的,已记不起来,老人结句:“添得灯光胜月光。”这事经过七十多年,成为旧话了。
曲园老人,人称他“拼命著书”,平伯传着衣钵,著书很多,如《冬夜》、《雪朝》、《西还》、《燕知草》、《杂拌儿》、《红楼梦研究》、《古槐梦遇》、《古槐书屋词》、《读词偶得》、《读诗札记》、《清真词释》等,嘉惠后学,贡献很大。
他于1917年(丁已年)十月和舅舅的女儿许定驯结婚。1977年,又复岁次丁已,梁孟偕老,整整六十花甲,平伯著《重圆花烛歌》,用古风叙述,某刊物上曾全篇登载。许夫人娴雅能曲,凡唱《西厢记》的,一般为《南西厢》,北曲传唱甚稀,而许夫人能唱北曲“哭宴”一折,由电台录音,然而录音被毁,前又重唱试录,以二胡伴奏,成绩很好。
他夫妇俩居北京数十年,而旧寓仍在苏州马医科巷,即春在堂故址,(编者按现已建成“俞樾先生故居”),可供四方人士游赏。
(原载《艺坛百影》)
(作者系原南社社长)
语可诲人光可鉴物
冯其庸
俞平老于去年十月逝世,噩耗传来,不胜痛悼,于时,我在天水,不能往吊。今年一月中,周颖南大兄自新加坡来,携来平老与他通信的复印稿,沉鼓鼓的两大包。他告诉我说,平老与他的通信已结集,很快出版,要我赶写一序。看样子已经事属紧近,无可推委,只得惶恐应命。
我与平老交往,已是平老的晚年,且因为平老年高,我也不敢多去打扰他,因而也就失去了不少请教的机会。此番面对着这么一大堆俞老的信件,又要我作序,我自然应该认真拜读。前前后后,我在这匆迫的时间里,一共读了三遍,我深深感到这对我是补上了十年学,或者说,弥补了我未能与平老多所请教的遗憾。
我国的文学传统,是十分重视书信的。在著名的《昭明文选》里,就收有书信三卷。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魏文帝《与吴质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等等,都收在文选里。至今流传下来的墨迹,则更是不可胜数,较早的有陆机的《平复帖》,王羲之的《丧乱帖》、《孔待中帖》等,还有转成石刻的《十七帖》,至于唐宋元明清各朝的名人尺牍,更是难计其数。
俞平老是当代著名的学者,著名的“红学家”,他与颖南大兄的通信,自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三日起①,到去年九月三日最后一封信,在这短短的十二年中,已经是积书盈尺了。这还仅仅是平老给颖南大兄一个人的信,推想过去他与其他人的通信,如他早年与顾颉刚的通信,及他在信中不时提到的他与叶圣陶老的通信,还有与
王伯祥、谢国桢诸老的通信,总之,他一辈子所作的书信,不知该有多少?可这是平老创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啊!如今在平老去世三个月后,颖南兄已经将此书信集编好付刊,这种精神实在令人感动。也可以稍慰平老于地下。平老的书信,是学问的渊薮,也是他生平的实录。他对往事的回忆,他对朋友的怀念,他对诗词的论评,他不经意间留下来的散文精品,以及他对“红学”的关切,还有作为书信文学,他在这方面留下的典范,特别是他一生襟怀磊落,豁达率真,对他的夫人则六十余年伉俪情深,一往如昔,这一切,都漾溢在他的书信里。我们只要随便翻读,就会感到这些书信语可诲人,光可鉴物。
平老是一位高寿的老人,整整活了将近一个世纪。又是一位早年成名的作家,他在二十岁以后就异军突起,步入文坛了。所以他的前尘梦影,稍一回忆乙,对后人来说,就成为历史实录。在这部书信集里,在在可以见到。例如一九七九年“五四”周甲纪念,他写《追忆往事诗》十章云:
一
星星之火可燎原,如睹江河发源始。
后此神州日日新,太学举幡辉青史。
二
风雨操场昔会逢②,登坛号召血书雄。
喧呼声彻闲门巷,惊耳谁家丈室中。③
三
马缨花发半城红④,振臂扬旌此日同。
一自权门撄众怒,赵家楼焰已腾空⑤。
四
罢课争将罢市连,新闻组好作宣传。
已教巨贾无青眼,又向当街散白钱⑥。
五
风生蘋末启舆谈,何用文心别苦甘。
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⑦。
六
阅人成世水成川,小驻京华六十年⑧。
及见天街民主化,重瞻魏阙峻于前。
七
清明时节家家雨⑨,五月花开分外鲜。
“四五”真堪随“五四”,波澜壮阔后居先。
八
“外抗强权”如反霸,“内除国贼”抵锄奸⑩。
昔年学子孤军起,今日工农大众欢。
九
北河沿浅柳毵毵。军幕森严忆“六三”■。
唤醒群伦增愤激,呼声遍应大江南■。
十
吾年二十态犹孩■,得遇千秋创局开。
耄及更教谈往事,竹枝渔鼓尽堪咳。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作于北京
以上十首追忆往事诗,历历叙这六十年前“五四”运动的前前后后,诸如学生大游行、北大预科风雨操场上的学生大会、火烧赵家楼、市民的大罢市、北大《新潮》期刊的诞生、一九一九年六月三日北洋政府军逮捕学生的“六三”事件等等,皆是当时的史实,可补史籍之失载。又如追怀顾颉刚先生的《思往日》五首附跋,记述他与顾老的交往和共研《石头记》的情况,不仅使我们可以得知两位大学者的深厚友谊,而且诗味醇厚深永,加以跋文稍稍阐发,令人把玩不已:
思往日
五首附跋
——追怀顾颉刚先生
其一
昔年共论《红楼梦》,南北鳞鸿互唱酬。
今日还教成故事,零星残墨荷甄留。
一九二一年与兄商谈《石头记》,后编入《红楼梦辨》中,乃吾二人之共同成绩。当时商札往还颇多,于今一字俱无。兄处独存其稿,闻《红楼梦学刊》将甄录之,亦鸿雪缘也。
其二
少同里闬未相识,信宿君家壬戍年。
正是江南樱笋好,明朝同泛在湖船。
一九二二年初夏,予将游美国,自杭往苏,访兄于悬桥巷寓,承留止宿,泛舟行春桥外。自十六岁离苏州,其后重来,匆匆逆旅,吴趋坊曲,挈伴同游,六十年中亦惟有此耳。
其三
悲守穷庐业已荒,悴梨新杭各经霜。
灯前有客跫然至,慰我萧寥情意长。
一九五四年甲午秋夕,承见访于北京齐化门故居。
呴沫情殷,论文往迹,不复道矣。
其四
朋簪三五尽吴音,合向耆英会上寻。
秘笈果然人快睹,征文考献遂初心。
六十年代初,兄每约吴门旧雨作真率之余,余浙籍也而生长苏州,亦得预焉。会时偶出珍翰异书相示。君夙藏《桐桥倚棹录》,盖孤本也,予为题绝句十八章。其十七云:“梓乡文献费搜
寻,夙稔君家雅意深。盼得流传人快读,岂惟声价重离林。”其后此书于一九八○年重印。
其五
毅心魄力迥气俦,长记闲谈一句留。
吧息比邻成隔世,而君著述已千秋。
兄尝以吴语语我夫妇云“吾弗是会做,吾是肯做。”生平坚毅宏远之怀,略见于斯。晚岁多病,常住医院。寓在三里河,与舍下毗邻。余去秋造访,于榻前把晤,面呈近刊词稿乞正,君呼小女读之,光景宛在目前,何期与故人遽尔长别哉!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三日,北京
一九七〇年,俞老下放到河南息县,于乡居生活,后来也颇多忆述,他在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给颖南兄的信中说新岁以来,体愈软弱,写作极少,兹抄奉一诗博粲,虽只廿八字,于昔下放河南居乡情况颇能概括,所居为农民弃屋,其敝陋不能想像,若遇大风雨雪皆有危险。经岁平安,感谢上苍,并非诗情,乃是实感,遂以白话写之,如是而已。
诗云:
出水银鳞不自怜,相依一往宛如前
旧茅未为秋风破,经岁平安全谢天
一九七○年在息县东岳集,借住农家废舍,东风夜卷茅栊,幸居停夜起维修,翌晨犹见残茅,飘浮塘上。遂忆杜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云云。方喜其适逢诗景,忧患余生,溺人必笑,初不觉处境之险也。
耐圃■后有《鹧鸪天》词云:
愁雨雪,变晴阴,农村广阔记犹新。友人相过居邻
好,汲井分柴助我勤。
于艰虞中见襟怀之开朗焉。而今人去三春,那更西窗剪烛,栖尘月梦,何幸天怜;促柱幺弦,终归辍响,昔日曾睹吾茅舍者,家中亦只韦柰、润民挈女华栋三人耳,设使他年重到,旧迹都迷,又不知其作何感想也。
我们读他给颖南兄的这封信,这首诗,诗后的附记,他夫人的《鹧鸪天》词,以及词后的短文,可以想见,这位七十老翁的乡居生活是何等艰难,而他和他夫人的襟怀又是何等的朗照!住在破茅屋里,突然遇上了大风雨,人也不堪其苦,可俞老却“方喜其适逢诗景”,俞夫人则说:“农村广阔记犹新”,这是何等的襟怀!
特别要提到的是俞老的《临江仙》纪事词,兹引录如下:
丙丁之际,有纪时事之《临江仙》,近稍流传而词或未安,改写于左:
周甲良辰虚废,一年容易秋冬。休夸时世若为容。新妆传卫里,裙样出唐宫。任尔追踪雉曌,终归啜泣途穷。能诛褒妲是英雄。生花南史笔,愧煞北门公。
己未正月
附注:
一、周甲两句谓婚姻六十年。
二、时世,犹言时妆。花间词“点翠匀红时世”。
三、天津于明代始设卫,曰天津卫。俗称卫里,今亦罕用。
四、雉,汉吕后名。曌,即照字,唐武后名,自造此字。
五、《诗经》:“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六、杜甫《北征》诗:“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谓杨妃。
七、南史氏,春秋时齐之太史,承上句借谓诗史。
八、北门学士,唐时谄事武后者。
平戏涂
很明显,这首词是鞭笞江青的,“丙丁之际”是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七年,词题就写明了“纪时事”,江青于一九七六年(丙辰)垮台,词语说:“新装传卫里”,“任尔追踪雉曌”,则毫无疑问是指江青。
我们统观以上所引的四组忆旧之作,从“五四”运动起,到他与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一九七○年他下放河南息县,一直到“丙丁之际”“四人帮”垮台,概括了多少重要史事。“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现在距离“四人帮”垮台,转瞬又已经首尾十六年了,俞老的这些追忆,也真正成为了史诗。
这里,我还要提到的是,在他与颖南兄的通信里,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商量《重圆花烛歌》的问题,他与叶圣陶老、谢国桢老也曾多次通信讨论此诗。此诗后来由颖南兄将俞老的手书和谢老的写本以及各家的题跋合印成册,以庆祝俞老九十华诞,我也曾为此卷写过跋文。从俞老晚年的诗作来说,这无疑是压卷之作,虽然是“重圆花烛歌”,但实际上也是一首史诗,全诗一百句,从一九一七年俞老与许氏表姊结婚起,一直写到一九七七年,中间六十年来的重大史事皆有概括。但恰恰省略了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俞老的这种省略,当然不是疏忽,也不是害怕,因为诉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灾难,一般来说,是毋庸害怕的,更没有什么“难言之隐”。俞老之所以不写这一段,是因为这是人所共知,人所共经的一场历史性的大灾难,现在灾难刚刚过去,余痛犹存,即使要说也说不完,倒不如不说也罢。所以我认为这一段“空白”,反而更使读者低徊思量,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我的这种体会,是否切合实际,现在平老已经不在,无从质证,只好姑妄言之而已。至于这首诗的艺术手法,我认为是融《秦妇吟》和“梅村体”于一炉,去其华瞻,增其质实。我的这种想法,是否能得其十一,也只能说是姑妄言之。
大家知道,俞平老不仅是学问大家,诗词名家,而且还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和闯将,他的新诗集《冬夜》、《西还》、《忆》,他的散文集《杂拌儿》、《燕知草》、《杂拌儿之二》等等,曾著名于世。这里摘录二通书信和二篇短文,以见俞平老散文的丰采。有人曾说,平老的散文是受《红楼梦》和《浮生六记》的影响,平老曾郑重说明,与其说他是受《红楼梦》和《浮生六记》的影响,毋宁说是受六朝四六骈文的影响来得符合实际,现在先引录平老的书信。颖南兄:
多日未通书问,以情怀甚劣,偃卧斗室,笔墨抛荒故也。
以内子之丧,承远致电音,旋奉手书吊唁,情意深厚,殁存均感!丧事至简,一日而毕。室内一切如旧,而伊人杳然。固知以理遣情,奈无处不枨触何。贱体幸粗安,堪纾远念。
前为兄题诗卷者,若北京张伯驹,上海李宝森皆作古人矣,不胜叹惋。若去岁佳游,诚可念也。
闻吴下曲园近有修复之说,云1985年可落成,自是佳讯,得见与否,未可定也。
言为心声,其辞多感,谅察为幸。
匆颂
俪祉,不具
平伯82.3.7
致荒芜■
示新诗,浣诵欣快。多历忧患,诗与年进,而一管狼毫,犹不减当年之勇,若弟者偶尔命笔,情多衰飒,弥觉不逮。近访圣翁(叶圣陶老人——引者)得一章,音旨尚和,即以候
教。以精神惝怳怳,涉笔易讹,奈何!
十一月十日
读以上两封信,虽然不能说是六朝四六骈文,但晋贤翰札和六朝文体的影响,依然可以寻绎。所以平老自述,信是实话。现在再摘录短文如下:
读“送春诗”书后■
余近句云:“儿情空自许,无复古来人。”(意即古时人,但“古、来”亦可分读,谓古人与来者也。)
顷上海汪补齐(葆楫)先生惠赠其先兄应千日记印本(前岁曾见其手稿本),读之颇多感想。其宣统辛亥二月朔日记云“送春诗所见甚伙,求其扫除翳障,独闻畦町者,实属不可多得,某报载有送春绝句云:
‘春竟归何处?年年说送春。可怜春自在,送尽古今人。’作者
不详,一憾事也。”赏音非虚,其遗憾诚有如君所言者。末句与上述拙作相似,七十余年后亦巧遇也。少小同在吴门,君出就学,我则家居,坊巷咫尺,无缘识面,其草桥同学,若伯祥、颉刚、圣陶者,其后皆为我忘年之交,共臻耄耋,而君独早世,观其遗文,美志不遂,良可痛惜。
时一九八五年乙丑春,平伯读后记
癸亥年初五之梦
平伯
似在老君堂归寓,得一古书琴谱之类,闻妻在隔壁吟唱。其曲名《辞祠禄词》(注),只听了三数句,清晰能理解。文词雅驯,似唐宋
八家,音调和平宛转,有似阳关三叠,醉翁操,歌罢寂然。初不拟出视,以不觉其身故,亦无伤逝之怀。于时天色阴沉欲雨,心情黯淡。旋醒,天甫黎明。
予昔有《梦雨吟》云:“闻声思暂对,睹影记前姿。”今则空间声而不睹影,又岂能暂对耶,晨起九点书。时润儿夫妇在返天津途中,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七日。
注:一名三同音字。宋人祠禄为大臣宫观虚衔,略似今之退休
养老金。
槐客平生
谈“咏花绝句”
平伯
昔有京师看花绝句云:
燕京游赏影匆匆,桃杏先春不耐风。
得见花王须秉烛,藤萝纡紫海棠红。
梨英未必逊丁香,素艳同登白玉堂。
何事春归恼红药,折为瓶供殿群芳。
以其平易,每以应属书者。
顷重阅儿时残帙,毗陵程惠英女史著《凤双飞》弹词,其第五十回开篇云:
梅花落尽杏花红,艳李天桃向日秾,
自是梨花多簿命,不关轻薄五更风。
其三、四句意颇凄凉。忆前人句云:“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怨五更风。”相似而更深美,不知二者是否有关?即余之旧作,是逞臆闲吟,抑效颦唱本书,亦茫如捕风矣。
甲子岁正月十四日,亡妻二周年
纪念书于北京三里河
以上三篇文章,总共只有六百来字,但每一篇都是写得珠圆玉润,曲折尽意,而且余味无穷,这实在是已经到了小品文的至高境界,这也才显出俞平老作为散文大家的风范。
最后,我们当然不会忘记俞平老更是一位“红学”大家,在他的通信里,是不可能不涉及到“红学”的,事实上,也确是从不同的角度涉及到了“红学”。现在我把这些涉及“红学”的信,择其要者,引述如下:
一九七九年五月,《红楼梦学刊》创刊,红学界举行大会,这是一次难得的红学盛会,当时红学界的前辈全部到了,计有茅盾、王昆仑、叶圣陶、俞平伯、顾颉刚、吴组缃、启功、吴世昌、吴恩裕、周汝昌、张毕来、端木蕻良等等。先是学刊编委邀请俞老任顾问,俞老因年高婉辞,后来邀请他参加成立大会,他欣然允诺。他在会后一九七九年六月二日的信中说:
上月《红楼梦学刊》开会颇盛,我非编委,亦偕圣翁列席,港报有传真照片,未知得见否?可见俞老对这次盛会是很重视的,事实上这一次确是红学界群贤毕至的盛会,现在上述与会的十二位老人,已经有七位去世了。
俞老对一九八○年六月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的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也是十分关心的,曾在好多次信中提及此事,如一九八○年一月一日的信中说:
《红楼梦》讨论会,将于六月中旬在美国威斯康辛开会,策纵来书意甚恳切,我自因衰病未能去,负此佳约,但总需写些诗歌文章以酬远人之望,亦不能草率,故颇费心。
他在一九八○年七月二日的信里说:
《红楼》本是难题,我的说法不免错误,批判原可,但不宜将学术与政治混淆。现得到澄清便好。承热情关垂,感谢感谢!
威斯康辛盛会情况,略见报载。如有人以电子计算机来研
“红”,得到前八十,后四十回是一人所作之结论,诚海外奇谈也。……
《红楼梦》成为“红学”,说者纷纷,目迷五色。我旧学抛荒,新知缺少,自不能多谈,只觉得宜作文艺、小说观,若历史、政治等尚在其次,此意亦未向他人谈也。
又他在一九八○年七月十四日的信里说:
承惠“红会文件”,首尾完整,阅之有味。论文中似以余英时、潘重规为较好,未知然否?“红学”索隐派祖蔡孑民,考证派宗胡适之(虽骂胡适,仍脱不了胡的范围)。考证派虽煊赫,独霸文坛,其实一般社会,广大群众的趣味仍离不开索隐,所谓双峰并峙,各有千秋也。于今似皆途穷矣。索隐即白话“猜谜”,猜来猜去,各猜各的,既不揭穿谜底,则终古无证明之日,只可在茶余酒后作谈助耳,海外此派似尚兴旺。考证切实,佳矣,却限于材料。材料不足,则伪造之,补拟之,例如曹雪芹像有二,近来知道皆非也。一或姓俞,一或姓潘,而同字雪芹。殆所谓“走火入魔”者欤!拉杂书之,以博一笑,不足为外人道也。
俞老在另外一些信里,还有一些关于“红会”的谈论,但大致相同,这里不再重复。
在俞老的信里反复谈论得较多的一件事,是关于吴世昌与周汝昌有关曹雪芹佚诗真伪问题的争论。
如一九八○年七月二日的信说:
周汝昌拟补曹诗,先不明言,近始说出,态度不甚明朗。吴世昌却硬说是真雪芹作,周决做不出,在港《广角镜》以长文攻击,且涉政治,更为不妥。
又同年七月十日信说:
周拟补三诗,如当时明说就好。吴武断第一首为曹氏原作却无证据,只说诗做得好,周决计做不出,不能说服人。又同年七月十四日信说:
前者兄托我请顾老写字,我只将纸送去,转述仰慕之意,未及其他。当二十年代之初,顾和我讨论《红楼梦》,以后即未再谈。及至写来一看,即此补拟之作,颇出意外。即转寄兄,而申明我表存疑,以诗虽尚佳,而来历不明也。今吴周之争,周则勉强交代,吴则盛气凌人,不知尚有后文否?我未参与,亦听之任之耳。
承嘱写字不难,而措词匪易。顾认为真笔,可以应入书,我知其拟作,即无从再提。确证其伪,与顾书对照,显彰友人之失;含糊其词,愈增来者之疑惑,即所谓“不必要的争论”也,以有此困难,遂未能应嘱,务乞谅之为幸。此外,在早些时候,即一九八○年三月五日和三月十八日,当顾老写好此诗后,他就反复说:
顾翁自动写些诗,殊可喜。如有笺道谢,我可转去。
此诗之真伪,我却不敢定。因众说不同也。
三月五日
所传雪芹诗句,难定是否原作,而顾翁墨迹堪珍,良朋酒边致赏,不虚矣。
平启三月十八日对于这首所谓曹雪芹的佚诗的态度,俞平老自始至终一直抱不信任的态度,对两家的批评,也显得十分公正。特别是他对顾老所写此诗,真是投鼠忌器,但他仍旧把它分开,对老朋友的书法,推重爱护备至,对所书的诗句,则仍持不信任态度,两者泾渭分明,清浊不能含糊。前辈学人的这种严正不阿的凛凛风范,实在是后学的楷模。
俞平老的这部通信集,实在是一份丰富的遗产,其内容决不是这短短的叙文所能表述完的。亦只能是取一勺以见大海而已。
一九八七年七月七日,平老曾自题云:
历历前尘吾倦说,方知四纪阻华年。确实,俞平老没有能给我们留下他的传记或者回忆录来,从这方面
来看,也许这位经受了长时期的惊涛骇浪的老人是“倦说”“前尘”了。但是,当我一次又一次地读完了这部书信集后,我又兴奋地感到,其实他没有“倦说”,相反,他却通过书信的方式,给他的知友,也是给后人,说了许多许多。这应该说,是颖南兄的一大功劳。
一九八八年,下距这位老人逝世大约不到两年的时候,他写下了以下的诗句:
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
严霜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
儒林外史录是诗只半首,可惜也。戊辰晚秋写于京师赠颖南兄留念
俞平伯
这首诗,仿佛是这位老人的总结,或者是他的偈语。他写下这首诗,大概也是有所寄托的罢。当然,这仍是我的臆说。
一九九一年二月十日夜一时
于京华宽堂
注:①见本书信。
②原汪一九一九年五月三日晚,在京北河沿北京大学预科之风雨操场,
召开京师各高等学校学生大会。
③原汪时侍亲寓居东华门箭杆胡同,与大学后垣比邻。
④原汪京师道树,旧多马缨花,俗称绒花,天安门前尤盛。
⑤原注曹汝霖住东单赵家楼胡同。
⑥原汪参加北大学生会新闻组时,偕友访京商会会长,要求罢市,欲散发
传单而纸张不足,代以送殡用之纸钱,上加朱戳标语,其不谙世情如此。
⑦原汪先是北大中国文学门班中同学王持期刊凡三,《新潮》为其中之
⑧原汪一九一五年来京,迄今六十五年,其间离京他往者数载。
⑨原注:丙辰清明节微雨。
■原注:引文八字,乃“五四”时口号。
■原注:北河沿西岸清译学馆,后为北大预科,又称三院。其年六月三日北洋政府军警拘禁各校生徙于北。残柳乾河,帐逢罗布。
■原注:其后政府摄于众议,巴黎和约山东条款卒未签字。
■原注:当时余浮慕新学,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浅。
■俞老的夫人许宝驯。
■此信是节录。
■原件无题,这是我暂拟的。——庸。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
相关地名
德清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