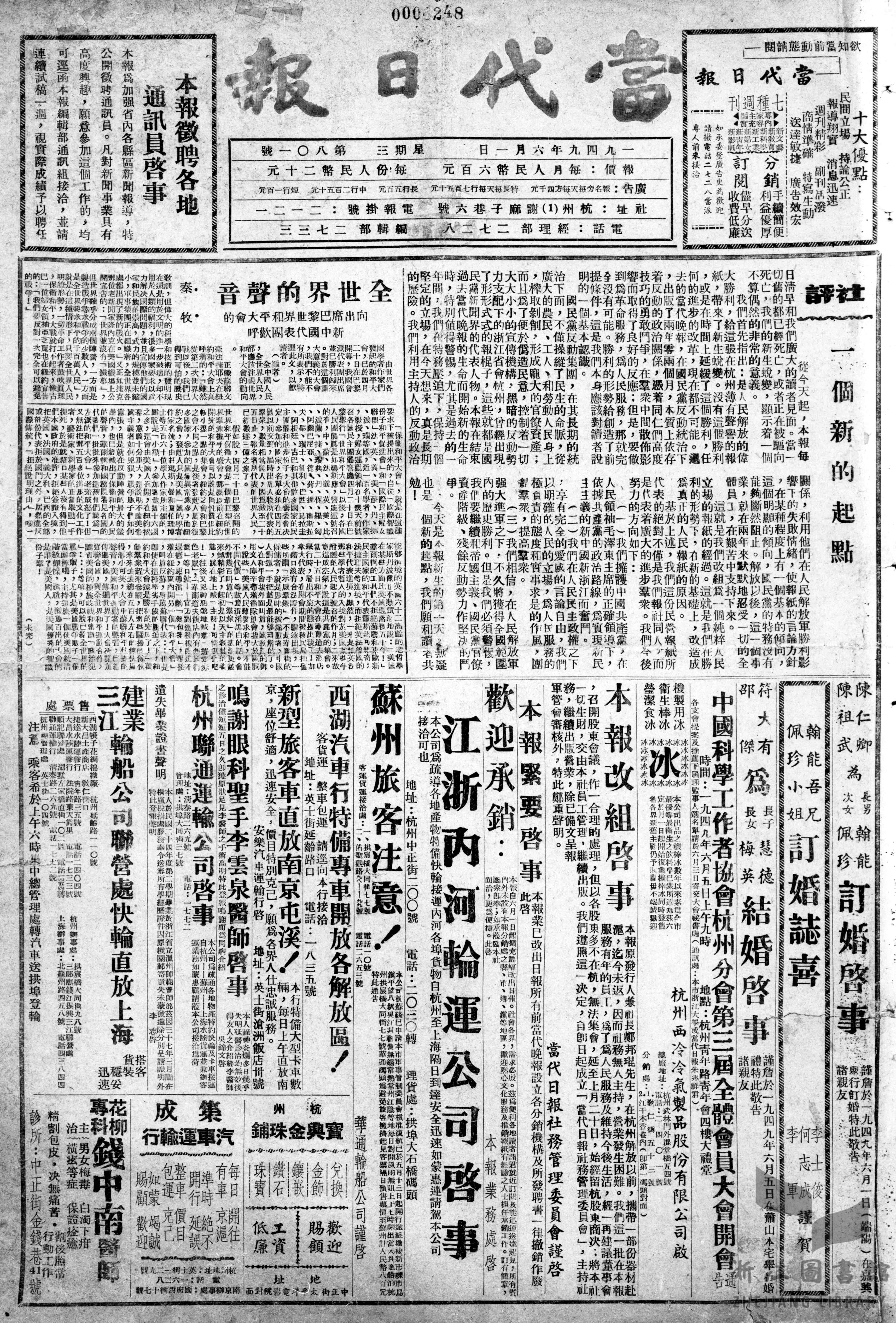内容
編輯同志:
讀了王西彥先生著的「神的失落」一書,我有下面幾點意見:
(一)作者寫這本書動機是什麽?作者在這本書的序中曾說「讓讀者重溫一個可怕的噩夢」
,這個可怕的噩夢對讀者有什麽幫助?
(二)本書爲解放前著作,最後出版爲一九五〇年一月,此書在目前是否有出版發行之必要,再版時作者是否同意?
(三)在本書的后記中,作者曾說這麽一句話:「在抗戰結束前夕……從自己國內一切情形上也看不出勝利的預兆」,這種說法是否抹殺中國人民在抗戰中英勇鬥爭事蹟,作者看不出勝利預兆又根據什麽來說?
(四)后記中又說過去曾有人對此書指出不合實際,不値一寫的批評。作者當時很吃驚,並認爲指責這書的人是沒有度過長期抗戰的痛苦,是一種色盲的論斷,這樣作者是否是犯了不接受批評和以功臣自居的錯誤?
此致敬禮
讀者邢子修編輯同志:
來信和附來邢子修同志的信,已經收到了,很感激。對於邢同志所詢問有關拙作「神的失落」(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的幾個問題,敬覆如下:
(一)邢同志問:「作者寫本書的動機是什麽?」我現在就抄錄我在這書的「三版自序」上的一段話來回答,那段話是這樣的:「這本小書,只是我原定的三個故事的第一個。……我所寫的,如果要給它一個總的題目,應該是『個人主義的滅亡』。在現在這樣的尖銳地戰鬥着的時代裏,在現在這樣的階級分明的社會裏,個人的戰鬥和掙扎有什麽用呢?不管他是怎樣的富於正義感,怎樣的懷有澎湃的熱情,怎樣的憧憬着遠大的理想,個人的戰鬥和掙扎,總之只能給自己換來失敗和絕望。這便是我所要在我的作品裏宣言和證明的。……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在今天,如果不能跨越自己,走向人民,在他前面就决不能有前途。而對於個人主義的減亡的宣告,便應該是跨越自己的第一步。」邢同志又問:「前序中曾說:『讓讀者重溫一個可怕的噩夢』,這個可怕的噩夢對讀者有什麽幫助?」在抗戰的末期,在國統區,在反動的統治之下,社會秩序非常混亂,惡勢力空前高漲,人民的痛苦,不可言狀。在這種情形之下,個人主義者的知識份子,往往陷入悲劇而無力自拔。這樣的「可怕的噩夢」,作爲一種歷史敎訓來看,對我們是不是有用呢?這至少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吧?
(二)邢同志問:「本書爲解放前舊作………在目前是否有出版發行之必要?再版時作者是否同意?」本書再版,作者自然是同意的,有「三版自序」為證。至於有沒有再版的必要,我的看法詳見對第一個問題的答覆。
(三)「后記」中「在抗戰結束前夕………從自己國內一切情形上也看不出勝利的預兆。」這句話是有語病的,對邢同志的指責,很感激。我當時所指的,自然是國統區內黑暗窒息的情形。(不是在當時的國統區,連勝利也叫做「慘勝」嗎?)讀者或者也可以知道,在當時的國統區,對於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英勇鬥爭,是不便公開的寫出來的。但「后記」上那樣的寫法,當然是不對的,的確會使人覺得我是在抹殺人民在抗戰中的英勇鬥爭,覺得我竟不能全面地看出抗戰勝利的預兆。
(四)邢同志認爲我在「后記」中,對當時有人指出本書所寫的故事「不眞實」,所以不應該寫和不値得寫的批評表示不能接受,是「犯了不接受批評和以功臣自居的錯誤」。對於這一點,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批評有各種各樣的批評,有正確的批評,也有不正確的批評。正確的批評應該接受,不正確的批評必須拒絕。邢同志難道以爲凡有批評,都應該接受嗎?至於爲什麽不接受,我在「后記」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在這裏不再贅述。
總之,「神的失落」並不是一部好作品,我自己也正在準備重新修正。對邢同志的關心和好意,我也很感激。如邢同志能對我那有連貫性的「追尋」三部作(另兩部為「尋夢者」和「人的道路」)作全面的批評,則更感激不盡了。此致敬禮!王西彥啓一九五一年九月三日浙大
讀了王西彥先生著的「神的失落」一書,我有下面幾點意見:
(一)作者寫這本書動機是什麽?作者在這本書的序中曾說「讓讀者重溫一個可怕的噩夢」
,這個可怕的噩夢對讀者有什麽幫助?
(二)本書爲解放前著作,最後出版爲一九五〇年一月,此書在目前是否有出版發行之必要,再版時作者是否同意?
(三)在本書的后記中,作者曾說這麽一句話:「在抗戰結束前夕……從自己國內一切情形上也看不出勝利的預兆」,這種說法是否抹殺中國人民在抗戰中英勇鬥爭事蹟,作者看不出勝利預兆又根據什麽來說?
(四)后記中又說過去曾有人對此書指出不合實際,不値一寫的批評。作者當時很吃驚,並認爲指責這書的人是沒有度過長期抗戰的痛苦,是一種色盲的論斷,這樣作者是否是犯了不接受批評和以功臣自居的錯誤?
此致敬禮
讀者邢子修編輯同志:
來信和附來邢子修同志的信,已經收到了,很感激。對於邢同志所詢問有關拙作「神的失落」(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的幾個問題,敬覆如下:
(一)邢同志問:「作者寫本書的動機是什麽?」我現在就抄錄我在這書的「三版自序」上的一段話來回答,那段話是這樣的:「這本小書,只是我原定的三個故事的第一個。……我所寫的,如果要給它一個總的題目,應該是『個人主義的滅亡』。在現在這樣的尖銳地戰鬥着的時代裏,在現在這樣的階級分明的社會裏,個人的戰鬥和掙扎有什麽用呢?不管他是怎樣的富於正義感,怎樣的懷有澎湃的熱情,怎樣的憧憬着遠大的理想,個人的戰鬥和掙扎,總之只能給自己換來失敗和絕望。這便是我所要在我的作品裏宣言和證明的。……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在今天,如果不能跨越自己,走向人民,在他前面就决不能有前途。而對於個人主義的減亡的宣告,便應該是跨越自己的第一步。」邢同志又問:「前序中曾說:『讓讀者重溫一個可怕的噩夢』,這個可怕的噩夢對讀者有什麽幫助?」在抗戰的末期,在國統區,在反動的統治之下,社會秩序非常混亂,惡勢力空前高漲,人民的痛苦,不可言狀。在這種情形之下,個人主義者的知識份子,往往陷入悲劇而無力自拔。這樣的「可怕的噩夢」,作爲一種歷史敎訓來看,對我們是不是有用呢?這至少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吧?
(二)邢同志問:「本書爲解放前舊作………在目前是否有出版發行之必要?再版時作者是否同意?」本書再版,作者自然是同意的,有「三版自序」為證。至於有沒有再版的必要,我的看法詳見對第一個問題的答覆。
(三)「后記」中「在抗戰結束前夕………從自己國內一切情形上也看不出勝利的預兆。」這句話是有語病的,對邢同志的指責,很感激。我當時所指的,自然是國統區內黑暗窒息的情形。(不是在當時的國統區,連勝利也叫做「慘勝」嗎?)讀者或者也可以知道,在當時的國統區,對於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英勇鬥爭,是不便公開的寫出來的。但「后記」上那樣的寫法,當然是不對的,的確會使人覺得我是在抹殺人民在抗戰中的英勇鬥爭,覺得我竟不能全面地看出抗戰勝利的預兆。
(四)邢同志認爲我在「后記」中,對當時有人指出本書所寫的故事「不眞實」,所以不應該寫和不値得寫的批評表示不能接受,是「犯了不接受批評和以功臣自居的錯誤」。對於這一點,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批評有各種各樣的批評,有正確的批評,也有不正確的批評。正確的批評應該接受,不正確的批評必須拒絕。邢同志難道以爲凡有批評,都應該接受嗎?至於爲什麽不接受,我在「后記」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在這裏不再贅述。
總之,「神的失落」並不是一部好作品,我自己也正在準備重新修正。對邢同志的關心和好意,我也很感激。如邢同志能對我那有連貫性的「追尋」三部作(另兩部為「尋夢者」和「人的道路」)作全面的批評,則更感激不盡了。此致敬禮!王西彥啓一九五一年九月三日浙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