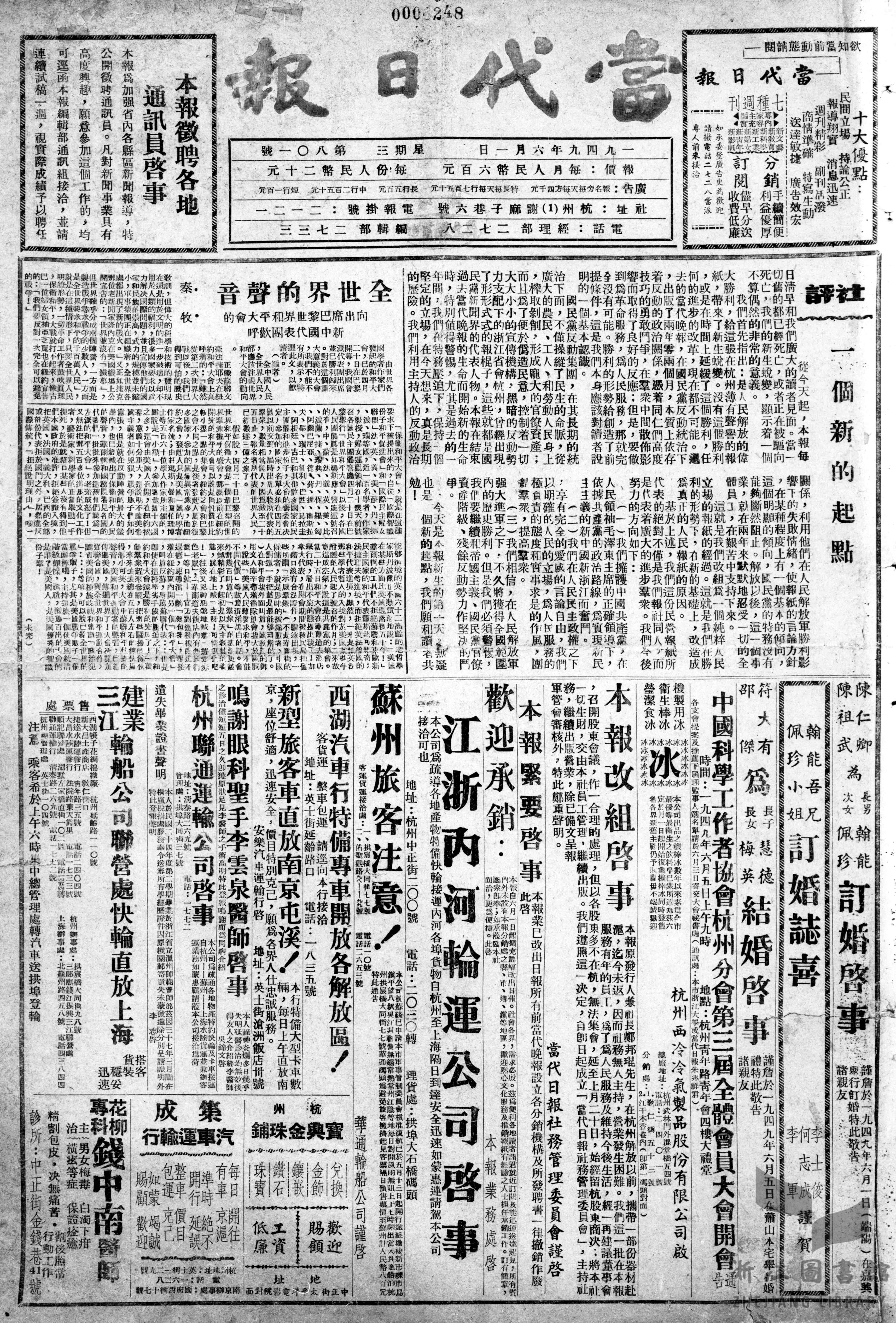内容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發表,引起了全國文藝界、敎育界、社會科學界和一般知識界關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廣泛的熱烈的討論。這是一場十分嚴重的思想論爭。因爲論爭的中心問題關涉到中國人民的歷史的道路:中國人民所走的是革命的道路呢,還是改良主義、投降主義的道路?這是一個帶有重大原則性質,必須正確地加以解答的問題。
兩個月來,許多同志對電影『武訓傳』、『武訓畫傳』及其它一切關於武訓的反動宣傳進行了嚴正的批判。最近發□『武訓歷史調查記』以無可辯駁的邏輯的力量作出了關於武訓問題的科學結論,並且在歷史研究工作、社會調查工作和文藝批評工作的方法上做了很好的示範。我自己很早就看了電影『武訓傳』,但並沒有能够充分地認識和及早地指出它的嚴重的政治上的反動性。雖然我在三月間舉行的第一届全國文化行政會議上對這電影作了批評,但現在看了許多同志的文章和材料之後,感覺着我當時的批評是極其不够的。現在,武訓的歷史已經完全清楚了;但對於引起這次論爭的電影『武訓傳』本身,却還需要就它的思想和藝術作系統的批判。我的這篇文章就是為這個目的寫的。
兩種歷史觀
電影『武訓傳』是一部關涉中國近代歷史的傳記影片。對待歷史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爲:歷史不是由階級和階級鬥爭造成的,而是由少數所謂先知先覺者造成的;社會的黑暗不是由於不合理制度的存在,而是由於人民自己沒有敎育,沒有文化,因此要改造社會,可以無需經過人民羣衆的革命鬥爭,推翻舊制度,建立新制度,祗需給人民以敎育和文化,就可以達到新的光明的世界。因此歷史的創造者和推動者,主要地不是勞動人民,而是有文化敎養的人們以及熱心於在人民中傳播『敎育』『文化』的人們。這是一種反人民、反科學的歷史觀點。宣傳這種觀點就是在思想上解除羣衆的武裝,散佈幻想,叫羣衆發生一種錯覺,以為在舊社會的制度下不經過羣衆的革命的方法而經過某些改良的方法就可以使他們的生活狀况獲得根本的改善。孫瑜在電影『武訓傳』中就是用藝術的手段巧妙地宣傳了這種思想。他把武訓的「興學」描寫爲勞動人民求解放的最可靠的道路。於是他就把武訓——這個封建社會中最醜惡、最虛僞、最反動的奴才,這個腐爛的封建文化的狂熱宣傳者——描寫爲『向封建統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鬥爭』的堅靭的革命戰士,不,簡直描寫爲一個神聖化了的人物:他『在雲端向下界微笑,給正得着解放的本階級勞動同伴們祝福』呢。就這樣,這個歷史上的反動派就成了中國人民的革命祖先,而解放了的中國人民就成了武訓事業的繼承者。這對於具有光榮革命傳統,今天正站在全世界反帝國主義鬥爭的最前綫英勇地、堅决地戰鬥着的中國人民,難道不是絕大的汚衊嗎?這種汚衊難道是能够容忍的嗎?
另一種與上述觀點完全對立的觀點,認爲:人類社會的基礎既然是由生產組成的,那末人類社會歷史的創造者,首先就是生產物質財富的勞動人民。勞動人民在他們每天創造物質財富的當年,不斷地創造歷史。特別在歷史的轉變關頭,當新的社會力量起來和舊的社會力量進行鬥爭的時候,决定鬥爭的結局的總是廣大的人民羣衆。人民羣衆是歷史的主要推動者。歷史上的每一個重大的進步或變革都必須經過人民羣眾的嚴重鬥爭,而不是單靠少數所謂先知先覺者所能完成的。任何英雄好漢,祗有當他正確地代表了歷史的前進方向,代表了或至少在某些重要方面代表了廣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時候,才能成為眞正的英雄好漢。如果違背了歷史的前進方向,違背了廣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不管他具有怎樣的個人品質,怎樣的才能、毅力,甚至有怎樣的『奇行特操』,都祗能成為可憐可笑的人物,最後終將被抛人歷史的垃圾箱中去。只有根據這種觀點來衡量和估價歷史人物,這才是正確的。因此,我們的文學藝術,祇能歌頌那些推動歷史前進,對人民有貢獻的人物,而决不應歌頌歷史上的反動派,或對人民毫無貢獻的人物。我們特別尊重自己民族的革命傳統,我們要把人民今天的鬥爭和過去的革命傳統正確地連結起來,因此我們决不能容忍對人民革命傳統的任何歪曲或侮蔑。許多同志批評電影『武訓傳』及其它關於武訓的錯誤文章,主要地就都是從這個根本點出發的。這是人民的、科學的歷史觀點。
人民的、科學歷史觀點和反人民、反科學的歷史觀點,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和賢產階級反動思想的區別。
許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徘徊在兩者之間,他們雖承認人民羣眾的革命鬥爭在歷史上的作用,但對這種作用的認識往往是抽象的,估計往往是不足的。又由於他們個人的出身和敎義,他們在解釋具體歷史現象或社會現象的時候,往往就自覺或不自覺地把文化看得高於一切,把個人的力量看得高於羣衆的力量,而特別有興趣於個人的奮鬥和成就,甚至個別的所謂『奇人奇事」。這和中國工業不發達,小生產佔絕對優勢,小資產階級衆多,文化落後的狀况是有很大關係的。這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形成了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盲目讚揚者的社會基礎。他們的盲目讚揚武訓和『武訓傳』,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受了關於武訓的反動宣傳的欺騙,另一方面也正是因爲這種反動宣傳恰好乘了他們缺乏歷史觀點和缺乏羣衆觀點的弱點,投合了他們的知識分子的個人主義的思想、情緒和心理。這就是爲甚麽在武訓的眞面目已經被揭露之後,還有一些人要找各種理由為武訓辯護,有些人甚至在理性上否定了武訓,在感情上還是同情他。
那末,究竟武訓和電影『武訓傳』有些甚麽地方那麽迷惑人呢?
武訓和電影『武訓傳』
迷惑人的地方在哪裏?
武訓並不是歷史上的什麽重要人物,他不過是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的各色各樣的奴才之一,但他却是其中的一個比較特殊的、帶有特別的虛僞性和欺騙性的奴才。電影『武訓傳』就以歷史的僞造和藝術的渲染把他描畫成一個革命人物和民族英雄。於是一具封建殭屍穿上了革命的衣服大搖大擺地走進人民的行列,在人民當中散佈毒素。因此我們要批判電影『武訓傳』,首先就必須揭露武訓的眞實面目。許多批評者從各方面進行了這個揭露的工作,而武訓歷史調查團則更作了一個關於武訓的全面的、澈底的揭露。
武訓和電影『武訓傳』有它迷惑人的地方。自然,許多人被迷惑,還不祗是因爲對武訓歷史眞相不明瞭的原故,而主要的,是由於缺乏以馬列主義觀點辨別事物的能力。
武訓出身貧農,從乞丐變爲高利貸者兼地主,他一生的歷史,基本上就是一個寄生者、剝削者的歷史。根據武訓歷史調查團的調查,在武訓的整個一生中,他祇有過一年多時間的勞動,而且他所從事的又只是一些鍘草、推磨之類的比較輕微的勞動,而不是生產中的主要勞動。在他的行乞生活中雖然有時也仍做些鍘草、推磨的工作,但那已不過是他行乞生活中的一種點綴,或者如同他的變戲法一樣,是行乞的一種節目而已。他事實上已經完全脫出了農民階級的軌道,而成爲了一個職業的乞丐,並且是一個耍着各種無賴手段的惡丐。電影『武訓傳』却把他描寫為勞動人民的忠實的兒子,特別强調他的終生勞動,說他『除去在破廟裏睡着了的時間以外,他的兩手從不休息』,這樣就把他的生活的墮落的寄生的性質掩蓋起來了。但是如果我們用科學的,階級的觀點觀察問題的話,那末,乞丐所屬的遊民階層是和工人農民眞正勞動階級不相干的。遊民是寄生者,又具有很大的破壞性,他們很容易變成爲反革命的工具,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以前寫的『共產黨宣言』中就講了的。事實上歷來反動統治者也總是從遊民階層中去物色、培養和提拔他的走狗的。武訓的歷史道路,也恰巧證明了這條眞理。武訓不是一個普通乞丐,而是一個打着『興學』旗幟的政治乞丐。他有了這個旗幟,不但行乙方便得多,而更重要的是找着了和封建統治階級通氣的門路。他果然得到了豪紳地主官吏的贊助和支持,使他辦起了所謂『義學』,他自己也成為了地主兼高利貸者。但他和普通地主是不一樣的。他雖然已經是一個三百多畝土地的所有者,而且以超過當時最高標準的利率放債,但是他的土地名義上是學田,而他的收租放債又都假『興學』之名以行,因而就在世人眼中掩蓋了他地主兼高利貸者的剝削者的身份。封建地主原是各式各樣的:有廟田所有者的宗敎地主,與武訓合作辦第二所『義學』的了證和尚就屬於這一類地主;也有學田及其它公田所有者的政治地主,武訓就是這樣的一個政治地主。武訓打着『興學』旗幟,憑仗着地主豪紳官僚的勢力,佔有了大量的土地和高利貸資本,放肆地對農民進行無情的殘酷的剝削。當地的貧苦農民叫武訓為『財迷』。武訓的剝削行為,就在讚揚他的許多傳記裏,也不能不透露一些出來,但在電影裏却完全被掩蓋了。武訓對家庭所表示的態度:『我的事,你別管,兄弟分家不相干』,『不顧親,不顧故』,『親戚朋友斷個淨』,並不是如一些武訓讚揚者所說的那樣,表現了武訓在親屬關係上的大公無私,而恰是表現了作爲地主兼高利貸者的武訓在對農民(包括他自己的親兄弟在内)的剝削關係上的冷酷和堅决。這可以看做是武訓背叛他所出身的農民階級而投降地主階級的决心書。從此,武訓交上了婁峻嶺、楊樹坊、施善政之流的大豪紳地主惡霸,而成爲了他們的座上賓。
武訓的利害還在於他雖然成了地主兼高利貸者,却始終穿着乞丐的衣服,並在行乞與强化佈施中繼續使用各種無賴的手段,他成爲一個穿着乞丐衣服的流氓政治地主。因爲如果脫下這衣服,他的欺騙作用就要失去,至少要大大地減少了。但是如果我們在確定一個人的階級成份的時候,不根據一個人表面的生活形態,而只根據他對生產資料的佔有關係的話,那末,對於武訓的鑑定除了他是地主兼高利貸者這個結論之外,就不能再有任何其它的結論了。
武訓的更迷惑人的地方,是他的『興學』的事蹟。武訓的『興學』,加上他的印發善書,獎勵節孝等等,本來完全是宣傳最反動的腐朽的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死心塌地地爲封建地主階級服務的;但是電影『武訓傳』却把他的『興學』描寫成反對封建地主統治,爲農民求解放的義舉。武訓被描寫成了『腦筋一點也不封建』,而且『堅靭地、百折不撓地和封建統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鬥爭』的革命英雄。這是一個絕大的誑騙。『興學』的口號是能够騙人的,不但在武訓生前,而且就在他死後的今天,這個口號還有迷惑人的力量。
『辦敎育總是好事』,許多武訓的擁護者和同情者這樣說,好像否定武訓就是輕視敎育似的。我們應當重視敎育,但不應當把敎育看成超階級、超政治的。斯大林同志在『與英國作家威爾斯的談話』中,有一段話說得非常好:
『敎育是一種武器,其效能是依誰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用這個武器去打擊誰爲轉移的。當然,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是需要受過高等敎育的人的。很明顯的,只要不是最愚蠢的人,都可以幫助無產階級去爭取社會主義,建立新社會。我並不輕視知識分子的作用,相反的,我更側重他們的作用。問題只在於說的是那一種知識分子,因爲知識分子是各色各樣的。』
事實很清楚,武訓所辦的『義學』是完全掌握在封建地主手中的。興辦『義學』,並不是武訓的甚麽創舉。早在淸初的時候,封建統治者就在各地辦了許多『義學』。那位一隻手血淋淋地鎭壓農民革命,另一隻手提拔武訓的山東巡撫張曜就是『義學』的積極提倡者。那末這種所謂『義學』,究竟是『打擊誰』,是打擊地主,還是打擊農民的呢,由這種『義學』所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究竟是擁護農民利益的,還是擁護地主利益的呢,難道不是一眼可以判斷出來的嗎?武訓自己也唱了:『壞人多,好人少,辦個義學錯不了。』武訓的『興學」就正是迎合了當時封建統治者籠絡人心的反動政策,因而『義學』就成了他投降封建統治階級並使自己也爬上地主階級行列中去的政治資本。
『在封建社會裏,祇能辦封建敎育,不能苛責武訓。』武訓的擁護者和同情者又這樣辯護着說,好像否定武訓就是否定一切過去時代的敎育似的。
我們並不一般地否定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敎育,並且承認敎育在各個歷史時代中的一定作用,而新敎育又正是從舊敎育發展來的。在這一點上,我們不但要將武訓和陶行知相區別,而且也要將武訓和孔子相區別,陶行知的道路是從一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發展爲革命的民主主義者的道路,他的敎育學說中有不少觀念論的因素,這是他的思想上的弱點。他錯誤地讚揚武訓就正是他的這種思想上的弱點的表現之一。但就他整個的政治傾向和他在晚年努力使他的敎育活動的內容革命化的事實來說,他無疑地是中國人民的傑出的敎育家之一。武訓是不能和他相提並論的。孔子是封建社會的偉大的敎育家;他與武訓不同,不祗因爲他生在二千多年前正當封建制度興盛,封建文化放出燦爛異彩的時代,而武訓所處的時代,則是封建統治基礎已面臨最後崩潰,而作爲這個基礎的上層建築物的封建文化已腐爛到喪失任何生命力的時代;而且也因為孔子在敎育思想和敎育方法上有卓越的貢獻,而武訓則不過是以『興學』做幌子,對敎育一無所知、一無所能的一個騙子而已。有些敎育工作者把武訓這樣一個人物放在敎育史上和陶行知、孔子並列,甚至高過陶行知、孔子的地位,這實在是敎育界的一件恥辱的事情。
『武訓爲窮孩子「興學」,他的動機總是好的。』這是為武訓辯護的一個最普遍、最動聽的理由了。電影『武訓傳』就肆意渲染了武訓爲着窮孩子的一片苦心。
武訓的動機是否眞爲窮孩子『興學』,這就不能單單根據武訓所打出的『興個義學爲貧寒』的招牌,而且具體考察武訓所辦的『義學』的實際內容和效果。
本來,武訓的『義學』,不論是從經費來源、敎學內容,學生成份來說,都是一開始就完全掌握在地主階級手中的。電影『武訓傳』却偏偏要說成是在武訓死後才被地主們搶過去的。武訓的興學本來是以『又有名,又行好,文昌帝君知道了,準敎你子子孫孫坐八抬大轎。』爲號召的,電影却揑造一些這樣相反的場面:武訓聽到學生讚『學而優則仕』,他的内心那樣地感到彷徨和痛苦;他流着淚再三叮嚀他的學生:『你們唸好了書,千萬不能忘記咱們窮人!』最後他又那樣充滿信心地說:『我不能休息!不等到每一個窮孩子都有書唸,都有飯吃的時候……我是不會休息的。』這一切描寫無非是要叫觀衆相信,不管『義學』的客觀效果如何,武訓的一顆赤熱的心始終是爲窮孩子的,爲着農民的。事實眞是這樣嗎?祗消舉出一個材料就可以解答這個問題了。據武訓歷史調查團的調查,武訓所辦的第一所學校『崇賢義塾』,頭七年,根本沒有蒙學,只有經班,而經班的學生全都是地主富農商人子弟,貧苦農民子弟是入不了經班的。武訓的心如果眞是爲窮孩子,那末,七年之久,他的學校中沒有窮孩子,他難道看不見嗎?很顯然,他的心中是根本沒有什麽窮孩子的地位的。
動機本來是主觀存在的東西,只有當一個人的主觀動機變爲行動而發生客觀效果的時候,我們才能有根據和可能檢驗他的動機。正如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說的,『社會實踐是檢驗主觀願望的標準,效果是檢驗動機的標準。』而效果的好壞則是以對人民有利或有害爲標準的。爲人民的動機與有利於人民的效果,必須統一起來。一個人的動機如果只是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那末,他就必然對自己所做的事情採取對人民十分負責的態度,而一當他發現自己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於人民不利的時候,他就立刻加以改正。一個人能否揭露並改正自己的錯誤缺點,這是檢驗他的動機是否眞好的最重要的標準。批評與自我批評,就是使爲人民的動機與有利於人民的效果統一起來的最可靠的良好的方法。凡是觀察事情不從唯物的、羣眾的觀點出發而從唯心的、個人的觀點出發的人,總是喜歡片面地強調動機,而忽視效果。凡是不願或不肯認眞地實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人又總是喜歡拿『動機』來做擋箭牌。
電影『武訓傳』及一切武訓宣傳者都特別歌頌了武訓的精神,甚麽『三十年如一日』啦,『忘我精神』啦,『毅力』啦,『苦行』啦,在電影『武訓傳』中,更把武訓的精神和馬列主義者所主張的『爲人民服務』的偉大思想混同起來。從這裏,就產生了電影『武訓傳』的最迷惑人的效果。
(本文轉入第四版)
(本文由第三版轉來)
人們同情着和讚歎着武訓的苦行。但是祗要稍稍分析一下,就可看出他的苦行祗不過是變戲法的訛詐手段(如吃五毒、吃瓦片、喝髒水等)和磕頭下跪的奴隸行爲的混合罷了,至於吃粗糧、宿破廟、不娶妻等等,姑無論武訓的實際行爲是否如此,這些事實本身又算得了甚麽苦行呢?如果這些都叫苦行,那麽全國千千萬萬勞動人民不是更大的苦行者嗎?
馬列主義者是反對個人苦行的,這不祗是因爲苦行違反人的生活的自然規律,而且更重要的是這種個人苦行不但不能解除或減輕羣眾的苦難,反而加深羣衆的苦難。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羣衆每天過着痛苦的生活,他們苦得够了,不再需要甚麽苦行,他們所渴望的是及早地儘可能地解除或減輕自己的痛苦。祇有少數吃飽了飯,活得無聊的人才提倡苦行,從別人受苦中尋找自己的快樂。祇有反動的藝術家,才把被壓迫人類的痛苦加以美化。
不錯,我們從來提倡艱苦奮鬥的作風。但我們决不是爲吃苦而吃苦,更不是以自苦爲樂,而是為了要把全世界受苦的人們解放出來,引導他們到幸福的生活去,這樣一個偉大的崇高的目的;正是被這個目的所鼓舞,我們才能够經受得起一切痛苦和磨難的考驗,直至犧牲自己的生命。這種艱苦奮鬥是跟任何不敢反抗不敢革命不敢犧牲生命的所謂『苦行』完全不同或完全相反的。正是因爲這樣,古今中外的反動統治者既不宣傳整個勞動人民的痛苦,更不宣傳革命家的犧牲,即願意宣傳那種對統治者無害因而統治者也無須去加害的以『苦行』招搖的個人。不少知識分子由於沒有經歷過羣衆鬥爭的大世面,羣眾鬥爭的大風雨,總是不能完全體味羣眾苦難的深沉和羣眾鬥爭的偉大,而祗醉心於各式各樣的個人的苦行及其功,他們不知道任何個人脫離羣眾就要成爲沒有力量的,也不可能有任何眞正的成就。
電影『武訓傳』特別强調武訓具有魯迅所說的『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孫瑜在『編導「武訓傳」前後』一文中說:『魯迅先生的這一名言自始至終地都寫在我的劇本上。』但是在事實上,武訓並沒有向勞動人民俯首,更沒有成爲勞動人民的『牛』,相反,他只是要求『孺子甘爲俯首牛』,向地主階級俯首,也向武訓本人俯首。而且,魯迅的詩是兩句,他的上句是『橫眉冷對千夫指』,孫瑜却故意隱瞞了。對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對人民的敵人,即使是最兇惡的敵人,决不低頭。這就是魯迅的這兩句名詩的不可分的含義。也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對己要和,對敵要狠。』祗有兩方面結合起來,才能成爲革命者,才是『爲人民服務』的正確的完整的觀念。武訓宣傳者,把『爲人民服務』的口號庸俗化了,割掉了它的階級的革命內容。『為人民服務』,第一,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有具體階級內容的,充滿戰鬥性的口號。不能籠統地來看人民,而必須分析人民這一槪念中是包含了幾個階級的;爲人民服務,就必須首先爲工農羣眾服務,因爲他們構成人民中的最大多數;他們是生產者,而工人又是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階級。第二,爲人民服務,必須對人民的各種敵人進行堅决的鬥爭,幫助人民打倒壓在他們頭上的反動派,清除反動派在人民中間所散佈的影響。毛澤東同志這樣地描寫着魯迅的性格:『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奴顏與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寳貴的性格。』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毛澤東同志又這樣描寫了一個眞正革命者所應當具備的氣概:『在野獸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我們要學景陽岡上的武松。』我們所需要的就是魯迅式的頑固性格,武松景陽岡打虎的勇敢精神。任何場合,我們都是反對對敵人磕頭的;那是一種下賤的、奴隸式的叛徒的行爲。『為人民服務』的戰鬥的口號必須和資產階級的虚僞的服務精神區別開來。
為歷來武訓宣傳者所頌揚的武訓一生的主要事蹟,就是『行乞』『興學』和『苦行』,電影『武訓傳』就把這些本來是落後的、反動的,但尙能迷惑人的事蹟再加上一層更迷惑人的、前進的革命的外衣,於是『行乞』變成勞動,『興學』變成對封建統治者的反抗鬥爭,『苦行』變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榜樣。把武訓這樣地理想化了之後,孫瑜先生還說他對武訓是用『批判的眼光』來描寫的,他把歷史的修改說成歷史的批判;把對武訓的巧妙的歌頌說成批評。他在『編導「武訓傳」前後』一文中說:『除了歌頌武訓的忘我精神以作服務人民的榜樣之外,影片裏批評了他的改良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的作風。』既然是『個人英雄主義』,爲甚麽又有可以作服務人民的榜樣的『忘我精神』呢?這兩者難道可以並存,可以相通嗎?作者在這段話裏如果不是說了雙層的假話就是陷進了雙重的錯誤:第一、武訓所走的並不是甚麽改良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的道路,而是十足的投降主義和奴才主義的道路;第二、作者在影片中並沒有批評改良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而是恰恰相反借武訓的所謂『行乞興學』的事蹟大大地鼓吹了落後的、反動的社會改良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武訓傳」電影主題的反動性主要也就在這裏。
關於武訓的反動宣傳都是有它歷史的、社會的根源的。
反動統治者,從滿淸王朝到蔣介石,他們如出一轍地先後表揚武訓,是不足爲怪的,因爲武訓正是適合維護他們的反動統治的一個有用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褒揚武訓,都是在他們感到自己的統治搖搖欲墜的時候。滿清朝廷准給武訓『樂善好施』字樣,作爲旌奬,是在一八八八年,正當太平天國之後二十四平,辛亥革命之前二十三年,那時封建秩序遭受了農民大革命浪潮的衝擊,正迅速地開始瓦解,而農民大革命正成了迎接歷史新時代的先聲。國民黨反動派在一九三四年發動武訓九十七週誕辰紀念的運動,蔣介石特爲從當時反革命軍事中心地的南昌行營給武訓紀念題字,以及一九三八年國民黨反動政府由林森、孔祥熙、何鍵、陳立夫會簽正式頒佈褒揚武訓的命令,正是在全國人民走向抗日高潮,人民革命力量經過曲折向前發展的時候。這說明了:反動統治者到了自己快要滅亡的時候,就好像一個人掉在水裏一樣,抓住一切浮在水上、能够抓到手的東西來挽救自己的覆沒,武訓就是在農民革命浪潮中捲起的渣滓而被反動統治者常作寶貝抓住的。
現在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以自己英勇的、頑强的、堅决的鬥爭推翻了內外壓迫者,爲歷來反動統治階級所表揚的武訓在新中國人民中應當再沒有他的地位了。爲甚麽關於武訓的宣傳不但沒有斂跡,反而盛行起來呢?這就是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的表現,這些思想在今天中國還有它的市場。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資產階級一方面不滿意這個統治的專橫殘暴,另一方面,又不相信並且害怕羣衆的力量,因此就不敢向反動統治階級堅决地進行鬥爭,而時常企圖尋找一個可以不經過鬥爭而得到改良的局面。
陶行知晚年成為了一個革命的民主派,但在提倡武訓這件事情上面却表現了他早年的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表現了他在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中的脆弱的一面。
在中國人民取得了全國性勝利之後,資產階級參加了人民民主政權,但他們中間却仍有一部分—人對於已經或正在死亡的舊制度、舊事物時常感到惋惜和留戀,而對於新生的事物表示冷淡和懷疑,對於人民革命更深入的發展則流露出彷徨恐懼的情緒。正如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所說的:『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規定了他們的軟弱性,他們缺乏遠見,缺乏足够的勇氣,並且有不少人害怕民衆。』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就有一種特別的責任,必須和資產階級破壞或妨礙人民民主專政的各種反動的錯誤的思想進行嚴肅的、堅决的鬥爭,肅淸其在人民内部,特別是在人民的先進分子中,共產黨員中的影響。在每個比較嚴重的政治鬥爭中,必須反對各式各樣的改良主義投降主義的思想,否則鬥爭就不能勝利前進。在抗美援朝運動中,我們首先反對了親美、恐美、崇美的思想;土地改革中首先反對了『和平分田』的思想;鎭壓反革命運動中,首先反對了『寬大無邊』的思想。
電影『武訓傳』就是資產階級的反動的改良主義思想在藝術上的表現之一。
電影借武訓的所謂『行乞興學』的事蹟用藝術的力量宣傳了這樣的改良主義思想:不觸動舊的社會經濟基礎,不破壞舊的政治制度,祇要在人民中普及文化教育,就可以根本改變人民的被壓迫的地位。旣然人民祗要有了文化就能解放,那自然就用不着羣眾的革命武裝鬥爭了。
電影中花了一千尺以上膠片來表現的武訓做夢的場面(孫瑜電影小說『武訓傳』中的所謂『狂想三部曲』)正是表現了作者的主題思想的。
作者在這幻夢和狂想中,描繪着人類社會的歷史:
『呻吟輾轉在脚底、在長鞭的尖端,流汗、流血的是萬千的農民……像牛像馬在染血的重枷鉄鍊下沉重的拉着犂,推着磨……」
『巨磨張着大嘴吞噬着無數的生命……血流成了紅河;骨肉壓榨成黏滯的醬……勞苦的人羣世世代代地永遠轉不出那黑暗痛苦的輪迴……張舉人的獰笑,忽然間把巨磨變成大石硯,黑墨磨動時濺出毒汁,飛灑在大羣「文盲」的眼睛裏:…』
『男、女、老的、小的……伸着手,扶着杖,用力睜着他們的看不見事物的雙眼,在人的「奈何橋」上戰戰兢兢地摸索着走,左邊是陡削的懸崖,右邊是無底的深淵,後面有張舉人拿着尖刀的筆;趙熊、魏俊披頭散髮,舉起大筆和巨墨在驅趕,前面獨木橋下括起陣陣的陰風和凄厲的哀號……。』
『「你們這些不識字的畜生,」舉人魔鬼在笑喊、「你們這些睜眼瞎子!我把你們都打下苦海,叫你們永世不能翻身!哈哈……」』(電影小說:『武訓傳』一〇一頁)
原來,農民的痛苦生活並不是由於封建地主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對他們的壓迫和剝削的結果,而祗是由於農民被地主階級剝奪了受敎育的權利,農民自己沒有文化,不識字,他們的眼睛『看不見事物』。那末有什麽辦法『翻身』呢?就祗有『學文化』了。
當武訓在夢中聽到義學的時候,他狂喜得大叫起來:『這不是從地底飛上了天嗎?……』他舉臂高呼:『窮孩子們,快跟我唸書去!』武訓從這個快樂的夢中驚醒,張目四望,就『好像來到了一個新的光明的世界。』不識字的,活該入地獄,唸了書可以上天堂。這就是電影『武訓傳』的中心思想。『唸了書才可以多知道世上的事情;才可以找着過好日子的道路。……』這一段被作者形容爲『包含着淵博的智慧』的老師的言語,難道不正是作者自己心中的言語,作者自己的思想嗎?
這種思想倒也不是甚麽新奇的東西。
列寧早在一九二三年所寫的『論我國革命』的一文中,就在關於文化與革命的關係問題上,嚴厲地批判了當時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人,那些『怯懦畏縮的改良主義者』的老爺們,他們死咬着實行社會主義一定要先有相當文化水平,列寧尖銳地反駁說:爲甚麽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造成這個相當文化水平的必要前提,即首先驅逐地主和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後向社會主義前進呢?他在同一年所寫的有名的『論合作制』一文中,也說在革命以前,工作重心祗能放在政治鬥爭、革命和奪取政權上面,而祗有在革命以後,工作重心才能移到和平的廣泛的文化建設的事業上來。當然列寧是正確的。俄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完全證實了他的預言。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所寫的有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也說過:
『中國歷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農民造成的,因爲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從農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敎育的人民,這個裏面,最大多數是農民。農村裏地主勢力一倒,農民的文化運動便開始了。………農民運動發展的結果,農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時間內,全省當有幾萬所學校在鄕村中湧出來,不若知識階級和所謂「敎育家」者流,空喚「普及敎育」,喚來喚去還是一句廢話。』
當然毛澤東同志是正確的,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完全證實了他的預言。
中國革命的經驗就是這樣的:首先發動農民武裝鬥爭,在廣大農村中推翻反動統治,建立革命根據地;然後在這個根據地上面逐步地發展人民的經濟和文化。現在,由於中國人民的全國性的勝利,特別是土地改革在全國實行,農民的文化獲得了歷史上從來未有的迅速的廣大的發展。可以斷定:在不久的將來,正如毛澤東同志在『中國人民政協第一届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詞』中所預言的,『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
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一個在歷史上曾經比歐洲其它資本主義先進國家文化落後,文盲衆多的沙皇俄國和一個在古代有過燦爛的文化,但在近代落伍了,文化落後,文盲特別衆多的中國,正是西方和東方的這兩個國家,首先取得了革命的大勝利。蘇聯現在不但成了世界上文化最發達的國家,而且正站在全人類文化的最高峯,指引世界人民前進的方向;新中國的新的人民的文化正在突飛猛進之中。道理是很簡單的:社會主義革命和人民革命創造了人民文化無限發展的前提。
不錯,孫瑜先生在『我怎樣表現武訓的「夢」』一文中說了:『單憑念書而不革命,不奪取政權,窮人受壓迫的命運是無法改變的。』但是,第一,一個藝術家的口頭上的表白,和他在藝術作品中所實際表現的有時並不完全是一回事,而且在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往往是作者的更眞實的思想和情感,讀者又是祗能從作品出發來判斷作者的;第二,社會民主黨也好,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也好,他們一般地在口頭上都不否定革命,他們倒是裝出十分愛護革命的樣子,他們說羣衆要革命,先要有文化,這樣從實際上來否定革命。電影『武訓傳』,正是宣傳了這種錯誤思想。
電影『武訓傳』寫了以武訓爲代表的『義學』運動,同時也寫了以周大為代表的農民革命,用作者的話,叫做『一武一文』,互相配合。但是這不但沒有能够挽救,而且更加深了電影『武訓傳』主題思想的錯誤。武訓和周大之間的友誼是一種完全違反歷史事實的揑造,因爲很顯然地,反動派和革命派之間是不可能建立那樣的友誼和事業上的合作關係的。作者在這裏不過是以周大作武訓的反襯,以誇大農民武裝鬥爭的失敗的和弱點的一面,來襯托武訓精神的偉大和他的興學事業的至少某種程度上的成功。這樣,就使電影『武訓傳』主題的反動性更加明顯了。
武訓生長在中國農民革命浪潮起伏的時期;山東多年都是捻軍活動的主要地區之一,就在他所出生的山東堂邑就有過農民武裝起義。一八六〇年,在邑堂柳林鎭距武訓的村子武莊不過七里地的另一個叫做小劉貫莊的村子裏,爆發了以著名的宋景詩爲首的農民起義。距武莊五里地的柳林鎭則是地主反革命武裝的堡壘。柳林的民團是最兇惡、最頑固的;團長不是別人,正是支持武訓辦成第一所義學、在電影中被描寫爲『開明士紳』的柳林地主楊樹坊的叔父楊鳴謙,楊鳴謙被宋景詩打死後不久,就由楊樹坊繼承了他叔父的這個反革命的民團團長的職務。宋景詩活動的期間,正常武訓二十多歲的時候,他沒有投奔宋景詩,却投奔了楊樹坊,他就這樣選擇了他的反革命的道路。據武訓歷史調查團的調查,當地年老農民至今懷念着他們當年革命的領袖,一提起宋景詩便眉飛色舞,講得津津有味,而一提到武訓,便表示沒有興趣和冷淡。這就可以看出農民階級的眞實感情,他們的明確的是非和熱烈的愛憎。我們當然不知道電影中的周大是否影射宋景詩,但是,無論如何,電影中的周大或實有其人的宋景詩和武訓之間,除了農民和地主、革命和反革命之間的不可調和的敵對的關係之外,是不可能再有任何其它的關係的。(未完)
兩個月來,許多同志對電影『武訓傳』、『武訓畫傳』及其它一切關於武訓的反動宣傳進行了嚴正的批判。最近發□『武訓歷史調查記』以無可辯駁的邏輯的力量作出了關於武訓問題的科學結論,並且在歷史研究工作、社會調查工作和文藝批評工作的方法上做了很好的示範。我自己很早就看了電影『武訓傳』,但並沒有能够充分地認識和及早地指出它的嚴重的政治上的反動性。雖然我在三月間舉行的第一届全國文化行政會議上對這電影作了批評,但現在看了許多同志的文章和材料之後,感覺着我當時的批評是極其不够的。現在,武訓的歷史已經完全清楚了;但對於引起這次論爭的電影『武訓傳』本身,却還需要就它的思想和藝術作系統的批判。我的這篇文章就是為這個目的寫的。
兩種歷史觀
電影『武訓傳』是一部關涉中國近代歷史的傳記影片。對待歷史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爲:歷史不是由階級和階級鬥爭造成的,而是由少數所謂先知先覺者造成的;社會的黑暗不是由於不合理制度的存在,而是由於人民自己沒有敎育,沒有文化,因此要改造社會,可以無需經過人民羣衆的革命鬥爭,推翻舊制度,建立新制度,祗需給人民以敎育和文化,就可以達到新的光明的世界。因此歷史的創造者和推動者,主要地不是勞動人民,而是有文化敎養的人們以及熱心於在人民中傳播『敎育』『文化』的人們。這是一種反人民、反科學的歷史觀點。宣傳這種觀點就是在思想上解除羣衆的武裝,散佈幻想,叫羣衆發生一種錯覺,以為在舊社會的制度下不經過羣衆的革命的方法而經過某些改良的方法就可以使他們的生活狀况獲得根本的改善。孫瑜在電影『武訓傳』中就是用藝術的手段巧妙地宣傳了這種思想。他把武訓的「興學」描寫爲勞動人民求解放的最可靠的道路。於是他就把武訓——這個封建社會中最醜惡、最虛僞、最反動的奴才,這個腐爛的封建文化的狂熱宣傳者——描寫爲『向封建統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鬥爭』的堅靭的革命戰士,不,簡直描寫爲一個神聖化了的人物:他『在雲端向下界微笑,給正得着解放的本階級勞動同伴們祝福』呢。就這樣,這個歷史上的反動派就成了中國人民的革命祖先,而解放了的中國人民就成了武訓事業的繼承者。這對於具有光榮革命傳統,今天正站在全世界反帝國主義鬥爭的最前綫英勇地、堅决地戰鬥着的中國人民,難道不是絕大的汚衊嗎?這種汚衊難道是能够容忍的嗎?
另一種與上述觀點完全對立的觀點,認爲:人類社會的基礎既然是由生產組成的,那末人類社會歷史的創造者,首先就是生產物質財富的勞動人民。勞動人民在他們每天創造物質財富的當年,不斷地創造歷史。特別在歷史的轉變關頭,當新的社會力量起來和舊的社會力量進行鬥爭的時候,决定鬥爭的結局的總是廣大的人民羣衆。人民羣衆是歷史的主要推動者。歷史上的每一個重大的進步或變革都必須經過人民羣眾的嚴重鬥爭,而不是單靠少數所謂先知先覺者所能完成的。任何英雄好漢,祗有當他正確地代表了歷史的前進方向,代表了或至少在某些重要方面代表了廣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時候,才能成為眞正的英雄好漢。如果違背了歷史的前進方向,違背了廣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不管他具有怎樣的個人品質,怎樣的才能、毅力,甚至有怎樣的『奇行特操』,都祗能成為可憐可笑的人物,最後終將被抛人歷史的垃圾箱中去。只有根據這種觀點來衡量和估價歷史人物,這才是正確的。因此,我們的文學藝術,祇能歌頌那些推動歷史前進,對人民有貢獻的人物,而决不應歌頌歷史上的反動派,或對人民毫無貢獻的人物。我們特別尊重自己民族的革命傳統,我們要把人民今天的鬥爭和過去的革命傳統正確地連結起來,因此我們决不能容忍對人民革命傳統的任何歪曲或侮蔑。許多同志批評電影『武訓傳』及其它關於武訓的錯誤文章,主要地就都是從這個根本點出發的。這是人民的、科學的歷史觀點。
人民的、科學歷史觀點和反人民、反科學的歷史觀點,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和賢產階級反動思想的區別。
許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徘徊在兩者之間,他們雖承認人民羣眾的革命鬥爭在歷史上的作用,但對這種作用的認識往往是抽象的,估計往往是不足的。又由於他們個人的出身和敎義,他們在解釋具體歷史現象或社會現象的時候,往往就自覺或不自覺地把文化看得高於一切,把個人的力量看得高於羣衆的力量,而特別有興趣於個人的奮鬥和成就,甚至個別的所謂『奇人奇事」。這和中國工業不發達,小生產佔絕對優勢,小資產階級衆多,文化落後的狀况是有很大關係的。這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形成了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盲目讚揚者的社會基礎。他們的盲目讚揚武訓和『武訓傳』,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受了關於武訓的反動宣傳的欺騙,另一方面也正是因爲這種反動宣傳恰好乘了他們缺乏歷史觀點和缺乏羣衆觀點的弱點,投合了他們的知識分子的個人主義的思想、情緒和心理。這就是爲甚麽在武訓的眞面目已經被揭露之後,還有一些人要找各種理由為武訓辯護,有些人甚至在理性上否定了武訓,在感情上還是同情他。
那末,究竟武訓和電影『武訓傳』有些甚麽地方那麽迷惑人呢?
武訓和電影『武訓傳』
迷惑人的地方在哪裏?
武訓並不是歷史上的什麽重要人物,他不過是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的各色各樣的奴才之一,但他却是其中的一個比較特殊的、帶有特別的虛僞性和欺騙性的奴才。電影『武訓傳』就以歷史的僞造和藝術的渲染把他描畫成一個革命人物和民族英雄。於是一具封建殭屍穿上了革命的衣服大搖大擺地走進人民的行列,在人民當中散佈毒素。因此我們要批判電影『武訓傳』,首先就必須揭露武訓的眞實面目。許多批評者從各方面進行了這個揭露的工作,而武訓歷史調查團則更作了一個關於武訓的全面的、澈底的揭露。
武訓和電影『武訓傳』有它迷惑人的地方。自然,許多人被迷惑,還不祗是因爲對武訓歷史眞相不明瞭的原故,而主要的,是由於缺乏以馬列主義觀點辨別事物的能力。
武訓出身貧農,從乞丐變爲高利貸者兼地主,他一生的歷史,基本上就是一個寄生者、剝削者的歷史。根據武訓歷史調查團的調查,在武訓的整個一生中,他祇有過一年多時間的勞動,而且他所從事的又只是一些鍘草、推磨之類的比較輕微的勞動,而不是生產中的主要勞動。在他的行乞生活中雖然有時也仍做些鍘草、推磨的工作,但那已不過是他行乞生活中的一種點綴,或者如同他的變戲法一樣,是行乞的一種節目而已。他事實上已經完全脫出了農民階級的軌道,而成爲了一個職業的乞丐,並且是一個耍着各種無賴手段的惡丐。電影『武訓傳』却把他描寫為勞動人民的忠實的兒子,特別强調他的終生勞動,說他『除去在破廟裏睡着了的時間以外,他的兩手從不休息』,這樣就把他的生活的墮落的寄生的性質掩蓋起來了。但是如果我們用科學的,階級的觀點觀察問題的話,那末,乞丐所屬的遊民階層是和工人農民眞正勞動階級不相干的。遊民是寄生者,又具有很大的破壞性,他們很容易變成爲反革命的工具,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以前寫的『共產黨宣言』中就講了的。事實上歷來反動統治者也總是從遊民階層中去物色、培養和提拔他的走狗的。武訓的歷史道路,也恰巧證明了這條眞理。武訓不是一個普通乞丐,而是一個打着『興學』旗幟的政治乞丐。他有了這個旗幟,不但行乙方便得多,而更重要的是找着了和封建統治階級通氣的門路。他果然得到了豪紳地主官吏的贊助和支持,使他辦起了所謂『義學』,他自己也成為了地主兼高利貸者。但他和普通地主是不一樣的。他雖然已經是一個三百多畝土地的所有者,而且以超過當時最高標準的利率放債,但是他的土地名義上是學田,而他的收租放債又都假『興學』之名以行,因而就在世人眼中掩蓋了他地主兼高利貸者的剝削者的身份。封建地主原是各式各樣的:有廟田所有者的宗敎地主,與武訓合作辦第二所『義學』的了證和尚就屬於這一類地主;也有學田及其它公田所有者的政治地主,武訓就是這樣的一個政治地主。武訓打着『興學』旗幟,憑仗着地主豪紳官僚的勢力,佔有了大量的土地和高利貸資本,放肆地對農民進行無情的殘酷的剝削。當地的貧苦農民叫武訓為『財迷』。武訓的剝削行為,就在讚揚他的許多傳記裏,也不能不透露一些出來,但在電影裏却完全被掩蓋了。武訓對家庭所表示的態度:『我的事,你別管,兄弟分家不相干』,『不顧親,不顧故』,『親戚朋友斷個淨』,並不是如一些武訓讚揚者所說的那樣,表現了武訓在親屬關係上的大公無私,而恰是表現了作爲地主兼高利貸者的武訓在對農民(包括他自己的親兄弟在内)的剝削關係上的冷酷和堅决。這可以看做是武訓背叛他所出身的農民階級而投降地主階級的决心書。從此,武訓交上了婁峻嶺、楊樹坊、施善政之流的大豪紳地主惡霸,而成爲了他們的座上賓。
武訓的利害還在於他雖然成了地主兼高利貸者,却始終穿着乞丐的衣服,並在行乞與强化佈施中繼續使用各種無賴的手段,他成爲一個穿着乞丐衣服的流氓政治地主。因爲如果脫下這衣服,他的欺騙作用就要失去,至少要大大地減少了。但是如果我們在確定一個人的階級成份的時候,不根據一個人表面的生活形態,而只根據他對生產資料的佔有關係的話,那末,對於武訓的鑑定除了他是地主兼高利貸者這個結論之外,就不能再有任何其它的結論了。
武訓的更迷惑人的地方,是他的『興學』的事蹟。武訓的『興學』,加上他的印發善書,獎勵節孝等等,本來完全是宣傳最反動的腐朽的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死心塌地地爲封建地主階級服務的;但是電影『武訓傳』却把他的『興學』描寫成反對封建地主統治,爲農民求解放的義舉。武訓被描寫成了『腦筋一點也不封建』,而且『堅靭地、百折不撓地和封建統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鬥爭』的革命英雄。這是一個絕大的誑騙。『興學』的口號是能够騙人的,不但在武訓生前,而且就在他死後的今天,這個口號還有迷惑人的力量。
『辦敎育總是好事』,許多武訓的擁護者和同情者這樣說,好像否定武訓就是輕視敎育似的。我們應當重視敎育,但不應當把敎育看成超階級、超政治的。斯大林同志在『與英國作家威爾斯的談話』中,有一段話說得非常好:
『敎育是一種武器,其效能是依誰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用這個武器去打擊誰爲轉移的。當然,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是需要受過高等敎育的人的。很明顯的,只要不是最愚蠢的人,都可以幫助無產階級去爭取社會主義,建立新社會。我並不輕視知識分子的作用,相反的,我更側重他們的作用。問題只在於說的是那一種知識分子,因爲知識分子是各色各樣的。』
事實很清楚,武訓所辦的『義學』是完全掌握在封建地主手中的。興辦『義學』,並不是武訓的甚麽創舉。早在淸初的時候,封建統治者就在各地辦了許多『義學』。那位一隻手血淋淋地鎭壓農民革命,另一隻手提拔武訓的山東巡撫張曜就是『義學』的積極提倡者。那末這種所謂『義學』,究竟是『打擊誰』,是打擊地主,還是打擊農民的呢,由這種『義學』所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究竟是擁護農民利益的,還是擁護地主利益的呢,難道不是一眼可以判斷出來的嗎?武訓自己也唱了:『壞人多,好人少,辦個義學錯不了。』武訓的『興學」就正是迎合了當時封建統治者籠絡人心的反動政策,因而『義學』就成了他投降封建統治階級並使自己也爬上地主階級行列中去的政治資本。
『在封建社會裏,祇能辦封建敎育,不能苛責武訓。』武訓的擁護者和同情者又這樣辯護着說,好像否定武訓就是否定一切過去時代的敎育似的。
我們並不一般地否定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敎育,並且承認敎育在各個歷史時代中的一定作用,而新敎育又正是從舊敎育發展來的。在這一點上,我們不但要將武訓和陶行知相區別,而且也要將武訓和孔子相區別,陶行知的道路是從一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發展爲革命的民主主義者的道路,他的敎育學說中有不少觀念論的因素,這是他的思想上的弱點。他錯誤地讚揚武訓就正是他的這種思想上的弱點的表現之一。但就他整個的政治傾向和他在晚年努力使他的敎育活動的內容革命化的事實來說,他無疑地是中國人民的傑出的敎育家之一。武訓是不能和他相提並論的。孔子是封建社會的偉大的敎育家;他與武訓不同,不祗因爲他生在二千多年前正當封建制度興盛,封建文化放出燦爛異彩的時代,而武訓所處的時代,則是封建統治基礎已面臨最後崩潰,而作爲這個基礎的上層建築物的封建文化已腐爛到喪失任何生命力的時代;而且也因為孔子在敎育思想和敎育方法上有卓越的貢獻,而武訓則不過是以『興學』做幌子,對敎育一無所知、一無所能的一個騙子而已。有些敎育工作者把武訓這樣一個人物放在敎育史上和陶行知、孔子並列,甚至高過陶行知、孔子的地位,這實在是敎育界的一件恥辱的事情。
『武訓爲窮孩子「興學」,他的動機總是好的。』這是為武訓辯護的一個最普遍、最動聽的理由了。電影『武訓傳』就肆意渲染了武訓爲着窮孩子的一片苦心。
武訓的動機是否眞爲窮孩子『興學』,這就不能單單根據武訓所打出的『興個義學爲貧寒』的招牌,而且具體考察武訓所辦的『義學』的實際內容和效果。
本來,武訓的『義學』,不論是從經費來源、敎學內容,學生成份來說,都是一開始就完全掌握在地主階級手中的。電影『武訓傳』却偏偏要說成是在武訓死後才被地主們搶過去的。武訓的興學本來是以『又有名,又行好,文昌帝君知道了,準敎你子子孫孫坐八抬大轎。』爲號召的,電影却揑造一些這樣相反的場面:武訓聽到學生讚『學而優則仕』,他的内心那樣地感到彷徨和痛苦;他流着淚再三叮嚀他的學生:『你們唸好了書,千萬不能忘記咱們窮人!』最後他又那樣充滿信心地說:『我不能休息!不等到每一個窮孩子都有書唸,都有飯吃的時候……我是不會休息的。』這一切描寫無非是要叫觀衆相信,不管『義學』的客觀效果如何,武訓的一顆赤熱的心始終是爲窮孩子的,爲着農民的。事實眞是這樣嗎?祗消舉出一個材料就可以解答這個問題了。據武訓歷史調查團的調查,武訓所辦的第一所學校『崇賢義塾』,頭七年,根本沒有蒙學,只有經班,而經班的學生全都是地主富農商人子弟,貧苦農民子弟是入不了經班的。武訓的心如果眞是爲窮孩子,那末,七年之久,他的學校中沒有窮孩子,他難道看不見嗎?很顯然,他的心中是根本沒有什麽窮孩子的地位的。
動機本來是主觀存在的東西,只有當一個人的主觀動機變爲行動而發生客觀效果的時候,我們才能有根據和可能檢驗他的動機。正如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說的,『社會實踐是檢驗主觀願望的標準,效果是檢驗動機的標準。』而效果的好壞則是以對人民有利或有害爲標準的。爲人民的動機與有利於人民的效果,必須統一起來。一個人的動機如果只是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那末,他就必然對自己所做的事情採取對人民十分負責的態度,而一當他發現自己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於人民不利的時候,他就立刻加以改正。一個人能否揭露並改正自己的錯誤缺點,這是檢驗他的動機是否眞好的最重要的標準。批評與自我批評,就是使爲人民的動機與有利於人民的效果統一起來的最可靠的良好的方法。凡是觀察事情不從唯物的、羣眾的觀點出發而從唯心的、個人的觀點出發的人,總是喜歡片面地強調動機,而忽視效果。凡是不願或不肯認眞地實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人又總是喜歡拿『動機』來做擋箭牌。
電影『武訓傳』及一切武訓宣傳者都特別歌頌了武訓的精神,甚麽『三十年如一日』啦,『忘我精神』啦,『毅力』啦,『苦行』啦,在電影『武訓傳』中,更把武訓的精神和馬列主義者所主張的『爲人民服務』的偉大思想混同起來。從這裏,就產生了電影『武訓傳』的最迷惑人的效果。
(本文轉入第四版)
(本文由第三版轉來)
人們同情着和讚歎着武訓的苦行。但是祗要稍稍分析一下,就可看出他的苦行祗不過是變戲法的訛詐手段(如吃五毒、吃瓦片、喝髒水等)和磕頭下跪的奴隸行爲的混合罷了,至於吃粗糧、宿破廟、不娶妻等等,姑無論武訓的實際行爲是否如此,這些事實本身又算得了甚麽苦行呢?如果這些都叫苦行,那麽全國千千萬萬勞動人民不是更大的苦行者嗎?
馬列主義者是反對個人苦行的,這不祗是因爲苦行違反人的生活的自然規律,而且更重要的是這種個人苦行不但不能解除或減輕羣眾的苦難,反而加深羣衆的苦難。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羣衆每天過着痛苦的生活,他們苦得够了,不再需要甚麽苦行,他們所渴望的是及早地儘可能地解除或減輕自己的痛苦。祇有少數吃飽了飯,活得無聊的人才提倡苦行,從別人受苦中尋找自己的快樂。祇有反動的藝術家,才把被壓迫人類的痛苦加以美化。
不錯,我們從來提倡艱苦奮鬥的作風。但我們决不是爲吃苦而吃苦,更不是以自苦爲樂,而是為了要把全世界受苦的人們解放出來,引導他們到幸福的生活去,這樣一個偉大的崇高的目的;正是被這個目的所鼓舞,我們才能够經受得起一切痛苦和磨難的考驗,直至犧牲自己的生命。這種艱苦奮鬥是跟任何不敢反抗不敢革命不敢犧牲生命的所謂『苦行』完全不同或完全相反的。正是因爲這樣,古今中外的反動統治者既不宣傳整個勞動人民的痛苦,更不宣傳革命家的犧牲,即願意宣傳那種對統治者無害因而統治者也無須去加害的以『苦行』招搖的個人。不少知識分子由於沒有經歷過羣衆鬥爭的大世面,羣眾鬥爭的大風雨,總是不能完全體味羣眾苦難的深沉和羣眾鬥爭的偉大,而祗醉心於各式各樣的個人的苦行及其功,他們不知道任何個人脫離羣眾就要成爲沒有力量的,也不可能有任何眞正的成就。
電影『武訓傳』特別强調武訓具有魯迅所說的『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孫瑜在『編導「武訓傳」前後』一文中說:『魯迅先生的這一名言自始至終地都寫在我的劇本上。』但是在事實上,武訓並沒有向勞動人民俯首,更沒有成爲勞動人民的『牛』,相反,他只是要求『孺子甘爲俯首牛』,向地主階級俯首,也向武訓本人俯首。而且,魯迅的詩是兩句,他的上句是『橫眉冷對千夫指』,孫瑜却故意隱瞞了。對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對人民的敵人,即使是最兇惡的敵人,决不低頭。這就是魯迅的這兩句名詩的不可分的含義。也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對己要和,對敵要狠。』祗有兩方面結合起來,才能成爲革命者,才是『爲人民服務』的正確的完整的觀念。武訓宣傳者,把『爲人民服務』的口號庸俗化了,割掉了它的階級的革命內容。『為人民服務』,第一,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有具體階級內容的,充滿戰鬥性的口號。不能籠統地來看人民,而必須分析人民這一槪念中是包含了幾個階級的;爲人民服務,就必須首先爲工農羣眾服務,因爲他們構成人民中的最大多數;他們是生產者,而工人又是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階級。第二,爲人民服務,必須對人民的各種敵人進行堅决的鬥爭,幫助人民打倒壓在他們頭上的反動派,清除反動派在人民中間所散佈的影響。毛澤東同志這樣地描寫着魯迅的性格:『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奴顏與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寳貴的性格。』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毛澤東同志又這樣描寫了一個眞正革命者所應當具備的氣概:『在野獸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我們要學景陽岡上的武松。』我們所需要的就是魯迅式的頑固性格,武松景陽岡打虎的勇敢精神。任何場合,我們都是反對對敵人磕頭的;那是一種下賤的、奴隸式的叛徒的行爲。『為人民服務』的戰鬥的口號必須和資產階級的虚僞的服務精神區別開來。
為歷來武訓宣傳者所頌揚的武訓一生的主要事蹟,就是『行乞』『興學』和『苦行』,電影『武訓傳』就把這些本來是落後的、反動的,但尙能迷惑人的事蹟再加上一層更迷惑人的、前進的革命的外衣,於是『行乞』變成勞動,『興學』變成對封建統治者的反抗鬥爭,『苦行』變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榜樣。把武訓這樣地理想化了之後,孫瑜先生還說他對武訓是用『批判的眼光』來描寫的,他把歷史的修改說成歷史的批判;把對武訓的巧妙的歌頌說成批評。他在『編導「武訓傳」前後』一文中說:『除了歌頌武訓的忘我精神以作服務人民的榜樣之外,影片裏批評了他的改良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的作風。』既然是『個人英雄主義』,爲甚麽又有可以作服務人民的榜樣的『忘我精神』呢?這兩者難道可以並存,可以相通嗎?作者在這段話裏如果不是說了雙層的假話就是陷進了雙重的錯誤:第一、武訓所走的並不是甚麽改良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的道路,而是十足的投降主義和奴才主義的道路;第二、作者在影片中並沒有批評改良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而是恰恰相反借武訓的所謂『行乞興學』的事蹟大大地鼓吹了落後的、反動的社會改良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武訓傳」電影主題的反動性主要也就在這裏。
關於武訓的反動宣傳都是有它歷史的、社會的根源的。
反動統治者,從滿淸王朝到蔣介石,他們如出一轍地先後表揚武訓,是不足爲怪的,因爲武訓正是適合維護他們的反動統治的一個有用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褒揚武訓,都是在他們感到自己的統治搖搖欲墜的時候。滿清朝廷准給武訓『樂善好施』字樣,作爲旌奬,是在一八八八年,正當太平天國之後二十四平,辛亥革命之前二十三年,那時封建秩序遭受了農民大革命浪潮的衝擊,正迅速地開始瓦解,而農民大革命正成了迎接歷史新時代的先聲。國民黨反動派在一九三四年發動武訓九十七週誕辰紀念的運動,蔣介石特爲從當時反革命軍事中心地的南昌行營給武訓紀念題字,以及一九三八年國民黨反動政府由林森、孔祥熙、何鍵、陳立夫會簽正式頒佈褒揚武訓的命令,正是在全國人民走向抗日高潮,人民革命力量經過曲折向前發展的時候。這說明了:反動統治者到了自己快要滅亡的時候,就好像一個人掉在水裏一樣,抓住一切浮在水上、能够抓到手的東西來挽救自己的覆沒,武訓就是在農民革命浪潮中捲起的渣滓而被反動統治者常作寶貝抓住的。
現在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以自己英勇的、頑强的、堅决的鬥爭推翻了內外壓迫者,爲歷來反動統治階級所表揚的武訓在新中國人民中應當再沒有他的地位了。爲甚麽關於武訓的宣傳不但沒有斂跡,反而盛行起來呢?這就是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的表現,這些思想在今天中國還有它的市場。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資產階級一方面不滿意這個統治的專橫殘暴,另一方面,又不相信並且害怕羣衆的力量,因此就不敢向反動統治階級堅决地進行鬥爭,而時常企圖尋找一個可以不經過鬥爭而得到改良的局面。
陶行知晚年成為了一個革命的民主派,但在提倡武訓這件事情上面却表現了他早年的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表現了他在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中的脆弱的一面。
在中國人民取得了全國性勝利之後,資產階級參加了人民民主政權,但他們中間却仍有一部分—人對於已經或正在死亡的舊制度、舊事物時常感到惋惜和留戀,而對於新生的事物表示冷淡和懷疑,對於人民革命更深入的發展則流露出彷徨恐懼的情緒。正如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所說的:『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規定了他們的軟弱性,他們缺乏遠見,缺乏足够的勇氣,並且有不少人害怕民衆。』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就有一種特別的責任,必須和資產階級破壞或妨礙人民民主專政的各種反動的錯誤的思想進行嚴肅的、堅决的鬥爭,肅淸其在人民内部,特別是在人民的先進分子中,共產黨員中的影響。在每個比較嚴重的政治鬥爭中,必須反對各式各樣的改良主義投降主義的思想,否則鬥爭就不能勝利前進。在抗美援朝運動中,我們首先反對了親美、恐美、崇美的思想;土地改革中首先反對了『和平分田』的思想;鎭壓反革命運動中,首先反對了『寬大無邊』的思想。
電影『武訓傳』就是資產階級的反動的改良主義思想在藝術上的表現之一。
電影借武訓的所謂『行乞興學』的事蹟用藝術的力量宣傳了這樣的改良主義思想:不觸動舊的社會經濟基礎,不破壞舊的政治制度,祇要在人民中普及文化教育,就可以根本改變人民的被壓迫的地位。旣然人民祗要有了文化就能解放,那自然就用不着羣眾的革命武裝鬥爭了。
電影中花了一千尺以上膠片來表現的武訓做夢的場面(孫瑜電影小說『武訓傳』中的所謂『狂想三部曲』)正是表現了作者的主題思想的。
作者在這幻夢和狂想中,描繪着人類社會的歷史:
『呻吟輾轉在脚底、在長鞭的尖端,流汗、流血的是萬千的農民……像牛像馬在染血的重枷鉄鍊下沉重的拉着犂,推着磨……」
『巨磨張着大嘴吞噬着無數的生命……血流成了紅河;骨肉壓榨成黏滯的醬……勞苦的人羣世世代代地永遠轉不出那黑暗痛苦的輪迴……張舉人的獰笑,忽然間把巨磨變成大石硯,黑墨磨動時濺出毒汁,飛灑在大羣「文盲」的眼睛裏:…』
『男、女、老的、小的……伸着手,扶着杖,用力睜着他們的看不見事物的雙眼,在人的「奈何橋」上戰戰兢兢地摸索着走,左邊是陡削的懸崖,右邊是無底的深淵,後面有張舉人拿着尖刀的筆;趙熊、魏俊披頭散髮,舉起大筆和巨墨在驅趕,前面獨木橋下括起陣陣的陰風和凄厲的哀號……。』
『「你們這些不識字的畜生,」舉人魔鬼在笑喊、「你們這些睜眼瞎子!我把你們都打下苦海,叫你們永世不能翻身!哈哈……」』(電影小說:『武訓傳』一〇一頁)
原來,農民的痛苦生活並不是由於封建地主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對他們的壓迫和剝削的結果,而祗是由於農民被地主階級剝奪了受敎育的權利,農民自己沒有文化,不識字,他們的眼睛『看不見事物』。那末有什麽辦法『翻身』呢?就祗有『學文化』了。
當武訓在夢中聽到義學的時候,他狂喜得大叫起來:『這不是從地底飛上了天嗎?……』他舉臂高呼:『窮孩子們,快跟我唸書去!』武訓從這個快樂的夢中驚醒,張目四望,就『好像來到了一個新的光明的世界。』不識字的,活該入地獄,唸了書可以上天堂。這就是電影『武訓傳』的中心思想。『唸了書才可以多知道世上的事情;才可以找着過好日子的道路。……』這一段被作者形容爲『包含着淵博的智慧』的老師的言語,難道不正是作者自己心中的言語,作者自己的思想嗎?
這種思想倒也不是甚麽新奇的東西。
列寧早在一九二三年所寫的『論我國革命』的一文中,就在關於文化與革命的關係問題上,嚴厲地批判了當時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人,那些『怯懦畏縮的改良主義者』的老爺們,他們死咬着實行社會主義一定要先有相當文化水平,列寧尖銳地反駁說:爲甚麽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造成這個相當文化水平的必要前提,即首先驅逐地主和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後向社會主義前進呢?他在同一年所寫的有名的『論合作制』一文中,也說在革命以前,工作重心祗能放在政治鬥爭、革命和奪取政權上面,而祗有在革命以後,工作重心才能移到和平的廣泛的文化建設的事業上來。當然列寧是正確的。俄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完全證實了他的預言。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所寫的有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也說過:
『中國歷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農民造成的,因爲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從農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敎育的人民,這個裏面,最大多數是農民。農村裏地主勢力一倒,農民的文化運動便開始了。………農民運動發展的結果,農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時間內,全省當有幾萬所學校在鄕村中湧出來,不若知識階級和所謂「敎育家」者流,空喚「普及敎育」,喚來喚去還是一句廢話。』
當然毛澤東同志是正確的,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完全證實了他的預言。
中國革命的經驗就是這樣的:首先發動農民武裝鬥爭,在廣大農村中推翻反動統治,建立革命根據地;然後在這個根據地上面逐步地發展人民的經濟和文化。現在,由於中國人民的全國性的勝利,特別是土地改革在全國實行,農民的文化獲得了歷史上從來未有的迅速的廣大的發展。可以斷定:在不久的將來,正如毛澤東同志在『中國人民政協第一届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詞』中所預言的,『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
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一個在歷史上曾經比歐洲其它資本主義先進國家文化落後,文盲衆多的沙皇俄國和一個在古代有過燦爛的文化,但在近代落伍了,文化落後,文盲特別衆多的中國,正是西方和東方的這兩個國家,首先取得了革命的大勝利。蘇聯現在不但成了世界上文化最發達的國家,而且正站在全人類文化的最高峯,指引世界人民前進的方向;新中國的新的人民的文化正在突飛猛進之中。道理是很簡單的:社會主義革命和人民革命創造了人民文化無限發展的前提。
不錯,孫瑜先生在『我怎樣表現武訓的「夢」』一文中說了:『單憑念書而不革命,不奪取政權,窮人受壓迫的命運是無法改變的。』但是,第一,一個藝術家的口頭上的表白,和他在藝術作品中所實際表現的有時並不完全是一回事,而且在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往往是作者的更眞實的思想和情感,讀者又是祗能從作品出發來判斷作者的;第二,社會民主黨也好,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也好,他們一般地在口頭上都不否定革命,他們倒是裝出十分愛護革命的樣子,他們說羣衆要革命,先要有文化,這樣從實際上來否定革命。電影『武訓傳』,正是宣傳了這種錯誤思想。
電影『武訓傳』寫了以武訓爲代表的『義學』運動,同時也寫了以周大為代表的農民革命,用作者的話,叫做『一武一文』,互相配合。但是這不但沒有能够挽救,而且更加深了電影『武訓傳』主題思想的錯誤。武訓和周大之間的友誼是一種完全違反歷史事實的揑造,因爲很顯然地,反動派和革命派之間是不可能建立那樣的友誼和事業上的合作關係的。作者在這裏不過是以周大作武訓的反襯,以誇大農民武裝鬥爭的失敗的和弱點的一面,來襯托武訓精神的偉大和他的興學事業的至少某種程度上的成功。這樣,就使電影『武訓傳』主題的反動性更加明顯了。
武訓生長在中國農民革命浪潮起伏的時期;山東多年都是捻軍活動的主要地區之一,就在他所出生的山東堂邑就有過農民武裝起義。一八六〇年,在邑堂柳林鎭距武訓的村子武莊不過七里地的另一個叫做小劉貫莊的村子裏,爆發了以著名的宋景詩爲首的農民起義。距武莊五里地的柳林鎭則是地主反革命武裝的堡壘。柳林的民團是最兇惡、最頑固的;團長不是別人,正是支持武訓辦成第一所義學、在電影中被描寫爲『開明士紳』的柳林地主楊樹坊的叔父楊鳴謙,楊鳴謙被宋景詩打死後不久,就由楊樹坊繼承了他叔父的這個反革命的民團團長的職務。宋景詩活動的期間,正常武訓二十多歲的時候,他沒有投奔宋景詩,却投奔了楊樹坊,他就這樣選擇了他的反革命的道路。據武訓歷史調查團的調查,當地年老農民至今懷念着他們當年革命的領袖,一提起宋景詩便眉飛色舞,講得津津有味,而一提到武訓,便表示沒有興趣和冷淡。這就可以看出農民階級的眞實感情,他們的明確的是非和熱烈的愛憎。我們當然不知道電影中的周大是否影射宋景詩,但是,無論如何,電影中的周大或實有其人的宋景詩和武訓之間,除了農民和地主、革命和反革命之間的不可調和的敵對的關係之外,是不可能再有任何其它的關係的。(未完)
相关人物
周揚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