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代时期
| 内容出处: | 《长春市志 商业志》 图书 |
| 唯一号: | 070120020220004162 |
| 颗粒名称: | 第二节 清代时期 |
| 分类号: | F729.493.4 |
| 页数: | 9 |
| 页码: | 9-17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长春市清代时期的商业演变情况。 |
| 关键词: | 长春市 商业演变 清代时期 |
内容
到了明代晚期,女真族日渐强大,与明朝之间的民族对立日趋尖锐,以致引起持续几十年的民族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原有的商业活动遭到了破坏,开原马市被关闭。及至1644年清军入关,除女真族的壮丁被编入八旗进关之外,他们的家属也都陆续随军“从龙入关”。因此,许多田园房舍被遗弃,人口锐减,今长春一带大部分变成了无人区。这次人口的迁徙,造成了元代以来又一次生产力的大破坏。耕种过的土地再次荒芜,女真族各部落间的商业交往随之中断。随着清代对东北的长期封禁,长春一带进入了一个社会经济活动比较萧条的时期。但在这个期间,修筑了清代柳条边新边(1670年至1681年间修筑),用以划定满蒙的界限,加强封禁,保护清朝的祖宗陵寝与特有的自然资源。这条国内边界,经过长春附近。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及其以后的几年里,长春附近人口有一次较大的增长。这是因为平定吴三桂等“三藩之乱”后,清政府为防御俄国的入侵,在东北设立边台、驿站、水师、航运和屯田,大批云贵、两广和闽浙等省的流人被押送到东北各地。其中的许多流人(包括他们的家属),被安置在从伊通边门(亦名易屯门、一统门等)起,向东北方向经由邢家台、水河台、马头台、九台、八台、七台、六台……直至松花江左岸一线的柳条边上,以及今双阳境内通往吉林的各个驿站。这些人被充作满洲八旗军人的奴隶,从事垦田、养马、修边、筑路、驿传等各种役差,在柳条边沿边和驿站周围开垦了一大批农田,形成了一批新的村落。但是由于奴隶的身份而不能积蓄自由支配的私有财产,所以也形成不了真正的商业活动。当时的人口分布是点状(柳条边门、边台或驿站)或线状(沿柳条边和驿站),其余更大的范围基本上仍属无人之境。据《鸡林旧闻录》所附李方远《张先生传》记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初冬流放伯都讷,途经今长春附近时,“历沈阳城,出威远门,即条子边也。过此,无一居民矣。时已初冬月晦,朔风吹面,寒气透衣,满地荒草,沙漠无际。黄羊、山雉群集,古木怪石嵯峨……”。可见当时的荒凉景象。但是此后不久,尽管清政府坚持封禁东北,今长春附近的大部分土地划为蒙地,但关内北方各省的农民,仍不断地流入。据1982年前后长春地区的地名普查结果表明:在现存的10786个居民点中,形成于明代晚期的仅21个,只占总数有千分之二。就是加上清代封禁前的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形成的村落,共计只有343个,仅占6.64%。在上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含今榆树、双阳两县及九台县境的柳条边内部分),雍正年代就出现了这几百个居民点中较大的村落——宽城子和长春堡。据近年社会调查结果编成的《农安县情》“广元店”条下记载:“高家先人于雍正末年从山东逃荒至宽城子(今长春)开设广元店(店主名为高广元)。在清道光初年,高家中的高希仲带领自己的一股人来此开荒立屯,为延续高家之名望,故名广元店。”由此可知,清雍正最后的几年(1732至1735年)宽城子已不同于一般居民点,是有商业店铺、客店和集市的地方,已成上万平方公里地域内的一个经济中心。
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辅国公恭格喇布坦承袭,成为又一代长春附近蒙地的新领主。这个人,为了增加蒙旗收入,一反过去蒙古王公不敢违背清廷禁令的作法,私下招募流民在他的领地上定居。乾隆年代后半期华北各省的水旱灾害,更加推动流民进入今长春一带。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已经达到数千户,开垦了几十万亩土地。一般流民,除简单的衣物与工具之外,没有什么财物,所以不能经营象样的商业。但是,在蒙古王公丈放荒地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有钱而且有一定地方势力的“揽头”。揽头作为中间人从蒙古王公手中包揽大片土地,转手分给流民,从中获取收益。揽头中有的是来自关内各省的商人,他们携带资金来到长春一带,开设经营粮食、油、酒、土产、农具和布匹的商号,同时兼营土地生意。还有的是蒙古王公手下的汉族管事,依靠与蒙古或蒙古官员的关系,充当揽头,也兼营商业。揽头也有大小之分,有些小揽头产生于较早到达此地并略有积蓄的流民。这些小揽头也往往经营农具、种子和日用品。这些新旧商人,在这个新垦区的不同地段,掌握了商品的流通。在伊通河与饮马河流域定居的流民,就依靠这些早期的粮栈、杂货店,获得农具、衣着和食盐。因为通货短缺,相当部分的买卖是依靠实物交换。也有的揽头开设的店铺,向农民赊销,因为这更有利于他们的收入。再晚些时候,那些较大的店铺,尤其是粮商、油坊和烧锅,就发行“私帖”(不能兑现但可周转的有价凭证),以便加快商业的周转。
从18世纪中期已经初步形成集市的宽城子,到嘉庆五年(1800年)设置长春厅时,就已经“农商云集,交易日酣,铺舍接修,顿成街市”(道光十七年二月《众商房基租章程碑记》)了。道光五年(1825年)长春厅衙署北迁宽城子,更进一步促进了厅治商业的繁荣,但是在此以前曾经有过商业集市的新立城和长春堡,却逐渐衰落。随着宽城子商业店铺的增多,再按原来蒙地农田的标准纳租,已经不宜,所以“长春厅阁会众商”共同商定了一个“房基租”标准,并立碑为证。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碑文中记载:“其商民占用铺舍分为四等,各照门面房间纳租。头等铺房每年按老银数纳租银一两三钱,二等每间年纳一两一钱,……岁月常额,遵行在案。”可见1837年以前,宽城子已形成相当规模的商业街,“门面房间”的数量已经很大,粮栈、油坊、烧锅、磨坊、杂货店、布屋、大车店、旅店、当铺、钱庄、饭馆、药店、裁缝铺、估衣铺、鞋帽店、皮铺、酱园、茶馆……都已一应俱全。除掉这些店铺之外,还有摊贩、行商和集市。宽城子不但有著名的马市,还有柴草市、菜市,以及专门容纳赶集农民和摊贩的市场。
长春(宽城子)商业资本的主要来源有:早期和当地官府打交道的“山西票庄”,从经营官府的存放款、转汇,进而经营商业和土地。随着垦区的扩大,来自冀东各县的商人,从大车店开始,逐步经营粮食、油、酒和钱庄。例如著名的“京东刘家”,经过几代经商直至1956年公私合营的益发合。在长春还未成为当地的商业中心以前,船厂(今吉林市)已是清代吉林将军的驻地,手工业与商业已经相当发达。长春一带开垦以后,船厂的一些商号开始进入长春,如著名的吉林牛家,先后开设了粮栈、杂货店、钱庄和药店等多种商号。比上述三地商人来长略晚的是柳条边内今辽南(清代盛京将军辖境,现在的辽宁省)的商人。
当时的商业和手工业、金融业之间,没有现代那样清楚的界限。多数商业资本都是兼营相互有关的几个行业。大小手工业作坊都是既加工又销售,一家大车店也是兼营粮食、土产的买卖,或代存代销货物。许多商业资本采取“联东联财”(同一个出资者,分设若干个店铺,盈亏共负的)、“联东不联财”(同一出资者经营的若干店铺之间完全独立核算的)等多种不同的经营方法,经营多种不同行业的商号,自设为联东商号融通资金的钱庄等。其中的大部分是采用“联东不联财”的办法。由若干个财东出资的商号,则按出资份额分劈红利。不属于出资者的经理人(通称“掌柜”),也按一定比例分得红利(通称为“身股”或“干股”)。各个商号(包括手工业作坊)雇用的店员(或工匠)通称之为“劳金”。另外还有没有薪水只供应食宿的学徒。规模较大,行业复杂的大商号,则同时设有不同等级的几级经理人。这种商业经营方式与从业人员结构,在长春存在了百余年,直至本世纪的五十年代。
长春厅管辖的垦区不断沿伊通河和饮马河由南向北扩展,在道光二年(1822年)丈放农安附近“蒙荒”,使辽代黄龙府,再次在废墟上重建农安城,成为长春厅北部的一个集镇。一些经营土地的揽头和已在宽城子营业的商号、作坊,陆续进入农安,在开放的垦区经营商号和作坊。
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在长春厅境内,由于地处东北内陆,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方面还没有直接的明显反映。但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形势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这次战争结束后,在英法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被迫开放10个口岸,其中的营口(原定为牛庄,后改为营口)成为东北的第一个对外开放港口。与此同时,在1860年前后,经过近百年的开垦,长春一带的农业生产已逐渐进入新的成长阶段,农产品已经自给有余,剩余农产品和土产,等待转化成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约在营口开港之后的几年内,长春一带的杂粮和大豆就开始运往营口,运销华北与东南沿海各省,或外销日本和西欧。同时关内各省的布匹、丝绸、竹制品、金属制品、茶叶、桐油、漆器、陶磁、中药、水产品和文化用品,也逐渐销到长春。日本和欧美的煤油、砂糖、火柴、棉纱、棉布和五金工具,也开始运入长春。
在设置长春厅之初,宽城子与昌图之间就有一条大道。营口开港之后,这条道成为联接长春、营口的最重要的商路。当时陆地运输的主要工具是马车(冬季降雪结冻期间也使用“爬犁”,即雪撬)。从长春运往营口的货物,要在冬季运到辽河岸边的通江口(亦名通江子,辽宁省昌图县境内)。入春辽河解冻后用帆船运往营口,陆上运输就随之停止。南运的货物以粮豆为主,北则运来自关内各地与进口的货物。长春成为长春厅境内最大的农产品集中地,也是外来货物再分散的中心。
营口开港以后,使长春和国际贸易联接起来了,与国内的长途贩运也发展起来了。与长春、通江口之间的商路形成的同时,沿途兴起了一种新的行业,民间通称为“大房子”。这个新行业,以前是大车店,限于接待过路的大车,供应食宿。后来就逐渐发展成代销、代购、仓储、抵押借贷、兑换钱钞,以及充当经纪人等等的行业。这些大房子是旅店、饭馆、仓库、钱庄综合在一起的商号,兴盛了几十年,直到辽河航运的衰落。与大房子兴起的同时,沿途也出现了饭铺、掌炉(即烘炉,亦称铁匠炉,为马匹挂掌和修理车具),出售适应大车运输所需的饮食,如烧酒、肉食和面食,流传到现在的“李连贵熏肉大饼”也属于这一类适应于冬季严寒的高热值、高脂肪的方便食品。
当时除冬季运往通江口的大豆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从长春直接用大车运往营口,返回时则载运杂货与进口的“洋货”。因此,长春南运的大豆(包括大豆的加工品:豆油、豆饼),分为“车豆”和“河豆”两种。“河豆”就是经过辽河船运的大豆,每年可在航运季节于通江口至营口之间往返5次。“车豆”就是用大车(铁路通车后则包括火车)直运营口的大豆。
大豆的远销与出口,对于长春商业有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大豆的出口,不仅对商业,而且对农业种植与农产品加工业,也引起了重大变化。原来以麻籽为主要食油原料,开始转向以大豆为主。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直到本世纪的头4年为止,大豆及其加工品都占出口总值的80%左右。长春厅境内的大豆种植面积均不低于拼地面积的20%,个别地方达到一半左右,在农作物中的地位一般仅次于高粱。在这个时候,来自河北、山东、山西、辽宁等省的商业资本,不仅进入了长春、农安等城镇开设粮栈,而且在农村有集市的地方开设杂货铺。这些商号又通过批发操纵农村中的行商,收购农民手中的粮豆。他们不仅收购秋粮现货,而且乘青黄不接之际收买以大豆为主的青苗。这些经营粮食的商号,以明显低于秋粮的价格,获取更高的利润。这种青苗交易,形成了早期的期货交易。后来,粮商与粮商之间,外商与粮商之间,也展开了期货交易,以便用有利的价格预先获得有把握的货源。但是,同时这种期货合同又辗转买卖,形成当时通称的“买空卖空”,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倒把”和“投机”。
长春一带的剩余农产品,随着营口的开港与国际贸易的展开,逐步走向了商品化。当时日本正处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对水稻使用的传统肥料——“鱼肥”(用无食用价值的鱼虾制成的肥料),开始被中国的豆饼所代替。西欧的近代工业已经相当成熟,大豆成为其食品工业和化学工业的重要原料。对日本和西欧的大豆贸易,使长春的粮栈、油坊等行业,空前地活跃起来了;宽城子也逐渐成为东北中部的商业重镇,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提高了。
1898年夏天,俄国人在长春附近动工修筑长春至哈尔滨、长春至大连间的中东铁路南满支线。大批来自山东、河北等省的筑路工人,进入长春南北的铁路沿线,随后还在城北二道沟修筑了长春历史上的第一座火车站——“宽城子车站”。由于远来的大批筑路工人,又刺激了粮米加工业的繁荣,粮食和日用品的批发零售商业,也随之趋于活跃。
由于俄国人的大批进入长春(1900年义和团运动开始之后,大批俄军占据长春),又有许多商人开始经营与俄国人之间的生意,向俄国人出售面粉、肉牛、蔬菜、酒类等生活用品。远在辽南的著名商人纪凤台,也于俄国人进入长春之后来到这里购置房产,开设商号。他与中国官府和俄国人都有很深的交往。他在长春城内北大街(今大马路南段,长春大街与四道街之间)开设了和成祥货栈,经营杂货、钱庄、粮栈和房地产业。和成祥修筑过两层的砖木结构楼房,曾是长春历史上的第一座楼房。这座楼房,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年,曾经作为清代东三省总督、吉林巡抚等达官贵人在长春暂住的“行台”;也接待过一些俄国官员、将领。纪凤台以经营对外贸易,尤其和俄国人作生意,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与日俄战争期间成为巨商,后来移居俄国,成为俄籍华人,他是在长春经商的商人中早期的买办。在日俄战争中,在本地不仅有向俄国人销售货物的商号,还有代销俄国商品,为俄军采购各种物资的商人,这些人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买办,发了“洋财”。原裕昌源老板王荆山,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1901年末,长春南北的中东铁路支线已经完成了铺轨工程,宽城子火车站也已基本建成。在宽城子站东侧,俄国人修建了一条商业街——“巴栅街”,有俄国人开设的商店和中俄商人的摊床。由于中东路跨越松花江大桥工程1903年才建成,全线至同年7月才正式通车。这时,与1904年2月爆发的日俄战争,相距只有几个月,而且日俄之间形势已经极度紧张,所以通车之后主要用于军运,直至这场战争结束,还没有显示过真正的商业作用。除俄国商人以外,中国和日本及西欧的商人,都没能利用这条铁路进行过商业运输。
日俄战争结束后的1906年4月,首批日本人进入长春。日本从俄国手中接管了孟家屯车站以南的铁路,并且开始经营“南满铁路”的营业。这一年里,孟家屯车站一带曾集聚过中外商民8000多人,各种商铺一度达到过300余家。首批到长的日本人,分别居住在西三道街一带,租赁中国人的房屋开设旅店、饭馆、杂货店、“脚行”(经营铁路托运、装卸、货物包装等业务的行业)、药店等商店,开始与中国人作生意。但是这一类多属日本的小商人。另有一些日本的大企业,开始在长春设立分支机构,主要有银行业(为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还有经营进出口的“三井物产株式会社长春支店”。这家商业公司对长春一带的农业和土特产进行过详细的调查,依靠铁路运输和远比中国商人雄厚的资金,很快就在长春的大豆(及其制品)与杂粮市场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1907年8月,日本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长春北头道沟一带购买了大片土地,划为长春“满铁附属地”,修建了“满铁”的长春车站。在附属地内规划了街道,计划建设几条商业街。1908年在长春站前的“日出町”(今长白路)开办了几十家日本人的“脚行”,代办“满铁”的商业运输,以倒买车皮谋利。在“富士町”(今黑水路)有20多家日本小饭馆,一时形成了一条“饭馆街”。晚些时候在“日本桥通”(今胜利大街)出现了一些日本的杂货店,出售日本产的纺织品、五金制品,以及开设小旅馆。因为这条街是连接长春城内与“满铁附属地”和长春车站的唯一大道,在这条街上可以兼做中日双方的生意,所以很快就热闹起来。因为日俄战后长春成为日俄铁路的分界点,各国旅客换乘的地方,所以“满铁”在1908年至1909年间,建成了一座当时最新式的旅馆——“满铁长春大和旅馆”。这座旅馆当时是唯一拥有水、电、暖气和卫生设备的欧洲式建筑,专供中外上层人士留宿。
随着日俄战争的结束与日本在长春设置“满铁附属地”的同时,根据《中日会议东三省善后事宜条约》,规定长春要“中国自行开埠通商”。因此,长春就有了当地的商埠,通称之为商埠地。长春商埠地南起长春城的北门外(今长春大街以北),东至伊通河畔,北至“满铁附属地”的南界(今上海路北),西至黄瓜沟一带(今东西民主大街之间),共计占地13500余垧。
长春开埠经过3年之后,初步建成了一条当时最大的商业街,即长春城北门(今大马路与长春大街路口)至“日本桥”(今胜利大街与上海路口偏北处)之间的“商埠大马路”。地方政府设置的“开埠局”(后改称“商埠局”),在陆续收购大片的民间土地之后,划分等级再向商民出租,限期动工,在主要街道两旁修建门市房屋。对于外国商人,在商埠地界内,也和中国人一样可以租用房地产,以便招引外商,并可适当控制。
由于主持开办长春商埠当局,从一开始就陷入资金不足的困境,所以只能收买划定区域中的部分土地,剩余的土地仅用官府命令的形式限定不得私相买卖。直到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为止,建成了大马路北段的出租市房200间,在北门外(今东三马路附近)修建了民房440间,开办了“老市场”(今大马路东,长春大街至东四马路之间)。集中一些饭馆、茶馆和妓院于平康里(今东三马路一带)。当时的地方政府官员,试图用声色招引顾客,推动市面的繁荣。
外国商人进入商埠地之后,开设各种商号,其中最主要的是收购大豆、土产和推销各自产品的外商分支机构。这些外商都有各自的特点,如美国的缝纫机和美孚公司的煤油,瑞典的火柴,英国太古洋行的砂糖、棉布和棉纱,亚细亚石油公司的煤油,美英烟草公司的卷烟,德国的枪支弹药和染料、西药,日本的棉织品和卷烟,瑞士的钟表,俄国的毛纺品,诺别力公司的煤油等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外商之间,外商与中国商人之间,都有激烈的竞争。例如日本人在1908年设厂的“广仁津火柴公司”(日名“日清磷寸株式会社”),就和瑞典的火柴经过长年的角逐,凭藉日本在华的特殊势力而取得了优势。日本为了占领卷烟的市场,依靠日本政府的出口补贴,用远低于日本国内市场的价格,在长春进行批发和零售。因为日本的烟草工业是官办的,并由日商东亚烟草株式会社统一经销,所以当时日本人称之为“官烟”。日本“官烟”在长春的零售价格,1910年前后竟达到:“星牌”每盒0.025元(日元),日本国内售价0.09元;“东方牌”0.07元,日本国内为0.15元;“樱桃牌”0.023元,日本国内为0.08元;“舞女牌”0.08元,日本国内为0.20元。总的日产卷烟零售价,只有日本国内的38%。当时运销长春的日产卷烟达到17种。美英烟草托拉斯生产的卷烟早在日俄战争之前就进入了长春,牌号达到26种。双方商战的结果,在长春市场上平分秋色。虽然也有国产的、俄国的、埃及的卷烟,还有菲律宾的雪茄,但都处在无足轻重的地位。
自从日俄战后,直至20年代,内外商人之间的大豆期货交易相当盛行。虽然中国粮商占据传统的熟悉市场与产地情况,拥有传统的收购关系,但与外商的期货交易反而常常处于下风。当时的外商,尤其是日本商人,往往借助外交势力,在订约后如果豆价上涨则索要现货;如果豆价下跌则寻找藉口废弃合同或要求降价。日本人为了使其“满铁附属地”早日繁荣,还千方百计地以降低税费等优惠条件,引诱中国粮商到“附属地”界内开办粮栈。还用铁路运输、电力供应等方便条件,吸引中国人在“附属地”内投资开办粮油加工业。为吸引中国商人开办粮栈,还在“附属地”内划定了“粮栈区”(今长春车站东南,伊通河以西地段)。日本国内的工业,多方设法窥测东北市场的需求,仿制中国的传统手工业产品。当时长春一带居民所需的“腿带子”(绑扎裤脚用的宽线带子,以副为单位),也由日本的机织品逐渐代替了来自关内的手工产品。中国传统的水烟丝,外商也有仿制品出售。其它大宗的纺织品(以棉布、棉纱为主),也以日本产品价格低于国产和欧美产品而逐渐占据优势。由于性能优良的德国的化工染料进入长春,也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的蓝靛(用蓼蓝叶为原料制作的蓝色染料)。
从外商进入长春起,就有许多外商从事非法经营。当时长春附近土匪猖獗,清末民初兵匪互相转化,地方豪绅自办武装,日本和德国商人就在长春经销军火,既有批发也有零售,从手枪、长枪,后来又增添了机关枪以及各种弹药一应俱全。零售可以现钱交易,大批的还可以订购和赊销。这种公开的军火买卖,与长春一带的土匪活动是密切相关的。外商还带来了半公开的毒品交易。日商在“附属地”、商埠地和城内,都开设有西药房。这些药店公开出售西药,暗地里批发零售鸦片、吗啡。在日本领事馆与日本警方的保护之下,中国当局无可奈何。即或查有实据或当场扣押日本人现行犯,在日本拥有领事裁判权的情况下,也只能将人犯引渡给日方了事。这种情况并不限于长春,日商还深入到长春周围的农安、德惠、双阳、九台等地用同样办法销售毒品。
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辅国公恭格喇布坦承袭,成为又一代长春附近蒙地的新领主。这个人,为了增加蒙旗收入,一反过去蒙古王公不敢违背清廷禁令的作法,私下招募流民在他的领地上定居。乾隆年代后半期华北各省的水旱灾害,更加推动流民进入今长春一带。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已经达到数千户,开垦了几十万亩土地。一般流民,除简单的衣物与工具之外,没有什么财物,所以不能经营象样的商业。但是,在蒙古王公丈放荒地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有钱而且有一定地方势力的“揽头”。揽头作为中间人从蒙古王公手中包揽大片土地,转手分给流民,从中获取收益。揽头中有的是来自关内各省的商人,他们携带资金来到长春一带,开设经营粮食、油、酒、土产、农具和布匹的商号,同时兼营土地生意。还有的是蒙古王公手下的汉族管事,依靠与蒙古或蒙古官员的关系,充当揽头,也兼营商业。揽头也有大小之分,有些小揽头产生于较早到达此地并略有积蓄的流民。这些小揽头也往往经营农具、种子和日用品。这些新旧商人,在这个新垦区的不同地段,掌握了商品的流通。在伊通河与饮马河流域定居的流民,就依靠这些早期的粮栈、杂货店,获得农具、衣着和食盐。因为通货短缺,相当部分的买卖是依靠实物交换。也有的揽头开设的店铺,向农民赊销,因为这更有利于他们的收入。再晚些时候,那些较大的店铺,尤其是粮商、油坊和烧锅,就发行“私帖”(不能兑现但可周转的有价凭证),以便加快商业的周转。
从18世纪中期已经初步形成集市的宽城子,到嘉庆五年(1800年)设置长春厅时,就已经“农商云集,交易日酣,铺舍接修,顿成街市”(道光十七年二月《众商房基租章程碑记》)了。道光五年(1825年)长春厅衙署北迁宽城子,更进一步促进了厅治商业的繁荣,但是在此以前曾经有过商业集市的新立城和长春堡,却逐渐衰落。随着宽城子商业店铺的增多,再按原来蒙地农田的标准纳租,已经不宜,所以“长春厅阁会众商”共同商定了一个“房基租”标准,并立碑为证。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碑文中记载:“其商民占用铺舍分为四等,各照门面房间纳租。头等铺房每年按老银数纳租银一两三钱,二等每间年纳一两一钱,……岁月常额,遵行在案。”可见1837年以前,宽城子已形成相当规模的商业街,“门面房间”的数量已经很大,粮栈、油坊、烧锅、磨坊、杂货店、布屋、大车店、旅店、当铺、钱庄、饭馆、药店、裁缝铺、估衣铺、鞋帽店、皮铺、酱园、茶馆……都已一应俱全。除掉这些店铺之外,还有摊贩、行商和集市。宽城子不但有著名的马市,还有柴草市、菜市,以及专门容纳赶集农民和摊贩的市场。
长春(宽城子)商业资本的主要来源有:早期和当地官府打交道的“山西票庄”,从经营官府的存放款、转汇,进而经营商业和土地。随着垦区的扩大,来自冀东各县的商人,从大车店开始,逐步经营粮食、油、酒和钱庄。例如著名的“京东刘家”,经过几代经商直至1956年公私合营的益发合。在长春还未成为当地的商业中心以前,船厂(今吉林市)已是清代吉林将军的驻地,手工业与商业已经相当发达。长春一带开垦以后,船厂的一些商号开始进入长春,如著名的吉林牛家,先后开设了粮栈、杂货店、钱庄和药店等多种商号。比上述三地商人来长略晚的是柳条边内今辽南(清代盛京将军辖境,现在的辽宁省)的商人。
当时的商业和手工业、金融业之间,没有现代那样清楚的界限。多数商业资本都是兼营相互有关的几个行业。大小手工业作坊都是既加工又销售,一家大车店也是兼营粮食、土产的买卖,或代存代销货物。许多商业资本采取“联东联财”(同一个出资者,分设若干个店铺,盈亏共负的)、“联东不联财”(同一出资者经营的若干店铺之间完全独立核算的)等多种不同的经营方法,经营多种不同行业的商号,自设为联东商号融通资金的钱庄等。其中的大部分是采用“联东不联财”的办法。由若干个财东出资的商号,则按出资份额分劈红利。不属于出资者的经理人(通称“掌柜”),也按一定比例分得红利(通称为“身股”或“干股”)。各个商号(包括手工业作坊)雇用的店员(或工匠)通称之为“劳金”。另外还有没有薪水只供应食宿的学徒。规模较大,行业复杂的大商号,则同时设有不同等级的几级经理人。这种商业经营方式与从业人员结构,在长春存在了百余年,直至本世纪的五十年代。
长春厅管辖的垦区不断沿伊通河和饮马河由南向北扩展,在道光二年(1822年)丈放农安附近“蒙荒”,使辽代黄龙府,再次在废墟上重建农安城,成为长春厅北部的一个集镇。一些经营土地的揽头和已在宽城子营业的商号、作坊,陆续进入农安,在开放的垦区经营商号和作坊。
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在长春厅境内,由于地处东北内陆,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方面还没有直接的明显反映。但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形势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这次战争结束后,在英法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被迫开放10个口岸,其中的营口(原定为牛庄,后改为营口)成为东北的第一个对外开放港口。与此同时,在1860年前后,经过近百年的开垦,长春一带的农业生产已逐渐进入新的成长阶段,农产品已经自给有余,剩余农产品和土产,等待转化成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约在营口开港之后的几年内,长春一带的杂粮和大豆就开始运往营口,运销华北与东南沿海各省,或外销日本和西欧。同时关内各省的布匹、丝绸、竹制品、金属制品、茶叶、桐油、漆器、陶磁、中药、水产品和文化用品,也逐渐销到长春。日本和欧美的煤油、砂糖、火柴、棉纱、棉布和五金工具,也开始运入长春。
在设置长春厅之初,宽城子与昌图之间就有一条大道。营口开港之后,这条道成为联接长春、营口的最重要的商路。当时陆地运输的主要工具是马车(冬季降雪结冻期间也使用“爬犁”,即雪撬)。从长春运往营口的货物,要在冬季运到辽河岸边的通江口(亦名通江子,辽宁省昌图县境内)。入春辽河解冻后用帆船运往营口,陆上运输就随之停止。南运的货物以粮豆为主,北则运来自关内各地与进口的货物。长春成为长春厅境内最大的农产品集中地,也是外来货物再分散的中心。
营口开港以后,使长春和国际贸易联接起来了,与国内的长途贩运也发展起来了。与长春、通江口之间的商路形成的同时,沿途兴起了一种新的行业,民间通称为“大房子”。这个新行业,以前是大车店,限于接待过路的大车,供应食宿。后来就逐渐发展成代销、代购、仓储、抵押借贷、兑换钱钞,以及充当经纪人等等的行业。这些大房子是旅店、饭馆、仓库、钱庄综合在一起的商号,兴盛了几十年,直到辽河航运的衰落。与大房子兴起的同时,沿途也出现了饭铺、掌炉(即烘炉,亦称铁匠炉,为马匹挂掌和修理车具),出售适应大车运输所需的饮食,如烧酒、肉食和面食,流传到现在的“李连贵熏肉大饼”也属于这一类适应于冬季严寒的高热值、高脂肪的方便食品。
当时除冬季运往通江口的大豆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从长春直接用大车运往营口,返回时则载运杂货与进口的“洋货”。因此,长春南运的大豆(包括大豆的加工品:豆油、豆饼),分为“车豆”和“河豆”两种。“河豆”就是经过辽河船运的大豆,每年可在航运季节于通江口至营口之间往返5次。“车豆”就是用大车(铁路通车后则包括火车)直运营口的大豆。
大豆的远销与出口,对于长春商业有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大豆的出口,不仅对商业,而且对农业种植与农产品加工业,也引起了重大变化。原来以麻籽为主要食油原料,开始转向以大豆为主。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直到本世纪的头4年为止,大豆及其加工品都占出口总值的80%左右。长春厅境内的大豆种植面积均不低于拼地面积的20%,个别地方达到一半左右,在农作物中的地位一般仅次于高粱。在这个时候,来自河北、山东、山西、辽宁等省的商业资本,不仅进入了长春、农安等城镇开设粮栈,而且在农村有集市的地方开设杂货铺。这些商号又通过批发操纵农村中的行商,收购农民手中的粮豆。他们不仅收购秋粮现货,而且乘青黄不接之际收买以大豆为主的青苗。这些经营粮食的商号,以明显低于秋粮的价格,获取更高的利润。这种青苗交易,形成了早期的期货交易。后来,粮商与粮商之间,外商与粮商之间,也展开了期货交易,以便用有利的价格预先获得有把握的货源。但是,同时这种期货合同又辗转买卖,形成当时通称的“买空卖空”,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倒把”和“投机”。
长春一带的剩余农产品,随着营口的开港与国际贸易的展开,逐步走向了商品化。当时日本正处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对水稻使用的传统肥料——“鱼肥”(用无食用价值的鱼虾制成的肥料),开始被中国的豆饼所代替。西欧的近代工业已经相当成熟,大豆成为其食品工业和化学工业的重要原料。对日本和西欧的大豆贸易,使长春的粮栈、油坊等行业,空前地活跃起来了;宽城子也逐渐成为东北中部的商业重镇,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提高了。
1898年夏天,俄国人在长春附近动工修筑长春至哈尔滨、长春至大连间的中东铁路南满支线。大批来自山东、河北等省的筑路工人,进入长春南北的铁路沿线,随后还在城北二道沟修筑了长春历史上的第一座火车站——“宽城子车站”。由于远来的大批筑路工人,又刺激了粮米加工业的繁荣,粮食和日用品的批发零售商业,也随之趋于活跃。
由于俄国人的大批进入长春(1900年义和团运动开始之后,大批俄军占据长春),又有许多商人开始经营与俄国人之间的生意,向俄国人出售面粉、肉牛、蔬菜、酒类等生活用品。远在辽南的著名商人纪凤台,也于俄国人进入长春之后来到这里购置房产,开设商号。他与中国官府和俄国人都有很深的交往。他在长春城内北大街(今大马路南段,长春大街与四道街之间)开设了和成祥货栈,经营杂货、钱庄、粮栈和房地产业。和成祥修筑过两层的砖木结构楼房,曾是长春历史上的第一座楼房。这座楼房,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年,曾经作为清代东三省总督、吉林巡抚等达官贵人在长春暂住的“行台”;也接待过一些俄国官员、将领。纪凤台以经营对外贸易,尤其和俄国人作生意,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与日俄战争期间成为巨商,后来移居俄国,成为俄籍华人,他是在长春经商的商人中早期的买办。在日俄战争中,在本地不仅有向俄国人销售货物的商号,还有代销俄国商品,为俄军采购各种物资的商人,这些人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买办,发了“洋财”。原裕昌源老板王荆山,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1901年末,长春南北的中东铁路支线已经完成了铺轨工程,宽城子火车站也已基本建成。在宽城子站东侧,俄国人修建了一条商业街——“巴栅街”,有俄国人开设的商店和中俄商人的摊床。由于中东路跨越松花江大桥工程1903年才建成,全线至同年7月才正式通车。这时,与1904年2月爆发的日俄战争,相距只有几个月,而且日俄之间形势已经极度紧张,所以通车之后主要用于军运,直至这场战争结束,还没有显示过真正的商业作用。除俄国商人以外,中国和日本及西欧的商人,都没能利用这条铁路进行过商业运输。
日俄战争结束后的1906年4月,首批日本人进入长春。日本从俄国手中接管了孟家屯车站以南的铁路,并且开始经营“南满铁路”的营业。这一年里,孟家屯车站一带曾集聚过中外商民8000多人,各种商铺一度达到过300余家。首批到长的日本人,分别居住在西三道街一带,租赁中国人的房屋开设旅店、饭馆、杂货店、“脚行”(经营铁路托运、装卸、货物包装等业务的行业)、药店等商店,开始与中国人作生意。但是这一类多属日本的小商人。另有一些日本的大企业,开始在长春设立分支机构,主要有银行业(为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还有经营进出口的“三井物产株式会社长春支店”。这家商业公司对长春一带的农业和土特产进行过详细的调查,依靠铁路运输和远比中国商人雄厚的资金,很快就在长春的大豆(及其制品)与杂粮市场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1907年8月,日本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长春北头道沟一带购买了大片土地,划为长春“满铁附属地”,修建了“满铁”的长春车站。在附属地内规划了街道,计划建设几条商业街。1908年在长春站前的“日出町”(今长白路)开办了几十家日本人的“脚行”,代办“满铁”的商业运输,以倒买车皮谋利。在“富士町”(今黑水路)有20多家日本小饭馆,一时形成了一条“饭馆街”。晚些时候在“日本桥通”(今胜利大街)出现了一些日本的杂货店,出售日本产的纺织品、五金制品,以及开设小旅馆。因为这条街是连接长春城内与“满铁附属地”和长春车站的唯一大道,在这条街上可以兼做中日双方的生意,所以很快就热闹起来。因为日俄战后长春成为日俄铁路的分界点,各国旅客换乘的地方,所以“满铁”在1908年至1909年间,建成了一座当时最新式的旅馆——“满铁长春大和旅馆”。这座旅馆当时是唯一拥有水、电、暖气和卫生设备的欧洲式建筑,专供中外上层人士留宿。
随着日俄战争的结束与日本在长春设置“满铁附属地”的同时,根据《中日会议东三省善后事宜条约》,规定长春要“中国自行开埠通商”。因此,长春就有了当地的商埠,通称之为商埠地。长春商埠地南起长春城的北门外(今长春大街以北),东至伊通河畔,北至“满铁附属地”的南界(今上海路北),西至黄瓜沟一带(今东西民主大街之间),共计占地13500余垧。
长春开埠经过3年之后,初步建成了一条当时最大的商业街,即长春城北门(今大马路与长春大街路口)至“日本桥”(今胜利大街与上海路口偏北处)之间的“商埠大马路”。地方政府设置的“开埠局”(后改称“商埠局”),在陆续收购大片的民间土地之后,划分等级再向商民出租,限期动工,在主要街道两旁修建门市房屋。对于外国商人,在商埠地界内,也和中国人一样可以租用房地产,以便招引外商,并可适当控制。
由于主持开办长春商埠当局,从一开始就陷入资金不足的困境,所以只能收买划定区域中的部分土地,剩余的土地仅用官府命令的形式限定不得私相买卖。直到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为止,建成了大马路北段的出租市房200间,在北门外(今东三马路附近)修建了民房440间,开办了“老市场”(今大马路东,长春大街至东四马路之间)。集中一些饭馆、茶馆和妓院于平康里(今东三马路一带)。当时的地方政府官员,试图用声色招引顾客,推动市面的繁荣。
外国商人进入商埠地之后,开设各种商号,其中最主要的是收购大豆、土产和推销各自产品的外商分支机构。这些外商都有各自的特点,如美国的缝纫机和美孚公司的煤油,瑞典的火柴,英国太古洋行的砂糖、棉布和棉纱,亚细亚石油公司的煤油,美英烟草公司的卷烟,德国的枪支弹药和染料、西药,日本的棉织品和卷烟,瑞士的钟表,俄国的毛纺品,诺别力公司的煤油等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外商之间,外商与中国商人之间,都有激烈的竞争。例如日本人在1908年设厂的“广仁津火柴公司”(日名“日清磷寸株式会社”),就和瑞典的火柴经过长年的角逐,凭藉日本在华的特殊势力而取得了优势。日本为了占领卷烟的市场,依靠日本政府的出口补贴,用远低于日本国内市场的价格,在长春进行批发和零售。因为日本的烟草工业是官办的,并由日商东亚烟草株式会社统一经销,所以当时日本人称之为“官烟”。日本“官烟”在长春的零售价格,1910年前后竟达到:“星牌”每盒0.025元(日元),日本国内售价0.09元;“东方牌”0.07元,日本国内为0.15元;“樱桃牌”0.023元,日本国内为0.08元;“舞女牌”0.08元,日本国内为0.20元。总的日产卷烟零售价,只有日本国内的38%。当时运销长春的日产卷烟达到17种。美英烟草托拉斯生产的卷烟早在日俄战争之前就进入了长春,牌号达到26种。双方商战的结果,在长春市场上平分秋色。虽然也有国产的、俄国的、埃及的卷烟,还有菲律宾的雪茄,但都处在无足轻重的地位。
自从日俄战后,直至20年代,内外商人之间的大豆期货交易相当盛行。虽然中国粮商占据传统的熟悉市场与产地情况,拥有传统的收购关系,但与外商的期货交易反而常常处于下风。当时的外商,尤其是日本商人,往往借助外交势力,在订约后如果豆价上涨则索要现货;如果豆价下跌则寻找藉口废弃合同或要求降价。日本人为了使其“满铁附属地”早日繁荣,还千方百计地以降低税费等优惠条件,引诱中国粮商到“附属地”界内开办粮栈。还用铁路运输、电力供应等方便条件,吸引中国人在“附属地”内投资开办粮油加工业。为吸引中国商人开办粮栈,还在“附属地”内划定了“粮栈区”(今长春车站东南,伊通河以西地段)。日本国内的工业,多方设法窥测东北市场的需求,仿制中国的传统手工业产品。当时长春一带居民所需的“腿带子”(绑扎裤脚用的宽线带子,以副为单位),也由日本的机织品逐渐代替了来自关内的手工产品。中国传统的水烟丝,外商也有仿制品出售。其它大宗的纺织品(以棉布、棉纱为主),也以日本产品价格低于国产和欧美产品而逐渐占据优势。由于性能优良的德国的化工染料进入长春,也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的蓝靛(用蓼蓝叶为原料制作的蓝色染料)。
从外商进入长春起,就有许多外商从事非法经营。当时长春附近土匪猖獗,清末民初兵匪互相转化,地方豪绅自办武装,日本和德国商人就在长春经销军火,既有批发也有零售,从手枪、长枪,后来又增添了机关枪以及各种弹药一应俱全。零售可以现钱交易,大批的还可以订购和赊销。这种公开的军火买卖,与长春一带的土匪活动是密切相关的。外商还带来了半公开的毒品交易。日商在“附属地”、商埠地和城内,都开设有西药房。这些药店公开出售西药,暗地里批发零售鸦片、吗啡。在日本领事馆与日本警方的保护之下,中国当局无可奈何。即或查有实据或当场扣押日本人现行犯,在日本拥有领事裁判权的情况下,也只能将人犯引渡给日方了事。这种情况并不限于长春,日商还深入到长春周围的农安、德惠、双阳、九台等地用同样办法销售毒品。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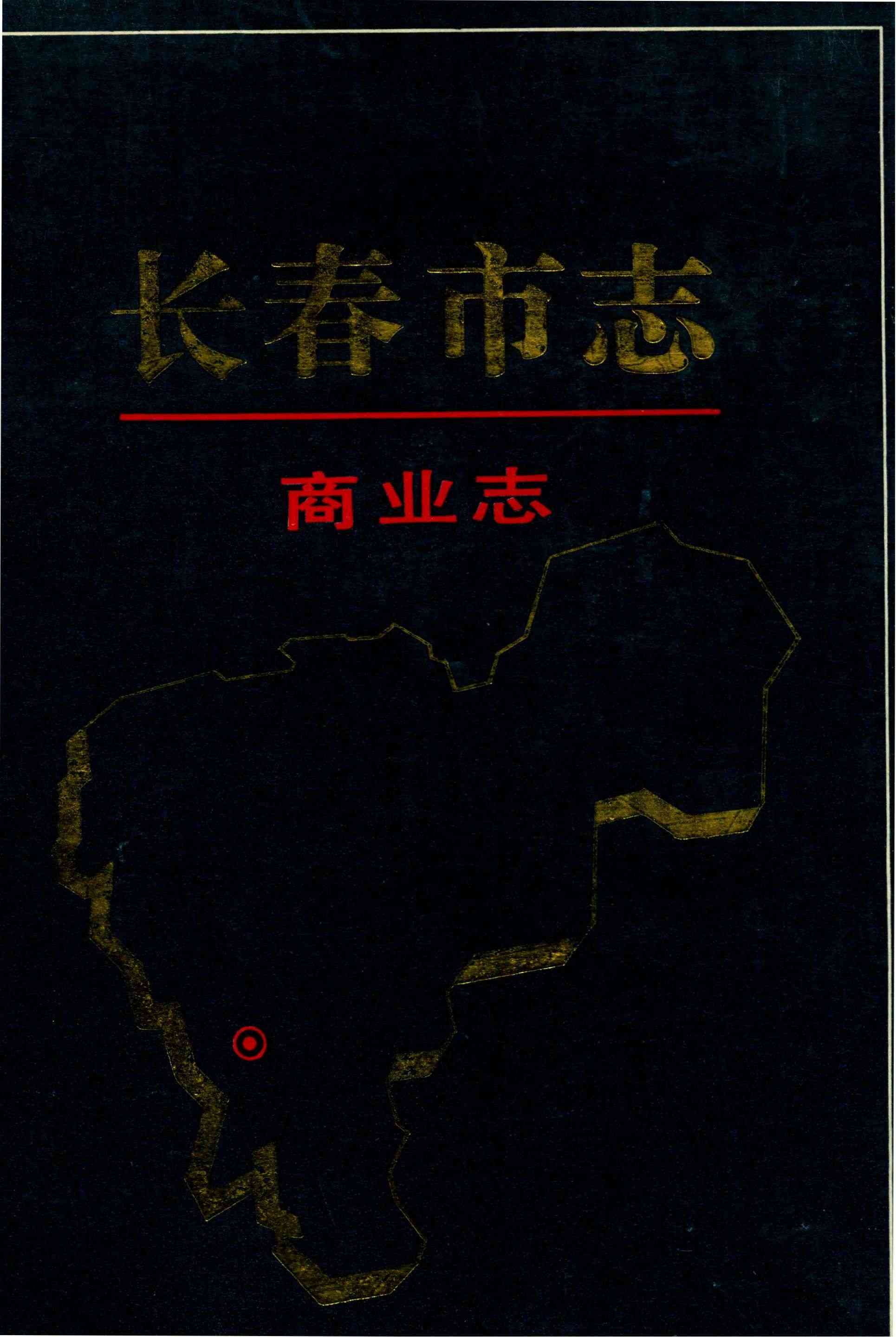
相关地名
长春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