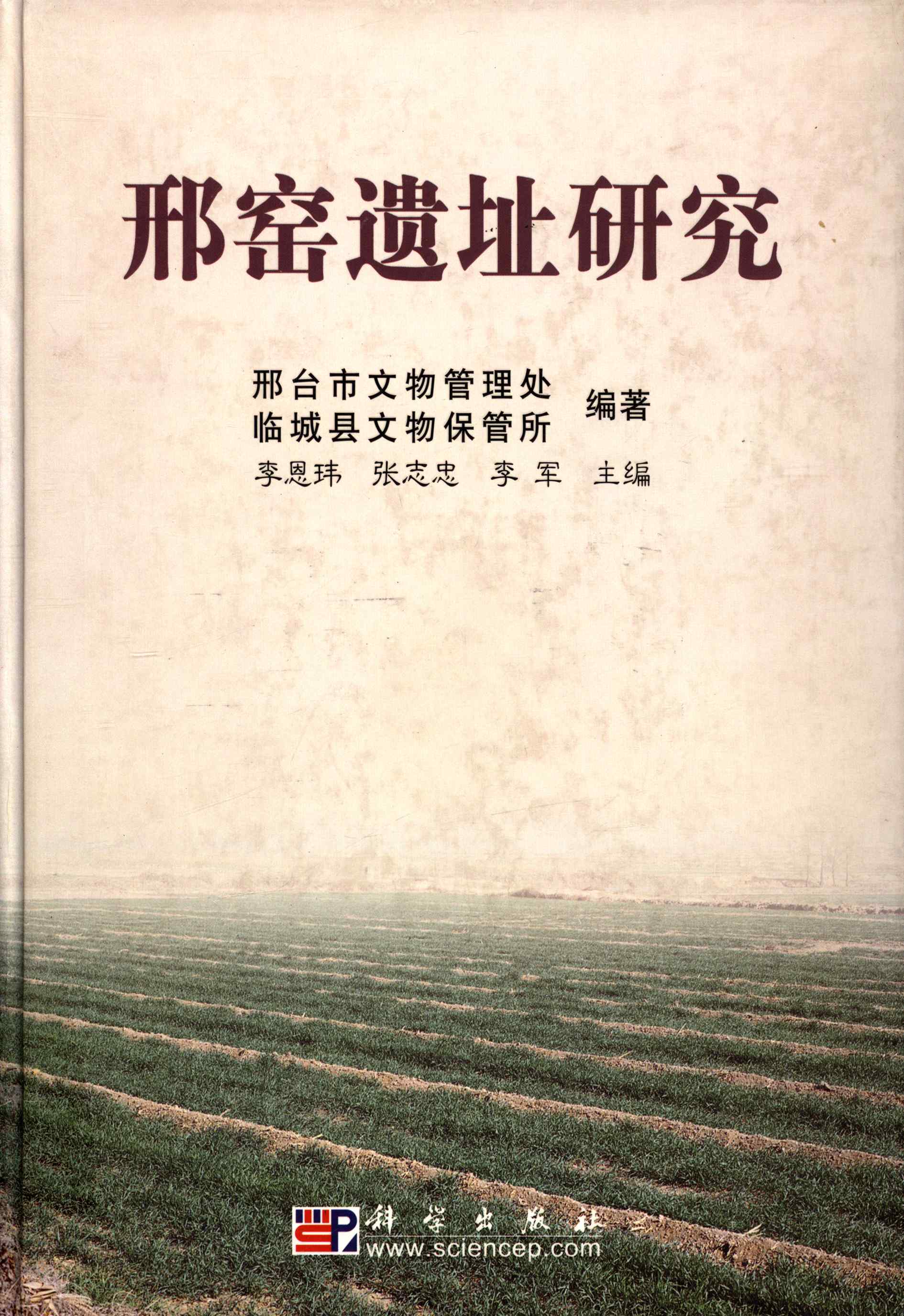内容
“邢窑”为我国唐代北方著名白瓷窑场之一,因首创白瓷烧造之先河,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末邢窑发现以来,伴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和增多,诸多专家、学者对邢窑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证和研究,笔者也参与其间进行了讨论[1]。自此,将邢窑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关于邢窑的一些问题有的在古陶瓷界尚有不同认识,有的还没有充分展开讨论,本文对尚未涉及的一些问题试作初步探讨,以谈个人浅见,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邢窑瓷器釉色的种类
邢窑是以烧制精美绝伦的白瓷而著称于世,一般提及邢瓷只是针对白瓷而言,其他类釉色的瓷器还不为人们所了解。调查资料证明,邢窑在烧制白瓷的同时,还烧制青釉瓷、黄釉瓷、黑釉瓷、酱色釉瓷、点彩釉瓷和三彩釉陶等多种釉色的瓷器。
白釉瓷白瓷为邢窑的主产品。器物胎体所施白色釉实际上是一种釉质很细,玻璃质极强的透明釉。这一特点使胎色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对釉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就是说,胎体的色调对釉的呈色有一定的衬托作用。早期的白瓷,胎体白度不高,呈灰白色,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在胎体的表面均施加白色化妆土进行护胎,因而釉色多呈乳白色,看起来好像有点浑浊之感。由于胎体和釉的膨胀系数有较大差异,釉层多有细碎的冰裂开片。唐代邢窑粗白瓷虽然也有化妆土护胎,釉色的白度还不够,但由于胎体毕竟稍为细致,已不见冰裂纹现象。细白瓷的胎体白净细腻,无须再用化妆土,施釉入窑烧制后,呈现出胎体的本来面目,釉色就显得洁白无瑕。尽管邢窑白瓷均为透明度很强的白色釉,但由于时代不同,釉的配方也可能有所不同,釉色的白度也存在着差异。具有隋代及以前风格的作品,釉色的白度较之唐代的白瓷稍为逊色。前者积釉处呈现出白中闪绿的色调,后者较少见到积釉现象,在某些器物的釉层厚处则呈现出白中闪蓝的色调,整体效果是白中微泛青色。这种外观上的特征差异,釉的化学组成不同是其主要因素,但与瓷器烧成的气氛和温度也有一定的关系。
青釉瓷也是一种强玻璃质釉料,和白瓷釉的区别是它本身含铁量较高。青瓷器物呈现的色调随着釉层的厚薄而有所变化。釉层厚的呈青绿色,色调深。釉层薄的呈青黄色,色调浅。邢窑青瓷器物多施化妆土护胎,釉层薄的作品,呈现出较浅的青黄色,这种色调已基本接近早期白瓷的色调。
黄釉瓷釉质大多细腻而有光亮,有的呈淡黄色。也有的呈深黄色。极少数的黄釉瓷作品釉质较粗,色调也显得暗淡。
黑釉瓷釉层一般较厚,釉质细,釉色大多漆黑光亮。这类釉色的瓷器,由于正烧的缘故,形成了上部釉层较下部为薄的现象。有的作品如罐,上部釉层较薄,显出黑褐色,下部则出现滴釉现象。
酱釉瓷釉质和黑色釉大致相同,一般釉层很薄,呈现出淡褐色调。
彩釉瓷色彩覆盖于釉层之下。在坯胎上先行施以点彩,然后罩以釉汁,胎、彩、釉同时高温一次烧成。
三彩釉陶属于低温铅釉的范畴,是铅和石英配制的一种透明釉。釉质很细,明亮光润且流动性很强,釉层有细小的开片。三彩釉分单彩、两彩和多彩三种。单色有黄色和深咖啡色,双彩和多彩主要有黄、绿、红、蓝、白等多种色素相间施用且釉层较为凝厚。工匠们巧妙的施釉方法,加上烧制时釉的流淌,色调从浓到淡,显得融合绚丽,斑驳多彩。
二、邢窑与北方诸白瓷窑口的关系
邢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唐人李肇在《国史补》所记:“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可见邢窑的白瓷销路之广,影响之深远。邢窑白瓷自北朝的创始,历经隋代、唐初的发展,李唐一代已经发展成为烧制白瓷的著名窑场。自此,邢成了我国陶瓷史上“南青”、“北白”的发展格局。应当肯定,唐代瓷器生产的卓越成就与邢窑的出现以及北方白瓷的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邢窑、巩县窑、定窑同属于北方的三大白瓷窑场,产品都曾作为贡品供朝廷使用。从上述各窑址出土的器物来看,他们有许多的共同点。均烧造碗、盘、壶、瓶、罐等类的白瓷器皿,尤其以碗、盘为最多。这一点三个窑口基本是一致的。巩县窑为河南烧造白瓷水平最高的一处窑场,唐开元中已向宫廷烧制贡瓷。武周、玄宗年间由于东都洛阳的繁荣使它的发展达到鼎盛。巩县窑烧制的白瓷其胎质呈灰白和土白两种。灰胎颗粒一般较粗含气孔。土胎较细,杂质极少。胎表多施化妆土,釉层较厚且釉色均匀细润光亮。碗类器物同邢窑产品相似,多为侈口,圆尖唇或翻沿圆唇,有圆饼足、玉璧足、浅圈足(玉环足)等几种类型。也曾发现过和邢窑相同的口沿略外撇的曲腹四出碗。瓷器的成型工艺和邢窑也基本相同,对口沿的处理也大致一样。定窑白瓷始烧于晚唐,比邢窑烧造白瓷的历史要晚的多。由于两窑在地理位置上相处不远,唐代白瓷产品的造型大多是仿制于邢窑,造型风格和邢窑相似。邢窑影响了早期定窑,晚唐五代邢窑逐渐走向衰落时,邢窑匠师去定窑从事制瓷生产是可能的,定窑是在继承邢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理化测试数据表明巩县窑白瓷胎釉中Fe2O3的含量分别为1.28%和0.57%,定窑分别为1.07%和0.96%。邢窑白瓷Fe203的含量为0.58~0.88%和0.49~0.98%。Fe2O3含量的高低,决定胎釉的白度和纯度。就其邢窑瓷片理化数据来看,Fe2O3含量低于巩、定二窑。因此邢窑器物的胎体和釉色的白度都高于上述二窑。诚然,胎釉的化学成分对瓷器的呈色关系至关重要这一点无可非议,但烧瓷技术的熟练程度不同,瓷器的工艺效果也就不相一致。邢窑工匠集多年烧造瓷器之经验,已能够严格控制窑炉温度,烧制火候掌握的恰到好处,瓷器显得洁白无瑕。定窑在唐代制瓷技术与邢窑相比要逊色的多,加上胎釉中Fe2O3含量稍高,瓷器的白度和邢窑对照,显示出一定的差异。巩县窑白瓷胎中Fe2O3含1.28%,白中带黄,呈土白色。胎泥原料处理的不太充分,颗粒结构粗糙,釉色因之显得白度不够,其工艺水平相当于邢窑的粗白瓷。
耀州黄堡窑场位于唐长安城京畿北部,它创始于初唐,盛唐时才烧造白瓷。因耀州地处唐朝腹地范围之内,盛唐之后邢窑、巩县窑白瓷贡往长安[2],得以在京师广泛流行。此时黄堡窑因环境条件和烧造技术上的原因,无法仿制出邢窑釉色细腻洁白,胎壁极薄的白瓷器皿。而巩县窑白瓷釉色乳黄和较厚的胎壁,技术精度并不像邢窑那样高。黄堡、巩县二窑胎土条件接近,当邢、巩二窑白瓷在京师供不应求时,黄堡窑场模仿巩县白瓷产品也就应运而生了[3]。黄堡窑制作的产品一种是细白瓷,釉色白中泛黄,具有乳浊之感。一种粗白瓷,胎质颗粒较大,粗疏多气孔,且胎色黄灰,釉下施化妆土护胎用以掩盖胎体上的瑕疵。器物造型与邢窑相似,表明耀州窑除与巩县窑的关系密切外,与邢窑也有不同程度的交流。
井陉窑发现于20世纪的80年代末期,所处地理位置介于邢、定二窑中间地带。东南一百公里为唐代“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邢窑窑场。东北百十公里是宋代独领风骚的定窑。井陉窑造瓷器的时间始于隋,灭于元,长达700年之久。它的烧造时间比邢窑烧造的历史稍晚,但早于定窑。李唐一代井陉窑与邢窑一样是一处以烧制白瓷为主的窑场[4]。因井陉窑距邢窑甚近,制瓷业必然受邢窑影响。井陉窑烧器物造型与邢窑相同,以白瓷碗为例与邢窑风格趋相一致,均为侈口,尖圆唇或圆唇,有圆实足、玉璧足、宽圈足(玉环足)。釉色也趋向于邢窑白瓷,不同的是胎体较厚。除此之外井陉窑还烧制同邢窑一样的黑釉、酱釉、黄釉瓷和釉下点彩器物。两窑产品趋向一致的造型、类似或相同的釉色都表明两窑之间的密切关系。
山西平定唐代所烧白瓷碗的造型风格与邢窑也完全一致,不同的是胎体较厚。平定窑所处位置与河北邢窑和定窑成三足鼎立之势,且又与井陉窑相距甚近,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尚有待于研究。
三、邢窑唐三彩
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劳动人民创造了无数罕见的珍品,唐三彩就是其中之一。邢窑虽以烧造白瓷而闻名于世。但就其装饰成就来讲最突出的就是烧制绚丽的三彩器。邢窑三彩从出土器物及标本残件来看有人物、动物和日用器皿三大类。人物有侍立俑、素烧佛像及佛龛。动物仅见马俑。人物俑均采用前后分模模制,动物俑则用模中压泥成坯,然后黏合而成。日用器皿有碗、罐、盘、杯、钵、盆、枕等。其器物造型与邢窑同期瓷器造型相一致,其中三彩环柄杯为仿唐金银器制品,其造型优美。加之三彩釉的流淌,显得五彩缤纷,绚丽多姿。和三彩器同时出土的窑具有三角支钉。支垫有大小之分,均呈抹角三角形饼状,下部平整,上置三个支钉,支钉呈乳突状。支垫上留有褐色釉滴,表明在烧成过程中被它支烧的器物曾将溶化流淌的三彩釉滴在这些支垫上。这些支具正是邢窑窑场烧造过唐三彩的实物证明。邢窑唐三彩和支烧工具的发现表明在唐代邢窑不仅烧制高温釉瓷器,也兼烧温釉的三彩器。它是继河南巩县、陕西黄堡之后我国发现的第三处烧造唐三彩窑场。
唐三彩的胎体制做均以含有一定杂质的高岭土为原料,然后在胎体上施以白色化妆土后入窑焙烧,器形烧成后在器物表面再施以矿物质为釉料的着色剂二次入窑烧成。由于釉色中含有铜、铁、钴、锰等元素,加之釉里加入炼铅溶渣和铅灰作助熔剂,经过800℃的低温烧制使釉色呈深绿、浅绿、黄、蓝、白、红、褐等多种色彩。邢窑烧制的三彩器其胎体有白胎、红胎和白中泛灰的粗胎三种类型。从坯胎的烧结程度来看,白色胎体比较坚硬,红胎和白中泛灰的粗胎较松软。其中白胎器物与巩县三彩白色胎体相同,均以瓷土做原料,制作过程中对瓷土的淘洗、陈腐较为精细,故烧制的器物吸水率低,表明烧结度高,故而胎体坚实且又致密,但烧结程度均达不到瓷化的标准。两窑器物釉色相比存在着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巩县三彩釉色绚丽,釉质有乳浊感。邢窑三彩虽不及巩县三彩绚丽多姿,但釉的质感很强。这点与黄堡三彩玻璃质感强的釉色较趋向一致。从烧造时代上看,巩县三彩出现于唐初,盛唐发展成熟,唐中期以后逐步衰退。黄堡的三彩盛唐始有发现,中晚唐尚在烧造。邢窑三彩就目前考古资料来看,始烧于唐早期。它的出现晚于巩县窑和耀州黄堡窑。其出土人物俑同河南巩县三彩窑址出土的“抱物俑”完全一致[5]。由此可见两窑关系密切。李唐一代邢、巩二窑同为北方著名烧造白瓷的窑场,所烧白瓷都曾作为贡品贡往长安,或作为商品而远销海外。两地窑工必然相互往来进行技艺交流。可以说邢窑白瓷的出现比巩县窑要早,而影响了巩县窑。巩县窑三彩器的创烧又早于邢窑,反之又影响了邢窑。这是两窑窑工多年来互相借鉴学习和交流的必然结果。因邢窑尚没有对遗址进行大规模揭露和发掘,就目前资料来看邢窑唐三彩烧造量极小,没有形成规模和批量生产[6]。其产量比京畿长安附近的黄堡窑场和紧邻东都洛阳的巩县窑要小的多。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李唐一代风靡天下的邢窑白瓷“天下无贵贱通用之”造成巨大社会需求量,白瓷成为烧制的主产品。另一方面,与唐三彩绚丽华贵,是专供上层社会人物使用或殉葬的物品而一般人享用不起也有关系。
唐末,安禄山、史思明起兵范阳(今涿州),安史之乱祸起河北。自此,藩镇割据,战事频繁,邢州首当其冲。据《新唐书》所载在会昌三年至光化元年邢州发生较大战争七次,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五代结束了唐王朝统治,全国统一局面遭到崩溃。邢窑唐三彩同邢窑白瓷一样从此一蹶不振走向消亡。
四、隋代精细透光白瓷
隋代精细透光白瓷始发现于1984年。当时在内丘西关北窑址地表采集到4件白瓷杯残件,其中1件在烧制过程中与匣钵粘连在一起[7]。如此精美之器如果不是在窑址上发现,又有粘连在窑具上的残片做证,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为当时产品。故当时我们将这种精细白瓷定为隋代产品[8]。对此,考古界和古陶瓷界尚有不同看法,叶喆民先生认为是唐代之物[9]。1988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布探方对内丘西关北窑址进行了试掘。揭露面积共36平方米,在灰坑中的隋代文化层内出土了精细透光白瓷200余片。这一发现亦证实这种精细透光白瓷确为隋代遗物无疑。
隋代结束了南北分立的局面。随着杨氏政权的日益巩固,和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刚刚结束了戎马生涯的最高统治者追求奢侈生活的欲望便日益膨胀起来。遂钦命御府监、太府丞何稠组织仿造波斯锦和玻璃器,以供御用。
何稠,中亚何国人。出身于精通西亚的粟特人家庭。这对其后来的西亚技术与我国传统技术相结合研制玻璃带来了极大便利条件。《隋书·何稠传》载“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即成,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玻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绿瓷指何物,金家广先生认为是何稠为复苏“久绝玻璃之作”通过经绿瓷而仿制“与真不异”的玻璃。绿瓷仿制玻璃必然选择窑场,南北朝分裂的局面形成后,北朝只好在距邺城较近的地点另辟烧瓷基地。河北内丘适处北朝腹地范围之内,且原料丰富,易于开采,林木茂盛,燃料取之不尽,加之滏阳河支流水源充足,交通便利。上述条件的形成,使制瓷业在内丘逐渐发展成强大的烧瓷中心,并成为北方烧造青瓷的窑口之一。故何稠“以绿瓷为主”的试验作坊可能选择内丘制瓷窑场。可喜的是在内丘西关北窑址中发现大量隋代玻璃质感极强的青瓷残片,玻璃釉层特厚,有的器物可达3毫米之多。且色泽呈浅绿色,与玻璃相比确有“与真不异”之感。故金家广先生认为这些青瓷产品是何稠仿制的玻璃器,并命名为“内丘仿玻璃绿瓷”或“何稠绿瓷”[10]。如果这一推论是正确的,内丘高档细白瓷的发现极有可能是何稠在内丘烧瓷基地仿制绿瓷的同时或仿制绿瓷成功之后的又一创举。
从内丘西关北窑址采集和出土精细透光白瓷来看,与隋代同期的青瓷、白瓷器物造型完全一致。其做工极为精细,制作十分规整。且胎釉浑然一体晶莹光润,釉面有的洁白如雪,有的呈乳汁玻璃状光泽。这种精细透光白瓷与尚处于发展阶段的隋代白瓷相比,要胜其百倍,就连唐代“盈”字、“翰林”款贡品白瓷与之相比也相差甚远,与现代白瓷相比亦毫无逊色之处。
就目前考古资料来看,这种精细透光白瓷仅发现于西关北一处窑址,内丘其他窑址所不见。墓葬出土物仅见河南巩县夹津口出土2件白瓷杯[11]。除此之外,其他隋代墓葬和遗址中尚无见到同类遗物出土的报道。目前可谓稀世珍品了。因此,它的使用主人也绝不是一般官吏。这就不得不使我们把它的出现与隋王室联系起来,这种产品可能是为隋室烧造的贡品,专供皇帝御用之器。过去,人们根据文献记载将邢瓷的进贡时间定为唐代。而今出土的隋代精细透光白瓷极有可能是何稠为隋王室所烧之器。如果这一推测成立的话,邢窑的进贡时间可提早到隋代。窑址调查表明精细透光白瓷的烧造时间仅限杨隋一代。它与前期的北朝白瓷无传承关联,与后期的唐代白瓷也没有渊源关系。从这点上看,着实令人难以理解。我国古代器物的演变规律一般为创始、发展、鼎盛、衰落四个时期,邢窑亦不例外。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邢窑白瓷创始于北朝,历经隋代、唐初的发展,中唐达到了鼎盛阶段。尚处于发展阶段的隋代白瓷较前代虽有进步,但大部分器物仍采用北朝时期在灰白的胎体上施化妆土,以掩盖胎体衬托白度这种方法。也就是说在烧制白瓷技术尚不成熟的情况下,精细透光白瓷突然出现在世人面前,昙花一现随即又无缘无故消失了,这一现象原因何在?为何唐初白瓷还是在承袭隋代普通白瓷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呢?是到唐中期才烧造出贡品细白瓷么?这一连串的问题更是令人费解。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当时精细透光白瓷是为满足隋朝皇室奢侈生活之欲专门派人为皇室研制的贡品。产品烧制成功后,皇室将制瓷配方控制起来,使邢窑工匠无法得到它。所以它与邢窑白瓷发展脉络不相一致,亦无渊源关系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也可能与隋朝短命有关。隋代立国仅28年,精细白瓷烧成后即被唐王朝所取代。在灭隋的战争中,各种生产力必然惨遭严重破坏,手工业亦不例外。窑场的毁灭,工匠的流失,制瓷配方的失传也是隋代精细透光白瓷销声匿迹的另一个原因。
关于精细白瓷的起源,以往陶瓷研究者认为始于明初的永乐年间。但永乐瓷器只达到半脱胎,成化时胎的薄度才达到几乎脱胎的地步[12]。从邢窑隋代精细透光白瓷来看,胎体厚度一般在1毫米左右,最薄的仅为0.7毫米,其制作水平已达到半脱胎,这无疑将我国薄胎瓷的烧造历史又上推了近千年。它的出现在中国陶瓷史和世界科技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五、邢窑“官”字款
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五代和辽、宋时期出现了“官”和“新官”的瓷器。这些“官”字款器在解放前就曾有出土,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解放后,随着此类器物出土的不断增多,才为国内外考古和古陶瓷界所关注,并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1984年唐代著名窑场——邢窑在内丘发现[13],考古调查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在窑址上发现唐代贡品“盈”字款瓷器。它的发现解决了西安、上海等地出土和馆藏“盈”字款的窑口问题。2003年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为了配合内丘县旧城改造,在拆迁礼堂建设步行商业街的工程中对建筑物地下的邢窑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晚唐文化层中发现10多片带有“官”字款的瓷片标本。“官”字款的首次发现无疑是邢窑考古的又一重要收获,它不但为邢窑的款识家庭又增添了新的品种。更重要的是为“官”字款的断代和“官”字款器物的窑口鉴别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实物资料。邢窑遗址所出“官”字款残件均为白瓷,器形为碗或盘,仅存底部。其足为圈足,除圈足无釉外器底均施满釉。“官”字均阴刻在器表底部圈足内的中心部位,分施釉前刻划与施釉后刻划两种,故字口亦出现有釉与无釉两种现象。所刻“官”字书体均为行书,字体大致雷同。
邢窑“官”字款的发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继定窑、耀州窑和赤峰缸瓦窑之后发现的第四处烧制“官”字款瓷器的窑口。上述窑场除耀州窑是一座以烧制青瓷为主的窑口外(发现的“官”字款器均为青瓷),其余三处窑场均为以烧制白瓷为主(烧制“官”字款器均为白瓷)。“官”字款的烧造时间,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邢窑出现在晚唐,定窑、耀州窑、赤峰缸瓦窑出现于稍晚的五代时期。四处窑场的共同点或为官窑(赤峰缸瓦窑为辽代官窑,定窑在五代即为官窑)或烧制贡品供宫廷使用。从这一点上看,“官”字器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四处窑场都与宫廷有着紧密的联系。于是有人提出“唐代瓷器有了长足进展,产品质量提高,使用普遍,形成官私通用的局面。我认为到了晚唐,官窑就应兴起”[14]。邢窑“盈”字款器的发现将官窑的兴起推到了唐代中期。
目前,我国内蒙、辽宁、北京、河北、西安、湖南、浙江等地出土“官”字款器100多件。出土最多的为西安火烧壁发现的一批窖藏瓷器,在完整的52件瓷器中带“官”字款的白瓷就有33件之多[15]。其次为定县五号宋代塔基出土“官”字款白瓷器18件[16]和浙江临安水邱氏墓中出土“官”字款白瓷3件,“新官”款白瓷11件[17]。其他器物均为零星出土,或来自于墓葬或出土于遗址。众多遗物的发现为“官”字款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但它们分属那个窑口的产品,有的已经搞清,有的看法不尽一致并引发颇多争议,至今还是未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究其原因,一方面与邢窑与定窑,定窑与赤峰缸瓦窑所烧白瓷造型接近,釉色相似不易区分有关,另一方面与烧造“官”字款的窑口发现不多也有关系。辽代官窑未发现之前,20世纪50年代初辽穆宗应历九年(公元959年)驸马赠卫国王墓出土4件“官”字款器[18引发了对“官”字款的讨论。金毓黻先生认为“凡有官字的白色瓷器并包括其他白色瓷器在内,都是辽国官窑出品”[19]。陈万里先生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辽国早期所用精美的白瓷很可能是曲阳的定窑所烧造”。还说“假定能在定窑的废墟碎片堆里找到“官”字的碎片,就可以证实了我的看法,为此我将保留这个“官”字器物的烧造地点”[20],后来冯先铭先生确曾在定窑遗址中发现带“官”字款的瓷片[21],实物印证了陈先生的观点。之后这种观点一直影响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赤峰缸瓦窑发现“官”、“新官”字款前。赤峰缸瓦窑“官”字款的发现重新甄别了一批辽瓷认为定瓷之物。
考古调查资料证实邢窑自唐中期的鼎盛,到唐代晚期已逐渐走向衰败。但此时的定窑白瓷烧制尚处在创始阶段,白瓷的质量根本无法与邢窑相抗衡。到五代时期烧制白瓷的技术才逐渐成熟而取代邢窑。定窑北宋之前制瓷工艺和烧制燃料与邢窑相同(定窑唐、五代时期以柴为燃料,烧还原气氛。器物釉色同邢瓷釉色趋向一致。北宋始改燃料为煤,烧氧化气氛,其釉色与邢窑白瓷明显不同,呈微黄色),到五代与邢窑晚唐白瓷产品质量亦相当。且定窑“官”字款发现较邢窑“官”字款早近半个世纪,误将邢窑“官”字款器定为定窑产品是有可能的。邢窑“官”字款的发现,对国内各地部分出土的“官”字款器亦有重新甄别之必要。西安火烧壁窖藏晚唐“官”字款白瓷作者根据陈万里先生首先提出“官”字款白瓷系定窑烧造之观点将这批瓷器定为定窑产品[22]。现在看来这种结论值得商榷。文中谈到这批瓷器“胎薄质细、瓷化程度很高。其釉质匀净,釉色白或白中闪青,碗盘器物的造型受唐代金银器的影响很大”[23]。这些特征、特点与邢瓷遗物多相一致。受金银器影响邢窑在唐代中期已出现仿金银器制品,遗址所出白瓷印花盘,深腹圈足杯和高足杯即是一例。从釉色白或白中闪青来看也具有邢窑釉色厚处白中闪蓝,整体色调白中微泛青色的这一特点,从时代上看,定窑烧造白瓷始于晚唐,此时尚不可能烧出如此精美之器供京室官宦之家享用。因而,这批瓷器极有可能为晚唐邢窑所制造。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白瓷,至今尚存争议。有的认为这批瓷器不是定窑产品[24]。有的认为带“官”字款的白瓷除了定窑和辽官窑之外,还应考虑到其他产地[25]。有人认为“定窑窑址出土的‘新官’字白瓷盘及其他白瓷器与临安出土的器物相印证,可以说解决了定窑‘官’、‘新官’款白瓷器的时代。而且也证明了临安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应是定窑的早期产品”[26]。也有人认为临安吴越国王钱镠之父钱宽及母水邱氏墓中出土的“官”、“新官”款器物为邢窑白瓷[27]。从钱宽墓出土15件细白瓷其制作精致,瓷化程度较高,釉色白略闪青黄这一点来看,也具有邢窑白瓷的特征。其白瓷盘与邢窑仿银制品海棠形白瓷盘形制相同,不同的是墓中出土物为素面,遗址所出有印花装饰。此墓与邢窑“官”字款时代相同,应为邢窑产品。至于墓中所出“新官”款只能说窑址现在尚无发现而已。除西安火烧壁白瓷窖藏及浙江临安钱宽墓出土“官”字款外,全国各地多有出土。因资料有限无法进行对照和分析,但不排除有些“官”字款器为邢窑烧造的可能性。当然,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待更多白瓷窑址的发现。
以往陶瓷研究者认为“官”与“新官”字款流行于五代未到北宋初的真宗这一历史时期内。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钱宽卒于859公元年的乾宁二年,葬于公元900年的唐光化三年)出土遗物的发现,将“官”、“新官”字款的出现时间又上推了半个世纪。唐代邢窑“官”字款的发现亦再次得到证实。
关于“官”、“新官”字款的含义,考古、古陶瓷界的专家和学者对此多有探讨。有人认为“这些产品是专为宫廷使用而生产的器物。它与一般瓷器有所不同,制瓷工人在器底划一“官”字以示区别,于是出现了“官”或“新官”字款的官窑器物”[28]。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官”字的含义“指官府而言,并非都是贡品,是为官府烧制而署的一种字款”。并结合各地出土物得出“官”字款白瓷“属于商品性质的瓷器”这一结论29]。笔者同意后一种说法。从目前全国各地出土“官”字款器范围之广、遗物之多这一现象来看,此种器物绝非皇家所独享的贡品。如为宫廷所享用之物,一般人就不可能得到和使用它。这点从定县塔基出土物亦可窥见一斑。如吴成训在施设“官”字款器上墨书题记“叁拾文足陌”。观其书法、文字甚为拙劣,可见不为当时的上层人物,只是在建塔时施舍几件瓷器以了心愿。又如“僧崇裕施叠(碟)子壹只”之题记,应为僧侣崇裕的平常使用之器[30]。再从全国各地出土“官”字款墓葬中的墓主人身份情况来看。除辽代驸马赠卫国王墓和吴越国王钱镠之父钱宽及夫人水邱氏墓中所葬人物为上层官宦之家外,其他墓主人身份多为一般阶层人物。墓中所出“官”字款也并非贡品。表明除官宦之家使用外,一般人仍可使用它。如果“官”字款器是宫廷贡品,那么这种产品就不是可交换的商品,一般人怎能得到它又在死后葬于墓穴之中呢?从出土遗物质量上看,辽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出土“官”字款白瓷大碗为一件严重变形的残次品[31]。西安火烧壁窖藏出土地点为唐长安城的安定坊,唐代这里为官宦人家之住所。窖藏瓷器中有一件五瓣浅口碗胎体严重变形[32]。从这一点来看,这批器物也不会是贡品。综上所述种种迹象表明,“官”字款器不是专为宫廷而制作的贡品。从官宦之家到普通阶层都可使用这一情况来看,当是一种流通的商品,所以人们极容易得到它。“新官”字款邢窑尚无发现,从钱宽墓出土“新官”器物来看,并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只能说目前尚无发现而已。关于“官”或“新官”字款孰早孰晚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新官”是对“官”字而言。也就是说“官”字款出现要早于“新官”。从唐后期藩镇政权反复更迭官府不断变换来看“官”与“新官”款识的出现时间不会相隔时间太久。换言之,也就是说“官”字款出现不久,随着藩镇政权的更迭随即出现了“新官”字款。之后“官”字款并未废弃而与“新官”字款同时使用以作为官府烧造瓷器的一种标记罢了。晚唐钱宽、水邱氏墓中“官”与“新官”器物同时出土亦得到了证实。关于定窑所出“官”与“新官”应为仿效邢窑而来。辽代官窑赤峰缸瓦窑所出“官”与“新官”器物或许与中原地区流入辽地的定窑工匠有关。辽建国初期,阿保机对手工业极其重视,将中原百工技艺人员掠来使其从事旧业,以促进辽国的经济发展。据文献所记,有辽以来,入主中原不可胜纪,仅明确占领定州就有数次之多。五代后梁德龙元年(公元921年)辽太祖神册二年“庚申,皇太子率王郁略地定州”。“俘虏甚众”,用以在辽地“建城置州”。世宗以定州俘户置民工织纴多技巧”[33],从定州多次遭受辽国入侵来看,定州制瓷工匠虽未提及,但从赤峰缸瓦窑遗址及辽墓出土白釉瓷器,可以明显看出受到定窑白瓷的影响。从辽国各项手工业工匠均为战争掠来这一点来看,定窑制瓷工匠被掠到辽国重操旧业肯定不乏其人了。定窑工匠在制瓷过程中将“官”与“新官”款识又用在辽官窑器物之上以作为官府瓷器的一种标记是有可能的,当然这一问题还有待于更多考古资料的发现来加以证实。
一、邢窑瓷器釉色的种类
邢窑是以烧制精美绝伦的白瓷而著称于世,一般提及邢瓷只是针对白瓷而言,其他类釉色的瓷器还不为人们所了解。调查资料证明,邢窑在烧制白瓷的同时,还烧制青釉瓷、黄釉瓷、黑釉瓷、酱色釉瓷、点彩釉瓷和三彩釉陶等多种釉色的瓷器。
白釉瓷白瓷为邢窑的主产品。器物胎体所施白色釉实际上是一种釉质很细,玻璃质极强的透明釉。这一特点使胎色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对釉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就是说,胎体的色调对釉的呈色有一定的衬托作用。早期的白瓷,胎体白度不高,呈灰白色,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在胎体的表面均施加白色化妆土进行护胎,因而釉色多呈乳白色,看起来好像有点浑浊之感。由于胎体和釉的膨胀系数有较大差异,釉层多有细碎的冰裂开片。唐代邢窑粗白瓷虽然也有化妆土护胎,釉色的白度还不够,但由于胎体毕竟稍为细致,已不见冰裂纹现象。细白瓷的胎体白净细腻,无须再用化妆土,施釉入窑烧制后,呈现出胎体的本来面目,釉色就显得洁白无瑕。尽管邢窑白瓷均为透明度很强的白色釉,但由于时代不同,釉的配方也可能有所不同,釉色的白度也存在着差异。具有隋代及以前风格的作品,釉色的白度较之唐代的白瓷稍为逊色。前者积釉处呈现出白中闪绿的色调,后者较少见到积釉现象,在某些器物的釉层厚处则呈现出白中闪蓝的色调,整体效果是白中微泛青色。这种外观上的特征差异,釉的化学组成不同是其主要因素,但与瓷器烧成的气氛和温度也有一定的关系。
青釉瓷也是一种强玻璃质釉料,和白瓷釉的区别是它本身含铁量较高。青瓷器物呈现的色调随着釉层的厚薄而有所变化。釉层厚的呈青绿色,色调深。釉层薄的呈青黄色,色调浅。邢窑青瓷器物多施化妆土护胎,釉层薄的作品,呈现出较浅的青黄色,这种色调已基本接近早期白瓷的色调。
黄釉瓷釉质大多细腻而有光亮,有的呈淡黄色。也有的呈深黄色。极少数的黄釉瓷作品釉质较粗,色调也显得暗淡。
黑釉瓷釉层一般较厚,釉质细,釉色大多漆黑光亮。这类釉色的瓷器,由于正烧的缘故,形成了上部釉层较下部为薄的现象。有的作品如罐,上部釉层较薄,显出黑褐色,下部则出现滴釉现象。
酱釉瓷釉质和黑色釉大致相同,一般釉层很薄,呈现出淡褐色调。
彩釉瓷色彩覆盖于釉层之下。在坯胎上先行施以点彩,然后罩以釉汁,胎、彩、釉同时高温一次烧成。
三彩釉陶属于低温铅釉的范畴,是铅和石英配制的一种透明釉。釉质很细,明亮光润且流动性很强,釉层有细小的开片。三彩釉分单彩、两彩和多彩三种。单色有黄色和深咖啡色,双彩和多彩主要有黄、绿、红、蓝、白等多种色素相间施用且釉层较为凝厚。工匠们巧妙的施釉方法,加上烧制时釉的流淌,色调从浓到淡,显得融合绚丽,斑驳多彩。
二、邢窑与北方诸白瓷窑口的关系
邢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唐人李肇在《国史补》所记:“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可见邢窑的白瓷销路之广,影响之深远。邢窑白瓷自北朝的创始,历经隋代、唐初的发展,李唐一代已经发展成为烧制白瓷的著名窑场。自此,邢成了我国陶瓷史上“南青”、“北白”的发展格局。应当肯定,唐代瓷器生产的卓越成就与邢窑的出现以及北方白瓷的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邢窑、巩县窑、定窑同属于北方的三大白瓷窑场,产品都曾作为贡品供朝廷使用。从上述各窑址出土的器物来看,他们有许多的共同点。均烧造碗、盘、壶、瓶、罐等类的白瓷器皿,尤其以碗、盘为最多。这一点三个窑口基本是一致的。巩县窑为河南烧造白瓷水平最高的一处窑场,唐开元中已向宫廷烧制贡瓷。武周、玄宗年间由于东都洛阳的繁荣使它的发展达到鼎盛。巩县窑烧制的白瓷其胎质呈灰白和土白两种。灰胎颗粒一般较粗含气孔。土胎较细,杂质极少。胎表多施化妆土,釉层较厚且釉色均匀细润光亮。碗类器物同邢窑产品相似,多为侈口,圆尖唇或翻沿圆唇,有圆饼足、玉璧足、浅圈足(玉环足)等几种类型。也曾发现过和邢窑相同的口沿略外撇的曲腹四出碗。瓷器的成型工艺和邢窑也基本相同,对口沿的处理也大致一样。定窑白瓷始烧于晚唐,比邢窑烧造白瓷的历史要晚的多。由于两窑在地理位置上相处不远,唐代白瓷产品的造型大多是仿制于邢窑,造型风格和邢窑相似。邢窑影响了早期定窑,晚唐五代邢窑逐渐走向衰落时,邢窑匠师去定窑从事制瓷生产是可能的,定窑是在继承邢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理化测试数据表明巩县窑白瓷胎釉中Fe2O3的含量分别为1.28%和0.57%,定窑分别为1.07%和0.96%。邢窑白瓷Fe203的含量为0.58~0.88%和0.49~0.98%。Fe2O3含量的高低,决定胎釉的白度和纯度。就其邢窑瓷片理化数据来看,Fe2O3含量低于巩、定二窑。因此邢窑器物的胎体和釉色的白度都高于上述二窑。诚然,胎釉的化学成分对瓷器的呈色关系至关重要这一点无可非议,但烧瓷技术的熟练程度不同,瓷器的工艺效果也就不相一致。邢窑工匠集多年烧造瓷器之经验,已能够严格控制窑炉温度,烧制火候掌握的恰到好处,瓷器显得洁白无瑕。定窑在唐代制瓷技术与邢窑相比要逊色的多,加上胎釉中Fe2O3含量稍高,瓷器的白度和邢窑对照,显示出一定的差异。巩县窑白瓷胎中Fe2O3含1.28%,白中带黄,呈土白色。胎泥原料处理的不太充分,颗粒结构粗糙,釉色因之显得白度不够,其工艺水平相当于邢窑的粗白瓷。
耀州黄堡窑场位于唐长安城京畿北部,它创始于初唐,盛唐时才烧造白瓷。因耀州地处唐朝腹地范围之内,盛唐之后邢窑、巩县窑白瓷贡往长安[2],得以在京师广泛流行。此时黄堡窑因环境条件和烧造技术上的原因,无法仿制出邢窑釉色细腻洁白,胎壁极薄的白瓷器皿。而巩县窑白瓷釉色乳黄和较厚的胎壁,技术精度并不像邢窑那样高。黄堡、巩县二窑胎土条件接近,当邢、巩二窑白瓷在京师供不应求时,黄堡窑场模仿巩县白瓷产品也就应运而生了[3]。黄堡窑制作的产品一种是细白瓷,釉色白中泛黄,具有乳浊之感。一种粗白瓷,胎质颗粒较大,粗疏多气孔,且胎色黄灰,釉下施化妆土护胎用以掩盖胎体上的瑕疵。器物造型与邢窑相似,表明耀州窑除与巩县窑的关系密切外,与邢窑也有不同程度的交流。
井陉窑发现于20世纪的80年代末期,所处地理位置介于邢、定二窑中间地带。东南一百公里为唐代“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邢窑窑场。东北百十公里是宋代独领风骚的定窑。井陉窑造瓷器的时间始于隋,灭于元,长达700年之久。它的烧造时间比邢窑烧造的历史稍晚,但早于定窑。李唐一代井陉窑与邢窑一样是一处以烧制白瓷为主的窑场[4]。因井陉窑距邢窑甚近,制瓷业必然受邢窑影响。井陉窑烧器物造型与邢窑相同,以白瓷碗为例与邢窑风格趋相一致,均为侈口,尖圆唇或圆唇,有圆实足、玉璧足、宽圈足(玉环足)。釉色也趋向于邢窑白瓷,不同的是胎体较厚。除此之外井陉窑还烧制同邢窑一样的黑釉、酱釉、黄釉瓷和釉下点彩器物。两窑产品趋向一致的造型、类似或相同的釉色都表明两窑之间的密切关系。
山西平定唐代所烧白瓷碗的造型风格与邢窑也完全一致,不同的是胎体较厚。平定窑所处位置与河北邢窑和定窑成三足鼎立之势,且又与井陉窑相距甚近,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尚有待于研究。
三、邢窑唐三彩
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劳动人民创造了无数罕见的珍品,唐三彩就是其中之一。邢窑虽以烧造白瓷而闻名于世。但就其装饰成就来讲最突出的就是烧制绚丽的三彩器。邢窑三彩从出土器物及标本残件来看有人物、动物和日用器皿三大类。人物有侍立俑、素烧佛像及佛龛。动物仅见马俑。人物俑均采用前后分模模制,动物俑则用模中压泥成坯,然后黏合而成。日用器皿有碗、罐、盘、杯、钵、盆、枕等。其器物造型与邢窑同期瓷器造型相一致,其中三彩环柄杯为仿唐金银器制品,其造型优美。加之三彩釉的流淌,显得五彩缤纷,绚丽多姿。和三彩器同时出土的窑具有三角支钉。支垫有大小之分,均呈抹角三角形饼状,下部平整,上置三个支钉,支钉呈乳突状。支垫上留有褐色釉滴,表明在烧成过程中被它支烧的器物曾将溶化流淌的三彩釉滴在这些支垫上。这些支具正是邢窑窑场烧造过唐三彩的实物证明。邢窑唐三彩和支烧工具的发现表明在唐代邢窑不仅烧制高温釉瓷器,也兼烧温釉的三彩器。它是继河南巩县、陕西黄堡之后我国发现的第三处烧造唐三彩窑场。
唐三彩的胎体制做均以含有一定杂质的高岭土为原料,然后在胎体上施以白色化妆土后入窑焙烧,器形烧成后在器物表面再施以矿物质为釉料的着色剂二次入窑烧成。由于釉色中含有铜、铁、钴、锰等元素,加之釉里加入炼铅溶渣和铅灰作助熔剂,经过800℃的低温烧制使釉色呈深绿、浅绿、黄、蓝、白、红、褐等多种色彩。邢窑烧制的三彩器其胎体有白胎、红胎和白中泛灰的粗胎三种类型。从坯胎的烧结程度来看,白色胎体比较坚硬,红胎和白中泛灰的粗胎较松软。其中白胎器物与巩县三彩白色胎体相同,均以瓷土做原料,制作过程中对瓷土的淘洗、陈腐较为精细,故烧制的器物吸水率低,表明烧结度高,故而胎体坚实且又致密,但烧结程度均达不到瓷化的标准。两窑器物釉色相比存在着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巩县三彩釉色绚丽,釉质有乳浊感。邢窑三彩虽不及巩县三彩绚丽多姿,但釉的质感很强。这点与黄堡三彩玻璃质感强的釉色较趋向一致。从烧造时代上看,巩县三彩出现于唐初,盛唐发展成熟,唐中期以后逐步衰退。黄堡的三彩盛唐始有发现,中晚唐尚在烧造。邢窑三彩就目前考古资料来看,始烧于唐早期。它的出现晚于巩县窑和耀州黄堡窑。其出土人物俑同河南巩县三彩窑址出土的“抱物俑”完全一致[5]。由此可见两窑关系密切。李唐一代邢、巩二窑同为北方著名烧造白瓷的窑场,所烧白瓷都曾作为贡品贡往长安,或作为商品而远销海外。两地窑工必然相互往来进行技艺交流。可以说邢窑白瓷的出现比巩县窑要早,而影响了巩县窑。巩县窑三彩器的创烧又早于邢窑,反之又影响了邢窑。这是两窑窑工多年来互相借鉴学习和交流的必然结果。因邢窑尚没有对遗址进行大规模揭露和发掘,就目前资料来看邢窑唐三彩烧造量极小,没有形成规模和批量生产[6]。其产量比京畿长安附近的黄堡窑场和紧邻东都洛阳的巩县窑要小的多。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李唐一代风靡天下的邢窑白瓷“天下无贵贱通用之”造成巨大社会需求量,白瓷成为烧制的主产品。另一方面,与唐三彩绚丽华贵,是专供上层社会人物使用或殉葬的物品而一般人享用不起也有关系。
唐末,安禄山、史思明起兵范阳(今涿州),安史之乱祸起河北。自此,藩镇割据,战事频繁,邢州首当其冲。据《新唐书》所载在会昌三年至光化元年邢州发生较大战争七次,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五代结束了唐王朝统治,全国统一局面遭到崩溃。邢窑唐三彩同邢窑白瓷一样从此一蹶不振走向消亡。
四、隋代精细透光白瓷
隋代精细透光白瓷始发现于1984年。当时在内丘西关北窑址地表采集到4件白瓷杯残件,其中1件在烧制过程中与匣钵粘连在一起[7]。如此精美之器如果不是在窑址上发现,又有粘连在窑具上的残片做证,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为当时产品。故当时我们将这种精细白瓷定为隋代产品[8]。对此,考古界和古陶瓷界尚有不同看法,叶喆民先生认为是唐代之物[9]。1988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布探方对内丘西关北窑址进行了试掘。揭露面积共36平方米,在灰坑中的隋代文化层内出土了精细透光白瓷200余片。这一发现亦证实这种精细透光白瓷确为隋代遗物无疑。
隋代结束了南北分立的局面。随着杨氏政权的日益巩固,和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刚刚结束了戎马生涯的最高统治者追求奢侈生活的欲望便日益膨胀起来。遂钦命御府监、太府丞何稠组织仿造波斯锦和玻璃器,以供御用。
何稠,中亚何国人。出身于精通西亚的粟特人家庭。这对其后来的西亚技术与我国传统技术相结合研制玻璃带来了极大便利条件。《隋书·何稠传》载“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即成,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玻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绿瓷指何物,金家广先生认为是何稠为复苏“久绝玻璃之作”通过经绿瓷而仿制“与真不异”的玻璃。绿瓷仿制玻璃必然选择窑场,南北朝分裂的局面形成后,北朝只好在距邺城较近的地点另辟烧瓷基地。河北内丘适处北朝腹地范围之内,且原料丰富,易于开采,林木茂盛,燃料取之不尽,加之滏阳河支流水源充足,交通便利。上述条件的形成,使制瓷业在内丘逐渐发展成强大的烧瓷中心,并成为北方烧造青瓷的窑口之一。故何稠“以绿瓷为主”的试验作坊可能选择内丘制瓷窑场。可喜的是在内丘西关北窑址中发现大量隋代玻璃质感极强的青瓷残片,玻璃釉层特厚,有的器物可达3毫米之多。且色泽呈浅绿色,与玻璃相比确有“与真不异”之感。故金家广先生认为这些青瓷产品是何稠仿制的玻璃器,并命名为“内丘仿玻璃绿瓷”或“何稠绿瓷”[10]。如果这一推论是正确的,内丘高档细白瓷的发现极有可能是何稠在内丘烧瓷基地仿制绿瓷的同时或仿制绿瓷成功之后的又一创举。
从内丘西关北窑址采集和出土精细透光白瓷来看,与隋代同期的青瓷、白瓷器物造型完全一致。其做工极为精细,制作十分规整。且胎釉浑然一体晶莹光润,釉面有的洁白如雪,有的呈乳汁玻璃状光泽。这种精细透光白瓷与尚处于发展阶段的隋代白瓷相比,要胜其百倍,就连唐代“盈”字、“翰林”款贡品白瓷与之相比也相差甚远,与现代白瓷相比亦毫无逊色之处。
就目前考古资料来看,这种精细透光白瓷仅发现于西关北一处窑址,内丘其他窑址所不见。墓葬出土物仅见河南巩县夹津口出土2件白瓷杯[11]。除此之外,其他隋代墓葬和遗址中尚无见到同类遗物出土的报道。目前可谓稀世珍品了。因此,它的使用主人也绝不是一般官吏。这就不得不使我们把它的出现与隋王室联系起来,这种产品可能是为隋室烧造的贡品,专供皇帝御用之器。过去,人们根据文献记载将邢瓷的进贡时间定为唐代。而今出土的隋代精细透光白瓷极有可能是何稠为隋王室所烧之器。如果这一推测成立的话,邢窑的进贡时间可提早到隋代。窑址调查表明精细透光白瓷的烧造时间仅限杨隋一代。它与前期的北朝白瓷无传承关联,与后期的唐代白瓷也没有渊源关系。从这点上看,着实令人难以理解。我国古代器物的演变规律一般为创始、发展、鼎盛、衰落四个时期,邢窑亦不例外。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邢窑白瓷创始于北朝,历经隋代、唐初的发展,中唐达到了鼎盛阶段。尚处于发展阶段的隋代白瓷较前代虽有进步,但大部分器物仍采用北朝时期在灰白的胎体上施化妆土,以掩盖胎体衬托白度这种方法。也就是说在烧制白瓷技术尚不成熟的情况下,精细透光白瓷突然出现在世人面前,昙花一现随即又无缘无故消失了,这一现象原因何在?为何唐初白瓷还是在承袭隋代普通白瓷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呢?是到唐中期才烧造出贡品细白瓷么?这一连串的问题更是令人费解。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当时精细透光白瓷是为满足隋朝皇室奢侈生活之欲专门派人为皇室研制的贡品。产品烧制成功后,皇室将制瓷配方控制起来,使邢窑工匠无法得到它。所以它与邢窑白瓷发展脉络不相一致,亦无渊源关系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也可能与隋朝短命有关。隋代立国仅28年,精细白瓷烧成后即被唐王朝所取代。在灭隋的战争中,各种生产力必然惨遭严重破坏,手工业亦不例外。窑场的毁灭,工匠的流失,制瓷配方的失传也是隋代精细透光白瓷销声匿迹的另一个原因。
关于精细白瓷的起源,以往陶瓷研究者认为始于明初的永乐年间。但永乐瓷器只达到半脱胎,成化时胎的薄度才达到几乎脱胎的地步[12]。从邢窑隋代精细透光白瓷来看,胎体厚度一般在1毫米左右,最薄的仅为0.7毫米,其制作水平已达到半脱胎,这无疑将我国薄胎瓷的烧造历史又上推了近千年。它的出现在中国陶瓷史和世界科技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五、邢窑“官”字款
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五代和辽、宋时期出现了“官”和“新官”的瓷器。这些“官”字款器在解放前就曾有出土,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解放后,随着此类器物出土的不断增多,才为国内外考古和古陶瓷界所关注,并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1984年唐代著名窑场——邢窑在内丘发现[13],考古调查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在窑址上发现唐代贡品“盈”字款瓷器。它的发现解决了西安、上海等地出土和馆藏“盈”字款的窑口问题。2003年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为了配合内丘县旧城改造,在拆迁礼堂建设步行商业街的工程中对建筑物地下的邢窑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晚唐文化层中发现10多片带有“官”字款的瓷片标本。“官”字款的首次发现无疑是邢窑考古的又一重要收获,它不但为邢窑的款识家庭又增添了新的品种。更重要的是为“官”字款的断代和“官”字款器物的窑口鉴别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实物资料。邢窑遗址所出“官”字款残件均为白瓷,器形为碗或盘,仅存底部。其足为圈足,除圈足无釉外器底均施满釉。“官”字均阴刻在器表底部圈足内的中心部位,分施釉前刻划与施釉后刻划两种,故字口亦出现有釉与无釉两种现象。所刻“官”字书体均为行书,字体大致雷同。
邢窑“官”字款的发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继定窑、耀州窑和赤峰缸瓦窑之后发现的第四处烧制“官”字款瓷器的窑口。上述窑场除耀州窑是一座以烧制青瓷为主的窑口外(发现的“官”字款器均为青瓷),其余三处窑场均为以烧制白瓷为主(烧制“官”字款器均为白瓷)。“官”字款的烧造时间,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邢窑出现在晚唐,定窑、耀州窑、赤峰缸瓦窑出现于稍晚的五代时期。四处窑场的共同点或为官窑(赤峰缸瓦窑为辽代官窑,定窑在五代即为官窑)或烧制贡品供宫廷使用。从这一点上看,“官”字器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四处窑场都与宫廷有着紧密的联系。于是有人提出“唐代瓷器有了长足进展,产品质量提高,使用普遍,形成官私通用的局面。我认为到了晚唐,官窑就应兴起”[14]。邢窑“盈”字款器的发现将官窑的兴起推到了唐代中期。
目前,我国内蒙、辽宁、北京、河北、西安、湖南、浙江等地出土“官”字款器100多件。出土最多的为西安火烧壁发现的一批窖藏瓷器,在完整的52件瓷器中带“官”字款的白瓷就有33件之多[15]。其次为定县五号宋代塔基出土“官”字款白瓷器18件[16]和浙江临安水邱氏墓中出土“官”字款白瓷3件,“新官”款白瓷11件[17]。其他器物均为零星出土,或来自于墓葬或出土于遗址。众多遗物的发现为“官”字款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但它们分属那个窑口的产品,有的已经搞清,有的看法不尽一致并引发颇多争议,至今还是未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究其原因,一方面与邢窑与定窑,定窑与赤峰缸瓦窑所烧白瓷造型接近,釉色相似不易区分有关,另一方面与烧造“官”字款的窑口发现不多也有关系。辽代官窑未发现之前,20世纪50年代初辽穆宗应历九年(公元959年)驸马赠卫国王墓出土4件“官”字款器[18引发了对“官”字款的讨论。金毓黻先生认为“凡有官字的白色瓷器并包括其他白色瓷器在内,都是辽国官窑出品”[19]。陈万里先生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辽国早期所用精美的白瓷很可能是曲阳的定窑所烧造”。还说“假定能在定窑的废墟碎片堆里找到“官”字的碎片,就可以证实了我的看法,为此我将保留这个“官”字器物的烧造地点”[20],后来冯先铭先生确曾在定窑遗址中发现带“官”字款的瓷片[21],实物印证了陈先生的观点。之后这种观点一直影响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赤峰缸瓦窑发现“官”、“新官”字款前。赤峰缸瓦窑“官”字款的发现重新甄别了一批辽瓷认为定瓷之物。
考古调查资料证实邢窑自唐中期的鼎盛,到唐代晚期已逐渐走向衰败。但此时的定窑白瓷烧制尚处在创始阶段,白瓷的质量根本无法与邢窑相抗衡。到五代时期烧制白瓷的技术才逐渐成熟而取代邢窑。定窑北宋之前制瓷工艺和烧制燃料与邢窑相同(定窑唐、五代时期以柴为燃料,烧还原气氛。器物釉色同邢瓷釉色趋向一致。北宋始改燃料为煤,烧氧化气氛,其釉色与邢窑白瓷明显不同,呈微黄色),到五代与邢窑晚唐白瓷产品质量亦相当。且定窑“官”字款发现较邢窑“官”字款早近半个世纪,误将邢窑“官”字款器定为定窑产品是有可能的。邢窑“官”字款的发现,对国内各地部分出土的“官”字款器亦有重新甄别之必要。西安火烧壁窖藏晚唐“官”字款白瓷作者根据陈万里先生首先提出“官”字款白瓷系定窑烧造之观点将这批瓷器定为定窑产品[22]。现在看来这种结论值得商榷。文中谈到这批瓷器“胎薄质细、瓷化程度很高。其釉质匀净,釉色白或白中闪青,碗盘器物的造型受唐代金银器的影响很大”[23]。这些特征、特点与邢瓷遗物多相一致。受金银器影响邢窑在唐代中期已出现仿金银器制品,遗址所出白瓷印花盘,深腹圈足杯和高足杯即是一例。从釉色白或白中闪青来看也具有邢窑釉色厚处白中闪蓝,整体色调白中微泛青色的这一特点,从时代上看,定窑烧造白瓷始于晚唐,此时尚不可能烧出如此精美之器供京室官宦之家享用。因而,这批瓷器极有可能为晚唐邢窑所制造。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白瓷,至今尚存争议。有的认为这批瓷器不是定窑产品[24]。有的认为带“官”字款的白瓷除了定窑和辽官窑之外,还应考虑到其他产地[25]。有人认为“定窑窑址出土的‘新官’字白瓷盘及其他白瓷器与临安出土的器物相印证,可以说解决了定窑‘官’、‘新官’款白瓷器的时代。而且也证明了临安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应是定窑的早期产品”[26]。也有人认为临安吴越国王钱镠之父钱宽及母水邱氏墓中出土的“官”、“新官”款器物为邢窑白瓷[27]。从钱宽墓出土15件细白瓷其制作精致,瓷化程度较高,釉色白略闪青黄这一点来看,也具有邢窑白瓷的特征。其白瓷盘与邢窑仿银制品海棠形白瓷盘形制相同,不同的是墓中出土物为素面,遗址所出有印花装饰。此墓与邢窑“官”字款时代相同,应为邢窑产品。至于墓中所出“新官”款只能说窑址现在尚无发现而已。除西安火烧壁白瓷窖藏及浙江临安钱宽墓出土“官”字款外,全国各地多有出土。因资料有限无法进行对照和分析,但不排除有些“官”字款器为邢窑烧造的可能性。当然,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待更多白瓷窑址的发现。
以往陶瓷研究者认为“官”与“新官”字款流行于五代未到北宋初的真宗这一历史时期内。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钱宽卒于859公元年的乾宁二年,葬于公元900年的唐光化三年)出土遗物的发现,将“官”、“新官”字款的出现时间又上推了半个世纪。唐代邢窑“官”字款的发现亦再次得到证实。
关于“官”、“新官”字款的含义,考古、古陶瓷界的专家和学者对此多有探讨。有人认为“这些产品是专为宫廷使用而生产的器物。它与一般瓷器有所不同,制瓷工人在器底划一“官”字以示区别,于是出现了“官”或“新官”字款的官窑器物”[28]。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官”字的含义“指官府而言,并非都是贡品,是为官府烧制而署的一种字款”。并结合各地出土物得出“官”字款白瓷“属于商品性质的瓷器”这一结论29]。笔者同意后一种说法。从目前全国各地出土“官”字款器范围之广、遗物之多这一现象来看,此种器物绝非皇家所独享的贡品。如为宫廷所享用之物,一般人就不可能得到和使用它。这点从定县塔基出土物亦可窥见一斑。如吴成训在施设“官”字款器上墨书题记“叁拾文足陌”。观其书法、文字甚为拙劣,可见不为当时的上层人物,只是在建塔时施舍几件瓷器以了心愿。又如“僧崇裕施叠(碟)子壹只”之题记,应为僧侣崇裕的平常使用之器[30]。再从全国各地出土“官”字款墓葬中的墓主人身份情况来看。除辽代驸马赠卫国王墓和吴越国王钱镠之父钱宽及夫人水邱氏墓中所葬人物为上层官宦之家外,其他墓主人身份多为一般阶层人物。墓中所出“官”字款也并非贡品。表明除官宦之家使用外,一般人仍可使用它。如果“官”字款器是宫廷贡品,那么这种产品就不是可交换的商品,一般人怎能得到它又在死后葬于墓穴之中呢?从出土遗物质量上看,辽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出土“官”字款白瓷大碗为一件严重变形的残次品[31]。西安火烧壁窖藏出土地点为唐长安城的安定坊,唐代这里为官宦人家之住所。窖藏瓷器中有一件五瓣浅口碗胎体严重变形[32]。从这一点来看,这批器物也不会是贡品。综上所述种种迹象表明,“官”字款器不是专为宫廷而制作的贡品。从官宦之家到普通阶层都可使用这一情况来看,当是一种流通的商品,所以人们极容易得到它。“新官”字款邢窑尚无发现,从钱宽墓出土“新官”器物来看,并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只能说目前尚无发现而已。关于“官”或“新官”字款孰早孰晚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新官”是对“官”字而言。也就是说“官”字款出现要早于“新官”。从唐后期藩镇政权反复更迭官府不断变换来看“官”与“新官”款识的出现时间不会相隔时间太久。换言之,也就是说“官”字款出现不久,随着藩镇政权的更迭随即出现了“新官”字款。之后“官”字款并未废弃而与“新官”字款同时使用以作为官府烧造瓷器的一种标记罢了。晚唐钱宽、水邱氏墓中“官”与“新官”器物同时出土亦得到了证实。关于定窑所出“官”与“新官”应为仿效邢窑而来。辽代官窑赤峰缸瓦窑所出“官”与“新官”器物或许与中原地区流入辽地的定窑工匠有关。辽建国初期,阿保机对手工业极其重视,将中原百工技艺人员掠来使其从事旧业,以促进辽国的经济发展。据文献所记,有辽以来,入主中原不可胜纪,仅明确占领定州就有数次之多。五代后梁德龙元年(公元921年)辽太祖神册二年“庚申,皇太子率王郁略地定州”。“俘虏甚众”,用以在辽地“建城置州”。世宗以定州俘户置民工织纴多技巧”[33],从定州多次遭受辽国入侵来看,定州制瓷工匠虽未提及,但从赤峰缸瓦窑遗址及辽墓出土白釉瓷器,可以明显看出受到定窑白瓷的影响。从辽国各项手工业工匠均为战争掠来这一点来看,定窑制瓷工匠被掠到辽国重操旧业肯定不乏其人了。定窑工匠在制瓷过程中将“官”与“新官”款识又用在辽官窑器物之上以作为官府瓷器的一种标记是有可能的,当然这一问题还有待于更多考古资料的发现来加以证实。
附注
[1][7][8]贾永禄、贾忠敏、李振奇:《谈邢窑》《河北陶瓷》1991年第2期。
[2]《大唐六典》,《新唐书》。
[3]王小蒙:《试论唐代黄堡白瓷的发展》、《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4期。
[4]孟繁峰:《井陉窑金代印花模子的相关问题》,《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本。
[5][6]贾成惠等:《浅议邢窑唐三彩》稿本。
[9]叶喆民:《三议邢窑》,《河北陶瓷》1986年第4期。
[10]金家广:《试揭何稠绿瓷之迷》,《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2期。
[11]王莉英:《关于白瓷的起源与产地》,《中国古陶瓷研究》创刊号。
[12]冯先铭等:《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13]内丘县文物保管所:《河北内丘邢窑遗址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第9期。
[14][28]冯永谦:《“官”和“新官”字款瓷器之研究》,文物出版社,《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
[15][22][23][29][32]王长启、成安生:《西安火烧壁发现晚唐“官”字款白瓷》,《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4期。
[16][30]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第8期。
[17]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
[18]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赤峰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8期。
[19]金毓黻:《略论近期出土的辽国历史文物》,《考古通讯》1956年第4期。
[20]陈万里:《我对辽墓出土几件瓷器的意见》,《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1期。
[21]冯先铭:《陶瓷浅说·定窑》、《文物》1959年第7期。
[24]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市文管会:《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天文图及“官”字款白瓷》,《文物》1979年第12期。
[25]冯先铭:《有关临安钱宽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问题》,《文物》1979年第12期。
[26]李辉柄:《关于“官”、“新官”款白瓷产地问题的探讨》,《文物》1984年第12期。
[27]蔡乃武:《<茶经·四之器>质疑——兼论瓯窑、越窑、邢窑及相互关系》,《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本。
[31]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2期。
[33]《辽史》卷二《太祖本纪》,卷三四《兵卫志》,卷三九《地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