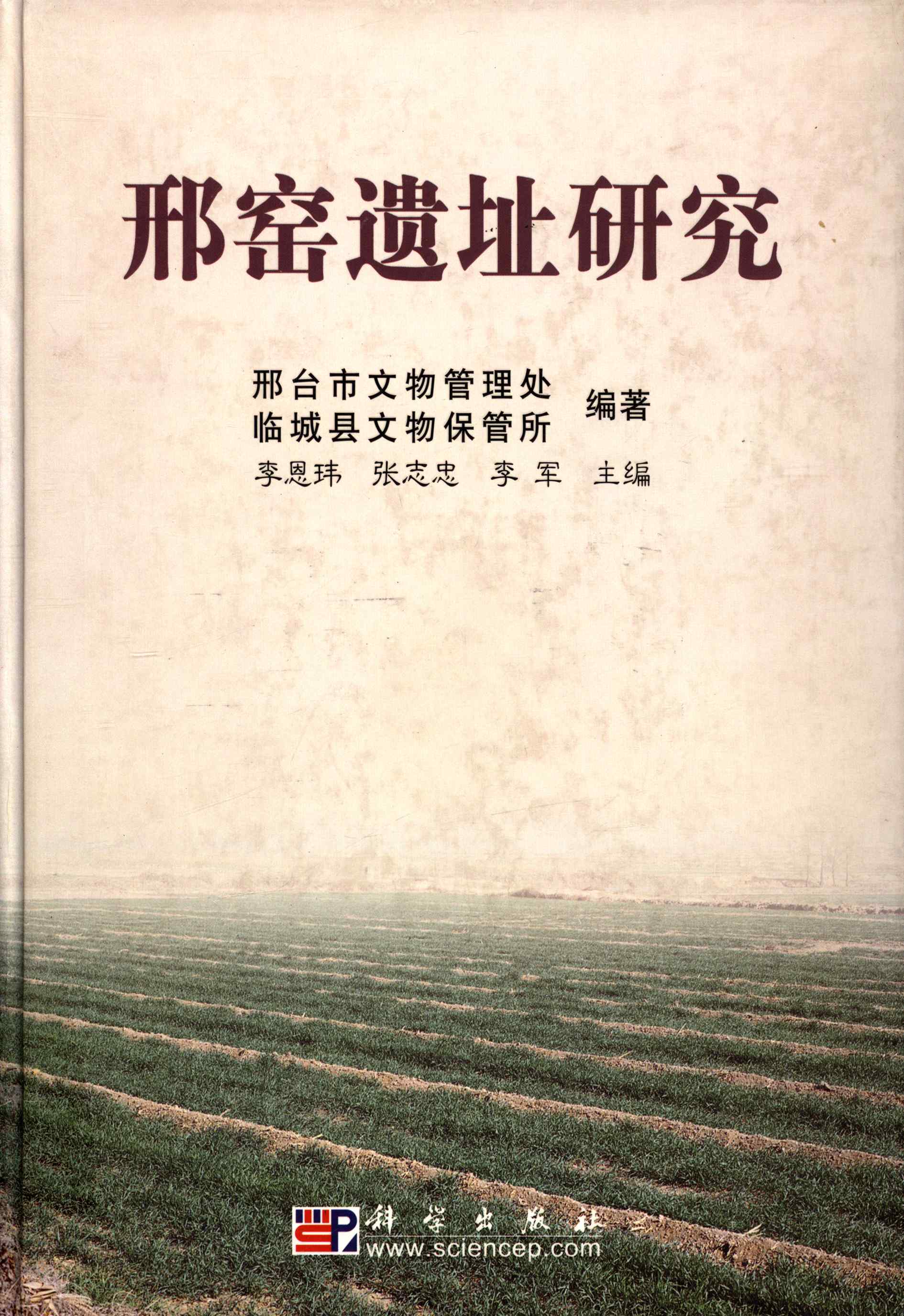内容
一、引言
唐代经济昌盛,文化繁荣,百工技艺均有高度成就。制瓷业亦不例外,当时金银器、漆器使用的逐渐衰退和铜器的禁制,以及斗茶之风的日益盛行,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瓷器的产量迅速增加,其制作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一时期,名窑辈出。南方出现了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系统,其产品“类玉”、“类冰”。北方则出现了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系统,生产的瓷器“类银”、“类雪”。自此形成了我国唐代瓷器生产“南青北白”的发展局面。
陆羽《茶经》云“邢州磁白茶色红”记载了邢窑烧造的白釉瓷。皮日休《茶中杂咏·茶瓯诗》曰“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说明了邢瓷的器物特征。《大唐六典》载“河北道贡邢州瓷器”,李肇《国史补》记“内丘白瓷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指出了邢州瓷的销售情况和烧造地点。尽管诸多文献中对邢窑有较详细的记载,并对邢瓷的特征,釉色及窑场所在地多有论及,由于长期以来未能找到其窑址,邢窑的面貌和内涵却无从得知,遂成为陶瓷界的“不解之谜”。1980年河北临城发现了唐代瓷窑遗址四处[1],出土了一些细白瓷标本,得以对北方邢瓷产品初见端倪。1984年在内丘境内发现古瓷窑遗址28处,除唐代邢窑遗址外,尚发现了烧制具有北朝、隋代瓷器特点的白瓷窑址[2],至此邢窑之谜得以解开。
关于邢窑的一些问题,有的在古陶瓷研究界尚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还没充分展开讨论。本文根据邢窑调查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对邢窑几个问题作一粗浅探讨,旨在抛砖引玉,敬请方家给予批评指正。
二、邢窑名称及产地
邢窑之名的含义,笔者认为有广义和狭义之别。顾名思义,邢窑之“邢”是邢州之简称,凡地处邢州范围之内的窑场,均应属于邢窑的范畴。受邢窑影响,其产品和邢瓷基本类似的制瓷业作坊,亦可称之为邢窑系或其分支,这是广义的解释。至于狭义的说法,是专指代表白瓷发展成就,烧制大量贡品而被载入文献的邢窑窑场。本文所论及的“邢窑”是就狭义而言。
邢瓷之研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邢窑在何处这一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研究邢瓷也就无从谈起了。
1980年在临城县治西北5公里的祁村一带发现唐代白瓷窑址后,曾在考古、古陶瓷界引起震动。诸多专家、学者对祁村窑址进行了考察,因为从地表存物的细瓷和粗瓷所具有的特征来看,它们和唐墓出土物以及存世的唐代白瓷比较对照,就其胎质、造型和釉色均极为相似[3]。部分学者认为祁村窑就是邢窑的一部分,至少也是邢窑的正统或亲支近派。并对窑址的地理位置也做了考证和推测,认为临城和内丘交界处的地理区划,时合时分,而窑址正处于这一地带。古时以州命名当是泛指,这样看来,邢窑窑址既不在邢台也不在内丘,而是在与内丘交界的临城县[4]。然而这一说法在当时并未被学术界所普遍接受。其主要争论焦点在于唐代李肇《国史补》中记载的邢窑在古称邢州的内丘县,而临城不属于邢州的范围之内,真正的邢窑应当到内丘去找[5]。但当时内丘境内的窑址尚未发现,坚信邢窑在内丘的说法因根据不足而缺乏说服力。
1984年,内丘邢窑遗址发现之后,证实了邢窑在内丘之说的正确性。但祁村窑是否邢窑,目前尚缺乏明确的结论。现在我们不妨把内丘窑和祁村窑所出器物做一对比分析,再将两县的地理沿革详加推敲,问题就会逐渐明朗了。
内丘唐代窑场集中在县城及其周围。从诸窑址出土白瓷标本来看,唐代细白瓷的产量约占白瓷产量的40%[6],并出土了典型的邢瓷贡品“盈”字款、“翰林”款标本。细白瓷作品其造型规整,制作精细,品种极为丰富。其胎质细腻,釉色洁白微闪蓝。扭曲变形的次品,上釉不匀和有积釉的作品极少见到。表明该窑在制坯、修坯工序上要求极为严格,已经能够适当地控制窑膛中温度,有较高的制瓷技术[7]。祁村窑址出土的瓷片标本中“类银”、“类雪”的细白瓷数量不及内丘,仅占白瓷产量的20%[8]。其他多为胎质粗糙,釉色发灰发黄的粗白瓷。造型也不及内丘的产品规整,修坯工序也略次。细白瓷如碗的底部有不少作品留有刀削痕迹,玉璧底足心往往留下乳突,不甚光滑。不同程度的施釉不匀和积釉现象也不少见,积釉处呈草绿色。釉色与内丘窑亦有不同,内丘窑产品多白中闪蓝,色调偏冷;祁村窑器物多为白色。积釉是由于施釉不均匀或烧成温度控制不佳所致,而釉色的差异说明两地的配釉方法有所不同,这尚需以后化验对比才能证实。但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从内丘窑址堆积中均有大量牛、马骨骼及牙齿推测,当时配制釉料时很可能掺入了动物骨灰。而祁村窑目前尚未发现有兽骨遗存的现象。总之,内丘、祁村窑场可能由于瓷土的来源与提纯,瓷釉的配制乃至烧成温度的高低以及其他诸多原因,形成了两窑产品之差异。
关于内丘和临城的地理沿革,内丘在隋以前称中丘县,因隋室讳“忠”,隋开皇初改称内丘县。县治所自北魏由现西丘村迁徙今治,至今未改。历史上除隋开皇三年至大业二年和唐武德四年曾隶属赵州外,一直归邢州管辖。临城自隋至唐初曾为房子县,其治所在今县治西南五公里的南台村南隅,唐玄宗天宝元年始改房子为临城并迁今治[9]。唐代临城属赵州,历史上从未属邢州。
由此可见,内丘和临城在同一大行政区内时合时分仅见于隋代和唐初。唐代两县的边界虽不能详细断定,但从唐前期临城县治在今县治西南五公里这一点来看,今临城之地似无属内丘的可能。而位于县治以北的祁村一带的窑址所在地则更非赵州莫属了。古代我国习惯以州命窑,正如磁州窑所在的磁县在磁州的辖区内,定窑所在的曲阳也在定州的范围之中,邢窑所在地当然要在邢州区域内,而决不会设置于赵州之域的临城县。显而易见,祁村窑恰恰缺乏当时被称为邢窑的最基本的条件了。《国史补》一书是庸人李肇做左司郎中时所著,成书于公元824年之后。书中所载是唐开元至长庆百余年间之事。李肇对于当时烧制贡品的邢窑地点应该说是清楚的,误记的可能性不大。况且内丘窑的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又十分吻合,说明邢窑产地在当时邢州的内丘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综上所述,邢窑的真正烧造地点在内丘。严格地说,将祁村窑称为邢窑的说法还有待做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从另一方面讲,由于祁村窑和邢窑相距甚近,制瓷生产必受邢窑影响,产品的造型和邢瓷也基本相似,属于邢窑系也是理所当然的。但这和称之为邢窑尚有所不同,正如安阳天禧镇窑、汤阴鹤壁窑属于磁州窑系而不能称之为磁州窑一样。
三、邢窑白瓷的产生与发展
“邢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过去,由于它的真正烧造窑址未被发现,其发生和发展过程一直没有能搞清楚。1984年内丘邢窑遗址被发现,并获得众多的实物标本,“邢窑之谜”才得以真正揭晓。
考古资料证明,青瓷的发展是在南方,北方青瓷的出现要比南方晚得多,但白瓷的发展却早于南方。邢窑是我国白瓷发展的代表窑,烧制白瓷的历史比其他白瓷窑要早。因此,究其邢窑白瓷的出现与发展,无疑对研究我国白瓷的起源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般来讲,每处窑场的兴衰都历经创始、发展、鼎盛、衰落四个阶段。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邢窑白瓷创始于北朝,历经隋代、唐初的发展,达到了唐代的鼎盛阶段,唐末五代走向衰败。
(一)创始时期
公元439年,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方,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社会状况由大动荡过渡到安定时期。之后,孝文帝实行了均田制,允许手工业者可以自己经营生产[10]。这一政策的实行,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制瓷业亦不例外,这点在北方同时期墓葬里瓷器出土量的迅速增多亦可得到证实。
白瓷是在烧制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种由青瓷到白瓷的转变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为什么我国白瓷首先出现于北方而不在南方这一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多有探讨。有人认为,白色表示悲哀,因此,形成了一种对纯素的白色的禁忌心理,这种心理不利于白瓷的早日出现[11]。也有人认为,一是青瓷在南方的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因而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传统风俗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是不易改变的。北方和南方不同,白瓷在北方出现以前,人们还没有形成使用青瓷的习惯,所以,白瓷易于使人接受。二是烧造技术与工艺上的原因[12]。笔者认为后一种说法比较可信。邢窑的早期青瓷产品,胎质虽不及南方青瓷致密,但就釉色而言却各有千秋。南方青瓷的釉色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有半木光。邢窑青瓷和南方不同,釉色分青绿和青黄两种,玻璃质较强。由于釉的玻璃质感强,一般器物的釉色随着胎色的变化而变化。胎质粗糙,胎色灰褐的器物呈青绿色。胎质较细,胎色黄白的作品则呈青黄色。这类釉色已基本接近早期白瓷的色调了。由于胎质及胎色的变化,白胎瓷既卫生,又给人以明快、舒服之感。邢窑窑工在青釉瓷的基础上,减少了铁的含量,创造了白瓷釉,白瓷也就应运而生了。早期白瓷的胎体多呈灰白色,为了改变胎体的颜色,增强瓷器的白度,邢瓷匠师在施釉的部位,增施化妆土工艺。这些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白瓷,很大程度上是利用釉的玻璃质感强这一特点用化妆土来衬白的。这些北朝的白瓷,在邢窑白瓷发展序列中,尚处于创始时期。虽然这些白瓷的白度还不够,与隋唐时期的白瓷相比有明显的原始性,但已是名副其实的白瓷了。自此,打破了商周以来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白瓷生产的先河,为唐代邢窑和北方白瓷的生产奠定了基础,对唐代白瓷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发展时期
如果说北朝白瓷尚处于早期的创始阶段,那么到隋代无论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较前有了长足的进展。内丘西关窑址调查表明,隋代已烧制出数量相当可观的白瓷了,与青瓷的产量相比可平分秋色。此时,白瓷中大部分器物还需施用化妆土进行护胎。胎质较北朝细腻坚实,釉色稳定,玻璃质感增强。釉色洁白的作品也成为此时的成功之作。更有甚者,在窑址采集到四件细白瓷杯残片,杯壁极薄,仅厚1~1.5毫米,胎釉浑然一体,洁白如雪,光润晶莹,瓷化程度极强,与现代白瓷相比亦毫无逊色之处。隋代能够烧制如此精美之器,如果不是在窑址上发现,又有粘连在窑具上的残片做证,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过去人们根据文献记载将邢瓷的进贡时间定为唐代,而今发现的隋代高档白瓷数量极少,可能是为皇室所做的特制器皿。如果这一推测成立的话,邢瓷进贡的时间就可能提早到隋代。
隋代高档细白瓷的发现,无疑是邢窑调查的重大收获。遗憾的是在具有北朝和初唐风格的瓷器标本中,尚没有发现具有此种特点的作品,也没有找到和它有渊源关系的同类。这类瓷器是否还有其他式样的产品,到唐代是否还有烧造,有待于以后经过对窑址的正式发掘,资料的不断完备来证实这些问题。总之,隋代细白瓷的出现标志着邢窑的制瓷技术日臻成熟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三)鼎盛时期
唐代结束了隋末以来的战乱局面,为唐王朝的经济繁荣创造了条件。邢窑经隋、唐初的发展,积多年烧造之经验,邢窑匠师已能很好的掌握制瓷原料的特性,进一步精选制瓷原料,成形、装饰、烧成工艺精益求精,创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产品——邢窑白瓷。窑址调查表明,唐代邢窑以烧制白瓷为主导。初唐之后白瓷使用化妆土的现象已基本消失了。细白瓷胎体致密洁白,釉色光润无瑕。从唐初之前的器外施半釉,底足露胎,改变为内外施满釉,底足心亦施釉。品种造型丰富多彩,趋于多样化,餐具、茶具、酒具、文具、盥洗具、储藏具、灯具、药用具、玩具、佛教用品及明器,无所不有。这直接反映了邢瓷已渗入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产品制作精工,一丝不苟,都当之无愧地为邢窑的代表作品。
中唐,正值邢窑的鼎盛期,这时期部分作品已出现了款识。就目前所见到的有“盈”字款20余件,“翰林”款1件。“盈”字款多见于碗、壶、盒等底足,“翰林”款仅见于罐类器的底部。字款均阴刻在器外底部的足心,分施釉前刻划与施釉后刻划两种。亦出现字口有釉、无釉两种现象。字体多为较胖的行楷字体。新发现的邢窑底款,以往不见于文献记载,为后人所不知。它的出土解决了西安、上海等地出土、馆藏“盈”字款,“翰林”款的窑口问题,并意味着邢瓷产品被宫廷和上层社会人物的使用和所受到的青睐。
(四)衰败时期
唐末,政治腐败,藩镇割据,战事频繁。据《新唐书》所载,在会昌三年至光化元年邢州发生较大的战争七次,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五代结束了唐王朝的统治,全国统一的局面遭到崩溃,战乱纷起使大批劳力被迫服役,手工业者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时期邢窑开始衰败,细白瓷少见,多烧制一些粗白瓷,且胎体粗松,胎色灰黄或灰青。有的器物亦出现釉下施化妆土的现象,制作工艺较前期粗糙,与邢窑细白瓷相比要逊色的多。从此,邢窑一蹶不振,无法与迅速崛起的定窑相竞争,而被其取代。
四、器形特点与装饰
邢窑始烧于北朝。这时期的制瓷技术尚未成熟,产品的种类较少,主要有碗、杯、盘、罐、瓶、钵等器皿。其造型特点是简朴、粗犷、古拙。一般器物的胎体厚重,如常见的深腹碗和杯,可分直口、敛口两式,腹较深,腹壁的外轮廓几乎由直线向下接近底部时内收,口沿处胎薄,下部厚实,平足较小。这样做的优点是增大容量,烧制时不易损坏。此种器形和南方同时期碗的造型基本相同,可能是受其影响所致。内丘西关窑址曾出土一件青瓷罐,盘口、肩部饰双泥条四系,上腹圆鼓,下腹稍瘦,器身高达50厘米,显得粗犷而有气魄,体现出邢窑早期器物的独特风格。
隋代邢瓷造型的显著变化,是器形的增多,由北朝的单一化趋于多样化了。隋邢瓷的造型特点总的来说是立式器皿增多,作品具有秀气、挺拔、豪放之感,多数器底足较高并微向外撇。碗、杯由直口或敛口演变为直口微侈,腹壁斜而直呈喇叭状,平足微凹,也有的做浅圈足。胎体的厚薄比例安排的比较协调,趋向于轻快,摆脱了厚重古朴的形式。罐一般无颈或短颈,系略高于口或与口平齐。瓶则多做盘口、流肩。瓶、罐的腹部由最大腹径在上部渐渐阔大呈近椭圆形,显得修长而不失稳重。高足盘是隋瓷中最为典型的一种器物,南北各地的窑场都大量烧造,它的基本特征是浅盘式,下面以空心的喇叭状高足来支承。邢瓷高足盘,最常见的有平底、侈口,或口沿外翻、圜底、弧腹、尖唇沿等式样。
可能是由于隋末唐初的战乱,使社会经济受到破坏的原因,初唐时期白瓷的产量和质量虽都优于隋代,精美的细白瓷作品却不多见,在造型上也无所建树。一般器物的形体较大,由隋代的秀长、挺拔向浑圆饱满过渡。
初唐之后,唐王朝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受其他工艺品的影响和人们审美观的提高,形制新颖,造形优美的邢瓷制品也就应运而生了。碗类器物由深腹演变为浅腹式,直腹变为曲腹或弧腹。口与底径的比例多为1:2。器形在统一中又有变化,如碗有多种形制,主要为敞口、敛口、折腰、花口四种。口沿可分圆唇、尖唇、圆唇外翻三种。足又分平足、圈足、玉璧足、玉环足四种。杯的形制也别具一格,有的做浅腹式,下饰鸟头型三足,增加了器物的神韵。另有仿银器的深腹圈足杯、高足杯,其造型灵巧而雅致,为邢窑工匠将金银器造型艺术用于陶瓷上的卓越创造。罐、鍑、钵腹部鼓圆,罐多饰双系,鍑均有三兽蹄足,其作品具有体态丰盈、浑厚、庄重、大方之感。
中唐的邢瓷在造型方面主要表现在器壁薄而均匀,器物的外轮廓多采用弧度较大、线条注意曲直变化的手法,使其具有很高的艺术魅力,达到了美观与实用相结合的效果,这是唐代邢瓷最典型的造型风格。
在装饰方面,北朝时期不论是青瓷还是白瓷,都注重于实用为主,多为素面,纹饰很少。仅见凸凹弦纹和莲花纹。弦纹一般用以装饰器物的口沿或腹部。莲花纹则是在碗或杯的腹部刻划上较为简单的几朵莲花相向排列一周,这些莲花纹饰的线条看起来还不够流畅,表现出北朝邢窑在瓷器装饰艺术上的原始性,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但表明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艺术题材的莲花图案已装饰到瓷器上来。
目前,由于窑址还未进行正式发掘,没有充分的考古资料来揭示它的真面目。但就所采集的标本来看,邢窑在隋代已掌握并使用了刻花、印花、贴花等装饰技法,还出现了艺术性较高的雕塑品。
刻花使用尖状或扁状工具,刻划出各种柔细的线纹图案。
印花使用模具压印图案。可分为两种,一是用模具在未干的胎体上压印。二是把胎泥塞进带有图案的两片模具中挤压成形后,再沾上配好的泥浆扣在一起粘接成器。
贴花将手制或模制的饰件用泥浆粘贴在器物的外壁上,以达到装饰的效果。
雕塑先用练制好的胎泥堆塑成形,然后用刀雕琢。此种技法仅用于人物或动物俑上。
刻花一般为弦纹、莲花或六至八瓣的花瓣组成的花朵,用以装饰瓷器的内外腹部和盘的内底。
印花和贴花均用来装饰器物的外部。如在隋代的黄釉扁壶上,肩部饰有对称的鸳鸯二系,工匠们巧妙地将眼睛做成圆孔用以作为绳穿。腹周围饰联珠纹,中间花叶丛中二人相对脚踏莲瓣之上,一人作吹乐状,一人作乐舞状。隋代扁壶无论在造型上还是在装饰图案上,都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体现了隋代邢窑匠师的工艺及艺术水平,为隋代陶瓷造型中的上乘之作。在一件白瓷标本上,采用了印花和贴花并用的手法。因标本残缺不知为何种器形,据观察似为六棱或八棱器。器外和每个侧面相应用联珠纹组成一长方形,长方形内印有花卉,在侧面的结合处采用了贴花装饰技法,因瓷片太残,贴花的图案内容不得而知,仅可看到附件为先粘贴在器面上,然后才入窑烧造。
雕塑制品人形灯和子母猴形象逼真,肌肉发达隆起,显示出雕琢技法娴熟,亦可称为上乘佳品。除此之外,尚发现飞禽类作品,饰孔雀羽毛纹饰,断头缺尾。此件作品不是实用器皿,当为装饰品。隋代设计新颖、造型优美的艺术瓷的出现,标志着邢瓷装饰艺术的进步和发展。
唐代邢窑仍沿用刻花、印花、贴花、雕塑等技法来装饰瓷器。和前所不同的是纹饰的线条比较流畅,图案的结构比较严谨,艺术手法更臻成熟,时代特点也较为明显。海棠形银盘是晚唐出现的新器形,主要形式之一由单线的花叶组成[13]。邢瓷中仿银制品海棠形白瓷印花盘残片同丹德丁卯桥出土的银盘形制基本相同[14],盘缘上的缠枝花纹,纤细规整,其纹饰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海棠型银盘边缘纹饰亦相似[15]。说明邢窑的仿银器制品,不但在造型上惟妙惟肖,而且在装饰方面的纹饰特点上也具相同的时代特征。莲花纹是邢瓷自北朝至唐所一直沿用的纹饰,从早期刻划简单的小朵莲花,到唐代制作精致的仰莲、覆莲纹佛像座的出现,一则表明了邢瓷装饰从简到繁的演变规律,二和这一时期大兴佛教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采集的众多瓷片标本中,发现有几片带有点彩的瓷片,点彩处釉层很厚,与无彩处相比明显突出。彩斑下出现了细碎的冰裂纹。观其瓷片,赭色的彩斑在洁白的器皿上显得清晰,悦目,给人以美的享受。目前,已知我国最早的使用釉下彩绘技法的是唐代长沙窑[16]。如果说釉下彩绘是长沙窑有历史意义的首创,则邢窑这种釉中点彩的技法也是一种创举。这种产品虽然现在发现的还太少,不能窥其全貌,相信随着邢窑的正式发掘和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对揭示釉中点彩这一技法的真面目将会有莫大的帮助。
唐代邢瓷的装饰成就,最突出的是烧制绚丽的三彩器。这是继河南巩县和陕西黄堡唐三彩窑址之后,我国发现的第三处烧制三彩的窑口。诚然,邢窑是以精湛的白瓷闻名于世,但三彩器的发现无疑为邢窑家族又添了新的品种。邢窑的三彩器,是在胎体上施加白色化妆土先行素烧,然后再施釉进行二次烧成。釉色可分为三种,前两种都是单色釉,呈黄和浅棕色。第三种是黄、绿、红、白、蓝等多种色素交错并用,色调从淡到浓,融合绚丽,工匠们以巧妙的施釉方法,加之烧制时釉的流淌,更显得活泼富丽,斑斑多彩。邢窑三彩同河南巩县三彩相比,其特点不同。主要表现在巩县三彩釉质具有乳浊感,而邢窑三彩不及巩县三彩华丽,但釉的质感很强。
邢窑发现之前,人们往往认为邢窑光素无饰,这种偏见是因考古资料缺少所致。从现已掌握资料来看,邢窑产品不但有装饰,而且手法众多。邢瓷尚素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它精湛的装饰技艺不能因此而被埋没。邢瓷的装饰艺术,同邢窑白瓷一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也应占有重要的地位。定窑是继邢窑之后兴起的宋代名窑。定窑的早期产品受邢窑之影响,造型风格和邢窑相似,装饰技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仿效邢窑。
五、窑具及装烧技法
邢窑的窑具有窑柱、垫圈、支珠、支钉,匣钵等。窑具的尺寸大小不同,均为瓷土制成,其中以三角支钉最多。
窑柱可分为两种。一种呈倒置蘑菇状,空心柄。另一种为圆柱束腰状,上下均为平面。
支钉分三角支钉和四齿支钉两种。三角支钉一面为平底,一面为尖状三乳突,乳突为手捏制,有的留下手指纹。四齿支钉,为空心柄状,柄呈圆形,一面有锯齿形四齿,一面有掏孔或做成平面。支珠和支钉同属支具,呈三棱锥形。
匣钵有直壁平底的筒状匣钵,直壁底斜收的漏斗状匣钵,敞口圜底的盘状匣钵和敛口平底的钵(盆)状匣钵四种。
窑具是研究装烧方法的重要依据。从采集的窑具可知,邢窑各时期及不同的瓷类,烧造工艺也不尽相同。
根据窑具与产品的粘连情况来看,邢窑早期白瓷还不见匣钵的使用,器底部留下的支钉痕迹说明是采用叠烧法烧成。装烧时,先将窑柱排放在窑台上,以淘洗后的瓷土废料(呈砂状)垫其下部使之固定。束腰圆柱式窑柱用以支承腹径较大的器物。蘑菇状窑柱用以支承碗、杯等腹径较小的器物。窑柱的平台上放上随手用胎泥捏制的圆形垫圈,其上放置产品,以起稳定作用。产品之内放置支钉,使器与器之间留有间隔,依次摞放。由于坯胎摞放承受压力较大,容易变形,故这一时期烧制的器物底部都较厚重。窑柱的高度,一般仅可摞放5~7件产品。观其窑柱的粘连物可知,第一个窑柱上产品摞满后,在柄之上放置泥条圈,再摞放另一个窑柱,以增加高度,直至适可而止。这种装烧方法的优点是,窑柱可使产品升高,便于充分利用窑膛内的空间和温度,能够使产品最大限度的受热。其缺点是除最上面的一件产品外,器内均留下支钉痕迹,显得美中不足。
隋代,邢窑开始使用保护坯胎不受火刺的匣钵。其匣钵多为筒式,质地粗糙较厚。一般白瓷碗、杯类产品仍用叠烧法烧造,单件烧的很少。以往,对于隋代是否使用匣体尚有争议。就目前资料所知,湖南湘阴窑为我国隋代使用匣钵的唯一窑场[17]。对此,曾有人提出异议[18]。邢窑匣钵的发现,得到证实。
唐代的匣钵除继续使用筒状匣钵外,又增添了新品种。匣钵均系拉坯成形,尺寸大小视所装器物的大小而定。筒状匣钵多装立式器皿,也有极少数的摞放坯胎。装烧时先将坯胎放入钵内,钵口置泥条圈后,再放相同规格的匣钵,摆放到适宜的高度而止。为防止火刺的侵入,最上件匣钵用盘式钵盖封口。漏斗状匣钵为一件一器单烧,装烧时将碗放入钵内,上面再置匣钵,依次摞放,码到一定的高度为止。这类匣钵一般均施黑釉或酱色釉,口沿和器外底部无釉,可能是为避免摞放时粘连的缘故。壁较其他形式的匣钵厚,内底放置支钉后装入产品。此种匣钵是否既作为匣钵烧制细白瓷,又可作为一种器皿使用,达到一举两得之目的。总之,匣钵的使用,是烧造工艺上的一大进步。特别是单件装烧的技法,使邢窑白瓷彻底消除了火刺和支钉痕。邢窑匣钵的出现与邢窑白瓷一样,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调查发现多处残窑炉底部,仅见到大量的柴灰,并无发现烧煤的迹象。说明邢窑烧瓷的燃料是柴而不是煤。邢瓷是在还原气氛中烧成,釉色白中泛青,具有冷色之美感,这也是烧柴一个佐证。我国用煤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汉代,邢窑所处的北朝至晚唐五代时期,煤的使用更是不断扩大。地质矿产资料表明,邢窑区域内的地表和沟谷中,有下二叠系山西组煤系地层的普遍出露,易于开采。邢窑舍煤而取柴的原因可能是太行山区古时柴草丰富,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另一方面,邢窑在用柴烧瓷的基础上,烧窑技术有了一个传统的模式,窑工熟练地掌握了还原烧成技术,对窑膛的温度已能严格地进行控制。煤的火焰较柴要短,温度难以掌握,从柴烧窑到用煤烧窑在窑炉的结构上和烧成阶段的技术上均要有一系列的变化,这需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来完成。邢窑的窑工在没有掌握烧煤技术时,可能就避长而扬短了。
六、邢窑之归属
在邢窑调查时,不断发现带有款识的器物标本,其中多见的是“盈”字款,其次为“翰林”款。目前,“盈”字和“翰林”款瓷器尚不多见。陕西曾出土三件“翰林”款白瓷罐,这种作品根据底部刻款的内容,基本上可推知是翰林院的定烧之物。“盈”字款瓷器除陕西大明宫遗址出土玉璧底中心刻“盈”字的白瓷碗外,上海博物馆亦收藏有一件传世品“盈”字款粉盒[19]。1975年河北省易县北韩村唐墓中出土一件“盈”字款执壶[20]。其他的尚未见报道。近年来,围绕“盈”字款瓷器问题。有人进行了多方探讨。由于大明宫遗址曾出土过“盈”字碗,为研究“盈”字款瓷器提供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大明宫是唐高宗李治以后诸皇帝料理政事之所,在这里出现“盈”字款瓷器可资说明此类作品应是宫廷用器。关于“盈”字的含义,最近据陆明华先生考证“盈”字款作品取唐代内府库“百宝大盈库”之“盈”字来作为标记,为供天子享用的定烧器[21]。这种判断基本上令人信服。如果这种推论是正确的,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问题:就是唐代烧制供品的窑口不只限于邢窑,其他如越窑、巩县等窑的贡品瓷器却怎么不以“盈”为标记?这种现象是否与窑场所属有关联?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充实,对于“官”、“新官”字款瓷器和官窑问题的研究也相继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将我国官窑的出现时间从宋代提早到了五代时期。冯永谦先生就曾明确地指出“唐代瓷器有了长足进展,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使用普遍,形成官私通用局面。我认为到了晚唐官窑就应兴起”[22]。现在我们根据邢窑产品和与之相似的祁村窑出土物以及内丘、临城两地的唐墓中瓷器出土情况试做分析,或对于认识上述问题会略有益处。
位于内丘的各处窑址中,曾发现过“盈”字款瓷器标本。临城境内的窑址也有带款识的瓷器出土,诸如“王”、“楚”、“弘”、“张”等这些多为姓氏刻铭。如果说“翰林”、“盈”字款瓷器是皇室的定烧器,那么这众多的姓氏刻铭,绝不会也是贡品。它的含义,或为单做共烧,以避免产品混杂,或为产品竞争而刻划窑主的姓氏,带有商标的性质。邢窑则没有发现姓氏刻铭。古时“盈”与“瀛”通用,虽然亦有“盈”姓,但内丘城众多的窑场为一家所有,或均出自“盈”姓工匠之手,似乎都不大可能。唯有“盈”字款瓷器是为宫廷烧造的贡品这种说法令人信服。从这一点上看,邢窑和祁村窑产品销路的来龙去脉就有点眉目了。
临城目前发现8座唐墓,除1座初唐墓葬中无细白瓷外,其余7座平民或低级官吏的小墓中出土文物62件,其中30件瓷器均为祁村窑的细白瓷[23]。比内丘唐墓出土的细白瓷数量要大得多。可以说,但凡临城发现唐墓就有细白瓷。而内丘这一现象实不多见,在发现众多的唐墓中,随葬细白瓷的仅有两座墓。如新城大和九年间的墓葬,出土陶俑、瓷器达70余件。按《大唐六典》所载的墓葬等级制度,应为五品官职之葬式,仅葬2件细白瓷高足杯和10余件黄釉及黑釉瓷。唐代,内丘、临城均生产细白瓷,相比之下,内丘的窑址数量及产量要比临城大得多,为什么墓葬出土情况却异乎寻常?是否可作如下推测,临城祁村窑系民窑,又处偏僻之地,烧瓷不受官府控制,产品销售自由,上层社会人物及当地人极容易得到它。而邢窑的细白瓷销售由官府控制,或专为宫廷而做,或远销海外和供上层社会使用,当地人难以得到,只能使用质量较次的粗白瓷和其他类瓷器。
至今内丘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很早以前,内丘烧造的瓷器很有名声,当时的皇帝传下了旨意,让为他烧造一个白瓷龙床,因为龙床的尺寸太大不好烧造,窑工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烧成,只好如实上奏,皇帝一怒之下就随口说出:“烧不成就散伙”。皇帝的话就是金口玉言,不能更改,所以窑场也就散伙了[24]。虽然民间传说不足以证明邢窑就是“官窑”,但是既有流传,也就有一定的来历。根据这一传说来看,邢窑与当时官府是有一定关系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邢窑在中唐以后已是一处官私通用的窑场,也就是说很可能就是早期所谓的“官窑”了。
七、余论
以往,瓷史研究者认为,北方白瓷出现于隋代。1971年在河南安阳洪河屯的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中首次发现了北朝的白瓷[25]。这批白瓷,无论胎釉的白度,烧成的硬度和吸水率,都无法和隋代的白瓷相比,显然尚处于创始阶段。尽管如此,它已是名副其实的白瓷了。这一发现,将我国白瓷的生产年代又上推了一个历史时期。于是有人提出北方早期白瓷的生产应在北齐。邢窑北朝烧造白瓷窑址的发现,证实了这种看法。
窑址调查表明,邢窑早期白瓷的生产比青瓷稍晚,它是在青瓷烧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青瓷到白瓷,是邢窑窑工经过长期实践的新成果,无疑是一种伟大的创举。它的发明是后来各种彩绘瓷器的基础,没有白瓷就不会有青花、釉里红、五彩、斗彩、粉彩等各种美丽的彩瓷[26]。它的出现,为我国陶瓷史开创了新的篇章,促进了陶瓷的繁荣和发展。在世界科技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
邢窑白瓷自北朝的创始,历隋代唐初的发展,到李唐一代已成为北方烧造白瓷的著名窑场,制作工艺精益求精,胎釉原料精心选制,装烧方法上日趋合理,采用单件正烧,制作了大量无与伦比的精美细白瓷。若以邢、越两窑相比,邢窑白瓷代表了当时白瓷的最高水平,越窑青瓷代表了当时青瓷的最高水平,这点就连抑白尚青的陆羽在道出“邢不如越”的同时,也道出“或邢州处越州上”的社会评价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总之,邢窑的鼎盛,改变了青瓷主导方向,使北方的白瓷生产获得了迅速发展,为后期定窑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1989年9月
唐代经济昌盛,文化繁荣,百工技艺均有高度成就。制瓷业亦不例外,当时金银器、漆器使用的逐渐衰退和铜器的禁制,以及斗茶之风的日益盛行,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瓷器的产量迅速增加,其制作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一时期,名窑辈出。南方出现了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系统,其产品“类玉”、“类冰”。北方则出现了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系统,生产的瓷器“类银”、“类雪”。自此形成了我国唐代瓷器生产“南青北白”的发展局面。
陆羽《茶经》云“邢州磁白茶色红”记载了邢窑烧造的白釉瓷。皮日休《茶中杂咏·茶瓯诗》曰“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说明了邢瓷的器物特征。《大唐六典》载“河北道贡邢州瓷器”,李肇《国史补》记“内丘白瓷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指出了邢州瓷的销售情况和烧造地点。尽管诸多文献中对邢窑有较详细的记载,并对邢瓷的特征,釉色及窑场所在地多有论及,由于长期以来未能找到其窑址,邢窑的面貌和内涵却无从得知,遂成为陶瓷界的“不解之谜”。1980年河北临城发现了唐代瓷窑遗址四处[1],出土了一些细白瓷标本,得以对北方邢瓷产品初见端倪。1984年在内丘境内发现古瓷窑遗址28处,除唐代邢窑遗址外,尚发现了烧制具有北朝、隋代瓷器特点的白瓷窑址[2],至此邢窑之谜得以解开。
关于邢窑的一些问题,有的在古陶瓷研究界尚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还没充分展开讨论。本文根据邢窑调查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对邢窑几个问题作一粗浅探讨,旨在抛砖引玉,敬请方家给予批评指正。
二、邢窑名称及产地
邢窑之名的含义,笔者认为有广义和狭义之别。顾名思义,邢窑之“邢”是邢州之简称,凡地处邢州范围之内的窑场,均应属于邢窑的范畴。受邢窑影响,其产品和邢瓷基本类似的制瓷业作坊,亦可称之为邢窑系或其分支,这是广义的解释。至于狭义的说法,是专指代表白瓷发展成就,烧制大量贡品而被载入文献的邢窑窑场。本文所论及的“邢窑”是就狭义而言。
邢瓷之研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邢窑在何处这一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研究邢瓷也就无从谈起了。
1980年在临城县治西北5公里的祁村一带发现唐代白瓷窑址后,曾在考古、古陶瓷界引起震动。诸多专家、学者对祁村窑址进行了考察,因为从地表存物的细瓷和粗瓷所具有的特征来看,它们和唐墓出土物以及存世的唐代白瓷比较对照,就其胎质、造型和釉色均极为相似[3]。部分学者认为祁村窑就是邢窑的一部分,至少也是邢窑的正统或亲支近派。并对窑址的地理位置也做了考证和推测,认为临城和内丘交界处的地理区划,时合时分,而窑址正处于这一地带。古时以州命名当是泛指,这样看来,邢窑窑址既不在邢台也不在内丘,而是在与内丘交界的临城县[4]。然而这一说法在当时并未被学术界所普遍接受。其主要争论焦点在于唐代李肇《国史补》中记载的邢窑在古称邢州的内丘县,而临城不属于邢州的范围之内,真正的邢窑应当到内丘去找[5]。但当时内丘境内的窑址尚未发现,坚信邢窑在内丘的说法因根据不足而缺乏说服力。
1984年,内丘邢窑遗址发现之后,证实了邢窑在内丘之说的正确性。但祁村窑是否邢窑,目前尚缺乏明确的结论。现在我们不妨把内丘窑和祁村窑所出器物做一对比分析,再将两县的地理沿革详加推敲,问题就会逐渐明朗了。
内丘唐代窑场集中在县城及其周围。从诸窑址出土白瓷标本来看,唐代细白瓷的产量约占白瓷产量的40%[6],并出土了典型的邢瓷贡品“盈”字款、“翰林”款标本。细白瓷作品其造型规整,制作精细,品种极为丰富。其胎质细腻,釉色洁白微闪蓝。扭曲变形的次品,上釉不匀和有积釉的作品极少见到。表明该窑在制坯、修坯工序上要求极为严格,已经能够适当地控制窑膛中温度,有较高的制瓷技术[7]。祁村窑址出土的瓷片标本中“类银”、“类雪”的细白瓷数量不及内丘,仅占白瓷产量的20%[8]。其他多为胎质粗糙,釉色发灰发黄的粗白瓷。造型也不及内丘的产品规整,修坯工序也略次。细白瓷如碗的底部有不少作品留有刀削痕迹,玉璧底足心往往留下乳突,不甚光滑。不同程度的施釉不匀和积釉现象也不少见,积釉处呈草绿色。釉色与内丘窑亦有不同,内丘窑产品多白中闪蓝,色调偏冷;祁村窑器物多为白色。积釉是由于施釉不均匀或烧成温度控制不佳所致,而釉色的差异说明两地的配釉方法有所不同,这尚需以后化验对比才能证实。但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从内丘窑址堆积中均有大量牛、马骨骼及牙齿推测,当时配制釉料时很可能掺入了动物骨灰。而祁村窑目前尚未发现有兽骨遗存的现象。总之,内丘、祁村窑场可能由于瓷土的来源与提纯,瓷釉的配制乃至烧成温度的高低以及其他诸多原因,形成了两窑产品之差异。
关于内丘和临城的地理沿革,内丘在隋以前称中丘县,因隋室讳“忠”,隋开皇初改称内丘县。县治所自北魏由现西丘村迁徙今治,至今未改。历史上除隋开皇三年至大业二年和唐武德四年曾隶属赵州外,一直归邢州管辖。临城自隋至唐初曾为房子县,其治所在今县治西南五公里的南台村南隅,唐玄宗天宝元年始改房子为临城并迁今治[9]。唐代临城属赵州,历史上从未属邢州。
由此可见,内丘和临城在同一大行政区内时合时分仅见于隋代和唐初。唐代两县的边界虽不能详细断定,但从唐前期临城县治在今县治西南五公里这一点来看,今临城之地似无属内丘的可能。而位于县治以北的祁村一带的窑址所在地则更非赵州莫属了。古代我国习惯以州命窑,正如磁州窑所在的磁县在磁州的辖区内,定窑所在的曲阳也在定州的范围之中,邢窑所在地当然要在邢州区域内,而决不会设置于赵州之域的临城县。显而易见,祁村窑恰恰缺乏当时被称为邢窑的最基本的条件了。《国史补》一书是庸人李肇做左司郎中时所著,成书于公元824年之后。书中所载是唐开元至长庆百余年间之事。李肇对于当时烧制贡品的邢窑地点应该说是清楚的,误记的可能性不大。况且内丘窑的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又十分吻合,说明邢窑产地在当时邢州的内丘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综上所述,邢窑的真正烧造地点在内丘。严格地说,将祁村窑称为邢窑的说法还有待做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从另一方面讲,由于祁村窑和邢窑相距甚近,制瓷生产必受邢窑影响,产品的造型和邢瓷也基本相似,属于邢窑系也是理所当然的。但这和称之为邢窑尚有所不同,正如安阳天禧镇窑、汤阴鹤壁窑属于磁州窑系而不能称之为磁州窑一样。
三、邢窑白瓷的产生与发展
“邢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过去,由于它的真正烧造窑址未被发现,其发生和发展过程一直没有能搞清楚。1984年内丘邢窑遗址被发现,并获得众多的实物标本,“邢窑之谜”才得以真正揭晓。
考古资料证明,青瓷的发展是在南方,北方青瓷的出现要比南方晚得多,但白瓷的发展却早于南方。邢窑是我国白瓷发展的代表窑,烧制白瓷的历史比其他白瓷窑要早。因此,究其邢窑白瓷的出现与发展,无疑对研究我国白瓷的起源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般来讲,每处窑场的兴衰都历经创始、发展、鼎盛、衰落四个阶段。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邢窑白瓷创始于北朝,历经隋代、唐初的发展,达到了唐代的鼎盛阶段,唐末五代走向衰败。
(一)创始时期
公元439年,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方,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社会状况由大动荡过渡到安定时期。之后,孝文帝实行了均田制,允许手工业者可以自己经营生产[10]。这一政策的实行,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制瓷业亦不例外,这点在北方同时期墓葬里瓷器出土量的迅速增多亦可得到证实。
白瓷是在烧制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种由青瓷到白瓷的转变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为什么我国白瓷首先出现于北方而不在南方这一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多有探讨。有人认为,白色表示悲哀,因此,形成了一种对纯素的白色的禁忌心理,这种心理不利于白瓷的早日出现[11]。也有人认为,一是青瓷在南方的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因而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传统风俗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是不易改变的。北方和南方不同,白瓷在北方出现以前,人们还没有形成使用青瓷的习惯,所以,白瓷易于使人接受。二是烧造技术与工艺上的原因[12]。笔者认为后一种说法比较可信。邢窑的早期青瓷产品,胎质虽不及南方青瓷致密,但就釉色而言却各有千秋。南方青瓷的釉色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有半木光。邢窑青瓷和南方不同,釉色分青绿和青黄两种,玻璃质较强。由于釉的玻璃质感强,一般器物的釉色随着胎色的变化而变化。胎质粗糙,胎色灰褐的器物呈青绿色。胎质较细,胎色黄白的作品则呈青黄色。这类釉色已基本接近早期白瓷的色调了。由于胎质及胎色的变化,白胎瓷既卫生,又给人以明快、舒服之感。邢窑窑工在青釉瓷的基础上,减少了铁的含量,创造了白瓷釉,白瓷也就应运而生了。早期白瓷的胎体多呈灰白色,为了改变胎体的颜色,增强瓷器的白度,邢瓷匠师在施釉的部位,增施化妆土工艺。这些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白瓷,很大程度上是利用釉的玻璃质感强这一特点用化妆土来衬白的。这些北朝的白瓷,在邢窑白瓷发展序列中,尚处于创始时期。虽然这些白瓷的白度还不够,与隋唐时期的白瓷相比有明显的原始性,但已是名副其实的白瓷了。自此,打破了商周以来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白瓷生产的先河,为唐代邢窑和北方白瓷的生产奠定了基础,对唐代白瓷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发展时期
如果说北朝白瓷尚处于早期的创始阶段,那么到隋代无论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较前有了长足的进展。内丘西关窑址调查表明,隋代已烧制出数量相当可观的白瓷了,与青瓷的产量相比可平分秋色。此时,白瓷中大部分器物还需施用化妆土进行护胎。胎质较北朝细腻坚实,釉色稳定,玻璃质感增强。釉色洁白的作品也成为此时的成功之作。更有甚者,在窑址采集到四件细白瓷杯残片,杯壁极薄,仅厚1~1.5毫米,胎釉浑然一体,洁白如雪,光润晶莹,瓷化程度极强,与现代白瓷相比亦毫无逊色之处。隋代能够烧制如此精美之器,如果不是在窑址上发现,又有粘连在窑具上的残片做证,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过去人们根据文献记载将邢瓷的进贡时间定为唐代,而今发现的隋代高档白瓷数量极少,可能是为皇室所做的特制器皿。如果这一推测成立的话,邢瓷进贡的时间就可能提早到隋代。
隋代高档细白瓷的发现,无疑是邢窑调查的重大收获。遗憾的是在具有北朝和初唐风格的瓷器标本中,尚没有发现具有此种特点的作品,也没有找到和它有渊源关系的同类。这类瓷器是否还有其他式样的产品,到唐代是否还有烧造,有待于以后经过对窑址的正式发掘,资料的不断完备来证实这些问题。总之,隋代细白瓷的出现标志着邢窑的制瓷技术日臻成熟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三)鼎盛时期
唐代结束了隋末以来的战乱局面,为唐王朝的经济繁荣创造了条件。邢窑经隋、唐初的发展,积多年烧造之经验,邢窑匠师已能很好的掌握制瓷原料的特性,进一步精选制瓷原料,成形、装饰、烧成工艺精益求精,创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产品——邢窑白瓷。窑址调查表明,唐代邢窑以烧制白瓷为主导。初唐之后白瓷使用化妆土的现象已基本消失了。细白瓷胎体致密洁白,釉色光润无瑕。从唐初之前的器外施半釉,底足露胎,改变为内外施满釉,底足心亦施釉。品种造型丰富多彩,趋于多样化,餐具、茶具、酒具、文具、盥洗具、储藏具、灯具、药用具、玩具、佛教用品及明器,无所不有。这直接反映了邢瓷已渗入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产品制作精工,一丝不苟,都当之无愧地为邢窑的代表作品。
中唐,正值邢窑的鼎盛期,这时期部分作品已出现了款识。就目前所见到的有“盈”字款20余件,“翰林”款1件。“盈”字款多见于碗、壶、盒等底足,“翰林”款仅见于罐类器的底部。字款均阴刻在器外底部的足心,分施釉前刻划与施釉后刻划两种。亦出现字口有釉、无釉两种现象。字体多为较胖的行楷字体。新发现的邢窑底款,以往不见于文献记载,为后人所不知。它的出土解决了西安、上海等地出土、馆藏“盈”字款,“翰林”款的窑口问题,并意味着邢瓷产品被宫廷和上层社会人物的使用和所受到的青睐。
(四)衰败时期
唐末,政治腐败,藩镇割据,战事频繁。据《新唐书》所载,在会昌三年至光化元年邢州发生较大的战争七次,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五代结束了唐王朝的统治,全国统一的局面遭到崩溃,战乱纷起使大批劳力被迫服役,手工业者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时期邢窑开始衰败,细白瓷少见,多烧制一些粗白瓷,且胎体粗松,胎色灰黄或灰青。有的器物亦出现釉下施化妆土的现象,制作工艺较前期粗糙,与邢窑细白瓷相比要逊色的多。从此,邢窑一蹶不振,无法与迅速崛起的定窑相竞争,而被其取代。
四、器形特点与装饰
邢窑始烧于北朝。这时期的制瓷技术尚未成熟,产品的种类较少,主要有碗、杯、盘、罐、瓶、钵等器皿。其造型特点是简朴、粗犷、古拙。一般器物的胎体厚重,如常见的深腹碗和杯,可分直口、敛口两式,腹较深,腹壁的外轮廓几乎由直线向下接近底部时内收,口沿处胎薄,下部厚实,平足较小。这样做的优点是增大容量,烧制时不易损坏。此种器形和南方同时期碗的造型基本相同,可能是受其影响所致。内丘西关窑址曾出土一件青瓷罐,盘口、肩部饰双泥条四系,上腹圆鼓,下腹稍瘦,器身高达50厘米,显得粗犷而有气魄,体现出邢窑早期器物的独特风格。
隋代邢瓷造型的显著变化,是器形的增多,由北朝的单一化趋于多样化了。隋邢瓷的造型特点总的来说是立式器皿增多,作品具有秀气、挺拔、豪放之感,多数器底足较高并微向外撇。碗、杯由直口或敛口演变为直口微侈,腹壁斜而直呈喇叭状,平足微凹,也有的做浅圈足。胎体的厚薄比例安排的比较协调,趋向于轻快,摆脱了厚重古朴的形式。罐一般无颈或短颈,系略高于口或与口平齐。瓶则多做盘口、流肩。瓶、罐的腹部由最大腹径在上部渐渐阔大呈近椭圆形,显得修长而不失稳重。高足盘是隋瓷中最为典型的一种器物,南北各地的窑场都大量烧造,它的基本特征是浅盘式,下面以空心的喇叭状高足来支承。邢瓷高足盘,最常见的有平底、侈口,或口沿外翻、圜底、弧腹、尖唇沿等式样。
可能是由于隋末唐初的战乱,使社会经济受到破坏的原因,初唐时期白瓷的产量和质量虽都优于隋代,精美的细白瓷作品却不多见,在造型上也无所建树。一般器物的形体较大,由隋代的秀长、挺拔向浑圆饱满过渡。
初唐之后,唐王朝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受其他工艺品的影响和人们审美观的提高,形制新颖,造形优美的邢瓷制品也就应运而生了。碗类器物由深腹演变为浅腹式,直腹变为曲腹或弧腹。口与底径的比例多为1:2。器形在统一中又有变化,如碗有多种形制,主要为敞口、敛口、折腰、花口四种。口沿可分圆唇、尖唇、圆唇外翻三种。足又分平足、圈足、玉璧足、玉环足四种。杯的形制也别具一格,有的做浅腹式,下饰鸟头型三足,增加了器物的神韵。另有仿银器的深腹圈足杯、高足杯,其造型灵巧而雅致,为邢窑工匠将金银器造型艺术用于陶瓷上的卓越创造。罐、鍑、钵腹部鼓圆,罐多饰双系,鍑均有三兽蹄足,其作品具有体态丰盈、浑厚、庄重、大方之感。
中唐的邢瓷在造型方面主要表现在器壁薄而均匀,器物的外轮廓多采用弧度较大、线条注意曲直变化的手法,使其具有很高的艺术魅力,达到了美观与实用相结合的效果,这是唐代邢瓷最典型的造型风格。
在装饰方面,北朝时期不论是青瓷还是白瓷,都注重于实用为主,多为素面,纹饰很少。仅见凸凹弦纹和莲花纹。弦纹一般用以装饰器物的口沿或腹部。莲花纹则是在碗或杯的腹部刻划上较为简单的几朵莲花相向排列一周,这些莲花纹饰的线条看起来还不够流畅,表现出北朝邢窑在瓷器装饰艺术上的原始性,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但表明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艺术题材的莲花图案已装饰到瓷器上来。
目前,由于窑址还未进行正式发掘,没有充分的考古资料来揭示它的真面目。但就所采集的标本来看,邢窑在隋代已掌握并使用了刻花、印花、贴花等装饰技法,还出现了艺术性较高的雕塑品。
刻花使用尖状或扁状工具,刻划出各种柔细的线纹图案。
印花使用模具压印图案。可分为两种,一是用模具在未干的胎体上压印。二是把胎泥塞进带有图案的两片模具中挤压成形后,再沾上配好的泥浆扣在一起粘接成器。
贴花将手制或模制的饰件用泥浆粘贴在器物的外壁上,以达到装饰的效果。
雕塑先用练制好的胎泥堆塑成形,然后用刀雕琢。此种技法仅用于人物或动物俑上。
刻花一般为弦纹、莲花或六至八瓣的花瓣组成的花朵,用以装饰瓷器的内外腹部和盘的内底。
印花和贴花均用来装饰器物的外部。如在隋代的黄釉扁壶上,肩部饰有对称的鸳鸯二系,工匠们巧妙地将眼睛做成圆孔用以作为绳穿。腹周围饰联珠纹,中间花叶丛中二人相对脚踏莲瓣之上,一人作吹乐状,一人作乐舞状。隋代扁壶无论在造型上还是在装饰图案上,都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体现了隋代邢窑匠师的工艺及艺术水平,为隋代陶瓷造型中的上乘之作。在一件白瓷标本上,采用了印花和贴花并用的手法。因标本残缺不知为何种器形,据观察似为六棱或八棱器。器外和每个侧面相应用联珠纹组成一长方形,长方形内印有花卉,在侧面的结合处采用了贴花装饰技法,因瓷片太残,贴花的图案内容不得而知,仅可看到附件为先粘贴在器面上,然后才入窑烧造。
雕塑制品人形灯和子母猴形象逼真,肌肉发达隆起,显示出雕琢技法娴熟,亦可称为上乘佳品。除此之外,尚发现飞禽类作品,饰孔雀羽毛纹饰,断头缺尾。此件作品不是实用器皿,当为装饰品。隋代设计新颖、造型优美的艺术瓷的出现,标志着邢瓷装饰艺术的进步和发展。
唐代邢窑仍沿用刻花、印花、贴花、雕塑等技法来装饰瓷器。和前所不同的是纹饰的线条比较流畅,图案的结构比较严谨,艺术手法更臻成熟,时代特点也较为明显。海棠形银盘是晚唐出现的新器形,主要形式之一由单线的花叶组成[13]。邢瓷中仿银制品海棠形白瓷印花盘残片同丹德丁卯桥出土的银盘形制基本相同[14],盘缘上的缠枝花纹,纤细规整,其纹饰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海棠型银盘边缘纹饰亦相似[15]。说明邢窑的仿银器制品,不但在造型上惟妙惟肖,而且在装饰方面的纹饰特点上也具相同的时代特征。莲花纹是邢瓷自北朝至唐所一直沿用的纹饰,从早期刻划简单的小朵莲花,到唐代制作精致的仰莲、覆莲纹佛像座的出现,一则表明了邢瓷装饰从简到繁的演变规律,二和这一时期大兴佛教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采集的众多瓷片标本中,发现有几片带有点彩的瓷片,点彩处釉层很厚,与无彩处相比明显突出。彩斑下出现了细碎的冰裂纹。观其瓷片,赭色的彩斑在洁白的器皿上显得清晰,悦目,给人以美的享受。目前,已知我国最早的使用釉下彩绘技法的是唐代长沙窑[16]。如果说釉下彩绘是长沙窑有历史意义的首创,则邢窑这种釉中点彩的技法也是一种创举。这种产品虽然现在发现的还太少,不能窥其全貌,相信随着邢窑的正式发掘和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对揭示釉中点彩这一技法的真面目将会有莫大的帮助。
唐代邢瓷的装饰成就,最突出的是烧制绚丽的三彩器。这是继河南巩县和陕西黄堡唐三彩窑址之后,我国发现的第三处烧制三彩的窑口。诚然,邢窑是以精湛的白瓷闻名于世,但三彩器的发现无疑为邢窑家族又添了新的品种。邢窑的三彩器,是在胎体上施加白色化妆土先行素烧,然后再施釉进行二次烧成。釉色可分为三种,前两种都是单色釉,呈黄和浅棕色。第三种是黄、绿、红、白、蓝等多种色素交错并用,色调从淡到浓,融合绚丽,工匠们以巧妙的施釉方法,加之烧制时釉的流淌,更显得活泼富丽,斑斑多彩。邢窑三彩同河南巩县三彩相比,其特点不同。主要表现在巩县三彩釉质具有乳浊感,而邢窑三彩不及巩县三彩华丽,但釉的质感很强。
邢窑发现之前,人们往往认为邢窑光素无饰,这种偏见是因考古资料缺少所致。从现已掌握资料来看,邢窑产品不但有装饰,而且手法众多。邢瓷尚素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它精湛的装饰技艺不能因此而被埋没。邢瓷的装饰艺术,同邢窑白瓷一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也应占有重要的地位。定窑是继邢窑之后兴起的宋代名窑。定窑的早期产品受邢窑之影响,造型风格和邢窑相似,装饰技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仿效邢窑。
五、窑具及装烧技法
邢窑的窑具有窑柱、垫圈、支珠、支钉,匣钵等。窑具的尺寸大小不同,均为瓷土制成,其中以三角支钉最多。
窑柱可分为两种。一种呈倒置蘑菇状,空心柄。另一种为圆柱束腰状,上下均为平面。
支钉分三角支钉和四齿支钉两种。三角支钉一面为平底,一面为尖状三乳突,乳突为手捏制,有的留下手指纹。四齿支钉,为空心柄状,柄呈圆形,一面有锯齿形四齿,一面有掏孔或做成平面。支珠和支钉同属支具,呈三棱锥形。
匣钵有直壁平底的筒状匣钵,直壁底斜收的漏斗状匣钵,敞口圜底的盘状匣钵和敛口平底的钵(盆)状匣钵四种。
窑具是研究装烧方法的重要依据。从采集的窑具可知,邢窑各时期及不同的瓷类,烧造工艺也不尽相同。
根据窑具与产品的粘连情况来看,邢窑早期白瓷还不见匣钵的使用,器底部留下的支钉痕迹说明是采用叠烧法烧成。装烧时,先将窑柱排放在窑台上,以淘洗后的瓷土废料(呈砂状)垫其下部使之固定。束腰圆柱式窑柱用以支承腹径较大的器物。蘑菇状窑柱用以支承碗、杯等腹径较小的器物。窑柱的平台上放上随手用胎泥捏制的圆形垫圈,其上放置产品,以起稳定作用。产品之内放置支钉,使器与器之间留有间隔,依次摞放。由于坯胎摞放承受压力较大,容易变形,故这一时期烧制的器物底部都较厚重。窑柱的高度,一般仅可摞放5~7件产品。观其窑柱的粘连物可知,第一个窑柱上产品摞满后,在柄之上放置泥条圈,再摞放另一个窑柱,以增加高度,直至适可而止。这种装烧方法的优点是,窑柱可使产品升高,便于充分利用窑膛内的空间和温度,能够使产品最大限度的受热。其缺点是除最上面的一件产品外,器内均留下支钉痕迹,显得美中不足。
隋代,邢窑开始使用保护坯胎不受火刺的匣钵。其匣钵多为筒式,质地粗糙较厚。一般白瓷碗、杯类产品仍用叠烧法烧造,单件烧的很少。以往,对于隋代是否使用匣体尚有争议。就目前资料所知,湖南湘阴窑为我国隋代使用匣钵的唯一窑场[17]。对此,曾有人提出异议[18]。邢窑匣钵的发现,得到证实。
唐代的匣钵除继续使用筒状匣钵外,又增添了新品种。匣钵均系拉坯成形,尺寸大小视所装器物的大小而定。筒状匣钵多装立式器皿,也有极少数的摞放坯胎。装烧时先将坯胎放入钵内,钵口置泥条圈后,再放相同规格的匣钵,摆放到适宜的高度而止。为防止火刺的侵入,最上件匣钵用盘式钵盖封口。漏斗状匣钵为一件一器单烧,装烧时将碗放入钵内,上面再置匣钵,依次摞放,码到一定的高度为止。这类匣钵一般均施黑釉或酱色釉,口沿和器外底部无釉,可能是为避免摞放时粘连的缘故。壁较其他形式的匣钵厚,内底放置支钉后装入产品。此种匣钵是否既作为匣钵烧制细白瓷,又可作为一种器皿使用,达到一举两得之目的。总之,匣钵的使用,是烧造工艺上的一大进步。特别是单件装烧的技法,使邢窑白瓷彻底消除了火刺和支钉痕。邢窑匣钵的出现与邢窑白瓷一样,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调查发现多处残窑炉底部,仅见到大量的柴灰,并无发现烧煤的迹象。说明邢窑烧瓷的燃料是柴而不是煤。邢瓷是在还原气氛中烧成,釉色白中泛青,具有冷色之美感,这也是烧柴一个佐证。我国用煤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汉代,邢窑所处的北朝至晚唐五代时期,煤的使用更是不断扩大。地质矿产资料表明,邢窑区域内的地表和沟谷中,有下二叠系山西组煤系地层的普遍出露,易于开采。邢窑舍煤而取柴的原因可能是太行山区古时柴草丰富,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另一方面,邢窑在用柴烧瓷的基础上,烧窑技术有了一个传统的模式,窑工熟练地掌握了还原烧成技术,对窑膛的温度已能严格地进行控制。煤的火焰较柴要短,温度难以掌握,从柴烧窑到用煤烧窑在窑炉的结构上和烧成阶段的技术上均要有一系列的变化,这需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来完成。邢窑的窑工在没有掌握烧煤技术时,可能就避长而扬短了。
六、邢窑之归属
在邢窑调查时,不断发现带有款识的器物标本,其中多见的是“盈”字款,其次为“翰林”款。目前,“盈”字和“翰林”款瓷器尚不多见。陕西曾出土三件“翰林”款白瓷罐,这种作品根据底部刻款的内容,基本上可推知是翰林院的定烧之物。“盈”字款瓷器除陕西大明宫遗址出土玉璧底中心刻“盈”字的白瓷碗外,上海博物馆亦收藏有一件传世品“盈”字款粉盒[19]。1975年河北省易县北韩村唐墓中出土一件“盈”字款执壶[20]。其他的尚未见报道。近年来,围绕“盈”字款瓷器问题。有人进行了多方探讨。由于大明宫遗址曾出土过“盈”字碗,为研究“盈”字款瓷器提供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大明宫是唐高宗李治以后诸皇帝料理政事之所,在这里出现“盈”字款瓷器可资说明此类作品应是宫廷用器。关于“盈”字的含义,最近据陆明华先生考证“盈”字款作品取唐代内府库“百宝大盈库”之“盈”字来作为标记,为供天子享用的定烧器[21]。这种判断基本上令人信服。如果这种推论是正确的,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问题:就是唐代烧制供品的窑口不只限于邢窑,其他如越窑、巩县等窑的贡品瓷器却怎么不以“盈”为标记?这种现象是否与窑场所属有关联?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充实,对于“官”、“新官”字款瓷器和官窑问题的研究也相继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将我国官窑的出现时间从宋代提早到了五代时期。冯永谦先生就曾明确地指出“唐代瓷器有了长足进展,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使用普遍,形成官私通用局面。我认为到了晚唐官窑就应兴起”[22]。现在我们根据邢窑产品和与之相似的祁村窑出土物以及内丘、临城两地的唐墓中瓷器出土情况试做分析,或对于认识上述问题会略有益处。
位于内丘的各处窑址中,曾发现过“盈”字款瓷器标本。临城境内的窑址也有带款识的瓷器出土,诸如“王”、“楚”、“弘”、“张”等这些多为姓氏刻铭。如果说“翰林”、“盈”字款瓷器是皇室的定烧器,那么这众多的姓氏刻铭,绝不会也是贡品。它的含义,或为单做共烧,以避免产品混杂,或为产品竞争而刻划窑主的姓氏,带有商标的性质。邢窑则没有发现姓氏刻铭。古时“盈”与“瀛”通用,虽然亦有“盈”姓,但内丘城众多的窑场为一家所有,或均出自“盈”姓工匠之手,似乎都不大可能。唯有“盈”字款瓷器是为宫廷烧造的贡品这种说法令人信服。从这一点上看,邢窑和祁村窑产品销路的来龙去脉就有点眉目了。
临城目前发现8座唐墓,除1座初唐墓葬中无细白瓷外,其余7座平民或低级官吏的小墓中出土文物62件,其中30件瓷器均为祁村窑的细白瓷[23]。比内丘唐墓出土的细白瓷数量要大得多。可以说,但凡临城发现唐墓就有细白瓷。而内丘这一现象实不多见,在发现众多的唐墓中,随葬细白瓷的仅有两座墓。如新城大和九年间的墓葬,出土陶俑、瓷器达70余件。按《大唐六典》所载的墓葬等级制度,应为五品官职之葬式,仅葬2件细白瓷高足杯和10余件黄釉及黑釉瓷。唐代,内丘、临城均生产细白瓷,相比之下,内丘的窑址数量及产量要比临城大得多,为什么墓葬出土情况却异乎寻常?是否可作如下推测,临城祁村窑系民窑,又处偏僻之地,烧瓷不受官府控制,产品销售自由,上层社会人物及当地人极容易得到它。而邢窑的细白瓷销售由官府控制,或专为宫廷而做,或远销海外和供上层社会使用,当地人难以得到,只能使用质量较次的粗白瓷和其他类瓷器。
至今内丘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很早以前,内丘烧造的瓷器很有名声,当时的皇帝传下了旨意,让为他烧造一个白瓷龙床,因为龙床的尺寸太大不好烧造,窑工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烧成,只好如实上奏,皇帝一怒之下就随口说出:“烧不成就散伙”。皇帝的话就是金口玉言,不能更改,所以窑场也就散伙了[24]。虽然民间传说不足以证明邢窑就是“官窑”,但是既有流传,也就有一定的来历。根据这一传说来看,邢窑与当时官府是有一定关系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邢窑在中唐以后已是一处官私通用的窑场,也就是说很可能就是早期所谓的“官窑”了。
七、余论
以往,瓷史研究者认为,北方白瓷出现于隋代。1971年在河南安阳洪河屯的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中首次发现了北朝的白瓷[25]。这批白瓷,无论胎釉的白度,烧成的硬度和吸水率,都无法和隋代的白瓷相比,显然尚处于创始阶段。尽管如此,它已是名副其实的白瓷了。这一发现,将我国白瓷的生产年代又上推了一个历史时期。于是有人提出北方早期白瓷的生产应在北齐。邢窑北朝烧造白瓷窑址的发现,证实了这种看法。
窑址调查表明,邢窑早期白瓷的生产比青瓷稍晚,它是在青瓷烧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青瓷到白瓷,是邢窑窑工经过长期实践的新成果,无疑是一种伟大的创举。它的发明是后来各种彩绘瓷器的基础,没有白瓷就不会有青花、釉里红、五彩、斗彩、粉彩等各种美丽的彩瓷[26]。它的出现,为我国陶瓷史开创了新的篇章,促进了陶瓷的繁荣和发展。在世界科技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
邢窑白瓷自北朝的创始,历隋代唐初的发展,到李唐一代已成为北方烧造白瓷的著名窑场,制作工艺精益求精,胎釉原料精心选制,装烧方法上日趋合理,采用单件正烧,制作了大量无与伦比的精美细白瓷。若以邢、越两窑相比,邢窑白瓷代表了当时白瓷的最高水平,越窑青瓷代表了当时青瓷的最高水平,这点就连抑白尚青的陆羽在道出“邢不如越”的同时,也道出“或邢州处越州上”的社会评价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总之,邢窑的鼎盛,改变了青瓷主导方向,使北方的白瓷生产获得了迅速发展,为后期定窑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1989年9月
附注
[1]河北临城邢瓷研制小组:《唐代邢窑遗址调查报告》,《文物》1981年第9期。
[2][6][7]内丘县文物保管所: 《河北内丘邢窑遗址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第9期。
[3]王舒冰:《大家都来关心邢窑》,《河北陶瓷》1984年第3 期。
[4]李辉柄:《唐代邢窑遗址考察与初步探讨》,《文物》1981年第9期。
[5]程再廉:《何处是邢窑》,《河北陶 瓷》1984年第1期。
[8]李知宴:《内丘邢窑的重大发现》,《河北陶瓷》1987,第4期。
[9]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
[10]《魏书》卷七上《高祖记》。
[11][12]李辉柄:《略谈早期白瓷》,《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
[13][14] [15]卢兆荫:《试论唐代的金花银盘》,《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
[16][26]中国硅酸盐学会:《中 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
[17]周世荣:《从湘阴古窑址的发掘看岳州窑的发展变化》,《文物》1978年第1期 。
[18]河北省邢窑研究组:《邢窑工艺技术研究》,《河北陶瓷》1987年第2期。
[19][21]陆明华:《邢窑“盈”字及 定窑“易定”考》,《上海博物馆集刊》第4期。
[20]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易县北韩村唐墓》,《文物》1987年第4 期。
[22]冯永谦:《“官”和“新官”字款瓷器矿研究》,《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23]李振奇:《河北临城七座唐墓》,《文物》1990年第5期。
[24]内丘县文化馆:《内丘民间故事选》 ,1984年内部资料。[25]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