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作者简介
董如昆,男,1944年出生,天津市宁河区东棘坨镇躲军淀村人。1958年考入天津市机电工业局技校,1960年分配到天津市起重运输设备厂工作,1962年响应国家号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1970年在公社修配厂工作,1980年受聘于芦台新生锅炉附件厂工作,1983年在潘庄镇锻压厂任副厂长,1985年在东棘坨乡丰源服装厂、津汉食品厂任厂长,1987年受聘于赵庄乡大赵村汽车水泵配件厂任厂长,1994年任泛马机械有限公司机加工主管、技术顾问,1996年任陈荷机械有限公司机加工主管、工程师,2005年任昌昊实业有限公司工程师,2014年退休至今。
乡村生活散记
董如昆(75岁)
读《百老话沧桑》丛书时,忽然想起在生产队时的几件往事,虽然都不是什么大事,但自忖毕竟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留有那个时代生活和发展的印痕,所以还是决定记述下来,与上岁数的人一起忆旧,与年轻人一起分享。
榨油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农村老百姓根本无油可供,只能是房前屋后收些大麻籽,自己榨点油,一家几口人一年也只有三五斤油罢了。用肉皮擦锅,熬一大锅白菜只滴几滴油的事都不是说笑话。那时生产队为解决社员的吃油困难,每年秋后,就会派人赶着马车或牛车,拉着自产的黄豆去唐山的胥各庄榨油,回来按工分多少分给社员食用。
一年旧历九月底,队长叫我和董书玉老叔去榨油。吃完中午饭,我俩就到了马号,因为我俩都不是车把式,为了安全,就选了头老实且腿脚快的牛。套了车到生产队库房,装了十几麻袋黄豆,早早吃了晚饭,带上干粮就出发了。为啥要晚上出发呢,因为从我们村到唐山附近的胥各庄,要途径小海北、马丛庄、大王御史、芦台、皂店、董代庄、新河庄,大约150里路,晚上出发为了争取在第二天天黑前到达,这样就免去了路上住店,再加上人吃马喂的,能给队里省下好几块钱呢。
从韩太庄村南上了205国道,奔了唐山方向的胥各庄出发。都说秋寒如虎,一点不假。一开始,我们还美哉悠哉地趴在牛车上兴奋地聊天,到了后半夜,就不说话了,冻的光打哆嗦了。董书玉老叔说,三九冻不死出力的人哪,咱跟车跑吧。为了抵御寒冷,我们爷俩就跟着牛车像原地踏步那样小跑。到芦台时太阳出来了,浑身觉得那个暖啊。路边讨了点热水吃了点干粮,傍晚时到了胥各庄,现在汽车一小时多一点的路程,牛车走了差点24小时啊。
卸了黄豆,榨油的人先将黄豆预热。大大的火炕,锅底架着树枝干柴,把黄豆散铺在炕上爆一宿,以提高出油率。第二天开榨时,将炕上爆热的黄豆装入一个直径一尺半左右,厚度二寸多,圆铁环内圆环、中间略微铺点稻草,五六个摞在一起为一榨。四五个青年小伙子赤身裸体,用力搬动螺旋榨机的大圆盘,借着多头丝杠和圆盘的冲击力将油挤出。
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就住在油坊的库房内,库房门口很大,挂着稻草帘子挡风。我们没有带被褥,夜里就盖麻袋,尽管麻袋不搪风,好在卸了黄豆麻袋多,多盖几层呗,这样住了两宿。
榨完油的豆饼像小磨盘子似的,一块有20多斤。油房有专门收购豆饼的,因为队长有话,价格合适可以卖掉。我们以黄豆质量好为由,据理力争,人家也不肯给涨一分钱,为了给生产队多卖点钱,我们就决定自己串村去卖。最后到了边各寨村,有个生产队要买,算账时对方少算了三块多钱,我说不对,那个会计好像瞧不起我们似的,把算盘扔给了我们,其实我们真不怕,因为董玉书老叔就是会计,不过他没有接算子,只是用眼神示意了一下我。我上学时珠算最好,父亲又是区里的老财粮委员,我就用倒扒皮的方式证明了他们少给了钱,结果他们都不好意思了。
回家是凌晨,卖了豆饼卸了载,车一下子轻了许多,牛也奔家心胜,不待扬鞭自奋蹄,前半夜时就到了家。早晨大喇叭就喊分油,分油是件欢天喜地的大事,家家有人来排队,人人都喜笑颜开。有的人家把油分回家,会熬上锅香喷喷的大白菜,焖一锅高粱米饭饱餐一顿;有的大方人家,会炸点油饼之类给孩子们解馋;但更多人家是节俭食用,以维持一年的用油。
卖瓜
公社化时,队里每年都要种上七八亩甜瓜,三五亩西红柿,除给社员分以外,要卖掉部分以维持生产队的正常开支,我每年这个季节都要当一把小商贩。队长每次找我时总是说,你会算账,大伙儿放心呢。早晨,队长会安排人摘好瓜和西红柿,早饭后就带上干粮,赶着装满西红柿、甜瓜的毛驴车出发了。一般是往俵口、东西塘坨等较大村队走街串巷去卖。一个车两个人,一个人负责约秤,一个人负责吆喝并算账收钱。有时忙得顾不上吃干粮,但只要有人买瓜就高兴。卖瓜的时节大都是七八月份,中午的太阳特毒,把人晒得满头大汗,有时卖的不顺利,没带干粮,又渴又饿,但满车的瓜果也不轻易吃,很有自觉性。
除了下村串街卖外,每年都要在立秋前的一个集日去芦台卖瓜,因为芦台人有咬秋的习惯,立秋节前的芦台集也是销售瓜果的旺季,特别是甜瓜和面瓜(俗称老太太乐),很受芦台人欢迎,只要喊出我们的瓜是躲军淀或韩太村的,人们就蜂拥而上。现在由于外地的哈密瓜、芒果、火龙果等充满市场,本地种甜瓜的也少了,所以很多人淡忘了咬秋的习俗,也有的以买西瓜为咬秋瓜了。
那时赶大车去60里外的芦台赶集卖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头天就要做好准备,晚饭后赶着牛车上路,要赶在天亮之前到达集市。现在60里路开汽车只用半小时,也就是踩一脚油门的事。那时就得折腾一宿,弄得是人困马乏。秋夜露水打湿了全身,满车的甜瓜面瓜,都怕压,车上没处躺,车辕子也没处坐,因为赶车的人都知道“压马、吊牛、逛荡驴”的俗语,意思就是马车可以坐辕子,重点儿没事;牛身子重,车辕子轻一些才好;毛驴是车辕子重了不行,轻了也不行,最好是不轻不重,我们只好跟着牛车缓步前行。
在集市上卖瓜,可不像在乡下串村卖瓜那么轻松,很累人。那时集市在芦台街里,买瓜的人忒多,脑瓜挨脑瓜的,有性急的还大呼小叫的,忙活得我俩汗顺脸流都顾不得擦,但卖得快心里高兴啊!我们那时卖瓜,从不看着人头多就乱涨价。卖完瓜,我和董学志也已是精疲力尽,董学志由于瘦小体质差,看上去更是疲惫不堪。傍晚,我们就住进张家马车店(现在区医院西侧靠南边),一切安置停当后,店主说电影院正放映南征北战电影,卖瓜的钱又没有数,你们不看看去呀!说实话,真想看,可舍不得自己的钱,又不能花卖瓜的钱,就没去。那时一盒“大婴孩”香烟才一毛多钱,也是掏自己的钱买的,集体的便宜不能占啊。睡觉时,因为随身带着卖瓜款,不敢两个人同时入睡,包不离手,手不离包,生怕有什么意外,其实那个年代很安全,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回家了,这回我们可以在车上放心大胆的睡觉啦,任其老牛在205国道上前行。人都说“老马识途”,老牛也识途,早起饮点水,喂点料,上路后不用人管,它会按照来时走过的路,一点不差的走回家。
买猪秧
七十年代初,上级号召大造农家肥,公社出台政策,提倡社员养猪,猪粪沤肥交生产队,以肥换工分,社员们纷纷报名养猪,因为积肥挣工分,一头猪抵得上半个劳力呢。
让社员养猪,就得买猪秧。为了方便群众,生产队采取了猪秧款队里垫付,秋后结算还款和队里派人统一买猪秧的办法,很受社员欢迎,因为买猪秧个人去要误工,有的人还犯怵出门。我是经常被派去买猪秧,一是我在城里当过工人,所谓的见过世面;二是队长信任,说我规矩,不耍滑占便宜。其实,最重要的是我家里有一辆大水管加重自行车,因为买猪秧队里不给派车,谁去谁自备交通工具和盛猪秧的家把式。
记得是1963年春,队长派董学志(已故)、董如善和我去赶玉田县鸦鸿桥集买猪秧。我们每人骑一辆加重自行车,后架上绑着两个用来盛猪秧的大筐,一百五六十里,坑坑洼洼的沙泡路,很是费劲。提前一天赶到鸦鸿桥住店,第二天大早赶集。那时候去外地赶集也不容易,要提前到本地粮站换好粮票,跨省市要用全国粮票,因为那时卖馒头大饼的都要粮票。集市那天一早,我们就直奔集市,把卖猪市场遛了几遍,基本物色好了卖主。买猪秧不但要看猪秧好不好,还要看猪拉稀不拉稀,可不能买了病猪啊。我们买猪不是单个挑,一买就是一窝,这样连窝端买好砍价,我们也省时间。一共选了4窝30多只猪崽,就开始谈价,几经周折谈妥了价格,却不着急抓猪过秤付款。这里有说道啊,因为卖猪的在卖前把猪喂得滚瓜溜圆,那都是钱呀!我们就故意磨磨蹭蹭,等看到猪尿也尿了,屎也拉了,好,过秤算账。装筐封好盖,骑车往家返,当天晚上住进了丰台东村供销社马车店。住店后,把猪崽放入猪圈内,喂食喂水后休息。
第二天继续往家赶,上午9点钟左右,江洼口过了摆渡后就开始刮风,有五六级,步步顶风啊,每个人还驮着100多斤的小猪崽,那个汗出的,袄都湿透了,风一吹,冰凉呱唧的。特别是江洼口至大月河的路,是一条高出地面两米的大道,别说骑车,就是推车也要使出全身的力气,否则自行车会被风吹倒。折腾的人气喘吁吁,小猪崽也吱哇乱叫。我们3人轮换着打头,后面俩个人会稍微省些力气。就是这样,还是遇上事了。董学志摔跤把小猪摔出筐外,跑出去两头,这可坏事了!我们留一个人看猪,另俩人漫野地和小猪展开了一场追逐的拼搏。沟沟坎坎,上上下下,连滚带爬,帽子丢了,鞋跑没了,连裤腰带都跑断了,狼狈不堪呀!多亏了大月河村耪地的社员们帮忙,才将两只猪崽逮着。
分猪秧用的是最传统最省事的法,那就是抓阄。农村历来有“万贯家财勾上死”之说,把30多头猪排成号做成阄,对号领猪,满意的欢欢喜喜,不满意的也只埋怨自己手臭罢了。
书法课
书法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有书法课,每周一节课专门学习书法,我们也叫做大仿课。每到上书法课时,我们就手托着五花八门的砚台,有方的,有圆的,也有用个小碗的。那时没有墨汁,用的基本上都是一种叫“金不换”的墨块,在砚台里放上适量的水研磨。碗不行,太光滑,研不了墨汁,那时同学们极友好,会给带碗的同学倒些墨汁用。有的人家没有墨了,就用锅底灰,遇上家长有耐心的,还会细心地把火灶头那块砖上的黑烟子刮下来,比锅底灰写字黑一些,只是锅底灰和灶门的烟灰不爱溶于水,要反复搅拌才行,而且用烟灰写的字不能摸,弄不好会抹得黑乎乎的一片,老师判作业也是小心翼翼的。常常是一节大仿课下来,学生们嘴上、手上、桌子上,甚至衣服上都是黑乎乎的。那时教书法的是吴玉鼎老师,大海北村人,右眼有点残疾(“玻璃花”),字写得好,脾气也好,说话慢条斯理、细声细气的,他看我们黑乎乎的模样,说过一句幽默的话:“喝墨水灵啊!”
那时,一支毛笔要用一两年。记得有一次笔头掉了,我用松香点燃后把笔头又安上了,继续用了很久。还记得,写字认真不认真老师很重视,但更重视的是坐姿和握笔的方法,老师每节课都对这方面给予强调和纠正。开始写大仿就是描红,那时没有田字格纸,只有从串学馆的小贩手里买大仿纸,回家后让大人给裁好订个本。大仿纸底下有正楷字的仿影,按照透过来的字体认真去描就行了,到五六年级就不让描了,但可以照着临摹。每节课都有课堂作业,下课就得交作业,由老师给判,较好的字,老师会给画个红圈。因为父亲是区政府的财粮委员,毛笔字写的很好,受父亲熏陶,我的毛笔字写的不错,老师总夸奖,就爱上书法课,我又是班长,每次发书法作业本,我的红圈得的特别多,心里就特别美。
后来我考上了市里中专技校,由于字写得好,就被推选为班干部,负责布置板报,偶尔有用毛笔抄写什么的,都是我的活,连老师都肯定我的毛笔字写得不错。回乡务农后,每年春节都给乡亲们写春联,从腊月十几开始,要写到大年二十九贴春联那天,都是尽义务,但很高兴。1995年我还加入了天津市书法协会,经常参加各种书法展出活动并获奖。
董如昆,男,1944年出生,天津市宁河区东棘坨镇躲军淀村人。1958年考入天津市机电工业局技校,1960年分配到天津市起重运输设备厂工作,1962年响应国家号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1970年在公社修配厂工作,1980年受聘于芦台新生锅炉附件厂工作,1983年在潘庄镇锻压厂任副厂长,1985年在东棘坨乡丰源服装厂、津汉食品厂任厂长,1987年受聘于赵庄乡大赵村汽车水泵配件厂任厂长,1994年任泛马机械有限公司机加工主管、技术顾问,1996年任陈荷机械有限公司机加工主管、工程师,2005年任昌昊实业有限公司工程师,2014年退休至今。
乡村生活散记
董如昆(75岁)
读《百老话沧桑》丛书时,忽然想起在生产队时的几件往事,虽然都不是什么大事,但自忖毕竟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留有那个时代生活和发展的印痕,所以还是决定记述下来,与上岁数的人一起忆旧,与年轻人一起分享。
榨油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农村老百姓根本无油可供,只能是房前屋后收些大麻籽,自己榨点油,一家几口人一年也只有三五斤油罢了。用肉皮擦锅,熬一大锅白菜只滴几滴油的事都不是说笑话。那时生产队为解决社员的吃油困难,每年秋后,就会派人赶着马车或牛车,拉着自产的黄豆去唐山的胥各庄榨油,回来按工分多少分给社员食用。
一年旧历九月底,队长叫我和董书玉老叔去榨油。吃完中午饭,我俩就到了马号,因为我俩都不是车把式,为了安全,就选了头老实且腿脚快的牛。套了车到生产队库房,装了十几麻袋黄豆,早早吃了晚饭,带上干粮就出发了。为啥要晚上出发呢,因为从我们村到唐山附近的胥各庄,要途径小海北、马丛庄、大王御史、芦台、皂店、董代庄、新河庄,大约150里路,晚上出发为了争取在第二天天黑前到达,这样就免去了路上住店,再加上人吃马喂的,能给队里省下好几块钱呢。
从韩太庄村南上了205国道,奔了唐山方向的胥各庄出发。都说秋寒如虎,一点不假。一开始,我们还美哉悠哉地趴在牛车上兴奋地聊天,到了后半夜,就不说话了,冻的光打哆嗦了。董书玉老叔说,三九冻不死出力的人哪,咱跟车跑吧。为了抵御寒冷,我们爷俩就跟着牛车像原地踏步那样小跑。到芦台时太阳出来了,浑身觉得那个暖啊。路边讨了点热水吃了点干粮,傍晚时到了胥各庄,现在汽车一小时多一点的路程,牛车走了差点24小时啊。
卸了黄豆,榨油的人先将黄豆预热。大大的火炕,锅底架着树枝干柴,把黄豆散铺在炕上爆一宿,以提高出油率。第二天开榨时,将炕上爆热的黄豆装入一个直径一尺半左右,厚度二寸多,圆铁环内圆环、中间略微铺点稻草,五六个摞在一起为一榨。四五个青年小伙子赤身裸体,用力搬动螺旋榨机的大圆盘,借着多头丝杠和圆盘的冲击力将油挤出。
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就住在油坊的库房内,库房门口很大,挂着稻草帘子挡风。我们没有带被褥,夜里就盖麻袋,尽管麻袋不搪风,好在卸了黄豆麻袋多,多盖几层呗,这样住了两宿。
榨完油的豆饼像小磨盘子似的,一块有20多斤。油房有专门收购豆饼的,因为队长有话,价格合适可以卖掉。我们以黄豆质量好为由,据理力争,人家也不肯给涨一分钱,为了给生产队多卖点钱,我们就决定自己串村去卖。最后到了边各寨村,有个生产队要买,算账时对方少算了三块多钱,我说不对,那个会计好像瞧不起我们似的,把算盘扔给了我们,其实我们真不怕,因为董玉书老叔就是会计,不过他没有接算子,只是用眼神示意了一下我。我上学时珠算最好,父亲又是区里的老财粮委员,我就用倒扒皮的方式证明了他们少给了钱,结果他们都不好意思了。
回家是凌晨,卖了豆饼卸了载,车一下子轻了许多,牛也奔家心胜,不待扬鞭自奋蹄,前半夜时就到了家。早晨大喇叭就喊分油,分油是件欢天喜地的大事,家家有人来排队,人人都喜笑颜开。有的人家把油分回家,会熬上锅香喷喷的大白菜,焖一锅高粱米饭饱餐一顿;有的大方人家,会炸点油饼之类给孩子们解馋;但更多人家是节俭食用,以维持一年的用油。
卖瓜
公社化时,队里每年都要种上七八亩甜瓜,三五亩西红柿,除给社员分以外,要卖掉部分以维持生产队的正常开支,我每年这个季节都要当一把小商贩。队长每次找我时总是说,你会算账,大伙儿放心呢。早晨,队长会安排人摘好瓜和西红柿,早饭后就带上干粮,赶着装满西红柿、甜瓜的毛驴车出发了。一般是往俵口、东西塘坨等较大村队走街串巷去卖。一个车两个人,一个人负责约秤,一个人负责吆喝并算账收钱。有时忙得顾不上吃干粮,但只要有人买瓜就高兴。卖瓜的时节大都是七八月份,中午的太阳特毒,把人晒得满头大汗,有时卖的不顺利,没带干粮,又渴又饿,但满车的瓜果也不轻易吃,很有自觉性。
除了下村串街卖外,每年都要在立秋前的一个集日去芦台卖瓜,因为芦台人有咬秋的习惯,立秋节前的芦台集也是销售瓜果的旺季,特别是甜瓜和面瓜(俗称老太太乐),很受芦台人欢迎,只要喊出我们的瓜是躲军淀或韩太村的,人们就蜂拥而上。现在由于外地的哈密瓜、芒果、火龙果等充满市场,本地种甜瓜的也少了,所以很多人淡忘了咬秋的习俗,也有的以买西瓜为咬秋瓜了。
那时赶大车去60里外的芦台赶集卖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头天就要做好准备,晚饭后赶着牛车上路,要赶在天亮之前到达集市。现在60里路开汽车只用半小时,也就是踩一脚油门的事。那时就得折腾一宿,弄得是人困马乏。秋夜露水打湿了全身,满车的甜瓜面瓜,都怕压,车上没处躺,车辕子也没处坐,因为赶车的人都知道“压马、吊牛、逛荡驴”的俗语,意思就是马车可以坐辕子,重点儿没事;牛身子重,车辕子轻一些才好;毛驴是车辕子重了不行,轻了也不行,最好是不轻不重,我们只好跟着牛车缓步前行。
在集市上卖瓜,可不像在乡下串村卖瓜那么轻松,很累人。那时集市在芦台街里,买瓜的人忒多,脑瓜挨脑瓜的,有性急的还大呼小叫的,忙活得我俩汗顺脸流都顾不得擦,但卖得快心里高兴啊!我们那时卖瓜,从不看着人头多就乱涨价。卖完瓜,我和董学志也已是精疲力尽,董学志由于瘦小体质差,看上去更是疲惫不堪。傍晚,我们就住进张家马车店(现在区医院西侧靠南边),一切安置停当后,店主说电影院正放映南征北战电影,卖瓜的钱又没有数,你们不看看去呀!说实话,真想看,可舍不得自己的钱,又不能花卖瓜的钱,就没去。那时一盒“大婴孩”香烟才一毛多钱,也是掏自己的钱买的,集体的便宜不能占啊。睡觉时,因为随身带着卖瓜款,不敢两个人同时入睡,包不离手,手不离包,生怕有什么意外,其实那个年代很安全,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回家了,这回我们可以在车上放心大胆的睡觉啦,任其老牛在205国道上前行。人都说“老马识途”,老牛也识途,早起饮点水,喂点料,上路后不用人管,它会按照来时走过的路,一点不差的走回家。
买猪秧
七十年代初,上级号召大造农家肥,公社出台政策,提倡社员养猪,猪粪沤肥交生产队,以肥换工分,社员们纷纷报名养猪,因为积肥挣工分,一头猪抵得上半个劳力呢。
让社员养猪,就得买猪秧。为了方便群众,生产队采取了猪秧款队里垫付,秋后结算还款和队里派人统一买猪秧的办法,很受社员欢迎,因为买猪秧个人去要误工,有的人还犯怵出门。我是经常被派去买猪秧,一是我在城里当过工人,所谓的见过世面;二是队长信任,说我规矩,不耍滑占便宜。其实,最重要的是我家里有一辆大水管加重自行车,因为买猪秧队里不给派车,谁去谁自备交通工具和盛猪秧的家把式。
记得是1963年春,队长派董学志(已故)、董如善和我去赶玉田县鸦鸿桥集买猪秧。我们每人骑一辆加重自行车,后架上绑着两个用来盛猪秧的大筐,一百五六十里,坑坑洼洼的沙泡路,很是费劲。提前一天赶到鸦鸿桥住店,第二天大早赶集。那时候去外地赶集也不容易,要提前到本地粮站换好粮票,跨省市要用全国粮票,因为那时卖馒头大饼的都要粮票。集市那天一早,我们就直奔集市,把卖猪市场遛了几遍,基本物色好了卖主。买猪秧不但要看猪秧好不好,还要看猪拉稀不拉稀,可不能买了病猪啊。我们买猪不是单个挑,一买就是一窝,这样连窝端买好砍价,我们也省时间。一共选了4窝30多只猪崽,就开始谈价,几经周折谈妥了价格,却不着急抓猪过秤付款。这里有说道啊,因为卖猪的在卖前把猪喂得滚瓜溜圆,那都是钱呀!我们就故意磨磨蹭蹭,等看到猪尿也尿了,屎也拉了,好,过秤算账。装筐封好盖,骑车往家返,当天晚上住进了丰台东村供销社马车店。住店后,把猪崽放入猪圈内,喂食喂水后休息。
第二天继续往家赶,上午9点钟左右,江洼口过了摆渡后就开始刮风,有五六级,步步顶风啊,每个人还驮着100多斤的小猪崽,那个汗出的,袄都湿透了,风一吹,冰凉呱唧的。特别是江洼口至大月河的路,是一条高出地面两米的大道,别说骑车,就是推车也要使出全身的力气,否则自行车会被风吹倒。折腾的人气喘吁吁,小猪崽也吱哇乱叫。我们3人轮换着打头,后面俩个人会稍微省些力气。就是这样,还是遇上事了。董学志摔跤把小猪摔出筐外,跑出去两头,这可坏事了!我们留一个人看猪,另俩人漫野地和小猪展开了一场追逐的拼搏。沟沟坎坎,上上下下,连滚带爬,帽子丢了,鞋跑没了,连裤腰带都跑断了,狼狈不堪呀!多亏了大月河村耪地的社员们帮忙,才将两只猪崽逮着。
分猪秧用的是最传统最省事的法,那就是抓阄。农村历来有“万贯家财勾上死”之说,把30多头猪排成号做成阄,对号领猪,满意的欢欢喜喜,不满意的也只埋怨自己手臭罢了。
书法课
书法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有书法课,每周一节课专门学习书法,我们也叫做大仿课。每到上书法课时,我们就手托着五花八门的砚台,有方的,有圆的,也有用个小碗的。那时没有墨汁,用的基本上都是一种叫“金不换”的墨块,在砚台里放上适量的水研磨。碗不行,太光滑,研不了墨汁,那时同学们极友好,会给带碗的同学倒些墨汁用。有的人家没有墨了,就用锅底灰,遇上家长有耐心的,还会细心地把火灶头那块砖上的黑烟子刮下来,比锅底灰写字黑一些,只是锅底灰和灶门的烟灰不爱溶于水,要反复搅拌才行,而且用烟灰写的字不能摸,弄不好会抹得黑乎乎的一片,老师判作业也是小心翼翼的。常常是一节大仿课下来,学生们嘴上、手上、桌子上,甚至衣服上都是黑乎乎的。那时教书法的是吴玉鼎老师,大海北村人,右眼有点残疾(“玻璃花”),字写得好,脾气也好,说话慢条斯理、细声细气的,他看我们黑乎乎的模样,说过一句幽默的话:“喝墨水灵啊!”
那时,一支毛笔要用一两年。记得有一次笔头掉了,我用松香点燃后把笔头又安上了,继续用了很久。还记得,写字认真不认真老师很重视,但更重视的是坐姿和握笔的方法,老师每节课都对这方面给予强调和纠正。开始写大仿就是描红,那时没有田字格纸,只有从串学馆的小贩手里买大仿纸,回家后让大人给裁好订个本。大仿纸底下有正楷字的仿影,按照透过来的字体认真去描就行了,到五六年级就不让描了,但可以照着临摹。每节课都有课堂作业,下课就得交作业,由老师给判,较好的字,老师会给画个红圈。因为父亲是区政府的财粮委员,毛笔字写的很好,受父亲熏陶,我的毛笔字写的不错,老师总夸奖,就爱上书法课,我又是班长,每次发书法作业本,我的红圈得的特别多,心里就特别美。
后来我考上了市里中专技校,由于字写得好,就被推选为班干部,负责布置板报,偶尔有用毛笔抄写什么的,都是我的活,连老师都肯定我的毛笔字写得不错。回乡务农后,每年春节都给乡亲们写春联,从腊月十几开始,要写到大年二十九贴春联那天,都是尽义务,但很高兴。1995年我还加入了天津市书法协会,经常参加各种书法展出活动并获奖。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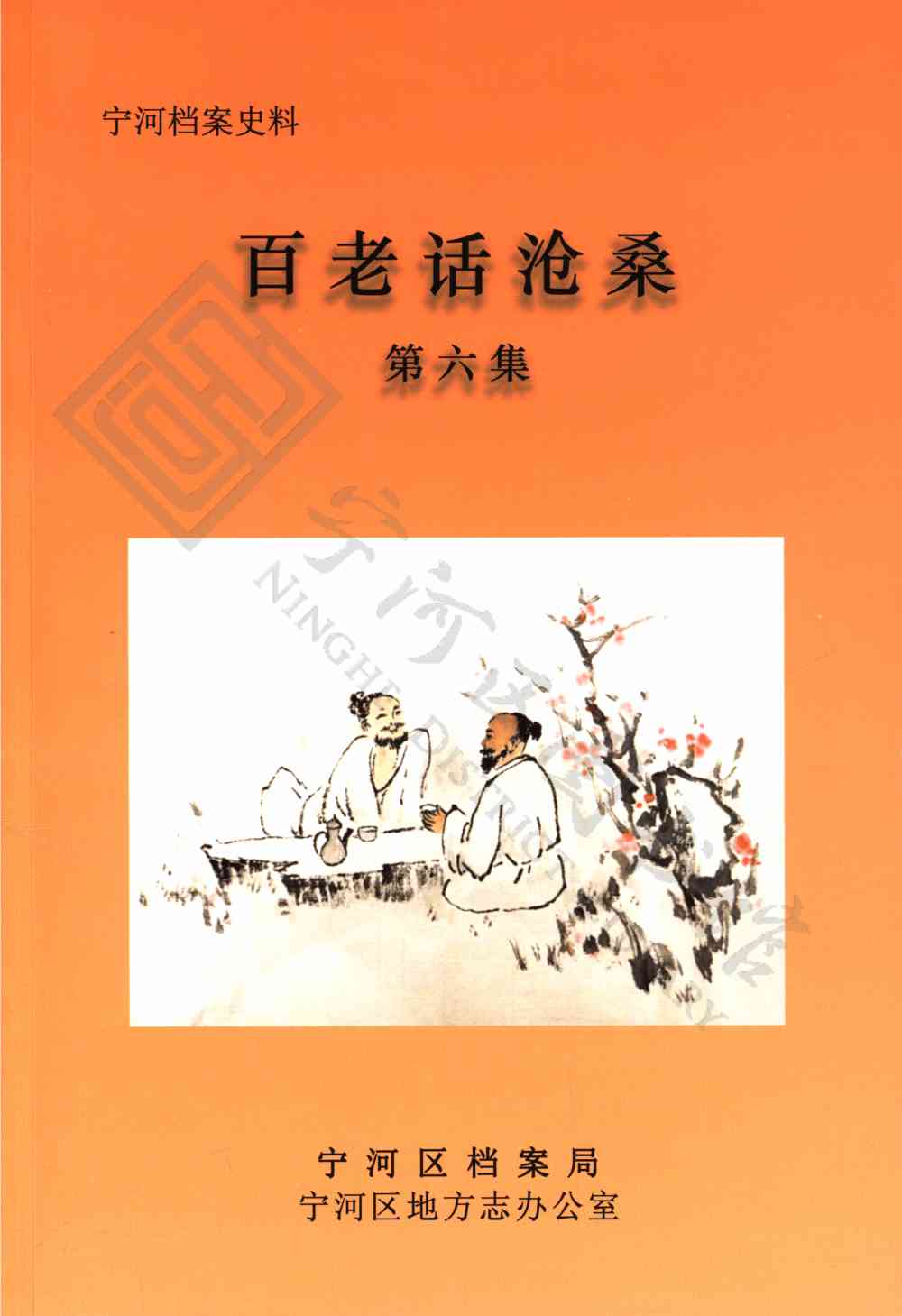
《百老话沧桑 第六集》
本文记述了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以来为人熟知和鲜为人知的史料。百余篇故事,从不同的角度,映现着时代的沧桑,镌刻着历史的印痕,记录着生活的风雨,熔铸着拼搏的辉煌,也彰显宁河人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特别是一张张浸洇着时代风云的珍贵照片,多维度、多层面地回顾了历史,记忆了生活,述说了奋斗,见证了发展。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