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的家乡往事
| 内容出处: | 《宁河文史资料第八辑》 图书 |
| 唯一号: | 021920020230002231 |
| 颗粒名称: | 朦胧的家乡往事 |
| 分类号: | K292.14 |
| 页数: | 14 |
| 页码: | 267-280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作者的家族历史和个人经历,包括父亲被关押、家庭贫困、作者在咖啡制造厂当童工、在伪满中央银行俱乐部当助理办事员等。作者还介绍了自己在空军技术院校任教近四十年的经历,并对家乡宁河的往事进行了回忆和讲述。 |
| 关键词: | 宁河县 李其颖 家乡往事 |
内容
我生于芦台,是地道的宁河人,尽管在关外生活了七十余年,可总是忘不了生我的那块土地——芦台。从部队退役后,空闲时间多了,怀念家乡的情绪更加强烈了,于是便把记忆中的家乡往事写了下来,原想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抒发自己的思乡情感,二是留给子女翻阅,让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是宁河人的后代。这次把稿子寄给宁河老乡,则又增添了一个目的,就是通过讲述家乡的一些往事,向家乡亲人们报个到。我这个年近八旬、身在长春的老军人,永远是芦台的子弟,是你们的乡亲。
一、我的家族
我们全家都是宁河人,在讲述故乡往事之前,先把我家老辈人和个人的情况做个概略的介绍。
我家祖居河北宁河已经上百年,据说是满清年代从湖北襄阳一带随官方移民到宁河的,并一直定居于宁河县城。我的祖父叫李华春,原是个货郎,略有积蓄后在县城开了个染坊。他们弟兄三个,他居长,下面有二弟旭春、三弟广春。祖父生三男一女:长子李成庆,字善卿,是我的父亲;次子李成禄,三子李成善,女儿李成娴。我母亲姓王,芦台农场岭头村人,出身于富裕中农之家,未读过书,是一位持家的旧式妇女,四十岁时起了个名字,叫素贞。我父母育有三个儿子,都出生于宁河,我是家里的老疙瘩,上面有两个哥哥,大哥李其昌,1919年生,二哥李其强,1925年生。
父亲生于1893年,幼时在宁河读过几年私塾,有一定的文化。十四岁到辽宁绥中等地学买卖、站栏柜。上世纪二十年代,他二十多岁时才回到家乡经商,并以祖父积攒的钱,以及从母亲家凑的钱作为资本,与其他几个人合股,在芦台开了家粮栈,叫“日升恒”,由他身兼掌柜(即经理),主持经营,地点在芦台大桥西。据说父亲的生意做得不小,成火车地经营北方的粮食,在芦台也算得上是小有名气的商号,我出生时家道正旺。我长大后母亲经常给我讲家史,(叫“讲古”),据她讲,父亲在芦台当“日升恒”掌柜的后期,大约在二十年代末、我一两岁的时候,正值军阀混战后期。某次从外地购进成火车的粮食时,途中火车被军阀征用,车上的粮食随之被劫走,下落不明。粮栈受此损失一蹶不振,资金大量亏损。事后股东们追究此事,提出质疑,认为资金亏损并非出于火车粮食被劫,而是被父亲个人私吞。于是向宁河县衙门提出控诉,状告父亲私吞股资,结果父亲因拿不出有力证据而败诉,被关押在县衙门的监狱里拘禁了两、三年,据母亲说,生我的时候我家还是个大家庭,除我们这一支五口人之外,还有二叔、三叔家都在一起过,没有分家,全家约有十几口人,家境小康。全家在芦台居住、经商近十年,直至“日升恒”倒闭。
1933年父亲被释放回家,他旋即投奔长春市的姑母处谋求出路,翌年,把我们全家接到长春市定居,并繁衍生息至今。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原来我们芦台五口之家,已经有四人作古关东:父亲病故于1947年4月,享年55岁;母亲病故于1953年3月,享年62岁;大哥病故于1980年,享年61岁;二哥病故于2000年,享年75岁。如今仅剩下我这个老宁河,继续存活在关东长春。尽管年事已高,我还是企盼着有生之年,能够再次踏上还乡之路,以圆此生最后回拜故土之情。
我1928年农历九月初二生于宁河县芦台镇,生我那年父亲36周岁,母亲37周岁。我6岁(1934年)随母亲到长春,14岁小学毕业,当时正值父亲失业,家中无力供我继续读书,便开始投身社会,在日本人的咖啡制造厂当童工,后来又在伪满中央银行俱乐部当过助理办事员(日本人叫“事务助手”)。1945年8月15日伪满垮台、东北光复,我又当过商店店员,读过中学、职业高中,任过小学教员。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后,才得以考入哈尔滨的东北农学院森林系再次读书。1950年12月,我响应政府号召,志愿参加抗美援朝,由东北农学院选送到空军长春预科总队参军。1952年7月我从哈尔滨空军第一航空学校毕业,留校任航空机械专业助教。同年8月,空军在长春组建第九航空学校时,我被调往九航校任飞行原理助教。此后便一直在航校任教,从排级助教,连级教员,营级、团级主任教员,副师级副教授,技术6级(正师级)教授,直至1988年12月退休。学校的名字几经变化,由九航校,先后改为第二航空机务学校、第二航空技术专科学校直至第二航空学院。到接到退休命令为止,我在空军技术院校,当了近四十年的技术教员。及至1999年,被移交到长春市军队离退休干部南岭休养所时,我已在部队生活了近五十个春秋。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整齐的营房、宽阔的机场、心爱的飞机、众多的亲密战友和独具一格的军旅生活。这一切都使我毕生为之倾心,我永远怀念这一切!
二、宁河旧事
我的幼年是在老家芦台、宁河等地度过的,当时我还不太懂事。后来常听母亲给我“讲古”,使我略微了解一些幼时家庭和家乡的情况。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在父亲被关押在县监狱的两、三年期间,家中失去生活来源,为了糊口,我们哥仨在母亲带领下,往来于县城李氏宗族和岭头村各舅父家庭之间。那期间我们吃尽了亲戚们的白眼,饱尝了世态炎凉之苦,勉强撑过了那段难关,直至父亲获释、全家出关迁往东北长春。
出关以前,在我的记忆中,我家在宁河先后住过四个地方:第一处是宁河县衙门头的二姨家,第二处是宁河县城东街,第三处是岭头村,第四处是芦台。
(一)杨家贞节二姨
在衙门头二姨家住的时候,我也就两三岁,父亲正在县衙门打官司,还未最后定案,但已经被拘禁起来。二姨家是一座不太大、但很整洁的临街四合院,灰色砖瓦房,大门朝东,出门的左侧就是衙门朝南的大门。二姨是个封建婚姻的受害者,而且很具典型性。据母亲讲,二姨比母亲大十几岁,18岁时嫁给宁河县姓杨的大财主家。婚后几个月男人便患痨病死去,她年纪轻轻的就守了寡,没有子女,独自一人,一守就是二三十年。杨家靠着财大气粗,为她申建了个“贞节牌坊”,成为全城有名的贞节烈女;可在我的记忆里,好像从未见过那牌坊是个什么模样。二姨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她终日满面冰霜、不苟言笑、性情古怪,这可能是由于她常年过着孤独的生活,大好的青春白白地为一块牌子而牺牲掉,以致造成孤僻的性格和寡欢的脾气。她对我这个小外甥不仅不亲近,反而见我就烦,甚至动则骂我“小猴七儿”,以致每次见到她,我就害怕,就往母亲背后藏。所以,我心目中的二姨母既不可亲、又不可近,从她身上找不到半点亲情的影子。我们住在二姨家的时间不长,那段时间母亲几乎每天跑来跑去地外出找熟人、托亲戚,为父亲打赢官司找门路、求解脱。那段时间,我随母亲曾经到西街李家老宅的二爷和三爷家走动。那是两所并列的灰砖瓦房,每所约有三五间,周围有围墙,中间隔着一道墙把两所房子分隔为两个独立的院子,二爷和三爷以及他们的后代就居住在那里,看上去是县城里的中等人家。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爷爷辈的家里串门,我亲眼看到过的宁河本家爷爷辈的情况,仅此而已,更多的事情就无从说起了。
(二)东街轶事
第二个住处在宁河县城东街,那是租住的一间小土坯房子,地处东街的东头、路北侧。那年我三四岁,父亲已经身陷囹圄,家庭全靠母亲一个人支撑,既要照顾我们哥仨生活,又要为父亲能够早日出来到处奔走。那房子的东头不远处有一条河,可能通往蓟运河吧?我说不清楚。记得那时母亲经常带哥哥出门,把我锁在家里,怕我自己出门掉到河水里出事。那条河确实不安全,我曾亲眼看到过,一个被河水淹死的小孩,被大人捞了起来,摆在岸边,一个妇女搂着尸体大声哭叫,引来周围人们的一片同情声。母亲外出有时也会带上我,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甘铸元大爹家,甘大爹是父亲的朋友,家道小康,在地面上估计是个有头脸的人物,他家的具体地址我说不清楚,但是记得那是一座独门独院的砖瓦房,院子不小,里面栽种了许多花草。母亲每次去都是为了父亲的事,求他设法把父亲早日解救出来。有时母亲一面与甘大爹说事,一面抹眼泪,甚至痛哭流涕,所以在我的心目中,去甘家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记得有一次母亲和哥哥一起出去,却把睡觉中的我独自锁在家里。当我醒来睁眼不见一个亲人时,恐惧地爬起来奔向屋门,可是门已经被从外面锁住,顿时令我六神无主,倍感恐惧,于是一面用力推门,一面大哭大叫,母亲不见了!哥哥也不见了!如何是好?不知过了多久,在我哭得已经没有力气的时候,他们终于回来了,总算结束了那恐怖的一幕。至今那一幕仍在脑海里留下模糊的影子。
我家的门外是县城的东街,斜对面有一处大宅院,大门总是关得紧紧的,显得门户森严,据说那是江苏省督军齐燮元的父亲齐茂林的宅子。按当时街面上的议论,齐燮元是宁河县出息的大人物。后来才知道,抗战时期此人当了汉奸,曾担任过伪华北临时政府的治安部总长,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枪毙于北平。关于他的事情,我们哥三个都听老宁河人讲过,还听说齐燮元小时曾与父亲在同一个私塾读过书。可是据后来我核对时间,齐的年龄比父亲大十四岁,不可能同时在一起读书,也许是同一个私塾先生教过的学生,用如今的话讲,仅仅是校友而已①。齐燮元年轻时到天津陆军学堂当学兵,即现在说的军校学员。据说学兵时期就参加过战斗,表现十分勇敢,毕业后当了军官,升迁很快,一直当到江浙督军、省长,二十年代已经是中国有名的大军阀,我曾在《民国演义》上,读到过有关他在众多军阀当中,左右逢源,迂回捭阖的记载,虽说演义难免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大体上应该是有根据的。他出息了,他在宁河的家人也随之有了名望,成为县城里的特大门。不过他父亲齐茂林并未离家随他生活,而是一直住在县城里。他家虽说宅深院大,但从院外却看不到豪华景象。他家的人与外人很少往来,终日大门紧闭,像是有意识地与世隔绝。只听邻居的大人们说起,他家院子里养了猴子、大鹅等动物,为他们看家守院,一旦有人进入,大鹅就会大叫着拧人,猴子更厉害,会把来人挠伤。听了这些传闻,我和哥哥总是绕路经过他家门前,不敢靠近。
在东街住的时间推算起来应该是1932年,那年夏天,县城东北面的大庙里(是魁星楼?还是文昌阁?),住进了不少的中国军队,天天在那里唱歌、上操。我和哥哥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这个消息,每天都去看热闹,大家围着看他们走步、喊操、刺杀、…。每当他们解散休息时,就会有几个士兵走到我们小孩子堆儿里逗大家,有时把我这样的幼儿抱起来,问东问西地逗着玩。他们一律灰色军装,头戴大沿帽,都很年轻、很活泼,看上去并不可怕,反而可亲,与后来在乡间见到的那些散兵游勇大相径庭。从时间上看,那些军人应该就是“9·18事变”后从东北退却到长城内冀东一带的东北军,或者是原来驻守在关里的东北军。从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看,正规的东北军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颇能战斗的军队,在“九·一八事变”中,如果没有蒋介石的“不准抵抗”军令限制,东北军是有可能能顶住日本关东军的入侵而避免东北沦陷的。“七七事变”后,东北军也为全民抗战而浴血奋战过,表明他们并不是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众。我的那段亲身感受,尽管属于小孩子的直觉,但是也说明那些正规的旧军队并不像某些文字写的那样,一律是草包、匪军。他们训练严格、纪律严明,在驻防中,不扰民、不欺民,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很坏的印象。我是他们之后的中国军人,尽管党派不同,但是我认为有必要为前辈的一些军人正名:我们中国军人历来大多数都是好的,并不是不堪一击的豆腐渣,如果说历史上曾经出过不堪一击的队伍的话,那是上层腐败或指挥失当造成的,应该属于上层官长的责任,因为世上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带不好兵的官长。
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战士颇能说明这个问题,昨天还是枪响就跑的国民党兵,今天被我们解放过来,上了战场马上就变成勇敢的战士。这个现象怎样解释?只能说队伍的性质变了,上层指挥不同了,因而同一个战士的表现也就变了。我们这一代由共产党、老八路带出来的学生兵,原本是些很少接近群众的书生,但是在老八路的教育下,很快就变成以人民为父母、待群众如家人的八路接班人。我们热爱老百姓,老百姓也信任我们,他们遇到困难总是首先想到找解放军,军人成为社会上最受信赖的群体、最可爱的人。什么原因?只能说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英明,组织领导有方,难道还会有其他别的解释吗!
(三)姥家——岭头
我家住过的第三处是岭头村,时间是1932年的秋天至1933年的秋天、在我四五岁之间,那里是母亲娘家,有三个舅舅居住在那里。我们搬到岭头的原因很清楚,就是没有经济来源,在县城里住不下去了。岭头是个地道的农村,村子有两条街——东街和西街,两街之间隔着个大壕沟,没有水,在壕沟的东侧有座小庙和一家铁匠炉。我的二舅叫王章,是个教书先生,住在西街路北;三舅叫王衡,是农民;老舅叫王柏,也是农民。他俩家在西街路南,住对面屋,两家分别有一头驴和马,用土改政策看,估计是个上中农吧!二舅家我从来没去过,只见过二舅一两次面,他是个瘦高、弯腰驼背、头顶帽头、戴副老花镜的老夫子,至于二舅上头是舅舅还是姨我就说不清了。刚到岭头时,我们住在三舅家里,家中有舅母、表兄和表嫂等,人口不少,我们四口突然到来使他家难于应对。所以不久我们就在东街的西头租借了一间草房,迁往那里自己起火,靠舅舅们的帮助维持生活。其实由于当时时局混乱,而且时旱时涝年景不好,舅舅们的日子也很艰难,没有多大的力量帮助我们,以致我家不时断炊,生活无着。记得入秋之后,哥哥多次带我到高粮地里,拾捡掉在地上的粮穗,以弥补粮食的不足。捡回粮穗之后,母亲便用木棍打掉带壳的米粒,再放到破缸里舂掉一些壳子,便成为我们的食粮。那年的春节我们是在岭头度过的,临近春节时,平日几乎很少有人走动的东西两条街,立刻热闹起来,外乡的小商贩纷纷集聚到街上,卖鞭炮的、卖对联的、卖各种年货的摊子摆在街道两旁。入夜,唱乐亭影的小戏班子在大车上支起屏幕、搭成戏台,点上汽灯,临街演唱起来,吸引许多村民围观,好不热闹。这一切都使得平日死气沉沉的农村,焕发出一缕生机,我们哥三个也因此而兴奋起来,融入迎接春节的欢乐海洋之中。我和二哥看到别家孩子手提灯笼玩耍时,我们便缠着母亲也要买一个,可是她哪里有钱买这种奢侈品呢!但是为了让我们过上一个快乐的节日,她想方设法地拣到一只上了锈的小铁盒子,剪掉周围大部的铁皮,然后用一块红纸剪成纸花贴在盒子的周围,里面点上一只别人送给的小蜡烛,灯笼便做成了。我和二哥提着它欢天喜地地度过了那贫困寒酸的除夕夜,这是母亲的剪纸作品第一次在我记忆里留下的印象。后来我们定居长春时,每到春节临近时,母亲总要用红纸剪一些娃娃、鲤鱼、公鸡、花朵等为主题的剪纸,张贴在窗玻璃上和门上,邻里都夸她手巧。由她亲手糊制的贴满剪纸的笸箩,一直保留到她离开人世后的五十年代中期,才从家中消失。至今回想起七十年前的剪纸灯笼的往事时,还从心里佩服母亲那精湛的剪纸技艺和乐观的心绪。如果她在解放后多活几年,一定会为点缀新社会而创制出许多剪纸艺术品的。
在岭头居住的第二年春天,我突然染上了小儿麻疹,终日高烧,满身斑点,难受得又哭又叫。那时的农村本来就缺医少药,境况窘迫的我家,就更谈不上求医抓药了。母亲焦急无奈地日夜抱着我在地上走来走去,总算挺了过来,我的高烧开始退了,身上和脸上的斑点也逐渐结成痂,一天天地好起来。按当地的民俗,小孩子得麻疹之后的结痂期,为了乞求子孙娘娘保佑,让孩子身上的斑痂早日脱落、不落“麻子”,应该买芝麻烧饼给病孩吃。母亲为了一个烧饼,走了几家烧饼铺,说了不少的好话,总算讨到一个已经干瘪了的烧饼给我。母亲为我不会生麻子而高兴,我则既想吃、又不舍得吃地啃尽了那个虽硬却香的干烧饼。岭头是个偏僻的北方农村,平时十分安宁,但是在三十年代初,由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导致国内北方混乱,这个村子经常成为散兵游勇袭扰的对象。当时村民把那些散兵叫做“大兵”,把逃避他们袭扰叫做“逃反”,在我的记忆里,那段日子,我家曾经几次随村民一起“逃反”,有时是白天,有时是夜晚,还有一次是大雨中逃出村庄。逃避的地点大都是附近大户人家的坟茔地,叫做“坟圈子”。每次“逃反”的时间大都不长,在野外呆上一天半日,“大兵”过村后,村民便返回家园。但是也有一次是逃往另一个村庄,躲避了两三天,才得以回村。平时村民家家都为“逃反”提前做好了准备,把家中的细软坚壁在草垛、地下、假壁墙等不易被发现的地方,并准备好衣服、鞋子等随身用品以及大饼子、咸鱼干等应急食品。我家没有细软可藏,但是大饼子和咸鱼干还是有所准备的,记得母亲为我们哥三个做了分工:大哥负责拿几双鞋子,二哥提大饼子,我拿小包咸鱼干,当听到有人敲锣大喊“大兵来了!大兵来了!”时,我们立即拿上应急物品,随着邻里的人们,逃向村外躲避。那些“大兵”是些三三两两掉队或逃亡的士兵,他们没有组织约束,也没有供应保证,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拿到哪里,有的甚至骚扰妇女,对她们施以非礼。记得那年秋季,一次母亲带着我和哥哥逃到外村躲大兵时,曾经亲眼目睹散兵扰民的经过。一天夜间,外逃的女村民为了避免遭受大兵的袭扰,大家都集中在一家的炕上,母亲抱着我、与另两位年龄大的妇女坐在炕沿附近,年轻的则挤成一团藏身于她们的背后。为了避免受到骚扰,年轻人的脸都用锅底灰涂抹成黑白相间的道道,很像京剧的脸谱。地下摆着农家木柜和长条板凳,柜上点着一盏若明若暗的小油灯。半夜时分,突然窜进个大兵,他高高、瘦瘦的,二十左右,一身不整洁的军装,提支长枪。进了屋子,坐在长板凳上,一面高声喊:“拿钱来!”,一面用枪托猛击地面,用以加强他的语气。当时炕上的女人们大都把头部压得很低,尽量使自己的脸庞躲开他的视线,只有母亲抬着头,用乞求的口气央求说:“老总,我们都是逃难的,那里有钱呢!”,那人其实也看到了当场的情景,料到从那些衣着褴褛的女人身上搜不到钱,但是还不死心,回过身来打开背后的木柜翻腾起来,自然是一无所获。还算万幸,最后他匆匆地开门离去,连头都没回。尽管当时我还是个幼童,但是那场面发生的一切,至今仍像电视剧一样,印在脑海里,甚至连那大兵的东北辽宁口音(当然是我长大后对照识别出来的)都记得清清楚楚。从当时家乡民不聊生的混乱状况可以看出,“9·18事变”不仅使三千万东北民众沦落为亡国奴,也波及到华北大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中国老百姓,使他们不得安生。
(四)重返芦台
1933年父亲被放了出来,回到岭头,失业在家。还是家在关外的姑妈惦记着我们一家,她给父亲寄来笔路费,让他到关外——当时的伪满洲国寻求生路。于是父亲便带上大哥出了关,投奔家在长春——即伪满首都“新京”的姑妈家,并在长春孟家桥粮食交易所谋了个记帐员的角色,暂时安顿下来。父亲离开老家后,母亲带二哥和我也离开了岭头,重返我的出生地芦台,等待父亲的消息。迁到芦台时,母亲找到一份临时工作,任务是替某主人家看管房子。那个主人家的姓氏我不知道,但是听说很有来头,是满清聂军门的儿媳,让母亲看管的是她存储财宝文物的一间房子,我们就住在那个房间里。地址大约是中街西大桥附近,在一座临街四合院里,是西厢房。正房住着的是姓李的商人家,主人叫李子真;东厢房空闲着。
到了芦台我们的生活一时安定下来,但是替人看家的差事并不好干,因为主人不时地为我们带来不愉快的插曲。这位女主人个头小小的、瘦瘦的,穿一身清末民初的抿怀衣装,一双三寸金莲,走起路来一摇三晃,像是从坟墓爬出来的古代僵尸,那是个主子气十足、高傲刁钻的老太婆。她对存放在屋子里的一些箱箱柜柜是否完好,里面的东西是否被我们挪动过,总是放心不下,因此隔三差五便来查看一番。进屋的第一件事就是,急不可耐地让母亲给她拿便盆来,伺候她解小手。方便完毕她立即精神焕发,一面审视那些箱柜的外表以及里面的扳指、水烟袋、念珠一类古董,一面拉长了脸以主子的口吻责问母亲。不是说我们动了她的东西,就是指责母亲箱柜没有擦洗干净。总之,在我和哥哥幼小的心灵上,一次又一次地留下的是那老妖婆的狰狞面目,以及随母亲一起受辱而激起的愤懑心情。为了发泄这股气愤,我俩常常捉几条小虫来,把虫子当成那老太婆,用树枝反复地抽打,还念念有词地喊着:“打死你,老妖精!打死你,老妖精!”,直打到虫子变成一滩稀泥,才算略解我们心头之恨。
我家的具体住址已经说不清楚,如今对照芦台街道图,按图索骥式的判断,可能是在中街西头的路南,记得我和哥哥曾经沿着街道往东头走,越走越繁华,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卖吃的、卖穿的、文具店、药铺,…,路北还有一家戏院。还记得在我家东面不远的路北,有一座很气派的祠堂,临街是些牌坊、房子、石碑类的建筑,院子深处有个很高很大的半圆型土包,可能是座坟墓。至今也不知道那是为哪位大人物修建的,是杜家?聂家?还是于家?会不会就是聂军门的祠堂呢?到现在也说不清楚。1934年的春节我们是在芦台度过的,家乡的节日精彩纷呈,热闹非凡,到处焰火,满街高跷,店铺门前灯红彩绿,人们喜气洋洋。元宵节放焰火,据母亲说,每放一个焰火就能打出一出戏来,能够看到戏里主角的摸样。我年龄太小、不懂戏,所以尽管我曾经身临放焰火的现场,但只留下了五彩烟花的印象,却从来没看到过人物的形象。焰火出现人物这个事,至今我依然没有搞明白,要么是对母亲讲的话理解有误,要么是外行看不出门道的缘故,还有待向老家的焰花专家请教,以解开这毕生之谜。
1934年的春天,母亲觉得我跟二哥终日在家淘气不是办法,应该让我们上学读书了。正好我家的斜对面是一所小学校,母亲便把我俩送去入了学,同在一年级读书。学校的校长为我俩分别起了学名,哥哥叫其祥、我叫其龙,可是当我们把学名告诉母亲时,她连呼不可,她说:“宁有富命、不叫富名,你怎么能叫“其龙”呢!皇上是龙,你敢‘骑’皇上?那是犯天条的啊!”第二天她找到了校长,说了这个道理,校长便把我的“龙”字改成了“荣”字;把哥哥的“祥”字改为“强”字,满足了母亲的请求。从那以后,我们便有了其荣、其强的学名,哥哥终生未变,我则于1946年,为了改大年龄、逃避国民党征兵,不得不改名为其颖;不过家人还是一直叫我其荣,直到现在。
芦台那所学校的大概环境至今我还依稀记得,学校在大街的北面,临近小河的东岸,周围是灰色砖砌成的院墙,校门面临大街,院子里是三排呈Ⅱ字形排列的教学用房,一律是灰砖瓦房,共有十几间。教务室和我们班的教室临街,我们的老师是一位年轻人,瘦瘦的脸上带一幅近视镜,身穿大袍。他好像是新教师,对小孩子不太耐心,动辄发脾气。我当时六岁,未经过幼儿教育,懂事甚少,铅笔不会拿,毛笔更不会握,甚至无法习字;老师讲算术加法时我一窍不通,像个小傻子。于是我便成为全班最落后的一个,时不时地受到这位老师的体罚,不是打手板,就是挨藤棍,打得我嚎啕大哭。哥哥在班里当副班长,看到我那幅可怜像又是着急,又是无奈。值得庆幸的是,学校有一位十分有耐心的副校长,年近四十。他了解到我的幼稚情况之后,便常常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抱着我、手把手地教我握毛笔的方法,给我讲一加一是什么意思。他的态度和善,不厌其烦,好像是对自己家里的孩子,跟那位班主任的粗暴态度大相径庭。那所学校属于当时的洋学堂,按着当时政府指定的教科书上课。记得我们学的课本中有:大狗跳、小狗也跳,…;猴子玩火…等适合孩子们学习的生动内容。另外还有手工课,体育课、音乐课等,教学内容表明,当时的国民教育还是很注重学生的全面培养的,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颇为注重素质教育。我们一年级小学生就开始上手工课,大家用小小的手工刀,把五颜六色的手工纸切成均匀的小条条,再用不同颜色的纸条编织成彩色条纹、花草等多种图案,对开拓儿童的美感、观赏能力、动手能力、形象思维等都十分有利。学校也注重学生的身体发育,记得有一次学校为全校学生量体重,地点是学校的大门洞里,工具是旧式大秤下面吊了个大筐,学生坐在筐里,由两位校役抬起秤来,为学生量体重。用现在的眼光看,那样的测量方法有些好笑,可是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学校能够作到那种程度,确也难能可贵。
在那所学校只读了几个月的书,但是却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1988年在我阔别故乡半个多世纪之后,回到老家探视时,曾有意地探询了我最早的母校,听说那所小学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被彻底毁坏,现在于另一个地点新修了一所,叫芦台第三小学。
1934年,大约是9月,父亲寄来笔路费,让母亲带我们哥俩到长春。我和哥哥退了学,随母亲坐火车出关进了东北。从那以后,我们家五口人便一生定居在东北长春,那年我六周岁。到我动手写这篇回忆文章时,父母亲和两位哥哥都已客逝关外,从宁河到长春的全家五口人,仅剩下一个年近八旬的我了,正像孔老夫子说的那样:“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自然规律不可抗拒,我何时追随他们而去,只能听其自然了。
一、我的家族
我们全家都是宁河人,在讲述故乡往事之前,先把我家老辈人和个人的情况做个概略的介绍。
我家祖居河北宁河已经上百年,据说是满清年代从湖北襄阳一带随官方移民到宁河的,并一直定居于宁河县城。我的祖父叫李华春,原是个货郎,略有积蓄后在县城开了个染坊。他们弟兄三个,他居长,下面有二弟旭春、三弟广春。祖父生三男一女:长子李成庆,字善卿,是我的父亲;次子李成禄,三子李成善,女儿李成娴。我母亲姓王,芦台农场岭头村人,出身于富裕中农之家,未读过书,是一位持家的旧式妇女,四十岁时起了个名字,叫素贞。我父母育有三个儿子,都出生于宁河,我是家里的老疙瘩,上面有两个哥哥,大哥李其昌,1919年生,二哥李其强,1925年生。
父亲生于1893年,幼时在宁河读过几年私塾,有一定的文化。十四岁到辽宁绥中等地学买卖、站栏柜。上世纪二十年代,他二十多岁时才回到家乡经商,并以祖父积攒的钱,以及从母亲家凑的钱作为资本,与其他几个人合股,在芦台开了家粮栈,叫“日升恒”,由他身兼掌柜(即经理),主持经营,地点在芦台大桥西。据说父亲的生意做得不小,成火车地经营北方的粮食,在芦台也算得上是小有名气的商号,我出生时家道正旺。我长大后母亲经常给我讲家史,(叫“讲古”),据她讲,父亲在芦台当“日升恒”掌柜的后期,大约在二十年代末、我一两岁的时候,正值军阀混战后期。某次从外地购进成火车的粮食时,途中火车被军阀征用,车上的粮食随之被劫走,下落不明。粮栈受此损失一蹶不振,资金大量亏损。事后股东们追究此事,提出质疑,认为资金亏损并非出于火车粮食被劫,而是被父亲个人私吞。于是向宁河县衙门提出控诉,状告父亲私吞股资,结果父亲因拿不出有力证据而败诉,被关押在县衙门的监狱里拘禁了两、三年,据母亲说,生我的时候我家还是个大家庭,除我们这一支五口人之外,还有二叔、三叔家都在一起过,没有分家,全家约有十几口人,家境小康。全家在芦台居住、经商近十年,直至“日升恒”倒闭。
1933年父亲被释放回家,他旋即投奔长春市的姑母处谋求出路,翌年,把我们全家接到长春市定居,并繁衍生息至今。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原来我们芦台五口之家,已经有四人作古关东:父亲病故于1947年4月,享年55岁;母亲病故于1953年3月,享年62岁;大哥病故于1980年,享年61岁;二哥病故于2000年,享年75岁。如今仅剩下我这个老宁河,继续存活在关东长春。尽管年事已高,我还是企盼着有生之年,能够再次踏上还乡之路,以圆此生最后回拜故土之情。
我1928年农历九月初二生于宁河县芦台镇,生我那年父亲36周岁,母亲37周岁。我6岁(1934年)随母亲到长春,14岁小学毕业,当时正值父亲失业,家中无力供我继续读书,便开始投身社会,在日本人的咖啡制造厂当童工,后来又在伪满中央银行俱乐部当过助理办事员(日本人叫“事务助手”)。1945年8月15日伪满垮台、东北光复,我又当过商店店员,读过中学、职业高中,任过小学教员。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后,才得以考入哈尔滨的东北农学院森林系再次读书。1950年12月,我响应政府号召,志愿参加抗美援朝,由东北农学院选送到空军长春预科总队参军。1952年7月我从哈尔滨空军第一航空学校毕业,留校任航空机械专业助教。同年8月,空军在长春组建第九航空学校时,我被调往九航校任飞行原理助教。此后便一直在航校任教,从排级助教,连级教员,营级、团级主任教员,副师级副教授,技术6级(正师级)教授,直至1988年12月退休。学校的名字几经变化,由九航校,先后改为第二航空机务学校、第二航空技术专科学校直至第二航空学院。到接到退休命令为止,我在空军技术院校,当了近四十年的技术教员。及至1999年,被移交到长春市军队离退休干部南岭休养所时,我已在部队生活了近五十个春秋。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整齐的营房、宽阔的机场、心爱的飞机、众多的亲密战友和独具一格的军旅生活。这一切都使我毕生为之倾心,我永远怀念这一切!
二、宁河旧事
我的幼年是在老家芦台、宁河等地度过的,当时我还不太懂事。后来常听母亲给我“讲古”,使我略微了解一些幼时家庭和家乡的情况。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在父亲被关押在县监狱的两、三年期间,家中失去生活来源,为了糊口,我们哥仨在母亲带领下,往来于县城李氏宗族和岭头村各舅父家庭之间。那期间我们吃尽了亲戚们的白眼,饱尝了世态炎凉之苦,勉强撑过了那段难关,直至父亲获释、全家出关迁往东北长春。
出关以前,在我的记忆中,我家在宁河先后住过四个地方:第一处是宁河县衙门头的二姨家,第二处是宁河县城东街,第三处是岭头村,第四处是芦台。
(一)杨家贞节二姨
在衙门头二姨家住的时候,我也就两三岁,父亲正在县衙门打官司,还未最后定案,但已经被拘禁起来。二姨家是一座不太大、但很整洁的临街四合院,灰色砖瓦房,大门朝东,出门的左侧就是衙门朝南的大门。二姨是个封建婚姻的受害者,而且很具典型性。据母亲讲,二姨比母亲大十几岁,18岁时嫁给宁河县姓杨的大财主家。婚后几个月男人便患痨病死去,她年纪轻轻的就守了寡,没有子女,独自一人,一守就是二三十年。杨家靠着财大气粗,为她申建了个“贞节牌坊”,成为全城有名的贞节烈女;可在我的记忆里,好像从未见过那牌坊是个什么模样。二姨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她终日满面冰霜、不苟言笑、性情古怪,这可能是由于她常年过着孤独的生活,大好的青春白白地为一块牌子而牺牲掉,以致造成孤僻的性格和寡欢的脾气。她对我这个小外甥不仅不亲近,反而见我就烦,甚至动则骂我“小猴七儿”,以致每次见到她,我就害怕,就往母亲背后藏。所以,我心目中的二姨母既不可亲、又不可近,从她身上找不到半点亲情的影子。我们住在二姨家的时间不长,那段时间母亲几乎每天跑来跑去地外出找熟人、托亲戚,为父亲打赢官司找门路、求解脱。那段时间,我随母亲曾经到西街李家老宅的二爷和三爷家走动。那是两所并列的灰砖瓦房,每所约有三五间,周围有围墙,中间隔着一道墙把两所房子分隔为两个独立的院子,二爷和三爷以及他们的后代就居住在那里,看上去是县城里的中等人家。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爷爷辈的家里串门,我亲眼看到过的宁河本家爷爷辈的情况,仅此而已,更多的事情就无从说起了。
(二)东街轶事
第二个住处在宁河县城东街,那是租住的一间小土坯房子,地处东街的东头、路北侧。那年我三四岁,父亲已经身陷囹圄,家庭全靠母亲一个人支撑,既要照顾我们哥仨生活,又要为父亲能够早日出来到处奔走。那房子的东头不远处有一条河,可能通往蓟运河吧?我说不清楚。记得那时母亲经常带哥哥出门,把我锁在家里,怕我自己出门掉到河水里出事。那条河确实不安全,我曾亲眼看到过,一个被河水淹死的小孩,被大人捞了起来,摆在岸边,一个妇女搂着尸体大声哭叫,引来周围人们的一片同情声。母亲外出有时也会带上我,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甘铸元大爹家,甘大爹是父亲的朋友,家道小康,在地面上估计是个有头脸的人物,他家的具体地址我说不清楚,但是记得那是一座独门独院的砖瓦房,院子不小,里面栽种了许多花草。母亲每次去都是为了父亲的事,求他设法把父亲早日解救出来。有时母亲一面与甘大爹说事,一面抹眼泪,甚至痛哭流涕,所以在我的心目中,去甘家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记得有一次母亲和哥哥一起出去,却把睡觉中的我独自锁在家里。当我醒来睁眼不见一个亲人时,恐惧地爬起来奔向屋门,可是门已经被从外面锁住,顿时令我六神无主,倍感恐惧,于是一面用力推门,一面大哭大叫,母亲不见了!哥哥也不见了!如何是好?不知过了多久,在我哭得已经没有力气的时候,他们终于回来了,总算结束了那恐怖的一幕。至今那一幕仍在脑海里留下模糊的影子。
我家的门外是县城的东街,斜对面有一处大宅院,大门总是关得紧紧的,显得门户森严,据说那是江苏省督军齐燮元的父亲齐茂林的宅子。按当时街面上的议论,齐燮元是宁河县出息的大人物。后来才知道,抗战时期此人当了汉奸,曾担任过伪华北临时政府的治安部总长,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枪毙于北平。关于他的事情,我们哥三个都听老宁河人讲过,还听说齐燮元小时曾与父亲在同一个私塾读过书。可是据后来我核对时间,齐的年龄比父亲大十四岁,不可能同时在一起读书,也许是同一个私塾先生教过的学生,用如今的话讲,仅仅是校友而已①。齐燮元年轻时到天津陆军学堂当学兵,即现在说的军校学员。据说学兵时期就参加过战斗,表现十分勇敢,毕业后当了军官,升迁很快,一直当到江浙督军、省长,二十年代已经是中国有名的大军阀,我曾在《民国演义》上,读到过有关他在众多军阀当中,左右逢源,迂回捭阖的记载,虽说演义难免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大体上应该是有根据的。他出息了,他在宁河的家人也随之有了名望,成为县城里的特大门。不过他父亲齐茂林并未离家随他生活,而是一直住在县城里。他家虽说宅深院大,但从院外却看不到豪华景象。他家的人与外人很少往来,终日大门紧闭,像是有意识地与世隔绝。只听邻居的大人们说起,他家院子里养了猴子、大鹅等动物,为他们看家守院,一旦有人进入,大鹅就会大叫着拧人,猴子更厉害,会把来人挠伤。听了这些传闻,我和哥哥总是绕路经过他家门前,不敢靠近。
在东街住的时间推算起来应该是1932年,那年夏天,县城东北面的大庙里(是魁星楼?还是文昌阁?),住进了不少的中国军队,天天在那里唱歌、上操。我和哥哥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这个消息,每天都去看热闹,大家围着看他们走步、喊操、刺杀、…。每当他们解散休息时,就会有几个士兵走到我们小孩子堆儿里逗大家,有时把我这样的幼儿抱起来,问东问西地逗着玩。他们一律灰色军装,头戴大沿帽,都很年轻、很活泼,看上去并不可怕,反而可亲,与后来在乡间见到的那些散兵游勇大相径庭。从时间上看,那些军人应该就是“9·18事变”后从东北退却到长城内冀东一带的东北军,或者是原来驻守在关里的东北军。从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看,正规的东北军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颇能战斗的军队,在“九·一八事变”中,如果没有蒋介石的“不准抵抗”军令限制,东北军是有可能能顶住日本关东军的入侵而避免东北沦陷的。“七七事变”后,东北军也为全民抗战而浴血奋战过,表明他们并不是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众。我的那段亲身感受,尽管属于小孩子的直觉,但是也说明那些正规的旧军队并不像某些文字写的那样,一律是草包、匪军。他们训练严格、纪律严明,在驻防中,不扰民、不欺民,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很坏的印象。我是他们之后的中国军人,尽管党派不同,但是我认为有必要为前辈的一些军人正名:我们中国军人历来大多数都是好的,并不是不堪一击的豆腐渣,如果说历史上曾经出过不堪一击的队伍的话,那是上层腐败或指挥失当造成的,应该属于上层官长的责任,因为世上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带不好兵的官长。
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战士颇能说明这个问题,昨天还是枪响就跑的国民党兵,今天被我们解放过来,上了战场马上就变成勇敢的战士。这个现象怎样解释?只能说队伍的性质变了,上层指挥不同了,因而同一个战士的表现也就变了。我们这一代由共产党、老八路带出来的学生兵,原本是些很少接近群众的书生,但是在老八路的教育下,很快就变成以人民为父母、待群众如家人的八路接班人。我们热爱老百姓,老百姓也信任我们,他们遇到困难总是首先想到找解放军,军人成为社会上最受信赖的群体、最可爱的人。什么原因?只能说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英明,组织领导有方,难道还会有其他别的解释吗!
(三)姥家——岭头
我家住过的第三处是岭头村,时间是1932年的秋天至1933年的秋天、在我四五岁之间,那里是母亲娘家,有三个舅舅居住在那里。我们搬到岭头的原因很清楚,就是没有经济来源,在县城里住不下去了。岭头是个地道的农村,村子有两条街——东街和西街,两街之间隔着个大壕沟,没有水,在壕沟的东侧有座小庙和一家铁匠炉。我的二舅叫王章,是个教书先生,住在西街路北;三舅叫王衡,是农民;老舅叫王柏,也是农民。他俩家在西街路南,住对面屋,两家分别有一头驴和马,用土改政策看,估计是个上中农吧!二舅家我从来没去过,只见过二舅一两次面,他是个瘦高、弯腰驼背、头顶帽头、戴副老花镜的老夫子,至于二舅上头是舅舅还是姨我就说不清了。刚到岭头时,我们住在三舅家里,家中有舅母、表兄和表嫂等,人口不少,我们四口突然到来使他家难于应对。所以不久我们就在东街的西头租借了一间草房,迁往那里自己起火,靠舅舅们的帮助维持生活。其实由于当时时局混乱,而且时旱时涝年景不好,舅舅们的日子也很艰难,没有多大的力量帮助我们,以致我家不时断炊,生活无着。记得入秋之后,哥哥多次带我到高粮地里,拾捡掉在地上的粮穗,以弥补粮食的不足。捡回粮穗之后,母亲便用木棍打掉带壳的米粒,再放到破缸里舂掉一些壳子,便成为我们的食粮。那年的春节我们是在岭头度过的,临近春节时,平日几乎很少有人走动的东西两条街,立刻热闹起来,外乡的小商贩纷纷集聚到街上,卖鞭炮的、卖对联的、卖各种年货的摊子摆在街道两旁。入夜,唱乐亭影的小戏班子在大车上支起屏幕、搭成戏台,点上汽灯,临街演唱起来,吸引许多村民围观,好不热闹。这一切都使得平日死气沉沉的农村,焕发出一缕生机,我们哥三个也因此而兴奋起来,融入迎接春节的欢乐海洋之中。我和二哥看到别家孩子手提灯笼玩耍时,我们便缠着母亲也要买一个,可是她哪里有钱买这种奢侈品呢!但是为了让我们过上一个快乐的节日,她想方设法地拣到一只上了锈的小铁盒子,剪掉周围大部的铁皮,然后用一块红纸剪成纸花贴在盒子的周围,里面点上一只别人送给的小蜡烛,灯笼便做成了。我和二哥提着它欢天喜地地度过了那贫困寒酸的除夕夜,这是母亲的剪纸作品第一次在我记忆里留下的印象。后来我们定居长春时,每到春节临近时,母亲总要用红纸剪一些娃娃、鲤鱼、公鸡、花朵等为主题的剪纸,张贴在窗玻璃上和门上,邻里都夸她手巧。由她亲手糊制的贴满剪纸的笸箩,一直保留到她离开人世后的五十年代中期,才从家中消失。至今回想起七十年前的剪纸灯笼的往事时,还从心里佩服母亲那精湛的剪纸技艺和乐观的心绪。如果她在解放后多活几年,一定会为点缀新社会而创制出许多剪纸艺术品的。
在岭头居住的第二年春天,我突然染上了小儿麻疹,终日高烧,满身斑点,难受得又哭又叫。那时的农村本来就缺医少药,境况窘迫的我家,就更谈不上求医抓药了。母亲焦急无奈地日夜抱着我在地上走来走去,总算挺了过来,我的高烧开始退了,身上和脸上的斑点也逐渐结成痂,一天天地好起来。按当地的民俗,小孩子得麻疹之后的结痂期,为了乞求子孙娘娘保佑,让孩子身上的斑痂早日脱落、不落“麻子”,应该买芝麻烧饼给病孩吃。母亲为了一个烧饼,走了几家烧饼铺,说了不少的好话,总算讨到一个已经干瘪了的烧饼给我。母亲为我不会生麻子而高兴,我则既想吃、又不舍得吃地啃尽了那个虽硬却香的干烧饼。岭头是个偏僻的北方农村,平时十分安宁,但是在三十年代初,由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导致国内北方混乱,这个村子经常成为散兵游勇袭扰的对象。当时村民把那些散兵叫做“大兵”,把逃避他们袭扰叫做“逃反”,在我的记忆里,那段日子,我家曾经几次随村民一起“逃反”,有时是白天,有时是夜晚,还有一次是大雨中逃出村庄。逃避的地点大都是附近大户人家的坟茔地,叫做“坟圈子”。每次“逃反”的时间大都不长,在野外呆上一天半日,“大兵”过村后,村民便返回家园。但是也有一次是逃往另一个村庄,躲避了两三天,才得以回村。平时村民家家都为“逃反”提前做好了准备,把家中的细软坚壁在草垛、地下、假壁墙等不易被发现的地方,并准备好衣服、鞋子等随身用品以及大饼子、咸鱼干等应急食品。我家没有细软可藏,但是大饼子和咸鱼干还是有所准备的,记得母亲为我们哥三个做了分工:大哥负责拿几双鞋子,二哥提大饼子,我拿小包咸鱼干,当听到有人敲锣大喊“大兵来了!大兵来了!”时,我们立即拿上应急物品,随着邻里的人们,逃向村外躲避。那些“大兵”是些三三两两掉队或逃亡的士兵,他们没有组织约束,也没有供应保证,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拿到哪里,有的甚至骚扰妇女,对她们施以非礼。记得那年秋季,一次母亲带着我和哥哥逃到外村躲大兵时,曾经亲眼目睹散兵扰民的经过。一天夜间,外逃的女村民为了避免遭受大兵的袭扰,大家都集中在一家的炕上,母亲抱着我、与另两位年龄大的妇女坐在炕沿附近,年轻的则挤成一团藏身于她们的背后。为了避免受到骚扰,年轻人的脸都用锅底灰涂抹成黑白相间的道道,很像京剧的脸谱。地下摆着农家木柜和长条板凳,柜上点着一盏若明若暗的小油灯。半夜时分,突然窜进个大兵,他高高、瘦瘦的,二十左右,一身不整洁的军装,提支长枪。进了屋子,坐在长板凳上,一面高声喊:“拿钱来!”,一面用枪托猛击地面,用以加强他的语气。当时炕上的女人们大都把头部压得很低,尽量使自己的脸庞躲开他的视线,只有母亲抬着头,用乞求的口气央求说:“老总,我们都是逃难的,那里有钱呢!”,那人其实也看到了当场的情景,料到从那些衣着褴褛的女人身上搜不到钱,但是还不死心,回过身来打开背后的木柜翻腾起来,自然是一无所获。还算万幸,最后他匆匆地开门离去,连头都没回。尽管当时我还是个幼童,但是那场面发生的一切,至今仍像电视剧一样,印在脑海里,甚至连那大兵的东北辽宁口音(当然是我长大后对照识别出来的)都记得清清楚楚。从当时家乡民不聊生的混乱状况可以看出,“9·18事变”不仅使三千万东北民众沦落为亡国奴,也波及到华北大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中国老百姓,使他们不得安生。
(四)重返芦台
1933年父亲被放了出来,回到岭头,失业在家。还是家在关外的姑妈惦记着我们一家,她给父亲寄来笔路费,让他到关外——当时的伪满洲国寻求生路。于是父亲便带上大哥出了关,投奔家在长春——即伪满首都“新京”的姑妈家,并在长春孟家桥粮食交易所谋了个记帐员的角色,暂时安顿下来。父亲离开老家后,母亲带二哥和我也离开了岭头,重返我的出生地芦台,等待父亲的消息。迁到芦台时,母亲找到一份临时工作,任务是替某主人家看管房子。那个主人家的姓氏我不知道,但是听说很有来头,是满清聂军门的儿媳,让母亲看管的是她存储财宝文物的一间房子,我们就住在那个房间里。地址大约是中街西大桥附近,在一座临街四合院里,是西厢房。正房住着的是姓李的商人家,主人叫李子真;东厢房空闲着。
到了芦台我们的生活一时安定下来,但是替人看家的差事并不好干,因为主人不时地为我们带来不愉快的插曲。这位女主人个头小小的、瘦瘦的,穿一身清末民初的抿怀衣装,一双三寸金莲,走起路来一摇三晃,像是从坟墓爬出来的古代僵尸,那是个主子气十足、高傲刁钻的老太婆。她对存放在屋子里的一些箱箱柜柜是否完好,里面的东西是否被我们挪动过,总是放心不下,因此隔三差五便来查看一番。进屋的第一件事就是,急不可耐地让母亲给她拿便盆来,伺候她解小手。方便完毕她立即精神焕发,一面审视那些箱柜的外表以及里面的扳指、水烟袋、念珠一类古董,一面拉长了脸以主子的口吻责问母亲。不是说我们动了她的东西,就是指责母亲箱柜没有擦洗干净。总之,在我和哥哥幼小的心灵上,一次又一次地留下的是那老妖婆的狰狞面目,以及随母亲一起受辱而激起的愤懑心情。为了发泄这股气愤,我俩常常捉几条小虫来,把虫子当成那老太婆,用树枝反复地抽打,还念念有词地喊着:“打死你,老妖精!打死你,老妖精!”,直打到虫子变成一滩稀泥,才算略解我们心头之恨。
我家的具体住址已经说不清楚,如今对照芦台街道图,按图索骥式的判断,可能是在中街西头的路南,记得我和哥哥曾经沿着街道往东头走,越走越繁华,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卖吃的、卖穿的、文具店、药铺,…,路北还有一家戏院。还记得在我家东面不远的路北,有一座很气派的祠堂,临街是些牌坊、房子、石碑类的建筑,院子深处有个很高很大的半圆型土包,可能是座坟墓。至今也不知道那是为哪位大人物修建的,是杜家?聂家?还是于家?会不会就是聂军门的祠堂呢?到现在也说不清楚。1934年的春节我们是在芦台度过的,家乡的节日精彩纷呈,热闹非凡,到处焰火,满街高跷,店铺门前灯红彩绿,人们喜气洋洋。元宵节放焰火,据母亲说,每放一个焰火就能打出一出戏来,能够看到戏里主角的摸样。我年龄太小、不懂戏,所以尽管我曾经身临放焰火的现场,但只留下了五彩烟花的印象,却从来没看到过人物的形象。焰火出现人物这个事,至今我依然没有搞明白,要么是对母亲讲的话理解有误,要么是外行看不出门道的缘故,还有待向老家的焰花专家请教,以解开这毕生之谜。
1934年的春天,母亲觉得我跟二哥终日在家淘气不是办法,应该让我们上学读书了。正好我家的斜对面是一所小学校,母亲便把我俩送去入了学,同在一年级读书。学校的校长为我俩分别起了学名,哥哥叫其祥、我叫其龙,可是当我们把学名告诉母亲时,她连呼不可,她说:“宁有富命、不叫富名,你怎么能叫“其龙”呢!皇上是龙,你敢‘骑’皇上?那是犯天条的啊!”第二天她找到了校长,说了这个道理,校长便把我的“龙”字改成了“荣”字;把哥哥的“祥”字改为“强”字,满足了母亲的请求。从那以后,我们便有了其荣、其强的学名,哥哥终生未变,我则于1946年,为了改大年龄、逃避国民党征兵,不得不改名为其颖;不过家人还是一直叫我其荣,直到现在。
芦台那所学校的大概环境至今我还依稀记得,学校在大街的北面,临近小河的东岸,周围是灰色砖砌成的院墙,校门面临大街,院子里是三排呈Ⅱ字形排列的教学用房,一律是灰砖瓦房,共有十几间。教务室和我们班的教室临街,我们的老师是一位年轻人,瘦瘦的脸上带一幅近视镜,身穿大袍。他好像是新教师,对小孩子不太耐心,动辄发脾气。我当时六岁,未经过幼儿教育,懂事甚少,铅笔不会拿,毛笔更不会握,甚至无法习字;老师讲算术加法时我一窍不通,像个小傻子。于是我便成为全班最落后的一个,时不时地受到这位老师的体罚,不是打手板,就是挨藤棍,打得我嚎啕大哭。哥哥在班里当副班长,看到我那幅可怜像又是着急,又是无奈。值得庆幸的是,学校有一位十分有耐心的副校长,年近四十。他了解到我的幼稚情况之后,便常常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抱着我、手把手地教我握毛笔的方法,给我讲一加一是什么意思。他的态度和善,不厌其烦,好像是对自己家里的孩子,跟那位班主任的粗暴态度大相径庭。那所学校属于当时的洋学堂,按着当时政府指定的教科书上课。记得我们学的课本中有:大狗跳、小狗也跳,…;猴子玩火…等适合孩子们学习的生动内容。另外还有手工课,体育课、音乐课等,教学内容表明,当时的国民教育还是很注重学生的全面培养的,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颇为注重素质教育。我们一年级小学生就开始上手工课,大家用小小的手工刀,把五颜六色的手工纸切成均匀的小条条,再用不同颜色的纸条编织成彩色条纹、花草等多种图案,对开拓儿童的美感、观赏能力、动手能力、形象思维等都十分有利。学校也注重学生的身体发育,记得有一次学校为全校学生量体重,地点是学校的大门洞里,工具是旧式大秤下面吊了个大筐,学生坐在筐里,由两位校役抬起秤来,为学生量体重。用现在的眼光看,那样的测量方法有些好笑,可是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学校能够作到那种程度,确也难能可贵。
在那所学校只读了几个月的书,但是却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1988年在我阔别故乡半个多世纪之后,回到老家探视时,曾有意地探询了我最早的母校,听说那所小学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被彻底毁坏,现在于另一个地点新修了一所,叫芦台第三小学。
1934年,大约是9月,父亲寄来笔路费,让母亲带我们哥俩到长春。我和哥哥退了学,随母亲坐火车出关进了东北。从那以后,我们家五口人便一生定居在东北长春,那年我六周岁。到我动手写这篇回忆文章时,父母亲和两位哥哥都已客逝关外,从宁河到长春的全家五口人,仅剩下一个年近八旬的我了,正像孔老夫子说的那样:“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自然规律不可抗拒,我何时追随他们而去,只能听其自然了。
附注
注释:
①齐燮元(1879—1946)字抚万,直隶宁河(现属天津)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为直系军阀。曾任江苏督军、苏皖赣巡阅使等职。1924年与盘踞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混战获胜。同年因直系在第二次直奉交战失败,被北洋军阀政府免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投敌,成为汉奸。曾任华北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总署督办和华北绥靖军总司令等职,配合日军“扫荡”,残杀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后被捕,1946年被国民政府枪决于北平。
关于父亲与他同学一事,是我小的时候听大人们说的,是谁说过已经记不清,不过我一直不相信。原因是:1、父亲从来没有亲口提起过这件事,也很少谈论有关齐燮元的事情。2、父亲出生于1893年,而齐燮元却出生于1879年,年长于父亲14岁,从年龄差上看,他们不可能是同期同学。3、父亲的后半生事业不顺,求职无着,而当时齐燮元正值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如果他们是同学的话,只要他肯投靠齐的门下,求个一官半职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事。可是
父亲却从来没有提过这类事,而且与齐从无联系,可见他们之间并无什么交往。据我的推测,如果说他们在学习上有什么关联的话,也许是教过齐燮元的老先生,十多年后也教过父亲,也就是说,他们至多有可能是同师之徒。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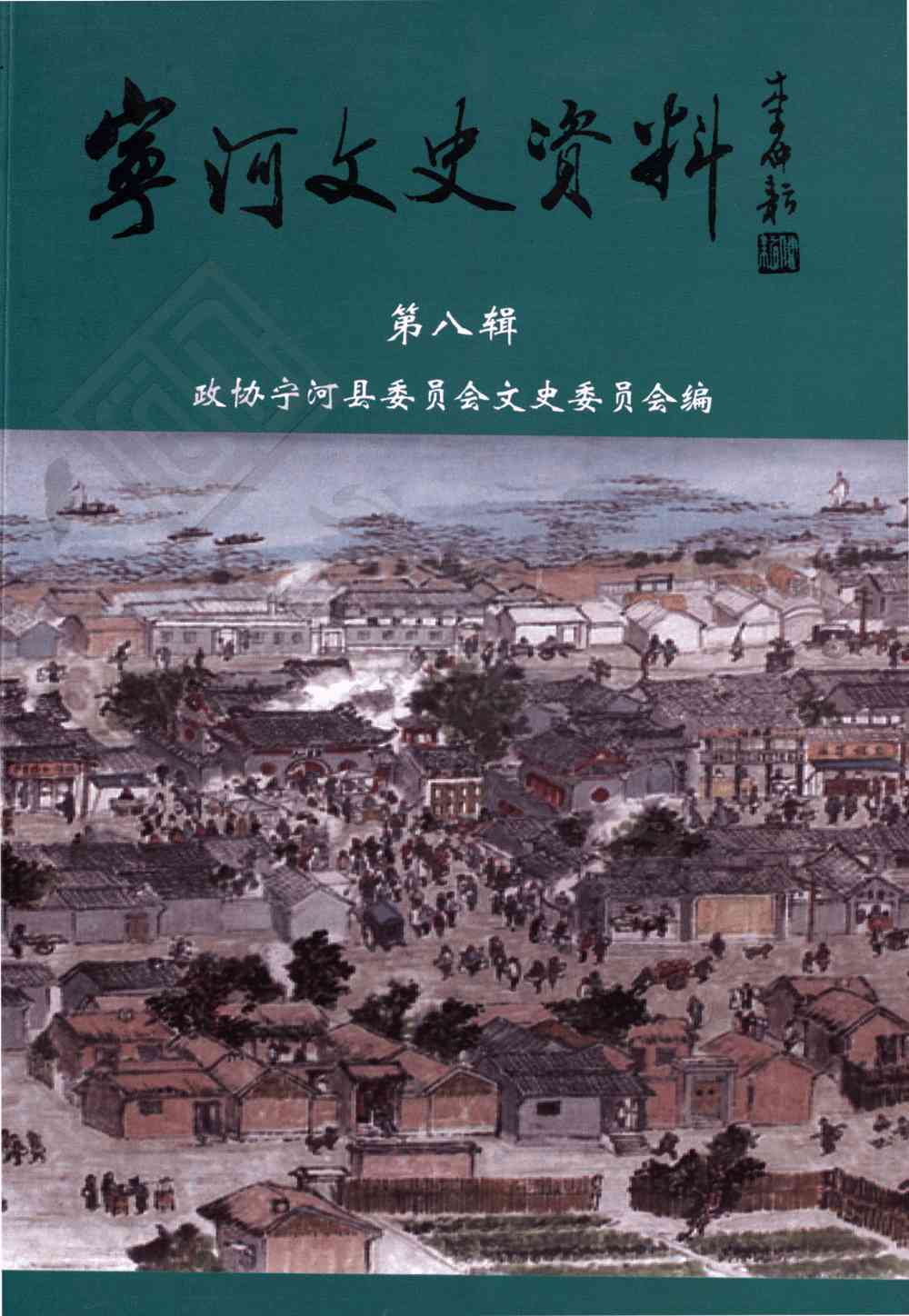
相关人物
李其颖
责任者
相关地名
宁河县现代产业园区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