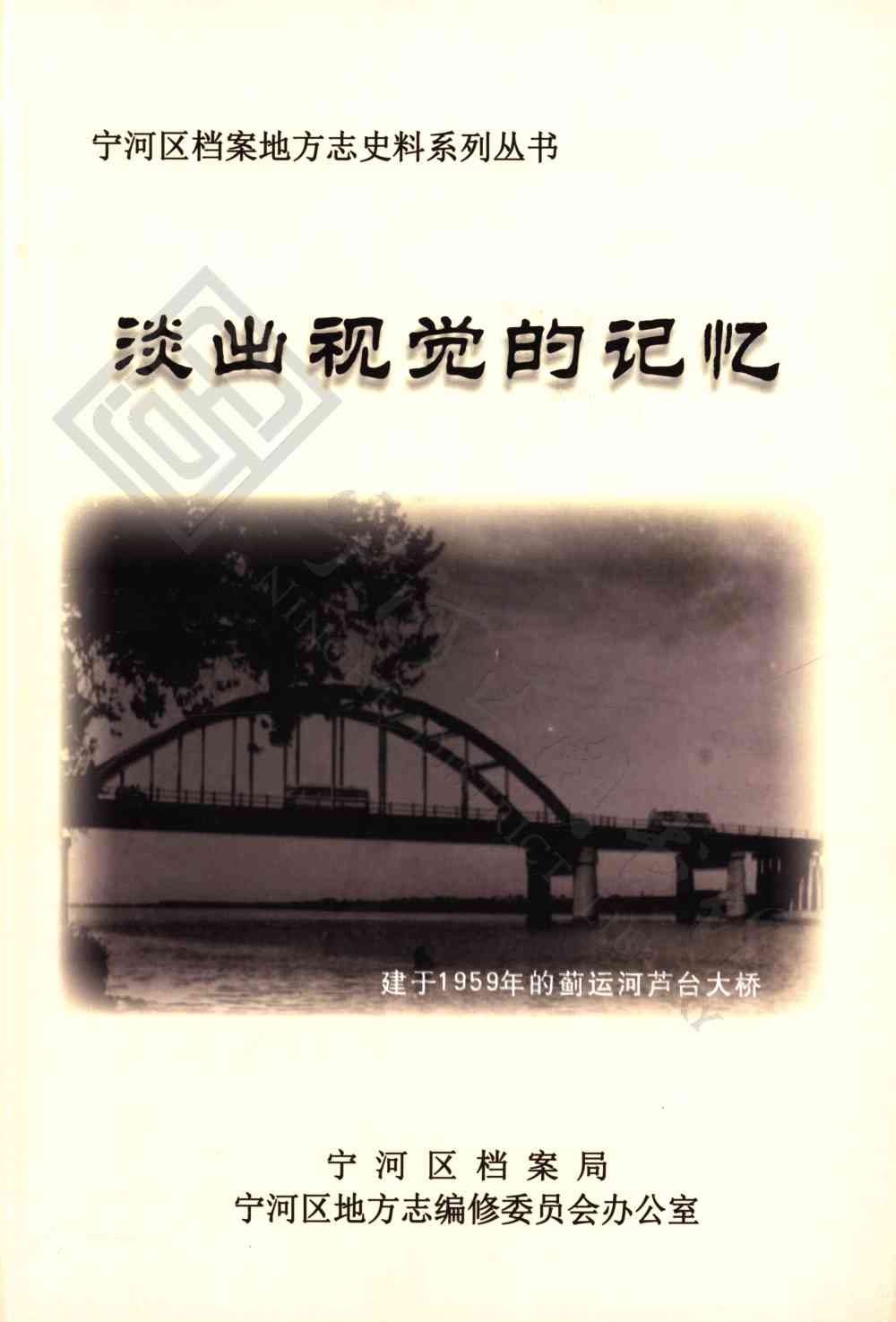内容
俗语说,“麦熟一晌,虎口夺粮”。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过麦秋的人,是很难体会这句话的真正含义的,更不会感受到虎口夺粮的那种紧张气氛的。因为现在都是机械收割,诸如拔麦子、晒麦、轧麦、扬场等过程都已经被机械化代替,直接颗粒归仓了。伴随着农民不知多少辈子的种麦和收麦的工具,也正在逐渐被人们淘汰,有的不但不为今人所知,甚至连老年人们也渐渐淡忘了。
种麦
记得小时候,常摇头晃脑地和小伙伴们唱这样一个歌谣:“王八一回头,碾子一转轴,今年发大水,明年好年头”。前两句有些令人费解,后两句却道出了经验之谈,即发过大水的农田,经过一秋的淹泡和一冬的冻化,洗了碱,粉了土,第二年是好种田的,特别是好种麦,而且会有好收成的。现在讲究种秋麦,产量高,但须肥水大,且由于根深,拔起来极费劲,只能用镰刀割,所以家家都要有磨刀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我们这一带的人们都种春麦,因为没有灌溉条件,基本上是听天由命,靠天吃饭。春麦要在立春以后的“七九”里种,即人们说的“七九麦”。“深谷浅麦,睁着眼儿的白菜”,“七九”时节正值春节期间,乍暖还寒,还没有完全解冻,用耠子在冻粉风化的土层上,浅浅地划出垄沟(因为底下还有冻层,不用多大力气,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人拉耠子),然后撒上麦种。撒麦种庄稼人口头语叫“点种”,是个技术活,一般都是队长指定的人来干,点种的人一般都是抱着个柳斗(或水斗子),里面盛着麦种,跟在耠子后面点种。抓麦种的手要扬过肩头,撒出去时,要靠食指将麦种掸开,让麦种均匀地落到垅沟里,远远望去,金黄的麦种,在阳光的照耀下,像一道靓丽的彩虹,煞是好看。撒完麦种后,要用木制的趟子趟平,边边沿沿没有趟到的,可用钉耙子搂平。过个三五天待冻土再融化一些,就可用绑了瓤子或草把的耠子,将垅背上的土豁起,形成厚厚的遮土,把籽种严严实实地覆盖,这样既防寒又透碱。待麦苗稍稍钻出遮土,远看青青近却无时,即可用趟子或钉耙子落土了。东风吹来满眼春,几天的功夫,广阔的麦田上就会展现一片喜人的翠绿。旋即,麦苗拔节抽穗,绿浪滚滚。麦熟时节,特别是人少地多的黄庄洼、东棘坨一带,一望无边的田野,到处是金色的麦浪,一派丰收景象。
拔麦
说“麦熟一晌”,是有道理的。早晨看麦子还是黄中带绿,只一个中午的日头暴晒,下午再看就蜡黄了,就可以收割了。蜡黄的时候收割最好,不但不掉粒,而且出面率也高,如果一旦麦子熟过了头,只要用力一攥,或装车时用力压挤,麦粒会自动爆落,损失就大了。
所谓“虎口夺粮”也绝不是耸人听闻。夏天天气多变,雷雨无常,一场飓风或一阵冰雹,可能会使一场眼瞅着到手的丰收灰飞烟灭,所以收麦犹如虎口夺粮,既令人兴奋又提心吊胆。
拔麦,是麦收的第一仗,也是男女老少收割忙的最壮观的场面。早晨是拔麦子最好的时机,天蒙蒙亮时,满田遍野已是人欢马乍。趁着凉爽,麦穗也经夜间的温洇锋芒收敛,攒足了力气的人们,争先恐后地拔着麦子,整个麦田弥漫着尘土的硝烟,像一缕缕缥缈的云雾,此起彼伏的哗哗拔麦声,像农夫们齐心合力弹奏的一曲曲妙不可言的丰收之歌。
在收麦的过程中,拔麦子是一项累活,因为不但要低头猫腰且几乎头点地,还要挥动双臂使出浑身的力气。有经验的人,会在手臂上缠一条毛巾用来擦汗,甚至套上手指套防止勒手而打血泡。拔麦是紧张的时刻,也是互相较量的时刻。数百亩麦田,平平坦坦,一望无边,毫无遮拦,谁快谁慢,一览无余。况且那是个显示谁英雄、谁怂蛋的节骨眼儿,用庄稼人的话,靶上看箭的时刻到啦!所以,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没有人肯甘心落后,特别是俊男靓女,早已跃跃欲试。生产队长一声令下,都玩了命般地拔麦,只见麦海金黄,人头攒动,尘土飞扬,壮观非凡。
记得那年,我们生产队挑选了20名青年小伙子去黄庄支援拔麦,因为我们这一带,祖祖辈辈一直大面积种植高粱,人们耪地的技术可谓娴熟。而黄庄一带麦田多,人家拔麦子的功夫可谓了得,简直叫人望尘莫及。尽管照顾我们的脸面,客主分开在麦田的两端各自拔麦,但一望无垠的麦田,没沟没堎没有遮掩物,谁快谁慢,显而易见。不大的功夫,黄庄的男人们就把我们超过去了,又一会,黄庄的青年妇女们也把我们超过去了,这下,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们都挂不住脸了。打头的哥哥小声问我,咱冲上去?!我那年刚参加生产队劳动,心里没跟,有些胆怯地问哥哥,行吗?哥说,不行也得试试,宁可累死也不能吓死!哥说着,就猫下腰,抡圆双臂,像箭一样窜了出去,身后腾起一溜烟尘。不一会,就超过了黄庄女人们,又一会,不但追上了黄庄男人们而且把他们也超了过去。这时,黄庄的男人们拔麦的行列里也冲出了一个人,与我的哥哥竞争起来。只看见茫茫麦海,看不见人,只有两溜白烟在向前。整个麦田都震惊了,人们都直起腰来,观看着,喝喊着。更有意思的是,一年后,黄庄那个青年妇女队长来我家相亲,一见是我哥哥,喜出望外,俩人的婚事立马就ok了,又一年后就成了我的嫂嫂。
拔麦是自由结组,三人一伍,领头的负责打腰(读药音,即负责打好捆麦子的腰子),最后一人要负责捆麦,中间的那个人往往是力量比较薄弱的,除负责自己拔麦,还要接应一下捆麦的人。拔麦的快慢,除看拔得快捷与否,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打腰。打腰最快的当属“狗抻腿”。即在紧张的拔麦中,用其中的一只手拧一小把长着的麦子飞快地就地打结,然后顺势拔起其中的一半,在地上铺开放麦,另一半还长在土里的麦子,则由捆麦人拔起用来捆麦。这样打腰的缺点是容易带土坷垃,所以不是较劲儿或竞赛的时候,一般不用,队长也不让用。打腰最慢的要数“王八大晒盖”了,即飞快地拔够一把,放在地上,从容打腰。也有“怀中抱月”的,即把麦子揽在怀抱中打腰。记得那时向老农们请教拔麦技巧时,他们绘声绘色的演示还有给打腰起的美妙名称,令我们目瞪口呆,惊叹不已。他们还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们绝招,如果你打头,而第二个人想超越你,在力量不相上下,速度基本相等的情况下,你可以一鼓作气,狂甩双臂,尽量把麦根的土猛猛地甩向身后,这个想超越你的人,会忍耐不住土坷垃抛头砸脸,十有八九要知难而退的。
拔麦时,要全身用力,特别是手要把麦子死死攥住,猛地拔起,手臂向后猛甩,把麦根的土甩掉,甩不掉的,在脚上狠磕一两下也就干干净净了。如果遇上干净的麦田,那是拔麦人的幸运,如果麦田长满芦草或棘棱狗子(一种带刺的野生植物)会使你的手勒得血泡棱棱或扎得鲜血淋淋,痛苦极了。
大人过麦秋,小孩也有活,那就是要随大人到麦田里去捡麦穗。记得我上小学时,生产队常常组织小学生去地里捡麦子,天蒙蒙亮就要出发,我们小朋友都愿意参加,不仅满田遍野人欢马乍,热闹非凡,更具诱惑的是太阳初升时,生产队的炊事员会赶着小毛驴车送来热气腾腾的雪白馒头和浓浓的绿豆汤(那时生产队蒸馒头的场景很吸人眼帘,盘上几个大锅灶,燃起熊熊柴火,一人来高的笼屉,蒸出来的馒头用大笸箩盛着)。其实,我们根本记不清能捡多少麦穗,但却深深记住了那热烈的劳动场面,感受了粒粒皆辛苦的教育和颗粒归仓的美德。
拉麦
拔下的麦子要用大马车运输,干燥、广阔的麦田哪里都是路,车把式站在高高的麦车上边吆喝牲畜边负责装车,两个跟车人用麦叉猛往车上挑麦,一马车会拉走很多麦子。躺满麦个子的麦田霎时就会空旷一大片。
拉麦子的大车要绑上架木,用绳子拦成网罩状,一则能拉得多,二来好装车。装好车后,要用绳子或钢丝缆绳把麦子勒紧,防止路上散落。勒麦子的绳子人们叫做煞绳,是很粗很长的麻绳,后来一般都用了钢丝缆绳。车把式喊声“打煞啦!”,跟车人就会从车头把煞绳抛向车尾,再把车尾别着麦子的绞锥拔出,插入煞车的吊梁里,用绞棍把煞绳勒紧。打煞时人们会把麦穗错开煞绳,以免勒煞到麦粒造成浪费。
人们把赶大车的叫车把式,那个年代车把式很吃香,就像刚有拖拉机、汽车时的司机一样,不是谁都可以干的,有顺口溜曾这样形容说“头等人,赶大车,小鞭一摇一块多”(指每天挣的补贴)。车把式很威风,红缨穗的鞭子一摇,随着一声洪亮的吆喝,马车就会在田野上奔驰起来,有的车把式不坐车,就手持短鞭,有的车把式坐在高高的麦车上,会手持大摇鞭驱赶着牲口。
垛麦
不要以为麦子到了场里就稳操胜算了。俗话说的很明确:“高粱到场,麦子到仓”才算收获,如果后期管理不好,遇上阴雨连绵照样会把麦子糟蹋在场里,即人们说的“烂场”。麦子进了场,如果不是遇到了恶劣天气,是不会马上垛垛的,而是要先铡麦头。场上早已准备好若干把铡刀,每把铡刀配上三四个人,掌铡刀和入刀的人都是队长挑选的细心人,否则容易把手指铡掉。铡麦时,将腰子以外的麦根去掉,保证腰子仍然紧紧地捆住麦头。这时,有人会将铡下的麦根迅速拉走到场外宽敞地方堆放,然后就开始垛麦了,先用一部分铡好的麦头朝上,堆成圆柱体的垛底,然后就可以把铡好的麦个子麦穗朝里码起来,到够一定高度时,再用麦头将麦穗朝外垒成尖锥形封顶,这样,即使下大雨,雨水也不会侵进麦垛,哪怕阴雨连绵也能抗一些时间。当然,一旦时间过长,队长会仔细检查,用手伸进麦垛试探,一旦麦垛里面发热烫手,会马上组织人倒垛,以防霉烂。
轧场
轧场比拔麦还要紧张,拔麦可在早晚,避免日晒,轧麦不行,太阳越火爆越好,所有人都要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干活。轧麦之前要先晒麦,把那些铡好的麦头在场上拆散摊开,在太阳底下暴晒,还要不停地用麦叉翻麦。老队长口头禅,“叉子尖上有火,越翻麦子干的越快”。大约到中午十二点左右,把麦子晒得用手一搓,麦粒哗哗爆出,队长会兴奋地把手中的麦子一扔大喊一声,轧场啦!准备好的轧场人员,就会像演马技一般闪亮登场,各自牵着戴好箍眼的马、骡等大牲口,套上二百左右斤的碌碡,在各自限定的范围内,开始轧场。那神气活现,催马扬鞭的情景,那马蹄踏踏,碌碡滚滚,麦穗哗哗爆响的场面,非常的激动人心,人人汗流浃背,但各个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就连赶来围观的孩子们也欢呼雀跃,因为他们也知道,轧完场即刻就会分粮,香喷喷的馒头、大饼马上就要到嘴啦!
轧完场,牲畜、碌碡都撤出场地,早已急不可耐的人们一涌而上,熟练地操起叉子(木制的三股叉、五股叉等)挑走麦滑秸(轧后的麦秸叫滑秸了)。然后,身强力壮的小伙们拉起大刮板或抄起小刮板,开始攒堆。扬场手们手持小簸箕,早已试好风向,站好位置,准备扬场。供梭手都是队长精心指定的棒小伙,因为扬场的速度快慢,在扬场手,更在供梭手。扬场手可以弯腰直腰,而供梭手只有手持木锨撅着屁股弯腰供梭,只有扬场人停下,供梭手才有片刻的喘息之机。但是没有人怕累,都巴望着早一点把麦子入仓为好。扬麦子要比扬高粱容易的多,皮轻、籽粒也轻,有一点儿风就能扬干净,甚至没有风,有经验的扬场手也能出手生风,把麦皮之类的杂物扬出。
场地的一边早已清扫干净,集合着叽叽喳喳等待分粮的家庭妇女和孩子。会计、保管的则在泵秤上早排上各家的手戳了(不用人去排队),家庭妇女眉开眼笑地拿着口袋在听着招呼等着分麦子呢。分了麦子互相帮忙运回家,一口袋麦子一百五十斤左右,有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干脆扛回家。生产队长则在张罗着将没有分的麦子入库,争取一天之内,麦光场净,哪怕有再大的风雨也美哉悠哉,无忧无虑了。轧场可以说是与拔麦同样紧张而又精彩的,人人争分夺秒,齐心协力,虎口夺粮。
精选的麦秸秆可以编帽子、编织扇子和工艺品,但大量的麦秸秆都做烧柴,或盖房时脱坯和泥房时的粘草。
麦收,不仅仅是收获麦子,更是寄托着穷人家的生存期望。因为麦熟以前,正是人们所说的青黄不接的时节,粮食不够吃的人家,自留地的麦子刚收浆时,就可以收下来来充饥,做成粘转转,非常好吃的。全年有无细粮,也在于麦秋有没有收获,过日子仔细的人家或粮食紧张的人家,还会用麦子去外村兑换些糙粮调剂来吃。记得小时候,麦黄时节,顽皮的我们在麦地里玩耍,捉“叫归”、捡鸟蛋时,常常将圆鼓鼓的麦穗扯下来,用火烧熟后搓粒吃,尽管因抹得满脸灰烬,嘴头黝黑遭到大人们的斥责,但沁心的麦香,六十多年后回忆起来还回味无穷。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的机械化成为了发展的趋势,旧时过麦秋的那种火热紧张的景况没有了,见证那个年代过麦秋所使用的工具也不多见甚至已经失传,但那些齐心协力、虎口夺粮过麦秋的热烈场面,融注了时代的印痕,走进了历史的记忆。
(李振起)
种麦
记得小时候,常摇头晃脑地和小伙伴们唱这样一个歌谣:“王八一回头,碾子一转轴,今年发大水,明年好年头”。前两句有些令人费解,后两句却道出了经验之谈,即发过大水的农田,经过一秋的淹泡和一冬的冻化,洗了碱,粉了土,第二年是好种田的,特别是好种麦,而且会有好收成的。现在讲究种秋麦,产量高,但须肥水大,且由于根深,拔起来极费劲,只能用镰刀割,所以家家都要有磨刀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我们这一带的人们都种春麦,因为没有灌溉条件,基本上是听天由命,靠天吃饭。春麦要在立春以后的“七九”里种,即人们说的“七九麦”。“深谷浅麦,睁着眼儿的白菜”,“七九”时节正值春节期间,乍暖还寒,还没有完全解冻,用耠子在冻粉风化的土层上,浅浅地划出垄沟(因为底下还有冻层,不用多大力气,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人拉耠子),然后撒上麦种。撒麦种庄稼人口头语叫“点种”,是个技术活,一般都是队长指定的人来干,点种的人一般都是抱着个柳斗(或水斗子),里面盛着麦种,跟在耠子后面点种。抓麦种的手要扬过肩头,撒出去时,要靠食指将麦种掸开,让麦种均匀地落到垅沟里,远远望去,金黄的麦种,在阳光的照耀下,像一道靓丽的彩虹,煞是好看。撒完麦种后,要用木制的趟子趟平,边边沿沿没有趟到的,可用钉耙子搂平。过个三五天待冻土再融化一些,就可用绑了瓤子或草把的耠子,将垅背上的土豁起,形成厚厚的遮土,把籽种严严实实地覆盖,这样既防寒又透碱。待麦苗稍稍钻出遮土,远看青青近却无时,即可用趟子或钉耙子落土了。东风吹来满眼春,几天的功夫,广阔的麦田上就会展现一片喜人的翠绿。旋即,麦苗拔节抽穗,绿浪滚滚。麦熟时节,特别是人少地多的黄庄洼、东棘坨一带,一望无边的田野,到处是金色的麦浪,一派丰收景象。
拔麦
说“麦熟一晌”,是有道理的。早晨看麦子还是黄中带绿,只一个中午的日头暴晒,下午再看就蜡黄了,就可以收割了。蜡黄的时候收割最好,不但不掉粒,而且出面率也高,如果一旦麦子熟过了头,只要用力一攥,或装车时用力压挤,麦粒会自动爆落,损失就大了。
所谓“虎口夺粮”也绝不是耸人听闻。夏天天气多变,雷雨无常,一场飓风或一阵冰雹,可能会使一场眼瞅着到手的丰收灰飞烟灭,所以收麦犹如虎口夺粮,既令人兴奋又提心吊胆。
拔麦,是麦收的第一仗,也是男女老少收割忙的最壮观的场面。早晨是拔麦子最好的时机,天蒙蒙亮时,满田遍野已是人欢马乍。趁着凉爽,麦穗也经夜间的温洇锋芒收敛,攒足了力气的人们,争先恐后地拔着麦子,整个麦田弥漫着尘土的硝烟,像一缕缕缥缈的云雾,此起彼伏的哗哗拔麦声,像农夫们齐心合力弹奏的一曲曲妙不可言的丰收之歌。
在收麦的过程中,拔麦子是一项累活,因为不但要低头猫腰且几乎头点地,还要挥动双臂使出浑身的力气。有经验的人,会在手臂上缠一条毛巾用来擦汗,甚至套上手指套防止勒手而打血泡。拔麦是紧张的时刻,也是互相较量的时刻。数百亩麦田,平平坦坦,一望无边,毫无遮拦,谁快谁慢,一览无余。况且那是个显示谁英雄、谁怂蛋的节骨眼儿,用庄稼人的话,靶上看箭的时刻到啦!所以,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没有人肯甘心落后,特别是俊男靓女,早已跃跃欲试。生产队长一声令下,都玩了命般地拔麦,只见麦海金黄,人头攒动,尘土飞扬,壮观非凡。
记得那年,我们生产队挑选了20名青年小伙子去黄庄支援拔麦,因为我们这一带,祖祖辈辈一直大面积种植高粱,人们耪地的技术可谓娴熟。而黄庄一带麦田多,人家拔麦子的功夫可谓了得,简直叫人望尘莫及。尽管照顾我们的脸面,客主分开在麦田的两端各自拔麦,但一望无垠的麦田,没沟没堎没有遮掩物,谁快谁慢,显而易见。不大的功夫,黄庄的男人们就把我们超过去了,又一会,黄庄的青年妇女们也把我们超过去了,这下,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们都挂不住脸了。打头的哥哥小声问我,咱冲上去?!我那年刚参加生产队劳动,心里没跟,有些胆怯地问哥哥,行吗?哥说,不行也得试试,宁可累死也不能吓死!哥说着,就猫下腰,抡圆双臂,像箭一样窜了出去,身后腾起一溜烟尘。不一会,就超过了黄庄女人们,又一会,不但追上了黄庄男人们而且把他们也超了过去。这时,黄庄的男人们拔麦的行列里也冲出了一个人,与我的哥哥竞争起来。只看见茫茫麦海,看不见人,只有两溜白烟在向前。整个麦田都震惊了,人们都直起腰来,观看着,喝喊着。更有意思的是,一年后,黄庄那个青年妇女队长来我家相亲,一见是我哥哥,喜出望外,俩人的婚事立马就ok了,又一年后就成了我的嫂嫂。
拔麦是自由结组,三人一伍,领头的负责打腰(读药音,即负责打好捆麦子的腰子),最后一人要负责捆麦,中间的那个人往往是力量比较薄弱的,除负责自己拔麦,还要接应一下捆麦的人。拔麦的快慢,除看拔得快捷与否,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打腰。打腰最快的当属“狗抻腿”。即在紧张的拔麦中,用其中的一只手拧一小把长着的麦子飞快地就地打结,然后顺势拔起其中的一半,在地上铺开放麦,另一半还长在土里的麦子,则由捆麦人拔起用来捆麦。这样打腰的缺点是容易带土坷垃,所以不是较劲儿或竞赛的时候,一般不用,队长也不让用。打腰最慢的要数“王八大晒盖”了,即飞快地拔够一把,放在地上,从容打腰。也有“怀中抱月”的,即把麦子揽在怀抱中打腰。记得那时向老农们请教拔麦技巧时,他们绘声绘色的演示还有给打腰起的美妙名称,令我们目瞪口呆,惊叹不已。他们还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们绝招,如果你打头,而第二个人想超越你,在力量不相上下,速度基本相等的情况下,你可以一鼓作气,狂甩双臂,尽量把麦根的土猛猛地甩向身后,这个想超越你的人,会忍耐不住土坷垃抛头砸脸,十有八九要知难而退的。
拔麦时,要全身用力,特别是手要把麦子死死攥住,猛地拔起,手臂向后猛甩,把麦根的土甩掉,甩不掉的,在脚上狠磕一两下也就干干净净了。如果遇上干净的麦田,那是拔麦人的幸运,如果麦田长满芦草或棘棱狗子(一种带刺的野生植物)会使你的手勒得血泡棱棱或扎得鲜血淋淋,痛苦极了。
大人过麦秋,小孩也有活,那就是要随大人到麦田里去捡麦穗。记得我上小学时,生产队常常组织小学生去地里捡麦子,天蒙蒙亮就要出发,我们小朋友都愿意参加,不仅满田遍野人欢马乍,热闹非凡,更具诱惑的是太阳初升时,生产队的炊事员会赶着小毛驴车送来热气腾腾的雪白馒头和浓浓的绿豆汤(那时生产队蒸馒头的场景很吸人眼帘,盘上几个大锅灶,燃起熊熊柴火,一人来高的笼屉,蒸出来的馒头用大笸箩盛着)。其实,我们根本记不清能捡多少麦穗,但却深深记住了那热烈的劳动场面,感受了粒粒皆辛苦的教育和颗粒归仓的美德。
拉麦
拔下的麦子要用大马车运输,干燥、广阔的麦田哪里都是路,车把式站在高高的麦车上边吆喝牲畜边负责装车,两个跟车人用麦叉猛往车上挑麦,一马车会拉走很多麦子。躺满麦个子的麦田霎时就会空旷一大片。
拉麦子的大车要绑上架木,用绳子拦成网罩状,一则能拉得多,二来好装车。装好车后,要用绳子或钢丝缆绳把麦子勒紧,防止路上散落。勒麦子的绳子人们叫做煞绳,是很粗很长的麻绳,后来一般都用了钢丝缆绳。车把式喊声“打煞啦!”,跟车人就会从车头把煞绳抛向车尾,再把车尾别着麦子的绞锥拔出,插入煞车的吊梁里,用绞棍把煞绳勒紧。打煞时人们会把麦穗错开煞绳,以免勒煞到麦粒造成浪费。
人们把赶大车的叫车把式,那个年代车把式很吃香,就像刚有拖拉机、汽车时的司机一样,不是谁都可以干的,有顺口溜曾这样形容说“头等人,赶大车,小鞭一摇一块多”(指每天挣的补贴)。车把式很威风,红缨穗的鞭子一摇,随着一声洪亮的吆喝,马车就会在田野上奔驰起来,有的车把式不坐车,就手持短鞭,有的车把式坐在高高的麦车上,会手持大摇鞭驱赶着牲口。
垛麦
不要以为麦子到了场里就稳操胜算了。俗话说的很明确:“高粱到场,麦子到仓”才算收获,如果后期管理不好,遇上阴雨连绵照样会把麦子糟蹋在场里,即人们说的“烂场”。麦子进了场,如果不是遇到了恶劣天气,是不会马上垛垛的,而是要先铡麦头。场上早已准备好若干把铡刀,每把铡刀配上三四个人,掌铡刀和入刀的人都是队长挑选的细心人,否则容易把手指铡掉。铡麦时,将腰子以外的麦根去掉,保证腰子仍然紧紧地捆住麦头。这时,有人会将铡下的麦根迅速拉走到场外宽敞地方堆放,然后就开始垛麦了,先用一部分铡好的麦头朝上,堆成圆柱体的垛底,然后就可以把铡好的麦个子麦穗朝里码起来,到够一定高度时,再用麦头将麦穗朝外垒成尖锥形封顶,这样,即使下大雨,雨水也不会侵进麦垛,哪怕阴雨连绵也能抗一些时间。当然,一旦时间过长,队长会仔细检查,用手伸进麦垛试探,一旦麦垛里面发热烫手,会马上组织人倒垛,以防霉烂。
轧场
轧场比拔麦还要紧张,拔麦可在早晚,避免日晒,轧麦不行,太阳越火爆越好,所有人都要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干活。轧麦之前要先晒麦,把那些铡好的麦头在场上拆散摊开,在太阳底下暴晒,还要不停地用麦叉翻麦。老队长口头禅,“叉子尖上有火,越翻麦子干的越快”。大约到中午十二点左右,把麦子晒得用手一搓,麦粒哗哗爆出,队长会兴奋地把手中的麦子一扔大喊一声,轧场啦!准备好的轧场人员,就会像演马技一般闪亮登场,各自牵着戴好箍眼的马、骡等大牲口,套上二百左右斤的碌碡,在各自限定的范围内,开始轧场。那神气活现,催马扬鞭的情景,那马蹄踏踏,碌碡滚滚,麦穗哗哗爆响的场面,非常的激动人心,人人汗流浃背,但各个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就连赶来围观的孩子们也欢呼雀跃,因为他们也知道,轧完场即刻就会分粮,香喷喷的馒头、大饼马上就要到嘴啦!
轧完场,牲畜、碌碡都撤出场地,早已急不可耐的人们一涌而上,熟练地操起叉子(木制的三股叉、五股叉等)挑走麦滑秸(轧后的麦秸叫滑秸了)。然后,身强力壮的小伙们拉起大刮板或抄起小刮板,开始攒堆。扬场手们手持小簸箕,早已试好风向,站好位置,准备扬场。供梭手都是队长精心指定的棒小伙,因为扬场的速度快慢,在扬场手,更在供梭手。扬场手可以弯腰直腰,而供梭手只有手持木锨撅着屁股弯腰供梭,只有扬场人停下,供梭手才有片刻的喘息之机。但是没有人怕累,都巴望着早一点把麦子入仓为好。扬麦子要比扬高粱容易的多,皮轻、籽粒也轻,有一点儿风就能扬干净,甚至没有风,有经验的扬场手也能出手生风,把麦皮之类的杂物扬出。
场地的一边早已清扫干净,集合着叽叽喳喳等待分粮的家庭妇女和孩子。会计、保管的则在泵秤上早排上各家的手戳了(不用人去排队),家庭妇女眉开眼笑地拿着口袋在听着招呼等着分麦子呢。分了麦子互相帮忙运回家,一口袋麦子一百五十斤左右,有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干脆扛回家。生产队长则在张罗着将没有分的麦子入库,争取一天之内,麦光场净,哪怕有再大的风雨也美哉悠哉,无忧无虑了。轧场可以说是与拔麦同样紧张而又精彩的,人人争分夺秒,齐心协力,虎口夺粮。
精选的麦秸秆可以编帽子、编织扇子和工艺品,但大量的麦秸秆都做烧柴,或盖房时脱坯和泥房时的粘草。
麦收,不仅仅是收获麦子,更是寄托着穷人家的生存期望。因为麦熟以前,正是人们所说的青黄不接的时节,粮食不够吃的人家,自留地的麦子刚收浆时,就可以收下来来充饥,做成粘转转,非常好吃的。全年有无细粮,也在于麦秋有没有收获,过日子仔细的人家或粮食紧张的人家,还会用麦子去外村兑换些糙粮调剂来吃。记得小时候,麦黄时节,顽皮的我们在麦地里玩耍,捉“叫归”、捡鸟蛋时,常常将圆鼓鼓的麦穗扯下来,用火烧熟后搓粒吃,尽管因抹得满脸灰烬,嘴头黝黑遭到大人们的斥责,但沁心的麦香,六十多年后回忆起来还回味无穷。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的机械化成为了发展的趋势,旧时过麦秋的那种火热紧张的景况没有了,见证那个年代过麦秋所使用的工具也不多见甚至已经失传,但那些齐心协力、虎口夺粮过麦秋的热烈场面,融注了时代的印痕,走进了历史的记忆。
(李振起)
相关人物
李振起
责任者
相关地名
宁河区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