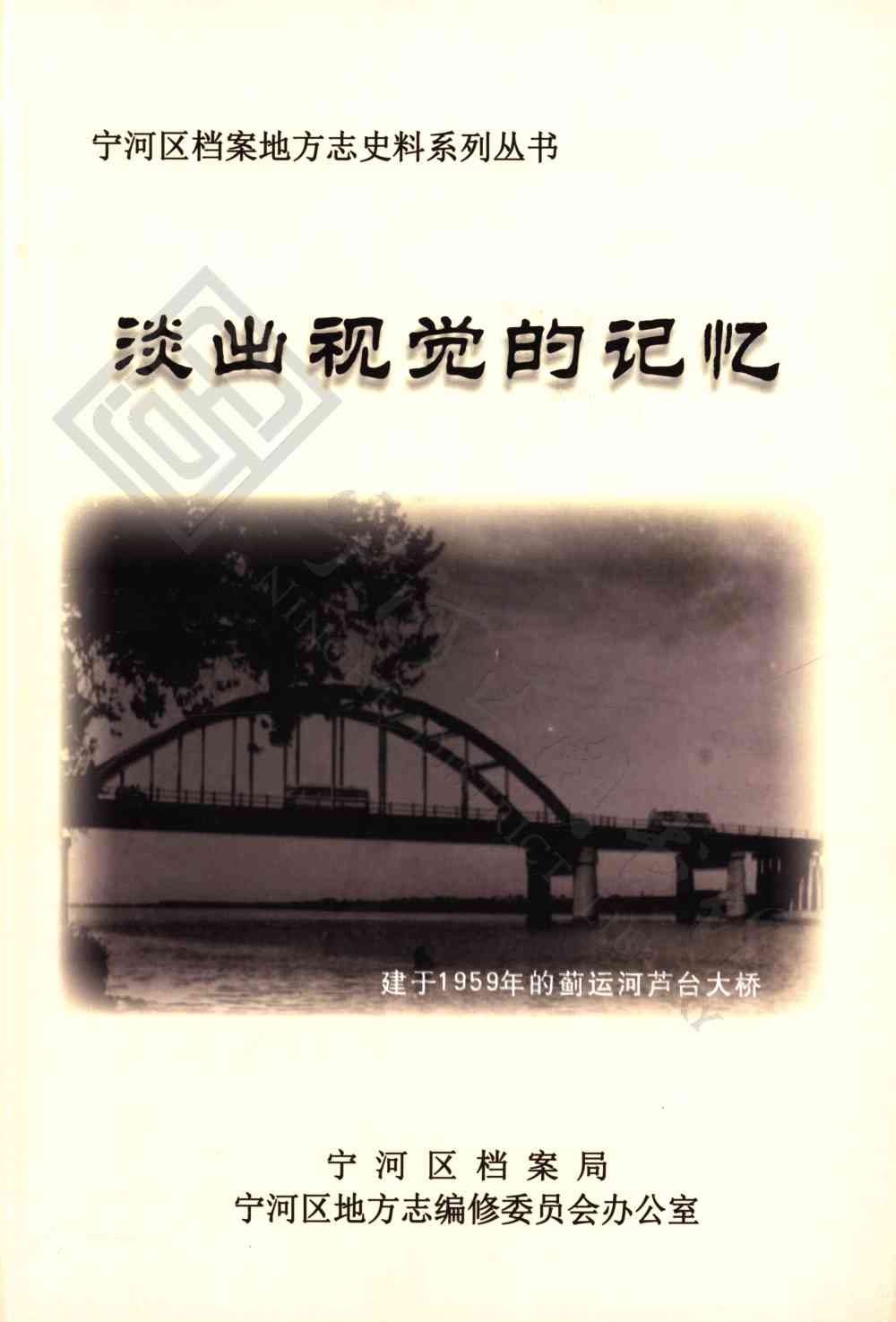碾米磨面话今昔
| 内容出处: | 《淡出视觉的记忆》 图书 |
| 唯一号: | 021920020230001929 |
| 颗粒名称: | 碾米磨面话今昔 |
| 分类号: | K875.2 |
| 页数: | 11 |
| 页码: | 62-72 |
| 摘要: | 本文讲述了碾米磨面的碾子和石磨,六十岁以上的农村人,都会有真实感受和深刻记忆,甚至有一种亲切、自豪感。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在小的时候几乎都帮家里碾过米、磨过面、推过小磨子。“千里迢迢在眼前,石头重重不是山,雷声隆隆不下雨,雪花纷纷不觉寒”。这则出现在早期小学课本里的谜语,那时的小学生们能轻而易举地猜出是石磨,而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不但很难猜出,更是很少见到过碾米磨面的碾子和石磨,有的甚至只在《地雷战》《红旗谱》等影视片里见过石碾与石磨了。 |
| 关键词: | 碾米 磨面 宁河区 |
内容
说起碾米磨面的碾子和石磨,六十岁以上的农村人,都会有真实感受和深刻记忆,甚至有一种亲切、自豪感。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在小的时候几乎都帮家里碾过米、磨过面、推过小磨子。“千里迢迢在眼前,石头重重不是山,雷声隆隆不下雨,雪花纷纷不觉寒”。这则出现在早期小学课本里的谜语,那时的小学生们能轻而易举地猜出是石磨,而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不但很难猜出,更是很少见到过碾米磨面的碾子和石磨,有的甚至只在《地雷战》《红旗谱》等影视片里见过石碾与石磨了。
石磨
磨,最初叫硙(wèi),汉代才叫磨,相传是鲁班发明的。鲁班发现人们吃面,都是把谷或麦子等原粮放在石臼里,也像舂米那样用粗石棍来捣,既费时费力捣的又少,而且捣出的面粉有粗有细,面质也不好。于是鲁班就从山上找来了两块石头,将石头凿成了两块厚度相同的扁圆柱形的石片,制成了磨面的磨而被人们使用开来。
石磨分上、下两扇。上扇可动,下扇固定,两扇相对的一面留有一个空膛叫磨膛。磨膛的上下接触面都錾有排列整齐的磨齿,用以磨碎粮食和磨成的面粉流出。下扇中间装有一个很短的立轴,用铁箍制成,即人们所说的磨脐子,以防止上扇磨片在转动时从下扇上掉下来。上扇有两个磨眼(指大磨,小磨只有一个磨眼),供添漏准备粉碎的粮食用,这样,谷物就会通过磨眼流入磨膛,均匀地分布到磨膛四周而被粉碎。粮食被磨成粉末后,会从磨缝中流出到石制或木制的磨盘上。大磨的厚度一般在四至六寸之间,也有更厚的。长度一般直径六十厘米至一米,也有更大一些的,但一头毛驴根本拉不动,得要大骡子大马才能拉得动。各村常用的一般直径不到八十厘米,两个人推或一头毛驴就能拉动。至于小磨,一般直径也就是二十厘米左右,在上扇上凿两个眼,按上硬木的磨梁子,一个人磨起来很容易。
大磨一般是架在石头或砖、坯垒成的台子上,一个村里会有三五个不等,基本上由拥有的人家管理。磨面是个费时又费事的活儿,而且既怕风尘又怕雨雪,因此有磨必须要有磨棚,以备刮风下雨都能使用,所以有磨的人家都同时盖有磨棚。说它费时,即磨面起码要磨三遍,仔细的人家甚至磨四遍,一口袋麦子一般要磨上一天的时间。说它费事,即磨面要有很多工序,如为了多出面粉,干燥的麦子要适当沁润,有经验的会喷一点水,没有把握的可用湿毛巾把麦子擦拭一遍。麦子磨面要靠箩,笸箩、簸箕、面箩、箩床、面升子等家把式都要一应备齐。每磨一遍(通俗的说法每一遍叫一览儿),要用面箩箩一遍,就是说磨几遍就要箩几遍。面还有白面和黑面之分,第二遍(即第二览儿)的面最白,大多数人家要掐出最白的面逢年过节或来人来客,总之,磨面要比碾米复杂得多。而小磨子几乎家家都有,但不是用来磨白面的,因为它的分量太轻,不能把麦子粉得太细,出不来高质量的面粉的,一般都是用来粉碎的,如把高粱、玉米磨成渣子熬粥,把黄豆粉成半儿磨豆腐等等。可以把小磨子放在较大的笸箩里,在家炕头上就能使用,极方便农户人家的随时之需。
大磨一般靠畜力,小磨子则是靠人力了。为了减轻推小磨人的力量,人们发明了晃杆作为助推的工具。晃杆一长一短,固定在一个点上,插在小磨的磨梁前端的眼里,助推人可以随着主推人的速度,很有节奏地摇晃着助推。如磨豆浆、高粱米等,一人主推兼添料,一人摇晃杆,这样,本来很累人的活,会轻松很多,而且,晃杆的不一定是大人,小孩也可,这也是农村孩子们乐此不彼的活儿。也有不用晃杆的,直接在磨粱的眼上插一根擀面棍,助推的人一只手在主推人的手之上用力就行了。
碾子
碾子,也是用人力或畜力把谷物脱壳或碾成碎渣、面粉的石制工具,在我们这一带主要是用来碾高粱米的。碾子一般都很大,大的千斤以上,小的也有数百斤,几乎村村都有,但各家各户有的不多。石碾一般建在村的中央或方便大家使用的地方。碾子由碾台、碾盘、碾磙和碾架等组成。碾盘很大,也和石磨的底盘一样,架在用石头或砖坯垒成的台子上,碾盘中心有一竖轴,连着碾架,架中装碾磙子,碾架外端的延长木,可作为人推碾的手柄或绑套牲畜的拉杆,人们一般把它叫做碾棍。碾盘和碾磙上分别由石匠凿刻有规律的纹理,以增加碾制粮食时的摩擦力,加快碾轧的速度。
碾米相对磨面要轻松些,别看碾子大,但转起来比较省力,一般两个人就可以了,所以用牲畜力的不多。碾米时,两个人要齐心协力也各有分工,一个人在碾棍的外端双手用力推,另一个人则在靠近碾盘的碾棍处,一手用力推,另一只手拿笤帚不停地“圆”碾盘上的粮食(包括翻动粮食)。所谓“圆”,就是把碾得膨胀出来的粮食,扫回原处,保持均匀的圆圈形状,以保证碾碡的中间准确地碾在粮食上。
碾米,是一项技术性比较强的活。高粱铺在碾盘的厚度是有讲究的,铺的过厚,则推着费劲,不易碾透;铺的过薄,几圈下来,会把高粱碾成渣子甚至面粉了。
配套工具
随着人们对石碾石磨加工粮食的使用,相配套的工具也相继多了起来,如筛面的箩子、箩床、筛子、盛面的笸箩、簸箕、撮子等,都必不可少。那时,这些东西几乎家家都有,而现在,这些东西有的在米面加工厂还可以看到,在各家各户已经很少看到了。
这些用具有些破损时,许多人家舍不得花钱买新的,就靠自己修修补补,实在不行了,就花钱请专门的修理匠来修。磨也如此,用的年号久了,原来的磨纹磨平了也要重新錾,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杵磨”。这些用具的修理匠和杵磨的基本都不是本地人,修理笸箩、簸箕的大多是南方人,当地人管他们叫“南蛮子”,而杵磨、杵碾磙、碾盘的,大多是北方山里人,当地人喊他们为“老北”。记得小时候,每到农闲时节,那些南来北往的修理匠、杵磨的就会出现在东棘坨、七里海一带村庄,南腔北调的吆喝声,响遍大街小巷,各具特色。北方来的杵磨人,会用他们粗犷雄浑的嗓音高喊,“杵磨的来啊,杵磨的有,谁家杵磨啊,赶快出来瞅……”特别有趣的是那些南方修箩子、簸箕的修理匠,他们身上挂着一串似铜似铁的东西,走街串巷时上下甩动,产生很大的“哗啦、哗啦”的声响,并夸(kuǎ)声夸调、抑扬顿挫地喊着,“张麻—易箩哦—张麻易箩!”引得孩子们跟在后面嬉笑追逐。尽管那时我们还很小,听不太懂他们的话,但一听那个“哗啦、哗啦”的声音就知道是干啥的来了,有心的孩子会跑回家问问大人修不修笸箩簸箕的。如有凑巧,赶上摇着拨浪鼓的货郎、麻绳换泥人儿的、磨剪子抢菜刀的、锔盆锔碗锔大缸,手艺人都来游街穿巷……,此起彼伏的声音会使村庄显得无限情趣。时到今日,也还有很多老人对他们的呼喊声记忆犹新,不信可去问问他们,备不准老人们会饶有兴趣地学上几句“杵—磨—的来啊”或“张麻—易箩哦”,甚至高亢地来一段“磨剪子来啊,抢菜刀!”。
值得记忆和赞叹的是,如果杵磨或翻新、修理箩子、笸箩、簸箕时,一时手头短缺或根本没有钱也不要紧,可以欠着,那些杵磨的和修理匠很好说话,他们会很大度地告诉你可以明年再给,或再晚一年给也行。手艺人们大方大度,村民们看在心里,感动在心头,也就极守信用,没有讨价还价的,更没有赖账的,哪怕是经手的大人出了意外,家人也会记得还账。有的人家也会以管饭的方法兑换费用,总之,都非常的和谐,彰显了民风的淳朴,民心的纯洁。那些出卖手艺的人走到哪,吃到哪,住到哪,哪个村都会有人热情地收留他们,不用担心有坑蒙拐骗的事情发生。大概是感恩村民们的善待,那些手艺人从不与村民们计较费用的多少,而且活计干得非常的到位,与村民们混熟了,来年再来时,还会带些当地的土特产分散给乡亲们。记得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村里一些人家盖房,就是北方山里那些曾经来这里杵磨的人给联系着买的檩子、木料。
石磨和碾子的使用
那时的孩子们,读书识字的不多,但会推小磨子的不少,因为生活所需,几乎家家都有小磨子,以备随时磨米、磨面、磨熬粥的渣子。有的孩子是要给母亲搭帮手的,家长把一升高粱交给你,就下田干活去了,你不能光顾贪玩,赶到大人回家做饭时你得把交给你的粮食磨完,否则,挨顿呵斥是小事,惹得大人生气了,屁股蛋上没准会落上两巴掌。
我最喜欢的是晚上和母亲一起磨豆瓣,或摊煎饼的粮食,因为每一次都是一顿美食的诱惑。母亲会把粉碎好的豆瓣或摊饼的麦子、高粱米、绿豆等提前泡好,然后用小勺一勺一勺地连汤带豆瓣地往小磨眼里灌着,我只需双手握着磨拐和母亲一起磨就行了。第二天清晨,母亲会把磨得粗糙的豆浆掺在干菜里做成小豆腐,或摊出软软乎乎散发着诱人香味的煎饼,全家人都会吃得津津有味,也不知道为啥那么香,现在想起来还有点要流口水。也有犯怵的时候,那就是每年二月二的摊煎饼,也不知道那时候的人们为什么那么能吃,十几口的一家人,要提前泡好一俩大盆高粱米、麦子、黄豆、绿豆等,磨完这些粮食,累得腰和胳膊要疼上好几大。
大多数农村的碾子、石磨和水井一样,都是公用的。“官船漏、官马瘦、官客来了满街遛”的俗说,在民风淳朴的乡间是不灵的,乡亲们使用时都懂得珍惜和爱护。碾子和磨不好使了,会有人家自愿且毫不声张地花钱请人杵的,尽管那时杵一盘大磨或碾子虽然只花几角钱,但对穷人家来说也是一笔费用,花起来也真是挺困难的。因为那时,几角钱就能买不少油盐酱醋等生活日用品,供一家人吃上好些时日的。
在碾子和磨的使用方面,村民们都很有自觉性,极懂先来后到排着顺序,甚至互相谦让。许多村有用小笤帚或炊帚疙瘩占碾子的风俗,即如果谁家要用碾子,只须提前一天晚上或当天早晨,在碾盘上放上一把炊帚之类的东西,就表示了有人今天要用碾子了(因为碾子一般都放在村中央,没有人具体管理)。而使用大磨则不用放物件去占了,只需用户提前与主人家打个招呼或询问有无人排号就可以了,人们都会自觉地讲究公德,没有强行抢占或使用的现象。后来有人把俗语说的“一把笤帚占个碾子”,用来形容不称职的人把持着重要位置,其实是反其意而用之了。在那个年代,没有行政命令,没有红头文件,一把小小的笤帚不仅真的能发挥占碾子的作用,而能衡量出村民们遵守乡俗民约的自律品德,说来当令我们后人汗颜与深思的啊!
碾米磨面如果使用畜力,人们不但要给牲口戴上箍眼还要戴上箍嘴,因为牲口也不傻,没人看着也会磨洋工或罢工;有人看着时也会“偷馋把嘴”,抽冷子往磨盘或碾盘上吞一口粮食,令人猝不及防,有的还会拱撒许多,常常把老太太们心疼得大声呵斥或用手拍打牲口。
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讲究,人们都会自觉地默默遵守,如使完大磨要“留膛”,即不要把磨膛里的粮食扫干净,一是以防空磨摩擦易受损;二是你把磨膛扫净,后用者要吃亏,因为填满一个磨膛得用一升左右的粮食。还有,借用别人家的畜力,干完活后要给牲畜犒力,即给主人家的牲口留一些麦麸子或粮食以示犒劳……
大概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离我村十几里远的芦台农场西双庄、小堼村等有了电,村里安装了用电打米磨面的工具,大人们常常带着自家的孩子用小拉车载着粮食去加工,省工省时省事,很多人家就不再自己碾米磨面了。到七十年代初,我们村里也通了电,建起了米面加工厂,人们就彻底从比较繁重的碾米磨面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了。那些大的石蹍、石磨就少有人问津了,但作为比较灵活机动的小磨子和一些相应的工具还是被一些人,特别是老人们所使用、眷恋和保留了许多年后才渐渐消失了。
用石碾、石磨粉碎食粮的时代过去了,尽管碾子和石磨,碾磨掉了祖祖辈辈无尽的岁月,留下的也将是渐行渐远的记忆,但令人难忘的是,石碾石磨曾经忠诚无悔地研磨着一代又一代的农耕岁月,风雨无阻地陪伴着繁衍生息的农家生活。也正是由于石碾、石磨的使用,衍生了许多寓意隽永、幽默横生、脍炙人口的语言,如“懒牛拉碾——连吆喝带赶”“懒驴上磨——屎尿多”“磨棚的驴——听吆喝”“磨棚的磨——听驴的”“拉磨的驴子断了套——空转一遭”“光着屁股推磨——转着圈儿丢人”等等,至今为人们所喜闻乐用。
(李振起)
石磨
磨,最初叫硙(wèi),汉代才叫磨,相传是鲁班发明的。鲁班发现人们吃面,都是把谷或麦子等原粮放在石臼里,也像舂米那样用粗石棍来捣,既费时费力捣的又少,而且捣出的面粉有粗有细,面质也不好。于是鲁班就从山上找来了两块石头,将石头凿成了两块厚度相同的扁圆柱形的石片,制成了磨面的磨而被人们使用开来。
石磨分上、下两扇。上扇可动,下扇固定,两扇相对的一面留有一个空膛叫磨膛。磨膛的上下接触面都錾有排列整齐的磨齿,用以磨碎粮食和磨成的面粉流出。下扇中间装有一个很短的立轴,用铁箍制成,即人们所说的磨脐子,以防止上扇磨片在转动时从下扇上掉下来。上扇有两个磨眼(指大磨,小磨只有一个磨眼),供添漏准备粉碎的粮食用,这样,谷物就会通过磨眼流入磨膛,均匀地分布到磨膛四周而被粉碎。粮食被磨成粉末后,会从磨缝中流出到石制或木制的磨盘上。大磨的厚度一般在四至六寸之间,也有更厚的。长度一般直径六十厘米至一米,也有更大一些的,但一头毛驴根本拉不动,得要大骡子大马才能拉得动。各村常用的一般直径不到八十厘米,两个人推或一头毛驴就能拉动。至于小磨,一般直径也就是二十厘米左右,在上扇上凿两个眼,按上硬木的磨梁子,一个人磨起来很容易。
大磨一般是架在石头或砖、坯垒成的台子上,一个村里会有三五个不等,基本上由拥有的人家管理。磨面是个费时又费事的活儿,而且既怕风尘又怕雨雪,因此有磨必须要有磨棚,以备刮风下雨都能使用,所以有磨的人家都同时盖有磨棚。说它费时,即磨面起码要磨三遍,仔细的人家甚至磨四遍,一口袋麦子一般要磨上一天的时间。说它费事,即磨面要有很多工序,如为了多出面粉,干燥的麦子要适当沁润,有经验的会喷一点水,没有把握的可用湿毛巾把麦子擦拭一遍。麦子磨面要靠箩,笸箩、簸箕、面箩、箩床、面升子等家把式都要一应备齐。每磨一遍(通俗的说法每一遍叫一览儿),要用面箩箩一遍,就是说磨几遍就要箩几遍。面还有白面和黑面之分,第二遍(即第二览儿)的面最白,大多数人家要掐出最白的面逢年过节或来人来客,总之,磨面要比碾米复杂得多。而小磨子几乎家家都有,但不是用来磨白面的,因为它的分量太轻,不能把麦子粉得太细,出不来高质量的面粉的,一般都是用来粉碎的,如把高粱、玉米磨成渣子熬粥,把黄豆粉成半儿磨豆腐等等。可以把小磨子放在较大的笸箩里,在家炕头上就能使用,极方便农户人家的随时之需。
大磨一般靠畜力,小磨子则是靠人力了。为了减轻推小磨人的力量,人们发明了晃杆作为助推的工具。晃杆一长一短,固定在一个点上,插在小磨的磨梁前端的眼里,助推人可以随着主推人的速度,很有节奏地摇晃着助推。如磨豆浆、高粱米等,一人主推兼添料,一人摇晃杆,这样,本来很累人的活,会轻松很多,而且,晃杆的不一定是大人,小孩也可,这也是农村孩子们乐此不彼的活儿。也有不用晃杆的,直接在磨粱的眼上插一根擀面棍,助推的人一只手在主推人的手之上用力就行了。
碾子
碾子,也是用人力或畜力把谷物脱壳或碾成碎渣、面粉的石制工具,在我们这一带主要是用来碾高粱米的。碾子一般都很大,大的千斤以上,小的也有数百斤,几乎村村都有,但各家各户有的不多。石碾一般建在村的中央或方便大家使用的地方。碾子由碾台、碾盘、碾磙和碾架等组成。碾盘很大,也和石磨的底盘一样,架在用石头或砖坯垒成的台子上,碾盘中心有一竖轴,连着碾架,架中装碾磙子,碾架外端的延长木,可作为人推碾的手柄或绑套牲畜的拉杆,人们一般把它叫做碾棍。碾盘和碾磙上分别由石匠凿刻有规律的纹理,以增加碾制粮食时的摩擦力,加快碾轧的速度。
碾米相对磨面要轻松些,别看碾子大,但转起来比较省力,一般两个人就可以了,所以用牲畜力的不多。碾米时,两个人要齐心协力也各有分工,一个人在碾棍的外端双手用力推,另一个人则在靠近碾盘的碾棍处,一手用力推,另一只手拿笤帚不停地“圆”碾盘上的粮食(包括翻动粮食)。所谓“圆”,就是把碾得膨胀出来的粮食,扫回原处,保持均匀的圆圈形状,以保证碾碡的中间准确地碾在粮食上。
碾米,是一项技术性比较强的活。高粱铺在碾盘的厚度是有讲究的,铺的过厚,则推着费劲,不易碾透;铺的过薄,几圈下来,会把高粱碾成渣子甚至面粉了。
配套工具
随着人们对石碾石磨加工粮食的使用,相配套的工具也相继多了起来,如筛面的箩子、箩床、筛子、盛面的笸箩、簸箕、撮子等,都必不可少。那时,这些东西几乎家家都有,而现在,这些东西有的在米面加工厂还可以看到,在各家各户已经很少看到了。
这些用具有些破损时,许多人家舍不得花钱买新的,就靠自己修修补补,实在不行了,就花钱请专门的修理匠来修。磨也如此,用的年号久了,原来的磨纹磨平了也要重新錾,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杵磨”。这些用具的修理匠和杵磨的基本都不是本地人,修理笸箩、簸箕的大多是南方人,当地人管他们叫“南蛮子”,而杵磨、杵碾磙、碾盘的,大多是北方山里人,当地人喊他们为“老北”。记得小时候,每到农闲时节,那些南来北往的修理匠、杵磨的就会出现在东棘坨、七里海一带村庄,南腔北调的吆喝声,响遍大街小巷,各具特色。北方来的杵磨人,会用他们粗犷雄浑的嗓音高喊,“杵磨的来啊,杵磨的有,谁家杵磨啊,赶快出来瞅……”特别有趣的是那些南方修箩子、簸箕的修理匠,他们身上挂着一串似铜似铁的东西,走街串巷时上下甩动,产生很大的“哗啦、哗啦”的声响,并夸(kuǎ)声夸调、抑扬顿挫地喊着,“张麻—易箩哦—张麻易箩!”引得孩子们跟在后面嬉笑追逐。尽管那时我们还很小,听不太懂他们的话,但一听那个“哗啦、哗啦”的声音就知道是干啥的来了,有心的孩子会跑回家问问大人修不修笸箩簸箕的。如有凑巧,赶上摇着拨浪鼓的货郎、麻绳换泥人儿的、磨剪子抢菜刀的、锔盆锔碗锔大缸,手艺人都来游街穿巷……,此起彼伏的声音会使村庄显得无限情趣。时到今日,也还有很多老人对他们的呼喊声记忆犹新,不信可去问问他们,备不准老人们会饶有兴趣地学上几句“杵—磨—的来啊”或“张麻—易箩哦”,甚至高亢地来一段“磨剪子来啊,抢菜刀!”。
值得记忆和赞叹的是,如果杵磨或翻新、修理箩子、笸箩、簸箕时,一时手头短缺或根本没有钱也不要紧,可以欠着,那些杵磨的和修理匠很好说话,他们会很大度地告诉你可以明年再给,或再晚一年给也行。手艺人们大方大度,村民们看在心里,感动在心头,也就极守信用,没有讨价还价的,更没有赖账的,哪怕是经手的大人出了意外,家人也会记得还账。有的人家也会以管饭的方法兑换费用,总之,都非常的和谐,彰显了民风的淳朴,民心的纯洁。那些出卖手艺的人走到哪,吃到哪,住到哪,哪个村都会有人热情地收留他们,不用担心有坑蒙拐骗的事情发生。大概是感恩村民们的善待,那些手艺人从不与村民们计较费用的多少,而且活计干得非常的到位,与村民们混熟了,来年再来时,还会带些当地的土特产分散给乡亲们。记得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村里一些人家盖房,就是北方山里那些曾经来这里杵磨的人给联系着买的檩子、木料。
石磨和碾子的使用
那时的孩子们,读书识字的不多,但会推小磨子的不少,因为生活所需,几乎家家都有小磨子,以备随时磨米、磨面、磨熬粥的渣子。有的孩子是要给母亲搭帮手的,家长把一升高粱交给你,就下田干活去了,你不能光顾贪玩,赶到大人回家做饭时你得把交给你的粮食磨完,否则,挨顿呵斥是小事,惹得大人生气了,屁股蛋上没准会落上两巴掌。
我最喜欢的是晚上和母亲一起磨豆瓣,或摊煎饼的粮食,因为每一次都是一顿美食的诱惑。母亲会把粉碎好的豆瓣或摊饼的麦子、高粱米、绿豆等提前泡好,然后用小勺一勺一勺地连汤带豆瓣地往小磨眼里灌着,我只需双手握着磨拐和母亲一起磨就行了。第二天清晨,母亲会把磨得粗糙的豆浆掺在干菜里做成小豆腐,或摊出软软乎乎散发着诱人香味的煎饼,全家人都会吃得津津有味,也不知道为啥那么香,现在想起来还有点要流口水。也有犯怵的时候,那就是每年二月二的摊煎饼,也不知道那时候的人们为什么那么能吃,十几口的一家人,要提前泡好一俩大盆高粱米、麦子、黄豆、绿豆等,磨完这些粮食,累得腰和胳膊要疼上好几大。
大多数农村的碾子、石磨和水井一样,都是公用的。“官船漏、官马瘦、官客来了满街遛”的俗说,在民风淳朴的乡间是不灵的,乡亲们使用时都懂得珍惜和爱护。碾子和磨不好使了,会有人家自愿且毫不声张地花钱请人杵的,尽管那时杵一盘大磨或碾子虽然只花几角钱,但对穷人家来说也是一笔费用,花起来也真是挺困难的。因为那时,几角钱就能买不少油盐酱醋等生活日用品,供一家人吃上好些时日的。
在碾子和磨的使用方面,村民们都很有自觉性,极懂先来后到排着顺序,甚至互相谦让。许多村有用小笤帚或炊帚疙瘩占碾子的风俗,即如果谁家要用碾子,只须提前一天晚上或当天早晨,在碾盘上放上一把炊帚之类的东西,就表示了有人今天要用碾子了(因为碾子一般都放在村中央,没有人具体管理)。而使用大磨则不用放物件去占了,只需用户提前与主人家打个招呼或询问有无人排号就可以了,人们都会自觉地讲究公德,没有强行抢占或使用的现象。后来有人把俗语说的“一把笤帚占个碾子”,用来形容不称职的人把持着重要位置,其实是反其意而用之了。在那个年代,没有行政命令,没有红头文件,一把小小的笤帚不仅真的能发挥占碾子的作用,而能衡量出村民们遵守乡俗民约的自律品德,说来当令我们后人汗颜与深思的啊!
碾米磨面如果使用畜力,人们不但要给牲口戴上箍眼还要戴上箍嘴,因为牲口也不傻,没人看着也会磨洋工或罢工;有人看着时也会“偷馋把嘴”,抽冷子往磨盘或碾盘上吞一口粮食,令人猝不及防,有的还会拱撒许多,常常把老太太们心疼得大声呵斥或用手拍打牲口。
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讲究,人们都会自觉地默默遵守,如使完大磨要“留膛”,即不要把磨膛里的粮食扫干净,一是以防空磨摩擦易受损;二是你把磨膛扫净,后用者要吃亏,因为填满一个磨膛得用一升左右的粮食。还有,借用别人家的畜力,干完活后要给牲畜犒力,即给主人家的牲口留一些麦麸子或粮食以示犒劳……
大概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离我村十几里远的芦台农场西双庄、小堼村等有了电,村里安装了用电打米磨面的工具,大人们常常带着自家的孩子用小拉车载着粮食去加工,省工省时省事,很多人家就不再自己碾米磨面了。到七十年代初,我们村里也通了电,建起了米面加工厂,人们就彻底从比较繁重的碾米磨面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了。那些大的石蹍、石磨就少有人问津了,但作为比较灵活机动的小磨子和一些相应的工具还是被一些人,特别是老人们所使用、眷恋和保留了许多年后才渐渐消失了。
用石碾、石磨粉碎食粮的时代过去了,尽管碾子和石磨,碾磨掉了祖祖辈辈无尽的岁月,留下的也将是渐行渐远的记忆,但令人难忘的是,石碾石磨曾经忠诚无悔地研磨着一代又一代的农耕岁月,风雨无阻地陪伴着繁衍生息的农家生活。也正是由于石碾、石磨的使用,衍生了许多寓意隽永、幽默横生、脍炙人口的语言,如“懒牛拉碾——连吆喝带赶”“懒驴上磨——屎尿多”“磨棚的驴——听吆喝”“磨棚的磨——听驴的”“拉磨的驴子断了套——空转一遭”“光着屁股推磨——转着圈儿丢人”等等,至今为人们所喜闻乐用。
(李振起)
相关人物
李振起
责任者
相关地名
宁河区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