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大营的杨柳青人在阿克苏
| 内容出处: | 《西青文史第十一册》 图书 |
| 唯一号: | 020620020230006272 |
| 颗粒名称: | 赶大营的杨柳青人在阿克苏 |
| 分类号: | K292.1 |
| 页数: | 12 |
| 页码: | 42-53 |
| 摘要: | 本文讲述了王桂萍的父亲从杨柳青到阿克苏的经历,以及父亲对家乡的眷恋和最后的嘱托。父亲在阿克苏的金店工作,并和当地一户人家的女儿结婚。他们生育了五个孩子,但父母于1974年双双去世。父亲非常勤劳、聪明和友善,而且能够写一手漂亮的小楷毛笔字。文章中还提到了王桂萍对父母和家乡的思念,以及将家乡的土带回新疆的愿望。 |
| 关键词: | 阿克苏 赶大营 杨柳青人 |
内容
我是赶大营的杨柳青人的后代。小时候经常听父母给我们讲老家杨柳青的故事,因此,在我的记忆中深深刻下了“我是杨柳青人”的印记。由于我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离开了父母到外县工作,加之父母已经离开我31年了,当时的许多记忆已经有些模糊。比如父母在杨柳青时居住在何街何巷、爷爷奶奶姓氏名谁都不记得了。但是父亲临终时的嘱托却一直响在我的耳畔。那时,父亲紧紧拉着我的手、含着眼泪对我说:“孩子,我自打年青时离开杨柳青到了阿克苏,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回杨柳青去看看,看来这个愿望是实现不了了。你记住,以后你一定要替我了了这个心愿,回杨柳青老家去看看。一定要记住抓一把家乡的土带回新疆,带回阿克苏,撒在我的坟上,我在九泉也能闭上眼了。”后来,我和支边到阿克苏的天津小伙子结了婚,回到了令父母魂牵梦萦的天津,回到杨柳青。我在子牙河畔挖了一大包故乡的土带回了新疆,不但把它撒在父母的坟上,也撒在了故去的埋在了异土它乡的亲戚朋友的坟上,告慰了他们的思乡之情。
我的父亲王子滨
父亲讳子滨,字起渭,取意姜子牙垂钓渭水河遇文王而腾达,同时也寓意是世居子牙河畔的杨柳青人。父亲是独子,世居杨柳青镇,两岁时就没了爹。那时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满清朝庭正处于“庚子事变”前夜,风雨飘摇,百业俱废,民不聊生,孤儿寡母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我奶奶靠在子牙河上划船运货养活她的妈妈和儿子。天不佑人,父亲六岁(1902年)时我奶奶又因劳累过度而撒手人寰,孤苦无助的父亲只有和姥姥艰难度日。1915年,父亲19岁,姥姥也去世了。镇上的乡亲看到父亲孤苦无依实在可怜,动了恻隐之心,对父亲说:“孩子,听说你的亲舅舅在新疆伊犁。你和别人搭伴去伊犁找舅舅去吧。”虽说故土难离,但走投无路的父亲思前想后,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于是牙一咬,告别了家乡,踏上了漫漫的西去赶大营的无归之路。父亲历尽千辛万苦,一年之后到了伊犁,去商会一打听,舅舅已经不在伊犁,去了南疆阿克苏了。父亲茫然了。好在伊犁商会对来投亲无着的乡亲都积极扶持,父亲得以在杨柳青人家开的商铺里学徒。依照规矩,学徒只管吃住而没有薪水,但东家得知父亲要去南疆找舅舅时,便破例给父亲支了薪水,父亲才能够到阿克苏找到舅舅。要知道,从伊犁到阿克苏有三、四千里的路途哇。
阿克苏古称“姑墨国”,在现在的温宿境内。阿克苏是清朝时新疆设省后才设的“道”,俗称“汉城”或“新城”,而温宿则俗称“回城”或“老城”。温宿在阿克苏的北面,距阿克苏十余公里。温宿,维吾尔语,直译为“十个水”,意译应为“泉城”。因为温宿的城乡遍地俱是泉水潺潺,城中的一口“老龙泉”的泉水,不知流淌了几千年,滋养着全城的人们。我姥爷、姥姥去世后,几经磨难,父亲从阿克苏迁到温宿,我也是在温宿成长起来,并且从温宿随爱人调回天津的。父母也是长眠在温宿的土地上。那里寄托着我太多的乡情和思恋。。阿克苏,维吾尔语直译为“白水”,意译应为“清水”。温宿的再北面,就是巍峨的天山山脉。天山的冰雪夏季溶化后,沿着山坡潺潺流下,汇成小溪,又汇成大河奔流向南,灌溉着千万亩良田,最后注入塔里木河。由于新疆的河床多是鹅卵石为底,所以,河水清澈见底,鹅卵石历历可见。(所谓“戈壁”,是指由大小鹅卵石、粗沙砾混合而成的荒原;沙漠则全是金黄的细沙粒儿。河水常年的运动,卷走了较小的沙石,只剩下冲不动的大鹅卵石了。细沙的河床,由于沙子有过滤的功能,即使大水能使沉沙泛起,只要水势稍缓,河水立刻变清。)“汉城”中的居民大都为汉族人,而“回城”中的居民大都为维吾尔族人。杨柳青人绝大多数都在阿克苏生活。我父亲的舅舅,也就是我的舅爷爷也在阿克苏经商。父亲到了阿克苏,见到了舅舅,互相倾诉了离别之情和家庭状况后,舅舅就把父亲介绍到一家杨柳青人开的金店中供职。
金店东家姓徐,挺和善、挺本分的一个人。东家夫妻俩只有一个女儿,漂亮、贤惠、文静。后来,东家变成了我父亲的岳父,东家的女儿成了我的母亲。我见过父亲十几岁时的相片,留着一条大辫子,戴着帽翅,浓眉大眼,笔挺的鼻子,特英俊、特帅气。母亲长得也不俗,是“美人胚子”的那种女人,到去世,快八十的人了,背不驼腰不塌,没有一根白头发。夫妻俩相濡以沫,恩恩爱爱度过一生,生了我们兄妹五人。父母于1974年双双谢世,相隔仅仅半年。
父亲很勤劳,很勤奋,也很聪明。小时候由于家境贫寒,不能读书,基本上是目不识丁。到我长大成人,父亲已经能写一手漂亮的小楷毛笔字了。从父亲的讲述中我得知,这全是父亲刻苦自学的结果。父亲每天在铺子里向帐房先生问几个字,店铺上板儿后就在地上铺上沙子苦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积月累,父亲写信居然也能“之乎者也”了。解放以后公私合营时,父亲的店铺合并到食品公司,父亲凭着才识,当上了会计。
父亲待人很友善、很大度。直到现在,无论尚在的老年人还是和我般般大的人,不分民族,说起我父亲,都是一句话:王爷,没说的,大好人。父亲鉴于自己幼年的不幸,特别惜苦怜贫。无论贫富贵贱一视同仁。平常做生意,遇到有人有难处想要货又没钱,他就给人,什么钱不钱的,先拿走再说。今年还不了,明年;明年还不了,后年;实在还不起了,不要了。就这样,父亲结了不少善缘。父亲在维吾尔人中有很高的威信,无论是商务上还是家务中有了纠纷,他们最常说的就是,请王爷评理。父亲居中说合,双方俱都心悦诚服。父亲的诚心待人,乐善好施,使自己以后也受益匪浅。民国二十几年时,新疆大乱,叛军见店铺就抢。父亲这时正在“回城”(温宿)做生意,恐惧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正当一家人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一天半夜,忽然有人砸门,父亲战战兢兢地出去查看,原来是乡下的一个朋友,曾得到过父亲帮助。他是来接父亲到他家去避难的。父亲他们匆匆换上朋友拿来的民族服装,坐上驴车,到了乡下。朋友把父亲他们藏在地窖里,只有晚上才能出来活动活动。一直躲藏到事态平稳。
父亲在我姥爷的金铺当了店员,按照规矩,东家管吃管住,平时零花钱可以预支,年底发薪。当父亲第一次拿到薪水时,舅舅对父亲说,你平时也用不着钱,不如我给你攒着,到时给你娶房媳妇。亲娘舅说了,而且冠冕堂皇的,父亲就把钱交给了舅舅,而且一交就是六年。等到父亲和母亲要成亲时,舅舅却把头一摇,不认账了。我姥爷确实看上我父亲了,所以,情愿倒贴钱,将母亲嫁给了父亲。姥爷、姥姥去世后,金店由父亲继续打理,生意也还可以。平稳过了几年舒心日子,不想祸从天降。有一天忽然店里来了几个人,对父亲说是来盘铺子的,边说边拿出一张契约。父亲接过来一看,原来舅舅倒了买卖,无力还债,便把父亲的金店顶给了债主。那时节,父母不在了,亲娘舅就是天了。父亲无力、也无心与亲娘舅纠缠,眼睁睁看着债主将满店的金银宝石收罗而去。为了避免同住一城,让舅舅为难,父亲举家搬到了温宿,一直到去世。母亲去世前给了我一包东西,有珊瑚、翡翠、玛瑙、红宝石等等。算是父亲一辈子的事业的佐证吧。
搬到温宿以后,父亲无力再办大买卖,就开了个杂货铺维持生计。两间不太大的门脸儿,生活日用品应有尽有。我记得很清楚,一溜三间房,左边的门脸儿是日用百货;右边的门脸儿是食品日杂;中间是开堂门。进了院子一溜五间平房。中间是客厅,两边是卧房,东西厢房是库房和伙房。我小时候最喜欢去食品店里玩。里面花花绿绿摆满了苏联的食品:方糖、水果糖、冰糖、各种罐头和糖果匣子。我最喜欢冰糖了,一尺多长的冰糖上粘满了五颜六色的小辣子、小葫芦、小茄子、小西红柿形状的水果糖,十分可爱。我经常趁大人不注意溜进门去抠冰糖上的水果糖吃。日杂也多为苏联货,五金、洋布不用说了,瓷器、玻璃器皿也大多是苏联货。我家现在还有那时苏联出产的碗呐。苏联那时已经很讲究商品的外包装和产品质量,糖果的外包装全是用马口铁做的,做工十分考究。我家现在还保留着一个圆的糖罐,一个方的糖匣子。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点儿没变形、没锈蚀不说,印的图案、花纹都清晰可见。1950年我大哥参加减租反霸时,买了没收地主老财的一张苏造钢丝弹簧床送给父亲,50块大洋,不便宜。父母去世前又给了我。在地主家用了不知多少年,跟我们家就小半个世纪。1994年我调回天津将它送给朋友时,仍然不摇不晃结结实实。
解放以后,除了有一年推行苏联花布,动员男的穿花衬衣、女的穿“布拉吉”之外,苏联货几乎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水的国产货,其中不乏天津货。大到铁牛拖拉机、五一手表、飞鸽、红旗自行车、蜜蜂缝纫机,小到天津蓝天牙膏、火柴等等全是天津货。父亲这种小商人也随着公私合营的进程步入了社会主义的行列。一解放,军管会就把父亲带走审查,让父亲交代问题。父亲说:我19岁从杨柳青赶大营到新疆,一直在阿克苏、温宿经商做生意,跟官面儿上从不往来,有什么好交代的呢?听说你以前开金货铺,现在又开着杂货铺,住着这么大的房子,能说没问题?金货铺是我承受孩子他姥爷的,后来黄了。我现在的铺面房子是我每年五‘塔哈’(维吾尔语,麻袋之意)大米租金租的。经过多次审查,确实无懈可击,于是把六皮箱家庭财产没收后,定了个“城市贫民”的阶级成分。每当说起这段,父亲总要感谢自己的舅舅。要是一直开着金店,准得落个“资本家”的帽子戴。这就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阿克苏商会的会长姓王,也是杨柳青人,人称“王商总”。王商总挺受同行尊重,解放以后被军管会叫去审查,不知因为什么罪恶,后来枪毙了。“文革”后,他的子女多次要求平反、落实政策,但因为年代久远,事实湮灭,案底也找不到,最后仍是不了了之。公私合营后父亲在食品公司做会计,因为父亲为人厚道,处世谨慎,在其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有惊无险的平安度过,直到退休。
我在家中最小,上面有俩哥哥,俩姐姐。大哥参加工作一直在法院。后来在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做书记,于1996年去世。有三男二女。其中长子和次子在威海工作。大嫂子和三儿子及两个女儿仍生活在温宿。二哥在温宿政府林业局工作,现已退休。二哥有三男一女,均在温宿工作。大姐已经去世,有一男三女,大女儿在北京中央实验话剧院,其余都在阿克苏工作。二姐今年69岁,健在。二姐夫也是杨柳青人,是在阿克苏的杨柳青人中出名的“董家酱园”的后人。有两男一女,也在阿克苏工作。从我姥爷算起,我们家在阿克苏已经是第五代人了。他们同祖辈一样,为阿克苏的繁荣和发展贡献着力量。我的两个女儿也都随我们回到了天津,大学毕业后都有了满意的工作。为建设天津贡献着力量。
回天津后我多次去杨柳青,抱着一丝的希望去寻根、寻亲,但都因我知道的太少而无果而返。听父亲讲,杨柳青镇最早只有一家王姓一家徐姓,后来像大树分叉一样分成许多家,但老祖宗是一个,也不知是真是假。我姥爷哥们五个,姥爷行大。二姥爷年轻时就去世了,三姥爷四姥爷也在新疆,五姥爷留在杨柳青。我姥爷只有母亲一个女儿,三姥爷的儿子叫徐恩奎,四姥爷的儿子叫徐恩普,还有徐恩华。是按“恩”字排行的。我的表哥们是按“松”字排行的,如徐松元,徐松林,徐松静等。不知这一点线索对我寻亲有无帮助。
阿克苏的乡亲们
清末民初时,阿克苏城很小,东西和南北长度都不到一公里。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主要街道是通往四个城门的两条街,交汇处称为“大十字”,也是城中心。杨柳青人的店铺就集中东西大街西面的南北两侧,是城中心的黄金地段。
南面临街的门脸是王商总的天津糕点铺,前店后厂,很大的一个作坊,专门制作京津风味的糕点,如大小八件、核桃酥、萨其马、槽子糕等。当然是清真的,不但汉族人买,连维吾尔族人也买。因为维吾尔人逢年过节,日常请客,招待客人,糕点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生意很好。王商总被枪毙以前,糕点铺着了一场大火。关于这场大火,轰动了整个阿克苏,各种传言都有。最有鼻子有眼的是有人亲眼看见火起时,有一对童男童女从门里走出来,手里牵着一根红绳,红绳牵到哪火就烧到哪,根本就扑不灭。糕点铺彻底毁了,从此阿克苏再也没有京津风味糕点不说,就连稍微像样的饼干也没有。我爱人1964年支边到阿克苏后,想吃点心,买了些饼干,一咬,差点把牙崩掉。江米条是用面粉做的,也是梆硬。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由内地人带入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有了高级的中、西糕点,但是天津的大小八件却是再也不见了。
再往西包括糕点铺后面往南的一大片,就是董家酱园,也是前店后厂,以制作各种酱菜为主,也做酱油、醋。规模很大,作坊里腌制酱菜的大缸就有一千多口,雇了十七、八个工人日夜生产。不但供应阿克苏全城,还批发到附近各县,生意很红火。1953年,我二姐嫁到董家时我去看过,还在生产。董爷在解放后的第一年就因“动火”(脑溢血)而去世。董家酱园由其孀妇董二奶奶支撑着,她也算是女中豪杰,将酱园经营得有条有理,直到公私合营。董爷娶妻两房,前面的妻子生了四个儿子,董二奶奶是填房,生有两个儿子。六个儿子没有一个是子承父业。我二姐夫董光诚大排行是老五,是董二奶奶所生,解放前十几岁时就在专员公署供职,解放后留用,仍在行政公署。最后在行署民政局福利院院长位置上离休(因为新疆是在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的率领下起义,和平解放的,所以留职人员都按离休对待)。二姐夫的弟弟董光和,大学毕业以后在阿克苏道桥处工作,后来调到武汉。这一段记述算是添补了谢玉明老先生《赶大营》文章中关于“董家酱园”的一点缺失吧。
从天津糕点铺东头向南拐是一溜小商铺,卖些土产日杂、小吃饮食什么的,全是杨柳青人开的。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是于大爷的贴饽饽熬小鱼,还有周姥姥的松花蛋。于大爷的饭馆儿门外垒了一个大灶台,上面支着一口“八沿儿锅”,从老远的地方就能闻到熬鱼的香味。周奶奶的松花蛋,最早我是喜欢看它的花纹,还挺纳闷儿,为什么鸭蛋上能长花纹而鸡蛋上就不长呢?还有一家饭馆的厨师也是杨柳青人,大人们管他叫“一马勺”。我问父亲为什么这么叫他,父亲告诉我“一马勺”以前在一个饭庄掌勺,红案上的师傅是个河南人,总受“一马勺”气,一次河南师傅配菜少配了一种菜,“一马勺”大发雷霆。河南师傅被骂急了,拿了个马勺就给了他一马勺,头上因此就落下个马勺型的伤疤,因此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一马勺”。由此也可以看出无论在什么年代、什么地方,天津人爱给人起外号的诙谐性格是改变不了的。其外号起的贴切、形象程度也是无与伦比的。
徐家因为在阿克苏的人口众多而成为大户,与天津糕点铺隔街相对。我姥爷的金铺就在街的金角位置,一个典型的京津建筑风格的店铺。除了经营金银首饰、珠宝玉器外,还兼营金银收售、加工业务。我的大舅人称“徐老总”,是粮食交易行的老板,经营着很大的一个粮食交易市场。市场主要从事粮油交易,不收摊位费,买卖双方成交后由买家按购买数量交一定的佣金给主家。徐家哥们几个统住在一个三进的大院子里,门口有几棵白杨树。我小时候就已经很粗了,1994年我调回天津时专门去看了看,院子是在解放以后早就建成人民电影院了。粮食市场变成露天电影院,宅院建成室内电影院了。但那几棵树还在,一个人已经搂不过来了。随着父亲搬去温宿及三、四姥爷的去世,我的舅舅们也就分居另过了。随着时代的变迁,我的表哥们没有一个是子承父业,纷纷弃商从政、从工、从文了。后代子孙们渐渐融入主流社会,与解放后移居新疆的汉族人相对而言变成当地的“土著”了,至今已传至第六代了,主要聚集在阿克苏,散布到全疆各地,从事各种工作。
乡情乡俗
不管阿克苏离杨柳青遥遥万里,也不管离开杨柳青几十年、几百年,祖辈们把浓重的乡情乡俗顽强地保留下来并一辈一辈地传承下去。
首先在语言上保持着浓重的杨柳青声调,纯粹的天津土话。我的平辈中比我年长十几、二十岁的,只要一开口说话,就是纯正的杨柳青音调。到我这里情况有些变化,在家时要严格地说杨柳青话,不然父亲要骂的;在学校要说当地话,不然同学要起哄笑话的。比如说“干什么”,当地说“干啥”,我在家说“干嘛”。如果一时忘记了场合而用岔了词,遭到的不是训斥就是哄笑。所以我说话的声调,一半是杨柳青的,一半是阿克苏的。回天津后又加上一点天津市里的,真的是“三不管”、“四不像”了。至于土话,不但我懂现在天津说的,而且我还懂现在天津不说的。比如“各闹”。什么意思?垃圾。天津叫“脏土”。倒垃圾,天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叫倒脏土,现在叫倒垃圾,而我们家一直叫“倒圪淖”。我母亲有一个装炒菜油的搪瓷罐,母亲管它叫“闷罐儿”,我现在还用着。至于像“棉靴头”、“关饷”、“靴掖子”等等这些土话,在天津是早以作古了,在阿克苏,不但我懂,下一代懂,而且就连常和我玩的朋友们也懂。
其次,是保留着杨柳青的风俗习惯。阿克苏的汉族人很多,各省人都有,但是过年时一定要蒸馒头、炖肉、吃饺子、贴对联、贴年画、放鞭炮的惟有杨柳青人。母亲每年过年时都要贴年画,而且一定是杨柳青年画。有传统的“连年有余”、“老鼠娶亲”,还有“四扇儿”,都是托人从乌鲁木齐甚至从杨柳青带来的,很不容易,所以一次要带好多。到“文革”时还有不少,“破四旧”一把火都烧了。现在想起来怪可惜的,那可都是老版的杨柳青年画啊。父亲常和我讲画中的戏曲故事。最常讲的是“二十四孝”的故事,什么“卧冰求鲤”、“老莱子彩衣娱亲”等。父亲还经常给我讲他小时候在杨柳青时的故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念的他们那时的一首童谣:“切登切,切登切,娘儿们穿的爷们儿鞋”。父亲说,可不是么,没两年,皇上下旨,妇女放脚,禁缠足。现在女的男的不是穿一样的鞋了吗。
那时我最高兴的就是过年了。不但有好东西吃,还有新衣服穿。我常因试穿新衣服不肯脱下来而遭母亲的呵斥,几乎年年如此。对襟棉袄、疙瘩袢扣的,挽腰的棉裤,梳两条小辫,戴一朵绒花。小闺女家,能不高兴吗。父亲管炖肉,母亲管蒸馒头。肉一炖一大盆,吃时挖几勺肉烩上白菜粉条。馒头一蒸一缸,放在院子里。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包饺子、守岁、听父亲讲在杨柳青过年时踩高翘、跑旱船、耍狮子的事。阿克苏也有高跷会,全是杨柳青人家的年青人组成的。我二姐夫董光诚,我二姐、我大嫂他们都在高跷会里。大年初一高跷会是一定要上街的,几乎全城的人都去看,不论民族。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初一早上天还不亮母亲就把我叫起来,穿戴好了以后,坐“六根棍”马车由温宿到阿克苏去拜年。
所谓“六根棍”是指车轱辘而言。那时阿克苏还没有胶皮轱辘马车,全是木轱辘马车,每个轱辘有六根木棍做辐条,车轮直径约1.5米。车走得很慢且颠簸,12公里的路要走两个小时以上。在街上熟人碰上都互相作揖,口称“发财”。到姥爷舅舅家拜年,我是要磕头的。当然也要给压岁钱。
我记得小时候母亲常领我去李二娘家串门。李二娘家有一间屋是从不让外人进入的。我出于好奇,曾捅开窗户纸偷偷看过,里面八仙桌上供着一只彩绘的泥娃娃,烧着香,还有一碗饭,一双筷子。饭是每顿都要换的。我好奇地问母亲那是什么,母亲告诉我,李二娘结婚几年没有孩子,有一年特地回天津,到“娘娘宫”拴了个娃娃回来,叫“大阿哥”。本来年年要拴一个更大的,因为离天津太远了,只好一直供着这一个“大阿哥”。后来李二娘子孙满堂,便对“大阿哥”敬重有加,一直供奉着了。我听了对“娘娘”也是崇拜不已。听父亲讲,“娘娘宫”又叫“天后宫”,供奉天后娘娘,又叫“妈祖”庙。“妈祖”是保佑渔人出海平安的,也是镇海的。妈祖神像的座下就是海眼,贴近神像仔细倾听,可以听见大海的波涛汹涌声,挪开神像可以看见翻滚的波涛。一个娘娘有如此的神通,我对娘娘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1974年,我第一次回到天津后专门去参拜了天后宫娘娘,瞻仰了我心仪以久的菩萨。
维吾尔人有自己的礼拜寺,回族人也有自己的清真寺,杨柳青人在阿克苏也有自己的同乡会,叫“公所”。进阿克苏北门右手即是,很大的院子里面有庙有议事厅有供人休息的客舍。我大姐大姐夫从乌鲁木齐搬到阿克苏,一时找不到房子,就住在公所的客舍里。每到初一、十五,人们便去烧香磕头求签扶乩。里面供奉的是什么菩萨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大人们围着一个沙盘念念有词,干什么我也不懂。只记得有一次大人们很激动,嚷嚷着,神仙发话了。我问父亲神仙说的嘛,父亲告诉我是“你问我,我问谁,除了宣统都是贼”。我再问是嘛意思,父亲摇摇头没说话。我记住了这句话,到底是什么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每次聚会,有婚丧嫁娶等大事就议一议,没大事就家不长里不短的聊一阵。我随大人去过几次,感觉很有意思。1957年,公所拆了,建成了阿克苏群艺馆。
我的父亲王子滨
父亲讳子滨,字起渭,取意姜子牙垂钓渭水河遇文王而腾达,同时也寓意是世居子牙河畔的杨柳青人。父亲是独子,世居杨柳青镇,两岁时就没了爹。那时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满清朝庭正处于“庚子事变”前夜,风雨飘摇,百业俱废,民不聊生,孤儿寡母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我奶奶靠在子牙河上划船运货养活她的妈妈和儿子。天不佑人,父亲六岁(1902年)时我奶奶又因劳累过度而撒手人寰,孤苦无助的父亲只有和姥姥艰难度日。1915年,父亲19岁,姥姥也去世了。镇上的乡亲看到父亲孤苦无依实在可怜,动了恻隐之心,对父亲说:“孩子,听说你的亲舅舅在新疆伊犁。你和别人搭伴去伊犁找舅舅去吧。”虽说故土难离,但走投无路的父亲思前想后,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于是牙一咬,告别了家乡,踏上了漫漫的西去赶大营的无归之路。父亲历尽千辛万苦,一年之后到了伊犁,去商会一打听,舅舅已经不在伊犁,去了南疆阿克苏了。父亲茫然了。好在伊犁商会对来投亲无着的乡亲都积极扶持,父亲得以在杨柳青人家开的商铺里学徒。依照规矩,学徒只管吃住而没有薪水,但东家得知父亲要去南疆找舅舅时,便破例给父亲支了薪水,父亲才能够到阿克苏找到舅舅。要知道,从伊犁到阿克苏有三、四千里的路途哇。
阿克苏古称“姑墨国”,在现在的温宿境内。阿克苏是清朝时新疆设省后才设的“道”,俗称“汉城”或“新城”,而温宿则俗称“回城”或“老城”。温宿在阿克苏的北面,距阿克苏十余公里。温宿,维吾尔语,直译为“十个水”,意译应为“泉城”。因为温宿的城乡遍地俱是泉水潺潺,城中的一口“老龙泉”的泉水,不知流淌了几千年,滋养着全城的人们。我姥爷、姥姥去世后,几经磨难,父亲从阿克苏迁到温宿,我也是在温宿成长起来,并且从温宿随爱人调回天津的。父母也是长眠在温宿的土地上。那里寄托着我太多的乡情和思恋。。阿克苏,维吾尔语直译为“白水”,意译应为“清水”。温宿的再北面,就是巍峨的天山山脉。天山的冰雪夏季溶化后,沿着山坡潺潺流下,汇成小溪,又汇成大河奔流向南,灌溉着千万亩良田,最后注入塔里木河。由于新疆的河床多是鹅卵石为底,所以,河水清澈见底,鹅卵石历历可见。(所谓“戈壁”,是指由大小鹅卵石、粗沙砾混合而成的荒原;沙漠则全是金黄的细沙粒儿。河水常年的运动,卷走了较小的沙石,只剩下冲不动的大鹅卵石了。细沙的河床,由于沙子有过滤的功能,即使大水能使沉沙泛起,只要水势稍缓,河水立刻变清。)“汉城”中的居民大都为汉族人,而“回城”中的居民大都为维吾尔族人。杨柳青人绝大多数都在阿克苏生活。我父亲的舅舅,也就是我的舅爷爷也在阿克苏经商。父亲到了阿克苏,见到了舅舅,互相倾诉了离别之情和家庭状况后,舅舅就把父亲介绍到一家杨柳青人开的金店中供职。
金店东家姓徐,挺和善、挺本分的一个人。东家夫妻俩只有一个女儿,漂亮、贤惠、文静。后来,东家变成了我父亲的岳父,东家的女儿成了我的母亲。我见过父亲十几岁时的相片,留着一条大辫子,戴着帽翅,浓眉大眼,笔挺的鼻子,特英俊、特帅气。母亲长得也不俗,是“美人胚子”的那种女人,到去世,快八十的人了,背不驼腰不塌,没有一根白头发。夫妻俩相濡以沫,恩恩爱爱度过一生,生了我们兄妹五人。父母于1974年双双谢世,相隔仅仅半年。
父亲很勤劳,很勤奋,也很聪明。小时候由于家境贫寒,不能读书,基本上是目不识丁。到我长大成人,父亲已经能写一手漂亮的小楷毛笔字了。从父亲的讲述中我得知,这全是父亲刻苦自学的结果。父亲每天在铺子里向帐房先生问几个字,店铺上板儿后就在地上铺上沙子苦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积月累,父亲写信居然也能“之乎者也”了。解放以后公私合营时,父亲的店铺合并到食品公司,父亲凭着才识,当上了会计。
父亲待人很友善、很大度。直到现在,无论尚在的老年人还是和我般般大的人,不分民族,说起我父亲,都是一句话:王爷,没说的,大好人。父亲鉴于自己幼年的不幸,特别惜苦怜贫。无论贫富贵贱一视同仁。平常做生意,遇到有人有难处想要货又没钱,他就给人,什么钱不钱的,先拿走再说。今年还不了,明年;明年还不了,后年;实在还不起了,不要了。就这样,父亲结了不少善缘。父亲在维吾尔人中有很高的威信,无论是商务上还是家务中有了纠纷,他们最常说的就是,请王爷评理。父亲居中说合,双方俱都心悦诚服。父亲的诚心待人,乐善好施,使自己以后也受益匪浅。民国二十几年时,新疆大乱,叛军见店铺就抢。父亲这时正在“回城”(温宿)做生意,恐惧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正当一家人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一天半夜,忽然有人砸门,父亲战战兢兢地出去查看,原来是乡下的一个朋友,曾得到过父亲帮助。他是来接父亲到他家去避难的。父亲他们匆匆换上朋友拿来的民族服装,坐上驴车,到了乡下。朋友把父亲他们藏在地窖里,只有晚上才能出来活动活动。一直躲藏到事态平稳。
父亲在我姥爷的金铺当了店员,按照规矩,东家管吃管住,平时零花钱可以预支,年底发薪。当父亲第一次拿到薪水时,舅舅对父亲说,你平时也用不着钱,不如我给你攒着,到时给你娶房媳妇。亲娘舅说了,而且冠冕堂皇的,父亲就把钱交给了舅舅,而且一交就是六年。等到父亲和母亲要成亲时,舅舅却把头一摇,不认账了。我姥爷确实看上我父亲了,所以,情愿倒贴钱,将母亲嫁给了父亲。姥爷、姥姥去世后,金店由父亲继续打理,生意也还可以。平稳过了几年舒心日子,不想祸从天降。有一天忽然店里来了几个人,对父亲说是来盘铺子的,边说边拿出一张契约。父亲接过来一看,原来舅舅倒了买卖,无力还债,便把父亲的金店顶给了债主。那时节,父母不在了,亲娘舅就是天了。父亲无力、也无心与亲娘舅纠缠,眼睁睁看着债主将满店的金银宝石收罗而去。为了避免同住一城,让舅舅为难,父亲举家搬到了温宿,一直到去世。母亲去世前给了我一包东西,有珊瑚、翡翠、玛瑙、红宝石等等。算是父亲一辈子的事业的佐证吧。
搬到温宿以后,父亲无力再办大买卖,就开了个杂货铺维持生计。两间不太大的门脸儿,生活日用品应有尽有。我记得很清楚,一溜三间房,左边的门脸儿是日用百货;右边的门脸儿是食品日杂;中间是开堂门。进了院子一溜五间平房。中间是客厅,两边是卧房,东西厢房是库房和伙房。我小时候最喜欢去食品店里玩。里面花花绿绿摆满了苏联的食品:方糖、水果糖、冰糖、各种罐头和糖果匣子。我最喜欢冰糖了,一尺多长的冰糖上粘满了五颜六色的小辣子、小葫芦、小茄子、小西红柿形状的水果糖,十分可爱。我经常趁大人不注意溜进门去抠冰糖上的水果糖吃。日杂也多为苏联货,五金、洋布不用说了,瓷器、玻璃器皿也大多是苏联货。我家现在还有那时苏联出产的碗呐。苏联那时已经很讲究商品的外包装和产品质量,糖果的外包装全是用马口铁做的,做工十分考究。我家现在还保留着一个圆的糖罐,一个方的糖匣子。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点儿没变形、没锈蚀不说,印的图案、花纹都清晰可见。1950年我大哥参加减租反霸时,买了没收地主老财的一张苏造钢丝弹簧床送给父亲,50块大洋,不便宜。父母去世前又给了我。在地主家用了不知多少年,跟我们家就小半个世纪。1994年我调回天津将它送给朋友时,仍然不摇不晃结结实实。
解放以后,除了有一年推行苏联花布,动员男的穿花衬衣、女的穿“布拉吉”之外,苏联货几乎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水的国产货,其中不乏天津货。大到铁牛拖拉机、五一手表、飞鸽、红旗自行车、蜜蜂缝纫机,小到天津蓝天牙膏、火柴等等全是天津货。父亲这种小商人也随着公私合营的进程步入了社会主义的行列。一解放,军管会就把父亲带走审查,让父亲交代问题。父亲说:我19岁从杨柳青赶大营到新疆,一直在阿克苏、温宿经商做生意,跟官面儿上从不往来,有什么好交代的呢?听说你以前开金货铺,现在又开着杂货铺,住着这么大的房子,能说没问题?金货铺是我承受孩子他姥爷的,后来黄了。我现在的铺面房子是我每年五‘塔哈’(维吾尔语,麻袋之意)大米租金租的。经过多次审查,确实无懈可击,于是把六皮箱家庭财产没收后,定了个“城市贫民”的阶级成分。每当说起这段,父亲总要感谢自己的舅舅。要是一直开着金店,准得落个“资本家”的帽子戴。这就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阿克苏商会的会长姓王,也是杨柳青人,人称“王商总”。王商总挺受同行尊重,解放以后被军管会叫去审查,不知因为什么罪恶,后来枪毙了。“文革”后,他的子女多次要求平反、落实政策,但因为年代久远,事实湮灭,案底也找不到,最后仍是不了了之。公私合营后父亲在食品公司做会计,因为父亲为人厚道,处世谨慎,在其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有惊无险的平安度过,直到退休。
我在家中最小,上面有俩哥哥,俩姐姐。大哥参加工作一直在法院。后来在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做书记,于1996年去世。有三男二女。其中长子和次子在威海工作。大嫂子和三儿子及两个女儿仍生活在温宿。二哥在温宿政府林业局工作,现已退休。二哥有三男一女,均在温宿工作。大姐已经去世,有一男三女,大女儿在北京中央实验话剧院,其余都在阿克苏工作。二姐今年69岁,健在。二姐夫也是杨柳青人,是在阿克苏的杨柳青人中出名的“董家酱园”的后人。有两男一女,也在阿克苏工作。从我姥爷算起,我们家在阿克苏已经是第五代人了。他们同祖辈一样,为阿克苏的繁荣和发展贡献着力量。我的两个女儿也都随我们回到了天津,大学毕业后都有了满意的工作。为建设天津贡献着力量。
回天津后我多次去杨柳青,抱着一丝的希望去寻根、寻亲,但都因我知道的太少而无果而返。听父亲讲,杨柳青镇最早只有一家王姓一家徐姓,后来像大树分叉一样分成许多家,但老祖宗是一个,也不知是真是假。我姥爷哥们五个,姥爷行大。二姥爷年轻时就去世了,三姥爷四姥爷也在新疆,五姥爷留在杨柳青。我姥爷只有母亲一个女儿,三姥爷的儿子叫徐恩奎,四姥爷的儿子叫徐恩普,还有徐恩华。是按“恩”字排行的。我的表哥们是按“松”字排行的,如徐松元,徐松林,徐松静等。不知这一点线索对我寻亲有无帮助。
阿克苏的乡亲们
清末民初时,阿克苏城很小,东西和南北长度都不到一公里。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主要街道是通往四个城门的两条街,交汇处称为“大十字”,也是城中心。杨柳青人的店铺就集中东西大街西面的南北两侧,是城中心的黄金地段。
南面临街的门脸是王商总的天津糕点铺,前店后厂,很大的一个作坊,专门制作京津风味的糕点,如大小八件、核桃酥、萨其马、槽子糕等。当然是清真的,不但汉族人买,连维吾尔族人也买。因为维吾尔人逢年过节,日常请客,招待客人,糕点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生意很好。王商总被枪毙以前,糕点铺着了一场大火。关于这场大火,轰动了整个阿克苏,各种传言都有。最有鼻子有眼的是有人亲眼看见火起时,有一对童男童女从门里走出来,手里牵着一根红绳,红绳牵到哪火就烧到哪,根本就扑不灭。糕点铺彻底毁了,从此阿克苏再也没有京津风味糕点不说,就连稍微像样的饼干也没有。我爱人1964年支边到阿克苏后,想吃点心,买了些饼干,一咬,差点把牙崩掉。江米条是用面粉做的,也是梆硬。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由内地人带入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有了高级的中、西糕点,但是天津的大小八件却是再也不见了。
再往西包括糕点铺后面往南的一大片,就是董家酱园,也是前店后厂,以制作各种酱菜为主,也做酱油、醋。规模很大,作坊里腌制酱菜的大缸就有一千多口,雇了十七、八个工人日夜生产。不但供应阿克苏全城,还批发到附近各县,生意很红火。1953年,我二姐嫁到董家时我去看过,还在生产。董爷在解放后的第一年就因“动火”(脑溢血)而去世。董家酱园由其孀妇董二奶奶支撑着,她也算是女中豪杰,将酱园经营得有条有理,直到公私合营。董爷娶妻两房,前面的妻子生了四个儿子,董二奶奶是填房,生有两个儿子。六个儿子没有一个是子承父业。我二姐夫董光诚大排行是老五,是董二奶奶所生,解放前十几岁时就在专员公署供职,解放后留用,仍在行政公署。最后在行署民政局福利院院长位置上离休(因为新疆是在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的率领下起义,和平解放的,所以留职人员都按离休对待)。二姐夫的弟弟董光和,大学毕业以后在阿克苏道桥处工作,后来调到武汉。这一段记述算是添补了谢玉明老先生《赶大营》文章中关于“董家酱园”的一点缺失吧。
从天津糕点铺东头向南拐是一溜小商铺,卖些土产日杂、小吃饮食什么的,全是杨柳青人开的。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是于大爷的贴饽饽熬小鱼,还有周姥姥的松花蛋。于大爷的饭馆儿门外垒了一个大灶台,上面支着一口“八沿儿锅”,从老远的地方就能闻到熬鱼的香味。周奶奶的松花蛋,最早我是喜欢看它的花纹,还挺纳闷儿,为什么鸭蛋上能长花纹而鸡蛋上就不长呢?还有一家饭馆的厨师也是杨柳青人,大人们管他叫“一马勺”。我问父亲为什么这么叫他,父亲告诉我“一马勺”以前在一个饭庄掌勺,红案上的师傅是个河南人,总受“一马勺”气,一次河南师傅配菜少配了一种菜,“一马勺”大发雷霆。河南师傅被骂急了,拿了个马勺就给了他一马勺,头上因此就落下个马勺型的伤疤,因此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一马勺”。由此也可以看出无论在什么年代、什么地方,天津人爱给人起外号的诙谐性格是改变不了的。其外号起的贴切、形象程度也是无与伦比的。
徐家因为在阿克苏的人口众多而成为大户,与天津糕点铺隔街相对。我姥爷的金铺就在街的金角位置,一个典型的京津建筑风格的店铺。除了经营金银首饰、珠宝玉器外,还兼营金银收售、加工业务。我的大舅人称“徐老总”,是粮食交易行的老板,经营着很大的一个粮食交易市场。市场主要从事粮油交易,不收摊位费,买卖双方成交后由买家按购买数量交一定的佣金给主家。徐家哥们几个统住在一个三进的大院子里,门口有几棵白杨树。我小时候就已经很粗了,1994年我调回天津时专门去看了看,院子是在解放以后早就建成人民电影院了。粮食市场变成露天电影院,宅院建成室内电影院了。但那几棵树还在,一个人已经搂不过来了。随着父亲搬去温宿及三、四姥爷的去世,我的舅舅们也就分居另过了。随着时代的变迁,我的表哥们没有一个是子承父业,纷纷弃商从政、从工、从文了。后代子孙们渐渐融入主流社会,与解放后移居新疆的汉族人相对而言变成当地的“土著”了,至今已传至第六代了,主要聚集在阿克苏,散布到全疆各地,从事各种工作。
乡情乡俗
不管阿克苏离杨柳青遥遥万里,也不管离开杨柳青几十年、几百年,祖辈们把浓重的乡情乡俗顽强地保留下来并一辈一辈地传承下去。
首先在语言上保持着浓重的杨柳青声调,纯粹的天津土话。我的平辈中比我年长十几、二十岁的,只要一开口说话,就是纯正的杨柳青音调。到我这里情况有些变化,在家时要严格地说杨柳青话,不然父亲要骂的;在学校要说当地话,不然同学要起哄笑话的。比如说“干什么”,当地说“干啥”,我在家说“干嘛”。如果一时忘记了场合而用岔了词,遭到的不是训斥就是哄笑。所以我说话的声调,一半是杨柳青的,一半是阿克苏的。回天津后又加上一点天津市里的,真的是“三不管”、“四不像”了。至于土话,不但我懂现在天津说的,而且我还懂现在天津不说的。比如“各闹”。什么意思?垃圾。天津叫“脏土”。倒垃圾,天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叫倒脏土,现在叫倒垃圾,而我们家一直叫“倒圪淖”。我母亲有一个装炒菜油的搪瓷罐,母亲管它叫“闷罐儿”,我现在还用着。至于像“棉靴头”、“关饷”、“靴掖子”等等这些土话,在天津是早以作古了,在阿克苏,不但我懂,下一代懂,而且就连常和我玩的朋友们也懂。
其次,是保留着杨柳青的风俗习惯。阿克苏的汉族人很多,各省人都有,但是过年时一定要蒸馒头、炖肉、吃饺子、贴对联、贴年画、放鞭炮的惟有杨柳青人。母亲每年过年时都要贴年画,而且一定是杨柳青年画。有传统的“连年有余”、“老鼠娶亲”,还有“四扇儿”,都是托人从乌鲁木齐甚至从杨柳青带来的,很不容易,所以一次要带好多。到“文革”时还有不少,“破四旧”一把火都烧了。现在想起来怪可惜的,那可都是老版的杨柳青年画啊。父亲常和我讲画中的戏曲故事。最常讲的是“二十四孝”的故事,什么“卧冰求鲤”、“老莱子彩衣娱亲”等。父亲还经常给我讲他小时候在杨柳青时的故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念的他们那时的一首童谣:“切登切,切登切,娘儿们穿的爷们儿鞋”。父亲说,可不是么,没两年,皇上下旨,妇女放脚,禁缠足。现在女的男的不是穿一样的鞋了吗。
那时我最高兴的就是过年了。不但有好东西吃,还有新衣服穿。我常因试穿新衣服不肯脱下来而遭母亲的呵斥,几乎年年如此。对襟棉袄、疙瘩袢扣的,挽腰的棉裤,梳两条小辫,戴一朵绒花。小闺女家,能不高兴吗。父亲管炖肉,母亲管蒸馒头。肉一炖一大盆,吃时挖几勺肉烩上白菜粉条。馒头一蒸一缸,放在院子里。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包饺子、守岁、听父亲讲在杨柳青过年时踩高翘、跑旱船、耍狮子的事。阿克苏也有高跷会,全是杨柳青人家的年青人组成的。我二姐夫董光诚,我二姐、我大嫂他们都在高跷会里。大年初一高跷会是一定要上街的,几乎全城的人都去看,不论民族。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初一早上天还不亮母亲就把我叫起来,穿戴好了以后,坐“六根棍”马车由温宿到阿克苏去拜年。
所谓“六根棍”是指车轱辘而言。那时阿克苏还没有胶皮轱辘马车,全是木轱辘马车,每个轱辘有六根木棍做辐条,车轮直径约1.5米。车走得很慢且颠簸,12公里的路要走两个小时以上。在街上熟人碰上都互相作揖,口称“发财”。到姥爷舅舅家拜年,我是要磕头的。当然也要给压岁钱。
我记得小时候母亲常领我去李二娘家串门。李二娘家有一间屋是从不让外人进入的。我出于好奇,曾捅开窗户纸偷偷看过,里面八仙桌上供着一只彩绘的泥娃娃,烧着香,还有一碗饭,一双筷子。饭是每顿都要换的。我好奇地问母亲那是什么,母亲告诉我,李二娘结婚几年没有孩子,有一年特地回天津,到“娘娘宫”拴了个娃娃回来,叫“大阿哥”。本来年年要拴一个更大的,因为离天津太远了,只好一直供着这一个“大阿哥”。后来李二娘子孙满堂,便对“大阿哥”敬重有加,一直供奉着了。我听了对“娘娘”也是崇拜不已。听父亲讲,“娘娘宫”又叫“天后宫”,供奉天后娘娘,又叫“妈祖”庙。“妈祖”是保佑渔人出海平安的,也是镇海的。妈祖神像的座下就是海眼,贴近神像仔细倾听,可以听见大海的波涛汹涌声,挪开神像可以看见翻滚的波涛。一个娘娘有如此的神通,我对娘娘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1974年,我第一次回到天津后专门去参拜了天后宫娘娘,瞻仰了我心仪以久的菩萨。
维吾尔人有自己的礼拜寺,回族人也有自己的清真寺,杨柳青人在阿克苏也有自己的同乡会,叫“公所”。进阿克苏北门右手即是,很大的院子里面有庙有议事厅有供人休息的客舍。我大姐大姐夫从乌鲁木齐搬到阿克苏,一时找不到房子,就住在公所的客舍里。每到初一、十五,人们便去烧香磕头求签扶乩。里面供奉的是什么菩萨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大人们围着一个沙盘念念有词,干什么我也不懂。只记得有一次大人们很激动,嚷嚷着,神仙发话了。我问父亲神仙说的嘛,父亲告诉我是“你问我,我问谁,除了宣统都是贼”。我再问是嘛意思,父亲摇摇头没说话。我记住了这句话,到底是什么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每次聚会,有婚丧嫁娶等大事就议一议,没大事就家不长里不短的聊一阵。我随大人去过几次,感觉很有意思。1957年,公所拆了,建成了阿克苏群艺馆。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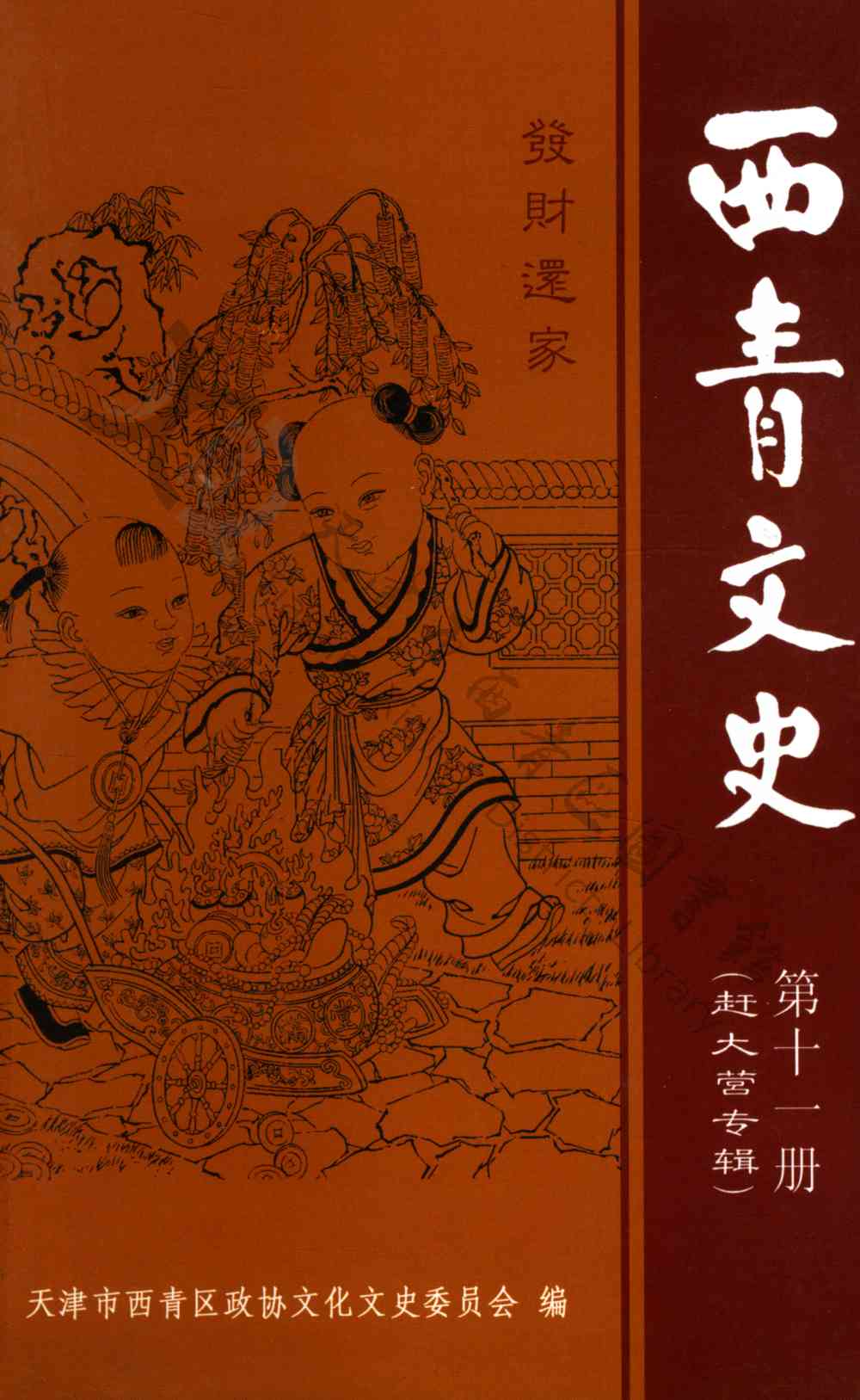
《西青文史第十一册》
本书分西域商旅图、杨柳青骄子、百业竞身手、文化大融合、寻访赶大营踪迹、寻访赶大营后裔栏目,收录了《赶大营的天津人 》、《已故诗囚王子钝》、《高万发的甜蜜事业》、《礼门公所的性质》、《赶大营的兴衰》、《新疆杨柳青后裔有多少》等文章。
阅读
相关地名
阿克苏地区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