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庭芳
| 内容出处: | 《天津第一座發電厂》 图书 |
| 唯一号: | 020020020230026134 |
| 颗粒名称: | 王庭芳 |
| 分类号: | K825 |
| 页数: | 12 |
| 页码: | 191-202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王庭芳从山东阳谷县出发,经历多次工作变动和不幸遭遇,最终在山西的工地与日本监工发生冲突并利用计谋进行报复。 |
| 关键词: | 王庭芳 人物传略 天津市 |
内容
別瞧我說着一嘴天津話,說实在的,我却是山东省阳谷县生人。提起来武二郞景阳崗打虎的地方,都知道吧?那地方离我們住处不远。再細說,我們还不算是阳谷县人,而是从我老爷爷那輩起,逃荒逃到阳谷县来的。听长輩們說,老爷爷当时挑着一副担子,前筐里放着我大爷爷,后筐里放着我二爷爷餓着肚子来到这里。然后便利用这副担子挑水燒水,开了个水灶。那时候,阳谷县水运繁盛,来往旅客很多。所以就靠着这个水灶,老爷爷,爷爷苦苦熬了兩輩子。
生我以后,母亲得了一种营养失調的病。有病沒錢治,光拿身子耗着,耗到后来,母亲一命嗚呼。父亲在家里呆不下去,便带着我一齐奔了济南,随后又由济南輾轉来到天津。那正是1937年的春天,蘆溝桥事变的前半年。一下車,我捫就投奔“电灯房”来了,因为我們一位叔伯兄弟的舅舅在电厂子燒鍋爐,便在他家先落住脚。事由很难找。好不容易才被荐到織袜子的作坊去。因为我岁数小,干不了重活,只叫我紡綫軸,紡了十个,我給坏了五对。內掌柜的火了,連一頓飯都沒管吃,把我攆回舅舅彖。
事由很难找。好不容易又被荐到三义庄丁記飯館当学徒。洗碟子刷碗,抬煤倒土,这活儿咱捫干得来,唯有一样,还得外饒着挨打,受駡,招气。掌柜的是变着法儿来收拾折磨小徒弟。咱是阳谷县武二郞打虎左近的人,受他这份轄治啊?沒那么容易的,熬了半年,咱王庭芳不給你干了,賭气溜走。这一来,沒地方糊嘴了,我呆在一个乡亲开的飯館楼上,长了一身的膿疱疥。飢一頓飽一頓的,瘦的不像样。可我幷沒閑着,看了不少的書。自然啦,那年月我也摸不着好書看,看的尽是劍俠書,什么三俠劍啦,靑城十九俠啦,虽然看得暈头暈腦,但是社会里的不平等現象,有的人吃穿不尽,有的人成天混不上一飽,这些事却一直在我腦子里轉。轉来轉去,自己給自己找到一条道路,打算跟一个老和尚去五台山修行。倒不是看破紅塵,而是想着学点武术,将来也做劍俠,抱打不平!幸亏我父亲注意上我了,看我看的很紧。我呢,也舍不得父亲,覚得他太苦了,我怎么能撂下他呢?总算沒拔腿。
1938年的冬天,也就因为舍不得父亲,我們爷倆一齐去当了华工。我們去的地方是山西段家嶺至宣崗鎭一带的鉄路工地,我們受的罪那眞是年靑一代人們想也想不出的。
剛一到段家嶺工地的时候,大約吃了一个星期的面食,以后就変样了,弄了三十多袋又黑又生芽子的大土豆,鹽也沒的吃,成天叫人們吃开了白水煮土豆。为了讓劳工們无处藏无处跑,給劳工們發了一种特制的“囚”衣,每人都罩上一套麻袋大衣麻袋褲,麻袋帽子麻發鞋。老远的一眼望去,个个都是高个儿,腰溜圓,每人扛着一把大鉄銑,眞是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又冷又餓,头頂着槍子干活,誰肯使劲啊?日本鬼子就叫监工来打大伙。最可恨的要屬监工小林了,他每天瞪圓了母狗眼,不是嫌这个除土不用劲打一棒子,就是嫌那个背土走的慢来一下子。监工們太狠了。他們狠,倒敎育了我們大伙,大家抱团抱的很紧,而且火頂腦門,恨不得整治他們一頓。
有天,我听說日本二掌柜的,叫西馬达的到工地上来检查。为什么要到我們这儿来呢?是包工大柜的朱八在鬼子面前夸下海口,說我們这一帮工人一个頂十个干,从来到山西沒跑过一个。西馬达登时挑大拇哥,喊着:“朱家大柜干活的頂好頂好。”一听这消息,我登时便計上心来,覚得打小林的机会到啦。
怎么打法呢?我找了兩位在外边創蕩多年的流浪汉徐大爷和刘大爷說:“你們二位合計什么呢?有什么高招敎給敎給我!
“你过来!”他們就对着我耳朵叨咕了一陣子。……
轉天,天还沒大亮呢,鉄鐺子就当当的敲了个山响,我們連忙揉了揉眼,伸了伸腰,一人喝了一碗谷子和黑皮土豆煮的粥。拿起鉄銑,頂着風寒上了工地。到了工地我們就扯閑天,大家一齐“揑窩窩”,故意一字儿排开,站在鉄道一边,手扶着銑,不干活。
小林从山弯子外轉来,老远就喊:“为什么不干活?”奔过来,举起打人的大馬棒,照着每个人的屁股上就是一下。打来打去,打到我这儿了,不动声色,我只用力把鉄銑往后一插。就听叭哧一声,小林的大棒子被洋鎬打断了。小林吃劲不住,往前一栽。乘这工夫,我来了个順手牽羊,小林鬧了个大趴虎,刘大爷一脚踩在小林的大胯上,喊了一声“打!”,十几个人都涌上来了。
“快跑,快跑呀!”徐大爷是去巡風的,这时从山弯子轉过来喊給大家听。
大伙撒腿就跑,給他来了个死无見証。唯有我沒跑,反倒抄起小林打断的半截馬棒,朝西馬达跑去。到他跟前,我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裝着哭丧臉的样儿,給小林这小子吿了一状。我說:“西馬达掌柜,小林的每天的苦力的‘三宾’的給。你看,我的大腿打坏啦,苦力們的打跑啦!”一边說着,我一边把打断的半截馬棒給西馬达看。
这时候,正好小林破口大駡,發瘋發狂的赶来。西馬达火儿了,过去喊叫小林:“你的苦力通統的打跑啦!”
小林怔住,連忙行礼。行礼也不行,西馬达上前跨了一步,嚷道:“苦力‘三宾’的給的不行!”紧接着掄起他那小蒲扇似的大手,一連打了小林兩記耳光。
把小林打的双臂直垂,一动也不敢动。我們工人們都回来了。哈哈,大伙可开心了。这是我参与的第一次的自發斗爭,以后我摸着了門道,动不动就来这一手儿。
不过,我們当时幷不願意只搞这种报复式的斗爭,我們都想当八路軍去。我們住的那个村子,白天鬼子兵在村口上放哨,大搖大摆的;太阳一偏西,他們就立刻扎在炮楼里了。从我們一去,見天見夜里都有鬼子兵失踪,被我們八路軍游击队摸了去。把我們喜欢坏了,恨不得有一天能冲出去找八路軍。后来,日本鬼子在山头上挖了个大洞,控制住制高点,以为这样万无一失了。哪想到我們游击队用大縄子拴了一个洋油桶,桶里面裝滿了炸藥,乘刮風的时候把它从山上滑下来,随着縄子还滑下兩个勇士来,把洋鉄桶送到山洞的小門上,然后兩人揪住繩子的兩头,把桶子悠进山洞里,把十来个鬼子給炸了个粉碎。
后来,游击队的活动發展到就是白天晌午的时刻也干起来了。这天,正是太阳晒得足足的呢,从山澗里来子三个身穿半新白皮褲袄的老百姓,牽着三匹駄着满満的麦秸的小毛馿,他們胸前都带着良民証,通过卡子口一直到我們工地上来了。离我們不远,他們把毛馿拴在棗树深处,从麦秸內拉出一把歪把子,兩支駁壳槍,往皮袄里一掖。一个人扛着歪把子跑进鉄道的桥底下。另兩个人就搖搖晃晃朝我們干活的地方来了。誰也睜着兩只大眼,可大伙都裝着沒有瞧見,自顧干自己的活儿。他倆过来了,拿起小麻袋和我們一起背土,一扎就扎进了人群里,鬼子也分不出他們是誰来。干着干着活,太阳偏西了,十来个鬼子兵和兩个监工的都围在一塊儿烤火,我們干活的,手冷不过,也可以到上边蹲一会儿再下来。我和一位李二伯也上去烤手了,他們倆也跟上来了。蹲在旁边,一边烤着手一边問:“老乡,从哪儿来的?”我一听是天津一带口音,就說:“我們都是从天津叫日本人招来的,也有他們抓来的。”有个黑臉的就說:“咱們都是老乡呢。”接着那另一个人就說:“老乡們別烤啦,快下去干活。”这句話透着硬,有点命令的口气。我們倆挺乖覚,立刻溜下来了。剛下来,就听上边一陣子駁壳槍响,嘎嘎嘎,咕咕咕,十来个鬼子全倒下来了。大伙一扭头,眼巴巴的望着这兩位游击队員,他們眞沉得住气,把十来杆大槍都背在肩上,朝炮楼走去。炮楼上的兩个鬼子兵趴在里面,一动也不动。这兩位围着炮楼子轉了一遭,看看沒有动靜,以为鬼子兵都給打死了昵,就想往回走了。但沒想到那兩个鬼子兵爬起来,接連响了几槍,把那位中等身材的大腿打伤。这时,桥下边的歪把子嘎嘎嘎的一陣响,立刻炮楼里槍声哑下去。兩个游击队員搀着那个受伤的同志走去。
这些事給我的印象太深了。眞恨不得馬上跑到八路軍那里去。事实上也不断有人跑走。可惜,我光轉念头沒有动脚儿,因为我讓父亲給絆住了。总不能把他孤零零地丢在山西呀。不过,我却接受了斗爭的影响。总是要反抗,而且一直向往着党。……
我是日寇接管“电灯房”的前些时候,經我舅舅介紹到厂里来的。在鍋爐房燒鍋爐。不久,日寇就接管了厂子。鬼子一来,压榨的更露骨,更瘋狂了。工人用流血斗爭換来的养老金,兩袋配售白面和煤賞錢都沒有了。还建立了“三人連环保”,下班要搜腰,把工人整治的連牛馬都不如。咱能看得慣这些嗎?咱得跟那些八路軍游击队学,給他們来个出其不意的。
这天。下班了,我沒有就走,先把飯罐里的小米飯湯在大汽管子蘭盤上加热。热得滾开的,我这才跑到前門。門口上,工人們排成了一列,正等着走狗馬大脚搜腰。
馬大脚一边讓工人們挨个給他张开双臂,一边嘴里还駡駡咧咧的說:“走,給我快走!”說着,輪到我了,他扫了我一眼,立刻就翻飯罐,我趁势一松手,于是一罐热滾滾的稀飯湯都潑在馬大脚的手上,脚上了。燙得这小子啊呀啊呀怪叫。嚷道:“好小子,你故意弄稀飯燙我。好,老子揍死你!”
我忍住笑說:“咦,飯罐子本来是盛飯的嘛,誰叫你来翻它?”
說得他无言可答,从我手中夺过飯罐,死命朝洋灰地上一摔。我心說,摔就摔吧,反正你小子讓我給燙啦。
以后,我又照方抓藥,把邢三整治了一下。邢三是誰?邢三原名叫李文森,是个白俄监工,专一的拿着鞭子抽打工人,长着一副吊死鬼的臉,見人总是苦臉蛋子,大伙想起天津当地傳說,邢三上坟的故事了,就給他起了这么一个外号。这天,我正弯着腰推着煤車住14号爐运煤。走到半路腰上,惹着这塊洋料了。他抓住我的后腰带,連推带駡的喊:“你的不使劲,快推,快推!”
咱吃他这个又推又操的嗎?气往上撞,我一轉身跳到煤車前面,大声駡他:“你他媽的推。爷爷沒劲儿。”
“邢三的鷹鈎鼻子上直冒汗珠儿,抬手就要打人。咱不能挨他的,往后退了兩步,駡道:“邢三,你有种跟爷爷下边打来。”
駡完回头便跑。这下,可把邢三气炸了肺,他抬腿就追,我就紧着跑。跑来跑去,我跑到12号爐子前头,正好鬼子山田在大駡推煤工人,嫌推煤推得太慢呢。我心生一計,弯腰鑽过煤墙洞,裝着很害怕的样儿,跑到山田跟前說:“山田先生。你看李文森的‘三宾’的給。上边推煤工都叫他打跑啦。”正好邢三也从煤墙洞里爬出来,朝我扑上来。我更有詞儿了,便說:“你看,他这不来了嗎?”
山田这儿正着急工人老是推得慢慢騰騰,煤不頂嗆呢!原来是监工的把工人全打跑了哇!山田上去,嚷道:“你的什么的干活?工人‘三宾’的給的不行。跑啦,跑啦的有!”
工人們一看有热鬧可瞧,誰不是給他加把子劲啊?都过来指着邢三喊:“都是他把人打跑的。煤才上木去。”
山田一听更急了,伸手把郉三拍、拍打了几下。邢三呆在那儿,居然委委屈屈的咧着大嘴直哭。我們看着可开心了。
是不是解解气,寻寻开心就滿足了呢?幷不滿足。誰不是窩着一肚子火在想斗爭的办法呢?有天,我們鍋爐房的一班工人,被监工的吆喝了一声,十来把鉄銑都給他撂下了。大伙七言八語的挤在一塊又扯开了,都說:“不能給他們鬼子干!得想法子啊!”
我說:“吿訴你們哥几个一点活路。人家胡头班的人,有的跑单帮,有的去賈家大桥打毛子工,一天能賺好几塊‘大棉被’票①,你們說咱們呢?”
“咱們給他外边干去,給他拆台,擱車。大伙齐心不?”
“齐心!誰要是心猿意馬,出門讓电車軋死他!”
“对,电車軋不死,来个驟車也得撞上他。哥儿們抱团,干哪!”說到这儿,大伙还对瞧了一眼,算是盟誓。
接着,我們就又拾起鉄銑,喊喝着“一、三、五、二、四”地低头干起活来。
这时候,富根大模大样从后楼走进鍋爐房。他看我們大家干活干的还起劲。这小子竟說:“干活大大的好。”說着要过一个煤鏟来,哈腰伸腿,也往爐膛里添煤,招呼大家向他学。
“干哪!干哪!加油干哪!”副班长催着大家,一边就拿大火扒扒灰。
火越燒越旺,唿唿的,連安全門都起劲了。富根咧着大嘴带笑地說:“頂好的有,頂好的有!”
“哎呀!哎呀!”乘他高兴的这时刻,我蹲在地上裝病造魔,嚷道:“厂长先生,我肚子痛,哎呀!我站不住啦。厂长讓我回去吧。”
富根这小子最会收买人心。居然叫値班的电工楊文貴到他家取藥。給了我一个藥丸,这才說:“你的回去。”
我捧着肚子出了大門。聞了聞那藥丸,一股子大烟味儿。眞他媽的会盜买人心,順手給他扔在馬路上。
次日早晨八点鐘光景,我們約好的几个工人都在电灯房东胡同集合起来。人不算多,有几个沒来的,可是一打听,进厂的只有把头和另外兩个人。工厂的大門已經上了鎖,鬼子怕沒有接班的人,把胡头那一班的人整个扣住了。总算不賴,哥儿們心齐。
我說:“好吧,咱們別在这儿等啦。这儿离厂子近,不太保险。走,先找老梁去。他大槪是讓梁大嫂拖住了脚。
我們找到了梁师付,跟着他一齐到北站打短工“卖現錢”。眞是什么鬼年月,在北站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沒碰上一个找人干活的,大家正起急呢,突然从南边开来一輛日寇抓人用的軍車。我一看来势不好,急忙招呼大家:“腿上加油,馬上走人哪!”只是腿再快,也沒有車軲轆轉的快,卡車已經停住,鬼子已經跳下車来了。逃走是来不及了。怎么办?人多智广,也不知是誰一眼看見馬路左边有輛轎車,正好机器坏了,停在那里。我們就一窩蜂的奔过去,推車便走。下来的日本鬼子干瞪了兩眼,沒敢抓人,他誤以为是坐汽車的人雇我們推車的了,不知里面坐的是什么人物,另抓別人去了。一关躱过,二关难逃,我們一看在外面干临时工是腦袋拴在褲腰帯上,也不是路。熬了八天只好硬着头皮又回到發电厂。斗爭的道路还是找不着呀!
解放了。炮火剛剛停下亲,我就从家里挖的地窖里跑出来,大踏步儿向工厂跑去。我爱人剛剛生产,只是我的心顧不上她了。再重要也沒有协助接管工厂这事儿重要了。瞧見軍代表,虽然我从来沒見过他,可我就像見了亲人似的,一面高兴,一面后悔,“如果那年在山西我跑过去,不管我爹,那我現在不曉得做了多少工作了。”
組織上也很重視我。第一次成立党課学習班,便吸收我参加。学習的內容是党員标准,党綱党章,革命史等等,对我来說,眞是有生以来头一次开窍,眼界开了,心胸大了。我这才懂得党的崇高和偉大。我的决心很足,要一輩子跟党走。
只是,我的覚悟不高,我还不能全心全意为了党,和党員的标准还有距离。过了些时候,我得了肺炎,在我病中,得到党組織上的关怀,特別是1950年电厂党支部整風,給了我很大敎育,我深深体会到党的英明和正确,所以当党在發电厂第二次吸收党員的时候,我便第一个交了志願書。不过这已是1952年了。
話还得从得病的事儿說起。病剛好,还沒有恢复健康呢,我就要求上班了。不这样作当时心里不舒服,一个工人一歇多半年,誰受得了呀?党組織怕我身体吃亏,也懂得我这迫切想要工作的心情,准我上班,但不叫我干司爐的重体力活,跟老工人耿庆祥一塊做鉗工,干些輕便活儿。耿师付是个党員,对我的关心眞是无微不至,有时連我喝水他都管。身体漸漸好了,我也要强,所以在大修13号爐的紧张工作中,我也沒有因为身体不好掉队。以后,厂內哪有工作我就到哪去打游击。下班以后,我不是进业校的門學習文化,就是进工会的門做工会工作。我是打三厂的工会一成立就担任小組长兼合理化委員的,后来就越来越多的搞起工会的工作来了。我的工作能力虽不高,当时的信念却只有一个,工人翻身了,能力低,也得好好干,好好鍛煉!
1953年的春天,党組織又調我到市委党校初級班学習。一去又是半年多。在党校放暑假的时候,我因为半輩子沒休息过,休息起来筋骨都覚得难受,便白天回厂,帮助工会搞工作。当时正是工会开展群众思想检查的阶段,很需要人手。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就抓些时間温習党校功課。晚上回到家里,因为街道上正在搞普选,我也参加了这項活动。虽然每天都很紧张,但我的心情却是十分愉快的。
从党校学習回来,組織决定叫我脫产搞工会工作,工会改选时,我被选为基層工会的副主席。光阴过的眞快,一晃我已在工会工作了七个年头了。但是,我的工作做的还有許多缺点,我要繼績努力,对于一个年輕的工人来說,这只不过是剛剛迈了第一步。
生我以后,母亲得了一种营养失調的病。有病沒錢治,光拿身子耗着,耗到后来,母亲一命嗚呼。父亲在家里呆不下去,便带着我一齐奔了济南,随后又由济南輾轉来到天津。那正是1937年的春天,蘆溝桥事变的前半年。一下車,我捫就投奔“电灯房”来了,因为我們一位叔伯兄弟的舅舅在电厂子燒鍋爐,便在他家先落住脚。事由很难找。好不容易才被荐到織袜子的作坊去。因为我岁数小,干不了重活,只叫我紡綫軸,紡了十个,我給坏了五对。內掌柜的火了,連一頓飯都沒管吃,把我攆回舅舅彖。
事由很难找。好不容易又被荐到三义庄丁記飯館当学徒。洗碟子刷碗,抬煤倒土,这活儿咱捫干得来,唯有一样,还得外饒着挨打,受駡,招气。掌柜的是变着法儿来收拾折磨小徒弟。咱是阳谷县武二郞打虎左近的人,受他这份轄治啊?沒那么容易的,熬了半年,咱王庭芳不給你干了,賭气溜走。这一来,沒地方糊嘴了,我呆在一个乡亲开的飯館楼上,长了一身的膿疱疥。飢一頓飽一頓的,瘦的不像样。可我幷沒閑着,看了不少的書。自然啦,那年月我也摸不着好書看,看的尽是劍俠書,什么三俠劍啦,靑城十九俠啦,虽然看得暈头暈腦,但是社会里的不平等現象,有的人吃穿不尽,有的人成天混不上一飽,这些事却一直在我腦子里轉。轉来轉去,自己給自己找到一条道路,打算跟一个老和尚去五台山修行。倒不是看破紅塵,而是想着学点武术,将来也做劍俠,抱打不平!幸亏我父亲注意上我了,看我看的很紧。我呢,也舍不得父亲,覚得他太苦了,我怎么能撂下他呢?总算沒拔腿。
1938年的冬天,也就因为舍不得父亲,我們爷倆一齐去当了华工。我們去的地方是山西段家嶺至宣崗鎭一带的鉄路工地,我們受的罪那眞是年靑一代人們想也想不出的。
剛一到段家嶺工地的时候,大約吃了一个星期的面食,以后就変样了,弄了三十多袋又黑又生芽子的大土豆,鹽也沒的吃,成天叫人們吃开了白水煮土豆。为了讓劳工們无处藏无处跑,給劳工們發了一种特制的“囚”衣,每人都罩上一套麻袋大衣麻袋褲,麻袋帽子麻發鞋。老远的一眼望去,个个都是高个儿,腰溜圓,每人扛着一把大鉄銑,眞是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又冷又餓,头頂着槍子干活,誰肯使劲啊?日本鬼子就叫监工来打大伙。最可恨的要屬监工小林了,他每天瞪圓了母狗眼,不是嫌这个除土不用劲打一棒子,就是嫌那个背土走的慢来一下子。监工們太狠了。他們狠,倒敎育了我們大伙,大家抱团抱的很紧,而且火頂腦門,恨不得整治他們一頓。
有天,我听說日本二掌柜的,叫西馬达的到工地上来检查。为什么要到我們这儿来呢?是包工大柜的朱八在鬼子面前夸下海口,說我們这一帮工人一个頂十个干,从来到山西沒跑过一个。西馬达登时挑大拇哥,喊着:“朱家大柜干活的頂好頂好。”一听这消息,我登时便計上心来,覚得打小林的机会到啦。
怎么打法呢?我找了兩位在外边創蕩多年的流浪汉徐大爷和刘大爷說:“你們二位合計什么呢?有什么高招敎給敎給我!
“你过来!”他們就对着我耳朵叨咕了一陣子。……
轉天,天还沒大亮呢,鉄鐺子就当当的敲了个山响,我們連忙揉了揉眼,伸了伸腰,一人喝了一碗谷子和黑皮土豆煮的粥。拿起鉄銑,頂着風寒上了工地。到了工地我們就扯閑天,大家一齐“揑窩窩”,故意一字儿排开,站在鉄道一边,手扶着銑,不干活。
小林从山弯子外轉来,老远就喊:“为什么不干活?”奔过来,举起打人的大馬棒,照着每个人的屁股上就是一下。打来打去,打到我这儿了,不动声色,我只用力把鉄銑往后一插。就听叭哧一声,小林的大棒子被洋鎬打断了。小林吃劲不住,往前一栽。乘这工夫,我来了个順手牽羊,小林鬧了个大趴虎,刘大爷一脚踩在小林的大胯上,喊了一声“打!”,十几个人都涌上来了。
“快跑,快跑呀!”徐大爷是去巡風的,这时从山弯子轉过来喊給大家听。
大伙撒腿就跑,給他来了个死无見証。唯有我沒跑,反倒抄起小林打断的半截馬棒,朝西馬达跑去。到他跟前,我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裝着哭丧臉的样儿,給小林这小子吿了一状。我說:“西馬达掌柜,小林的每天的苦力的‘三宾’的給。你看,我的大腿打坏啦,苦力們的打跑啦!”一边說着,我一边把打断的半截馬棒給西馬达看。
这时候,正好小林破口大駡,發瘋發狂的赶来。西馬达火儿了,过去喊叫小林:“你的苦力通統的打跑啦!”
小林怔住,連忙行礼。行礼也不行,西馬达上前跨了一步,嚷道:“苦力‘三宾’的給的不行!”紧接着掄起他那小蒲扇似的大手,一連打了小林兩記耳光。
把小林打的双臂直垂,一动也不敢动。我們工人們都回来了。哈哈,大伙可开心了。这是我参与的第一次的自發斗爭,以后我摸着了門道,动不动就来这一手儿。
不过,我們当时幷不願意只搞这种报复式的斗爭,我們都想当八路軍去。我們住的那个村子,白天鬼子兵在村口上放哨,大搖大摆的;太阳一偏西,他們就立刻扎在炮楼里了。从我們一去,見天見夜里都有鬼子兵失踪,被我們八路軍游击队摸了去。把我們喜欢坏了,恨不得有一天能冲出去找八路軍。后来,日本鬼子在山头上挖了个大洞,控制住制高点,以为这样万无一失了。哪想到我們游击队用大縄子拴了一个洋油桶,桶里面裝滿了炸藥,乘刮風的时候把它从山上滑下来,随着縄子还滑下兩个勇士来,把洋鉄桶送到山洞的小門上,然后兩人揪住繩子的兩头,把桶子悠进山洞里,把十来个鬼子給炸了个粉碎。
后来,游击队的活动發展到就是白天晌午的时刻也干起来了。这天,正是太阳晒得足足的呢,从山澗里来子三个身穿半新白皮褲袄的老百姓,牽着三匹駄着满満的麦秸的小毛馿,他們胸前都带着良民証,通过卡子口一直到我們工地上来了。离我們不远,他們把毛馿拴在棗树深处,从麦秸內拉出一把歪把子,兩支駁壳槍,往皮袄里一掖。一个人扛着歪把子跑进鉄道的桥底下。另兩个人就搖搖晃晃朝我們干活的地方来了。誰也睜着兩只大眼,可大伙都裝着沒有瞧見,自顧干自己的活儿。他倆过来了,拿起小麻袋和我們一起背土,一扎就扎进了人群里,鬼子也分不出他們是誰来。干着干着活,太阳偏西了,十来个鬼子兵和兩个监工的都围在一塊儿烤火,我們干活的,手冷不过,也可以到上边蹲一会儿再下来。我和一位李二伯也上去烤手了,他們倆也跟上来了。蹲在旁边,一边烤着手一边問:“老乡,从哪儿来的?”我一听是天津一带口音,就說:“我們都是从天津叫日本人招来的,也有他們抓来的。”有个黑臉的就說:“咱們都是老乡呢。”接着那另一个人就說:“老乡們別烤啦,快下去干活。”这句話透着硬,有点命令的口气。我們倆挺乖覚,立刻溜下来了。剛下来,就听上边一陣子駁壳槍响,嘎嘎嘎,咕咕咕,十来个鬼子全倒下来了。大伙一扭头,眼巴巴的望着这兩位游击队員,他們眞沉得住气,把十来杆大槍都背在肩上,朝炮楼走去。炮楼上的兩个鬼子兵趴在里面,一动也不动。这兩位围着炮楼子轉了一遭,看看沒有动靜,以为鬼子兵都給打死了昵,就想往回走了。但沒想到那兩个鬼子兵爬起来,接連响了几槍,把那位中等身材的大腿打伤。这时,桥下边的歪把子嘎嘎嘎的一陣响,立刻炮楼里槍声哑下去。兩个游击队員搀着那个受伤的同志走去。
这些事給我的印象太深了。眞恨不得馬上跑到八路軍那里去。事实上也不断有人跑走。可惜,我光轉念头沒有动脚儿,因为我讓父亲給絆住了。总不能把他孤零零地丢在山西呀。不过,我却接受了斗爭的影响。总是要反抗,而且一直向往着党。……
我是日寇接管“电灯房”的前些时候,經我舅舅介紹到厂里来的。在鍋爐房燒鍋爐。不久,日寇就接管了厂子。鬼子一来,压榨的更露骨,更瘋狂了。工人用流血斗爭換来的养老金,兩袋配售白面和煤賞錢都沒有了。还建立了“三人連环保”,下班要搜腰,把工人整治的連牛馬都不如。咱能看得慣这些嗎?咱得跟那些八路軍游击队学,給他們来个出其不意的。
这天。下班了,我沒有就走,先把飯罐里的小米飯湯在大汽管子蘭盤上加热。热得滾开的,我这才跑到前門。門口上,工人們排成了一列,正等着走狗馬大脚搜腰。
馬大脚一边讓工人們挨个給他张开双臂,一边嘴里还駡駡咧咧的說:“走,給我快走!”說着,輪到我了,他扫了我一眼,立刻就翻飯罐,我趁势一松手,于是一罐热滾滾的稀飯湯都潑在馬大脚的手上,脚上了。燙得这小子啊呀啊呀怪叫。嚷道:“好小子,你故意弄稀飯燙我。好,老子揍死你!”
我忍住笑說:“咦,飯罐子本来是盛飯的嘛,誰叫你来翻它?”
說得他无言可答,从我手中夺过飯罐,死命朝洋灰地上一摔。我心說,摔就摔吧,反正你小子讓我給燙啦。
以后,我又照方抓藥,把邢三整治了一下。邢三是誰?邢三原名叫李文森,是个白俄监工,专一的拿着鞭子抽打工人,长着一副吊死鬼的臉,見人总是苦臉蛋子,大伙想起天津当地傳說,邢三上坟的故事了,就給他起了这么一个外号。这天,我正弯着腰推着煤車住14号爐运煤。走到半路腰上,惹着这塊洋料了。他抓住我的后腰带,連推带駡的喊:“你的不使劲,快推,快推!”
咱吃他这个又推又操的嗎?气往上撞,我一轉身跳到煤車前面,大声駡他:“你他媽的推。爷爷沒劲儿。”
“邢三的鷹鈎鼻子上直冒汗珠儿,抬手就要打人。咱不能挨他的,往后退了兩步,駡道:“邢三,你有种跟爷爷下边打来。”
駡完回头便跑。这下,可把邢三气炸了肺,他抬腿就追,我就紧着跑。跑来跑去,我跑到12号爐子前头,正好鬼子山田在大駡推煤工人,嫌推煤推得太慢呢。我心生一計,弯腰鑽过煤墙洞,裝着很害怕的样儿,跑到山田跟前說:“山田先生。你看李文森的‘三宾’的給。上边推煤工都叫他打跑啦。”正好邢三也从煤墙洞里爬出来,朝我扑上来。我更有詞儿了,便說:“你看,他这不来了嗎?”
山田这儿正着急工人老是推得慢慢騰騰,煤不頂嗆呢!原来是监工的把工人全打跑了哇!山田上去,嚷道:“你的什么的干活?工人‘三宾’的給的不行。跑啦,跑啦的有!”
工人們一看有热鬧可瞧,誰不是給他加把子劲啊?都过来指着邢三喊:“都是他把人打跑的。煤才上木去。”
山田一听更急了,伸手把郉三拍、拍打了几下。邢三呆在那儿,居然委委屈屈的咧着大嘴直哭。我們看着可开心了。
是不是解解气,寻寻开心就滿足了呢?幷不滿足。誰不是窩着一肚子火在想斗爭的办法呢?有天,我們鍋爐房的一班工人,被监工的吆喝了一声,十来把鉄銑都給他撂下了。大伙七言八語的挤在一塊又扯开了,都說:“不能給他們鬼子干!得想法子啊!”
我說:“吿訴你們哥几个一点活路。人家胡头班的人,有的跑单帮,有的去賈家大桥打毛子工,一天能賺好几塊‘大棉被’票①,你們說咱們呢?”
“咱們給他外边干去,給他拆台,擱車。大伙齐心不?”
“齐心!誰要是心猿意馬,出門讓电車軋死他!”
“对,电車軋不死,来个驟車也得撞上他。哥儿們抱团,干哪!”說到这儿,大伙还对瞧了一眼,算是盟誓。
接着,我們就又拾起鉄銑,喊喝着“一、三、五、二、四”地低头干起活来。
这时候,富根大模大样从后楼走进鍋爐房。他看我們大家干活干的还起劲。这小子竟說:“干活大大的好。”說着要过一个煤鏟来,哈腰伸腿,也往爐膛里添煤,招呼大家向他学。
“干哪!干哪!加油干哪!”副班长催着大家,一边就拿大火扒扒灰。
火越燒越旺,唿唿的,連安全門都起劲了。富根咧着大嘴带笑地說:“頂好的有,頂好的有!”
“哎呀!哎呀!”乘他高兴的这时刻,我蹲在地上裝病造魔,嚷道:“厂长先生,我肚子痛,哎呀!我站不住啦。厂长讓我回去吧。”
富根这小子最会收买人心。居然叫値班的电工楊文貴到他家取藥。給了我一个藥丸,这才說:“你的回去。”
我捧着肚子出了大門。聞了聞那藥丸,一股子大烟味儿。眞他媽的会盜买人心,順手給他扔在馬路上。
次日早晨八点鐘光景,我們約好的几个工人都在电灯房东胡同集合起来。人不算多,有几个沒来的,可是一打听,进厂的只有把头和另外兩个人。工厂的大門已經上了鎖,鬼子怕沒有接班的人,把胡头那一班的人整个扣住了。总算不賴,哥儿們心齐。
我說:“好吧,咱們別在这儿等啦。这儿离厂子近,不太保险。走,先找老梁去。他大槪是讓梁大嫂拖住了脚。
我們找到了梁师付,跟着他一齐到北站打短工“卖現錢”。眞是什么鬼年月,在北站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沒碰上一个找人干活的,大家正起急呢,突然从南边开来一輛日寇抓人用的軍車。我一看来势不好,急忙招呼大家:“腿上加油,馬上走人哪!”只是腿再快,也沒有車軲轆轉的快,卡車已經停住,鬼子已經跳下車来了。逃走是来不及了。怎么办?人多智广,也不知是誰一眼看見馬路左边有輛轎車,正好机器坏了,停在那里。我們就一窩蜂的奔过去,推車便走。下来的日本鬼子干瞪了兩眼,沒敢抓人,他誤以为是坐汽車的人雇我們推車的了,不知里面坐的是什么人物,另抓別人去了。一关躱过,二关难逃,我們一看在外面干临时工是腦袋拴在褲腰帯上,也不是路。熬了八天只好硬着头皮又回到發电厂。斗爭的道路还是找不着呀!
解放了。炮火剛剛停下亲,我就从家里挖的地窖里跑出来,大踏步儿向工厂跑去。我爱人剛剛生产,只是我的心顧不上她了。再重要也沒有协助接管工厂这事儿重要了。瞧見軍代表,虽然我从来沒見过他,可我就像見了亲人似的,一面高兴,一面后悔,“如果那年在山西我跑过去,不管我爹,那我現在不曉得做了多少工作了。”
組織上也很重視我。第一次成立党課学習班,便吸收我参加。学習的內容是党員标准,党綱党章,革命史等等,对我来說,眞是有生以来头一次开窍,眼界开了,心胸大了。我这才懂得党的崇高和偉大。我的决心很足,要一輩子跟党走。
只是,我的覚悟不高,我还不能全心全意为了党,和党員的标准还有距离。过了些时候,我得了肺炎,在我病中,得到党組織上的关怀,特別是1950年电厂党支部整風,給了我很大敎育,我深深体会到党的英明和正确,所以当党在發电厂第二次吸收党員的时候,我便第一个交了志願書。不过这已是1952年了。
話还得从得病的事儿說起。病剛好,还沒有恢复健康呢,我就要求上班了。不这样作当时心里不舒服,一个工人一歇多半年,誰受得了呀?党組織怕我身体吃亏,也懂得我这迫切想要工作的心情,准我上班,但不叫我干司爐的重体力活,跟老工人耿庆祥一塊做鉗工,干些輕便活儿。耿师付是个党員,对我的关心眞是无微不至,有时連我喝水他都管。身体漸漸好了,我也要强,所以在大修13号爐的紧张工作中,我也沒有因为身体不好掉队。以后,厂內哪有工作我就到哪去打游击。下班以后,我不是进业校的門學習文化,就是进工会的門做工会工作。我是打三厂的工会一成立就担任小組长兼合理化委員的,后来就越来越多的搞起工会的工作来了。我的工作能力虽不高,当时的信念却只有一个,工人翻身了,能力低,也得好好干,好好鍛煉!
1953年的春天,党組織又調我到市委党校初級班学習。一去又是半年多。在党校放暑假的时候,我因为半輩子沒休息过,休息起来筋骨都覚得难受,便白天回厂,帮助工会搞工作。当时正是工会开展群众思想检查的阶段,很需要人手。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就抓些时間温習党校功課。晚上回到家里,因为街道上正在搞普选,我也参加了这項活动。虽然每天都很紧张,但我的心情却是十分愉快的。
从党校学習回来,組織决定叫我脫产搞工会工作,工会改选时,我被选为基層工会的副主席。光阴过的眞快,一晃我已在工会工作了七个年头了。但是,我的工作做的还有許多缺点,我要繼績努力,对于一个年輕的工人来說,这只不过是剛剛迈了第一步。
附注
①指伪币一元票。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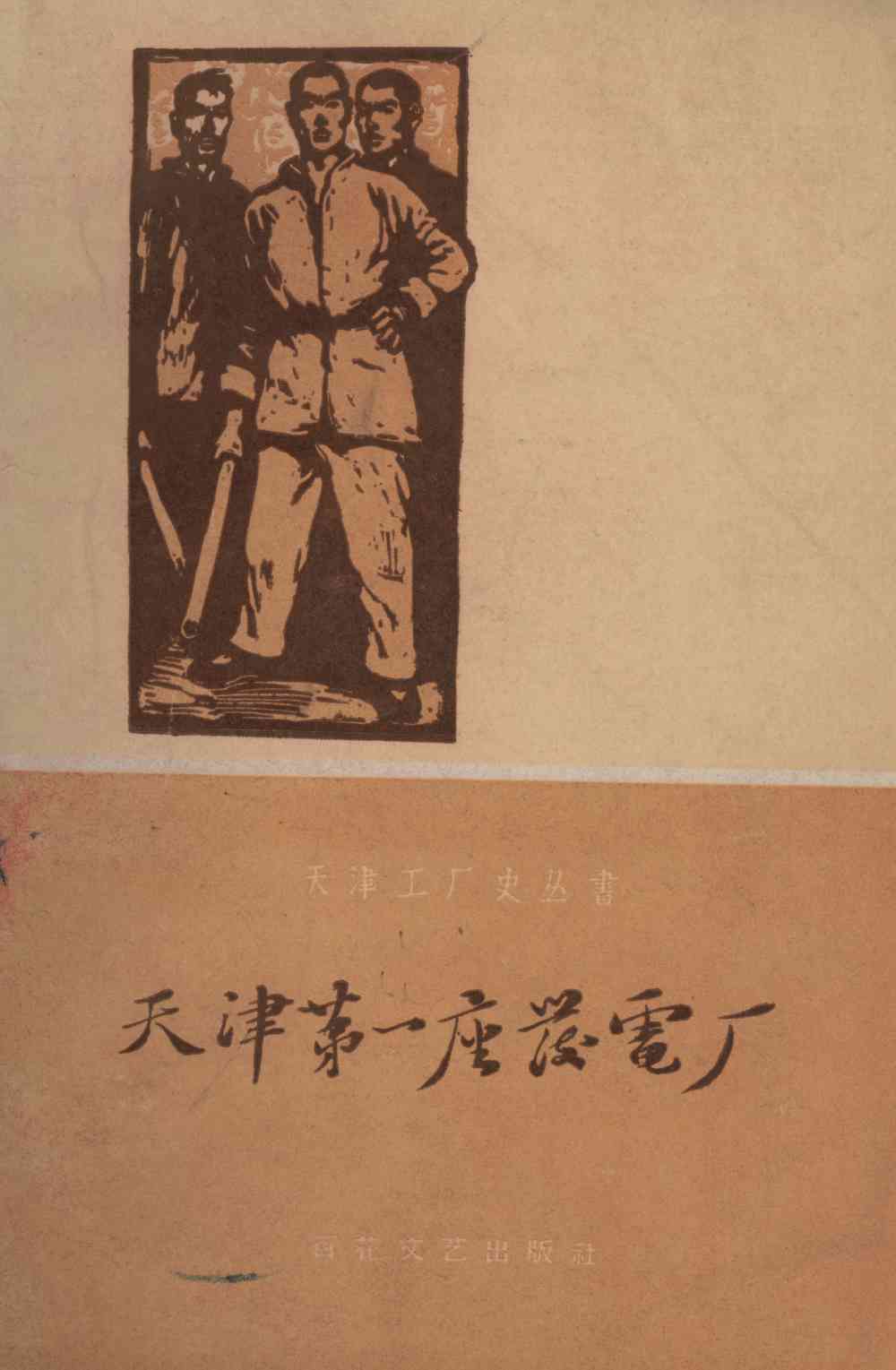
《天津第一座發電厂》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本书介绍了天津工厂史写作活动的成果和背景。该活动受到苏联先进经验的启示,在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委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和帮助下进行。工厂史写作活动鼓足了工人的干劲,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积极的、有才能的工人作者。
阅读
相关地名
天津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