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恩源
| 内容出处: | 《天津第一座發電厂》 图书 |
| 唯一号: | 020020020230026132 |
| 颗粒名称: | 于恩源 |
| 分类号: | K825 |
| 页数: | 18 |
| 页码: | 167-184 |
| 摘要: | 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于恩源在童年时期的艰苦生活和在工厂当学徒的经历。 |
| 关键词: | 于恩源 人物传略 天津市 |
内容
父亲是个沒有正式职业的流浪工人。靠卖短为生,今天車站干个零活,明天就給盖房子的当个小工。我們家人口偏偏很多,母亲一共生了我們哥八个,我是老六。賺的錢不够吃飽肚子的,成天在愁吃愁穿的过日子。
我記事的时候大約是十一二岁,三个哥哥已在工厂学徒。白給人家使喚还不行,还需要家里照顧他們的穿戴。我和四哥五哥就过流浪儿的生活,在街头找点閑活,帮助家內生活。平常是到野外坟地里打草,拾柴禾,有时候,遇上有錢人家办紅白事,我們就去打“小闊”,拿旗罗傘盖,或是打串灯。有时候,也跟着吹鼓手去敲小銅鑼,这叫当“黃梨”。白天干这个,晚上我們可以到李純祠堂里的貧民小学上兩个鐘头的不花錢的学。可惜我也沒識了几个字,一来是人家不好好敎,二来是我捫冻着餓着学,也学不不去。反正那就是替有錢人家做慈善事业,給他們賺名
誉罢了。我的第一个正式职业是到棉花棧擇棉花。到那儿,人家嫌小,把头不肯要。亏了有熟人說合,算是进去了。擇了半天,我手儿生,只擇了二斤来棉花。把头一看,說我跟他泡蘑菇,抄起竹棍子就打,把我吓的抱着腦袋跑出了棉花棧。白干了半天!
活儿很难找。正式工作是在兩年以后,我长成了半大小伙子,跟着爸爸哥哥到“电灯房”来当小工子。看見比国鬼住的那兩座考究的楼房了嗎?那都是我們一鍁一鍁地土挖下去,又一塊一塊地砖給盖起来的。我們爷几个干活干的卖力气,讓工头看中了。随后盖义国鬼子的球場,英国鬼子的跑馬場我們又都跟去了。因为有活干,哥几个都掙錢,家里这才算是顧得上嘴了。
这时节,三哥已經在一家电机厂出师了。認識人比較多,他对我的希望也大。就跟父亲說:“我現在能掙錢了,家里不用他們几个見天見都去掙現錢了。讓老六到三条石德利兴鉄工厂学徒去吧。”
学技术是好事。爸爸贊成,我也乐意。于是乐嘿嘿的跟着三哥到三条石去了。
德利兴机器厂在三条石算是数得上的大厂。光师付就有三十来位,徒弟就更多。当天按了手印,进了厂子。我三哥剛走。掌柜的就給我来了个下馬威,他說:
“于六,吿訴你,来这儿要好好干活学手艺,把师付們侍候好了。要是不啊,你可要知道家有家法,柜有柜章,厂有厂規。小心你的脊梁,屁股、腿!”看掌柜的那副凶相,再瞧瞧徒弟們那份惨样,一下子就把我弄的怵头了。我連忙应了兩声。跟着便由师付領着干活去了。
名义上是学徒,实际上学什么徒呀?拿我們当牛馬使唄。我干的是炊事員的打杂儿的工作,刷盤子洗碗。完了事再跟着师兄們裝卸生鉄,搬弄廢鉄,打扫院子。完了事再給师付們做小跑,买点心端飯泡茶。哪个师付叫,就給哪个师付干,別說干慢了,就是应慢了都打。师付們打起来是毫不留情,把当初他們受的气都使出来,他們認为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回可得显显威風了。大师兄們也打,那就純粹是拿小徒弟撒气了。
三条石是天津最早的冶金机械發源地,这儿的作坊鉄厂子如林似海,都是小本經营。那些厂主們,专一的利用小徒工,剝削的都沒了份儿。有人說拿人当牛馬使,說实在的,比牛馬都不如。牛馬不是还得讓睡够了覚嗎?我們这儿起早睡晚,一天要干上十七、八个小时的活。夜晚几十个徒弟滾在一塊睡,沒一个睡够覚的。有些徒弟惊吓得睡覚的时候鬧“梦囈”,冷丁地爬起来往院里跑,不曉得撞在那里,这才算是梦醒了,赶紧倒头再睡。一天缺覚可以,兩天也能对付,日子长了誰頂得住啊?把我們熬的都跟得了大病似的。走着走着道儿就能打盹,撞得头破血出。
在这活地獄里熬了几个月,实在熬不下去啦。这天下午,我借口要回家拿衣服向掌柜的請假,相上还眞准了半天假。天哪,我可見着太阳了。到了家,我鼻涕眼泪一齐来,抱住爹媽哭着嚷:“打死我,我也不回去了!这罪沒法受呀!”
三哥听說我不回去,气得什么似的,駡我沒出息。媽也劝我熬上四年,也就出来了。不行,說什么我也不回去。我算是吃了秤砣,鉄了心啦。
父亲知道我这罪难受,就說:“不去算啦,还是跟我干活吧!”我算是逃出了这座地獄……
1930年的春天,那年我正16岁。从三条石鉄厂子跑出来有一年了。三哥又煩人把我介紹到济南六合桅灯厂做学徒的。这家桅灯厂是当时山东省軍閥手下六大处的处长們合資办的,所以名字叫做六合。領东的經理姓焦,这小子是通过他的的小老婆和六大处的处长們的关系,才巴結上的这份差事。他的小老婆是軍閥张宗昌的姨太太。这个卖卖就是这么烏七八糟的搞起来的。可是表面看,这个厂子有錢有势,挺唬人。我去的时候,厂子剛剛建成,还沒有开工。工人也沒有招齐。徒工我是第一名。这可眞是歪打正着,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往后来的徒工,岁数比我大的也好,小的也好,通統称呼我大师哥。
厂子开工了,我被分配到机床車間做旋活。表面看,比三条石的鉄厂作坊来得新一些,骨子里可是換湯不換藥,有把头有监工,而且厂子里有規章,不許罢工怠工。对徒工,这儿倒是不用什么卖身契,可是徒弟得随叫随到,沒有工作时間,也是一干干到半宵才打住。也是不准出厂,不准請假,不准打架。厂方还特地訂制打徒工用的大板子,藤子竿做的敎鞭。还有几塊大砖是罰跪、罰站用的。我們徒工,不論那个,誰要是一天沒挨打,那算是交了好运啦。天下烏鴉一般黑。那年月,当徒工到处都是这样受折磨呀!
別瞧我做大师兄和他們一齐挨揍,可是我却不翻回手来,拿师弟們来出气。我受过苦,知道苦的滋味,大家苦还苦不够呢,怎么还能再駡师弟,再打师弟呢?我从来不打罵他們,而且遇上事总是尽量維护他們,替他們挨打!为什么这样作?当时思想幷不淸楚,現在可以分析分析这事了。这就是阶級友爱呀,我本能的要这样作。記得有一年,正是三伏天,热的人火燒火燎的,我們整天搬鉄,上車床子,澆鑄鉄活,得使多大劲,流多少汗哪?可是厨房的师付們也欺侮徒弟們,新蒸的饅头不給我們徒工們吃,专把剩下来的,长了老长毛儿的坏饅头讓我們打扫。咬一口臭味熏人,大伙掰开饅头,沒法往下咽,直翻白眼。我气往上撞,自己不吃沒什么,大伙都不能吃,我覚着我这做师哥的有点責任。便給出了个主意。把坏了的饅头都往房頂上扔,扔完了再要,要完了再扔。給他扔了个一光二淨,徒弟們就口口声声的喊着要新蒸的饅头。厨师付奇怪,怎么坏饅头都吃光了呢?就来查看,有大师哥带头,小徒弟們都上来啦。跟他吵架。
这家伙不說理,还要唬我們:“监工的来啦,你們不怕挨打嗎?你們要造反哪。”他这叫嗆火。大伙劲头儿起来啦,我也胆子壮啦,就帯头喊了一声:“打呀!”話到手到,我一手抓住他的脖領,用拳头朝他前胸来了兩下子。徒弟們跟上去了,七手八脚竟把他打倒在地。又踢又踹。
大伙的劲头更高啦,我喊了一声:“搶呀!”我們几十个徒工一窩蜂的跑进厨房,好像餓虎扑食,打开籠屜,把新蒸的饅头給搶了个精光。
还沒容我們吃完呢。有个小徒弟拚命跑来喊:“快跑呀,大监工的拿着鞭子来啦。”这一嗓子不要紧,把小徒弟們吓的炸了营,乱窜乱躱,这个监工的也是天津来的,是个流氓出身。整治我們徒弟那是又毒又狠。有好多徒弟都讓他打的發傻了。誰不是吓的藏藏躱躱呀。
他駡駡咧咧的掄起藤条鞭子朝我們乱抽乱打。我身子往后一撤,渾身一热,攔住他說:“喂喂,你別乱打人。冤有头債有主。什么事有我于恩源一人当。”
我才十六岁,看我說話这么硬气,大师哥往自己身上攬不是。把他猴嵬子气炸了肺。他丟开別的徒工揚鞭子朝我来了,咬着牙說,“我今天把你揍死!”
我也火上来了,嚷道:“来来来!今天卖給你兩下!”我拚命向他前胸撞去。
他把我揪住:“好小子,你認打認罰吧?認打,你看見我房內挂的二尺半长,寸半厚的檀木板子了沒有?老老实实挨他二十下。認罰,給我跪兩个鐘头的方砖。”
那年月,挨打不寒蠢,矮人一头跪半截身子,那才叫寒蠢呢。我不能給他下跪。說:“好吧,你打吧!”
这家伙咬紧了牙,屛住了气,掄开木板,照我后腿狠命打了十板。把我的褲子打开了花,馬上我覚着一陣針扎着的痛,屁股肿起多高。不过,我頂住了,沒哼一声。別說我挨的多痛了吧,連他打人的都累得呼呼直喘。
他歇了歇劲,喘着气和我說:“好小子,眞有骨头。打一半跪一半。去,拿兩塊砖头給我跪一个鐘点。”
嗬!我一寻思这小子和我耍手腕,攪弄我呀,打成这样,我还跪得下去么?这不是加倍的折磨我么?再說,我跪着,他歇着,有那么便宜的事么?打人还得費力气呢。我就成心气他:“咱們都是天津人,咱們說話可得算数。你說打我于恩源二十板子。你就打,打掉了屁股厌不言語一声。当着大伙的面,来来来!你打,你打吧!”
这兩句話把他僵住。腦袋一晃,扑过来,狠命又是十板子。这十板子打的更狠。皮开肉綻,血順褲角流了一地,我背过气去。后来亏师弟們把我抬回了宿舍……
一晃,在六合桅灯厂干了快二年了,光和师弟們一塊当苦力,正經的技术是半点也沒学会。一想到来的时候,父亲母亲千叮万嘱,三哥也斜眼瞧我,看我有沒有学本事的决心,我要是空着手来空着手回去,我对得住老人們的心嗎?可是,沒师付肯敎,問也白問。怎么办?凡事只怕有心人,我抓空儿就偸看师付們怎么干活,把他們操作手法一一牢記在心里。飯后,他們歇着的时候,我就悄悄溜进車間去試作。学这点本事,眞就跟做賊一样。日子长了大路活我算是差不离了。到三年头上,王师付才給一定时間,讓我上車床子摸摸活儿。可是只許我把着車头挑絲,不准自己动手卡活,他还是不敎給呀!
有一天,王师付叫我自己上輪,我沒摸过,怎么上也弄不好。气的王师付駡了我一句“笨蛋”!下边还踢了我一脚。用手把我推到一旁,伸手把輪子安上,从这儿起,再也不敎給我上輪子的活儿了。敎不敎在他,可是学不学却在我呀。我就乘他下班的时候,把輪子卸下,試着去安。安来安去,我就找着竅門了。有什么难的呀!
光靠偸艺不行。旋罗絲活怎么偸呢?旋多大罗絲需要多大数字的系数。这我可沒咒念了。我压根儿不懂数学!凑巧,主师付走了,換了一位黃师付来。这可是个老好人,五十出头的年紀,慈眉善目的,对徒弟說話从来不瞪眼。过了些日子,他和我說,“你們这些徒弟都規規矩矩的。我喜欢老老实实学手艺的孩子。有什么技术,我都敎給你們。决不往棺材里头带。”
我就跟他說了:“我沒拜过聖人,計算上一窍不通。旋什么活,自己心里沒数。”
黃师付点点头,說道:“我看你是眞心实意学本事。好吧,你明天买个紙折来。”
等我把紙折买来,几天的工夫他便給抄了滿滿一折子。旋什么活用多大数,那里面都有。这样一来,所有的旋活我都会做了。我有了本事。
看我頂起来了。經理却貪圖省倆工錢。把黃师付辞了。想不到我做徒弟的竟頂了他老师付的飯碗。怪不得人家不敎呢。旧社会逼的人和人之間得藏奸,留后手儿!这件事眞把我难受坏了。
可是,六合桅灯厂也沒有站住。經理吃私吃的太狠!連份假賬也交不出。六大股东又逼着他交賬,于是他来了个縱火自焚,好生生地从办公室里起了一把火。这一来,我們工人全都失业了。我拿了遣散費,回天津来了。
在天津,我在資本家办的全利鉄工厂当师付,一月能拿十元錢,后来漲到十二元。生活上比較安定了一些。七七事变以后就又不行了。日本鬼子进关,所有中国人办的鉄工厂都受排挤。生活难以維持,我們就辞活了。那年月,机器匠的手艺,沒有車床子是混不上吃的,万般无奈,硬着头皮到日本工厂来干活儿。
我去的那家鉄厂叫“东和”。势力不小,工人多,材料多,倉庫总是滿滿的。大伙瞧着又恨又气。再加上物价一年比一年的往上漲,逼得大家生活毫无着落。不管怎样,人总得活呀,一来二去的大伙偸上他了。我們不叫偷,大伙有句行話,叫做“捎他小日本的!”
当时厂里有个叫王錫文的。一家六口,靠他一个人那点工資怎么活呀?他就想出来一个点子,不論天晴天阴,見天見他都离不开一把破雨傘。原来这把雨傘里正好擱几根鉄棍,天天他都捎几根走。长了,日本鬼子就起了疑心,問他:“你的傘的什么有?”
王錫文沉不住气了,这一支吾不吃紧,戏法变漏,讓鬼子搶过来雨傘,把鉄棍搜出。打了他一頓不要紧,还把王錫文拴在馬路的电綫杆子上,用皮带抽。
大伙找我来了,讓我給想想法子。我一說情,那鬼子倒更冒火了,說是“白帽衙門的給!”把人送走那还了得,又去找日本掌柜的。掌柜的看我技术頂嗆,所以另眼看待一番,三說兩說的,把王錫文放下来了。白帽衙門是不送了(要送去,就得押解到日本去做劳工),可是非开除不可。开除不吃紧,事由不好找,他一家六七口,馬上就得断頓呀。那时候我們还做加活。就由我領头把包外活做罗絲的錢都給了王錫文。
王錫文走了。日本鬼是任誰也沒吓住。我們还是偸。
有天,王洪举准备把鉄棍截短,好拿出去。正用車床切鉄棍呢,讓鬼子工头一眼看見了。这工夫,我正在后边庫房里面拿材料呢,听見徒弟招呼我,連忙三步幷兩步的跑进东和的办公室。
一进去,正好鬼子田川用木棒子打老王,打一棍子問一声:“你的鉄棍子的什么干活?”
不能看着自己哥們挨打呀,我过去用手一攔,說道:“鉄棍子我的干活。他的好人。”
听說是我叫老王截鉄棍,田川把捧子放下。想不到事情竟这样完了。不光完了,掌柜的东和还把田川这小子駡了一頓,嫌他不問靑紅皂白就打人。
怎么掌柜的东和对我这么大的面子呢?兩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的技术不賴,无形中成了工人中的技术头儿,鬼子格外看待我三分;一个原因是鬼子有鬼,他也想利用我。从这起,經常他約我下飯館喝酒去。
喝着喝着酒,有回他問我:“于,你的馬車的有?”
我登时就明白了。可我故意給他打岔:“工人沒有錢,馬車的怎么有?”
“不是的!”他摆摆手,“你的外边的馬車的有。”
我赶紧問他:“你找馬車什么的干活?”
这小子憋的沒轍,說实話了。原来他也要偸。而且要和我搭伙,拉一趟有我一趟的好处。我連一秒鐘的犹豫都沒有,心里的話:“你要是偸了,还有我們穷哥們吃飯的活路嗎?”可我沒动声色,倒是点头說好,“我給办,我給办。”
这小子等了几天,看我沒办,又約我喝酒,又給我說好的。可是推了几次,这家伙也就明白了,知道我不給他办。把臉一整,老是斜眼瞪我。
鬼子心眼还不小,先来个下馬威給我瞧瞧。故意抓碴儿把王洪举开除了。这是逼我呀。我一寻思,中国人不能給他鬼子干这个,爽性我辞活吧!
从东和鉄工厂下来,我到富源鉄工厂来了。也是日本人开的厂子。机器設备比东和厂好,我用的是大車床,出活挺快。沒干了几个月,日本鬼子又看上我了。把我叫到柜房談話:“你的干活大大的好,工头的干活的有。他們通統你的管理。
什么?給鬼子当工头?我是从挨打受駡里长大的。怎么能干这个騎在工人头上的事?我当时拒絕了。
过了些日子。掌柜的富源又找着我說:“你的工头大大的好,發財大大的有!”
“我不願意發財,我願意干活。腦筋的不行。”我这回答复的更加干脆。
看我一次再次的不肯。富源这小子倒有个蔫主意。把工头的事儿暗暗扣在我腦袋上了。有天,有个工人要鑽头,富源竟把工具箱的鑰匙交給了我,讓我給他拿!
我心里可別扭透了。眞是有亏良心,做了多么对不起大伙的事。咱們是凭手上的汗換飯吃的工人,怎么能爬在穷哥們的腦袋上当工头呢?趁晌午大伙歇息,我把事儿和大伙說了。我还眞沒有这么沉不住气过。
大伙一听,出我的意外,异口同声,倒說这是一樁好事!他們講的有理:“你想啊,要是你当了工头,那不和大伙当了工头一样嗎?有什么事不就有个遮遮掩掩,事情不就好办了嗎?”
对呀!当工头看怎么当了。我的心不在他那边。由这儿起,我把工头的权限全攬过来了。工具工賬都攬在我的手心里。当天,我就給大伙开了个方便之門。出了好主意:“从今天起,鬼子不在,咱們就做包工活,鬼子来了,咱們就做日工活。”
这一来,把大伙乐坏了。干包工活的时間加多,大伙的工資全拿多了。
光这样还不解恨。从这儿起,我还不断溜进鬼子监工的屋里去給大家改工賬,将包工的印章“包字”抹下去,打上一个“日”字的印章。这样鬧,大伙更合适了,包工活按量計算,量多了,多拿錢;日工活,戳子多了,多一戳多拿一天的工資。合着我們每个人都是一日双工。鬼子讓我給他管工人,好哇,看我給他管的多好啊!就这样,我們一直胡弄鬼子,直到“八一五”他們垮台,降服。
国民党接收大員来了。富源鉄工厂为伪經济部接收。原来我是工头,于是大員們还叫我当工头。我心說我这工头不比寻常,是穷哥們的“坐探”,不是侍候你們“飞来牌”的。当工头我不干!宁可餓死也不干,我又辞活了。
朋友們介紹我到伪中紡七厂原动部来了。凭我的手艺,凭我的經历,楞給評了个三等工。三等工就三等工,反正比当工头心里还好受一些。
到了国民党办的工厂,好呀,比鬼子办的工厂还复杂,帮派橫行,到处都是把头。当时原动部的大把头叫何文甫,还有一个就是南市流氓头子××的徒弟。这兩派是大眼瞪小眼,暗地里叫劲。有天,何文甫叫我到他办公处开会。我不知是什么事就去了。
万万想不到何文甫开的是国民党的党会,把国民党布置的当前任务,大批拉攏工人扩大势力,偵察进步工人,防諜防“奸”的任务都說給大家听了,随后就說我們原动部的××是靑帮分子,不听从他的調度指揮,接着竟把我抬出来了,說是:“兄弟們,今天在这个会上我保举于恩源于师付当班长,大伙看好不好?”下面都是他养的一撥子狗,就齐声开哄,炸窩似的喊:“好嘛,好嘛!”
鬧了归齐,还是讓我当工头呀?我要当工头何必到你这儿拿一个三等工的工錢呢?当場我沒好反駁,下来我可不客气,当場謝絕了。何文甫挺不滿意,咧着大嘴說:“唉!你这就不对了,我連我們党的秘密都跟你說了,咱們有交情嘛。別客气了!于老弟,咱們好的时候还在后头呢。”
那年月,我是这么个处世哲学:占便宜的事,咱們不攬,吃亏的事咱們不干,能惹的惹,不能惹的咱們躱。不过,到底还是沒有完全躱淸,后来还是和××拜了一把子盟兄弟。我心里却始終他合不到一塊去,記得为了一丁点小事,就和××打过兩架。唉!勾心斗角,那碗飯可眞是不好吃呀!
解放战役中,棉紡七厂駐有国民党炮兵,所以満大的一个厂子都被炮火轟毁。单单留下了發电厂部份。解放以后,这部份便改为于庄發电四厂了。我这才算是正式成为电厂的修配工人,算是专做汽机保全工作了。
翻身之后,我要說的話可多了,生活变了,地位变了,思想变了,一切都变了。但从我切身来說,我覚得变得最大的还是这些:以前,我好像只会干活,可是解放后,我逐漸發現我不光会干活,而且还有时想創造、捉摸一些什么。劳动和創造,这是工人的最大特色。开初我想了一点改进、創造,这都是自然而然的那么随便一想;但是党却抓住这星星点点,又支持又鼓励。后来有了些成績,本来这些成績都应該归功于党,但居然讓我做了好几年的劳动模范。这些事迹大致是这样:
1953年在發电四厂改建水泵,評做市級劳模。
1954年在發电四厂設計上煤工具,又被評做市級劳模。
1956年發电四厂和三厂合幷,我这才調到三厂的汽机分場。三厂的設备,虽然在解放后發展得是一日千里,但在新中国的电业發展史上却早已是提都提不上的一个又小又旧的厂子了。可在我眼睛里却还是头一遭見过这么大的場面。好在是解放了,从心里有那么一股要做好,也敢做好的勇气。所以困难越大,問題越多,自己倒是越来劲儿,一年当中,有几項改进。比較突出的是創造了危急保安器,在汽机上安上这玩艺,一有事故馬上就可中断。再不会發生什么危险。这一来,电厂的安全問題,便更加有保障了。这一年,我不仅被評做劳模,而且有个报紙还記載了这些事,說我是什么千手于。使我非常不安,但也确实給了我很大鼓励。
1957年改进風泵压力簧片,縮短升压时間一分鐘,延长了寿命,还解决了运行与維修爭着用風的矛盾。过去簧片一天至少要坏一兩次,改进以后,六七个月才坏一次。为这点成績,我又被評做劳模。
1958年大搞双反运动。我是工会生产委員。必須带头上陣突破保守思想。电厂的历史比較长,机器陈旧,有些老工人的思想也陈旧,不敢突破常規,干什么都凭老經驗。这些老經驗有不少是不能适应咱們大躍进的时代了。得把它撵走,于是我們組織了一个老年机智突击队,专門負責解决疑难問題,攻打关鍵。用实际行动把老年工人的腦筋打开。在反官僚主义上,也不簡单,我們和靑工一起搜集廢料,預計要献价値黃金800兩的东西,結果完成了1000兩还多。1958年是大躍进的第一年,事情特別多,我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一樁事也發生在这一年。那就是开始制作6800瓩的發电机。
事情是这样:大躍进声中,毛主席到天津視察来了。在参覌工业展覽館时,他对电业职工指示說:“發电厂可以搞点制造。”党委根据这个英明的指示,决定利用原有的汽輪發电机的轉子,自制一台6800瓩的汽輪發电机(包括整套的附屬設备),这个重大的任务在發电厂来說,自从建厂54年以来还是头一遭。我們检修分場修配車間仅有几台皮带式的旧車床、一台小龙門刨、一台小牛头刨。十几个老年工人还身担着五台机輪發电机、十三台式样不同的鍋爐大小修任务,除此以外就是百十个靑年工人和徒工,他們之間有新从学校轉来的,有从农村来的,大部份是新工人。从制造一开始就把这个繁重而光荣的任务交給了我。我带領着一部份检修工人就开始了制造工作。通过参加工作的同志們研究,个个斗志昂揚。但是困难的关鍵問題重重出現,比如十几吨重的高、低压缸大鑄件的加工,光靠我們現有的几台小床子是啃不动的。我想我現在是一个工人提拔的工程师。困难再大也不能向困难低头,再者党交給我們这項制造任务正处在目前电网紧张,需要生产大躍进的日子里,能提前多發一度电,那就是多增加一份巨大的动力。何况我們制造的是6800瓩汽輪發电机呢?当时我就想起了党敎育我的話,有事多想想,多和群众商量,就沒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所以我就根据党的話,通过苦思和学習別厂的土洋結合的办法,提出了一个大型土立車床的草圖,找来了工程技术人員和我們一起工作多年的老工人王桂林同志共同研究。反复研究修改,一台用洋灰作成的三米八立式土車床便設計成功了。解决了大型鑄件加工的困难。
另外,在土車床加工低压缸滑动面时,遇到了沒有大立銑車床不能加工的困难,我就主动的帮助王祥瑞、王桂林兩位师付硏究出利用土立車床上加小車头,用螞蟻啃骨头的方法代替了大立銑車床。后来又听取同志們的意見,使手动进刀改为土法自动进刀,加大进刀量,同时用三把刀旋活,提高效率四倍。旋高压缸找正是一項精密細致的工作,我們沒有找正工具,針对这个困难,我又和老同志們研究,提出了“四角針点”找正法,使旋高压汽缸的任务順利完成,平面瓢偏最大在0.1公厘以內。直徑橢圓度在0.2公厘以内,不亞于制造厂的加工件。隔板槽的間隙最大差0.6公厘以內。达到合格。
党敎导我們作为一个生产战綫上的直接領导者必須經常关心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才能更好的發揮群众积極性。我在領导自制6800瓩汽輪發电机工作中遵循着这一指示,哪里有困难我就到哪里去,不分黑夜白天亲自到現場指导,多方面注意安全和質量的检查,抓住关鍵,然后找大伙商量,發揮群众智慧。群众干劲冲天,困难关鍵問題眞是手到擒来,不但在繁重的起重工作中沒發生任何事故,保証了安全,組裝也找到了一些制經驗。
1959年9月26日,在苦战八九兩个月的口号下,6800瓩發电机,最后完成了。做为向偉大的国庆十年的一項献礼,我們把捷报一直送到北京去。
这一次的制造任务給我的敎育意义很大,我現在正和伙伴們一起等待新的任务。我們正为制造一个一万瓩以上的發电机在做准备呢。
(厂史編写小組整理)
我記事的时候大約是十一二岁,三个哥哥已在工厂学徒。白給人家使喚还不行,还需要家里照顧他們的穿戴。我和四哥五哥就过流浪儿的生活,在街头找点閑活,帮助家內生活。平常是到野外坟地里打草,拾柴禾,有时候,遇上有錢人家办紅白事,我們就去打“小闊”,拿旗罗傘盖,或是打串灯。有时候,也跟着吹鼓手去敲小銅鑼,这叫当“黃梨”。白天干这个,晚上我們可以到李純祠堂里的貧民小学上兩个鐘头的不花錢的学。可惜我也沒識了几个字,一来是人家不好好敎,二来是我捫冻着餓着学,也学不不去。反正那就是替有錢人家做慈善事业,給他們賺名
誉罢了。我的第一个正式职业是到棉花棧擇棉花。到那儿,人家嫌小,把头不肯要。亏了有熟人說合,算是进去了。擇了半天,我手儿生,只擇了二斤来棉花。把头一看,說我跟他泡蘑菇,抄起竹棍子就打,把我吓的抱着腦袋跑出了棉花棧。白干了半天!
活儿很难找。正式工作是在兩年以后,我长成了半大小伙子,跟着爸爸哥哥到“电灯房”来当小工子。看見比国鬼住的那兩座考究的楼房了嗎?那都是我們一鍁一鍁地土挖下去,又一塊一塊地砖給盖起来的。我們爷几个干活干的卖力气,讓工头看中了。随后盖义国鬼子的球場,英国鬼子的跑馬場我們又都跟去了。因为有活干,哥几个都掙錢,家里这才算是顧得上嘴了。
这时节,三哥已經在一家电机厂出师了。認識人比較多,他对我的希望也大。就跟父亲說:“我現在能掙錢了,家里不用他們几个見天見都去掙現錢了。讓老六到三条石德利兴鉄工厂学徒去吧。”
学技术是好事。爸爸贊成,我也乐意。于是乐嘿嘿的跟着三哥到三条石去了。
德利兴机器厂在三条石算是数得上的大厂。光师付就有三十来位,徒弟就更多。当天按了手印,进了厂子。我三哥剛走。掌柜的就給我来了个下馬威,他說:
“于六,吿訴你,来这儿要好好干活学手艺,把师付們侍候好了。要是不啊,你可要知道家有家法,柜有柜章,厂有厂規。小心你的脊梁,屁股、腿!”看掌柜的那副凶相,再瞧瞧徒弟們那份惨样,一下子就把我弄的怵头了。我連忙应了兩声。跟着便由师付領着干活去了。
名义上是学徒,实际上学什么徒呀?拿我們当牛馬使唄。我干的是炊事員的打杂儿的工作,刷盤子洗碗。完了事再跟着师兄們裝卸生鉄,搬弄廢鉄,打扫院子。完了事再給师付們做小跑,买点心端飯泡茶。哪个师付叫,就給哪个师付干,別說干慢了,就是应慢了都打。师付們打起来是毫不留情,把当初他們受的气都使出来,他們認为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回可得显显威風了。大师兄們也打,那就純粹是拿小徒弟撒气了。
三条石是天津最早的冶金机械發源地,这儿的作坊鉄厂子如林似海,都是小本經营。那些厂主們,专一的利用小徒工,剝削的都沒了份儿。有人說拿人当牛馬使,說实在的,比牛馬都不如。牛馬不是还得讓睡够了覚嗎?我們这儿起早睡晚,一天要干上十七、八个小时的活。夜晚几十个徒弟滾在一塊睡,沒一个睡够覚的。有些徒弟惊吓得睡覚的时候鬧“梦囈”,冷丁地爬起来往院里跑,不曉得撞在那里,这才算是梦醒了,赶紧倒头再睡。一天缺覚可以,兩天也能对付,日子长了誰頂得住啊?把我們熬的都跟得了大病似的。走着走着道儿就能打盹,撞得头破血出。
在这活地獄里熬了几个月,实在熬不下去啦。这天下午,我借口要回家拿衣服向掌柜的請假,相上还眞准了半天假。天哪,我可見着太阳了。到了家,我鼻涕眼泪一齐来,抱住爹媽哭着嚷:“打死我,我也不回去了!这罪沒法受呀!”
三哥听說我不回去,气得什么似的,駡我沒出息。媽也劝我熬上四年,也就出来了。不行,說什么我也不回去。我算是吃了秤砣,鉄了心啦。
父亲知道我这罪难受,就說:“不去算啦,还是跟我干活吧!”我算是逃出了这座地獄……
1930年的春天,那年我正16岁。从三条石鉄厂子跑出来有一年了。三哥又煩人把我介紹到济南六合桅灯厂做学徒的。这家桅灯厂是当时山东省軍閥手下六大处的处长們合資办的,所以名字叫做六合。領东的經理姓焦,这小子是通过他的的小老婆和六大处的处长們的关系,才巴結上的这份差事。他的小老婆是軍閥张宗昌的姨太太。这个卖卖就是这么烏七八糟的搞起来的。可是表面看,这个厂子有錢有势,挺唬人。我去的时候,厂子剛剛建成,还沒有开工。工人也沒有招齐。徒工我是第一名。这可眞是歪打正着,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往后来的徒工,岁数比我大的也好,小的也好,通統称呼我大师哥。
厂子开工了,我被分配到机床車間做旋活。表面看,比三条石的鉄厂作坊来得新一些,骨子里可是換湯不換藥,有把头有监工,而且厂子里有規章,不許罢工怠工。对徒工,这儿倒是不用什么卖身契,可是徒弟得随叫随到,沒有工作时間,也是一干干到半宵才打住。也是不准出厂,不准請假,不准打架。厂方还特地訂制打徒工用的大板子,藤子竿做的敎鞭。还有几塊大砖是罰跪、罰站用的。我們徒工,不論那个,誰要是一天沒挨打,那算是交了好运啦。天下烏鴉一般黑。那年月,当徒工到处都是这样受折磨呀!
別瞧我做大师兄和他們一齐挨揍,可是我却不翻回手来,拿师弟們来出气。我受过苦,知道苦的滋味,大家苦还苦不够呢,怎么还能再駡师弟,再打师弟呢?我从来不打罵他們,而且遇上事总是尽量維护他們,替他們挨打!为什么这样作?当时思想幷不淸楚,現在可以分析分析这事了。这就是阶級友爱呀,我本能的要这样作。記得有一年,正是三伏天,热的人火燒火燎的,我們整天搬鉄,上車床子,澆鑄鉄活,得使多大劲,流多少汗哪?可是厨房的师付們也欺侮徒弟們,新蒸的饅头不給我們徒工們吃,专把剩下来的,长了老长毛儿的坏饅头讓我們打扫。咬一口臭味熏人,大伙掰开饅头,沒法往下咽,直翻白眼。我气往上撞,自己不吃沒什么,大伙都不能吃,我覚着我这做师哥的有点責任。便給出了个主意。把坏了的饅头都往房頂上扔,扔完了再要,要完了再扔。給他扔了个一光二淨,徒弟們就口口声声的喊着要新蒸的饅头。厨师付奇怪,怎么坏饅头都吃光了呢?就来查看,有大师哥带头,小徒弟們都上来啦。跟他吵架。
这家伙不說理,还要唬我們:“监工的来啦,你們不怕挨打嗎?你們要造反哪。”他这叫嗆火。大伙劲头儿起来啦,我也胆子壮啦,就帯头喊了一声:“打呀!”話到手到,我一手抓住他的脖領,用拳头朝他前胸来了兩下子。徒弟們跟上去了,七手八脚竟把他打倒在地。又踢又踹。
大伙的劲头更高啦,我喊了一声:“搶呀!”我們几十个徒工一窩蜂的跑进厨房,好像餓虎扑食,打开籠屜,把新蒸的饅头給搶了个精光。
还沒容我們吃完呢。有个小徒弟拚命跑来喊:“快跑呀,大监工的拿着鞭子来啦。”这一嗓子不要紧,把小徒弟們吓的炸了营,乱窜乱躱,这个监工的也是天津来的,是个流氓出身。整治我們徒弟那是又毒又狠。有好多徒弟都讓他打的發傻了。誰不是吓的藏藏躱躱呀。
他駡駡咧咧的掄起藤条鞭子朝我們乱抽乱打。我身子往后一撤,渾身一热,攔住他說:“喂喂,你別乱打人。冤有头債有主。什么事有我于恩源一人当。”
我才十六岁,看我說話这么硬气,大师哥往自己身上攬不是。把他猴嵬子气炸了肺。他丟开別的徒工揚鞭子朝我来了,咬着牙說,“我今天把你揍死!”
我也火上来了,嚷道:“来来来!今天卖給你兩下!”我拚命向他前胸撞去。
他把我揪住:“好小子,你認打認罰吧?認打,你看見我房內挂的二尺半长,寸半厚的檀木板子了沒有?老老实实挨他二十下。認罰,給我跪兩个鐘头的方砖。”
那年月,挨打不寒蠢,矮人一头跪半截身子,那才叫寒蠢呢。我不能給他下跪。說:“好吧,你打吧!”
这家伙咬紧了牙,屛住了气,掄开木板,照我后腿狠命打了十板。把我的褲子打开了花,馬上我覚着一陣針扎着的痛,屁股肿起多高。不过,我頂住了,沒哼一声。別說我挨的多痛了吧,連他打人的都累得呼呼直喘。
他歇了歇劲,喘着气和我說:“好小子,眞有骨头。打一半跪一半。去,拿兩塊砖头給我跪一个鐘点。”
嗬!我一寻思这小子和我耍手腕,攪弄我呀,打成这样,我还跪得下去么?这不是加倍的折磨我么?再說,我跪着,他歇着,有那么便宜的事么?打人还得費力气呢。我就成心气他:“咱們都是天津人,咱們說話可得算数。你說打我于恩源二十板子。你就打,打掉了屁股厌不言語一声。当着大伙的面,来来来!你打,你打吧!”
这兩句話把他僵住。腦袋一晃,扑过来,狠命又是十板子。这十板子打的更狠。皮开肉綻,血順褲角流了一地,我背过气去。后来亏师弟們把我抬回了宿舍……
一晃,在六合桅灯厂干了快二年了,光和师弟們一塊当苦力,正經的技术是半点也沒学会。一想到来的时候,父亲母亲千叮万嘱,三哥也斜眼瞧我,看我有沒有学本事的决心,我要是空着手来空着手回去,我对得住老人們的心嗎?可是,沒师付肯敎,問也白問。怎么办?凡事只怕有心人,我抓空儿就偸看师付們怎么干活,把他們操作手法一一牢記在心里。飯后,他們歇着的时候,我就悄悄溜进車間去試作。学这点本事,眞就跟做賊一样。日子长了大路活我算是差不离了。到三年头上,王师付才給一定时間,讓我上車床子摸摸活儿。可是只許我把着車头挑絲,不准自己动手卡活,他还是不敎給呀!
有一天,王师付叫我自己上輪,我沒摸过,怎么上也弄不好。气的王师付駡了我一句“笨蛋”!下边还踢了我一脚。用手把我推到一旁,伸手把輪子安上,从这儿起,再也不敎給我上輪子的活儿了。敎不敎在他,可是学不学却在我呀。我就乘他下班的时候,把輪子卸下,試着去安。安来安去,我就找着竅門了。有什么难的呀!
光靠偸艺不行。旋罗絲活怎么偸呢?旋多大罗絲需要多大数字的系数。这我可沒咒念了。我压根儿不懂数学!凑巧,主师付走了,換了一位黃师付来。这可是个老好人,五十出头的年紀,慈眉善目的,对徒弟說話从来不瞪眼。过了些日子,他和我說,“你們这些徒弟都規規矩矩的。我喜欢老老实实学手艺的孩子。有什么技术,我都敎給你們。决不往棺材里头带。”
我就跟他說了:“我沒拜过聖人,計算上一窍不通。旋什么活,自己心里沒数。”
黃师付点点头,說道:“我看你是眞心实意学本事。好吧,你明天买个紙折来。”
等我把紙折买来,几天的工夫他便給抄了滿滿一折子。旋什么活用多大数,那里面都有。这样一来,所有的旋活我都会做了。我有了本事。
看我頂起来了。經理却貪圖省倆工錢。把黃师付辞了。想不到我做徒弟的竟頂了他老师付的飯碗。怪不得人家不敎呢。旧社会逼的人和人之間得藏奸,留后手儿!这件事眞把我难受坏了。
可是,六合桅灯厂也沒有站住。經理吃私吃的太狠!連份假賬也交不出。六大股东又逼着他交賬,于是他来了个縱火自焚,好生生地从办公室里起了一把火。这一来,我們工人全都失业了。我拿了遣散費,回天津来了。
在天津,我在資本家办的全利鉄工厂当师付,一月能拿十元錢,后来漲到十二元。生活上比較安定了一些。七七事变以后就又不行了。日本鬼子进关,所有中国人办的鉄工厂都受排挤。生活难以維持,我們就辞活了。那年月,机器匠的手艺,沒有車床子是混不上吃的,万般无奈,硬着头皮到日本工厂来干活儿。
我去的那家鉄厂叫“东和”。势力不小,工人多,材料多,倉庫总是滿滿的。大伙瞧着又恨又气。再加上物价一年比一年的往上漲,逼得大家生活毫无着落。不管怎样,人总得活呀,一来二去的大伙偸上他了。我們不叫偷,大伙有句行話,叫做“捎他小日本的!”
当时厂里有个叫王錫文的。一家六口,靠他一个人那点工資怎么活呀?他就想出来一个点子,不論天晴天阴,見天見他都离不开一把破雨傘。原来这把雨傘里正好擱几根鉄棍,天天他都捎几根走。长了,日本鬼子就起了疑心,問他:“你的傘的什么有?”
王錫文沉不住气了,这一支吾不吃紧,戏法变漏,讓鬼子搶过来雨傘,把鉄棍搜出。打了他一頓不要紧,还把王錫文拴在馬路的电綫杆子上,用皮带抽。
大伙找我来了,讓我給想想法子。我一說情,那鬼子倒更冒火了,說是“白帽衙門的給!”把人送走那还了得,又去找日本掌柜的。掌柜的看我技术頂嗆,所以另眼看待一番,三說兩說的,把王錫文放下来了。白帽衙門是不送了(要送去,就得押解到日本去做劳工),可是非开除不可。开除不吃紧,事由不好找,他一家六七口,馬上就得断頓呀。那时候我們还做加活。就由我領头把包外活做罗絲的錢都給了王錫文。
王錫文走了。日本鬼是任誰也沒吓住。我們还是偸。
有天,王洪举准备把鉄棍截短,好拿出去。正用車床切鉄棍呢,讓鬼子工头一眼看見了。这工夫,我正在后边庫房里面拿材料呢,听見徒弟招呼我,連忙三步幷兩步的跑进东和的办公室。
一进去,正好鬼子田川用木棒子打老王,打一棍子問一声:“你的鉄棍子的什么干活?”
不能看着自己哥們挨打呀,我过去用手一攔,說道:“鉄棍子我的干活。他的好人。”
听說是我叫老王截鉄棍,田川把捧子放下。想不到事情竟这样完了。不光完了,掌柜的东和还把田川这小子駡了一頓,嫌他不問靑紅皂白就打人。
怎么掌柜的东和对我这么大的面子呢?兩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的技术不賴,无形中成了工人中的技术头儿,鬼子格外看待我三分;一个原因是鬼子有鬼,他也想利用我。从这起,經常他約我下飯館喝酒去。
喝着喝着酒,有回他問我:“于,你的馬車的有?”
我登时就明白了。可我故意給他打岔:“工人沒有錢,馬車的怎么有?”
“不是的!”他摆摆手,“你的外边的馬車的有。”
我赶紧問他:“你找馬車什么的干活?”
这小子憋的沒轍,說实話了。原来他也要偸。而且要和我搭伙,拉一趟有我一趟的好处。我連一秒鐘的犹豫都沒有,心里的話:“你要是偸了,还有我們穷哥們吃飯的活路嗎?”可我沒动声色,倒是点头說好,“我給办,我給办。”
这小子等了几天,看我沒办,又約我喝酒,又給我說好的。可是推了几次,这家伙也就明白了,知道我不給他办。把臉一整,老是斜眼瞪我。
鬼子心眼还不小,先来个下馬威給我瞧瞧。故意抓碴儿把王洪举开除了。这是逼我呀。我一寻思,中国人不能給他鬼子干这个,爽性我辞活吧!
从东和鉄工厂下来,我到富源鉄工厂来了。也是日本人开的厂子。机器設备比东和厂好,我用的是大車床,出活挺快。沒干了几个月,日本鬼子又看上我了。把我叫到柜房談話:“你的干活大大的好,工头的干活的有。他們通統你的管理。
什么?給鬼子当工头?我是从挨打受駡里长大的。怎么能干这个騎在工人头上的事?我当时拒絕了。
过了些日子。掌柜的富源又找着我說:“你的工头大大的好,發財大大的有!”
“我不願意發財,我願意干活。腦筋的不行。”我这回答复的更加干脆。
看我一次再次的不肯。富源这小子倒有个蔫主意。把工头的事儿暗暗扣在我腦袋上了。有天,有个工人要鑽头,富源竟把工具箱的鑰匙交給了我,讓我給他拿!
我心里可別扭透了。眞是有亏良心,做了多么对不起大伙的事。咱們是凭手上的汗換飯吃的工人,怎么能爬在穷哥們的腦袋上当工头呢?趁晌午大伙歇息,我把事儿和大伙說了。我还眞沒有这么沉不住气过。
大伙一听,出我的意外,异口同声,倒說这是一樁好事!他們講的有理:“你想啊,要是你当了工头,那不和大伙当了工头一样嗎?有什么事不就有个遮遮掩掩,事情不就好办了嗎?”
对呀!当工头看怎么当了。我的心不在他那边。由这儿起,我把工头的权限全攬过来了。工具工賬都攬在我的手心里。当天,我就給大伙开了个方便之門。出了好主意:“从今天起,鬼子不在,咱們就做包工活,鬼子来了,咱們就做日工活。”
这一来,把大伙乐坏了。干包工活的时間加多,大伙的工資全拿多了。
光这样还不解恨。从这儿起,我还不断溜进鬼子监工的屋里去給大家改工賬,将包工的印章“包字”抹下去,打上一个“日”字的印章。这样鬧,大伙更合适了,包工活按量計算,量多了,多拿錢;日工活,戳子多了,多一戳多拿一天的工資。合着我們每个人都是一日双工。鬼子讓我給他管工人,好哇,看我給他管的多好啊!就这样,我們一直胡弄鬼子,直到“八一五”他們垮台,降服。
国民党接收大員来了。富源鉄工厂为伪經济部接收。原来我是工头,于是大員們还叫我当工头。我心說我这工头不比寻常,是穷哥們的“坐探”,不是侍候你們“飞来牌”的。当工头我不干!宁可餓死也不干,我又辞活了。
朋友們介紹我到伪中紡七厂原动部来了。凭我的手艺,凭我的經历,楞給評了个三等工。三等工就三等工,反正比当工头心里还好受一些。
到了国民党办的工厂,好呀,比鬼子办的工厂还复杂,帮派橫行,到处都是把头。当时原动部的大把头叫何文甫,还有一个就是南市流氓头子××的徒弟。这兩派是大眼瞪小眼,暗地里叫劲。有天,何文甫叫我到他办公处开会。我不知是什么事就去了。
万万想不到何文甫开的是国民党的党会,把国民党布置的当前任务,大批拉攏工人扩大势力,偵察进步工人,防諜防“奸”的任务都說給大家听了,随后就說我們原动部的××是靑帮分子,不听从他的調度指揮,接着竟把我抬出来了,說是:“兄弟們,今天在这个会上我保举于恩源于师付当班长,大伙看好不好?”下面都是他养的一撥子狗,就齐声开哄,炸窩似的喊:“好嘛,好嘛!”
鬧了归齐,还是讓我当工头呀?我要当工头何必到你这儿拿一个三等工的工錢呢?当場我沒好反駁,下来我可不客气,当場謝絕了。何文甫挺不滿意,咧着大嘴說:“唉!你这就不对了,我連我們党的秘密都跟你說了,咱們有交情嘛。別客气了!于老弟,咱們好的时候还在后头呢。”
那年月,我是这么个处世哲学:占便宜的事,咱們不攬,吃亏的事咱們不干,能惹的惹,不能惹的咱們躱。不过,到底还是沒有完全躱淸,后来还是和××拜了一把子盟兄弟。我心里却始終他合不到一塊去,記得为了一丁点小事,就和××打过兩架。唉!勾心斗角,那碗飯可眞是不好吃呀!
解放战役中,棉紡七厂駐有国民党炮兵,所以満大的一个厂子都被炮火轟毁。单单留下了發电厂部份。解放以后,这部份便改为于庄發电四厂了。我这才算是正式成为电厂的修配工人,算是专做汽机保全工作了。
翻身之后,我要說的話可多了,生活变了,地位变了,思想变了,一切都变了。但从我切身来說,我覚得变得最大的还是这些:以前,我好像只会干活,可是解放后,我逐漸發現我不光会干活,而且还有时想創造、捉摸一些什么。劳动和創造,这是工人的最大特色。开初我想了一点改进、創造,这都是自然而然的那么随便一想;但是党却抓住这星星点点,又支持又鼓励。后来有了些成績,本来这些成績都应該归功于党,但居然讓我做了好几年的劳动模范。这些事迹大致是这样:
1953年在發电四厂改建水泵,評做市級劳模。
1954年在發电四厂設計上煤工具,又被評做市級劳模。
1956年發电四厂和三厂合幷,我这才調到三厂的汽机分場。三厂的設备,虽然在解放后發展得是一日千里,但在新中国的电业發展史上却早已是提都提不上的一个又小又旧的厂子了。可在我眼睛里却还是头一遭見过这么大的場面。好在是解放了,从心里有那么一股要做好,也敢做好的勇气。所以困难越大,問題越多,自己倒是越来劲儿,一年当中,有几項改进。比較突出的是創造了危急保安器,在汽机上安上这玩艺,一有事故馬上就可中断。再不会發生什么危险。这一来,电厂的安全問題,便更加有保障了。这一年,我不仅被評做劳模,而且有个报紙还記載了这些事,說我是什么千手于。使我非常不安,但也确实給了我很大鼓励。
1957年改进風泵压力簧片,縮短升压时間一分鐘,延长了寿命,还解决了运行与維修爭着用風的矛盾。过去簧片一天至少要坏一兩次,改进以后,六七个月才坏一次。为这点成績,我又被評做劳模。
1958年大搞双反运动。我是工会生产委員。必須带头上陣突破保守思想。电厂的历史比較长,机器陈旧,有些老工人的思想也陈旧,不敢突破常規,干什么都凭老經驗。这些老經驗有不少是不能适应咱們大躍进的时代了。得把它撵走,于是我們組織了一个老年机智突击队,专門負責解决疑难問題,攻打关鍵。用实际行动把老年工人的腦筋打开。在反官僚主义上,也不簡单,我們和靑工一起搜集廢料,預計要献价値黃金800兩的东西,結果完成了1000兩还多。1958年是大躍进的第一年,事情特別多,我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一樁事也發生在这一年。那就是开始制作6800瓩的發电机。
事情是这样:大躍进声中,毛主席到天津視察来了。在参覌工业展覽館时,他对电业职工指示說:“發电厂可以搞点制造。”党委根据这个英明的指示,决定利用原有的汽輪發电机的轉子,自制一台6800瓩的汽輪發电机(包括整套的附屬設备),这个重大的任务在發电厂来說,自从建厂54年以来还是头一遭。我們检修分場修配車間仅有几台皮带式的旧車床、一台小龙門刨、一台小牛头刨。十几个老年工人还身担着五台机輪發电机、十三台式样不同的鍋爐大小修任务,除此以外就是百十个靑年工人和徒工,他們之間有新从学校轉来的,有从农村来的,大部份是新工人。从制造一开始就把这个繁重而光荣的任务交給了我。我带領着一部份检修工人就开始了制造工作。通过参加工作的同志們研究,个个斗志昂揚。但是困难的关鍵問題重重出現,比如十几吨重的高、低压缸大鑄件的加工,光靠我們現有的几台小床子是啃不动的。我想我現在是一个工人提拔的工程师。困难再大也不能向困难低头,再者党交給我們这項制造任务正处在目前电网紧张,需要生产大躍进的日子里,能提前多發一度电,那就是多增加一份巨大的动力。何况我們制造的是6800瓩汽輪發电机呢?当时我就想起了党敎育我的話,有事多想想,多和群众商量,就沒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所以我就根据党的話,通过苦思和学習別厂的土洋結合的办法,提出了一个大型土立車床的草圖,找来了工程技术人員和我們一起工作多年的老工人王桂林同志共同研究。反复研究修改,一台用洋灰作成的三米八立式土車床便設計成功了。解决了大型鑄件加工的困难。
另外,在土車床加工低压缸滑动面时,遇到了沒有大立銑車床不能加工的困难,我就主动的帮助王祥瑞、王桂林兩位师付硏究出利用土立車床上加小車头,用螞蟻啃骨头的方法代替了大立銑車床。后来又听取同志們的意見,使手动进刀改为土法自动进刀,加大进刀量,同时用三把刀旋活,提高效率四倍。旋高压缸找正是一項精密細致的工作,我們沒有找正工具,針对这个困难,我又和老同志們研究,提出了“四角針点”找正法,使旋高压汽缸的任务順利完成,平面瓢偏最大在0.1公厘以內。直徑橢圓度在0.2公厘以内,不亞于制造厂的加工件。隔板槽的間隙最大差0.6公厘以內。达到合格。
党敎导我們作为一个生产战綫上的直接領导者必須經常关心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才能更好的發揮群众积極性。我在領导自制6800瓩汽輪發电机工作中遵循着这一指示,哪里有困难我就到哪里去,不分黑夜白天亲自到現場指导,多方面注意安全和質量的检查,抓住关鍵,然后找大伙商量,發揮群众智慧。群众干劲冲天,困难关鍵問題眞是手到擒来,不但在繁重的起重工作中沒發生任何事故,保証了安全,組裝也找到了一些制經驗。
1959年9月26日,在苦战八九兩个月的口号下,6800瓩發电机,最后完成了。做为向偉大的国庆十年的一項献礼,我們把捷报一直送到北京去。
这一次的制造任务給我的敎育意义很大,我現在正和伙伴們一起等待新的任务。我們正为制造一个一万瓩以上的發电机在做准备呢。
(厂史編写小組整理)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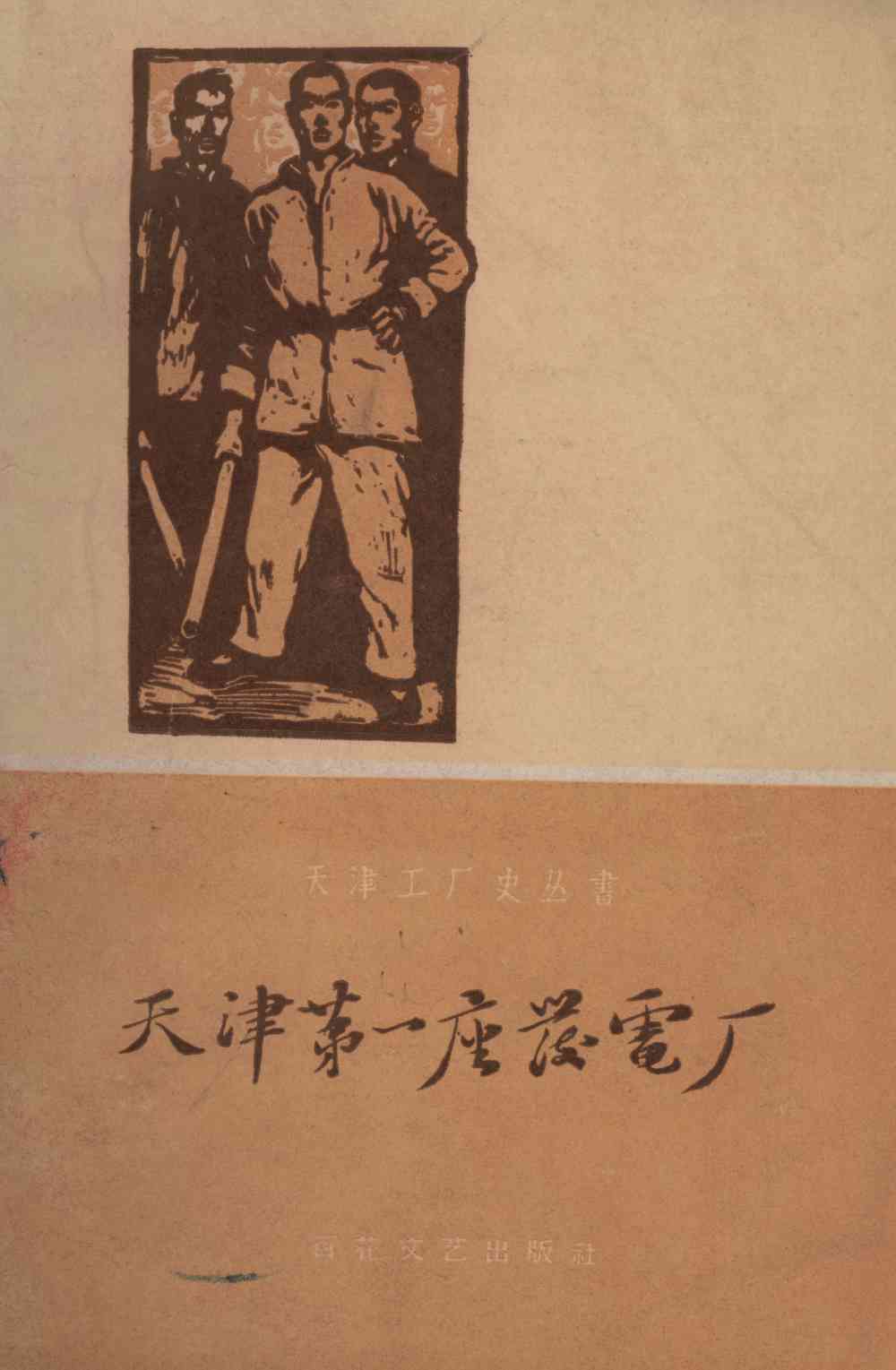
《天津第一座發電厂》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本书介绍了天津工厂史写作活动的成果和背景。该活动受到苏联先进经验的启示,在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委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和帮助下进行。工厂史写作活动鼓足了工人的干劲,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积极的、有才能的工人作者。
阅读
相关机构
相关地名
天津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