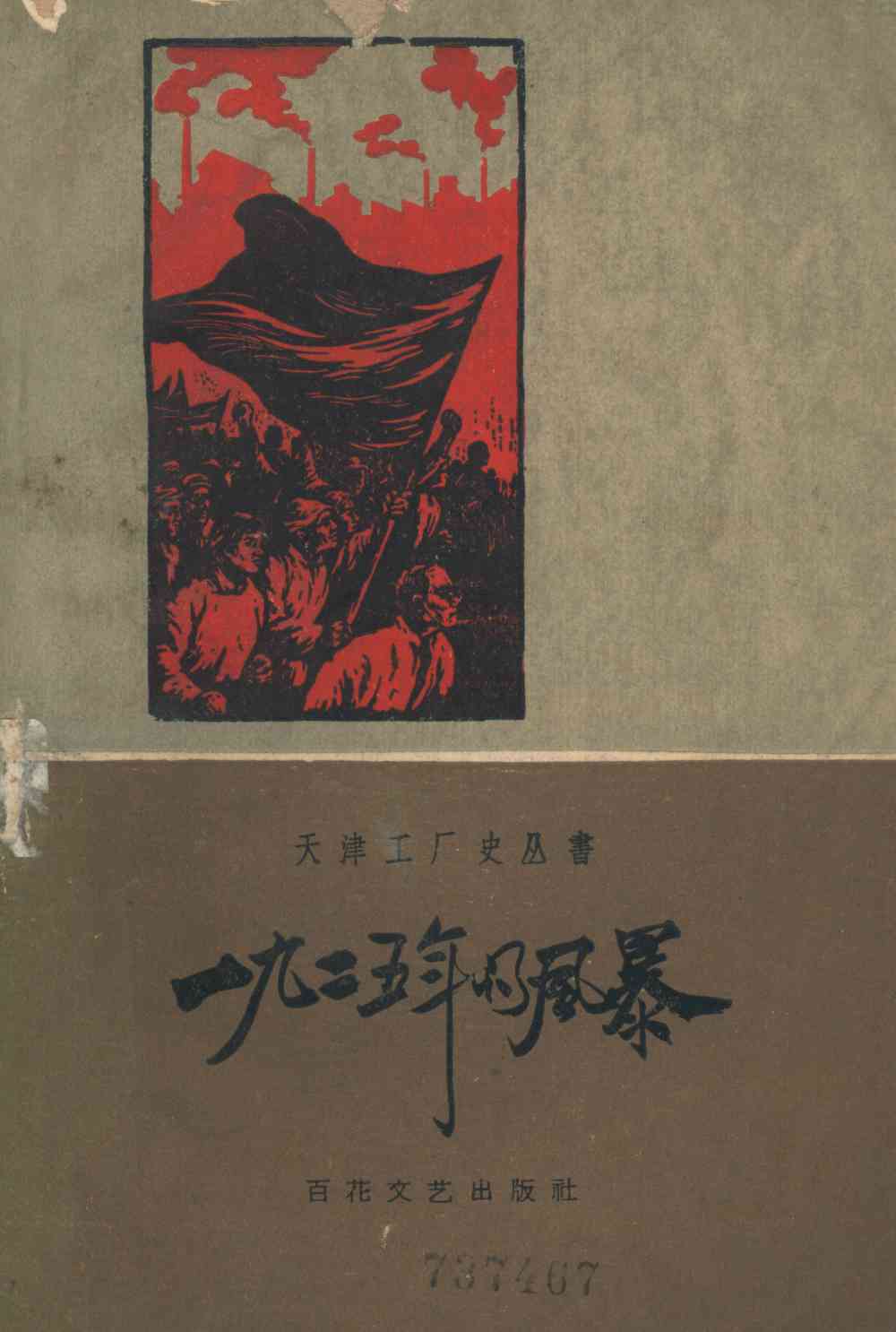内容
別看我現在是紗場乙班的班主席,又是个共产党員,可是十几年以前,在黑暗的日子里,我陈宝树却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
三十七年以前,我出生在文安县的一个村庄里,那时全家四口人:奶奶、父亲、母亲和我,一家子就靠一亩半坟地生活。文安地势不好,差不多年年閙水灾,一閙灾就沒得吃。为了活着,父亲扛过河壩,当过“华工”。媽媽給闊人家当过老媽子。九岁那年,家里又添了一口人——一个少爷沒娘的小閨女,媽媽可憐她流离失所,宁肯自己少吃一口,把她收养了,当作童养媳。
連年水灾,在家乡越过越沒活路,听人說天津工厂多,穷人家无論大人小孩都可以混口吃的。父亲和媽媽信以为眞,就把地卖了,带着一家老小来到天津。到了天津,父亲还到河壩上扛活,又托人介紹,把我和那小閨女送到宝成紗厂(現在的棉紡三厂)当学徒。那时当学徒,整天挨打受气,还不掙錢,父亲又只能养活自己。实指望上了工吃碗飽飯,沒料到生活更苦了。日子不多,奶奶就活活的餓死了,父亲跟着外招工的走了。剩下媽媽守着一帮孩子(那时我又有了兩个弟弟),整天地哭奶奶、哭日子。有一天,媽媽忽然沒了,我到处去找,閙半天她老人家在乱葬崗上哭我死去的奶奶哩。我过去拉着母亲的衣服說:“媽,咱走吧!儿子学徒养活不了你,討着要着也养活你!”第二天,我就不到宝成上工了,和一群小叫化子走遍了天津市去要飯。
可也不能总要飯呀,十二岁那年,我又到北洋紗厂去学徒。好容易学会了接头,又受当头的剝削。比如,我看十九塊板(每塊板有六个錠子),可是拿十四塊板的工錢,那五塊板的錢被搖車的裝到自己腰包里去啦!那个年月,只得吃哑巴亏,要是把把实惹翻了,更得吃苦头。尽管忍气吞声,也断不了受气。有时,接头馒头那个搖車的女把头就端着大碗凉水,照着我的腦袋澆,我剛要抬手擦,她又是一毛棍把我的手打下去。咱穷也不能总受这个呀!一賭气給他娘的撂了台。
我16岁那年,正是日本統治时期,我和一帮要飯的孩子到日本倉庫里挑砖、打滓灰活。天下的老鴰一般黑,在这里除同样受工头的剝削,还挨日本人的揍,有一次,有三个穷哥們,实在餓不过了,偸了鬼子几塊餅干吃,日本人为了追查这三个人,把我們打得死去活来。可大伙鉄了心,認可挨揍,也不叫工患难的穷哥們遭难。晚上,我遍体鱗伤,連爬带走地回到家,媽媽見了,忍不住痛哭起来。
为了全家生活,轉年媽媽也到裕大(現在棉紡三厂)倒綫,我又到中山鋼厂(現在天津鋼厂)作了拔絲工。虽然全家三口人上工,还总是飢一頓飽一頓,有时就光吃拾来的爛菜帮子。一連好几年,我就是这样整天当“苦力”,整天吃不飽飯。
二十一岁我上裕大紗厂鍋爐房抬煤去。每月才掙五十五斤杂粮,这些杂粮除了山芋干、杂合面,就是四分之一的老玉米面。媽媽由于餓伤再加上累,得了喘病,被厂方开除了。家里的生活全靠我和我那老婆(我們在灶炕里拜了个天地,就結婚了)維持。說起我那老婆来,眞是个可憐的好人儿。她从九岁开始,就在宝成紗厂上工,小小的年紀,天天站着干十二个鐘头的活儿,骨头嫩,累成了罗圈腿,連走路都困难,每天媽媽和弟弟架着她去上班。到了車間还得挨打受气。就这样,她总是把杂合面、老玉米面留給媽媽弟弟吃,自己只吃山芋干。我心疼她,就省下杂合面餑餑給她吃。那时候,我一天抬十二小时的煤,一筐煤二百八十斤,兩个人一天抬三百多筐,你想想,得付出多大的劳动力啊!为了叫家里的人們吃得飽些,我干完十二个小时的累活,回到家,抄起扁担又到中山鋼厂抬煤、挑砖去。黑間白日地連軸轉,干着牛馬不如的累活,右肩起了一个大包,又紅又肿,扁担一压,膿包里就流血流膿。
就这样,我沒歇过一天工,因为人一歇工,牙也得歇工。有一次,因为累,肚里又沒食,眼前一冒金星,就暈倒了。
常言道:“人急造反,狗急跳墙”,当牛当馬还閑着半挂腸子,还眼睜的瞅着全家人忍飢挨餓,我可就豁出去,我想:“要活下去,在这个年月傻干可不行,一定要‘偸’,对,‘偸’!狠狠地‘偸’他們!为什么他們能活我不能活?”于是就找和我一塊抬煤的胡廷琴去商量。那天,他們全家老小正捧着草籽(是一种野菜,用这种东西磨成的面粉沒粘性,發散,所以用手捧着吃)餑餑吃,看看炕上連个枕头也沒有,我可就說了:“老胡啊!咱倆找点(外快)吧!老这样,忍到多咱是头呀!”沒想到老胡也憋着劲要“偸”哩,沒費口舌,我們倆就成同伙了。
这天黑夜,我二人爬上大場的太平鉄梯,奔天窗撕下防空帘里子(防空帘是双層的,里層是紅色,外層是黑色),繃在棉袄上肩里,就越墙走了。过了兩天,我們留神一看,不知什么时候,防空帘又添上新的里子了。任何动靜也沒有,我們暗暗發笑,心說鬼子眞孝順,又把肥肉送到咱爷們嘴头上来啦!胆子大起来,我們索性拿起整塊的来。
又是一天深夜,我倆把摘下来的防空帘捆了兩綑,用紗錠带子纏着,順着河沿大墻走。一慌张,“噗喳”一声,連人带布滾到河里去,水齐着脖子,河面还有一層薄冰,我二人不上不下的給卡在那儿了,一个劲打扑通,好不难受。好容易我踩着老胡的肩膀爬上来,老胡把防空帘投給我,我又把紗錠带子遞到老胡手中,把他从河里系上来。我們手忙脚乱地把这些事情剛剛办完,远远的来了巡邏的,我倆急忙跳到大墙里,用爐灰渣埋起防空帘,就溜回家去了。轉天下班回家,我正躺在炕上睡覚,听見工房弄当里紛紛傳說:“今天到厂里拾煤核儿的老婆儿和小孩儿們好运气,在煤灰渣里撿了一大捆布,一人鬧了一塊!”我想:这也很好,老婆儿和小孩儿們的身上补釘罗补釘,淨露着肉,也应該閙件新褂子穿穿了。
說句迷信話,那时候,我二人眞有点“賊星照命”,成天价滿腦袋瓜子里沒別的就是一个“偸”,漸漸的我們的眼界寛了,閱历广了,胆子更大了;由“偷”防空帘改为“偸”紗,由“偷”单批紗改“偷”合股紗,小“偸”不解气,就大“偸”;一麻袋一麻袋的合股紗往外扛,紗到了小販手里,錢到了我們手中,不光我們家里的人吃得飽了,还帮助了受苦受难的哥儿們。有个叫陈瑞的弟兄跟我一塊干活,他大哥得病死了,买不起棺材,当时人們都穷得叮当乱响,往那儿借錢呀!我知道了这事,立刻給他送去五百塊錢,他拿这笔錢把丧事办了。
我們干得太露形了,把鬼子也眞“偸”急了,就加紧防备起来。夜里,警崗由三个小时一換,改为一个小时一換;巡罗的人增多了,日本鬼子、他的爪牙王副官、陈巡长也都不断出来巡查。風声紧得很。但是为了吃飯,我們还得冒险,还得“偷”。
一天晚上,我們兩人又进厂了。剛走上半截楼梯,就听背后有人踩着地面沙沙响,我立刻把老胡一把拉在墙根隐蔽,不会儿这声音远了。我倆輕着脚步又往上走,剛走到楼梯頂,又从老远傳来“咔咔”的皮鞋声,不会儿,就从下面射来一道白光,我倆赶紧趴下,那道白光扭向窗戶又轉向护厂的围墙。皮鞋声和白光往前移动,漸漸的听不眞鞋声了。我叫老胡放哨,我先进去。窗戶打开剛迈进一条腿,下面突然傳来一个很低的声音:“誰呀?誰呀?”我一听語音不是別人,正是伪警苗三,这人吃过我們的甜头:我放心了,低声回答:“是我呀!苗三。”
“哦!宝树,現在这么紧,你怎么还……?”他的話还沒說完,我赶紧說:“你快走吧,苗三!”他走开了,我这才和老胡鑽进大場,里面漆黑,点着带来的洋腊,用破帽头遮着火光,兩人爬着往前走。从窗外不时射进来一道一道的白光,当我背着裝滿紗的麻袋,从楼涕頂往下走时,这顆心哪,象有秤鉈墜着似的难受。这一夜,关口总算闖过去了。
可是灾禍終于临头了。
一天,天还沒亮,我剛睡醒,忽然从外面闖进来几个伪警,不容分說,把我从被窩里拉出来。我一想:准是犯案了!他們連拉带架地把我弄到厂門口一間小屋里。王副官气汹汹地向我說:“好小子!胆子倒不小,你把偸的紗卖哪儿啦?”我說:”你問的是嘛?我不知道!”
“好!你还鉄嘴鋼牙呢!”他那副鬼臉显得更凶恶,馬上叫他手下的弟兄打我,几个伪警拥上来,照着我的臉狠打,打得我的耳朵嗡嗡响,眼前冒金星,我心里說:“好歹毒的家伙們,打吧,大爷豁出这条命跟你們拚啦!”几个伪警打人累得出了汗,便脫下棉袄接着打。这时,王副官又走来問我:“你跟誰合伙偸的?快說!”我的嘴肿得张不开了,只好搐搖头回答他:“不知道!”他一怒立刻吿訴一个伪警:“去,把收买小貨的楊老头带来!”我一听才明白了,完了!一定是这个糟老头坏的事,每次卖給他紗,他总說:“兄弟,放心吧!刀子擱在胸口上我也不說出你来。”可是事情到底叫他敗露了。不大会儿,楊老头被带来了。王副官問我:“認識他嗎?”我搖搖头,头还沒搖定,“啪!啪!”又是一頓大嘴巴子,楊老头哭丧着臉向残哀求:“兄弟,你就招了吧!要不咱們都完了!”我慢慢睜开眼皮一看,不光是楊老头站在面前,他身旁还摆着一堆合股紗,这回是有人証又有物証。伪警們拉着我到厂里河沿花窖一間小屋門前。日本人、伪警察們都围着我,又是一陣毒打;日本人打累了,伪警察打,打得我兩只眼晃晃忽忽地光看見人影,認不出都是誰来。
日本厂长左藤看了看我,兩眼瞪得象包子一样大,呲着牙对王副官說:“你們統統的打他三天三夜!”他这一放屁不要紧,日本人和伪警察更是凶上加凶,把我打得死去活来。
晚上,我迷迷忽忽地,不知道多咱老胡也被他們逮来啦。他們把我們倆用一根縄子吊在厂长室前面的一棵棗树上,脚后跟悬在地上,要是累了,想动弹一点都不行。深夜,凉風还很颼臉,臉上和身上的伤口,被寒風吹得杀疼。忽然从远处走来兩三个人影。我渾身一陣顫抖,怕又是来人打我們。等他們走近一看,原来是和我們一塊干活的弟兄們。他們有的拿来棉袄給我們披上,有的喂我們水和吃的,我瞅着他們的臉,心里也暖和多啦!伤口也不那么杀疼啦。就这样子,白天被伪警們架走、毒打;晚上,弟兄們就来照顧我們。
三天三夜熬过去了。
我和我的老婆都被开除出厂了。老婆的兩只眼哭得象桃儿一样,和我一塊儿走出工厂。这天黄昏,鬼子和伪警把我的全家老小都从工房里赶出来。全家人和破破爛爛的东西都堆在楊庄子渡口,天色昏暗,眼前一片黑幽幽南海河水,眞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儿是我們的容身之处啊,媽媽哭哭啼啼地說:“宝树!咱們算完嘍,要家沒家,要事由儿沒事由儿,干脆都投河吧!”媽媽的話,多么叫人扎心啊。可是我說:“媽!咱們不能死!一定要熬着,咱們熬得出来!說完,我就在堤道上,用炕席、破棉被搭了一个窩鋪,一家子先在那里藏身。到后来,我才知道卖紗的錢,被一个伪警长一古腦儿从媽媽手中詐走了。
我們一家子蹲在那个窄小阴暗的窩鋪里,談論着将来怎么走好运,不受鞭打,不再过飢餓的生活。可是在那黑暗的日子里,我作梦也沒想到,象我这样一个日伪时期做牛做馬的工人,解放后当了工厂的主人,过着这样丰衣足食的生活。
三十七年以前,我出生在文安县的一个村庄里,那时全家四口人:奶奶、父亲、母亲和我,一家子就靠一亩半坟地生活。文安地势不好,差不多年年閙水灾,一閙灾就沒得吃。为了活着,父亲扛过河壩,当过“华工”。媽媽給闊人家当过老媽子。九岁那年,家里又添了一口人——一个少爷沒娘的小閨女,媽媽可憐她流离失所,宁肯自己少吃一口,把她收养了,当作童养媳。
連年水灾,在家乡越过越沒活路,听人說天津工厂多,穷人家无論大人小孩都可以混口吃的。父亲和媽媽信以为眞,就把地卖了,带着一家老小来到天津。到了天津,父亲还到河壩上扛活,又托人介紹,把我和那小閨女送到宝成紗厂(現在的棉紡三厂)当学徒。那时当学徒,整天挨打受气,还不掙錢,父亲又只能养活自己。实指望上了工吃碗飽飯,沒料到生活更苦了。日子不多,奶奶就活活的餓死了,父亲跟着外招工的走了。剩下媽媽守着一帮孩子(那时我又有了兩个弟弟),整天地哭奶奶、哭日子。有一天,媽媽忽然沒了,我到处去找,閙半天她老人家在乱葬崗上哭我死去的奶奶哩。我过去拉着母亲的衣服說:“媽,咱走吧!儿子学徒养活不了你,討着要着也养活你!”第二天,我就不到宝成上工了,和一群小叫化子走遍了天津市去要飯。
可也不能总要飯呀,十二岁那年,我又到北洋紗厂去学徒。好容易学会了接头,又受当头的剝削。比如,我看十九塊板(每塊板有六个錠子),可是拿十四塊板的工錢,那五塊板的錢被搖車的裝到自己腰包里去啦!那个年月,只得吃哑巴亏,要是把把实惹翻了,更得吃苦头。尽管忍气吞声,也断不了受气。有时,接头馒头那个搖車的女把头就端着大碗凉水,照着我的腦袋澆,我剛要抬手擦,她又是一毛棍把我的手打下去。咱穷也不能总受这个呀!一賭气給他娘的撂了台。
我16岁那年,正是日本統治时期,我和一帮要飯的孩子到日本倉庫里挑砖、打滓灰活。天下的老鴰一般黑,在这里除同样受工头的剝削,还挨日本人的揍,有一次,有三个穷哥們,实在餓不过了,偸了鬼子几塊餅干吃,日本人为了追查这三个人,把我們打得死去活来。可大伙鉄了心,認可挨揍,也不叫工患难的穷哥們遭难。晚上,我遍体鱗伤,連爬带走地回到家,媽媽見了,忍不住痛哭起来。
为了全家生活,轉年媽媽也到裕大(現在棉紡三厂)倒綫,我又到中山鋼厂(現在天津鋼厂)作了拔絲工。虽然全家三口人上工,还总是飢一頓飽一頓,有时就光吃拾来的爛菜帮子。一連好几年,我就是这样整天当“苦力”,整天吃不飽飯。
二十一岁我上裕大紗厂鍋爐房抬煤去。每月才掙五十五斤杂粮,这些杂粮除了山芋干、杂合面,就是四分之一的老玉米面。媽媽由于餓伤再加上累,得了喘病,被厂方开除了。家里的生活全靠我和我那老婆(我們在灶炕里拜了个天地,就結婚了)維持。說起我那老婆来,眞是个可憐的好人儿。她从九岁开始,就在宝成紗厂上工,小小的年紀,天天站着干十二个鐘头的活儿,骨头嫩,累成了罗圈腿,連走路都困难,每天媽媽和弟弟架着她去上班。到了車間还得挨打受气。就这样,她总是把杂合面、老玉米面留給媽媽弟弟吃,自己只吃山芋干。我心疼她,就省下杂合面餑餑給她吃。那时候,我一天抬十二小时的煤,一筐煤二百八十斤,兩个人一天抬三百多筐,你想想,得付出多大的劳动力啊!为了叫家里的人們吃得飽些,我干完十二个小时的累活,回到家,抄起扁担又到中山鋼厂抬煤、挑砖去。黑間白日地連軸轉,干着牛馬不如的累活,右肩起了一个大包,又紅又肿,扁担一压,膿包里就流血流膿。
就这样,我沒歇过一天工,因为人一歇工,牙也得歇工。有一次,因为累,肚里又沒食,眼前一冒金星,就暈倒了。
常言道:“人急造反,狗急跳墙”,当牛当馬还閑着半挂腸子,还眼睜的瞅着全家人忍飢挨餓,我可就豁出去,我想:“要活下去,在这个年月傻干可不行,一定要‘偸’,对,‘偸’!狠狠地‘偸’他們!为什么他們能活我不能活?”于是就找和我一塊抬煤的胡廷琴去商量。那天,他們全家老小正捧着草籽(是一种野菜,用这种东西磨成的面粉沒粘性,發散,所以用手捧着吃)餑餑吃,看看炕上連个枕头也沒有,我可就說了:“老胡啊!咱倆找点(外快)吧!老这样,忍到多咱是头呀!”沒想到老胡也憋着劲要“偸”哩,沒費口舌,我們倆就成同伙了。
这天黑夜,我二人爬上大場的太平鉄梯,奔天窗撕下防空帘里子(防空帘是双層的,里層是紅色,外層是黑色),繃在棉袄上肩里,就越墙走了。过了兩天,我們留神一看,不知什么时候,防空帘又添上新的里子了。任何动靜也沒有,我們暗暗發笑,心說鬼子眞孝順,又把肥肉送到咱爷們嘴头上来啦!胆子大起来,我們索性拿起整塊的来。
又是一天深夜,我倆把摘下来的防空帘捆了兩綑,用紗錠带子纏着,順着河沿大墻走。一慌张,“噗喳”一声,連人带布滾到河里去,水齐着脖子,河面还有一層薄冰,我二人不上不下的給卡在那儿了,一个劲打扑通,好不难受。好容易我踩着老胡的肩膀爬上来,老胡把防空帘投給我,我又把紗錠带子遞到老胡手中,把他从河里系上来。我們手忙脚乱地把这些事情剛剛办完,远远的来了巡邏的,我倆急忙跳到大墙里,用爐灰渣埋起防空帘,就溜回家去了。轉天下班回家,我正躺在炕上睡覚,听見工房弄当里紛紛傳說:“今天到厂里拾煤核儿的老婆儿和小孩儿們好运气,在煤灰渣里撿了一大捆布,一人鬧了一塊!”我想:这也很好,老婆儿和小孩儿們的身上补釘罗补釘,淨露着肉,也应該閙件新褂子穿穿了。
說句迷信話,那时候,我二人眞有点“賊星照命”,成天价滿腦袋瓜子里沒別的就是一个“偸”,漸漸的我們的眼界寛了,閱历广了,胆子更大了;由“偷”防空帘改为“偸”紗,由“偷”单批紗改“偷”合股紗,小“偸”不解气,就大“偸”;一麻袋一麻袋的合股紗往外扛,紗到了小販手里,錢到了我們手中,不光我們家里的人吃得飽了,还帮助了受苦受难的哥儿們。有个叫陈瑞的弟兄跟我一塊干活,他大哥得病死了,买不起棺材,当时人們都穷得叮当乱响,往那儿借錢呀!我知道了这事,立刻給他送去五百塊錢,他拿这笔錢把丧事办了。
我們干得太露形了,把鬼子也眞“偸”急了,就加紧防备起来。夜里,警崗由三个小时一換,改为一个小时一換;巡罗的人增多了,日本鬼子、他的爪牙王副官、陈巡长也都不断出来巡查。風声紧得很。但是为了吃飯,我們还得冒险,还得“偷”。
一天晚上,我們兩人又进厂了。剛走上半截楼梯,就听背后有人踩着地面沙沙响,我立刻把老胡一把拉在墙根隐蔽,不会儿这声音远了。我倆輕着脚步又往上走,剛走到楼梯頂,又从老远傳来“咔咔”的皮鞋声,不会儿,就从下面射来一道白光,我倆赶紧趴下,那道白光扭向窗戶又轉向护厂的围墙。皮鞋声和白光往前移动,漸漸的听不眞鞋声了。我叫老胡放哨,我先进去。窗戶打开剛迈进一条腿,下面突然傳来一个很低的声音:“誰呀?誰呀?”我一听語音不是別人,正是伪警苗三,这人吃过我們的甜头:我放心了,低声回答:“是我呀!苗三。”
“哦!宝树,現在这么紧,你怎么还……?”他的話还沒說完,我赶紧說:“你快走吧,苗三!”他走开了,我这才和老胡鑽进大場,里面漆黑,点着带来的洋腊,用破帽头遮着火光,兩人爬着往前走。从窗外不时射进来一道一道的白光,当我背着裝滿紗的麻袋,从楼涕頂往下走时,这顆心哪,象有秤鉈墜着似的难受。这一夜,关口总算闖过去了。
可是灾禍終于临头了。
一天,天还沒亮,我剛睡醒,忽然从外面闖进来几个伪警,不容分說,把我从被窩里拉出来。我一想:准是犯案了!他們連拉带架地把我弄到厂門口一間小屋里。王副官气汹汹地向我說:“好小子!胆子倒不小,你把偸的紗卖哪儿啦?”我說:”你問的是嘛?我不知道!”
“好!你还鉄嘴鋼牙呢!”他那副鬼臉显得更凶恶,馬上叫他手下的弟兄打我,几个伪警拥上来,照着我的臉狠打,打得我的耳朵嗡嗡响,眼前冒金星,我心里說:“好歹毒的家伙們,打吧,大爷豁出这条命跟你們拚啦!”几个伪警打人累得出了汗,便脫下棉袄接着打。这时,王副官又走来問我:“你跟誰合伙偸的?快說!”我的嘴肿得张不开了,只好搐搖头回答他:“不知道!”他一怒立刻吿訴一个伪警:“去,把收买小貨的楊老头带来!”我一听才明白了,完了!一定是这个糟老头坏的事,每次卖給他紗,他总說:“兄弟,放心吧!刀子擱在胸口上我也不說出你来。”可是事情到底叫他敗露了。不大会儿,楊老头被带来了。王副官問我:“認識他嗎?”我搖搖头,头还沒搖定,“啪!啪!”又是一頓大嘴巴子,楊老头哭丧着臉向残哀求:“兄弟,你就招了吧!要不咱們都完了!”我慢慢睜开眼皮一看,不光是楊老头站在面前,他身旁还摆着一堆合股紗,这回是有人証又有物証。伪警們拉着我到厂里河沿花窖一間小屋門前。日本人、伪警察們都围着我,又是一陣毒打;日本人打累了,伪警察打,打得我兩只眼晃晃忽忽地光看見人影,認不出都是誰来。
日本厂长左藤看了看我,兩眼瞪得象包子一样大,呲着牙对王副官說:“你們統統的打他三天三夜!”他这一放屁不要紧,日本人和伪警察更是凶上加凶,把我打得死去活来。
晚上,我迷迷忽忽地,不知道多咱老胡也被他們逮来啦。他們把我們倆用一根縄子吊在厂长室前面的一棵棗树上,脚后跟悬在地上,要是累了,想动弹一点都不行。深夜,凉風还很颼臉,臉上和身上的伤口,被寒風吹得杀疼。忽然从远处走来兩三个人影。我渾身一陣顫抖,怕又是来人打我們。等他們走近一看,原来是和我們一塊干活的弟兄們。他們有的拿来棉袄給我們披上,有的喂我們水和吃的,我瞅着他們的臉,心里也暖和多啦!伤口也不那么杀疼啦。就这样子,白天被伪警們架走、毒打;晚上,弟兄們就来照顧我們。
三天三夜熬过去了。
我和我的老婆都被开除出厂了。老婆的兩只眼哭得象桃儿一样,和我一塊儿走出工厂。这天黄昏,鬼子和伪警把我的全家老小都从工房里赶出来。全家人和破破爛爛的东西都堆在楊庄子渡口,天色昏暗,眼前一片黑幽幽南海河水,眞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儿是我們的容身之处啊,媽媽哭哭啼啼地說:“宝树!咱們算完嘍,要家沒家,要事由儿沒事由儿,干脆都投河吧!”媽媽的話,多么叫人扎心啊。可是我說:“媽!咱們不能死!一定要熬着,咱們熬得出来!說完,我就在堤道上,用炕席、破棉被搭了一个窩鋪,一家子先在那里藏身。到后来,我才知道卖紗的錢,被一个伪警长一古腦儿从媽媽手中詐走了。
我們一家子蹲在那个窄小阴暗的窩鋪里,談論着将来怎么走好运,不受鞭打,不再过飢餓的生活。可是在那黑暗的日子里,我作梦也沒想到,象我这样一个日伪时期做牛做馬的工人,解放后当了工厂的主人,过着这样丰衣足食的生活。
相关地名
天津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