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回忆片断
| 内容出处: |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 图书 |
| 唯一号: | 020020020230024231 |
| 颗粒名称: | “一二·九”运动回忆片断 |
| 分类号: | K264.5 |
| 页数: | 10 |
| 页码: | 71-80 |
| 摘要: | 本文章回忆了天津学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经历,包括参与“一二·九”运动、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南下宣传和“民先”组织的成立等。文章还描述了天津学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受到的打压和挫折,以及他们坚持斗争的信念和勇气。 |
| 关键词: | 天津市 一二·九运动 回忆片断 |
内容
回忆天津“一二·九”学生运动
朱光
一九三五年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运动时,我是天津法商学院的学生。当时,这个学校的政治势力比较复杂,有国民党、国家主义派(青年党)、第三党(农工民主党)各派势力,以及在共产党影响下的抗日救亡派。在《何梅协定》签字以后,反动党派日趋消沉,学生群众的抗日情绪日趋高涨,共产党的影响也就日益扩大。学校中的抗日救亡派是以教授杨秀峰、温健公、闻永之等和学生共产党员郝金贵、朱纪章(朱光)等为核心,以左倾学生为主体而形成的,在学校建立了经济学会、政治学会、时事座谈会等组织,经常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并且实际上已经能够控制学生自治会。
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天津各校学生经过串联,也于十二月十八日走上街头。当时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大城市的党组织遭受很大损失,直到这时候,我还没有和市委取得联系。所有这次游行的部署和口号的拟定,我们都是和杨秀峰、温健公二教授商量决定的,但我们之间并没有党的关系。在这次游行示威的活动之后,我才和市委张先生(李铁夫同志)接上关系,并指示我今后直接受市委领导,不参加学校党组,专门负责天津学联的工作。
“一二·一八”大游行遇到的阻力不太大,军警没有使用大刀、水龙来对付学生,不象北平那样发生激烈冲突,因而没有损伤一兵一卒,这就为后来学生运动的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大游行以后不久,在十二月二十八日,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当时参与学联活动的积极分子,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有:南开大学的程人士(程宏毅)、王绶昌、李涛、沙兆豫,北洋工学院的有徐瑞恩(徐达本)、孙景芳、刘讷,法商学院的庄金林、阮务德、刘立栻、傅朋竹、王民生、郝金贵,扶轮中学的袁家珂,汇文中学的姚大衡,觉民中学的朱缙章,女师附中的王玉玲(安琳)、朱淑宜(朱峥),商职学校的刘增奎、刘岫珊(田冀)、刘济光(刘瑞方)等。
接着,又成立了平津学生联合会。北平学联与我接头的人有:北京大学的于毅夫、燕京大学的王汝梅、清华大学的黄诚、中国大学的董某等。其后不久,天津各界救国会也成立了,我代表学联参加,工人救国会和农民救国会暂时尚未公开,一切事情都由我代转。后来,又在北平成立了华北各界救国会,天津有我和刘清扬参加。大约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前后,全国学生联合会在无锡成立,天津的代表是庄金林等。接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也宣告成立。
一九三六年一月,平津学生联合会发起组织南下宣传团,以北平学生为主体,天津参加的只有二、三十人,主要是北洋工学院的同学,法商学院只有庄金林和我两个人参加。
根据事先的约定,我们从天津出发,到达高碑店后与北平同学汇合,然后分作两路南下。其中一路不数日在大兴镇就被军警包围,强令返回北平。我们这一路,在永清、固安、安次、新城、雄县一带的村庄里巡回宣传;为了躲避军警的追捕,很少进入城镇,有时我们还和军警捉迷藏,比如白天向前行进了三十里,夜间又后退或转进六十里。这样在农村里回旋了二十多天,到达了保定城东南距城十余里的板桥镇。我们不想再前进了,就突然闯进了河北省府所在地保定市,在市内举行了游行示威及街头宣传活动。
河北省教育厅知道我们进入保定后,有点张皇失措,出面把我们安置在一所中学校里休息,并给我们准备了馒头和燉肉。我们闹不清河北省当局的意图,因为怕军警前来捕人,所以那一夜大家都没有敢睡觉。我们背靠背地坐着,就彼此议论开了:我们这次走出城市到农村宣传,虽然起到了“唤起民众”的作用,但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城里去读书,农民也仍是种地、交租、受压迫,知识分子如何能与农民结合起来呢?同学们意识到:必须采取其他结合的办法才行!这就产生了在农村举办夜校、识字班的想法,决定建立个“义教”促进会的组织。另外,大家也希望把这次南下宣传团从组织上巩固下来,决定改个名称,叫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民先”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这个组织后来逐渐发展扩大,遍及全国。
一九三六年的五月,天津学生又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当时的形势是,日本不断增兵华北,战争一触即发;在海河出现大批浮尸,传闻是日本人修筑秘密军事设施后杀害的中国工人;在北平因被捕学生郭清死在狱中,爆发了一次象征性的“抬棺”游行;学校当局以会考对学生施加压力。……基于以上这些情况,天津学联决定在“五·卅”惨案纪念日时,举行一次反日大示威。不料在准备过程中,被当局知道了,听说正在布置警车、水龙等来对付游行。学联得此信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提前在五月二十八日举行游行。
学联对这次游行作了周密的准备工作。预定分南北两路集合,南边的各校在南开中学集合,走西马路、北马路、大胡同到金钢桥;北边的各校在河北体育场集合,经大经路到金钢桥,然后两路大军汇合,走东马路、南马路,最后在南开中学解散。这次游行准备了大批传单,有给工人的,有给市民的,有给军警的,还有告全国同胞书和通电等。游行时拟定的口号有:“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抵制日货,制止走私”,“武装保卫华北”,“拥护二十九军继续抗日”,“停止一切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为了防备军警的袭击或捣乱,准备了两个总指挥,一个是公开的,一个是秘密的;秘密的总指挥由我担任。此外还组织了纠察队、交通队等,负责保卫、联络等工作。
游行的提前行动是成功的。因事出突然,当局准备不及,只在法商学院的门前一带布置了军警,阻止同学上街。于是我们便使用了一个声东击西的策略,一面组织一部分同学与军警纠缠,假装冲向门外;一面在学校南墙推开一个豁口,大部分同学进入仅有一墙之隔的天津师范学校,并与该校同学一起来到邻近的商职学校。三校同学汇合后,便拉出了队伍,当军警们发觉时,大队人马已经过了新开河桥。沿途又陆续集合各校同学,汇成浩大队伍,直奔金钢桥。这时,金钢桥上已有重兵把守,阻止队伍过桥。我们便把专为军警印制的传单散发给他们,并呼喊口号:“发扬二十九军抗日传统!”“拥护天津军警继续抗日!”
对下层军官及士兵进行分化瓦解工作,有些士兵听了表情很激动。这时南路的学生也赶来了,我们便四个人一排,挽起手臂冲过了金钢桥,与南路同学汇合一起,浩浩荡荡地奔向东马路。军警这时忙把刺刀收起,沿着东马路跑步去东南角一带警戒,以防止学生们冲入日租界,闹出乱子来。
我们在冲过了金钢桥后,就在官银号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这时,农民救国会和工人救国会都派代表来参加大会,这两个组织当时还处于半公开的状况下,所以没有打出旗帜来。会场上,宣讲人员分头演说,散发传单,书写标语,气氛极其热烈。参加这次大会的人数估计总有四、五万人之多。
这一年暑假以后,我就离开了法商学院到北平教书去了。这时,日本人强迫天津当局逼走了法商学院的院长杨亦周,再后就强行解散了这个在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学校。
记“一二·九”运动赴南京请愿的经过
王刚
出发之前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举行抗日爱国大游行。消息传到南开中学,同学们纷纷议论,课堂内外立即沸腾起来。大家表示要走出课堂,为挽救民族的灾难采取行动。学生自治会十八日上午在瑞廷礼堂召开全校学生大会,由高三同学吴祖贻主持,讨论救国行动,由我和同学申宪文在会场临时商议后,经申宪文提议到南京请愿去,立刻有孙会芳(孙方)同学起立发言附议,到会同学一致鼓掌表示赞成,经全体举手表决通过,高中三个年级十六个班的同学一律去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大家决议请愿的内容为:①反对华北特殊化,要求取消冀东伪组织和冀察政务委员会;②要求中央政府出兵保卫华北,收复东北;③要求改革现行教育制度,实施非常时期救国教育。并决议立即由全体高中同学举行无记名投票,选举“南开中学非常时期委员会”领导请愿行动。结果选出:吴祖贻、郑怀之、申宪文、王树勋(王刚)、贾维茵、吴锡武(吴宪)、滕国定(滕晨)、吴铸、高云屏、张学诗、刘嘉谟、周艮良、李金榜、李如鹏、万树人、梁华錩(白文治)、何乃康、鄜炳耀、罗德洪、汪绍诚等二十一名委员,并互推吴祖贻、郑怀之、申宪文三人为正副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组织股,庶务股,交际股,交通股,宣传股。决定参加请愿的同学共三百七十人,按每班编三个小组,共编成四十八个小组。于当天晚九时分乘租来的八辆载重汽车,开进天津西火车站,决定当夜搭乘三〇五次平浦快车南下。
西站被阻
天津当局获悉南中同学进西站拟登车南下请愿的消息后,极力阻止这一爱国行动,由铁路局下令三〇五次平浦快车停在天津总站,不开进西站。并派来津浦铁路局驻津办事处处长王锡符、津浦警务总段长王维俊、天津市公安局秘书张书成到车站,劝阻同学们离站回校,声言绝对不许同学们上车。非常时期委员会三个正副主任委员和交际股负责人贾维茵同学,代表全体请愿同学在站长室和铁路、公安当局的代表等人进行了长达七小时的争辩和交涉。全体请愿同学都站在露天站台上,并组织了一批同学在站台下的铁轨上卧轨。口号是:“为了救国,不让我们上车,我们誓死不让火车通过。”大家冒着西北风,在零下十几度的寒夜,从晚十点一直坚持到后半夜五点。登车的交涉没有结果,所有火车都不开进车站。非常时期委员会见当局态度死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经全体同学一致决议,放弃登车,改为徒步南下。大家依次整队,怀着满腔悲愤,在黑暗中脚踏积雪,面迎寒风,一字长蛇,沿着铁路线向南方进发。我们的队伍刚离西站不远,三〇五次平浦快车从我们后面开来,傍着我们的行列辘辘闯过。我们徒步到杨柳青镇时,东方的天色已快亮了。
从杨柳青折回
南开中学当局对我们去南京请愿的爱国行动,采取釜底抽薪和分化瓦解的手段,以同情和关心的面目实行阻挠。当我们开大会决定请愿后,学校主任喻传鉴决定给学生家长或保证人发通知,报告学生的请愿举动,要求出面劝阻。同学们在西车站交涉登车时,有许多学生家长来到车站,劝其子弟回家,不让去南京请愿。很多同学不顾家长的阻拦,坚持请愿,也有不少同学在家长的逼迫之下,洒泪离队,被家长领回。十九日清晨,我们到达杨柳青镇时,学校派来了张信鸿、孟志孙、郑新亭、叶石甫、韩叔信等五名平日受同学们尊敬的老教师说服我们。他们表示钦佩同学们的爱国行动,但从同学们的安全着眼,无准备的长途步行去南京不是好办法,力劝大家回校,从长计议。并有南开校友申郁文也赶来,极力说服大家,并表示大家回校后,愿出力协助我们达到请愿目的。这时有的学生家长也从天津赶来,接其子弟回家。我们从出发时到现在,先后离队的同学已有九十多人,所余同学经过一夜不眠,远道跋涉,困乏疲劳,既冷又饿,考虑到此后二百多人南行,生活没有安排,在老师们的劝导下,非常时期委员会下午二时决定暂先让年幼的、身体较弱的、不宜长途徒步的同学约二百人回校。学校从天津租来载重汽车将这批同学接回。这时仍坚持徒步南下的尚有七十多人,人少力孤,在老师的一再敦促之下,最后在晚七时半亦返回了学校。
秘密筹划到达南京
请愿同学返校后,非常时期委员会在瑞廷礼堂后台化装室继续筹备去南京请愿的行动。决心坚持去南京的同学都分头自筹旅费。为了防止校方和天津市当局的阻挠,决定分成小批秘密出发。一部分同学去塘沽分批乘轮船从海路经上海转南京,另一部分同学由陆路乘火车去南京。我是交通股负责人,先由我去塘沽探路,并带领第一小批同学出发。我们到塘沽后,遇大沽口外水浅冰封,海船不能靠近,没有船只。当夜借宿在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码头的工人值勤室,次日找到一只向海轮运食物的出海驳船,将我们带到大沽口外十几里的渤海面,登上了排水量三千吨的“顺天”号海轮。船费每人五元,供伙食,睡在船底货仓的铁板上。经过四天抵达上海外滩码头,在上海住旅馆,等待后面乘“新铭”轮和“通州”轮的大批同学汇齐,共同乘沪宁火车去南京。
请愿经过
从海路和陆路到南京的同学共有一百零九人,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南京东方旅馆汇齐,大家拥挤着睡在地板上。旅馆里由于我们的到来突然增添了宪兵站岗巡逻,还有便衣密探化装监视我们。当夜我们全体开会商议请愿行动。适逢次日是一九三六年元旦,这一天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重要人物照例去东城外紫金山中山陵参谒,因此大家一致决定,明天清晨齐赴中山陵哭陵。会议开到后半夜,大家入睡很晚,加以旅途的劳顿,次晨醒来已八点钟,乃急忙集合奔赴中山陵。半路上迎面遇见许多汽车,乘载“党国大员”风驰电掣地从中山陵驶进城内,这是他们已谒陵完毕,我们赶到中山陵,扑了一个空,大家只好瞻仰孙中山先生塑像和陵寝,败兴而归。
我们在南京先后进行了两次请愿。第一次是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要见院长蒋介石,由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代表接见了请愿代表吴祖贻、郑怀之、申宪文和贾维茵等同学。第二次是到教育部,由部长王世杰接见了全体请愿同学。同学们交了请愿书,当场提出请政府出兵收复失地、保卫华北和我们反对华北特殊化以及要求实行非常时期救国教育的意见。翁文灏和王世杰对请愿同学都是摆出一副官僚架子,装腔作势地用谎话诓骗请愿同学。他们的答复都是说政府对日本的侵略有既定的对策,绝不放弃华北,而且还要收复东北,要同学们回去安心读书,准备报效国家。我们来自华北的学生亲眼见到日寇步步进逼,政府则一再退让,在失地辱国的事实面前听了毫无诚意的回答都很气愤。但没有一个同学当场指出政府的骗术,提出质问,而是默默地退出会场,表现得软弱无力。
被迫北返
南开中学当局派教师韩叔信、唐炳亮,从天津跟踪赶来,劝阻我们的请愿活动,他们还串通在南京的南开校友,如南京金城银行经理王恩东等人出面在同学中活动,说什么同学们请愿,已受到政府两次接见,请愿的目的已达到,要适可而止,离宁北归,如果再坚持下去,出了事不好收拾。同学们开会展开争论,只有滕国定、王树勋等少数同学发言主张采取进一步行动,到国民政府去,不达目的不止;多数同学在教师和校友的劝说下表示可以不再请愿,经过表决通过回津。次日到浦口登上铁路局专备的挂有两节三等车厢的火车,将我们直送到天津。我们临离浦口时有罗德洪、王鹏远、吴纳孙、梁华錩、鄜炳耀等同学没有上火车,他们徒步去芜湖一带农村旅行宣传,半月后才回到天津。
南开中学高中同学的这次请愿行动虽然表达了同学们高度的爱国精神,但由于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请愿的指导思想不统一,政治上表现软弱,组织上较松散,很容易地被当局所分化,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就被迫北返了。经过请愿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这就教育了大家,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卖国降日政策开始有了认识,打破了过去对它的幻想,并促使大家深思,寻求有效的救亡之路。这次请愿使同学们受到了一次锻炼,为天津市下一步的学生救亡活动,以及后来八年浴血抗战准备了干部。
〔附说明〕南开中学到达南京请愿的一百零九名同学中,当时有高云屏(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吴锡武(后名吴宪,现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同学是共产党员。由于当时党的方针是在当地开展救亡工作,对南京政府不寄希望,主张不发动去南京请愿。他们当时虽然被选为非常时期委员会的委员,但对待学生群众这一自发请愿,只是随队参加,而没有积极领导。当时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尚未传达到天津的党组织,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倾向还没有得到纠正。
(一九八〇年六月)
朱光
一九三五年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运动时,我是天津法商学院的学生。当时,这个学校的政治势力比较复杂,有国民党、国家主义派(青年党)、第三党(农工民主党)各派势力,以及在共产党影响下的抗日救亡派。在《何梅协定》签字以后,反动党派日趋消沉,学生群众的抗日情绪日趋高涨,共产党的影响也就日益扩大。学校中的抗日救亡派是以教授杨秀峰、温健公、闻永之等和学生共产党员郝金贵、朱纪章(朱光)等为核心,以左倾学生为主体而形成的,在学校建立了经济学会、政治学会、时事座谈会等组织,经常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并且实际上已经能够控制学生自治会。
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天津各校学生经过串联,也于十二月十八日走上街头。当时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大城市的党组织遭受很大损失,直到这时候,我还没有和市委取得联系。所有这次游行的部署和口号的拟定,我们都是和杨秀峰、温健公二教授商量决定的,但我们之间并没有党的关系。在这次游行示威的活动之后,我才和市委张先生(李铁夫同志)接上关系,并指示我今后直接受市委领导,不参加学校党组,专门负责天津学联的工作。
“一二·一八”大游行遇到的阻力不太大,军警没有使用大刀、水龙来对付学生,不象北平那样发生激烈冲突,因而没有损伤一兵一卒,这就为后来学生运动的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大游行以后不久,在十二月二十八日,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当时参与学联活动的积极分子,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有:南开大学的程人士(程宏毅)、王绶昌、李涛、沙兆豫,北洋工学院的有徐瑞恩(徐达本)、孙景芳、刘讷,法商学院的庄金林、阮务德、刘立栻、傅朋竹、王民生、郝金贵,扶轮中学的袁家珂,汇文中学的姚大衡,觉民中学的朱缙章,女师附中的王玉玲(安琳)、朱淑宜(朱峥),商职学校的刘增奎、刘岫珊(田冀)、刘济光(刘瑞方)等。
接着,又成立了平津学生联合会。北平学联与我接头的人有:北京大学的于毅夫、燕京大学的王汝梅、清华大学的黄诚、中国大学的董某等。其后不久,天津各界救国会也成立了,我代表学联参加,工人救国会和农民救国会暂时尚未公开,一切事情都由我代转。后来,又在北平成立了华北各界救国会,天津有我和刘清扬参加。大约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前后,全国学生联合会在无锡成立,天津的代表是庄金林等。接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也宣告成立。
一九三六年一月,平津学生联合会发起组织南下宣传团,以北平学生为主体,天津参加的只有二、三十人,主要是北洋工学院的同学,法商学院只有庄金林和我两个人参加。
根据事先的约定,我们从天津出发,到达高碑店后与北平同学汇合,然后分作两路南下。其中一路不数日在大兴镇就被军警包围,强令返回北平。我们这一路,在永清、固安、安次、新城、雄县一带的村庄里巡回宣传;为了躲避军警的追捕,很少进入城镇,有时我们还和军警捉迷藏,比如白天向前行进了三十里,夜间又后退或转进六十里。这样在农村里回旋了二十多天,到达了保定城东南距城十余里的板桥镇。我们不想再前进了,就突然闯进了河北省府所在地保定市,在市内举行了游行示威及街头宣传活动。
河北省教育厅知道我们进入保定后,有点张皇失措,出面把我们安置在一所中学校里休息,并给我们准备了馒头和燉肉。我们闹不清河北省当局的意图,因为怕军警前来捕人,所以那一夜大家都没有敢睡觉。我们背靠背地坐着,就彼此议论开了:我们这次走出城市到农村宣传,虽然起到了“唤起民众”的作用,但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城里去读书,农民也仍是种地、交租、受压迫,知识分子如何能与农民结合起来呢?同学们意识到:必须采取其他结合的办法才行!这就产生了在农村举办夜校、识字班的想法,决定建立个“义教”促进会的组织。另外,大家也希望把这次南下宣传团从组织上巩固下来,决定改个名称,叫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民先”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这个组织后来逐渐发展扩大,遍及全国。
一九三六年的五月,天津学生又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当时的形势是,日本不断增兵华北,战争一触即发;在海河出现大批浮尸,传闻是日本人修筑秘密军事设施后杀害的中国工人;在北平因被捕学生郭清死在狱中,爆发了一次象征性的“抬棺”游行;学校当局以会考对学生施加压力。……基于以上这些情况,天津学联决定在“五·卅”惨案纪念日时,举行一次反日大示威。不料在准备过程中,被当局知道了,听说正在布置警车、水龙等来对付游行。学联得此信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提前在五月二十八日举行游行。
学联对这次游行作了周密的准备工作。预定分南北两路集合,南边的各校在南开中学集合,走西马路、北马路、大胡同到金钢桥;北边的各校在河北体育场集合,经大经路到金钢桥,然后两路大军汇合,走东马路、南马路,最后在南开中学解散。这次游行准备了大批传单,有给工人的,有给市民的,有给军警的,还有告全国同胞书和通电等。游行时拟定的口号有:“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抵制日货,制止走私”,“武装保卫华北”,“拥护二十九军继续抗日”,“停止一切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为了防备军警的袭击或捣乱,准备了两个总指挥,一个是公开的,一个是秘密的;秘密的总指挥由我担任。此外还组织了纠察队、交通队等,负责保卫、联络等工作。
游行的提前行动是成功的。因事出突然,当局准备不及,只在法商学院的门前一带布置了军警,阻止同学上街。于是我们便使用了一个声东击西的策略,一面组织一部分同学与军警纠缠,假装冲向门外;一面在学校南墙推开一个豁口,大部分同学进入仅有一墙之隔的天津师范学校,并与该校同学一起来到邻近的商职学校。三校同学汇合后,便拉出了队伍,当军警们发觉时,大队人马已经过了新开河桥。沿途又陆续集合各校同学,汇成浩大队伍,直奔金钢桥。这时,金钢桥上已有重兵把守,阻止队伍过桥。我们便把专为军警印制的传单散发给他们,并呼喊口号:“发扬二十九军抗日传统!”“拥护天津军警继续抗日!”
对下层军官及士兵进行分化瓦解工作,有些士兵听了表情很激动。这时南路的学生也赶来了,我们便四个人一排,挽起手臂冲过了金钢桥,与南路同学汇合一起,浩浩荡荡地奔向东马路。军警这时忙把刺刀收起,沿着东马路跑步去东南角一带警戒,以防止学生们冲入日租界,闹出乱子来。
我们在冲过了金钢桥后,就在官银号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这时,农民救国会和工人救国会都派代表来参加大会,这两个组织当时还处于半公开的状况下,所以没有打出旗帜来。会场上,宣讲人员分头演说,散发传单,书写标语,气氛极其热烈。参加这次大会的人数估计总有四、五万人之多。
这一年暑假以后,我就离开了法商学院到北平教书去了。这时,日本人强迫天津当局逼走了法商学院的院长杨亦周,再后就强行解散了这个在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学校。
记“一二·九”运动赴南京请愿的经过
王刚
出发之前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举行抗日爱国大游行。消息传到南开中学,同学们纷纷议论,课堂内外立即沸腾起来。大家表示要走出课堂,为挽救民族的灾难采取行动。学生自治会十八日上午在瑞廷礼堂召开全校学生大会,由高三同学吴祖贻主持,讨论救国行动,由我和同学申宪文在会场临时商议后,经申宪文提议到南京请愿去,立刻有孙会芳(孙方)同学起立发言附议,到会同学一致鼓掌表示赞成,经全体举手表决通过,高中三个年级十六个班的同学一律去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大家决议请愿的内容为:①反对华北特殊化,要求取消冀东伪组织和冀察政务委员会;②要求中央政府出兵保卫华北,收复东北;③要求改革现行教育制度,实施非常时期救国教育。并决议立即由全体高中同学举行无记名投票,选举“南开中学非常时期委员会”领导请愿行动。结果选出:吴祖贻、郑怀之、申宪文、王树勋(王刚)、贾维茵、吴锡武(吴宪)、滕国定(滕晨)、吴铸、高云屏、张学诗、刘嘉谟、周艮良、李金榜、李如鹏、万树人、梁华錩(白文治)、何乃康、鄜炳耀、罗德洪、汪绍诚等二十一名委员,并互推吴祖贻、郑怀之、申宪文三人为正副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组织股,庶务股,交际股,交通股,宣传股。决定参加请愿的同学共三百七十人,按每班编三个小组,共编成四十八个小组。于当天晚九时分乘租来的八辆载重汽车,开进天津西火车站,决定当夜搭乘三〇五次平浦快车南下。
西站被阻
天津当局获悉南中同学进西站拟登车南下请愿的消息后,极力阻止这一爱国行动,由铁路局下令三〇五次平浦快车停在天津总站,不开进西站。并派来津浦铁路局驻津办事处处长王锡符、津浦警务总段长王维俊、天津市公安局秘书张书成到车站,劝阻同学们离站回校,声言绝对不许同学们上车。非常时期委员会三个正副主任委员和交际股负责人贾维茵同学,代表全体请愿同学在站长室和铁路、公安当局的代表等人进行了长达七小时的争辩和交涉。全体请愿同学都站在露天站台上,并组织了一批同学在站台下的铁轨上卧轨。口号是:“为了救国,不让我们上车,我们誓死不让火车通过。”大家冒着西北风,在零下十几度的寒夜,从晚十点一直坚持到后半夜五点。登车的交涉没有结果,所有火车都不开进车站。非常时期委员会见当局态度死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经全体同学一致决议,放弃登车,改为徒步南下。大家依次整队,怀着满腔悲愤,在黑暗中脚踏积雪,面迎寒风,一字长蛇,沿着铁路线向南方进发。我们的队伍刚离西站不远,三〇五次平浦快车从我们后面开来,傍着我们的行列辘辘闯过。我们徒步到杨柳青镇时,东方的天色已快亮了。
从杨柳青折回
南开中学当局对我们去南京请愿的爱国行动,采取釜底抽薪和分化瓦解的手段,以同情和关心的面目实行阻挠。当我们开大会决定请愿后,学校主任喻传鉴决定给学生家长或保证人发通知,报告学生的请愿举动,要求出面劝阻。同学们在西车站交涉登车时,有许多学生家长来到车站,劝其子弟回家,不让去南京请愿。很多同学不顾家长的阻拦,坚持请愿,也有不少同学在家长的逼迫之下,洒泪离队,被家长领回。十九日清晨,我们到达杨柳青镇时,学校派来了张信鸿、孟志孙、郑新亭、叶石甫、韩叔信等五名平日受同学们尊敬的老教师说服我们。他们表示钦佩同学们的爱国行动,但从同学们的安全着眼,无准备的长途步行去南京不是好办法,力劝大家回校,从长计议。并有南开校友申郁文也赶来,极力说服大家,并表示大家回校后,愿出力协助我们达到请愿目的。这时有的学生家长也从天津赶来,接其子弟回家。我们从出发时到现在,先后离队的同学已有九十多人,所余同学经过一夜不眠,远道跋涉,困乏疲劳,既冷又饿,考虑到此后二百多人南行,生活没有安排,在老师们的劝导下,非常时期委员会下午二时决定暂先让年幼的、身体较弱的、不宜长途徒步的同学约二百人回校。学校从天津租来载重汽车将这批同学接回。这时仍坚持徒步南下的尚有七十多人,人少力孤,在老师的一再敦促之下,最后在晚七时半亦返回了学校。
秘密筹划到达南京
请愿同学返校后,非常时期委员会在瑞廷礼堂后台化装室继续筹备去南京请愿的行动。决心坚持去南京的同学都分头自筹旅费。为了防止校方和天津市当局的阻挠,决定分成小批秘密出发。一部分同学去塘沽分批乘轮船从海路经上海转南京,另一部分同学由陆路乘火车去南京。我是交通股负责人,先由我去塘沽探路,并带领第一小批同学出发。我们到塘沽后,遇大沽口外水浅冰封,海船不能靠近,没有船只。当夜借宿在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码头的工人值勤室,次日找到一只向海轮运食物的出海驳船,将我们带到大沽口外十几里的渤海面,登上了排水量三千吨的“顺天”号海轮。船费每人五元,供伙食,睡在船底货仓的铁板上。经过四天抵达上海外滩码头,在上海住旅馆,等待后面乘“新铭”轮和“通州”轮的大批同学汇齐,共同乘沪宁火车去南京。
请愿经过
从海路和陆路到南京的同学共有一百零九人,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南京东方旅馆汇齐,大家拥挤着睡在地板上。旅馆里由于我们的到来突然增添了宪兵站岗巡逻,还有便衣密探化装监视我们。当夜我们全体开会商议请愿行动。适逢次日是一九三六年元旦,这一天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重要人物照例去东城外紫金山中山陵参谒,因此大家一致决定,明天清晨齐赴中山陵哭陵。会议开到后半夜,大家入睡很晚,加以旅途的劳顿,次晨醒来已八点钟,乃急忙集合奔赴中山陵。半路上迎面遇见许多汽车,乘载“党国大员”风驰电掣地从中山陵驶进城内,这是他们已谒陵完毕,我们赶到中山陵,扑了一个空,大家只好瞻仰孙中山先生塑像和陵寝,败兴而归。
我们在南京先后进行了两次请愿。第一次是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要见院长蒋介石,由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代表接见了请愿代表吴祖贻、郑怀之、申宪文和贾维茵等同学。第二次是到教育部,由部长王世杰接见了全体请愿同学。同学们交了请愿书,当场提出请政府出兵收复失地、保卫华北和我们反对华北特殊化以及要求实行非常时期救国教育的意见。翁文灏和王世杰对请愿同学都是摆出一副官僚架子,装腔作势地用谎话诓骗请愿同学。他们的答复都是说政府对日本的侵略有既定的对策,绝不放弃华北,而且还要收复东北,要同学们回去安心读书,准备报效国家。我们来自华北的学生亲眼见到日寇步步进逼,政府则一再退让,在失地辱国的事实面前听了毫无诚意的回答都很气愤。但没有一个同学当场指出政府的骗术,提出质问,而是默默地退出会场,表现得软弱无力。
被迫北返
南开中学当局派教师韩叔信、唐炳亮,从天津跟踪赶来,劝阻我们的请愿活动,他们还串通在南京的南开校友,如南京金城银行经理王恩东等人出面在同学中活动,说什么同学们请愿,已受到政府两次接见,请愿的目的已达到,要适可而止,离宁北归,如果再坚持下去,出了事不好收拾。同学们开会展开争论,只有滕国定、王树勋等少数同学发言主张采取进一步行动,到国民政府去,不达目的不止;多数同学在教师和校友的劝说下表示可以不再请愿,经过表决通过回津。次日到浦口登上铁路局专备的挂有两节三等车厢的火车,将我们直送到天津。我们临离浦口时有罗德洪、王鹏远、吴纳孙、梁华錩、鄜炳耀等同学没有上火车,他们徒步去芜湖一带农村旅行宣传,半月后才回到天津。
南开中学高中同学的这次请愿行动虽然表达了同学们高度的爱国精神,但由于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请愿的指导思想不统一,政治上表现软弱,组织上较松散,很容易地被当局所分化,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就被迫北返了。经过请愿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这就教育了大家,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卖国降日政策开始有了认识,打破了过去对它的幻想,并促使大家深思,寻求有效的救亡之路。这次请愿使同学们受到了一次锻炼,为天津市下一步的学生救亡活动,以及后来八年浴血抗战准备了干部。
〔附说明〕南开中学到达南京请愿的一百零九名同学中,当时有高云屏(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吴锡武(后名吴宪,现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同学是共产党员。由于当时党的方针是在当地开展救亡工作,对南京政府不寄希望,主张不发动去南京请愿。他们当时虽然被选为非常时期委员会的委员,但对待学生群众这一自发请愿,只是随队参加,而没有积极领导。当时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尚未传达到天津的党组织,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倾向还没有得到纠正。
(一九八〇年六月)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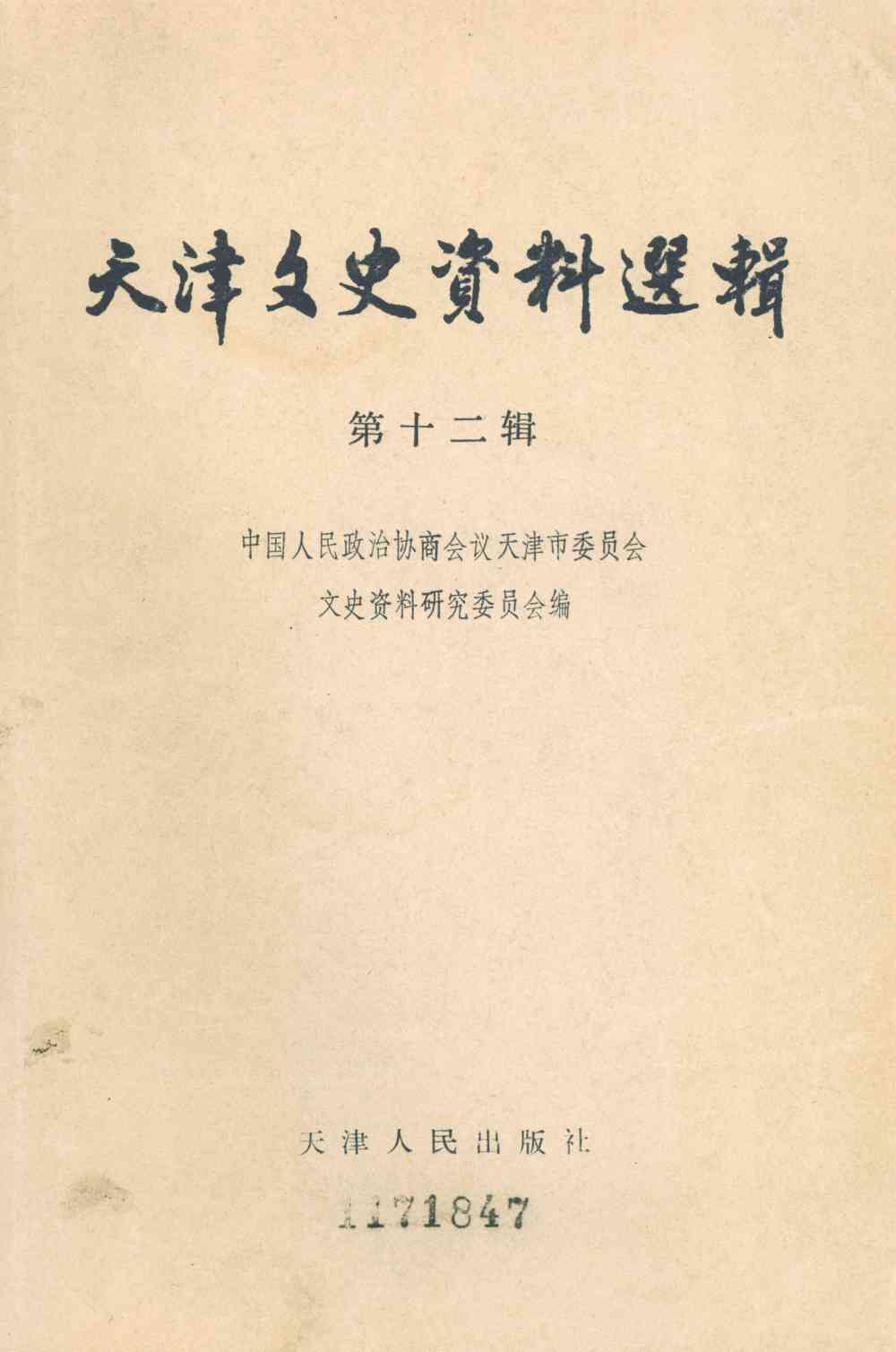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一二·九’运动在天津”、“参加天津学术抗日爱国运动的回忆”、“反动学生组织诚社始末”、“孙良诚从军始末及投敌经过”等十余篇文章。
阅读
相关地名
天津市
相关地名